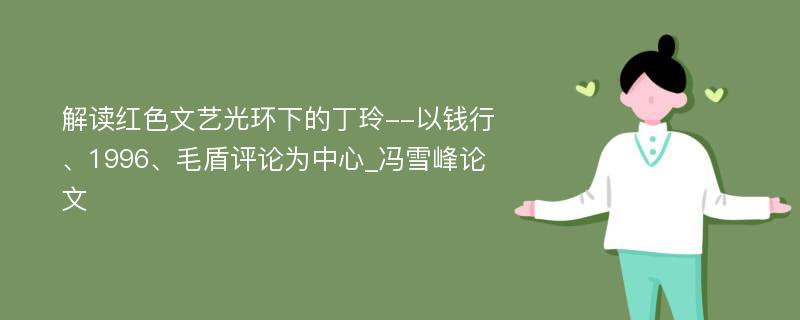
红色文艺光环下的丁玲解读——以钱杏邨、冯雪峰、茅盾的评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环论文,文艺论文,茅盾论文,红色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7年,丁玲以其处女作《梦珂》开始登上文坛,不久《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也陆续刊出,迅疾在文坛刮起了一阵旋风。正如当时一篇评论所指出的那样:“丁玲女士是一位新进的一鸣惊人的女作家。自从她的处女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在《小说月报》上接连发表之后,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①从此,围绕丁玲的评论大量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左翼文学批评界对丁玲始终给以了极大的关注,丁玲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左翼批评界注意的焦点,其蕴含的红色经典意义逐渐生成和清晰,这种情形在早期重要的几位左翼文学批评家阿英(钱杏邨)、冯雪峰和茅盾的评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对丁玲的评论既有合理的历史内核,初步展示了左翼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成绩、特点,但很多时候也带有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幼稚和偏颇,对丁玲颇多误读,留下了很深的“左”的痕迹。而这种批评模式在后来的文学实践中更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人们反思。 钱杏邨早年是“太阳社”的重要成员,曾经以《死去的阿Q时代》一文在批评界一鸣惊人。钱杏邨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深受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拉普”和“纳普”理论的影响,用所谓无产阶级文学教条理论来剪裁丰富的文学现象,在对许多作家的评论中都典型体现出“唯我独革”的心态,而《死去的阿Q时代》这篇文章也集中反映了钱杏邨激进而又偏颇的文学理念。他武断地把文化批判从思想领域引入到文学领域,以作家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来划分阵营,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看成革命文学的对立面,宣称:“不但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只有具着狂风暴雨的革命精神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忠实诚恳情绪在全身燃烧,对于政治有亲切的认识,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线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②然而这样一篇充斥许多错误观念的文章竟然被当时的“太阳社”吹捧为“实足以澄清一般的混乱的鲁迅论,是新时代的青年第一次给他的回音”③。可见钱杏邨的批评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影响。随后钱杏邨在对茅盾、叶绍钧、陈衡哲、凌叔华、苏雪林、白薇、庐隐等许多作家的评论中都沿袭了这样的批评模式,即把作家的阶级立场放置在首要的位置,要求作家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创作原则,他对丁玲的评论自然也无法跳出这样的模式。 丁玲在文坛刚刚产生影响的时候,就进入到钱杏邨的批评视野,丁玲作品的时代性和独特性引起了他的特殊兴趣。1929年,钱杏邨在《海风周报》上发表《〈在黑暗中〉——关于丁玲创作的考察》一文,这篇文章也是丁玲研究出现的最早一篇论文,着重对丁玲刚刚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进行了评论。在此基础上,钱杏邨又在稍后以“钱谦吾”的笔名发表《丁玲》一文,此外,钱杏邨还曾经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关于〈母亲〉》等文章中对于丁玲的小说《水》和《母亲》做过评论。在这些评论中,钱杏邨一方面展现出了他敏感的文学嗅觉,比较准确地指出了丁玲创作的独特价值;但另一方面,他某些地方流露的文学感悟能力又常常被他信奉的机械唯物论观念所窒息、扼杀,呈现出“扭曲现实”的脸谱主义,因而他对丁玲的评价很多时候是不客观的,对作家更多的是责难而不是理解,这种盛气凌人的批评自然难以经受历史的考验。 在钱杏邨看来,丁玲之所以迅速在文坛上崛起,取代了以前冰心、庐隐等女性作家的位置,很重要的一点是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中贡献出了一群性格独异的新女性。他说:“这几部创作,是一贯的表现了一个新的女性的姿态,也就是其他的女性作家的创作中所少有甚至于没有的姿态,一种具有非常浓重的‘世纪末’的病态气分的所谓‘近代女子’的姿态。”④对于丁玲出色的描写能力和把握人物精神世界的能力,钱杏邨也颇为欣赏,他说:“作者似长于性欲描写。那种热情的,冲动的,大胆的,性欲的,一切性爱描写的技巧,实在是女作家中所少有的。”⑤他进而把丁玲笔下女主人公的精神特点概括为:“她们的生活完全是包含在灵与肉,生与死,理智与感情,幸福与空虚,自由与束缚,以及其他一切的这样的现象的挣扎冲突之中,而终于为物质的诱惑所吸引,在苦闷的状态的内里,陷于灰心,丧志,颓败,灭亡……”⑥这些语言是批评家在直接感悟作品、进入作家心灵世界后的真实显露,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钱杏邨作为一个评论家毕竟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眼光。就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最早一位新兴文学的研究者和批评者,钱杏邨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视野并不狭窄,他的批评尝试涉足于一个相当广的范围……这种广泛的研究和阅读培养了他的艺术鉴赏力。”⑦因而,我们看到,当稍晚丁玲因为创作长篇小说《母亲》而遭到某种指责,批评这部作品主题“太模糊,不亲切”等诸多缺陷时,钱杏邨倒是站出来为丁玲辩护,批评那些评论者“理解太机械,没有理解得‘艺术形象化’的意义”。钱杏邨还以少有的宽容说:“《母亲》虽然有缺点,但这缺点并不能掩饰它的优点,在1933年的中国文坛中,毕竟是一种良好的收获。”⑧钱杏邨对丁玲的这些评论,无疑是评论家在某种程度上忠实于客观生活,忠实于艺术感受、一定程度冲破左倾观念束缚所获得的成就,在丁玲研究中自有其应有的价值。 但是,此时的钱杏邨无论就其总体批评观念还是批评语言来说,都带有浓重的左倾文艺理论基调,是机械唯物论的代言人,庸俗的社会学评论成为其理论出发点,他对丁玲的评论中更是时时表现出了这些典型特征。在革命文学刚刚萌发的时期,钱杏邨就提出了“力的文艺”的口号,“我们不能不应用Marxism的社会学的分析方法”⑨。但“力的文艺”在他这里只是简单的“阶级”的代名词而已。后来他进一步发挥说:“一个普罗列塔利亚作家要想在一切方面都坚强起来,他一定要能够把握得普罗列塔利亚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他应该懂得普罗列塔利亚的唯物辩证法,他应该用着这种方法去观察,去取材,去分析,去描写。”⑩在这种观念指导下,钱杏邨在评论作家时就经常把落脚点放在作家的阶级意识和作品的社会内容上,把文学和生活的复杂关系简单化,文学作品和批评家先入为主的观念是否吻合以及吻合的程度成为衡量作品成败的标尺。钱杏邨的这些批评理论在他对丁玲的评论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这一切都使得钱杏邨的作家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己批评观念的附庸,失去了应有的活力,成为左倾机械唯物论批评滥觞时期的代表之作。 钱杏邨认为,丁玲固然为中国新文学贡献出了一些独特的元素,然而她早期的几部作品因为描写的对象是受到“五四”影响的新女性,这些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成为落后时代的产物,其存在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是彻底失去理想的颓废者,应该全盘否定。这种观察的出发点和他当年批判鲁迅如出一辙。他为此激烈批评丁玲笔下的这群新女性:“反映在丁玲的创作里的女性姿态,就是这样的一群姿态:她们拼命追求肉的享乐,她们把人生看得非常阴暗,她们感受性非常的强烈,她们追求刺激的心特别的炽怪……”“在每一篇里,都涂着很浓厚的伤感的色调,显示出作者的对于‘生的厌倦’而又不得不生的苦闷灵魂。”(11)很显然,钱杏邨的这些指责是非常过火的,完全不承认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过积极作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这样,丁玲早期作品中最富有生命力、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叛逆型女性形象的意义被钱杏邨一笔勾销了。不仅如此,钱杏邨还处处要求作家去表现所谓进步的阶级意识,在题材上去写所谓的“尖端题材”,把有机的、丰富的现实主义内涵凝固为公式化的创作模式。他这样批评丁玲的作品:“《在黑暗中》只表现了作者的伤感,只表现了这一种人生。作者对于文学本身的认识,仅止于‘表现’,没有更进一步的提到文学的社会意义……作者只认识‘文学是人生的表现’的一个原则,忘却了‘尖端的题材’的摄取。”(12)其实,钱杏邨这里所念念不忘的“文学社会意义”、“尖端题材”正是庸俗社会学批评最常使用的名词,这样的后果必定使文学成为宣传的工具,把所有作家的创作绑在公式主义的战车上。从这样的观念出发,他极力批评丁玲落后的阶级意识导致了作品灰色的格调:“作者不曾指出社会何以如此的黑暗,生活何以这样的乏味,以及何以生不如死的基本原理,而说明社会痼疾的起源来。”(13)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被钱杏邨完全等同起来,文学直接变成了诠释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 正是抱着这样偏激的批评观念,当丁玲后来逐渐放弃了早期的文学理想,走上“革命与恋爱”模式的创作道路时,钱杏邨倒反而大加赞赏。因为在他看来,丁玲的这些作品代表了一种进步的革命立场,是作家世界观转变的标志。钱杏邨对丁玲的《韦护》评论道:“这一部长篇的主旨,很显然的,是‘革命的信心’克服了‘爱情的留恋’,这一个概念就是很正确的概念,是她在前期所绝对不会如此主张的概念。……这是她思想的发展。”(14)这分明是用政治标准代替了艺术本身的标准,客观的效果必然是从根本上取消了艺术自身。对于丁玲抛弃“革命加恋爱”模式后创作的《水》,钱杏邨将其视为当时左翼文艺运动最优秀的成果:“作为反映这一题材的主要作品,那是丁玲的中篇小说《水》。《水》不仅是反映了洪水的灾难的主要作品,也是左翼文艺运动1931年的最重要的成果。……作者深刻地抓住了在洪水泛滥中的饥饿大众的,在实际生活的体验中逐渐生长的,一种新的斗争的个性,辩证法的描写了出来。”(15)钱杏邨之所以推崇《水》,就是因为《水》展示了丁玲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成为他心目中最符合革命文学规范的样本。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钱杏邨此时的文学批评因为常常搬用国际流行的无产阶级文学话语,以激进、革命的姿态出现,再加上当时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水平普遍不高,很容易被同时期的左翼文学界奉为经典。可以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不少评论丁玲的文章都或多或少受到钱杏邨观点的影响,甚至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仍能在丁玲评论中见到类似模式的批评。但实际上,这种批评模式是建立在十分错误的理论基础上的,如冯雪峰所批评的那样:“将具体生活现象变成了概念,将意识形态看成简单的抽象的东西,也将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看成机械的简单关系。”(16)“钱杏邨的文艺批评,自他的开始一直到现在,都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17)因而它在文学实践中带来的危害也更大,这一点越到后来看得愈清楚。 冯雪峰早年是一个痴迷文学创作的诗人,他从事丁玲评论的工作虽然略晚于钱杏邨,但较为清醒的头脑、扎实的理论功底使得他的批评比起钱杏邨要客观得多。在冯雪峰的心目中,丁玲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使得冯雪峰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关注丁玲的创作道路。从1932年他发表《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到建国后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冯雪峰对丁玲创作中出现的许多现象都及时给予揭示,这些文章在丁玲研究中自然也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左翼文学时期的冯雪峰与左倾机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钱杏邨有着不少的区别。冯雪峰虽然支持“创造社”、“太阳社”对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但又十分不满于他们对于文学简单、机械的理解;更不满意他们在批评中粗暴的态度和关门主义倾向。因而冯雪峰在左倾文学理论泛滥、甚嚣尘上之时,却能够冷静思考,甚至给予一定程度的抵制,是十分难得的。如冯雪峰1928年发表的《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就充分显示了其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独立思考能力,对于极端左倾批评理论抱有警惕和怀疑的态度。他很不赞同钱杏邨等那种动辄否定反封建意义、否定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做法,坚持认为中国反封建革命的任务并未完成,也为鲁迅的价值进行辩护:“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18)对于丁玲创作中出现的“革命与恋爱”模式的作品,冯雪峰虽然也肯定它是作家创作道路的一次重要转变,但并没有像钱杏邨那样把《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等作品抬到那样高的地位,他甚至认为丁玲的《田家冲》“至多不能比蒋光慈的作品更高明”(19)。这说明冯雪峰对当时盛行的这种模式化创作的弊端是有所认识的。对于丁玲投身左翼文学运动后创作的《水》,冯雪峰也没有像其他评论家那样无限夸大它的意义,认为“这还只是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20)。随着冯雪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水平的逐步提高,他对左倾机械唯物论危害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后来能够站在更宽阔的视野对其前期评论的不足进行反思和修正。这一点在他1947年所写的《丁玲文集·后记》中就已表现出来。在这篇带有总结丁玲创作道路意味的文章中,冯雪峰对“莎菲型”女性的评价比起早年的激烈指责要温和一些,他肯定丁玲的《梦珂》“闪耀着作者的不平凡的文艺才分,惹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却也更透明地反射着那时代的新的知识少女的苦闷及其向前追求的力量”。“第二篇问世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梦珂》的一个发展,艺术手段也高得很远了。”(21)同时,对于他自己和钱杏邨都曾经高估的《水》,也更能清醒地发现其隐含的问题所在:“《水》,以艺术对现实对象的深度和艺术的精湛而论,反而大不及以前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它的不满人意的地方,照我看来,是在于以概念的向往代替了对人民大众的苦难与斗争生活的真实的肉搏及带血带肉的塑像。……这作品是有些公式化的,同时也显见作者的生活和斗争经验都还远远地不深不广。”(22)丁玲小说《水》存在的这些问题实质上是作者片面理解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作家世界观、创作方法等关系带来的结果,作者往往生吞活剥地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生活的真切感受中,通过艺术手段所自然达到的。丁玲创作中的这些问题在当时左翼作家中是普遍存在的,冯雪峰的这些评论,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片面的左倾唯物论的要害,对于纠正左翼作家创作中的概念化倾向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于包括丁玲曾经受到热捧的“革命恋爱”小说,此时冯雪峰也能冷静地剖析其致命的弱点,“仅仅千篇一律地在所谓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一些意识上的纠纷上兜圈子,并没有深掘到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上的冲突实在反映着时代的矛盾根源和阶级关系。”(23)这可以看作冯雪峰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于这种概念化创作模式的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算。对于后来丁玲曾经遭受很多非议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冯雪峰也力排众议,给以充分肯定:“《我在霞村的时候》,作者所探究的一个‘灵魂’,原是一个并不深奥的,平常而不过有少许特征的灵魂罢了;但在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这在落后的穷乡僻壤中的小女子的灵魂,却展开了她的丰富和光芒的伟大。”(24)冯雪峰认为,小说之所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作者长久体验生活、拥抱生活,进而用形象的方式来塑造人物。考虑到冯雪峰这篇文章的写作已经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当时的绝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党的领导者对文艺问题的权威论断,他仍然能从复杂人性的角度来切入,显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到了后来,冯雪峰在评论丁玲的著名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已经能够较为纯熟地运用恩格斯典型性理论来分析作品,从而对作品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主义特征做了很好的阐释。他说:“我认为这一部艺术上具有开创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似的作品;同时,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现时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这就是它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25) 但冯雪峰文学批评的复杂之处在于:虽然冯雪峰曾经较早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工作,虽然他不认同“创造社”、“太阳社”的理论主张,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盛行的机械唯物论加以抵制和批评。但总体来说,他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左”的教条理论束缚,在反“左”的同时自己也不知不觉间陷入“左”的理论怪圈,因而在对不少文学理论问题的理解上亦有明显的失误,这些失误在他对丁玲的评论上都一一暴露了出来。冯雪峰早年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尽管与钱杏邨等人的观点有明显的分野,但不能否认的是也有不少“左”的论调,比如对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时期的先进作用估计不足,认为他们只能充当革命的“附庸”。同时也错误地认为五卅以后“国民主要(次要当然要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是应该生活在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26)。进而混淆了社会性质。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冯雪峰在评论丁玲转向革命文学之前的作品时,对作者描写的一群小知识分子就充满了排斥和否定,甚至由此来批评作家所谓错误的政治立场:“丁玲在写《梦珂》,写《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写《阿毛姑娘》的时期,谁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领有着坏的倾向的作家。那倾向的本质,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ken)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他指责《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知识女性流露的是一种“苦闷的,无聊的,厌倦的不健康的心理状态”(27)。这样的论点和钱杏邨对丁玲的评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其实这种过火的、以作家政治立场划线的做法恰恰和他曾经流露的较为正确的观点处于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冯雪峰很长一段时间就这样来回摇摆。 由于冯雪峰此时的文艺评论模式在整体上无法完全与钱杏邨划清界限,也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那种他所批判的钱杏邨式的机械唯物论痕迹在其评论丁玲的文章中也是经常可以见到。例如,当时盛行着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就一再被冯雪峰当作评判作家的工具,其实质就是片面夸大“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对创作起着直线式的决定作用,鲜明地强调作家作品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倾向;要求作家选取所谓的重大题材,突出工农大众的历史作用等。这些倾向在冯雪峰左联时期写作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一文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很大程度上带有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通病。丁玲参加左翼文学活动后,急于要摆脱以前的创作模式,于1931年发表了小说《水》。这篇小说在艺术上虽然很粗糙,存在很多缺陷,因而谈不上有多少艺术的创造。但因为它直接选取了当时中国南方洪水泛滥的重大事件,在作品中讴歌了农民觉醒、反抗的斗争生活。这些在钱杏邨、冯雪峰甚至茅盾等不少左翼批评家看来,标志着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开始被作家自觉运用,不仅是丁玲创作也是左翼文学上的重大事件,于是《水》就被赋予了特殊重要的地位。为此,冯雪峰认为丁玲的《水》意味着作家在思想上有了巨大的飞跃,同以前的旧意识彻底决裂,成为了“新的小说家”。冯雪峰理解的新小说家只是就作家的世界观来谈的,根本没有涉及到任何文学内在因素:“新的小说家,是一个能够正确地理解阶级斗争,站在工农大众的利益上,特别是看到工农劳苦大众的力量及其出路,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的作家!”(28)冯雪峰还总结出《水》在文坛上出现的价值:“第一,作者取用了重要的巨大的现实的题材……第二,在现象的分析上,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定的理解。第三,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29)到了20世纪40年代,冯雪峰依然坚持认为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是作家思想进步的表现,“《水》依然是作者发展上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我们新文艺发展上的一个小小标志”(30)。这些都是从阶级论出发,把艺术视作政治附庸的产物。冯雪峰特别看重作家世界观的改造,特别看重作品中表现出的阶级意识。在他看来,只要一个作家“从观念论走到唯物辩证法,从阶级观点的朦胧到走到阶级斗争的正确理解”,马上就会成为一个“新的作家”。(31)至于作品艺术上的成败得失则被放在了无足轻重的地位,这都证明冯雪峰一旦涉足到具体的文学对象时也会深深地陷入他所否定的左倾机械论的泥淖。因此,人们惋惜地发现,一个并不缺少美的感受和创作经验的批评家,一个并不缺少丰富理论素养的批评家,在对《水》的评论中竟然出现了让人难以接受的,也被历史证明是不准确的结论。即使在后来冯雪峰总结历史教训,对早期左翼文艺理论思潮开始系统反思的背景下,在涉及评论丁玲时,这种机械、生硬套用政治理论术语、主题先行,忽视对作品进行精细美学分析的模式仍很严重。如动辄批评丁玲早期作品主人公只是“空虚”、“绝望”、“没有拥有时代前进的力量”(32),动辄把是否能反映出较广、较深的社会内容作为人物典型化的唯一尺度,甚至把典型性和阶级性当做同一概念而误用。他批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黑妮“没有完全写好”,“这个人物和小说中故事的联系虽然是有机的,但说到以她的性格去和她的环境、事件及别的人物相联系,则其有机性就不够充分和深刻”(33)。冯雪峰的审美判断在这里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可见,冯雪峰的文学批评始终是矛盾的统一体,在丁玲评论中,他惊人的才华和平庸的见解常常交织在一起。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尚未成熟、独创性理论匮乏且左倾观念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冯雪峰和他的很多同时代人一样,也无力摆脱这样的悲剧宿命。 在左翼文学批评家中,茅盾的文学批评是很有个性的。由于茅盾从事实际的文学批评很早,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文学经验,而且对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和思潮涉猎很广,因此并不像钱杏邨那样对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充满狂热、亢奋,态度较为审慎。即使在左倾唯物论大行其道的时候,他也有不同程度的抵触,宁愿保持一种距离。同时,茅盾在进行具体的文学评论时,更多地是从文学的角度而不是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对文学本质的见解比起钱杏邨和冯雪峰来都更准确、更贴近文学本体;对作家的态度也较为宽容和温和,远远没有像钱杏邨的粗暴和冯雪峰的严厉。因此,当茅盾评论丁玲的时候,自然就带来一些特别新鲜的元素,显示出了左翼文学批评的实绩和高度。 茅盾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他是带着“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而跨入到左翼文学的批评阵营来的。当钱杏邨把国际上的“拉普”和“纳普”那套理论拿来当作至高无上的原则,并把火力对准鲁迅等“五四”时代的作家时,茅盾本能地挺身而出,捍卫着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精神,批评钱杏邨的那套头脚倒置的所谓新写实主义理论,和钱杏邨展开激烈的论战。茅盾坚持认为作家应该描写客观存在的现实,现实是具体可感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干巴巴的主观理念,否则必定造成对现实的歪曲。他说:“慎勿以‘历史的必然’当作自身幸福的预约券,且又将这预约券无限止地发卖……把未来的光明粉饰在现实的黑暗上。”(34)茅盾对于忽略艺术美感、片面夸大文学宣传作用的观点也十分反感,批评倡导“革命文学”的作家“有革命热情而忽略于文艺的本质,或把文艺也视为宣传工具”(35),这不啻是对钱杏邨等的棒喝,在庸俗社会学面前亮出了鲜明的反对大旗。同时茅盾还认识到,五四新文学的反封建意义是不能简单否定的,它在中国社会的进程中曾经扮演着积极、进步的角色。所以茅盾1933年发表的《女作家丁玲》对丁玲早期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评论,就能从反封建的历史环境中揭示莎菲等充满叛逆和反抗传统礼教的精神,敏锐发现这些女主人公和“五四”时代的精神关联。茅盾说:“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莎菲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旧礼教的叛逆者。”显然,茅盾认为评论人物不能离开其具体的历史环境。莎菲虽然是“五四”时代的青年女性,但当时中国反封建的历史进程并没有结束,而且有时还在激烈进行,莎菲们的反抗当然在一定的阶段仍具有积极的意义。茅盾的这些见解比起钱杏邨甚至冯雪峰都更加符合实际。对于莎菲等遭人非议的恋爱生活方式,茅盾也不是简单地否定,更不是像钱杏邨那样动辄上纲上线,斥责其“堕落”,也没有像冯雪峰那样斥责她们是一群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恋爱至上主义者”。他更多地是一种理解和同情:“她要求一些热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热爱着而又蔑视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爱者,她终于从腼腆拘束的心理摆脱,从被动的地位到主动……这是大胆的描写,至少在中国那时的女性作家中是大胆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36)茅盾把左翼批评家常常从政治角度切入评价“莎菲型女性”的做法还原为社会和文化心理的层面,将其解读为“性爱矛盾心理的代表者”,可谓别出心裁,更有说服力。 综观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能够像茅盾这样精细入微地从作品入手,进而恰如其分地总结出作家作品的创作特色以及文学史意义,并抱以一种和作家平等的姿态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姿态,确实非常罕见。在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中,李健吾曾经发表过很好的见解:“一个作者不是一个罪人,而他的作品更不是一片罪状……在文学上,在心灵的开花结实上,谁给我们一种绝对的权威,掌握无上的生死?”(37)批评家的角色更多地是用心灵去咀嚼和体味杰作的魅力,而不是法官和裁判。显然,茅盾的文学批评实践很接近李健吾的这种理想,他对丁玲《莎菲女士日记》的这些评论历来被人们视为权威和经典是很有道理的,它一扫当时的那种死抱僵硬文学理论、执着于政治功利批评的做法,把文学审美的主动权真正交给了读者。稍后茅盾评论丁玲的小说《母亲》,也依然延续了这样的模式。丁玲在转向革命文学后虽然告别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时代,不仅创作了带有浓厚“革命加恋爱”题材意味的《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等作品,也创作了诸如《水》《田家冲》此类凸显革命和反抗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一时赢得了左翼文学界的喝彩,但丁玲也深深地陷入困惑之中。作为一个很有天分的作家,她当然知道这类紧跟左翼文艺潮流的作品是难以获得长远的生命的。带着矛盾的心理,她有意把笔触拉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创作了和时代保持一定距离的小说《母亲》。然而小说刚刚问世,那些信奉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批评家马上就横加指责,如署名“犬马”的作者批评《母亲》描写的时代太模糊,缺乏时代精神,“所以在下笔的时候,不自觉的会怀着感伤的情调,多作‘开元盛世’的追忆,以及关于这破落大户的叙述,而不能实际把握住那一时代,为那一时代的运动与转变画出一个明显的轮廓。”(38)他也同时批评《母亲》很多描写日常生活的篇章是刻意模仿《红楼梦》。对于这种盛气凌人、缺少宽容精神的批评,茅盾十分反感,他认为这对于丁玲过于苛刻,完全是从抽象观念出发而不是从真实的艺术感受出发得出的错误结论。茅盾反驳说:“这些真是具体地(不是概念)地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夜‘维新思想’的决荡与发展。并不是一定要写‘革命党人’的手枪炸弹才算是‘不模糊’地描写了那‘动荡的时代’!”(39)茅盾这里所致力的是建立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互相理解、彼此尊重的平等关系,这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是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做法。 然而,茅盾的文学批评道路也不是一条直线,有时会出现微妙的变化,呈现出不平衡甚至矛盾的状态。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茅盾实际参加“左联”组织从事文学批评时,左倾的文学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留下了时代的烙印,批评成就和特色都有所减弱。如茅盾早期所写的作家论,“比较尊重作家创作的选择及其特殊的艺术追求,也比较注意审美的判断……这时茅盾的批评是比较宽容和切实的。”(40)但是到了1933年他所写的《女作家丁玲》,也在很多方面附和流行的左倾理论,从作家世界观的转变来机械地理解丁玲创作的转向。作家的阶级立场、生活道路等非文学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他原来较少关注的题材、主题等也逐渐排斥了对作品美感的咀嚼和欣赏。如茅盾把丁玲的创作道路划分为《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期、“革命与恋爱”时期和以《水》为代表的时期,这样的划分显然是以丁玲思想的历程而不是以文学本身的逻辑进程作为依据。他认为作家思想的进步必然造成文学世界的进步,其结果自然无形地把《水》提高到和作品自身不相称的位置:“《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现才能的更进一步的开展……可是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41)事实上,虽然《水》的确终结了“革命加恋爱”的文学创作模式,但却同时开启了概念化更为严重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模式,而这种模式给文学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遗憾的是茅盾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评论基调人们都似曾相识地在钱杏邨、冯雪峰那里见到过。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像无物之阵那样无处不在的时候,即使茅盾这样出色的批评家也无法独善其身,真正与其划清界限。直到晚年,茅盾对这些现象才能做出较为彻底的反思,认为这是左翼文学批评整体水平的贫弱所导致:“健全正确的文艺批评尚未建立起来,批评家尚未摆脱旧的习惯。”(42) 钱杏邨、冯雪峰和茅盾都是中国左翼文学较有影响的批评家,在血与火的年代,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扩大了左翼文艺的影响。在对著名左翼作家丁玲的评论中,他们几乎同时发现了这位作家的文学生命,并以自己的批评方式做出了阐释,不少地方充满真知灼见,构成了丁玲研究历史链条的重要一环。但也应该看到,钱杏邨、冯雪峰、茅盾的丁玲评论存在的缺陷也是无可避讳的,他们都企图通过具体的文学形象来图解意识形态领域的抽象概念,文学审美的中介方式几乎消失了,文学被封闭地焊接在政治、阶级等的标签上,因而丁玲一定意义上成为了他们发挥这种批评理念的传声筒。人们看到的是,在丁玲红色意义凸显的背后却是对文学本体的迷失,中国左翼文学批评由此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和挑战。钱杏邨、冯雪峰和茅盾在评论丁玲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在中国左翼文艺思潮中是带有共性的,在今天仍不失为供人们反思的典型范例。 ①毅真:《丁玲女士》,《妇女杂志》1930年第16卷第7期。 ②钱杏邨:《死去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号。 ③《〈太阳〉月刊编后》,1928年3月号。 ④(11)(13)(14)钱谦吾(钱杏邨):《丁玲》,《现代中国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年版。 ⑤⑥(12)钱杏邨:《〈在黑暗中〉——关于丁玲创作的考察》,《海风周报》1929年第1期。 ⑦(34)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第127页,第1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⑧钱杏邨:《丁玲的〈母亲〉》,原载《现代》1933年11月第4卷第4期。 ⑨钱杏邨:《关于文艺批评——力文艺自序》,《海风周报》1929年第9期。 ⑩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拓荒者》创刊号1930年1月10日。 (15)钱杏邨:《1931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北斗》1932年第2卷第1期。 (16)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雪峰文集》第2卷,第1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7)冯雪峰:《“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雪峰文集》第2卷,第349页。 (18)(26)画室(冯雪峰):《革命与知识阶级》,《无轨列车》,1928年第2期。 (19)(20)(27)(28)(29)(31)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原载《北斗》1932年第2卷第1期。 (21)(22)(23)(24)(30)(32)冯雪峰:《〈丁玲文集〉·后记》,《雪峰文集》第2卷第205页,第209页,第208页,第212页,第210页,第2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5)(33)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原载《文艺报》1952年第10期。 (35)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28年10月第19卷第10期。 (36)(41)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1933年第2号。 (37)刘西渭(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第5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8)犬马:《读〈母亲〉》,《申报·自由谈》1933年6月28日。 (39)茅盾:《丁玲的〈母亲〉》,载《文学》1933年第1卷第3期。 (40)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2)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标签:冯雪峰论文; 丁玲论文; 茅盾论文; 梦珂论文; 文艺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母亲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