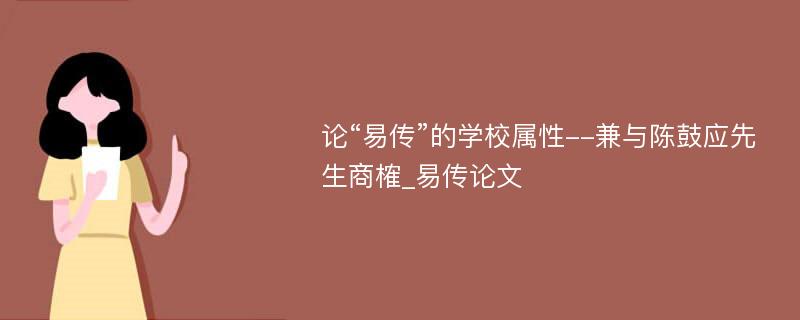
论《易传》的学派属性——与陈鼓应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属性论文,易传论文,陈鼓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2)01-0008-11
在近年的学术界,陈鼓应先生所著《易传与道家思想》不啻空谷蛩音,石破天惊。《易传》一向被视为与《易经》并传的儒家经典,数千年来,无人质疑。被陈先生断给了道家学派;历史上分野鲜明的中国哲学两大流派——道家与儒家,两者的差别被陈先生消融了,消融到道家一边,儒家则变得不知去向。历代传易诸家,荀卿、扬雄以至周敦颐、邵雍、朱熹等皆是道家。所谓儒家也者,成为只剩冠冕缨緌、褒衣博带,矩行规步,无非揖让之礼;口宣指划,全是仁义说教;并无哲学语言,甚而面目不清的一群衣冠人物。
陈书所有文章都贯穿着“道家文化主干说”的一条主线。先生初来也,即声言大陆批儒不深不透,应该继续。然而扬汤止沸,无如釜底抽薪,于是有“道家文化主干说”出;复因不破则不立,于是又有《易传》乃道家思想的一系列论证。用力之勤,收功之伟,为近年所仅见。而且影响广泛,一时洛阳纸贵矣。
《易传》的著作年代,经过宋代欧阳修质疑之后,一直被视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无论坚持春秋末期,还是战国前期、中期以及晚期诸说,都有当代名家的论证成说。几乎不须考据,根据需要取用即可。陈鼓应先生即是引据疑古大师之论断,将《易传》的著作年代订为战国晚期的。这样就使《易传》不仅产生在《庄》《孟》之后,亦在《管子》书后。而且出于同一目的,取唐兰先生将马王堆出土的《经法》等书确定为战国早中期说,而将帛书《易之义》、《要》断定为秦火之后。这样一来,形势便很明显了。后出之书,承袭前人思想,这是思想发展的通则,加之陈先生的如椽妙笔,缜密论证,一座精彩的“七宝楼台”便被构筑起来。予观陈先生书,虽目迷五色,而心不能无疑也,仅献其愚,以就正于陈先生及海内外方家。
一、关于《系辞传》的著作年代及名义问题
先考察一下《易传》的著作年代。
自欧阳修疑古成说,提出“系辞非圣人之所作”后,《易传》的著作年代便成为悬而难决的问题。现代以来,最为流行的是战国晚期说,比较慎重的是中期说,只有少数学者坚持孔子和春秋末期说。诸说之间聚散分合,远非如此崭然分明。其间值得注意的问题还有:其所确定之年代,是指书的创始、流传、写定还是勒成卷帙,汇编成册等问题,都须搞清。不可用编成、产生等不确定语塞责。不然,纷坛聚讼,永无止息之日矣。总之,摈弃信史于不顾,仅以个别字词为据,推翻成说,窃以为不可。予取《易传》创始于孔子,初具规模于孔子商瞿师弟之间,口耳流传于春秋战国之际,写定亦即成书于战国前期,早于庄、孟为说。兹博采众家,述之如后:
《周易》本是占筮之书,但到春秋时期,人们在占筮之余,已经开始对卦象进行分析,作出义理的解释。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以《周易》见陈侯,筮遇《观》之《否》,其解爻辞曰:“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左传》、《国语》此类卦象分析的筮例甚多,表明这时人们已不满足于爻辞的占断,还必须作出所以然的解释。不在于这种分析与后来的《易传》如何的相似,而在于这种需要构成了对《周易》卦象爻辞作出义理分析的普遍社会需求;而且此时已经有了类似的专书。据《左传》记载,韩宣子聘鲁时,在太史处见到《易象》和《鲁春秋》两书,赞叹道:“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昭公二年》)杜预认为《易象》就是《周易》上下经之象辞。然晋也有《周易》流传,如无新解创意,韩宣子就不会如此倾倒赞叹了。李学勤先生判断说:“《易象》应该是论述卦象的书。”[1]既有社会需要,又有先行文献,《易传》产生在春秋末期的充足条件已经具备。那么剩下的就是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了。
孔子整理传授包括《周易》在内的六经,史籍备载,诸子称道,要想一笔抹杀殊非易事。(“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太史公自序》)。“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滑稽列传》)问题在于孔子的整理传授工作,是否如其所自云的“述而不作”。此语是谦词还是实述,余意兼而有之。述是继承讲述,作是创制著作。《诗》《书》《易》《礼》皆作自前人,而《春秋》却作自孔子,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在一些人的眼中,这种所谓作,不过是在原有史书基础上的笔削删述而已。然而所以笔削的标准,发凡起例的原则,却非孔子不能为。这背后是需要一个思想体系作支撑的。诚然如陈先生所说,仁义的观念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但将仁与义的观念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以之建成一个学术系统的,却是孔子。正如道字出现于老子之前,并无碍于老子享有道论哲学的发明权一样。所以孔子道仁义,可以称之为述中有作。对于《易》《礼》《诗》《书》等,也应当作如是观。述是不能理解为转述或徒事背诵的,只能是讲述,讲述就离不开多方为喻,比兴发挥,务以阐明其所蕴含之义理为指归。那么这种讲述也就是作。但“作”在当时似乎仅指经典的著作,为什么只说孔子作《春秋》,而不说孔子作《易传》乃至于《诗》《书》《礼》《乐》呢?固然是因为《诗》《书》《礼》《乐》原本就作自往圣先贤,比如“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说文王;“制《礼》作《乐》”则属于周公;传说《诗经》的作者也都是前代的大贤。孔子的自谦,有其必然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被孔门视若大经大法的著作中,缺少社会历史观的经典,不得不由孔子笔削补著,《春秋》的删述是堪与《诗》《书》《礼》《乐》比美的大制作,故尔被孟子称之为“作”。而对于《易》《诗》《书》《礼》《乐》,孔子只是删定、只是述而已。至于《易传》只是述《易》的产品,本来就不在“作”的范围之内,当然也就谈不上孔子“作”《易传》的问题了。但其属于“述”的范围,是述中之作。
《论语·述而》篇记有:“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路》篇还有孔子引《易》之文的记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意为:根据《恒卦》爻辞,无恒之人,必承其羞,这是不待占而可知的。)这是孔子学《易》并倾向义理的直接证据。邓立光博士指出《宪问》篇载“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曾子的补充论证正是引用《艮·象传》:“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之辞。[2]若非曾子其时已有《象传》,亦必是其援引孔子论《易》语。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加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列传》都载有孔子传《易》于商瞿,自瞿六传而至齐人田何,再传至淄川人杨何的渊源系统。据《太史公自序》言,司马谈为太史公,受《易》于杨何。迁传父学,则其述《易》之辞,有自来矣。此而不可信,则将何信?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迁于《易传》只举《彖》、《系》、《象》、《说卦》、《文言》八传,不及《杂卦》、《序卦》。又偏于八传之前着一“序”字。序者,发端、次第之谓也。《尔雅·释诂》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谓端绪也。”透露了此八传,皆作始于孔子,而并非完成于孔子也。(孔颖达《正义》云:“序,《序卦》也。”从之则整句难通,异读则愈加费解,故不从。)
据子贡“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论语·公冶长》)的慨叹,说明一般弟子,只能接闻“夫子之道德文章”。至于“性与天道”,以其高深而属于术业专攻的学问。朱熹解释此语时就认为“盖圣门教不躐等”,因而“学者有不得闻者”(《四书集注》)。根据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如《易》与《春秋》之义理,必是另有讲授,有类今之研究班之属,不仅口耳相授,而且相与切磋。当时或无讲稿,然而孔子学易心得,师弟论学语要,不容没有提纲和笔录。即使口耳相传,尔后勒之于简策.有所遗漏,有所增补,有所舛误,要非初不出于孔子也。则《易》之十翼,孔门传《易》者讲授之类编也。孔子殁后,七十子必有整理孔子遗教之议,《易传》的整理与《论语》的编辑,大约是同一时期或稍后的工作。
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经传,并《二三子问》、《要》、《易之义》诸篇,更进一步说明《易传》与孔子的关系。《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以此为疑,孔子则认为《周易》“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而乐其辞”。又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又“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3]不仅证明了《史记》不误,而且可以和今本《系辞》相印证。李学勤先生在《周易经传溯源》一书中一一作了比勘。同时指出“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一语与《孟子》所记“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句式的相似。既然后者是因笔削《春秋》而发,则前者也必因于《易》有所述作而言,而此述作只能是解释其所乐爻辞的《易传》。
张岱年先生曾批评将《易传》成书限定在秦汉之间的说法“疑古过勇”,经过缜密论证,他指出:“《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著作。”[4]
刘大钧先生接着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详密的考证,将《易大传》各篇文字与老庄、思孟的传世著作相比勘,认定“《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写成”;“《易大传》之《彖》《象》《文言》为思孟学派所整理、润色,《系辞》中亦有思孟学的内容”(《周易概论·关于周易大传》)[5]。
高亨先生认为《彖传》是《易传》中最早的一篇,只解卦名义和卦辞,《象传》不解卦辞只解爻辞,应在其后。因其用韵多系楚地方言,作者当为馯臂子弓及其后学。[6]易卦名义和卦爻辞,是学《易》首要讲论的问题,孔子商瞿不应不赞一语,而待再传弟子解决。子弓之学得自商瞿,或其用楚语改定而已。荀子常以孔子、子弓并称,誉为“圣人”“大儒”,足以说明子弓易学的渊源所自。若为其所自著,则径自名家可矣,何须强调师承关系?又,战国前期的古书,如《礼记》中子思所作的《坊记》、《中庸》、《表记》、《缁衣》、《深衣》等篇,体裁句式,辞彩文气,都与《文言》、《系辞》极其近似,且有引《易》之文,可见是子思在模仿《易传》的文风。据高亨先生考证《礼记·深衣》称引“《易》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出自《象传》,足证《象传》作于《深衣》之前。而公孙尼子所作《乐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以下二十二句,确系袭用《系辞》而略加改动。馯臂子弓、子思和公孙尼子都在“七十子之弟子”之列。根据以上诸先生的论断,可见《易传》不会晚于七十子活动的战国前期。
欧阳修之疑《易传》,是因为他认定,“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易》字当系笔误),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易童子问》)。在欧阳修看来,孔子著作只能是言简义深的经书,而《易大传》则不惟词繁而且相互矛盾,圣人必不如此。斯论未免过于绝对,按照李零先生的考证,古书的形成确有其逐渐定型的通例,应该首先承认有一孔子以及商瞿草创的著作文本,亦即廖名春先生所称之祖本。孔子师弟间相与讨论的心得、议论,主攻易学的商瞿诸子,不容没有简单的笔记和课后的整理,不然如何记诵如何传播?今查《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也并不皆词约义丰。笔削《春秋》是著书,可按义例删改;讲解《易经》是授课,更多随文发挥,此坛堂讲录当与《论语》相去不远。何况讨论之辞不尽出自孔子。除“子曰”者外,余者当系从学弟子述师意之言。唯其如此,才能有“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间者在焉”(同上)。欧阳修说:“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此语尤误。凡标明“子曰”者,仿《论语》之例,皆当时及门弟子所记授课之要也。如系讲师之言,当标以某子,如曾子、公孙尼子之类。战国儒家之书,皆以传孔子之学为号召,余者或有发挥,或稍变其语,大抵皆孔子讲易论道之意。至于欧阳修所谓二三其说以至于五,有的不过述异闻,有的则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论《易》而已。如易卦起源问题即是。由之亦可证孔子讲《易》非一次,听讲之徒非一人。后经历传分合,至于战国前期写定。欧阳修其误在于不知《易传》多系弟子手记师言,并据以再加发挥的结果,与《论语》成书一样,未经孔子手定也。但欧阳修承认其虽非圣人之言,“而圣人法天地之蕴则具存焉”(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易类》),以及《易传》产生在去圣未远的三代之末,仍不失为卓识。
再说名义。陈先生认为帛书《系辞传》尾题一“系”字,因而疑及今本《系辞传》与《彖》、《象》一样,应该称为《系传》。引证《说文解字注》系为总持,结束之意。“《系》之尾题以综论总括经义,这种体例,颇似《楚辞》篇后附以‘乱’以结括全篇。王逸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陈先生同时指出“称之为《系》,绝非《系辞》的省称,因为他们是不同的概念”。[7]此论甚有见地,可备一说。但因之认为,《系辞传》之名是抄定者不知“系”的含义,见传文中多次出现“系辞”一词,便随意改题《系辞》。则恐有违于事实。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引《系辞传》语称之为《易大传》,后人遂以通称。欧阳修则说:“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传尚存,此所谓《系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系辞》矣。”并且认为“《系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远矣”。朱伯崑先生认为“此传是通论《周易》之大义,不是如《彖》《象》那样逐句解经”。[8]此所以称大传也。高亨先生也认为:《系辞传》之系辞与文内系辞其义不同。然则以何不同,则语焉不详。实则一以指系于爻下者,一以总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爻下系辞之总体义涵者也。因为易经之精神俱已分见之于卦爻系辞,再加总括综理其各卦爻辞串讲以见其整体义理精神,谓之为经立传可矣,称之为系辞立传亦可矣。系辞本指爻下所系之辞,《系辞传》系指为系辞所作之传,久而久之,《系辞传》亦简称《系辞》,如《彖传》径称《彖》然。是以卦爻之系辞与《系辞传》之系辞,其名义之不同端在于此,岂有他哉。由此可以判定《易大传》是系统阐述、发挥《易经》精神的哲学论著,立论的依据全是《易经》卦象及其系辞,故有《系辞传》之称。所谓传有传达义,即须忠实地阐发经典的原意,容许传者从不同角度多方阐述发明,也可有不同的理解,但不容许自相矛盾。如《春秋》三传即是从不同侧面对《春秋》经文的传述,《左传》则史实,《殻梁》则义理,《公羊》事理兼顾,各有侧重。《易》之十翼,亦孔门先儒攻《易》之十面受敌法也。
二、关于天道等概念及学派属性问题
陈书将“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解释为孔子哲学没有性与天道,从来不谈性与天道,干脆就是无此概念。可说是对古代文法语式的挑战,比如某之友家藏历代名画,为某所亲见,然不轻以示人。于是某说:“友之藏画,近代以来可得而见也,明清以上不可得而见也。”不可得而见就一定是没有?此犹不足为喻。因为是人皆知明清书画民间尚有深藏者。而性与天道则不然,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子贡何从而知之?并且明确说是“孔子所说的性与天道”,可见子贡知道孔子说过。这个“不可得而闻”,向来含有不可轻易得闻之的意思。以“不可得而闻”等于罕言等于不言等于无闻等于没有,是否有武断之嫌。子贡所云“不可得而闻”者,未闻之前,遗憾之辞也;既闻之后,赞叹之辞也。按照现代逻辑“否命题包含着正命题”的通则,此语恰恰证明了孔子哲学是包含着天道观的。
陈书认为《易传》道德概念的哲学含义与老庄相同。韩愈《原道》曾分析儒道之别曰:“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原道》)合仁与义,就是包含仁与义,而且不仅仁与义,因为以为仁与义之和等于道德,则去仁与义之后,也就等于没有了道德。只是“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而已,虚位就是可以向里填充不同的内容。显然认为孔孟所谓道德只是仁与义的人伦道德,是不符合韩愈原道之意的。也就是说孔孟之道,比老庄之道,含有更为丰富的内含。如韩愈所理解的圣人之道是:“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送浮屠文畅师序》)岂止仁义而已。这个“学究天人之际”的所以然之道,正是儒家所独有的特色。而与道家的“以辅天地之自然而不敢为”的自然之道,是有严格区别的。
笔者承认孔子晚于老子,并曾问学于老聃。东周学术氛围还是颇为浓厚的,谈论天道与人事、道与德异同的现象普遍存在。《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与孔老并世的子产就说过:“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只是老子对天道作了全新的解释。孔子是了解老子哲学的,但并没有为孔子所接受。孔子同意老子效法天道的“无为而治”是一种理想的最高境界,但认为只有尧舜才能做到。然而世无尧舜,人竞有为,而儒门的主张是推行符合天道的有为。孔子认为老子所云“以德报怨”的思想,不符合公平原则,所以提倡“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论语·宪问》)。
更何况,儒家认为人伦道德本来就是上承于天道天德的。而且这种思想来源于孔子整理前的《诗》《书》《易》所体现出的天道人事观念。如《诗》有“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周颂》);“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雅》);《书》有“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召诰》)。按朱熹的解释,天命就是天道。这个“于穆不已”的天道,就是《易传》“生生不息”的天德。《烝民》诗则说明了天则与民德之和谐。《召诰》的天命观,更是超越于宗教之上,天不仅命吉凶、命历年,而且命人以明哲。都说明了儒家的人伦道德与天道的关联。至于说“孔子谈道与德,都属人伦规范之义”,亦恐有误。
在《论语》中,“道”字凡六十余见,其含义至为复杂。从抽象到具体;从自然到社会;从哲学、伦理到道德修养、政治举措,包罗宏富而且深微。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虽则是谈孝悌,却是由一般论及特殊;又如“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其义蕴岂人伦一语可了?要了解孔子这句话的深刻含义,首先应当理解和把握孔子此处所说之“道”的真正内涵。细加体味,此所谓“道”,应是一带有规律性,全局性的概念。用朱熹的话来解释,它是“人事当然之实理,乃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可以不闻者”(《论语·或问》)。试想,此处所谓道,仅是仁义礼智信之属,朝闻之而夕死。无乃太过轻简乎?!孔孟确有为道德理想献身的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了正义,曾不吝惜身家性命者有矣。人世固有重于生者,然而在鱼与熊掌可以兼得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舍生取义”。而此处之“朝闻”,本没有“夕死”之必然和必要,所以言之者,乃是就其价值等量甚而逾值而言也。这就意味着孔门将闻道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此道对于道德而言,乃是指其所以然之故。也就是说人固应为事业而生,也应为理想而死。但应该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即一定了悟所以生死的意义。唯有如此,方能达到一个自觉的境界,而非凭借血气之勇,抑或信仰痴迷。所以说,此处之道,既是自然的普遍法则,又是由之而下贯人生的崇高意境。唯其如此,才可以说早上听到这样高妙的道理,即使夕死也不枉此生了。
《论语》里与《易》相联系的天道概念是天命,如“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知天命即是知天道;“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唯天为大”似乎只是赞叹天体的广漠,可是有“唯尧则之”,则只能将其理解为天道,如此方可效法之;“畏天命”(《季氏》),即敬畏天道;以及《阳货》篇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正是借天行以明天道。怎么能说儒家没有效法天道的思想?
小戴《礼记》应是春秋末至汉初儒家著作的总集,其中子思《中庸》的“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以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这里的道,明显的是属于自然规律和包括人性法则在内的天之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明确指出天道自然规律是致中和。天地之所以各得其所,万物之得以生长发育,都是天道平衡中和作用的产物。《中庸》的道论,与《易大传》的道论是极为相近的,而与《老子》的道论大相径庭。子思的思想,如果不是传自或本于孔子,也不出七十子论学的范围。
《周易》经传皆取象于自然而效法之也,宜可称之为自然哲学。古人称之为天人之学。道与天道的观念出在孔老之前,两位圣哲不仅各作了不同解说,更为重要的是将之引向了不同的方向。
陈书引李镜池先生从六十四卦检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诉”等彖辞,名之曰自然主义哲学。似乎任何探讨万物起源于自然及其成长过程和条件的论述,都是自然主义哲学。而且是自然哲学就一定是老庄哲学。如此,中西自然主义哲学者多矣,皆称之为道家可乎?又引《豫·彖传》“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曰:“迹近‘无为主义’的道家主义思想。”(见《〈彖传〉与老庄》一文)省刑罚或使刑罚措而不用即刑罚清,与老庄的根本反对法令刑罚也是大异其趣的,更何况以顺动也是有为,一点也不迹近无为主义。足见都在谈论天道,可是对待天道的视点与态度,却截然不同。至于又说《易传》阴阳刑德思想承袭黄老道家,则是道家思想互相矛盾,自乱其例矣。
道家之道,似乎只是用来修身。庄子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土苴,以治天下国家。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庄子·让王》)儒家之圣人异于是,《系辞传》明确宣示圣人“明于天之道”的目的在于“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中庸》也说:“诚者,非独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是说人效法实在的天道,不仅成就一己,还要仁民而爱物。与《泰·彖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的精神是一致的。什么是裁成辅相?就是尽人、尽物之性,就是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这是《尚书·尧典》“天工人其代之”思想的深化。道家则主张“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秋水篇》明确反对“络马首穿牛鼻”的“尽物之性”,当然也就反对裁成辅相和积极地参“赞天地之化育”了。
《系辞传》记有“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系辞传》)金景芳先生曰:“盖顺者,顺于命也,故天助之;信者,信于道也,故人助之。孔子所独具之精神,端在于此。盖所贵于知命者,乃在明了宇宙变化之法则,以求得人生行为之法则,而此行为法则,非以顺应自然法则为已足,乃在‘裁成辅相’,以增进人类之幸福。”而《老子》则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在自然面前,人是被动的,顺应而已,而不敢有任何积极的作为。主张坐而守之,等待“万物将自化”。并且认为这种“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不否认老子哲学的合理性,也无论这种无为哲学,是否过于消极,只想说明《易传》与《老子》思想悬隔甚远,并不相似。
儒家关于天道变化的认识更多地来自《易经》本身,如欧阳修《易童子问》论《文言传》卦象与义理之关系:“童子问: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何谓也?曰:其传久矣,而世无疑焉,吾独疑之也。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执于象也,则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其余如相对的观念等,可以说儒、道都是得自《易经》,而两家不相沿袭。
陈书认为《易传》《复》卦之复即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之复,故属道家思想。《系辞下》引“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按《复卦》震下坤上,一阳来复,天地之心见,为复善之义,也有重复之义。《象》曰:“刚反,动而以顺行。”“刚反”就是阳刚返回。孔子因之与颜回的改过复善之勇联系起来。其结果就是《复卦》六二爻辞“不远复,无祗悔,元吉”了。此“复”与孔子“克己复礼”之“复”义同。《易传》解“复”,完全是根据《复》卦爻辞和卦象震下坤上在六十四卦中顺序而言。一阳来复与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大异其趣。老子并不赞赏勃勃生机的万物并作,而主张冷眼观看万物向原点的复归。老子给无以名之的道,“强名之曰大,大曰远,远曰逝,逝曰返”。“反者道之动”,其所谓“复”,即是返,即是万物按照道的规律,发展变化,复归于无的过程,是一完整过程的终结。而一阳来复,是指阴霾充塞到极点之后,阳气又从阴极之下复生,从而获得新的增长点,虽只一阳,而复兴之势已具,故称之为“复”,是一过程终结之后,从旧一轮过程中获得新基点的新一轮过程的开始。同是一复,一是走向兴盛,一是走向衰亡,旨趣根本不同。也可说两者之复,同来自《复》卦,但理解不同。
因此,与其说《易传》承袭道家,不如说儒道两家天道观皆源自《易经》,所谓“易老同源”说之易是指《易传》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易老同源,必须加上同源而异流,方才符合事实。何以见得?《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是说《易经》。儒家《易传》哲学与道家老子哲学也都讲阴阳,只不过儒是乾坤并建,阴阳兼重,但如不当其位,则阴阳皆贱。道家是重阴而轻阳。比较而言,儒家更合于《易经》原典精神,所以儒家为之作传,直接解《易》,属于继承发展;道家只取其一偏,故另起炉灶另建新体系,属于创新改造。儒道两家不可能不互相影响,但影响有多种形式,应包括反面影响,儒道思想正是从相反的影响中,互相论辩而相去愈远。一个思想体系,绝非东拼西凑(即使杂揉,也须揉而使之融合方可)可以建立起来的。所以不可看到字句相同便以为从另一家抄袭而来。而且孰先孰后,并无定论。即使论定,由于文字词语更多是公用的沟通工具,专用的概念范畴,也可能成为辨析争议的对象,同一概念范畴因之会有不同的解释与含义。即使含义相同,也还有个所以然之不同在。即使其有许多观念范畴相同,但这些范畴概念在其学派体系中所占据之地位,是否能影响到学派的主旨属性,也是应予优先考虑的。
按照这一原则,再分析一下《易传》“太极”的观念是否来自《庄子》。
《庄子》书的文句是:“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大宗师》);而《易传》的文句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通观上下文意,是论证语,一概念初次出现方有此句式。而《庄子》书之“太极”是现成语,即首先以肯定有此太极为前提,然后才可谈及有物在其上下。此又为否命题,按照逻辑,否命题当然出现在正命题之后。《易传》自太极以下,即是所谓道。而《庄子》之道“生天生地”,复在“太极”之上,是对儒家将太极置于最高地位的否定。所以太极概念的原创权还应属于儒家。太极作为本体的概念出现,当与《尚书》皇极观念有关,其辞亦由皇极演化而来。在《洪范》九畴之中,皇极是最具哲学义蕴的概念。然其所阐发乃中正哲学,与宇宙生成模式或本体论关系不大。惟其“皇极,皇建其有极”,与“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两语,予人本体论思维颇有启发。皇本训大,以此易彼而赋予新意,使成一新范畴,是完全有可能的。
儒家不具有原创性,本来是需要证明的论题,而在陈先生书中实际上成为前提。凡与其他各家共有的概念范畴,皆为儒家受之于他人。不仅《彖传》“时”的概念来源于道家《老子》、《经法》和《管子·白心》,而且《孟子》的天时地利亦来自兵家,是受战国时代“审势度势”思想的影响,而不违农时则“是受了管子学派和稷下学派的经济思想的影响”。总之,造时势者,虽有百家,儒家不与焉。那么,孟子所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岂不真成圣之趋时髦者了吗?
关于道家与黄老道家,司马谈明说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道家综合众家之长的一派,所取于儒家者正多。今反说儒家尚刚尚阳重时重义的观念,都来自稷下与黄老道家,将置服膺黄老的司马谈说于何地?正是因为黄老学派兼采众长之后,渐失老庄处柔守雌自然无为的宗旨,学派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原始道家之学反无传人,学派亦因之式微,固有其内在原因为之先导也。
太史公未将阴阳家归入道家,而其学已为道家袭取。《庄子·天下》说:“《易》以道阴阳。”道阴阳不等于就是阴阳家,可能是道家也可能是儒家。就像《易大传》论道,而非道家一样。儒家治《易》系统彰彰详明,见之于《史记·孔子世家》,哪一位是阴阳家?阴阳是当时之通识,要在于作何解释,如何利用而已。关心民情农事的儒家,岂得不通四时阴阳?“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阴阳家不过只是阐明事实,进而祈福避祸,使人动辄触忌,而未作超升之形上思维。建立天道人道合德之存在之价值者,是由孔子商瞿师弟相与论《易》而完成的。这一论《易》成果就是被称为十翼的《易大传》。太史公父子亲得其传,考订为八种。或以为太史公父子俱传史学,而其术不同,谈服膺黄老,而迁则属意于儒。但于《易》之所属,并无异辞。司马迁于《滑稽列传·传论》中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并将《易传》属之孔子。司马谈亦尝言之矣:“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通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六艺经传之简篇动以千万,故尔叹息儒学难于通习。《易》为六艺之一种,是其承认包括《易》在内的六艺为儒家世守之学,论学而首引《易大传》,而未闻道家有传《易》者。
关于古书学派属性的判定,首先,固然要根据历史的记载,但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其最高范畴,核心观念,即其世界观哲学体系,是由那些概念范畴组成,此而确定之后,其余概念隶属什么层次,哪些是原创,哪些是引进,引进后作了怎样的改造?虽属直接引进,并无改变,但只要与整体相统一,不相抵捂,也将无碍于成为其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之,不能将其肢解,以其一部分思想概念来自他家,而随意改变其学派属性。
其次,看其学术方向,即其社会历史观,其所设计的社会理想蓝图以及操作的方式方法,亦即其学其术到底要把社会引向何处?这是不能不察的,因为都属于确立学派所必备的条件。在这些方面,儒道名法墨,确实是界划清楚的。此其所以为不同学派也。至其命名,当然要以原始学派的性质而定。而其后学之徒的学派属性,就要视其与原始学派承袭的关系和程度而确定。如果其改变了以上两大方面之一,而又没有明确的解释,不能直通也非曲通,则其将不属于该学派必矣。
最后,还要考察其与既有历史文献的关系。应该说儒道两家,其思想来源之经典依据,皆为上古之两部文献,《书》与《易》也。儒家孔子受其熏陶而皆继承发扬之;道家老子所受影响,虽亦是这两部书,但各取所需矣。于《易》顺取者少,而于《书》逆取者多。此所以儒道殊途也。
以此原则律帛书《易传》与传本《系辞》的歧异,亦可概见其学派属性。据专家考订,两本固然有早晚之别,但也不排除并行之成分。“儒分为八”,当时理解或已不同;嗣后口耳相授,讹传自所难免,传抄之舛误亦可断言。更何况传习者,语音不同,性情有异,所受所解因之也就不同,加之多历年所,遂形成不同传本。但考其概念范畴未出儒家范围也。楚地固然为道家发祥盛行之地,然楚地亦不乏儒者,帛书《易》出于楚地便以为道家传本,其误已如前述。陈来先生齐鲁楚三派说可谓确论。[10]
关于学派的特质,不能将儒家说成仅仅崇尚阳刚,这只是就其与道家的纯任阴柔相比较而言。严格地讲,儒家是两者兼重。儒家理想的人格如《易传》所讲,是“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系辞传下》);又要“不刚不柔”(《诗·商颂》),“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认为“一阴一阳”同不可测(《系辞传上》),未发之前,无分轩轾;发用之时,所重所取之标准,惟在随时权变之中而已。真正只重阳刚主张用强的是法家,只主阴柔而用弱的是道家。“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狂者的阳刚之美,狷者的阴柔之美,皆为孔子所称许。如果与法家比较,儒家又显得注重阴柔了,因为法家是纯任刚阳。如果说道家不止老庄,甚至老庄不能代表道家主流,黄老学也是主张刚柔相济的,这就大谬不然了。一学派的定名往往是由原始名家及其学术的根本特征而定。如果失去了这一特征,也就脱离了这一学派,甚至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充足理由和条件。所以吾固曰:黄老之学兴而道家之学遂亡。
向见陈先生论《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引崔述认为《论语》是“孔子既殁数十年后,(按:不知为何非要待数十年门弟子星散之后?)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编”。“而《老子》则为老子所自撰,它的成书早于《论语》”。自撰书是否早于编辑所成书,暂置毋辨,奇怪的是陈先生论证的逻辑标准。陈先生说“先秦典籍引孔子说,无称《论语》者;唯《礼记》曾引述,而《礼记》编成于汉初”。但“《老子》成书甚早,从先秦各家多曾引述《老子》原文或论述《老子》思想可为明证”。前者是说书名,后者是说引文,不知如何可比?更有甚者,标题“古籍记载,与孔子同时的叔向曾引述《老子》”,而证据竟然出之于《说苑》。刘向编《说苑》于西汉末不知要比大小《戴记》晚几何年。《说苑》可以为据,而《礼记》不可,是陈先生论孔老用双重标准也。不意此一方法复见之于《易传与道家思想》一书。如说:“天行健(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蛊·彖传》:“终则有始,天行也。”“天行”二字,“悉为道家黄老学派所习用”(31页),其来源,当然也是出自道家典籍。如《十大经·正乱》“夫天行有正信,日月不处,启然不怠,以临天下”;《文子·上德》“天行不已,终而复始”;《庄子·天道》“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73页)。果真如此,则文、庄之“天行”又何从而来?《天道》篇历言孔子,独不受“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以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之影响?在陈先生看来,孔子的话,“只具常识意义,而无哲学意涵”(32页)。因此,虽字面相同,道家和《易传》也非受其影响。而“天行健”与《老子》“建德若偷”(四十二章)及“周行而不殆”(二十五章),虽文异而义同(47页)。这种随意性较强的双重论证法,如何让天下人折服?
总之,无论从著作成书年代、主要学术概念,还是学派特质诸方面分析,《易传》为儒家所著典籍,殆无疑义。因此,陈先生所说《易传》与黄老、稷下道家相同之处,只能说明是《易传》对这两派道家的影响,而不是相反。名家论学,往往如九方皋之相马,志在千里,而遗其骊黄(见《列子·说符》)。而今陈鼓应先生之立论也,则并良马与毛色两失之矣。
收稿日期:2001-05-21
标签:易传论文; 国学论文; 儒家论文; 陈鼓应论文; 论语论文; 战国论文; 孔子论文; 易经论文; 中庸论文; 道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