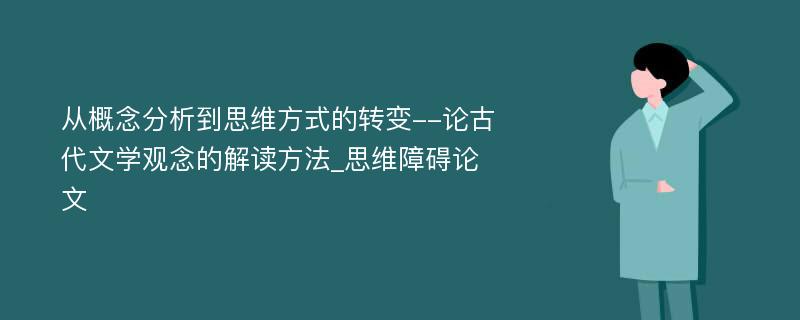
从概念分析到转换思维方式——试谈古代文学概念的阐释方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思维方式论文,古代文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1)03-0362-07
一
由于历史造成的语言、思维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许多概念都非常不好理解,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常用的基本概念,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最有趣的是,有些概念在没有进入理论上的界定、分析、证明之前,大家不仅在心理上对它格外清晰,使用时也极为得心应手,如同它们具有一种先在的自明性。但是一旦把它们纳入到理论的研究范围内,企图弄清它的本质属性时,就会事与愿违地引发一场百家蜂起的理论论争。结果也往往是:你不说我反而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争来鸣去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比如《文心雕龙》中的“风骨”,这两个字究竟是两个概念还是一个概念,究竟是以“风”为主还是以“骨”为主,在明清时代就产生了分歧。建国以后,学术界对“风骨”涵义的不同解释据统计不下20余种,其中又分为形式内容说、缘情体物说、风格说等。有的在分而论之遇到障碍时,便会回到“合”的立场,如认为它是对理想作品的总体的审判规范。对这种问题学术界素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是因为“科学化”的程度还不够,只有使用更加科学的工具和方法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另一种则与此截然相反,认为来自西方的那一套工具本就不适应国情,因而从逻辑上说也就不可能把问题解决掉,反而只会增加更多的紊乱和障碍。前者明显带有强烈的科学主义的色彩,因而它在一些时代很受重视,比如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代学者们;后者则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们把文学看作是国家民族的象征,因此反对科学主义的实质也就是在文化战线上的反殖民主义。这里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个具有前提性的问题,即采用科学主义的方法,把中国古代文论当作科学分析的对象,这种作法在逻辑上有没有先在的自明性。这就不再是去考问科学主义的合理性或局限性;也不再是去追究民族主义骨子里的保守性。这些不仅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它们应该属于社会学或文化学的研究课题,而不应该被搅和到古代文论里面来。
因此,在这里我们要反思的就不是认识论的问题,不是去考察哪一种理论方法更有利于古代文论讲得更合理一些(亦即更符合我们的现实需要);而是要对方法本身作一本体论的考察,它可以表述为,一般解释方法自身是如何可能的?或者从古代文论存在论的角度追问它自身的“敞开”、“显现”是如何可能的。
追索这问题时,我们首先碰到的是这个问题的不可能性。阐述与理解的问题,在中国哲学与文艺理论中即所谓的“言意”之辨,它本身就属于那种“越讲越糊涂”的话题。关于语言符号能否完整传达出人心中的意义意味,中国的大多数思想家和艺术家都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言不尽意”。这一方面我们也不再赘述,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以玄学对玄学。比较可观的,我以为反倒是西方那些从理性迷梦中走出来的叛逆者。例如柏格森就曾以小说中的人物为例,指出了依靠语言符号的媒介,我们只能“围绕着对象转”,而无法从内部来把握它,他说:“这些符号和观点是把我放在这个人物以外;它们向我提供的,只是它与别人共有的、并非专属于他的东西。但是那个是他自身的东西,那个构成他的本质的东西,由于按照定义就是内在的,我们是无法从外面感觉到它的,由于它与任何东西都不能通约,我们也是无法用符号来表达它的。”[1](PP.135-136)从中可以知道,在言与意、符号与实体、意识与对象之间横隔着一条无法穿越的领域,它是使不同的事物获有其各自本体性的基本保证。有了它的存在,不同的事物即使再接近也不可能完全合一,这就像中国哲人讲的捉鱼的工具,即使它天天都能捉住鱼,与鱼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它毕竟不是鱼本身,同时它也无法满足人对鱼的需要,所以人们在捉到鱼后仍不可避免地要“得鱼而忘筌”。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片无法穿越的领域也就是哲学家康德指出的人的认识能力与“不可知”之物之间的鸿沟,另一方面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类一直要努力冲破的樊篱。人们不能承认这样的事实: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及其最骄傲的理性在这个世界上还要因受到限制而有所顾忌。所以自从人意识到他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那一天起,他就一直要证明自身的无所不能。而语言文字则被看作是人的理性能力的集中表现。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原始时代的“咒语”或“文字的灵物崇拜”中看出来。在巫术思维中,事物的名称是任何事物存在的核心所在,所以不仅被掌握了名称的动、植物,马上就成了人类的亲属,从此不再危害人类;而且人一旦不小心“丢了”自己的名字,其后果也往往是灾难性的,因为其仇人将会用法术加害于他。固然我们可以说这完全是原始思维不能够区别开思维与存在的结果,也只有在这里才有着思维与存在的绝对统一,这也是后面将要讲的海德格尔所追求的“思”的人类学基础。然而我们不要忘了,原始时代的这种精神结构,在几乎所有的场合正是我们嘲弄、急于与之告别的“愚昧”、“落后”、“野蛮”的东西。这是一切古代文化遗产的共同命运,古文论亦如此。我们根本不顾它们的发生背景和其自身的存在方式,强行施以科学主义的诊治和解构,让它们来适应理性的标准,甚至以为这样做是给它们带来“第二个春天”,以便使它们在第一个春天里低层次的、混沌的、粗糙的感性形态,在理性的太阳下,长成具有现代性的、清晰的、精致的科学形态。这种思潮在某种意义上又迎合了整个现代世界的科学化进程,因而也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很少有人想到要去追问一下这种作法是否具有逻辑上的自明,或者说虽然有极少数的人问了,但却在科学时代的众声喧哗中被淹没了。
这也就是说,我们在阐释古文论时所遇到的困难,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研究自身,它在更深的意义上牵涉的是人类理性本身的有效性及其局限性的大问题,或者说我们信仰的科学主义和所使用的理性分析方法是否真的具有无须追问的自明性。我们现代人的思维、价值观念以及我们的认识方法对古代的文化遗产是否有效,是否能正确认识和阐释它们,倘若认真追究起来,它是没有任何自明性可以作保证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对象是死的,它本身已无法回应或反驳,这种死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过去的事物,而且科学主义的逻辑要求它必须是死的,那样人的理性才能畅通无阻和建立其权威性。这一切从表面看来似乎已完美无缺了,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虽然所研究的对象是死的,也不再分辨什么,但研究者却是活的,他自身作为活的生命所不可缺少的个性与主观性仍无法被消灭或被整齐划一,这就使研究结果的歧义性和多元性具有了逻辑上的必然。面对同一个对象,使用相同的概念分析操作方式,居然常常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实在是对理性主义者的莫大讽刺;而有时为了达成共识,人们不得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强行规范个体的意识活动。但是意识形态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每一次变化都会给古文论的研究带来巨大的震荡,这往往使学者们应接不暇地进行平反昭雪、重评重估,推翻一种受旧意识形态支持的理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学说来支持新的意识形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表面看着虽极热闹,但对于古文论研究本质上的深入却十分可疑。这里应该补充一点,不仅仅是如郭沫若与萧涤非那样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对杜甫可以有完全相反的评论;还应该包括、或者说更有现实意义的是我们近年来不断引进的西方思潮在古文论领域所引发的变革,尤其是各种新方法自身的问题。我这里主要不是指懂不懂外文或是否读懂了原文,正如我们在前面的反思,它是针对着科学方法本身而言的,亦即这种概念分析方式对中国古代人的文学经验以及其理论结晶是否具有逻辑上的自明性。
二
20世纪的中国古文论研究,其方法论最显著的变革即以概念分析为中心的科学方法取代了传统的以直觉感悟为核心的诗学经验方法,而建立一套古文论的科学形态也早已成为共识。在强烈的现实需要与文化利用的驱动下,很少有人会想到再去追问它在逻辑上的自明性,当然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人们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不到这种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对科学主义方法论的怀疑和追问,实际上也是从西方的“自我批判”中受到启发的,尤其是西方19世纪末以来那些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尽管我们可以引进大量的西方新思潮,也可以把它们一个个地在中国古文论的园地里作实验,甚至在表面上也带来了新一轮的热烈争鸣;但是由于我们依旧没有考察过其方法论自身的合理性,所以学术界的讨论仍然更多地局限在方法论的范围,如方法是否适用,是否被真正掌握,以及在对方法的理解上是否能够一致等。而一旦人们对新概念新方法的新奇感和陌生感消退,蓦然回首却发现,虽然我们拥有如此多的理论工具,但遗憾的是我们在古文论园地里的所作所为却乏善可陈,这尤其表现在新问题的提出以及在旧问题的深入上。对问题的疏离在更深的意义上它表明的是古文论研究远离了其对象的具体存在。“思维无对象则空”,这是它的必然性命运。
一种号称科学的方法为什么没能深入到对象的内在性之中?先进的理论工具又为什么不能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更为直接的联系,所有这一切困惑和疑问都要求我们必须回过头来,重新思考一下我们过去极少注意的一个具有前提性的问题:这就是在某种领域使用某种方法之前,必须要对方法本身是否具有逻辑上的自明性进行严格的考察,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种方法在现实过程中的有效性。从相反的角度来说,这么做的目的则是要正确认识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因此,对古文论中最为普通的概念分析方法进行一种前提性的分析考察,其目的也不是要否定该方法本身(因为这种方法在现代世界所取得的成功早已众所周知,这也正是一切针对它的民族主义的批判不能叫人接受的原因),而只是要检讨一下它在古文论研究范围之内有无合理的存在根据,或者说它是不是所有可能的方法中最好的那种。进而言之,如果说概念分析方法已成为文明时代的主流而我们根本不可能罢黜它,那么我们在使用它时还必须注意些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先行考察,将会对我们的古文论研究产生重要的帮助,尤其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本文在一开始所指出的那种现象,即当我们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去处理一个古文论概念时,为什么会出现越分析越混乱的尴尬局面。
对分析方法本身的怀疑和追究,在哲学史上当然要首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早期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影响,后者正是通过对理性主义(其核心为二元论)的批判性考察确定了它的有效性,指出“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只是“人种偶然的特性”,“认识只是人的认识,并束缚在人的智力形式上,无法切中物的本身的本质,无法切中自在之物”[2](P.23)。这一观点对于限制欧洲哲学史上自17世纪以来理性主义的极度扩张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重新在思维与存在之间作了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区分。沿着现象学对理性进行限制的思路,海德格尔进一步贬低了理性在哲学中的地位,打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旗帜,他的意思是说,前者是属于自然的存在本身,后者却是理性思维关于存在的“表象”。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前者也不可能通过后者敞亮、澄明自身。相反的是逻辑思维和理性化的语言只能遮蔽人的真实存在。人在理性化了的各种交流媒介中,也不可能发生具有本真意义的精神交往。人在日常世界中使用的理性语言被海德格尔称为“闲谈”,它“对本己的自我充耳不闻”[3](P.324)。而真正的交流应该是“把言谈时‘话题’所及的东西公开出来”,是“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来让人看”[3](P.41)。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同“存在”本身进行交流。为了放弃这种理性化的语言及其交流方式,海德格尔积极努力把诗的语言以及诗人的思维方式引入到其哲学系统之中,希望以此来改变西方哲学过度的理性异化现状。而在晚年他的看法似乎更加悲观,他认为交流的障碍正是语言本身,它在有所表达的同时又必须有所遮蔽,所以人们永远不可能达到“言尽意”的境界。由于语言本身的这种局限性,所以任何阐释、对话、交流的真实性显然就缺乏一种不证自明的前提。由此看来,我们古文论研究中的各种歧义、误解、含混不清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从逻辑前提的角度来说,理性主义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它缺乏一种自明性的前提,这并非是说它从来就是这样,而是说它在逾越了自身的界限之后丧失了其自明性。比如它的概念分析方法,它在自然科学中自然有它无须分辨的自明性,而一旦它试图进入人文和艺术领域,这就首先需要进行论证才行。但是依靠着科学在近代取得的辉煌的物质文明成就,它作为一种被认可了的万能的“技术”手段,不经任何论证就闯进了精神的领域,并蛮横地把精神存在变成它研究分析的对象。所以海德格尔曾尖锐指出:“甚至人变成主体而世界变成客体这回事,都已是技术的本质是把自身设施出来的结果。”[1](P.378)海德格尔的这些思考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西方哲学与文艺理论,而在中国古文论中较早对这个问题有所觉察并给予较多注意的当是海外学人叶维廉。叶维廉认为,当人们把概念分析的方法用于中国诗歌研究之时,它实际上同时肯定了这样几个前提:
(1)观物者是秩序的赋予者,真理的认定者;(2)理性和逻辑是认知真理的可靠工具;(3)主体(观者)是拥有了先验的综合知识的理力(柏拉图所认定的知智;康德的超验自我);(4)序次性的秩序和由下层转向高层的辩证运动;(5)抽象体系比具体存在重要[4](P.43)。
其实稍加追问就不难发现,这些前提并不具备逻辑上的自明性,尤其是对于重直觉非知识,重灵感非思辨,讲求天人、物我、情景合一的中国古典诗学。所以上述的第一和第二条根本就靠不住,恰恰相反的是,中国诗人为了抵达物我合一的精神境界,经常自觉地消除其主观性,这就是庄子《齐物论》中所谓的“吾丧我”,而几乎中国古代所有的艺术家都从这句话中受到启发,并贯彻于他们的艺术实践之中。虽然中国诗人有时也会讲到主客关系,如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中曾写道:“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但是,这里的“客”不是西方那种与“主”相对立的存在,更不是主体为了“它自己的存在”而必须要“扬弃那另外一个独立的存在”[5](P.123);它是以一种贵宾的身份到场的,它不仅与主人一样拥有平等的地位和尊严,而且,它时常还要比主人更高一些,因为它更是主人要亲近、学习和向往的存在。在这种语境中,主客之间的关系已超越了矛盾对立,进驻到和谐统一的层面,它们互补同构为一个有机整体,一方的本质性以另一方存在的圆满性为依据,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倘若再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着眼,这个问题就会看到更加清楚。理性思维的基础是二元论,而诗性思维的基础是一元论。前者的目的在于要解析出对象身上所具有的那些合主观目的论的性质,以便加以利用,它在物我之间奉行的是一种“货物交换价值的原则”;而后者的目的在于放弃主观性并以此举措来取消物我之间由于理性的片面发展而造成的分裂状态,以便复归它们之间源初的同一性,因此它遵从的是一种和平共处的交往原则。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也可称之为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对立。由于理性思维完全以人的实用目的为价值标准,所以它只注重“物”之“理”这种属人的抽象形式(“物”之“理”也就是“人”之“理”),甚至为此目的而有意漠视、扭曲、改造“物”的具体存在,在理性世界中,这种作法是倍受赞誉的。这也就是叶维廉所指出的“抽象体系比具体存在重要”这一理性思维的原则。但是与前面的第一、第二条一样,它同样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尤其是对于诗人来说。例如,原始思维根本就不注重乃至有意忽略主客观之区别[6](P.30);而秉承着原始思维血统的文明时代的诗人,无论中西历来也都一致地被看作是一种“非理性”或“不可理喻”的存在物。中国诗学还认为不独写诗要“不涉理路”(严羽《沧浪诗话》),解诗亦然,同样“不可于名物上寻义理”(《朱子语录》卷一一七)。因此可以反问:诗人关注的本是具体存在,所使用的也原非理性思维,那么,上述的第一、第二、第五等是如何能够成立的呢?即使它借助某种现实需要得以建立起来,但又如何能够长治久安呢?
所以,中国古文论研究也就难免于古人所说的“死参”之忌。例如,中国哲学和文艺理论中经常碰到的“气”,用概念分析的方法,首先就要去追问它到底是精神性的呢?还是物质性范畴?如果从孟子那里出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意志力(“浩然之气”),即看作是精神范畴,但再用它去解释《周易》的唯物论之气(“阴阳”),马上就遇到极为不利的反证。这并不是概念分析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它本不适用于研究对象,因为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与未有主客之分、“未始有物、未始有封”的原始思维更接近[7](PP.77-82)。这种古今的交流障碍,就其是两大不同的存在结构之对话的角度,也就类似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语言障碍。因为所面对的只是已被抽象掉背景的纯粹符号,而不是可以直观的事物本身,这就往往会发生驴唇不过马嘴的误解。鲁迅曾举过一个误译的例子。西文中有一个词,写作"Milky Way",从字面上可直译为“牛奶路”,但是实际含义却应是“银河”,因为它与一个古希腊神话有关,在古希腊神话中,银河乃是由于天后赫拉的乳汁喷洒而形成的[8](P.347)。当然,这也可看作是由于注重“抽象体系”而忽略“具体存在”所导致的一场闹剧。它的真实性、可靠性不是非常地可疑吗?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很多参加过批改古文翻译试卷的老师都有过这种经验,批改过程中常常会有驴唇不对马嘴的译文叫大家忍俊不住。其实我时常感到,也许当今的古文论研究在古人看来,与那些学生的答卷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因此,古文论研究中的概念分析方法,由于它不可能有其逻辑上的自明性,故在本质上可以把它叫做“硬译”方法论,它并不是一种最好的、也最适合其研究对象的理论工具。
三
直面真实存在的问题,当然不是为了否定理论研究的价值,恰恰相反,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要为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逻辑基础。为了达到理解、阐释、交流和对话的真实性与可能性,前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们的探索对于我们所面对的“摆脱概念分析方法之后向何处去”这一现实问题,是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一番梳理与检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德格尔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海德格尔对语言的交流问题是非常悲观的。在此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他的悲观主要是针对语言在现代社会中过分的理性化状况,是针对在文明世界中培育出来的语言“分析本性”而发。由于这种语言无法接触到事物的存在,它只能围绕着作为人的主观表象而存在的“对象”转,无法钻进事物的内部,所以它始终局限在人的主观性范围之内。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任务不是整天作符号游戏,而是要“面对事情本身”,所谓的“事情本身”,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事物在人的思维中那种“观念的运动”,它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澄明”,“澄明即自由的敞开之境究竟是不是那种东西”[9](PP.66-69)。也可以这样注释,所谓的“自由的敞开之境”,主要是指一种不带有任何知识的、理性的、主体的等先在因素的语境,因为海德格尔认为“理性之光”,不仅不关注存在之澄明,反而正是由于它的投射和“取象”,遮蔽了存在自身之澄明。我以为,澄明更汉语化的表述是“明”,明字从日从月,它表达的是“物”在自然天光中的显现,是生理性的“看”或摆脱了理性束缚的感性直观,如俗所谓的“眼见为实”。质言之,它就是事物自身表现自身。从相反的、同时也是海德格尔特别强调的方面看,它就是放弃逻辑化了的思维和理性化了的言语之后的那种诗的语境。
海德格尔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看来,要彻底避免思维的逻辑化,就要采用诗人的诗性思维来思考存在;要彻底避免语言的理性化,就要返回到语言的原始形态中去。这两者实际上又是一致的。海德格尔的建设性工作也主要在后者。返归语言的原始形态,在学理上的根据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即原始语言与原始存在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前者就是后者的“澄明”。这种原始的澄明之所以在后来变得晦而不明了,是因为理性的积淀埋葬了人的本真存在。由于这种理性化是从古希腊柏拉图时代开始的,所以重新追寻语言的本真意义也要以希腊语的讨论为起点。他是希望通过改变作为思维媒介的语言的性质来改变逻辑思维的存在方式。这就是海德格尔,特别是在他后期每个语词必以其古希腊语义为标准的原因。海德格尔对于我们的启示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如果要避免理性思维的局限性,不是在它内部进行更为周密化的安装和改造,而是必须转换这种以概念分析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本身。
其次,同样的情况还可从人类学家那里看到。在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中,曾经弥漫着一股极其浓厚的欧洲中心论色彩,他们把欧洲式的生活方式看作是文明的顶峰,把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当作真理的标准,以此为前提把其它的文化和文明统统贬低为野蛮的、落后的、愚味的社会形式。因此,在早期的人类学著作中,曾一度充斥着种种对非欧属文明的轻率的论断、漫画式的扭曲和强烈的殖民主义解释。这种研究与前文讲的理性思维对古代文化的做法是极其一致的,他们在逻辑上本来也就是一个系统。但是随着欧洲中心论这种曾一度具有自明性的理论前提的破产,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放弃其固有的观念,不再把非欧属文明看作是欧洲文明的低级阶段,而是看作一个个独立的文化系统。为了能够真正地理解这些文化,他们放弃自身的语言系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深入到一些原始部落中去,“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便对他们所研究的文化现象达到直接的认同。这就是所谓的“与调查对象共同生活的研究方法”[10](P.311)。为了真正地认识对象,或者说为了同存在的真实性发生关系,人类学家曾设计了多种方法用来限制其自身的主观性。然而犹有不胜之处。这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所指出的,“人类学家是人。他不可能完全抛开他自己的感情与偏见,因为这是他的文化塑造成的。他要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意识到这些东西,这样才能使它们受到控制”[11](P.253)。这样,人类学家所提供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充分控制我们自身的主观性,以便使学术研究更具严肃性。
第三,回转到中国古文论研究的历史上来看,应该说,限制论者的主观性,充分尊重对象自身的存在背景,这正是我们一个悠久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在于:如何训练一种能够直接认同对象的思维方式,以及如何结合对象的存在背景来把握它。庄子强调的“心斋”、“目击而道丰”属于前者;而孟子所主张的“知人论世”说则属于后者。后人所谓的“论从史出”也庶几近之。这种学术方法在近现代又有着长足的发展,例如,章学诚讲的“六经皆史”,就是要求摆脱封建时代经学研究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教义,而从社会的和历史的角度去接受古代典籍。由他本人所开山的“浙东史学”,创立了集考订(历史资源)、辞章(历史语言学)、义理三位一体的“实学”方法论[12](PP.275-279),至今犹广有影响;又如国学大师陈寅恪著名的“诗史互证”的、融考据与历史为一体的方法,或纠旧史之误,或补史料之阙,使千载之前的社会生活历历在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尝自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他的意思是说,研究古代易受史料残缺之影响,而研究当代又易受感情之困扰,都不易做到客观公正;还有另一位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所创立的同样著名的“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推崇和运用;在当代的新一轮的国学热中,叶舒宪等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所谓的“三重证据法”,在王国维的方法之上又加以人类学的方法[13](P.3)。所有这些方法的创新和应用,它表明的是这样一种自觉的意识与追求,即要对论者的主观性进行必要的限制,以避免把我们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古人及其文化,这种方法在逻辑上可以表述为:用存在的自身显示它的存在,用真实的历史思维显示历史的真实存在。因此,学术研究的目的也就不再是对历史的“文化利用”,以避免把自身功利性的“善”当作是最高价值,而是把客观存在的“真”做为思维的目的。这当然与海德格尔的“澄明”有殊途同归的性质;同时,它也是中国古人所强调的“注古人者”“当以古人还古人”(周亮工编《尺牍新钞》二集)这一治学态度在现代社会中的延伸。
在本世纪前期,郭沫若曾经感慨,“材料的真伪”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14](PP.3-4)。其实,现在还要强调的一点是,不仅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伪材料危险,而且那些没有逻辑依据的假思维也同样危险。因为它同样会使我们的研究处于一种无根的基础之上,从而丧失它的真实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中国古文论研究,在其方法论上很有必要进行一场具有根本性的变革,而其核心之处,则可以描述为从概念分析到转变思维方式。只有化自身为对象,才能突破科学主义及其逻辑方式的根本性局限,达到最高意义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一种天衣无缝式的原始统一。虽然这种纯粹的统一或“无差别”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把它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则正是走在通往真理的大道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收稿日期:2000-08-03
标签:思维障碍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文化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哲学家论文; 古文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