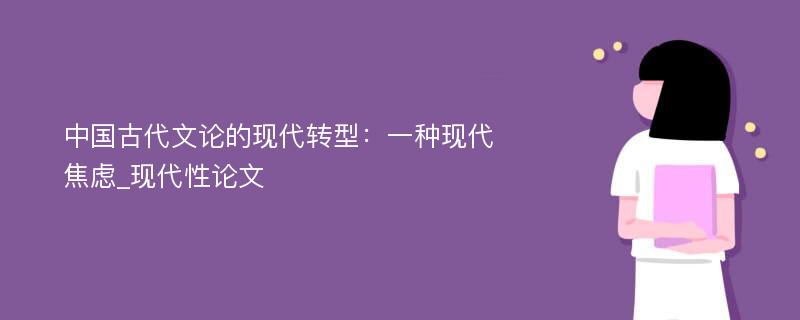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场现代性焦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性焦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9)04-0048-06
十几年前学术界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后,学者们很快把眼光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当代命运,希图对这份仅属于本民族的思想文化遗产进行重新编程,升级为现代版本: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题由此应运而生并成为热门话题。但十余年过去,未见有以古代文论为理论话语基质的文学理论成型,也未见有以诸如载道、言志、风骨、神韵、妙悟、格调一类术语组合而成的概念系统进行有效的文学批评。倒是在“现代转换”这一口号下学人们持续地发表着各种关于当转换或不当转换、可转换或不可转换的高见。主张“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者情真意切、迫不及待,反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者则愤世嫉俗、谨守国粹。如此生动的学术文化景观,令人从中品味出五四至今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的一场历史大戏——现代性焦虑。
一、本土文化身份的失落与寻觅
作为后发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中国现代文明史就是一部追随并摹仿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而且这部历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现代性焦虑”。现代性焦虑最早表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口号。“体”、“用”二分实际上意味着“真理”与“方法”的分裂,这种既要维护本土核心价值观又要运用外来文明的技艺制造财富的心态,导致洋务运动时代的知识分子惶恐不安地游走于忠孝节义和坚船利炮之间。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深陷这种现代性焦虑之中,他们大胆地引进西方技术,同时也坚定地维护古老帝国的核心价值观。他们无法理解现代性在科学技术和宪政民主两大领域里的胜利实际上是同一个方案的两个结果而已,所以他们的内心肯定充满改良的激情和对结果的惶恐,只能谨慎地去缝补儒家伦理与工业技术之间的裂隙。19世纪晚期以来,洋务运动时代知识分子的这种现代性焦虑在中国知识界的现代性进程中持续地存在着。
怎样在保持文化身份的民族同一性的基础上实现富国强兵之梦,这是洋务运动提出的一个尖锐的问题,也是一百多年来一直困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难题,进而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现代性焦虑的根源。从洋务运动与立宪派的分歧到“全盘西化”与现代新儒家的分歧,延续至今日知识界关于普世性价值的讨论,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一直浸泡在这种现代性的焦虑之中。当我们竭力追逐西方现代性的技术成就时,我们害怕它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当我们精心维护本土文明的核心价值时,我们又害怕它变成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障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崛起遭遇西方霸权的全球化浪潮,我们重建民族文化身份同一性的诉求遭遇西化的理论话语统治,这种现代性的焦虑越发剧烈了,因为引发焦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曾自信地写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1]209不过洋务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像张之洞想象的那样能够二者兼顾,相反却滋生出一种两难的焦虑。直到现在,新自由主义和新传统主义在“普世价值”等问题上的针锋相对,仍然有当年的影子。当代知识界固然不会再为是否引进工业技术而焦虑了,但是面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现代性工程时,我们所遭遇的价值观层面的两难处境更加难解:一边是“先验理性”、“自由意志”、“普世价值”等等,一边是“精神家园”、“民族传统”、“文化身份”等等,当代中国思想界每天都在左顾右盼地找寻兼容两端的新理论,但谁也没有了张之洞处理“体”、“用”二元关系时的那份自信。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及其前奏“中国文论失语症”,都是由于现代性焦虑而生出来的某种自我塑型的诉求。其外表形态是学术话语,而其内在动机则是文化身份失落后的寻觅。
曹顺庆先生将“中国文论失语症”视作一种“文化病态”[2]。提出“失语症”问题十年后,他在解释“失语症”的病因时指出,“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病因在于把中国文化同现代化对立起来,进行文化上的“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我丑化”[3]。真正令曹顺庆忧虑的是中国现代教育对传统文化的忽视,而他寄希望于救治“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办法也是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由此可见,“失语症”提出者们想说出的不是学术上的发现,而是文化上的焦虑。所以学术界有人认为“失语症”的提出是后殖民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结果[4]。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现代性霸权面前自感被“他者化”的学人们当然会对话语权问题倍加敏感。
继“失语症”问题之后出现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则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主张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和反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人都认可一个现象,即西方文论及其摹仿者占据中国文学批评舞台的情况是不正常的。这一点正好反映出两大阵营的学者都未跳出现代性焦虑的宿命,只是各自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有所不同而已。第一种方案是要正面对抗西方现代性的霸权,方案制订者们意欲通过改装自己手中的武器占据与西方理论平等交往的地位;第二种方案是彻底拒绝西方现代性的诱惑,方案制订者们希望通过维护文化身份的纯洁性达到话语权的自我确证。其实这两种策略在中国的现代性焦虑诞生以来一直都存在着:当年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是急于把中国转换成能够与西方平起平坐的现代性国家,而现代新儒家则力图回到宋明理学以维护前现代性的生存方式的合理性。在西方的现代性面前,他们都害怕自我的失落:
后发现代性社会语境中的我们,必须认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在现代性方案的展开历史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这一宿命无法超越,所以我们的焦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再造新异原则
阿多尔诺在论述现代性时用“新异原则”来概括审美现代性的特质。在阿多尔诺看来,从古典的和谐整一走向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就是新异化的意义经验取代前定规范被赋予普遍性的价值,这一点也得到T·贡巴尼翁的赞同。后者在《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中视“新之迷信”为现代性的第一个悖论[5]5。科学技术使得人类进入工业产品构筑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因为科技的快速发展而日新月异地变化其形态,所以,现代性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以时尚见长、现代性世界中的思想以新奇见长、现代性世界中的艺术以反传统见长……,现代性的世界充满了对“新”的崇拜。现代性本身就是一部不断创新不断改变永无止境的“浮士德”历史,这样就产生了A·吉登斯所描述的那种“自反性的现代性”——为创新而不惜破坏既定的自我。但是,中国古典文明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稳固型文明结构,新奇和变异很难为这种文明形态所接受。现代性传入中国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又生出了一种焦虑,它表现为两种思想诉求的激烈对立:以不变应万变和以万变应不变。前者超然物外地坚守着绝对的自我,后者则坚定地追寻与时俱进的变革。
李欧梵先生指出:“自晚清以来,日益面向前的思想(以区别过去面向经典儒学的总倾向)无论从字面还是从比喻的意义上讲,都充满着‘新’的内容;从1898年的‘维新’运动到梁启超的‘新民’概念,到具体表示‘五四’的新青年、新文化和新文学,‘新’这一形容词几乎伴随着所有的社会和知识界的运动,使中国摆脱昔日的桎梏,从而成为‘现代’国家。因此,‘现代性’在中国不仅意味着对当前的专注,而且也意味着放眼求索‘新意’,从西方求索‘新奇’。”[6]后发现代性国家对新异性的追求,其强烈程度不亚于那些现代性的先驱者,因为落伍的感觉使他们迫切地要求改变现状,走出先前历史的惯性。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展开了一场被称作“改革开放”的现代性工程,这场工程以史无前例的姿态致力于革新,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面貌在这期间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因为革新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其必然的后果就是新异原则成为人们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涵,从对新奇事物的宽容到崇拜一切有新意的事物。同时,“现代化”、“现代意识”等术语也成为了近三十年来主流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在奔向现代性的道路上,人们唯恐自己缺乏求新求异的能力,因为这本身就是落伍。而在思想文化界,新异原则促使知识分子们不断地追寻新的阐释技术和理论话语,不断地转换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
中国的文学学术也是在求新求异的呼声中走过这三十年的历程的。三十年来,我们像近代史上的那场西学东渐运动一样,“别求新声于异邦”,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性西学东渐运动。这场运动的历史背景是极左时代的僵化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规训与惩罚导致人们强烈地要求变革。在我们无法自力更生地提供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的处境下,大规模地引进西方近现代的理论话语就成为了迅速接近现代性的最佳方案。况且近现代西方理论话语的特质就在于其突出的创新性。
在文学理论领域,上世纪80年代各种新奇的西方现代文论前赴后继地涌入中国。新奇的术语、新奇的视野、新奇的观念等等,的确让中国学人感受到一种走出藩篱、卸去重负的畅快,他们前所未有地体验到了一种现代性的经验,即新异感。也正是在这现代性的意义经验——新异感——的诱惑下,文学学术界和文学批评界争先恐后地寻求理论话语的转型。学者们陶醉于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新方法新论题新视野之中,整个文学学术界像中国的经济一样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在文学学术的几大专业中,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因为与西方或中国当下文化现象密切相关,其新异性的现代经验可以直接从研究对象中获得;文学理论专业起着为文学研究提供元话语的作用,它的求新求异系其天职,否则文学学术的创新便失去了原动力;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属于历史学科,其研究对象永远不可改变,它的新异性现代经验来自于从文学理论那里引入新的阐释技术来解读文本,或来自于发现新的历史文献资料。唯有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它似乎介于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两大学科之间。这就是说,作为经验学科的古代文论,其新异性的现代经验可以通过引入新的阐释技术来解读那不可“转型”的对象——古代文论文本——而形成,但这样做则意味着它放弃了作为理论学科的那种创造新的理论元话语的功能。古代文论到底是一种研究对象还是指导研究的理论话语?是用现代文论话语对之进行研究以形成学术创新的价值,还是将它本身转变成一种新的理论话语以指导文学研究?这种学科身份的两难定性导致了古代文论学科创新性问题上的疑惑。
大多数主张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学者都毫不隐讳地声称“‘古代’文论通过不断地调整它丰富的姿态而跻身于‘现代’思想”[7]。但作为一种经验研究的对象,为其注入新的理论元话语,促使其产生新异性的现代经验,这种所谓的“转型”是颇令人怀疑的,因为这一做法事实上是把古代文论当成了纯粹的“理论”而异化了它作为历史事实的对象性特质。也正是因此,急于求取创新性的学人们至今仍然未能做出“转换”的产品来,仍然处于为创新而“构思”的焦虑之中。
三、当代语境中的阐释有效性
马尔库塞和阿多尔诺都把理性的工具化视作现代性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在他们看来,现代性起源于人类依照自己的功利性目的对自然进行改造的活动,这种为实现功利性目的而展开的活动在为人类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得启蒙理性堕落为工具理性。利益、利润、效率、成功、财富等等成为了现代性社会中人们的一种主流价值观,主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生活的批判性反思中,主体性形而上学也是导致现代人用技术改变自然的原生态,从而让大地进入贫乏的黑夜的原因。
加拿大学者伊芙琳·格伯雷借分析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小说《洼地》反思了现代性因理性的工具化而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效率的意识形态”[8]。在伯格雷看来,“效率”一词是19世纪机器对自然的主宰时代出现的,该词表现了人对于使用技术手段控制和改变自然以获取满足自身需求的物质财富的肯定。随着现代性的展开,“效率”成为一种价值评价的准则,继而它发展至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
早在狄更斯的笔下,作为具有询唤功能的意识形态的“效率”就受到过尖刻的嘲讽。在《艰难时世》中,狄更斯描写了两个信奉边沁主义价值观的企业家。他们用利润评价一切,用数字衡量一切,所有的人间情感对他们而言都纯属多余;用这两个人物来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作注解是再合适不过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恰恰是现代性对技术理性的肯定以及引导人们将价值准则从超验神学回归日常生活,这才有了现代社会的繁荣和富裕。所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急于摆脱贫困而全心全意地追随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并不特别关注,相反却坚信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化的知识有助于摆脱“士文化”清谈误国的窘境,因为经世致用的知识能够带来国家富强的“效率”。80年代知识界对古代士文化的批判使学者们开始关注近代“实学”的兴起,他们认为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最早的现代化吁求。这些批判背后的思想动机在于通过知识的“效率”化寻找通向现代性的道路。
意识形态化的“效率”概念不仅导致现代人的价值观回归日常生活并受到物质财富的获取与占有的主宰,而且它也渗透到知识活动之中;现代性以工具理性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引向实用化。20世纪人类知识活动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实用型知识成为主导性知识,二是人文知识走出思辨模式转而寻求一种对实证事实具有阐释效率的分析技术。阐释的有效性在20世纪下半期的人文知识活动中上升为普遍价值准则。知识分子们不再追求关于宇宙或历史的终极真理式、最高立法式的解说,而是动用某种分析技术展示日常生活的意义。这种转变的根源乃在于现代性赋予的“效率”概念。因为追求效率,我们把高雅的古典文化文本变成大众文化文本来解读,就像地方政府热心于发掘本地的历史文化来制造有“效率”的文化产业一样。
因为追求“效率”意味着进入现代性的殿堂,所以当代知识生产的各个专业或学科都将自己的理论话语指向现实世界的诸种实践性的现象:都力求使自己变成“有用”的知识,谁也不愿意被冷冷清清地摆放在典雅的博物馆中。在种种现代理论轮番登台竭力展示自己对当代文化实践的“阐释有效性”的学术语境中,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感受到了“寡居”的苦闷。连先秦神话的研究都可以向原型理论“转型”,那么古代文论作为文学理论学科的阐释有效性更应该得到彰显。于是,在唯恐失去对当代文化实践的理论影响力、变成“无用”的博物馆展品的心态下,中国古代文论学科提出了“现代转换”的诉求。
“失语症”的诊断本来就是出于对中国文论丧失了当代语境中的阐释有效性的忧虑,而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则更进一步地涉及到了所谓“古为今用”的问题。论者们急于将冷兵器时代的古董改造成能够作用于现代文化战场的独门利器,从而展示出古代文论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效率”。1997年,有论者提出要对古代文论进行“开发利用”,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创造性地发展古代文论,利用其理论资源来建设现代文艺学,总结和指导当代文艺创作实践[9]。可见人们不满于古代文论的“花瓶”地位,硬是要在这花瓶上安装几盏现代性的效率之灯。还有一位论者的设想更显功能主义特点,他主张古代文论应当飞入寻常百姓家,与音乐舞蹈书画工艺园林甚至化妆服饰等联系起来[10]。现代性的效率概念只允许那些具备阐释有效性的理论话语在当代文化舞台上引领风骚,而现代性的巨大诱惑力让知识生产者们为走上当代文化舞台殚精竭虑,甚至不惜来一场“SHAPING”运动以图在现代性的学术文化世界里被派上用途。当人们意识到古代文论对当代文化经验的阐释有效性不足时,便产生了“转型”以求效率的想法。
四、学科化的自我定位
现代性对人类知识生产的另一个影响是知识的学科化分解。
古典文化是一种整一型文化,它依靠一元论和决定论的绝对性力量将全部知识和思想统摄为一个稳定的整体,西方文明史上的逻各斯、上帝意志、理性等,中国文明史上的道、皇权、理等,都是这种绝对性的力量。整一型的文化中,各种知识虽然自有其对象、自有其功能,但它们最终受制于那个一元论的绝对力量,因为这力量对宇宙的终极真理和人类社会的本真意义作了霸权化的规定:哪怕是几何学,其中几何形体之间的逻辑关系仍然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整一型文化借助于绝对性力量的立法功能,为人们提供了统一的社会身份、价值观念和理解方式,甚至为人们建立了共同的精神家园。但是现代性的展开打破了古典文明的整一型结构。启蒙主义要求取缔绝对性力量的霸权化统治,让人的先验理性或感觉经验成为真理或意义的源泉,即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人为自己立法”。现代社会在现代性的驱动下进入了一种“碎片”状态;人被逐出共同的家园,享受到自由也忍受着流浪之苦。对于知识界而言,现代性的“区分”功能的结果即是知识的专业性分解。失去了超验性力量的统治之后,知识裂变为诸多的学科;每一种学科都必须为自己划定独有的对象、设立独有的概念和逻辑程序、构建独有的方法、论证独有的价值,由此才能确证本学科的自主性地位和存在的合法性。现代高等教育和学术体制的基础就是这种学科化的知识分类。任何一种知识想要在现代教育和学术体制中获得地位,都必须有明确的学科自主性的特质,甚至所谓跨学科的研究也只能是在数个已经获得知识自主性地位的学科之间进行。文学研究自然也得在现代性的知识专业化、学科化分解中“为自己立法”。近代以来,文学研究开始借助于康德美学、浪漫主义的天才诗学以及唯美主义的艺术自律论等思想资源向学科的独立自主进发。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在语言论转向的思想潮流中,文学理论为了建立学科化的自主性知识体系将语言分析和审美自律结合起来,形成了形式主义文论,文学理论真正走上了学科自主化道路。
这种知识学科化、专业化的现代性诉求在中国的出现,大概始于1904年清政府制订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关于“文学研究法”课程内容的设计虽然保留了古代学术文史哲混合的特性,但毕竟构想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化知识框架。经过二三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按国际惯例的发展以及50年代效法前苏联的“院系调整”,以知识的专业化和学科化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和学术体制基本形成。文学学术领域也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等几个主要的分支学科。但是,1949年至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研究作为知识生产实践并未获得独立的地位,它被总体化的政党意识形态控制着;像古典时代的超验本体对全部知识的控制一样,极左时代的文学学术也是没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和专业化的边界的。从80年代起,学术界出现了要求学科知识自主自立的声音,文学理论界的学者开始尝试用审美本体论或文学主体性等概念来构建独立的文学理论,通过对文学场的自律性的论证完成文学研究作为现代性知识活动的工程,即文学理论的学科专业化。到90年代,官方实行了一系列学术体制化的措施,包括制订学科分类目录、资助研究项目、评定科研成果、奖励科研人员、组织行业学会等等。进入新世纪后,除少量民间学者外,体制内的研究者都已在学科专业谱系中安顿好了位置:他们皓首穷经于书斋之中,充分地享受着学术体制化带来的优越回报。当学科知识专业化把现代性工程的巨大收益奉送给学者们时,当学者们激情四溢地赞颂现代性带来的进步时,现代性的隐忧也日渐显露,那就是知识的单一化和人格的单面化。当然,在后发现代性社会语境中,现代性的正面价值刚刚上市不久,人们对其负面的隐忧还未有警惕。
介于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两大二级学科之间的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性的知识学科化工程中是一个尴尬的角色。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前学科的古典文化,但对象不等于学科知识属性,古代文学研究者可以引用现代学术话语来阐释这对象,从而形成现代意义的学科知识系统。古代文论则不然,它是一套理论话语或思想踪迹,它本身是关于对象的言说的理论依据或阐释技术。古代文论形成于前学科的古典文化时代,因而在现代性语境中,即在只有具备学科知识专业化身份的理论话语才能进行有效性阐释活动的语境中,古代文论的前学科属性和理论话语属性相互矛盾,这使得它迷失于现代性的学科分类大厦的门前,难于自我确定学科专业身份。如果不对它进行“转换”,讲究合理化的现代性是不会接受它的言说合法性的。
形成于前学科时代的中国古代文论,倘若作为研究对象,它进入现代学科体系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倘若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则不可能成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部分。理论话语是对研究对象进行阐释的方法、策略、视角、知识依据、评估坐标,就此而言,古代文论无法提供现代性学术体制所要求的学科化视野、分析方法、实证知识、逻辑化结构、形式化概念等,因而它不可能成为一种理论话语;它只是现代性思想的对象而不是对对象的现代性思想。正如李建中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古代文论用隐喻性的话语策略描述审美经验,是一种诗性的言说[11]。它的知识生产方式是一种非实证性的经验描述和非形式化的意象隐喻,所以它不可能被转换为现代性意义上的实证化、学科化、形式化的知识。但是,不能进入现代性殿堂不等于没有价值,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论对于走出现代性隐忧是有意义的,只是不要把它向现代性“转换”,因为它本身还没有染上现代性的那些毛病。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题提出以来,大多数主张者都是在一种现代性思维的前提下力图把古代文论辨析成一种具备了学科化潜质的知识体系。这种辨析明显地见出论者渴望为古代文论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安排一个功能性位置的焦虑之情。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讨论中暴露出的现代性焦虑,其根源在于我们长期信奉的一种进步论历史观。进步论历史观把历史描述为人类在崇高目标的引导下由低级到高级、由原始到现代、由野蛮到理性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那些代表着现代的、新颖的或未来的东西才是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因此对于自感落伍于先发现代性国家的中国来说,最令知识分子急切渴盼的就是怎样尽快地把自我“转型”为现代性的主体,体现出历史进步性。但是现代性的隐忧在于西方霸权、知识的形式化和单面化、文化的同质化等等,它意味着本土文化身份的失落、原典性知识的解构、稳固型价值的崩溃以及诗性意义经验的祛魅。我们越是接近现代性,我们就越发清晰地感受到现代性在文化功能上的两面性,所以当现代性在中国展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既渴望又恐惧的心态便日益明显,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题之所以被提出的文化心理原因。
[收稿日期]2009-02-18
标签:现代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失语症论文; 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