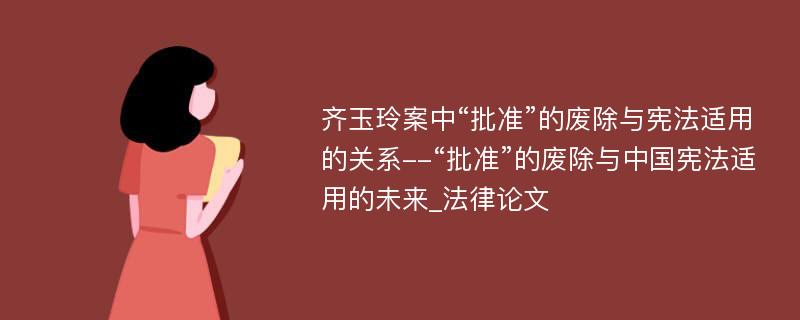
废止齐玉苓案quot;批复quot;与宪法适用之关联——齐案“批复”的废止与中国宪法适用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法论文,中国论文,未来论文,齐玉苓案论文,quo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齐玉苓案“批复”的意义
齐玉苓案“批复”的发布引起了中国宪法学界对中国宪法适用的理论和实践的广泛和热烈的讨论。首先是对该“批复”的定性和一些学术概念,特别是宪法司法化的讨论。有观点认为该“批复”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①标志着宪法进入了司法诉讼程序。有学者认为是“司法抢滩”,②有学者认为是属于“滥用司法解释权”,③也有学者从宪法的适用与解释的区别来分析,认为该“批复”是关于宪法的适用,而非解释,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越权。④就宪法司法化这一概念而言,虽然有学者对此概念提出了质疑,⑤但是该概念应该说是已经被大部分中国宪法学者所接受并运用。⑥有学者从“违宪审查”与“司法判断”这一对概念出发,认为最高法院和大部分学者心目中的“宪法司法化”的概念是属于对宪法的“司法判断”,而非违宪审查,而且还是停留在“法律政策学”层面。⑦其次是对法院适用宪法的可行性的讨论,特别是通过比较研究来论证中国宪法适用的可行性。有学者指出,基于中国宪法制度的规定,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在中国根本不可能。⑧另有学者则从比较法的角度来分析该“批复”和宪法司法化在中国的可行性。数位学者通过对德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比较研究后认为,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中国宪法司法化可行的甚至是最好的途径。⑨也有学者认为德国的经验证明宪法不仅可以司法化,而且可以在私法案件中加以适用。⑩有学者对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了比较研究,也有学者对法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些比较研究的文章大部分也都涉及这场宪法司法化讨论的第三个中心议题,那就是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将来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模式。
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指出,中国宪法学者们就该“批复”达成了三个基本共识:(1)齐王苓案并非真正的宪法诉讼或者违宪审查案件。(2)宪法不仅是政治纲领,而且是法律,从而应该可以由法院加以解释。(3)必须考虑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11)笔者认为,即使这场历时近8年的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没有任何其他成果的话,以上三点共识已经能够充分证明齐玉苓案“批复”所引发的学术讨论对中国宪法学的研究和认识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更何况这场讨论还对宪法学中许多其他的概念,诸如宪法司法化、宪法适用、违宪审查、司法判决等,外国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机制,以及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诸如宪法的公法属性问题和宪法在私法领域的适用问题等,都作出了深入的讨论。因此,笔者认为该“批复”所引发的讨论是非常正面的,并对中国宪法学的发展,特别对宪法适用的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现在,该“批复”被废止了,《法学》童之伟教授所组织的这次对该“批复”的废止与宪法适用的真实关系或可能的联系的笔谈势必会延续这8年来的讨论,让宪法学界对中国宪法的适用作出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二、“批复”废止的利与弊
笔者认同我国许多学者在过去的8年中对该“批复”的法律地位的看法:由于该“批复”所涉及的案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审查或者解释案件,因此该“批复”所具有的完全是象征性的意义。(12)该“批复”所引发的讨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对真正的宪法审查制度,特别是法院行使宪法审查或者解释的渴望。姜明安教授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意图可能是通过不具有争议性的案件来确立其将来在其他案件中行使宪法审查或者解释权的可能性。强世功教授也认同此观点。(13)但是正如童之伟教授所述,该案在法律解释,特别是宪法解释这一层面上并不会对中国宪法的适用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14)这也是为什么强世功教授认为在这场讨论中存在宪法“缺位”这一现象的原因。(15)
如果说当年的“批复”对中国宪法的适用和解释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影响的话,那么今天该“批复”的废止应该会和当年“批复”的出台一样,也不会对中国宪法的适用和解释产生任何的实质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所废止的只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司法解释,而非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司法解释。
有学者认为“批复”的废止反映了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不可能再提宪法司法化,也不可能有法院来解释宪法。(16)廉希圣教授则认为,废止“批复”很难说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是肯定会有影响,特别是当具体法律没有对公民的有关的宪法权利作出规定但该权利受到侵犯时,该公民是否能够得到司法救济?(17)
笔者的观点是,虽然该“批复”的废止让许多学者感到失望,不过其废止也许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其中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大家回到中国的现实中来,认真对待中国的宪法以及重视如何在中国的宪法所建立的宪政制度中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当然,笔者并不是否定借鉴外国经验的作用,而是建议尽量在中国宪法所建立的宪政框架下来借鉴外国的经验。
三、《香港基本法》与宪法适用
虽然中国宪法的适用还在争议之中,但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被称为“小宪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自从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就不停地被香港法院在许许多多的案件中加以适用和解释,也被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过三次。这证明依据中国宪法所制定的《香港基本法》下的有关该“小宪法”的违宪审查机制的运作是成功和有效的。
在香港回归近12年以来,由于香港保留了原来的普通法制度,在诸多的涉及《香港基本法》的案件中,有关违反《香港基本法》的诉讼都是针对香港政府或者是具有公共职能的机构的,而非针对任何私人机构。换句话说,被认为违反《香港基本法》的一方是广义的香港政府,具体包括香港的立法机关(其立法违反《香港基本法》)、行政机关(包括特首和所有政府机关),以及基层法院。就基本权利的诉讼而言,除了《香港基本法》之外,香港还有《人权法案条例》,该《人权法案条例》是香港立法局在1990年制定的,其目的是把《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本地化。该条例第7条明确规定条例只对香港政府和所有的公共机构具有约束力。因此,该条例对公民和私人机构并不适用。以平等权为例,若任何政府机关或者公共机构的行为违反了平等权并因此侵犯了某公民的利益的话,那么该公民就可以依据《人权法案条例》和《香港基本法》中的有关平等权的规定来针对所涉及的政府机构或者公共机构提起诉讼,法院可以适用《人权法案条例》和《香港基本法》中有关平等权的规定来判案。但是,若某公民认为作为其雇主的一家私人公司违反了平等权的话,法院就不能在诉讼中适用《人权法案条例》或者《香港基本法》中的有关平等权的规定。宪法中有关平等权的规定要求香港特区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来保护香港居民在私法关系中的平等权。从1995年开始,香港特区政府陆续制定了《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以及《种族歧视条例》来确保公民平等权在私法领域的实现。因此,在2000年涉及国泰航空公司的一宗案件中,(18)国泰航空公司要求女机舱服务员比男机舱服务员早5年退休的规定违反了《性别歧视条例》的相关规定,而不是违反了《人权法案条例》或者《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这说明香港的法院是把《香港基本法》视为公法,因而只调整公法关系,即个人和政府机构或者其他公共机构之间的关系,而不调整纯私法关系。
香港的上述司法实践是其保留了英国的普通法制度的结果。虽然英国并没有如德国、法国那样严格的公、私法之分,但是英国的法院通过判例对公、私法程序的应用作出了区分。在欧莱利诉麦克曼一案中,(19)英国上议院指出如果案件的性质是属于公法范围,即对政府机构行使权利是否合法或者越权提起诉讼的话,那么该诉讼就是公法诉讼,就应该通过公法程序(即司法复核的程序)来提起诉讼,而非通过私法的程序来提起诉讼。
香港的司法实践与张千帆教授对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或者说宪法诉讼制度所进行的比较研究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张教授文章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宪法是公法,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国家,或者说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就他所举的美国的案例来看,是和英国以及香港的司法实践相类似的。所不同的是,美国是采用政府行为的概念,即看某一行为是否构成政府行为来确定,该行为是否受司法审查的约束。而英国和香港则是看某一机关是否是政府机关,以及看该机构是否行使公共职能。(20)若某非政府机构行使公共职能的话,其行为也受司法审查的约束。因此,在香港行使公共职能的非政府机构(包括私人机构)也不可以违反《香港基本法》和《人权法案条例》的有关规定。当然他认为美国的经验证明在例外的情况下宪法可以适用于私人或者说私法关系。(21)
他通过对德国的判例研究后认为,德国宪法可以间接适用于私法关系。(22)虽然笔者不是德国法的专家,但对张教授文章中所提及的德国的案例“联合抵制电影案”的理解是,违宪审查所针对的对象是下级法院所作出的违宪的判决。当事人的主张也是该下级法院作出了违宪的判决,而非对方当事人的行为违宪。因此,在此案中,我们仍然可以视德国的宪法法院是在审查下级(其他)法院的行为是否违宪。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德国宪法的适用对象仍然是广义的政府概念中的下级司法机关。
把宪法定性为公法对正确看待和理解宪法司法适用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上的通说是宪法是属于公法,宪法所针对的是公权力或者说是公权力的使用。中国宪法应该也不例外。中国传统的把宪法作为万法之母的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虽然我国所有的法律都明确规定是根据宪法所制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数百部全国性法律中的实质性规定在宪法中都可以找到依据。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但是规定所有的法律都是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并没有错,这是因为宪法把立法权授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宪法的授权而制定全国性法律,这就说明所有法律都是根据宪法的规定而制定的。宪法并不直接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中国宪法也是如此。因此,对中国宪法适用的范围首先取决于我们对中国宪法的定性。
四、议会至上与法院适用宪法的关系
在众多的讨论中国的法院是否可以适用宪法判案的文章中,被认为最强有力的反对法院适用宪法的理据之一就是中国宪法的规定,即把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权授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法院就没有可能对宪法作出解释。(23)另外一些学者则希望批复可以起到突破这一宪法障碍的作用,并最终对现有宪政体制,特别是宪法作出修改。(24)这些讨论背后所反映的宪法理论问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的常设机构的最高权威性是否允许法院适用宪法呢?换句话说,议会至上和法院适用宪法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呢?
由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议会制,或者说是由英国的议会制演变而成的,因此我们也许可以从英国的宪政发展中得到一定的启示。英国在1998年制定了《人权法》并于2000年正式生效。由于议会至上仍然是英国的宪法原则之一,若《人权法》授权法院对议会所制定的其他法律是否符合《人权法》,并有权宣布违反《人权法》的其他法律无效的话,那么就会和议会至上的原则相冲突。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制定《人权法》的目的就是要把《欧洲人权公约》转变成为英国的国内法,由于《欧洲人权公约》的法律地位高于英国国内其他的国内法,这就在事实上要求《人权法》的实际地位要高于英国其他的国内法。在这种情况下,《人权法》的做法是授权英国的高等法院以上的法院可以对英国的议会所制定的其他法律是否与《人权法》相冲突作出认定,但是无权宣布该与《人权法》相冲突的其他法律或者其中的某个条文无效。(25)至于如何处置与《人权法》相冲突的其他法律或者其中的某个条文,则由议会自己决定。通过这种做法,一方面法院可以行使涉及基本权利的违宪审查权,另一方面又可以确保议会至上的原则没有受到影响。
笔者认为,在其他学者所讨论的不同的违宪审查的模式之外,若我国的学者们的共识是有必要让法院在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的话,那么英国的模式有其值得借鉴之处。具体的做法是,我们可以把英国《人权法》授予英国的高等法院以上的法院的权力赋予中国的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但同时保留现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的制度。这种做法又可以说是对《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的变形。《香港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区法院有终审权,但是特区法院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受制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对《香港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在中国大陆,我们可以授予法院解释法律,包括解释宪法的权力,但是保留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
五、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批复”被废止之后,宪法学界应该把讨论的中心放在如何在中国宪法所建立的宪政制度中解决中国宪法的适用问题。在这方面,学界应该首先对中国宪法的定性达成共识。在完全认同比较宪法研究成果对中国宪法适用的重要性的同时,笔者觉得宪法学界不应忽视自己的两个特别行政区,特别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适用《香港基本法》(“小宪法”)方面的实践和经验对中国宪法适用的未来发展的借鉴作用。同时,与我国宪政体制有着悠久历史关系的英国最新的宪政发展对我国宪法适用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注释:
①参见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
②参见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法学》2001年第11期。
③参见江平等:《宪法司法化四人谈》,《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
④同上注。
⑤参见许崇德:《“宪法司法化”质疑》,《探索研究》2006年6月10日。
⑥胡锦光教授早在1993年就讨论了该概念。参见胡锦光:《宪法司法化的必然性与可行性探讨》,《法学家》1993年第1期。
⑦参见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⑧参见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
⑨同上注;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蔡定剑:《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等。
⑩参见童之伟:《宪法司法化引出的是是非非》,《中国律师》2001年第12期。对德国的分析大部分学者认为德国宪法是可以适用于私法诉讼的(参见上注蔡定剑文),张千帆认为适用是有限制的(参见上注张千帆文)。
(11)同前注⑦,强世功文。
(12)参见张志铭:《也谈宪法的司法化》;转引自上注⑦,强世功文。
(13)同前注⑦,强世功文。
(14)同前注②和⑩,童之伟文。
(15)同前注⑦,强世功文。
(16)参见《我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有关司法解释废止》,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300/23231/2008/12/ji816191359132180029519-0.htm,2009年2月20日访问。
(17)同上注。
(18)See Tsang v.Cathay Pacific Airways Ltd,[2002]2 HKLRD 677.
(19)See O'Reilly v.Machnan,[1983] 2 AC 237.
(20)See De Smith,Woolf & Jowell's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Chapter 3,Sweet & Maxwell,1999.
(21)同前注⑨,张千帆文。
(22)同上注。
(23)同前注⑩,童之伟文。
(24)参见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5)See Section 4 of Human Rights Act 1998,http://www.opsi.gov.uk/AGTS/acts1998/ukpga-19980042-en-1#pd2-11g4,last visit on Feb.20,2009.
标签:法律论文; 香港基本法论文; 违宪审查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法院论文; 时政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