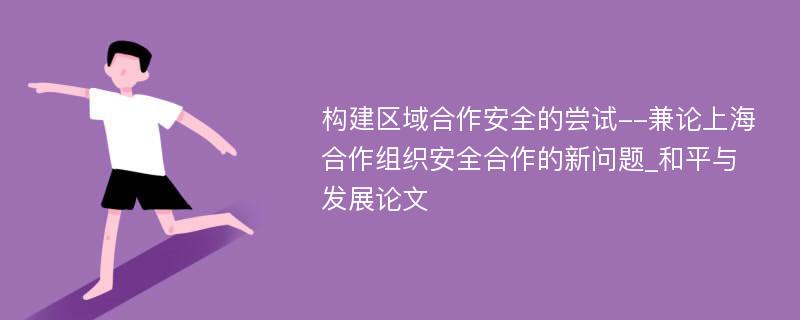
构建区域合作安全的尝试——兼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新问题论文,区域合作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地区安全合作一直是工作重心之一。5年来,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由传统安全领域到非传统安全领域、由单一合作领域到综合合作领域发展,体现了这一新生合作组织在冷战结束后多变的地区形势下积极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努力,也体现了各成员国在新型国家关系前提下推动地区安全机制发展的探索。2006年的上海峰会是上合组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各成员国元首共同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中提出“将研究在本组织框架内建立预防地区冲突机制的可能性”①,这对今后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 预防冲突的国际安全合作实践
合作与冲突,一直是人类社会不同群体间关系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尤其是在这类关系体现为以国家为主体的时代。合作带来建设性的后果,而冲突则导致破坏性的后果。为了防止各类冲突威胁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各国学者、政治家曾经在这一领域中做过有益的理论探索和国际实践。
(一)关于和平研究。“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又被称为“和平与冲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和平研究的基本观点和研究主旨是:和平与冲突之间有一些过程和许多因素是相互关联的,甚至有时互为条件。在一些时期,不成功的和平进程可能会导致冲突;同样,运用冲突的方式也可能实现和平。这里面有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和两种过程互为转变的规律尚未被人们所认知。“如何对冲突与和平进行开拓性的研究,从而实现一个更加公正与和平的世界,是和平研究追求的目标,其研究的重点是如何用和平方式实现和平”②。和平与冲突研究在19世纪末始于美欧国家的学者层面。1948年,美国曼彻斯特学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和平研究机构;1959年,挪威奥斯陆成立了国际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和平研究创始人之一约翰·加尔通任研究所所长,并创办了第一个和平研究刊物《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20世纪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历史,赋予了在这一时期渐成体系的和平研究突出的时代烙印。首先,预防战争和武器控制成为20世纪和平研究的主题。赖特、理查森和辛格等学者将人类的战争现象从社会学的范畴分离出来,并引用数学模型和数据分析,对人类认识战争冲突,尤其是大国间的核战争冲突的引发条件带来了理性的推动。其次,和平研究向冲突的转化深入。世界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大国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军事对立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如何缓解及消除战争冲突的威胁被认为是和平研究的使命。和平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实现“暴力不在场”,而且更重要的是解决“隐藏起来的冲突”③。拉帕波特、米切尔和克里斯伯格等人的防止冲突升级和冲突化解的概念,丰富了和平研究理论的发展。第三,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开始纳入和平研究的视野。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的冲突形式暂时不再以大国间核战争的方式发生,而在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处于非主导地位的冲突因素的影响力却明显上升。森哈斯、博尔丁和孔卡等人将贫富差距、社会地位不平等、全球性环境恶化以及民族、宗教、部落、派系间认同程度等因素列入和平研究的关注范围。和平研究学派在预防冲突的领域中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但受时代的局限也有一些重要问题不能解决。除学科跨度大、研究方法难以整合等学术原因外,对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资源分配不公正和世界层面中国际事务决定权分配不平等的无奈,显露了这一学派在霸权存在前提下预防冲突研究的先天不足。
(二)关于预防性外交。冷战结束后,大国和国家集团间的战争威胁大大减轻,原先在大国关系等基本矛盾影响下处于次要地位的民族、宗教、领土和资源等固有矛盾的影响力上升,由此而引发的区域冲突不仅未能减少,反而在增加。而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军事打击、强制和平与经济制裁等应对冲突的传统方法在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国际社会开始寻求一种预防冲突的新思路,始于冷战时期的预防性外交此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获得长足发展。最早的“预防性外交”概念提出者是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他将联合国阻止中东、非洲地区冲突演化为大国之间对抗的政策努力定义为“预防性外交”④。冷战结束后,地区性冲突频频发生的复杂形势促使国际社会将预防性外交由理论性的政策转化为实践性的措施。1992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布·加利发表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其中对预防性外交做出系统阐述。他认为,预防性外交应是“防止争端在有关各方之间出现、防止现有争端升级为冲突的行动”,为实现这些有效的行动,还应包括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信任措施以及维和部队的预防性部署和设立非军事区等⑤。在联合国的推动下,预防性外交的研究成为冷战后颇具影响的流派,对缓解冷战后的地区冲突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对现存的国际法体系和国际关系原则构成了一定挑战。因此,国际社会长期未就预防性外交达成共识,而在冷战后单边霸权严重膨胀的背景下,预防性外交极易被个别在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大国所利用,甚至蜕变成强权政治工具⑥。
(三)关于安全区域主义。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波及各民族国家的大背景下,人们对民族国家的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相互关联的认可不断加深,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预防冲突的能力被纳入一种依存关系中。由于冷战时期全球性大国及大国集团对抗关系解体,地区性国际政治力量次区域安全格局的制度化安排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驱动下,安全区域主义(security regionalism)理论的研究渐渐兴起。莱克和摩根等人以“区域安全复合体”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提出了不可分离的、逐级递升的区域安全秩序“五种模式”,即权力抑制(包括霸权、均势和联盟等)、大国协调、集体安全、多元安全共同体和一体化或合并安全共同体(amalgamated security);阿约伯、赫特纳等人在“多元安全共同体”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区域社会”以及“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概念。安全区域主义者希望构建一种区域安全体系,即将冲突关系转化成竞争关系,最终走向合作关系的连续性运动过程,而安全区域主义研究试图证明的就是从冲突、竞争及合作同在的“安全复合体”向建立全面合作的“安全共同体”的可能性。赫特纳对“安全区域主义”定义的概括较具代表性:“在特定地理范围内——一个建设中的区域,将包含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冲突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包含对外合作关系和内部和平的安全共同体的努力”⑦。安全区域主义者的努力促进了国际社会对当前冲突动力、冲突预防和共同安全等现实问题的理性认识,但它同样忽略了全球和地区霸权存在的前提,以至于在现实中大国强权的不公正关系基础上指导构建安全共同体时就难免陷入“规范的困境”⑧。
二 上合组织区域潜在冲突因素分析
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构成的共同区域约有30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欧亚大陆的2/3;在这一区域中居住的人口达14.8亿,相当于世界人口的1/4。冷静地分析这一组时常被引用的数字,人们不难发现隐含在这一庞大概念后面的潜在冲突动力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一)错综复杂的地缘文化结构与差异。上合组织6个成员国所覆盖的广袤地区,是当今世界上地缘文化成分最复杂的区域之一。几千年来,以汉儒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南亚文明、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代表的阿拉伯文明、以东正教文化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以及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代表的中亚文明,在这个广大的空间里演绎了无数次的碰撞、冲突、交织和融合。尤其在中亚,世界历史上的各大文明板块在这里交汇、挤压,形成了长期动荡不安的“文化破碎地带”。这种特殊的地缘文化条件,一向吸引着欧亚大陆各地霸权的目光,所有曾经称雄于世的帝国几乎都把中亚看作地理连接的重要环节和欧亚交通的中心枢纽加以控制,马其顿人、波斯人、匈奴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建立的政权以及后来的沙俄和英国,均将中亚作为跨欧亚帝国的疆域或殖民统治的版图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几千年欧亚文明发展形成了这样一幅路线图: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当这一大陆上处于边缘位置的文化板块在不受重大干扰发育起来后,它的活动范围即开始向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漂移,这种趋势或者与当地本土文化发生交叉,或者与同时兴起并进入中心地区的其他文化板块的延伸发生碰撞。这种过程周而复始地不断发生,造成的终极结果是对不同文化融合的促进,但在客观上带来的直接影响却是一次次文明冲突引发的动荡。而中亚地缘政治上的虚弱与重要的战略地位间的强烈反差,更吸引着大陆上各大强权的觊觎,从而又加剧着这种动荡不安的循环往复⑨。作为不同质文化载体的各大帝国的活动轨迹,“碾碎”了多数欧亚民族社会正常发展的路径。源于不同地理环境的民族文化特征、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文化内容,均在欧亚大陆中心区域的一次次的强权博弈中发生位移和割裂,形成了当今在这一地区存在着数百个民族主体的既成事实。当欧洲工业文明兴起后,欧亚大陆上曾经繁荣数世纪的古老农业文明、绿洲文明和草原文明开始急剧衰落。随着列强殖民文化的进入,欧亚地区各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留下了深刻的文明冲突烙印。19世纪初以来的欧亚区域文化发展历程,强势文化主体以征服者和管理者自居,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需要推动着区域一体化。在这种极不对称的强弱关系下,各民族虽勉强将各自的社会发展进程纳入了这种一体化系统中,但以霸权为动力的一体化进程只是在政治层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而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和对立迫于强势压力转入社会层面,并在不断积累。一旦依托于外来霸权建立的权力中心削弱和消失,内在的文明冲突因素就以民族主义的形式施放出来。在新的权力体系尚未形成或功能不全时,这种施放过程对地区现有秩序具有很大破坏性。
(二)国家权力核心更迭中的社会资源分配矛盾。上合组织的中亚成员国至今所经历的国家历程十分短暂。在有限的10几年独立建国历史中,以本土化政治结构为基础不断强化的“总统制”政权几乎成为中亚各国不期选择的共同模式。在苏联解体后的特殊历史时期,权力相对集中的“总统制”政权体系为捍卫新获得独立的主权和保障社会系统的重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各国精英集团基本掌控了本国的主要资源,从而大大加剧了他们的继任力量发育和成熟的困难。而中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民族国家雏形,不论是曾经称雄一时的帖木儿帝国,还是曾经在沙皇俄国和中国清朝政府之间搞平衡外交的哈萨克汗国,不论是最后被征服的浩罕汗国,还是持续存在到十月革命的布哈拉汗国,由于它们均未曾经历完备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政权建设,世袭汗王制度延续的经验与现代民族国家政权需要解决的问题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18~19世纪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进入,使中亚各民族自然的国家化进程在实际上被中断。而在沙俄统治时期和苏联时期,中亚各主体民族精英集团的形成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外族强权干预的痕迹。沙俄在征服和治理中亚的历史中,曾人为地、有选择地在中亚民族的不同部族中制造明显的亲疏关系,由此形成了当今中亚各国不同部族、不同地区之间在政治和经济资源分配上的极大不均衡。这种现实正左右着中亚各国进入政权更迭阶段的政治格局发展。2005年3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事变就是典型的例证。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当今一些试图按照自身需要“改造”中亚各国政体的大国势力。它们不满于原苏联地方领导人改头换面建立的“后苏联政治体制”,试图以“规范的民主程序”督促中亚各国完成目前的国家政权更迭,民主培训、监督选举、非政府组织以及出口民调等方式都毫不吝惜地派上了用场。但是它们忽略了两个最根本的要素:一是转型时期中亚地区政治平衡的脆弱性;二是中亚民族自身的深厚政治文化传统。中亚地区的政治更迭过程还在继续,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在继续,由此不断产生的问题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在继续(10)。
(三)近年异常活跃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冷战的结束给欧亚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原有的两个世界性霸权的对立和冲突不复存在以及由此形成的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威胁大大减弱。而本来覆盖在这一对主要矛盾下、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却因这一世纪性变化在地区安全形势中的影响力大大提升。当前,在欧亚地区可能引发冲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1)民族矛盾日渐突出。欧亚地区各国都是多民族国家,而各民族国家形成的特殊经历,造成了不同民族占有国家资源的极大不均等,跨界民族问题、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问题、世居民族与迁入民族问题等,一直困扰着各国领导集团。在独立建国初期,各国精英明智地淡化和回避了这一领域中的矛盾,为国家的稳定发展赢得了时间。但原有的矛盾条件和潜在的冲突因素并没有得到基本解决,随着政治敏感时期的到来,欧亚地区的民族矛盾有更加激化的趋势。(2)宗教极端势力活动回潮。由于中亚的特殊地域条件,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的国际反恐行动对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打击是有限的。车臣恐怖势力在遭受严厉打击后又推出新领导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仍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3国交界处制造事端;“伊斯兰解放党”近年继续蔓延,其存在几乎遍及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国际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对欧亚地区的影响正在引起各国的警惕,而2005年5月发生的“安集延事件”几乎引发的跨国骚乱更将现实的冲突威胁摆到人们面前(11)。(3)各国发展的利益差异加剧。由于地理条件不同,欧亚各国资源占有极不平衡,这不仅体现在石油、天然气等关系国民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战略资源上,而且还体现在土地、水源、矿产等关系各国居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稳定的基本生存资源上。若无有效的协调手段出台而任其发展下去,由此引发冲突只是时间问题(12)。(4)有组织跨国犯罪活动猖獗。与中亚相毗邻的阿富汗、巴基斯坦部族势力强大,政府控制能力有限,一些在当地盛行的“犯罪经济”活动通过中亚地区影响着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安全,尤其是毒品种植在阿富汗屡禁不绝。据联合国禁毒署专家提供的数据,阿富汗2000年的鸦片产量占世界的70%,2004年的海洛因产量为420吨(生产1公斤海洛因需要10~15公斤的鸦片膏),占世界产量的87%,而被查出经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走私的毒品占阿富汗毒品非法输出的24%(而专家估计的包括未查出部分的总量占60%以上)(13),中亚各国及俄罗斯已成为向欧亚大陆毒品走私的重要通道。
三 构建上合组织框架内预防冲突机制的现实前景
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的签署,标志着这个国际组织的正式成立。但是,如果以上合组织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作为考察对象,则必须从它的早期雏形——“上海五国”时期开始。被称作“上海进程”的地区合作活动已经持续了10年,若针对预防冲突的能力建设而言,上合组织取得的成就不仅仅局限于已经达成的有形成果上,而且还体现在促进地区和谐发展的理念推动与机制完善上。
(一)建立成员国政治上的互信关系。1991年8月,苏联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八一九事件,苏联党和国家的各级系统随之土崩瓦解。同年12月底,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宣布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定》,从此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正式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苏联的解体标志着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这一重大事件引起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根本性改变,也对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国家关系定位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对于原苏联与中国有着共同边界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而言,此时最现实的担心是原可依托的军事大国瞬间消失后带来的空前军事安全危机。为了消除新独立国家的安全威胁,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彻底告别霸权心态、努力放下大国架子,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合作的方式,与中国寻求和平解决遗留问题的途径,共同消除传统的军事安全威胁对新生国家发展的牵制,并由此赢得克服社会转型的各种困难的时间和精力(14)。在冷战结束的巨大落差和冲击面前迅速调整对外政策思路的中国政府,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积极外交,通过主动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努力营造一个全面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外部环境。在冷战后的全新国际关系形势下,达到这样理想周边环境的唯一途径和可靠方式,就是与有关邻国在睦邻友好关系基础上发展互信合作(15)。历史进程中的机遇与欧亚各民族发展的要求,使中国与原苏联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之间在国家利益上出现重要的重合。1996年4月和1997年4月,中国和上述4国分别在上海和莫斯科签署的《中、俄、哈、吉、塔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中、俄、哈、吉、塔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不仅以成功解决中国与原苏联4个共和国间历史遗留问题而成为预防性军事外交的典范,而且为此后新型安全合作关系的拓展奠定了重要的政治互信基础。
(二)推动国际政治民主意识的确立。上合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普遍要求。冷战的不对称结束,片面地刺激了大国集团力量不均衡发展。仍然承袭冷战思维的单边主义、新干预主义和“民主改造”等理念和行为,加剧了国际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和不稳定。尤其在全球化进程对世界不发达地区形成压力的背景下,在有关国家出现的不适甚至反弹正在酝酿着新的冲突。在维护地区稳定的活动中,上合组织对此形成深刻而积极的认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建立21世纪新型国际秩序的进程缓慢而不均衡,各国相互联系与依存日益加深。国际社会拥有实现稳定、和平和普遍发展的良好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和威胁”(16)。基于对构建地区及世界新秩序进程中面临的复杂问题和诱发冲突的风险,上合组织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际合作方向不仅在冷战后“为建立互信、互利、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型全球安全架构做出建设性贡献”(17),而且在预防地区性冲突的安全合作中将排除霸权因素作为重要前提,并通过一系列有创新、有实效的实践活动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从而对更广泛的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发展产生着示范作用。
(三)倡导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精神。上合组织反对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相等同的全球化观,坚持世界整体进步与多元文化共同繁荣的理念。同时,重视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差异可能引发冲突的合理性,在承认不同质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基础上,积极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化解因文明对立而积累的冲突因素,为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的互相理解、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创造条件。上合组织在自己的合作实践中提出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重要精神,体现了冷战后多数国家和民族在面对全球化冲击时的共同心态。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上合组织各成员国超越了民族传统、宗教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为获得共同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和良好区域环境,通过平等协商建立了政治上的信任、安全上的协作、经济上的互补关系,以颇具创新意义的国际实践解答着上世纪末困扰国际社会的“文明冲突”命题。“上海精神”体现了东方哲学中“和而不同”的理念。这种精神不仅“已植根于各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之中”,而且“越来越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18)。
(四)逐步完善的各级层沟通协调机制。《联合国宪章》明确地将区域性组织纳入解决地区冲突与维护国际和平的世界安全体系之中,并规定区域组织在“将地方争端提交安理会以前,应依该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力争和平解决”(19)。2002年公布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指出,各成员国将“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其他有关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发展国家间睦邻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20),作为处理地区及国际事务的基本国际法指南,并在不断扩大的安全合作领域中逐步建立起具有积极预防地区冲突功能的各级机制:在协商解决地区总体安全问题与制定宏观发展战略的国家元首会议的指导下,各国总理会晤、外交部长会晤、国防部长会晤、经贸部长会晤、安全与执法部门领导人会晤、交通部长会晤以及文化部长和紧急状态救灾等部门领导人会晤,基本形成了多边、多级和多部门的交流磋商机制。针对各层面的不同的责任领域和职能特点,上合组织正在从预防冲突发生、应对突发事件、化解冲突因素等方面健全着自己的工作机制。
当然,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预防地区冲突机制是区域安全合作的长期目标,在推动这一进程的道路上存在着大量的困难、阻力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为推动区域安全合作不断向既定目标前进,首先应明确几个基本领域中的任务:第一,有针对性地加强成员国在近期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形势下的政治互信关系;第二,以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为当前的工作重心;第三,研究制定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近、中、远期发展规划;第四,加强与联合国在日常工作中的联系,发展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东盟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北约等地区安全合作组织或合作论坛的交流与对话,探讨在预防地区冲突领域中合作的可能性。就目前地区形势而言,安全合作仍是上合组织不可偏废的重要职能,有目标、逐阶段、分领域地推动预防地区冲突能力建设,必将成为对地区长期和平与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业。
注释:
①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新华网2006年6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6/15/content—4703028.htm.
② 刘成:《西方国家和平研究综述》,载《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③ 〔美〕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著、卢彦名译:《和谐致平之道——善于和平学的几点阐释》,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④ Michael S.Lund,Early Warning and Preventive Diplomacy,Managing Global Chaos,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6,p.398.
⑤ Boutros Boutros—Ghali,An Agenda for Peace,United Nations,1992,pp.11~19.
⑥ 李莉:《冷战后预防性外交的发展及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0期。
⑦ Bjö rn Hettne,Regionalism,Security and Development: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op.cit.,pp.13~28.
⑧ 郑先武:《安全区域主义:构建主义者解析》,载《国际论坛》2004年第4期。
⑨ 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43页、第47页和第115页。
⑩ Боришполец Ксения,Выбо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опы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Централъ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006 NO 1.
(11) И.звягелъская,ШОС в контексте усилий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Централъной Азии(тезисы)//Ш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Москва,1 июня 2005г.),c.173.
(12) К.Т.Валентини,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межгосударстрвенных воцых отношений//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в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в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13~15 мая 2002г.,c.65.
(13) Ирина Комиссина,Афганистан:наркоторговля и регионалъ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ъ// Централъ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005 NO 6.
(14) И.Η.Комиссна,А.А.Куртов,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ов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Е.М.Кожокина,Россий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Москва,2005г.,c.16.
(15) Дмитрий Трофимов,Шанхайский процесс—от“Пятерки”к“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итоги 1990—х,проблемы и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Централъ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002 No 2(20),2002.
(16)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新华网2006年6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6/15/content—4703028.htm.
(17) 同上。
(18) 胡锦涛:《共创上海合作组织更加美好的明天——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载《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6月16日。
(19)《联合国宪章》第8章,第52条,第2款。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charter/chapter8.htm.
(20)《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网。http://www.sectsco.org/news—detail.asp?id=14&LanguageID=1
标签:和平与发展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欧亚联盟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安全文化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