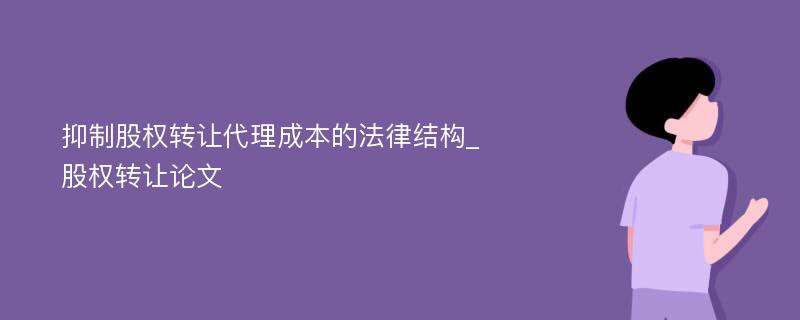
抑制股权转让代理成本的法律构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股权转让论文,抑制论文,成本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股权转让成为公司法理论与实务部门共同关注的话题。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股权转让纠纷呈激增态势。在众多的股权转让纠纷中,股权(包括股权权能)转让合同的效力、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限制转让的正当性、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及效力等,一直是困扰理论界与司法实务部门的重大疑难问题。而其中最为核心的命题是,股权转让中的私权自治与国家强制的边界如何厘定。股权与物权、债权同属私权,股东处分其部分权能——投票权——从而谋取利益似乎亦无不可。正如有学者认为,“股东可将自己在特定期间内的表决权让渡或处置给他人”,但“表决权的买方在行使表决权时应依法行事,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使的表决权不得逾越有权处分股东的表决权范围。”①翻诸公司法条,对此未设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72条在设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内转让和对外转让股权的规则后,在第4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从而将《公司法》第72条设定为“选出式”,即公司法提供默认的标准安排,允许股东自行议定股权转让规则。然而,实践中,对该条款的理解却歧见迭出。
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效力已经成为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某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规定,职工结婚生育,即要强制收回职工股。此种条款违背了公序良俗,显属无效。”②就抽象的意义而言,章程限制股权自由转让的正当性如何,其边界如何设定,是否存在不容悖反的公序良俗,如果有的话,又当如何妥为厘定,凡此种种,均值慎思。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诉争,也日益频繁。《公司法》第72条对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作了如下安排:其一,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二,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在司法实务中,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若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时,转让人能否反悔,即撤销转让之意思表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赋予出让股东反悔权,以形成一种价格拍卖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出让股东的利益;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应赋予出让股东反悔权,因为优先权人一经向出让股东做出有效的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在优先权人和出卖人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合同,这一合同的内容和出让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内容相同。这一合同虽然未经要约、承诺等缔约程序,但其系依法律规定的方式而产生,也具有生效合同的全部效力。④
优先购买权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同等条件”。从商事习惯看,“同等条件”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可以包括同等价格条件(如对价形式、价金数额及支付方式等),也可以包括价格之外的因素(如高管延聘、职工安置等)。但同等条件能否设定为“购买人须为同事、朋友、亲戚”关系,则不无疑问。
股权转让的诸多问题,究其根源,均在于股权转让中的私权自治与国家强制的边界难以厘定。在传统的规范分析层面上,这些问题很难获得理想的解决思路。就此而言,本文尝试拓展分析理路,遵循法律经济学进路,探求规则内生的经济逻辑,以求得论说的正当性。
一、股权转让的性质:股东身份的概括继受
20世纪90年代,关于股权性质的论争,一度成为公司法学界的学术盛事,形成了所有权说、债权说、社员权说、股东地位说、独立民事权利说等较有影响力的观点。⑤其中,尤以股权物权说和股权债权说为主要论说。然而,股权物权说无法解决股东与公司同时对公司财产拥有所有权而产生的“一物二主”问题;股权债权论同样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股东劣后于债权人受到清偿。现在学界形成的共识是,股权是独立于物权与债权的一种特殊权利形态,它是指股东针对公司财产(包括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按其持股份额享有的权利,这一权利既包含着财产因素,又包含着精神(身份)因素。
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股权的权能主要包括:其一,投票权,即对公司未决事项予以票决的权利;其二,收益权,即股息与红利请求权;其三,剩余财产分配权,即在公司解散时按其持股份额分取剩余财产的权利;其四,占有及处分权,即股东占有股票(或其他投资凭证)并为转让、赠予等处分行为的权利。
股权是一种兼具人身权与财产权性质的特殊权利形态,是投资者基于股东身份而获得的针对公司有形和无形财产的概括性权利。因此,股权转让在属性上至少应包括财产权利的转移和股东身份的让渡这一双重意义。股权的转让毋宁说是纯粹权利的转让,还不如说是身份的概括继受,这也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盛行的“股权社员权说”一脉相承。⑥作为社员权的应有之义,股权受让方在继受权利的同时也继受了义务,其义务来源于股权行使外部性⑦所产生的代理成本。
在经济学意义上,股权是一种质量识别成本极其高昂的“信任型”产品,⑧其行使存在着相当大的代理成本。彼时语境下的“代理成本”,仅仅指由于信息不对称、股权分散且集体行动成本高昂,公司管理者的自利行为损害了股东利益的情形。⑨但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出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了很大的缓解,“代理成本”的内涵和外延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产生也不再局限于公司管理者与股东之间,股东彼此之间也会产生代理问题。简言之,当被称为“委托人”的一方的福利,取决于被称为“代理人”的一方的行为时,就产生了“代理问题”。⑩
通常而言,公司存在三类代理问题。第一类问题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是传统的代理命题;第二类问题是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小股东利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股东行为这一意义上,小股东被称为委托人,大股东则可称为代理人。(11)甚至只要公司的部分股东能够做出影响全体股东利益的决定,也会产生代理问题。第三类代理问题涉及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债权人、雇员和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12)
股权转让的代理成本,表现为股权行使的外部性,易言之,一方股东行使股权的行为,在为其带来利益的同时,如果损害了其他股东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则会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负外部性,即产生股权行使的代理成本。该代理成本的产生原因有二。
其一,股权具有共益权属性,其不当行使会伤及其他股东利益。根据股权的内容和行使目的,股权可分为自益权与共益权。自益权是指股东专为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如分红权、公司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自益权主要是财产权。而共益权则是指为自身利益并兼为公司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包括表决权、选举权、查阅权等,共益权主要是人身权。自益权的行使不会带来代理成本,但共益权则不然。如果转让股权中的共益权而不转让自益权,将会导致受让人获得的身份权与转让人保留的财产权相分离,带来了激励的错配。例如,股东卖出投票权以获取价金,尽管符合意思自治的正当性外观,但由于其导致股东的投票权与投票后果的承担相分离,将引发不负责任的投票风险,从而损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从其他股东虽不是投票权买卖合同的当事方却仍然受损这一角度而言,投票权买卖产生了代理成本,故应为法所不许。其二,股权转让具有遏制公司管理者与股东之间代理成本的功效。公司管理者利用信息不对称滥权谋私,损害股东利益,产生了传统意义上的代理成本。股权的自由转让创造了反映着公司治理水平的股权价格和公司并购市场,如果管理者滥权谋私、股东抛售股票,将会导致公司股价直线下挫,公司将面临被收购的威胁,现任管理者职位堪虞。因此,顺畅的股权转让市场有利于降低管理者的代理成本。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股东会决议或者公司章程条款中限制或者禁止股权转让的约定,尽管符合“资本多数决”的正当性外观,但它可能伤及股东的退出权,进而减损了资本市场对高管的制约力量,从而间接地推高代理成本,其正当性应予审慎考量。
正因为如此,股权转让与物权或债权转让的理路判然有别。所有权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即只要他人不加干预,所有权人自己便能实现其权利。所有权的义务主体是所有权人之外的一切人,后者所负的义务是不得非法干预所有权人行使权利,是一种特定的不作为义务。而债权则具有相对性,具有特定的义务主体,即债权人的请求权只对特定的债务人发生效力。总之,物权或债权的转让不会产生外部性问题,而股权(包括其权能)的转让则须考虑其潜藏的外部性所引发的代理成本。股权转让的受让方继受的并非仅仅是权利,而是概括继受了股东身份,必须接受此种身份所带来的有利或者不利后果。一方面,相关法律规定必须使股东身份产生的投票权等共益权与其自益权相匹配,以降低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在意思自治的前提下,股东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达成限制股权转让的合约安排,而且在资本多数决条件下,有时小股东虽未同意,大股东也会达成强制转让股权或强制锁定股权等种种限制性条件,从而产生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凡此种种,均须在合同自由、资本多数决与降低代理成本之间求取适当的平衡。
二、禁止股东出卖投票权:抑制代理成本的考量
投票权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弥补着公司法规则之于具体公司治理的不足。在法律经济学意义上,公司法是规范公司设立与运作的标准合同形式。立法者将公司设立及运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以法律的形式转化成公共产品,向公司参与者提供,便形成了公司法规则。这些规则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公司参与方的需求,从而有效地降低协商成本,使他们能够将谈判焦点集中于特定事项。但另一方面,面对纷繁芜杂的公司实践,规则本身的不周延性使其难免挂一漏万,公司的特殊事项必须留待公司各参与方自行议定解决。
投票机制正发挥着此项功能。投票权意味着权利人有权对公司法未予明确规定的事项做出决议。股东享有公司投票权的原因在于,股东是公司财产的剩余索取权人。在公司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中,债权人拥有固定的利息收入,经理及雇员已就薪酬计划与公司有过协商安排。这些对公司收入拥有固定索取权的人缺乏适当的投票激励。而对于股东而言,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都必须一体承受,他们永远站在最后一线与公司兴衰与共。作为剩余索取权人,股东拥有最适当的激励去做出理性的投票。当然,集体选择问题(13)使得股东的投票绩效并非总是尽善尽美。但一般而言,公司管理人员明白,如果公司经营绩效不理想,股东将有可能行使投票权将其免除职务。避免遭到股东驱逐的压力就像高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那样,迫使高管为股东利益善尽职守。在这一意义上,股东的投票权发挥着降低管理者的代理成本的作用。
除了抑制公司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降低其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代理成本之外,股东投票的第二个机理是使投票权与剩余索取权相配比。剩余索取权是指股东就其持股份额而享有的分红权及公司解散之后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在美国各州,关于股东投票的绝大多数基础性规则都保持着一致:所有的普通股都拥有表决权,所有的投票都拥有相同的权重;除股东外,其他公司参与方都没有表决权,除非合同中另有明确约定。
所谓投票权与剩余索取权相配比,是指如果每股所拥有的剩余索取权相同,则其所附着的投票权权重也应相同,而这正是前面探讨的投票功能的逻辑性结果。投票权与投票者在公司中的剩余利益如影随形,剩余利益的相等份额必须伴随着相同的表决权重,否则将产生不必要的代理成本。易言之,如果投票者的表决权与其剩余索取权不成比例,则他们无法获得自己努力所带来的等同于其表决权比例的利益份额,也无须按其表决权比例承担可能造成的损失。这样,利益和风险机制的匮乏使得他们不可能做出最优的决策。或者更为糟糕的是,拥有相对于其持股比例而言过高的投票权,还会诱发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等道德风险。
禁止购买投票权,正是上述法理的延伸。其意亦在于确保表决权与剩余索取权结为一体,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代理成本。
总之,就纯粹的私权交易而言,股东投票权买卖似乎并无违法之处,但由于带来了巨大的代理成本,极易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故应为法所不许。这种立法范式曾因限制了当事人的合同自由而备受诟病。如有学者认为,股东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股东,他们是投资者,而对投资者而言,出路比发表意见更重要。(14)鉴于此,另有学者认为,如果投资者不能或不愿行使他们的表决权,应当允许他们将其出卖。(15)但如果本着投票权必须与剩余索取权相配比的分析理路,就不难理解,倘使他人可以买入投票权,则必定会造成投票权人和剩余索取权人相分离、从而投票权人无须承担投票后果的情形,最终将诱发投票不负责任、投票敲诈等道德风险。
另外,公司中的表决权买卖与政治选举中的贿选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在本质上,两者都是选举代表组成代表机构服务于投票者利益或者决定某些特定事项。在政治领域中,贿选是被绝对禁止的,这主要是出于公平的考量。由于财富的边际效用的递减效应,穷人的一块钱会比富人的一块钱更加值钱,所以穷人更有可能贱卖他们的投票权,最终导致投票权集中在富人手中。如果允许政治领域中的表决权买卖,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会传导到政治上。但穷人和富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富人不应当有特权,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富人具有更强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类似的道理在于,在公司法领域,也没有理由认为,富人具有更强的服务于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的意愿和能力,因而在不受合同义务拘束(委托投票机理)和信义义务拘束(信托投票机理)的情况下,不应允许富人拥有更多的公司投票权。富人如果想获得更多的投票权,可以通过购买股权或者接受他人委托(受到委托合同的拘束)或者信托(受到信义义务拘束)的方式来实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造成投票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分离的股东投票权买卖,世界各国一般均予以禁止。
三、降低股权转让代理成本的制度安排
如前所述,股东转让股权不仅是一种财产处分行为,而且也是一种身份让渡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有涉他性,即股权转让会涉及公司、其他股东、债权人等诸多第三方利益。在以法律方式设定股权转让的结构时,必须遵循的总体原则是:内化行为主体的交易成本,减少或者避免产生代理成本等负的“外部性”。大体说来,股权转让的法定结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创设投票权与收益权及罢免权相配比的制度安排,以降低代理成本。因为投票权应当与剩余索取权相配比,故而“一股一票”获得了牢固的法理支持。实践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世界各国的公司法,均将同类别的股份享有同等的表决权视为通行规则。(16)在该理路之下,投票权买卖为法之不许。尽管《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股东是否有权单独卖出表决权,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10条规定“……投票权征集应采取无偿的方式进行,并应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信息”,相当于否定了表决权买卖。我国在2005年开始推进的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证监会亦三令五申地禁止投票权的买卖行为。(17)
另外,各国公司法一般均要求,投票权除了体现为对公司重大经营事项的决策权之外,还体现为罢免董事的权利,以维持股东对董事的监督功能,降低董事滥权谋私的代理成本。例如,按照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律,大股东拥有中途无故罢免董事的不可撤销的权利。(18)德国的默认规则是,四分之三以上表决权股份可以无故罢免股东选任的监事会成员。(19)美国最重要的立法例把无故罢免董事的权利设定为默认规则,但章程可对此做出除外规定。(20)我国《公司法》第38条也把股东“选举和更换董事”设定为默认权利。因此,如果某公司章程规定,股权转让之后受让方不拥有罢免现任董事的权利,那么,章程的此项约定将会因为剥夺了股东罢免董事的权利而推高董事滥权或怠惰的代理成本,给公司带来潜在的损害,应属无效。
其二,合理创设委托投票、劝诱投票和信托投票制度,抑制管理层和异议股东的代理成本。前述分析理路还可运用于股东委托投票机制上。各国公司法律往往通过限制股东做出不可撤销的委托,来防止“投票权不可出售”这一规则受到侵蚀。在这一规则之下,一项委任他人投票的股东委托,可以因为投票者另作授权而被撤销;甚至一项意在不可撤销的委托,也只有与股票方面的“利益”相“捆绑”时,“不可撤销”才有约束力。如股东以股票为担保,从受托投票人处获得贷款。(21)
这些制度安排的原理是,委托投票权机制的建立,已经使股东表决权与剩余索取权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分离,产生了一定的代理成本。如果不可撤销的委托具有法律效力,则必定会造成投票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分离的情形。在现实中极易发生在任管理层劝诱股东将投票权委托管理层行使,以巩固其自身职位。这种情形一旦发生,股东投票对于管理层的潜在监督作用将消解为零,从而产生极大的代理成本。也正因为如此,各国对劝诱委托投票一向严加规制,以抑制其中潜在的代理成本。当然,任何制度均是双刃剑,它的负面效应是使得异议(造反)股东更难以挑战现任管理层,反而更不利于市场向管理层施加压力以降低管理层怠惰或滥权产生的代理成本。因而,各国在创设劝诱投票法律制度时,均力求在难度方面达至最优的平衡。(22)
同样的情形亦适用于投票权信托。投票权信托在形式上也使投票权与剩余索取权产生了分离,同样存在代理成本的隐患。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引入受信人的信义义务,即要求受信人善尽忠实与勤勉之责,本着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投票,从而遏制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鉴此,如果股权转让中存在有悖前述法律机理的安排,例如,规定受让股东必须将其投票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现任管理层行使,也应属无效。
其三,特殊群体的股权转让受到限制。发起人在公司设立阶段与公司发生着诸多潜在的关联交易,公司及后续股东因此承担着诸多“意外”债务。为遏制其中的道德风险,降低发起人行为的代理成本,世界各国公司法普遍要求发起人“锁仓”一定时期后才能够转让其股权。例如,《公司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类似地,对于公司管理人员等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的特殊群体,法律对其股权转让予以限制,亦在于绑定其自身与公司财产的价值,从而抑制这些“内部人”的代理成本。
当然,除了法律的标准安排之外,许多公司还通过选择上市而遵循相关上市规则,特别是遵循更为严格的锁仓期安排,从而自愿地做出了承诺。例如,目前我国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创业板公司,发起人的锁仓期一般为三年。
其四,特殊类型公司的股权转让受到限制。通常而言,对于封闭式公司而言,限制股权对外转让的目的在于维系公司内部的互信与团结。
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6.27节第3小节规定:“授权对股票转让或者转让登记进行限制,是为了:(1)当公司依赖股东的数量或者身份而存在时,维持公司的地位;(2)依据联邦或者州证券法保留豁免权;(3)出于其他合理的目的。”(23)目前世界各国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限制,主要从公司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着手,形成了以下几种立法模式:仅规定同意权,不规定优先购买权;仅规定优先购买权,不规定同意权;既规定同意权,又规定优先购买权;授权公司章程规定或协议约定同意权、优先购买权或其他限制。(24)
前述股权转让的法定安排,可以理解为公司参与方在信息充分、而且谈判成本足够低的情况下,本来会达成的议定安排。公司法把它们上升为标准化的制度安排,节约了各方谈判的成本。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股权转让的法定结构中彰显的国家强制力,在本质上也具备了契约的要素。
四、抑制代理成本的约定选择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公司法通过允许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对股东转让股权进行限制。然而,此种限制性约定在什么范围内有效,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在我国,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均允许以约定的方式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其一,《公司法》第72条在明确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内部自由转让的原则并对股权对外转让做出一定的限制后,又在第4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其二,《公司法》第142条第2款在对发起人、董事等股权转让做出一定的限制之后,又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如此规定的法理基础至为明显:由于公司股权结构、人合性要求等存在诸多差异,可以赋权股东通过章程实现自治,依据自身情况制定股权转让的条件,从而满足了“各方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适用或退出公司法的某项规定”(25)的要求。
在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章程限制性规定可谓五花八门,概括而言,可分为“禁止股权转让”、“强制股权转让”、“对股权转让施加其他限制”等类型。
其一,禁止股权转让。此种章程规定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直接禁止股权转让的规定,如某些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规定,在任何情况下股东均不得转让股权。有的公司甚至在章程中直接规定,“股东有生之年均不得转让股权”。第二,间接或者变相禁止股权转让,即对股权转让设置了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如要求股权转让获得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或要求股权转让事先获得董事会成员的一致许可等。在传统的私法观念上,禁止财产流通向来被认为违背了公共政策。因而,章程的此种约定带来了“契约必须遵守”与保障股东的退出权之间的冲突。
其二,强制股权转让。此为禁止股权转让之反面,即章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不论股东是否同意,股权均须强制转让。根据触发股权强制转让的事由,此类条款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身份绑定类。如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退休、解聘、辞职等原因离开公司,其所持股份必须在股东内部转让。第二,违法情事类。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若因违法而遭受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其股份必须转让给员工持股会或其他股东。第三,条件严苛类。如公司章程规定,女员工在持股期间怀孕或休产假的,股份必须转让给员工持股会或其他股东。凡此种种强制转让股权规定的效力,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其三,其他限制。除了前述“禁止股权转让”和“强制股权转让”的两个极端情形外,绝大多数国家允许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施加限制,如德国《有限公司法》第15条规定:“股份可转让并可继承,章程可就股份转让规定其他条件。”《公司法》第72条在第4款也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倘若依循传统的民法私权观念,非经股权所有者许可,强制转让股权与强制锁定股权均为法所不许。然而,如前所述,股权不同于物权与债权,在公司“吸收了所有投资者的财产”的意义上,每一位投资者的财产已经成为一种“被动性财产”;另外,在公司这一诸多利益相关人组成的多元权利束中,一方行使权利将会给其他主体带来外部性,这使得股权的行使理路与所有权绝对的理路判然有别。
在美国公司法上,“判断限制股份转让是否有效的普通法标准是,它必须‘没有不合理地限制或者禁止流通性’。”(26)借鉴这一逻辑,同时鉴于《公司法》第72条第4款中公司章程可以限制股权转让的规定容易被理解为公司章程可以任意限制股权的转让,我们亟需确定一套判断标准,以厘定何为股权转让的“合理”限制。在法律经济学意义上,行为人必须内化自身交易成本,避免道德风险等代理成本,在“转让权”与“限制转让权”之间寻求妥当的平衡。
股东的退出权是抑制控股股东与高管的滥权行为,降低其代理成本的重要安排。在通常意义上,股东的话语权可分为积极话语权(用手投票)和消极话语权(用脚投票)两种,后者即为股东的退出权。美国公司法学者罗伯特·汉密尔顿(Robert W.Hamilton)强调了退出权的重要意义:“在封闭式的公司中,对于少数股东而言,‘退出’权相当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退出权,他们的利益就处于由居于控制地位的股东的行为带来的极大风险之中。”(27)而且,在德国公司法上,即使“公司章程可以完全禁止股份的转让。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股东继续留在公司已成为不合理的强求之时,股东也有退出公司的权利。”(28)
禁止股权流通伤害了股东退出权这一根本权利,极大地诱发了控股股东与高管的滥权激励,放大了道德风险。对于一家具体的公司而言,如果股权无法转让,将无法形成公司控制权交易市场,进而无法遏制控股股东和高管的滥权行为,后者将在“反正公司不会被他人收购,自己职位无虞”的逆向激励下,通过种种关联交易中饱私囊。因而,为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在保障股东的退出权与“禁止转让的契约必须遵守”产生冲突时,必须明确前者的权利位阶高出一筹。(29)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在一定条件下强制转让股权以及对股权转让设置其他限制性条件,却不会无效,因为后者并未根本阻塞股东的退出权,不至于放大道德风险,产生巨额代理成本。在解释为什么“禁止股权转让的契约”无须遵守时,还可以遵循长期契约与短期契约存在差异的视角。一个较为显见的理解是,判断“股权永远不得转让”将产生什么后果,远远比判断“在某些情形下必须转让股权”会产生什么后果要复杂而困难得多。
在传统法上,“契约必须遵守”的观念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合同是不连续的交易(discrete transactions),即存续时间较短、人际接触极为有限、交易风险容易测度。(30)典型的情形是简单的即时清结合同,如买卖合同等。在这种合同中,合同各方将未来的各种因素都“提前”纳入缔约时的考虑范围,并据此设计交易规则,以求拘束各方。
然而,与即时清结的短期合同相反,公司合同是一种长期契约。在公司这一相对而言变动不居、长期存续的关系中,面对纷繁芜杂、诡秘多端的商业环境,股东各方要事先合理准确地评估未来的成本和效益、并将其作为建立股东合理预期的基础,并不现实。而且,为了维护初始合作的良好信任气氛,股东各方往往本着乐观的情绪来制订公司章程。于是,如果只是依靠公司成立时的书面约定,来处理公司发展过程中潜在的种种机会主义行为,则表面上是在执行公司合同,保护股东预期,而事实上却是违背了股东各方的合理预期。
即便是力主“自由放任”思想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也承认长期契约中自由意志的局限:“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好法官,但这一原则的例外情形是:个人试图在当前做出一项不容更改的判断,即在某一未来甚或长远的未来中什么是他的最佳利益(易言之,这种判断勉为其难)……当约束人们的契约,规定的不只是简单地做某事,而且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内持续地做某事,并且本人没有任何权力撤销这一约定时,我们就不能假定这一契约是他们自愿达成的,否则将十分荒唐。”(31)这一论述获得了经验的支持。基于经验证据的调查,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得出结论:“对于未来将会出现的无数意外,个人无法完全认知,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假定;简而言之,大量的证据倾向于认为,的确存在低估不确定性的倾向”。(32)与此一脉相承的是不完备契约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使得事先不可能拟定完全契约,或者拟定完全契约因成本过高而不必要。
出于对公司成功的渴望和乐观情绪,股东各方往往对失败的后果、特别是对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滥权谋私的后果估计不足,极易发生判断上的错误——系统性地低估风险……即往往把一些并不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视为规律,并以此判断事物的发展趋势……于是,如果目前相安无事,股东就会认为前路一马平川,没有崎岖和波折……因为存在这种认识上的系统性错误,要求股东全面考量放弃股份转让权会诱发控股股东及高管哪些道德风险,进而会产生哪些代理成本,已经大大超出了股东在订立章程之初所能预见的范围。就此而论,禁止股权转让的章程规定无法拥有等同于普通合同的拘束力。
在普通的合同中,由于情势变更或者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发生变化,可以对合同进行更改,或者当事人以违约赔偿为代价而违反合同,尚有救济路径可循;而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之初或公司经营某一时点“资本多数决”的产物,一旦形成禁止股权转让的章程规定,即为公司制度,非经绝大多数股东同意不可更改。于是,如果该章程条款具有法律效力,则欲转让股权的股东将陷于“被锁定于”投资之中而无法自拔的尴尬境地,面对控股股东及高管高企的道德风险却毫无救济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同为股权转让的限制,特定情况下强制转让股权、或者股权转让的其他章程限制性规定,将特定情事与具体后果直接挂钩,大大提升了可预见性,已属短期契约,遵守其约定在通常情况下不会违背合同各方的意愿,而且不会产生负的外部性等代理成本,“契约应予遵守”的规定应予奉行。
“强制转让股权”以及“股权转让的其他章程限制性规定”的效力,与“禁止股权转让”的章程规定一样,本质上均为章程条款的正当性判断问题。在这方面,还应区分章程的初始条款及后续修订条款,以尊重契约的市场价格机制力量。
在公司成立之初,发起人先行起草章程,然后才可能向社会募集股份。在理论上,如果章程条款对投资者不利,他们就会用脚投票,股票发行价格将直线下挫,甚至无人问津。发起人对这种可能性的担忧,使其不敢轻易在章程中引入对投资者明显不利的条款。因而,在公司成立之初,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公司参与方通过权衡和博弈、自主议定章程条款,最终将达成最优选择。然而,在经营过程中修改章程,公司参与方的合意却远不够充分,产生了股东被盘剥的可能。为简化分析,兹举例释明如下:
某公司章程包含有A条款,一些投资者认为,因为A条款的存在,该公司每股值95元;如果没有A条款,则该公司每股值100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公司股票发行价不高于95元,这些投资者还是愿意购买,否则他们就可能置之不理。于是,因为投资者在购买股份之前就看到了这些条款,如不满意,大可不买。所以,我们还是能够认为,这一条款本身并没有减损投资者的任何权益。但后续章程修改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因为投资者已经“沉淀”了资本,即使章程的修改不利于投资者,但投资者受制于辨识和反应能力,不可能马上做出反应。他们即便不看好股票后期的市场表现,也不可能撤销交易,只能寻求在二级市场上“用脚投票”,但往往这时股价已经相应回落,投资者仍难逃章程不利修改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从公司管理层(他们往往负责章程的制定)的角度,又当如何分析章程的修订?仍沿续前述例子,初始章程如果载有不利于股东利益的条款,使得原本值100元的股票,在投资者眼里跌至每股95元,投资者的出价将不高于95元,甚至只愿出92元、91元……这样,管理层就必须承受至少每股5元的价格损失。这种股票折价发行的压力,使得管理层不敢轻易在初始章程中上下其手,以免募股失败。但章程的后续修改情形则大不相同,管理层因为不必承担全部的冒险成本,他们极可能将章程导向不利于股东的修改。
总之,根据私权基本法理,在股东财产上设定的任何负担如果已经事先获得股东的同意,则不能认定为是不合理的限制。章程初始条款中的股权转让限制,可以推定为获得了股东的同意;而章程的修订条款如果为股东转让股权设定了负担,则不能推定为获得了全体股东的同意,而必须经该修订条款拘束下的所有股东同意。鉴于我国公司法并不允许股东对公司章程有保留条款,因此可借鉴《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3条第3款的规定,在章程所规定的股东义务之外再行设定股东义务时,必须经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
此种分析理路可用于排除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章程条款的效力判断方面。具体说来,《公司法》第72条最后一款是对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补充性规定,即允许通过公司章程来排除或者限制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根据前述分析,应区别以下情况予以处理:(1)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或者有限责任公司存续期间全体股东一致表决同意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来排除或者限制部分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由于经过了全体股东的一致认可,因此公司章程排除或者限制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宜认定有效;(2)有限责任公司存续期间,多数股东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形式排除或者限制少数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由于该项规定未经过少数股东的同意,应认为其侵犯了股东权利,该项修改当属无效。(33)
五、出让股东“反悔权”:人为增加代理成本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若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时,转让人能否拥有“反悔权”,即是否有权撤销转让之意思表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主张赋予出让股东所谓“反悔权”的理由在于,这样有利于形成价格拍卖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出让股东的利益。而主张不应赋予出让股东“反悔权”的理由则在于,其他股东一经向出让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即缔结了一份内容和出让股东与第三方议定事项相同的合同。
应予指出的是,此种情境下的股东“反悔权”,本是一个假命题,因为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并无“反悔权”这一权利形态。严格来讲,此问题探讨的是,出让股东与第三方就股权转让达成价款等交易条件,通知其他股东之后,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此时,出让股东是否有权撤销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
一种反对赋予出让股东“反悔权”的传统规范法学观点认为,优先购买权在本质上属于形成权。(34)王泽鉴教授将优先购买权界定为附条件的形成权。认为优先权人得依一方的意思表示形成以义务人和第三人买卖合同同样条件为内容的合同,无须义务人(所有权人或出卖人)的承诺,不过此项权利附停止条件,须待义务人出卖标的物与第三人时,才能行使。(35)
在民法形成权的一般制度背景下考察,可以做如此理解:出让股东与第三方议定股权转让事项之时,隐含着向潜在的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转让股权的自愿,因此被法律构造成一个锁定的连环交易:只要出让人打算向第三人转让股权,在其他股东打算优先受让时,必然转化为向其他股东的股权出让交易。因而,在传统的规范法学意义上,出让股东当无“反悔权”,否则会导致出让股东无限制违约的可能。
而以降低代理成本为核心的法律经济学视角亦认为,赋予出让股东“反悔权”,同样至为不妥。买卖交易是典型的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而且在不伤及第三方(包括国家、集体)利益的情况下,双方的利益分配取决于他们的博弈能力,而并不存在必须最大化某一方利益的正当性,更不应允许存在一方福利完全取决于另一方行为的“代理问题”。在股权转让的语境下,无论股权转让价格是高还是低,其本质上均为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的利益分配差异,并没有一个层级更高的价值观,支撑着必须最大化转让方或者受让方的利益。因而,主张赋予出让股东以“反悔权”,以最大化出让股东利益的观点,无异于使受让股东的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让股东“是否反悔”或者“是否与第三方通谋恶意竞价”,从而凭空创设了出让股东与受让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问题,并不具有正当性。而且,在经济学意义上,任何定价都应是风险加权之后的结果,出价人必须承担自己对交易定价的后果,股权转让亦不例外。
优先购买权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同等条件”。在实践中,“同等条件”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可以包括同等价格条件(如对价形式、价金数额及支付方式等),也可以包括价格之外的因素(如职工安置等),甚至还可能体现为“购买人须为同事、朋友、亲戚”关系等,而到底哪些条件可以被公司法接纳为第72条意义上的“同等条件”,从而其他股东在满足这一条件基础上将产生“优先购买权”,则不无疑问。
在传统的规范分析意义上,股权出让方似乎完全可以自行设定股权转让的交易条件,既可以包括价金、数量等财产关系条件,也包括同事、亲友等人身关系条件。然而,在法律经济学意义上,股权转让的“同等条件”却不能以人身关系为基础。因为,股权转让必须是一种市场化的公允交易,即可以通过市场博弈来达成的交易。在股权转让中,其他股东被赋予优先权的基础——“同等条件”,应当是可以被抽象为价金的条件,即陌生人可以通过努力(报出更高的价格)而成就的条件,应当具有“可交易性”,包括股权转让的价格、数量、价金支付方式,甚至也包括职工安置(可以通过付出金钱来完成),而不能要求“购买人须为同事、朋友、亲戚”等人身关系条件,因为这些先天条件无法通过后天努力而实现,否则将造成出让股东向其他股东施加代理成本的格局。
在“与公司有关纠纷”中,股权转让纠纷之所以占相当大的比例,其主要原因在于涉诉各方对于股权转让中私权自治和国家强制的边界认识不清。而在一个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对效率有着极高要求的商事领域,“司法市场”有简洁明快地解决纠纷的需求。另外,正如自然界因物种的纷繁芜杂而富于多样性一样,调整不同领域的法律,其公平目标的实现方式也或有差异。相对于婚姻家庭等伦理情感法律领域、甚至相对关乎人之生死的刑事法律领域而言,公司法以及更为宽泛意义上的商法对于公平目标的追寻,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几乎完全等同于对效率的追求,尊重情感、伦理等在其他法律场域中可能要被考虑的多维目标,在商事领域则很难顾及。
对于效率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的效率分析。正如有学者指出,商法领域内的学术争议,更多地不是集中于法院是否应当追求效率,而是法院应如何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36)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降低代理成本为核心的法律经济学分析进路,对股权转让的私权自治与国家强制的边界厘定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完成股权转让的法律构造,有助于确立市场预期,减少纷争并降低讼累,最终提升社会福利。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研究生李润同学对案件的检索与整理付出了辛劳,在此表示谢忱。
①参见刘俊海:《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第二届公司法司法适用高端论坛论文集》,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与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联合举办,2012年5月。
②宁金成:《有限责任公司设限股权转让效力研究》,《第二届公司法司法适用高端论坛论文集》,2012年5月。
③参见蒋大兴:《被忽略的价格形成机制——论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中转让人的反悔权》,《第二届公司法司法适用高端论坛论文集》,2012年5月。
④参见赵旭东:《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和效力》,《第二届公司法司法适用高端论坛论文集》,2012年5月。
⑤参见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7—319页。
⑥该说首创于1875年的德国法学家瑞纳德(Renaud)。该学说认为,股东是公司的社员,股权是股东基于这种社员资格而享有的一种社员权。参见康德琯:《股权性质论辨》,政法论坛》1994年第1期。
⑦外部性又称为溢出效应、外部影响或外差效应,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分为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和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⑧通常而言,产品和服务可归为以下三类:(1)“搜寻型”产品和服务,例如衣服、鞋子和珍珠项链。这种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在被消费之前就可以确定,故其质量发现的成本极低;(2)“体验型”产品和服务,例如工作、电影、报纸、酒类和食品等。这种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在消费者购买之前通常难以确定,但可以在消费之后做出评价。故其购买前的质量发现成本较高,购买之后的质量发现成本则较低;(3)“信任型”产品和服务,例如保健、幼儿园、宗教和精神安抚、公司治理改革等。这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即使在客户消费结束之后仍然很难做出评价,或者即使能够做出评价,其代价也非常高昂。故“信任型”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无论在购买前还是购买后,其发现成本都较高,股权即属其一。参见Michael R.Darby and Edi Karni,“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6,no.1,1973,pp.67-68.转引自罗培新:《公司高管薪酬:制度积弊及法律应对之限度——以美国经验为分析视角》,《法学》2012年第12期。
⑨阿道夫·A.伯利、加德纳·C.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甘华鸣、罗锐韧、蔡如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30—132页。
⑩关于公司法语境下的代理成本问题的详细分析,参见莱纳·克拉克曼、亨利·汉斯曼等:《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罗培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52页。
(11)控股股东所拥有的所有权比重越低,这些问题就越严重。参见Luca Enriques and Paolo Volpin,"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s in Continental Europe," Journal o 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1,no.1,2007,pp.117-140.
(12)更进一步的分析,参见莱纳·克拉克曼、亨利·汉斯曼等:《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第36—52页。
(13)在通常情况下,有权投票的股东人数众多。除非在极端情况下,散股股东的投票对于结果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当成千上万的投票权人有权投票时,没有人期望自己的投票能够决定“博弈”结果。这样,股东就缺乏适当的边际激励去搜集掌握公司的相关信息,以做出正确的投票。这就是股东保持理性冷漠的集体行动问题。
(14)J.A.C.Hetherington,"When the Sleeper Wakes:Reflection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hareholder Rights," Hofstra Law Review,vol.8,1979-1980,pp.193-194;Nicholas Wolfson,"A Critique of Corporate Law," University o f Miami Law Review,vol.34,1979-1980,p.959; Albert Hirschman,Exit,Voice,and Loyalty: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and States,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21-30.
(15)Timothy K.O'Neil,"Rule 19c-4:The SEC Goes Too Far in Adopting a One Share,One Vote Rul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83,1988-1989,pp.1057,1077.
(16)如《公司法》第104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在美国,极少数的一些公司拥有不同种类的普通股,其表决权重各不相同。参见Daniel R.Fischel,“Organized Exchanges and the Regulation of Dual Class Common Stock,”University o f Chicago Law Review,vol.54,1987,pp.118,119.
(17)《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53条规定:“公司及其非流通股股东、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利用不正当手段干扰其他投资者正常决策,操纵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或者进行不正当利益交换的,中国证监会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认定主要责任人员为市场禁入者,一定时期或者永久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业务机构的高级管理职务”。该条从反面角度禁止了投票权买卖。
(18)分别参见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168条和第303条;《法国商法典》第L.225—18条和第L.225—103条;《意大利民法典》第2383条和第2367条、《意大利金融调解合并法》第126—2条(规定了任期内解职的情形,并且规定了股权公开交易的公司召开临时会议的最低持股要求);《日本公司法》第339(1)条(该条规定,只要多数同意即可无理由地解除职务)。
(19)《德国股份公司法》第103条第Ⅰ款。
(20)参见《修正示范商业公司法》第8.08(a)条。
(21)例如美国《纽约商事公司法》第609节(F)项规定:(1)如果股东已经将股票抵押给投票代理人,股东就不能撤销委托书;(2)如果投票代理人已经购买了或同意购买股东的股票,委托投票权通常被看作是股票交易的一部分,股东就不能撤销委托书。
(22)在美国,对于劝诱委托投票的严苛规制,向来是造反股东采取行动的主要障碍。1992年,SEC放松了诸多备案和披露要求,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Regulation of Communication among Shareholders,Exchange Act Release,no.34-31326(1992))的确,目前仍然存在股东集体行动的重大障碍,包括协同一致投票的5%以上的股东登记和披露要求。参见SEC Rule 13d-5(17 C.F.R.§240.13d-5(2008)).然而,今天的监管规则并非完全不利于美国的造反者。有益于其的法律规定并不少见。例如,法律要求进行广泛的信息披露,确保造反者的投票征集材料可以实际送达股东,而且通常允许小股东将股东议案附加于公司的投票委托表格之中。另外,美国还允许对成功的造反者的选战花费予以事后补偿的国家。例如,参见Rosenfeld v.Fairchild Engine & Airplane Corp.,128N.E.2d 291(N.Y.1955).转引自莱纳·克拉克曼等:《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第64页。
(23)沈四宝编译:《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24)参见王艳丽:《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再认识——兼评我国新〈公司法〉相关规定之进步与不足》,《法学》2006年第11期。
(25)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519页。
(26)罗伯特·W.汉密尔顿:《美国公司法》,齐东祥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218页。
(27)罗伯特·W.汉密尔顿:《美国公司法》,第216页。
(28)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493页。
(29)参见罗伯特·W.汉密尔顿:《美国公司法》,第218页。
(30)Paul J.Gudel,"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Exchange," Buffalo Law Review,vol.46,1998,pp.763-764.
(31)John Stuart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936,pp.959-960.
(32)Kenneth Arrow,"Risk Perception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Economic Inquiry,vol.20,no.1,1982,pp.1,5.
(33)参见马更新:《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几个实务问题的探讨》,《第二届公司法司法适用高端论坛论文集》,2012年5月。
(34)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35)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
(36)Lewis A.Kornhauser,"Constrained Optimization:Corporate Law and the Maxim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 in Jody S.Kraus and Steven D.Walt,eds.,The Jurisprudential Foundations of Corporate and Commercial La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87.
标签:股权转让论文; 法律论文; 代理成本论文; 公司法论文; 股权转让协议论文; 股权分配论文; 股权论文; 股东表决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