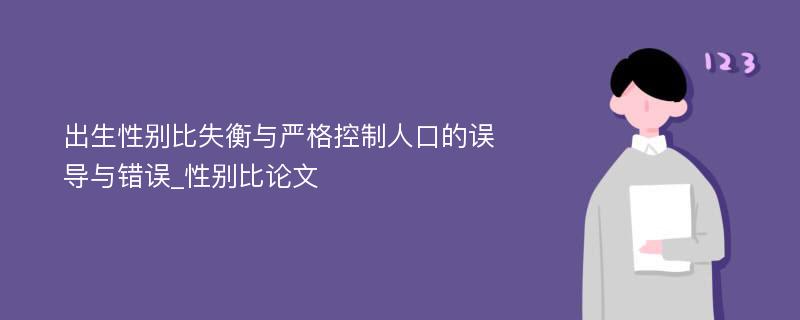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口中论文,严控论文,人口论文,性别比论文,制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尽管在初始的前4年中, 每年都超出了建立在独立随机事件基础上的正常值域上限107,而被列为异常, 但实际失调以整数年计算却是始自1984年,到200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已长达21年。伴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的速度从缓慢到加速,失调从轻度到重度,相应生育水平的波幅变化却由大到小、经稳定转为下降。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的这种相应变动,是在紧缩生育政策后,有了胎儿性别检测技术这一前提条件下的“特殊”反映。出生性别比是一个遵从大数定律的指标,失调必是人为干扰孕前或孕后胎儿性别所致,否则,不会发生失调。20多年间的生育水平波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主要是因人工流产女胎量的逐年加大,使本应出生的女婴量也随之相应加速减少造成的。
中国实施计划生育30多年来,既有执行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的生育政策,创造世界生育水平下降奇迹的时期;也有执行未考虑以人为本、脱离群众的紧缩生育政策,迫使计划生育工作及生育水平都陷入“怪圈”而历经曲折的时期。至于生育水平波幅逐渐变窄直至下降,而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性失调程度由缓慢加深到急剧加深,二者间的这种极不正常的一下一上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极端的人口现象。本文拟以回顾人口控制所走过的辉煌与曲折的道路,来论述相关人口控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21年中不可回避的若干问题,以便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一、出生性别比失调归因分析反映出的问题
若根据联合国(United Nations,1955)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102~107来判别,从1980年起,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开始失调,对此,业内人士众说纷纭。当出生性别比正处在107~108或略高于108时,有学者提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域上限是独具108或108左右,从而否认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异常。然而,出生人口性别比很快突破了108。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不断异常升高, 国内各种不同的归因结论相继问世。如徐毅等(1991)认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的原因,主要是瞒报、漏报女婴所造成的统计上的假象。乔晓春(1992)认为,1982年人口普查有漏报,1990年人口普查漏报更为严重,中国实际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在近十几年可能有所提高,但估计不大可能超过107, 现实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真实提高”和“虚假提高”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1993年,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出生性别比研究”课题组提出,人口普查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而日趋严重,出生性别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其归因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关系密切(于学军等,2000)。此外,还有与此相同或颇为近似的结论(顾宝昌、徐毅,1994)。出生性别比失常是中国和其他一些男性偏好强烈的国家和地区,在生育率迅速下降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涂平,1993)。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第一位原因是女婴漏报,加上溺弃女婴的陋习在少数地区仍然存在(曾毅等,1993);城镇出生性别比上升是“假性上升”,而农村出生性别比是“真性”与“假性”影响大致持平(李伯华,1994);出生婴儿性别比在中国是108左右, 如果调查结果高于这个数,一般就暗示着女婴有可能漏报(蒋正华,1994),等等。
笔者始终认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所谓的瞒报漏报女婴之类的统计不实问题,更不是所谓的生育率迅速下降的产物。如果把生育上男性偏好强烈的中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作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成因,那么,中国20世纪70年代创世界生育率下降奇迹时期,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就应失调,且失调程度也应比现在严重。但当时出生人口性别比却基本稳定,平均为106.3。10年内生育率下降了一半的日本,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十分稳定。
从人口统计学看,尽管在特定时期内的特定国家和地区,其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调有着高度相关关系,但仅以此为据简单下结论,则有失偏颇。因为相关分析首先要定性,即定性是相关分析的前提条件。只有在确定了其间确实存在着相关关系时,才能进一步做定量分析。凭借人口统计学中指标间相互关系的常识,若从相关指标逻辑关系上分析,惟一可直接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成因,到目前为止只可能是人工流产女胎导致本应出生的女婴而未出生。人工流产女胎,一方面使本应出生的女婴大大减少,另一方面也使总出生人口相应减少,生育率下降。
综观对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的各种归因分析与结论,从中不难看出,凡是没有建立在相关基础理论上的任何推论,都是靠不住的;任何以现象来解释现象和未透过现象分析其本质的所有结论,也是靠不住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误用相关分析得出的结论并非少见。因此,今后在认识上、分析研究上、决策咨询与决策上,都要尽可能避免类似问题再度发生。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决策失误
迄今为止,一些外国学者将中国近期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与旧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相联系。因为不分城乡地推行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必然令人联想到其在广大农村实施中难免会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生育问题上,正当在男性偏好相对突出的广大农村普遍推行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之时,出生人口性别比恰巧呈现出异常升高的态势。于是一些外国学者在未经调查又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把农村多数家庭强烈的男孩偏好与“只能生育一个孩子”间的矛盾,以及将此矛盾与一直把溺女婴作为旧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成因的结论相联系。例如,寇尔(Coale,1992)认为“溺婴的传统做法重新出现”; 艾尔德(Aird,1990)认为,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是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的溺杀女婴的结果;霍尔(Hull,1990)也认为首位的原因是溺杀女婴。
这些外国学者把旧中国低年龄人口性别比近似为相应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从而定论溺女婴陋习导致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然而,把低年龄人口性别比近似的作为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其本身就存在着把旧中国女性低年龄人口死亡概率超常高于男性这一重要因素未考虑在内的重大缺陷。另外,无论是从人口统计学时限规定上看,还是从出生人口性别比定义及其内涵上看,所溺女婴都应在未溺前纳入出生人口及其分性别统计。即使溺前未统计,事后也应补上。因为人口的出生,指的是那些发生在出生时刻有生命现象的活产婴儿,而所溺女婴发生时间必是在出生那一时刻之后,即出生事件在前,溺女婴事件在后。可见,出生女婴与所溺女婴在统计时限概念上根本不同。凡是称旧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研究者,均未将所溺女婴归入女婴出生统计,故得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误论。若得出的结论是0岁性别比失调就无可非议了。由此可知,与出生人口性别比有关的只能是未发生出生事件的那些胎儿的性别是否受到干预而发生了变化。只要有相当数量的孕妇对所孕女胎实施了流产,那么,由此所导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动,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
20世纪80年代至今,受人口控制及其所形成的年龄结构影响,中国年均净增人口从1500万左右降至1000万左右。与之相比的极少数溺女婴现象,其量是微乎其微的,在出生性别比统计中可以忽略不计。
1992年,国内大多数研究人员,将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1989年出生人口性别比(111.92)失调的主要成因,误归咎于瞒漏报女婴,从而把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说成是统计不实。事实上,这就等于否定了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果,表明实际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远不像普查所揭示的那样严重。1994年,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1/2~3/4是由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注:于学军等主编:《中国人口发展评论:回顾与展望》,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
由于政策决策者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与分析上欠缺科学论证,尤其是未充分倾听不同意见,难以全面、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进程,在指导思想与认识上难免出现偏差。这也是计划生育工作及其人口控制成效往往被高估、被夸大,一些结论经不起实践检验,一些做法不能持久,一些问题被掩盖的原因所在。最为明显的是,对当时已持续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未能正确认识, 既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够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监管和及时纠正,最终酿成了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逐年持续加剧的历史性失误。
三、紧缩政策与低生育水平付出的代价
20世纪70年代实施“晚、稀、少”生育政策成效显著。它不仅对当时及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而且对80年代后期以来的劳动就业、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都起了持续减缓压力等积极作用。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全社会都在尽享着“人口红利”带来的持久效应。若1979年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不刮“紧缩生育政策风”,1980年的全国生育水平,无疑将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这样,“人口红利”的作用,必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显现。此外,当时生育水平在城镇降至只生育一个孩子,在农村降至生育不足三个孩子,且其第三孩生育又处在急剧下降的通道中,都是在生育政策允许计划生育两个孩子的条件下实现的。
然而,当时有学者做了中国百年人口预测,提出按照1980年平均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的误称)为1.5的测算方案制订长期人口发展规划, 可能更切合实际。规划2000年全国总人口为11.3亿,而2020年和2030年均为11.8亿;认为在全国大约有1.2亿育龄妇女中,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仅占6%,要提高到占百分之六七十, 这中间包含着一场深刻的生育观上的革命,工作十分艰巨。一定要大力做好提高和巩固“一胎率”工作,实现20世纪末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设想(宋健等,1981)。时过不久,又有学者提出,12亿绝不是一项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而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实现21世纪总人口稳定在八九亿水平的长远规划也是有希望的,如果20世纪最后18年的工作做得不好,过去的努力就要事倍功半,百年后全国人口突破十五六亿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计划生育工作做得稍差一些,2000年总人口将超出12亿,但超出不会很多(田雪原,1984)。今天看来,虽然实践已对这些结论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但在当时“左”的思潮尚未清除,违背科学发展进程,超越发展阶段的“大跃进”思想,仍有相当广泛的市场基础。
从人口科学来看,人口预测完全是一种不同参数下的人口发展趋势模拟。至于其准确性,一是取决于预测模型的科学性;二是取决于参数的模拟是否与未来实际人口变动的相应参数吻合。参数的选择与确定,只有经过深入的社会实地调查,反复比较研究,反复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后,才能在多次论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因此,人口预测的前期工作是十分繁杂而艰巨的。即使这样,人口预测也没有数十年可信度的实例,更何况百年、数百年的人口预测。当时有学者认为,“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注: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远脱离实际。可见,即使是相当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预测,也只能作为人口规划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指令性的人口计划目标来执行。
在“晚、稀、少”生育政策远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本应稳定的生育政策,受所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及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和其相关论述的舆论影响,诱发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急于求成,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中的“提倡”二字,不分城乡地紧缩成了“只能”。其结果不仅没能将生育水平紧缩下来,反而引发了生育水平和人口出生率的报复性反弹,也使计划生育工作遇到了空前未有的阻力,而且在国内外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长期负面影响(马瀛通,2002)。
在生育水平及其生育模式大幅滑坡的情况下,大部分地区为了年人口计划的达标而在统计中掺“水分”。因此,“水分”便成了人口计划达标的人为筹码与公开秘密。计划生育工作所走的这段弯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斥责“左”的东西时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7页。)
相对“只准”生育一个孩子来说,始于1984年的完善生育政策,虽使生育政策的可行性大为改善,但多数农村地区的生育政策偏紧问题仍未根本解决。而在那些凡经批准又恢复执行“晚、稀、少”生育政策的农村,生育水平及相关指标不仅迅速恢复到了1980年水平,而且还创出了历史新低,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也从未发生异常。
1991年5月12日,在多数农村地区生育政策偏紧、人口计划又难以完成的双重矛盾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从实际人口控制能力出发,以远宽松于现行生育政策限定的出生人口量,求实地调整了20世纪末人口控制计划目标,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个必须尽最大努力才能完成的计划。显然,这是自1980年以来,最具求实意义的一项决策。
然而,调整人口计划的实质及其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未被逐级所认识。落实到农村家庭实处的具体出生计划,并未因人口计划的调整而有任何变动,偏紧的生育政策仍是惟一的准绳。
在生育率越低越好这一偏颇观点的影响下,鉴于各地仍把执行偏紧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计划生育率”作为考核的内容,加之在省级以下的各级行政区,人口计划又普遍存在着下达不合理及不科学的考核、评比、排队等问题,从而导致上报的出生人口数普遍都远远小于计划下达的出生人口数。如果上报的出生人口数果真是这样,那么,国家实在是没有调整人口计划的必要。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逐级出于政绩考虑,普遍都是以考核的指标内容为依据,有组织地在其统计中“注水”。这种虚报的人口计划完成情况,因其所依据的是生育政策,所以就与计划生育政策所限定的计划出生人口数颇为近似,从而把本应尽最大努力才能完成的年人口计划,竟按偏紧的生育政策所限定的计划出生人口数而轻松完成。其“水分”之大,竟使在客观存在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内,理应出现的高峰这一必然人口现象也被“水分”淹没了,就是在其峰值年份也未见到一点出生高峰的踪影。显然,此间的成绩是被虚假数字过分夸大。这种自下而上的虚报,竟迫使国家统计局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准确性,也大失水准且每况愈下。
鉴于各地普遍顾虑在人口普查中暴露出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中的“水分”,故各种应付考核的对策使2000年人口普查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此次普查的低年龄人口仅以国家教委统计的相应小学入学人数作为参照,其间漏报数量要以千万计。无疑,这将给今后工作及其目标的制定带来了一大难题。
始于1984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在持续了数年的缓慢加重而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生育水平才略显下降端倪。伴随着人为干扰胎儿性别的数量加速上升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程度的加剧,生育水平才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较其之前有了较为明显的下降。
随着B超仪的日趋增多及检测胎儿性别的逐步蔓延,流产女胎的数量同时也呈加速增长,从而使出生女婴比重本已偏低的问题日趋严重。本应出生的女婴因胎儿性别选择而流产,故大大减少了本应出生的人口数量。人口出生数量如此减少的这种变化过程,既是1984~1990年间,生育率在前期呈波幅变小,末期呈略微下降的主要成因;也是1991~2004年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急剧加重,生育率明显下降的主要成因。至于极少数农村家庭为达到生一个男孩目的,采用“游击”方式生育的女孩之多,虽令人吃惊,但对整体生育水平来说却可忽略不计。据分析,以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度失调为代价的2000年全国妇女平均预期终身生育子女数,最乐观的估计约为1.8~2.0。
近年来的农村社会调查显示,虽然坚持要生有一个男孩的家庭比例较高,但要生有一男一女的家庭却仍占绝大多数。囿于多数农村地区的生育政策是,已有一个女孩的夫妻可允许计划生第二孩,因此,孕妇第一胎做性别检测的很少。即使第一胎性别检测为女,大多数也是生下这个女孩并如实申报,但对所生第二孩却非要等到胎儿直至检测为男性时才生;囿于生育政策不允许已有一个男孩的夫妻生第二孩,部分家庭为了再生一个,要么将男婴误报为女婴,要么瞒报出生。极少数所生两个及以上都为女孩的家庭,为了生有一个男孩,往往瞒报出生,逃避处罚,直到他们认为相关政策对己适宜时,才去申报出生。足见人为胎儿性别选择及流产女胎,既是致成第二孩及以上分孩次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并随孩次升高而升高的成因,也是致成第二孩及以上分孩次出生性别比远高于第一孩出生性别比的成因。分析与近期的调查都表明,瞒报的男婴要多于女婴,甚至女婴还有可能多报,否则,就不合乎那些计划外生育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逻辑。因此,实际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及低年龄人口性别比,只有较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高而没有较其低的可能性。
随着时间的顺延,年龄则从高向低顺延。2000年人口普查的全国低年龄人口性别比,从10岁的111.39至1岁的122.65,呈逐年龄持续显著上升态势,即随时间的顺延,呈逐年加速异常上升态势。据此可以推断:一是1990~1999年间的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呈逐年加剧态势;二是2000年普查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因大幅低于1岁的性别比5.79个点而与其上升态势不符,合乎逻辑的是,其最低也要等于或大于1岁的性别比(122.65)。据此推算,至少要有30.28%的孕妇做过胎儿性别检测;三是2000年人口普查时的全国分市、镇、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同理最低也要等于或大于各自1岁性别比114.95、121.42和125.49。据此推算,分别至少要有15.38%、27.90%和35.70%的孕妇做过胎儿性别检测。然而, 在男性偏好相当微弱或基本消失的大城市城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就从未发生过失调。
近期,对以持续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为代价或为主要成因所获取的低生育水平,务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代价既是酿成新人口问题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危险信号和警钟,也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规律认识不够充分,多数农村地区生育政策仍然偏紧等问题的综合反映。
四、出生性别比失调下的婚配年龄段婚配性别比问题
一个人口在其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主要生育旺盛年龄段妇女的年龄结构又相对变动不大的条件下,该人口的历年出生率必处于相对稳定而又无较大明显差异的状态。因此,由历年新生人口构成的各低年龄人口,其数量间的差异必然也相对很小。若在此条件下的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重度地升高性失调,就必将酿成在其进入婚配年龄段时,凸现出女性人数的相对短缺,危及此年龄段人口的婚配性别平衡问题。这无论是从以人为本、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方面考虑,还是从影响未来家庭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方面考虑,都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大事。
20世纪80年代的低年龄分性别死亡水平,因早已降至相当低且变动又小,故可将低年龄段的各分年龄性别比作为近似相应年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即使从1984年开始,有了胎儿性别选择与人工流产女胎的影响,仍可以照样近似地使用。鉴于此间历年的人口出生率波幅较大,其所生成的分年龄人口势必其间差异也较大。因此,即使20世纪80年代的若干年份出生人口性别比有一定程度的失调,但在平均初婚年龄男性大于女性3岁左右的婚龄差条件下, 进入婚配年龄段内的分年龄男女人口绝对数差异,恰好对此婚配年龄段人口的婚配性别比起了一种平衡调节作用。可见,20世纪80年代中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及其失调程度,不足以构成其婚配年龄段人口的婚配性别比失调。因此,中国在2010年前,进入婚配年龄段的人口不会出现婚配性别比失调的问题。
上述结论清晰地告诉我们,历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其进入婚配年龄段的婚配性别比,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婚配性别比”,是指婚龄青年性别比,也泛指第三性别比。不同年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并不等于其进入婚配年龄段后,相应婚配年龄段的婚配性别比也失调;进入婚配年龄段的人口,其婚配性别比正常与否,关键取决于进入婚配年龄段动态变化的总计人口分性别结构是否匹配,而不取决于各相应年龄在出生时一定程度上的性别比是否正常。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个人口在一定时期内的出生男婴数与女婴数之比,不同年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由不同年份出生人口中的男婴数与女婴数之比。不同年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所代表的分性别出生人口绝对数是不同的,其间差异或大或小或基本无差异。婚配年龄主要涉及的是一个主要初婚年龄区间或称主要初婚年龄段,而不是同龄男女人口数的一一对应。因此,婚配年龄的性别比正常与否,关键是在主要初婚年龄段内总的男女人口绝对数是否匹配,而不是其各分年龄人口的性别比是否正常。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或超常升高,使不少人产生了这样一种误解,即当这一批人到了婚配年龄时,将有相当数量的男性找不到配偶。如果这样,即使同年出生的人口,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6~107的值域范围,在历经死亡变动到了初婚年龄时,若其尚存到初婚年龄的人口其性别比为105~106,那么,同龄人口的婚配也将有5%~6%的男性成不了婚。以此类推,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男性成不了婚的比重就越大。由此可见,在远离非稳态人口条件下,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来推断未来婚配性别比失衡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只要婚配不是在同龄人口中进行,就必须考虑分年龄分性别的结构差异,即必须考虑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绝对数差异。因为婚配性别比不同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因此,不可将其等量齐观,简单化之。
目前多数业内人士都是以历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否正常,来推断其相应进入婚配年龄时的婚配性别比是否正常,这种推断是不正确的。因为人口出生率在持续波幅较大与波幅较小条件下,所生成的历年0岁人口数量差异大不相同,而这种数量差异的大小,可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一定程度失调的条件下,在其进入婚配年龄段时,既有产生婚配性别比失调的一面,也有不产生失调的一面。因此,简单的以某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来定论在其进入婚配年龄段时的婚配性别比也一定失调,显然是要出问题的。
若历年的人口出生率波幅较小,那么,相应所生成的历年0岁人口间的数量差异也较小。在人口出生率平稳或变动较小的条件下,鉴于历年0 岁人口间的绝对数差异不大,若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那么,相应所表征的男女绝对数差异,在其婚龄差区间,就不足以对其婚配年龄上的男女数量起平衡调节作用。所以,出生时的性别比失调,在其进入婚配年龄段时其婚配性别比也失调。可见,在人口出生率平稳或变动较小的时期,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则基本决定了其进入婚配年龄段时的婚配性别比也失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年的人口出生率波幅都较小。在此条件下,绝大多数研究出生性别比失调成因的结论错误,导致了主管部门的误断及决策问题上的失误。这种失误,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严重性,既给予了淡化又给予了否定。因此,麻痹了人们对其关注及重视,延误了对它的及早纠正。这即使其后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进一步加剧,也使约在2010年以后才开始逐步显现的婚配年龄段婚配性别比失调,在一段时期内将呈逐年加重态势。至于是否因此而一定会引发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根据历史的经验现在还不能武断地做出肯定的回答。目前只能断言的是,不可低估因此问题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可能性。当然,对持续升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纠正得越早,未来相应所受其害的持续时间及所付代价也必然相应减少,反之就增大。
鉴于有可比性的缘故,笔者采用联合国曾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上限为107,作为推算依据,以中国1990和2000年人口普查中相同出生队列性别比较高值为选取对象,并将其近似地视为历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这样就可留有余地地推算出因胎儿性别选择而流产的女胎数。结果显示,因流产女胎使本应在1984~1990年间出生的女婴短缺了约230万,年均女婴短缺数量约为32.86万;使本应在1991~2000年间出生的女婴短缺了约1026万,年均女婴短缺数量约为102.6万。1991~2000年的年均女婴短缺数量,不仅远高于1984~1990年,而且还是它的3.12倍(见表)。
鉴于1984~1990年间的历年出生人口绝对数差异较大,尽管此间的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但从此间的分年龄人口差异及其失调程度来分析,在进入婚配年龄段时其婚配性别比都不会发生失调。因此,在2010年前,不可能在数量上发生“男子娶妻难”的问题。
上述估算的短缺女婴量是根据表中历年出生人口数和从出生队列选择的性别比(近似视为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通过男婴出生比例=出生婴儿性别比/100+出生婴儿性别比,女婴出生比例=1-男婴出生比例,可分别得到出生男婴数和出生女婴数。然后,以出生人口性别比上限107为标准,计算分性别出生婴儿数。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计算的出生女婴数,减去以失调出生人口性别比计算的出生女婴数,即为因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而在分母中异常减少的出生女婴数;以失调出生人口性别比计算的出生男婴数,减去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计算的出生男婴数,即为因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而在分子中异常增加的出生男婴数;相应于以出生人口性别比上限107为标准的分子异常增加量与分母异常减少量,基本是相同的。因此,无论是选择分子的男婴异常增加量,还是选择分母的女婴异常减少量,只要将其乘以2, 其结果就基本可以视为是所孕胎儿在中晚期经性别检测后,因人工流产女胎所酿成的本应出生而未能出生的女婴数。
表 1984~1999年中国出生人口数及按性别比计算的分性别比出生人口数、女婴差异数
万人
年份 出生人口数 出生人口性别比 出生男婴 出生女婴
出生人口性别比=107
女婴差异数
(M)
(F[,1])出生男婴 出生女婴F[,2] F[,2]—F[,1]
1984
2055108.64 1070
985
1062
993
8
1985
2202108.65 1147
1055
1138
1064
9
1986
2384108.47 1240
1144
1232
1152
8
1987
2522109.12 1316
1206
1304
1218
12
1988
2457110.11 1288
1169
1270
1187
18
1989
2407111.59 1269
1138
1244
1163
25
1990
2391113.39 1271
1120
1236
1155
35
1991
2258113.48 1200
1058
1167
1091
33
1992
2119114.61 1132
987
1095
1024
37
1993
2126115.21 1138
988
1099
1027
39
1994
2104116.59 1133
971
1088
1016
45
1995
2063117.77 1116
947
1066
997
50
1996
2067118.52 1121
946
1068
999
53
1997
2038120.48 1114
924
1053
985
61
1998
1991122.07 1094
897
1029
962
65
1999
1909122.65 1052
857987
922
6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鉴于男婴出生比例=出生男婴数/出生男婴数+出生女婴数,尽管在出生人口中, 分性别的婴儿出生概率略有差异,但分性别出生婴儿所占比例,在出生人口数不变的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任何变动,基本可以近似视为减少的女婴出生量或增加的男婴出生量都是“双向”的,或称是2倍的量。此处选用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上限107作为标准,主要是为了充分估计问题,在计算上也留有余地。对于所测算的数据,只有通过验算证实也是正确的,才能认为初步推算的结果是可信的。
如以出生人口性别比上限107为标准,其男婴出生比例是0.5169,女婴出生比例是0.4831。在以女婴出生比例为条件时,可知每出生0.4831女婴则相应出生0.5169男婴,因此,每出生0.4831女婴×2,即0.9662个女婴(近似为1个女婴),才相应出生0.5169个男婴×2,即1.0338个男婴(近似为1个男婴)。若仍以此为例,一般算法应该是:每出生1个女婴所需的出生婴儿数为1÷0.4831=2.0700,每出生1个男婴所需的出生婴儿数为1÷0.5169=1.9346。
以1999年为例,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2.65,则男婴出生比例为0.5509;女婴出生比例为0.4491;出生人口为1909万,出生男婴数=1909万×0.5509=1052万,出生女婴数=1909万-1052万=857万;以出生人口性别比上限107为标准计算,得到男、女婴出生数分别为987万和922万。异常短缺的女婴数为65万×1.9346=125.75万。另外,若将推算短缺的女婴数(125.75万)加到出生女婴数(857万)中,失调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22.65)就可以还原为107,就可验证推算的正确性。如1025万÷(857万+125.75万)=1.0705,当女婴为100时,出生人口性别比107.05与107较接近,所以,证实了短缺女婴数为125.75万是可靠的。
1984~1999年,以出生人口性别比上限107为标准,总计短缺的女婴为1126万。若2000~200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均按122.65计算,总计短缺的女婴为650万。 这样,因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在1984~2004年间短缺女婴为1776万。
上述的推算结果,若考虑到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对1998~2000年历年人口数的调整,显然原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是偏低的。为了充分估计问题,女婴的最大短缺量估计在1800万左右。
近来有学者误用出生人口性别比概念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数据推算短缺的女婴数,推断婚配年龄段的婚配性别比失调问题,得出一些令人震惊的结论,造成一些认识上的混乱。如有人提出中国近一个时期以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导致短缺了3000万女婴,将产生3000万“光棍”,并指出,2005年起中国开始出现男子娶妻难(解振明,2004),是过于夸大了失调程度及其后果。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婚配调节只不过是一系列调节机制中的一环,仅在此环节上的调节欠畅,还不足以断定必对全局产生影响。因为婚配调节,总是受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婚配观念的制约,而影响婚配观念诸因素作用力的大小,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不同。显然,婚配调节不单纯是一个婚配年龄段人口的男女数量匹配问题,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及婚姻观念、择偶观念、择偶条件的变化,除一部分选择终身不婚的独身者外,最终无偶可择的将是综合素质较差的那部分男性婚配年龄人群,而该人群恰恰又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主要诱因。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当这部分人口进入婚配年龄段时,终将是引发婚配性别比失调及相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不可掉以轻心。然而,因战争或天灾人祸所酿成的婚配年龄段人口婚配性别比失调问题,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中国自古以来的各朝各代都有因战争丧失了不少男青壮年人口的时期,“二战”后一些欧洲国家,以及朝鲜战争后的朝鲜,无一不是这样。虽然这些婚配年龄段人口的婚配性别比失调,都是女多于男的偏低性失调,但其实质都是进入婚配年龄段人口所发生的婚配性别比失调。这种失调几乎均未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进入婚配年龄段的男多于女的偏高性失调在旧中国也出现过,同样未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近十来年的各低龄人口性别比失调程度要比旧中国高得多,因此,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假定进入婚配年龄段的婚配性别比偏高性失调与偏低性失调的影响作用是一样的,那么,今后只要能妥善地解决好相关问题,历史上可以避免发生的问题,今后仍可以避免发生或发生的轻一些。
五、稳定低生育水平,力促出生性别比复归正常
稳定低生育水平与力促失调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复归正常,是一项必须实施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本来是不相关的两个指标,然而,在具备了检测胎儿性别的现代科技条件下,因对胎儿性别检测技术的滥用监管不力,竟使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转化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关问题,从而使稳定低生育水平与力促失调的出生性别比复归正常,成了解决一对相互掣肘矛盾的复合体问题。若在全国生育水平中,扣除掉出生性别比深度失调的因素影响,即把人工流产的女胎假定还原回本应出生的女婴,估计现生育水平大约就在更替生育水平上下。因此,在通过立法来确保对胎儿性别检测技术的监管下,失调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复归正常的过程中,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不可有丝毫的麻痹和懈怠。尤其是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度失调的地区,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低生育水平是内含有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因素在内的低生育水平,一旦胎儿性别检测技术的应用得到有效监管,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复归正常,也就是说,酿成出生性别比失调成因的人工流产女胎数,又逐渐地被恢复为正常的出生女婴数,那么,是否还能稳定住低生育水平?如果不能,那么,失调的出生性别比若复归正常,究竟会对生育水平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务必要做到心中有数。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复归正常,生育水平有可能回到更替生育水平以上。因此,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复归正常的过程中,仍要继续大力降低生育水平。
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不要让下一代人承担因上一代人过错而带给他们的惩罚。明天的中国人口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我们今天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的认识和努力。要全面认识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现状,只有真正深入实地调查,而不是被带领到那些专供应付检查及参观的地方做调查,才可能调查到真实情况,掌握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现状,才能不被虚假的数字所迷惑,才能对目前低生育水平及人口控制能力有一个客观而清醒地认识,才能在努力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实事求是地解决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
中国人口控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21年所突出显现出来的问题,暴露出人口科学研究工作的滞后,暴露出决策不仅科学论证不足,而且缺乏群众的民主参与及听证。中国人口研究工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探索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发展规律,增强预见性,减少盲目性。然而,部分已被实践检验证实是错了的东西,至今也未见有人反思。
今天,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为此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其中有的代价是失误性的。失误是构建和谐社会危害最大的因素之一,失误的代价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所经历的道路太曲折,付出的努力太艰辛。因此,回顾中国从严控制人口的历程,有喜也有忧,有经验也有教训。然而,将其作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所经历的一个短暂侧面史,来引以为鉴,就足见科学二字的分量,足见严肃科学,重视科学,尊重科学,增强决策与指导工作的科学性是何等的重要。
标签:性别比论文; 生育率论文; 生育年龄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怀孕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 人口普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