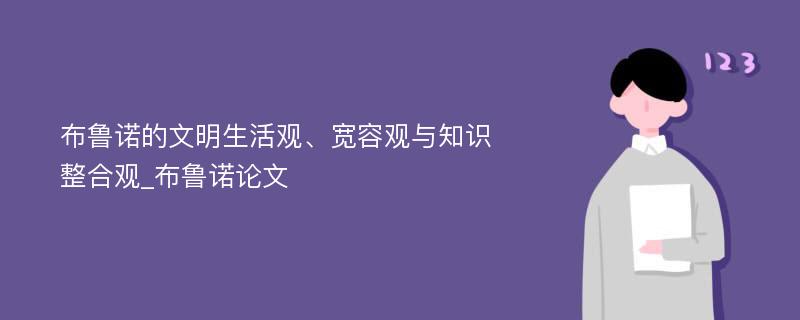
布鲁诺思想中关于文明生活、宽容及知识的完整性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鲁诺论文,完整性论文,宽容论文,观点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难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这是由于我置身于你们中间、面对享有如此声誉的听众。对我以及我这一代的许多欧洲青年来说,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她是希望所在。在我这次极其荣幸的来访中,我内心又涌起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感情。从一方面说,我有幸发现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她所具有的风俗、语言和景色与我所熟悉的很不相同,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好像在自己的家里,好像又回到了自己所生活过的卡拉布里亚大学里,回到了与一大群来我省进修意大利文化的中国学者和学生接触的那种习以为常的情景中。在1979年,正是由于吕同六教授的友谊和慷慨,我在卡拉布里亚与中国有了第一次接触,接触到她的佳肴、她的传统、她的文化。
自那以来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中布鲁诺的研究经历了辉煌的阶段。在意大利和全世界发表了许多关于他哲学思想的论文。在德国、西班牙、罗马尼亚、日本、美国、丹麦也开始翻译了布鲁诺的意大利语著作和他的部分拉丁文著作,现在,因为有了由意大利文化专家梁禾翻译的、由享有盛誉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举烛人》,中国在研究和普及布鲁诺思想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只有在自如地驾驭对一个文本的评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阅读一部作品并将它翻译成各种语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乔万尼·阿基列契亚编辑、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哲学研究所所长切拉尔多·马洛达主持、巴黎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布鲁诺的七部意大利文著作的现代评论版,显然是本世纪出版界最重要的事件。
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由于罗马教廷的命令而遭火焚,作为一个宇宙无限论的哲学家被载入史册。他比哥白尼还要哥白尼,他要比那个波兰天文学家的天才发现走得更远:布鲁诺把这个从旧宇宙学(即地心说)跨向新宇宙学(即日心说)的一步,视为宇宙革命的第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布鲁诺认为,哥白尼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自己数学计算的巨大的革新意义:地心说一旦被摧毁,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可以是组成无限宇宙的许许多多行星系的一个。在一个不再存在绝对中心的宇宙里谈论日心说毫无意义。空间的无限已经取代了关于它有限的说法:新的可能性打开了人的头脑,使它可以巡游到无限的世界,使从旧哲学沉重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思想能驶向新的、无限的终极的世界。
但是,布鲁诺的这种对哥白尼的激进理解导致了一个显而易见、似非而是的现象。一旦否认宇宙以人为中心(即人是宇宙的中心),将人挪置到了最边缘的空间,那么同时恰恰是在这个边缘上,作为个人,人重新找到了自我:在一个没有绝对中心的宇宙里,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是一个中心。
布鲁诺为使人类重获一个不仅不取缔、相反重视差异的天地,而把关于世界是封闭的、有限的古老概念、把一个严格系统化的世界打破了。在这个无限的空间里,最大与最小的原子核一概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每个物体,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
布鲁诺抨击障碍,打破局限,但他不取消差异。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他明显地注重细节,也注重局部和个别现象,注重具体的个人。在《驱逐趾高气昂的野兽》中极优美的一页里,布鲁诺回忆起距那不勒斯不远的故乡诺拉镇上的一些人物。在此,通过罗马神墨丘利(即希腊神赫耳墨斯)完成份内任务的过程,让众神之王丘比特的心态表露无遗,以此表现他是怎样对表面上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心的:
丘比特命令说[……]阿尔本佐的妻子瓦丝塔,当她想要在两鬓做卷头发时,由于火钳烧得太烫,而烧掉了57根头发,但是只要这次她没烧着脑袋,闻到那焦臭你们就别埋怨[……]让旦尼斯师傅把在桌上裁剪的裙子扯掉。让康斯坦丁诺床上的十二个臭虫跳出来,让它们到枕头那儿去:七个大的,四个小的和一个中的,至于它们的前途怎样,我们到了明天晚上掌灯时再说。等到同一个时辰里的15分钟过去之后,让舌头在上颚转上四圈,费如洛的老女人的下颚的第三个床牙就会掉下……(见我关于布鲁诺的书,耶鲁大学出版社英文版第90-91页)
这段对日常琐事的滑稽描述表明了在“微小”、在那些似乎是多余的事情上下功夫的必要。布鲁诺强调观察在每个人物身上发生的具体忧虑所表现的人生微观现象的必要性。布鲁诺坚持对人生无所不在的具体烦恼和各个人物的微观世界进行观察的必要性。尤其是对不同的对象(无论是人还是动植物)持续关注,以使人在看问题时灵活地使用合适的立场,让人必须进入每一个具体事件的细节中去。墨丘利的介入,使布鲁诺有机会指出,任何事物不管大小都是一个整体的某个部分。
布鲁诺在否认有任何局限存在和保存差异之间保持一种困难的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使其核心思想的一部分得以具体和形象化。这位宇宙无限论的哲学家选用地名诺拉诺来给自己的作品签名,以此来纪念自己地理和文化上的根基。
也许布鲁诺这个理论上的努力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最近几年里,欧洲共同体所有的国家一直在寻找这个艰难的平衡:取消国界,打破国家之间的障碍,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而不是消除各自的文化、各自的语言和不同的历史根基。同样,不应当把对自己民族性的合理捍卫与强暴的民族主义、与建立在种族优势和种族主义的变态意识基础上的陈旧的扩张主义野心混淆起来。
尽管历史环境和经济状况不同,这些论题也伴随了中国关于自己文化特性的讨论。在你们的共和国里有许多民族共存,有多种语言和不同的宗教信仰。这里,人们同样力图保存自己的文化根基,而不失去同属一个多民族的、同属一个已经代表了世界上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的伟大国家的意识。
在布鲁诺的哲学里,多元性是一个生动的部分,它代表了我们所处的现实的特点。语言的多样性和民族的多样性不应当被视为人类发展的障碍,相反,它们应当被作为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保存下来。
在认识论上同样如此。布鲁诺一再坚持哲学思想和方法的多样化。一个真正的哲人不会保持单一性,而是讲究多重性;不会只谈论一门哲学,而是各门哲学;不会局限于一种方法,而会使用多种方法;不是只坚持一个真理,而是各种真理。在一个无限的宇宙之内,在一个没有中心的宇宙里,不可能提出一个绝对的、对全人类、对各个历史阶段都合适的观点。
多元性不仅标志着我们生活的现实,而且对立事物的互相转换和共存也同样是我们现实的特征。现实是基于对立现象的转换和互补而存在的:一个起点的延伸往往与另一个的衰退共存。这种永恒的互换,简单说来也就是中国哲学中阴阳互换互补的理论。所有的存在都是在不断地运动,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布鲁诺将亚里士多德古老的宇宙论与托勒密理论互相分离的状况结合了起来:天和地、高和低,在无限宇宙的内部存在着同样的规律,它们是由同样的物质形成。最大的天体系(如太阳)和最小的(如蚂蚁)均以不同的比例,由相同的基质组成,它们都受到同样的生命力的推动。
在布鲁诺的哲学思想里,人与任何动物的区别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没有一个上帝曾宣判人要比动物高超。因为从大自然本身来说,所有的存在都以同样的基质构成。人胜于蛇或狗熊的优势并非由于抽象的等级划分而得到确认,而是通过具体的自然条件,在于特殊的体态成形。人能够比动物更会利用他们的躯体。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来改造自然,建立文明;人能够完成的事业,其他任何生物绝对无法完成。
人也是跟其他动物一样的动物。但人通过双手和智慧能够解脱自己的动物状态,变成“大地之神”。布鲁诺在《驱逐趾高气昂的野兽》和《贝加索神马之迷》中对双手的赞美,是对人从自然转向文化过程的象征性歌颂。劳动,即体力和脑力的操作,是我们实现各种目标、发展我们智慧的唯一手段。
然而为了从根本上理解这个对劳动、对实践、对作业的赞美,我们得观察一下布鲁诺的有争议目标。我们的哲学家知道,16世纪的欧洲正处于极度的危机之中。从各个方面来看,社会都在宣扬那种让人无动于衷、让人呆滞闲散的榜样。布鲁诺对这种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抨击,只要它们在哪里出现,他就会在哪里向它们进攻:在文学里、宗教里或者哲学中。当然它们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表现,但其本质都一样。
现在我们先讲文学方面。克里斯多弗罗·哥伦布的远航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在欧洲引起了对黄金时代神话的复兴。“新世界”里原始人群的生活在诗人和作家的笔下泛滥,于是人们向往起那个大自然能够自然而然地向人们提供所有需求的幸福时代。这样人类可以远远地避开生产和劳动,人生可以坠入懒散和无所事事之中。布鲁诺清楚地分析了这个神话复兴的消极意义,他力图从根子上打破构成这个神话的各个要点。闲散不能使人幸福。相反,闲散使人不幸,正因为它会迫使人跟动物一样地生活,使人失去任何社会和文化目的。
在宗教方面布鲁诺的评击更加猛烈。人不应当在获得天堂永生的许愿下牺牲现世的生命。作为个人来说,人只生存一次,所以不应当放弃现世的生命而去追求不存在的神圣天堂里的生命。宗教宣扬这个虚假的观点并不能够完成它本应有的使命。根据布鲁诺自己对宗教本源的解释,它首先应该是结合的意思,也就是说把所有的人联接起来,加固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宗教不应当把人和上帝用神秘的渠道结合起来,而应当把人与人连接起来,让个人和属于他的群体结合起来。宗教的礼仪规矩应当只有一个社会功能:它们首先应当鼓励那种在确保和平和秩序下文明共存的、在尊重政治体制基础上的行为榜样。
为此,布鲁诺驳斥基督教的各种信条。像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那样的宗教改革提倡者,他们只是挑起了内战和破坏,并使欧洲更快地陷入了最黑暗的社会堕落和无知的深渊之中。新教徒们为自己对动词结合所作的完全不同的解释奋力抗争:对他们来说,宗教只能创造上帝与个人之间的单一的关系,一种神秘的关系。这种观点完全排除了超凡和现世之间的任何关系,排除了上帝和作为社会群体的众人的关系。简而言之,基督教徒只有被动地接受上帝的审判:辩护论(即拯救是上帝的恩赐,人只有通过虔诚的信仰而不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来获得这种恩赐)和先决论(即人无法改变上帝的意志)使信徒们失去对自己行为的任何责任。假如人无法通过自己的善行来获得拯救,那么我们在人间所有的努力和贡献都将毫无意义。
从这些立场看问题,黄金时代的异教徒神话与基督教徒人间天堂——亚当和夏娃在无知和闲散中幸福度日的神话完全吻合。这两个神话都把劳动看作是一种惩罚,是对人类的痛苦的折磨。
布鲁诺无情地批判这种宗教和劳动概念。布鲁诺的《驱逐趾高气昂的野兽》与马基亚弗利的观点一致,也是一篇怀念古罗马时代的挽歌。这个古老民族的信仰和习俗中没有任何神话的成份,而只有强烈的社会意义。他们对人的奖赏和赞誉完全基于个人的功绩:众神只对为拯救祖国和民政事业有壮举的人授予荣耀;神明只奖励那些为巩固社会关系而作的贡献和成就。
显然这些题目距离你们亚洲文化并非遥远。让我们在不忘历史和文化巨大差异的前提下想一想,让人从恐惧和超自然的力量下解放出来,为文明生活而去集中思考社会和国家机构的问题,不正是孔子和孔家学派的焦点所在吗?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彻底理解布鲁诺所肯定的吃苦耐劳的重要性。宗教和道德哲学只应当为人类服务。人们不能放弃个人的努力,而被动地容忍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我们的命运并非先天所定。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悲欢离合、兴衰荣辱并不是命运左右的结果。事实不是如此。布鲁诺认为,人自由驾驭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前途、自己的生命。当然,人生之途并非容易。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应该去战胜各种困难、各种束缚、各种障碍。但最终通过积极和艰难的劳动,是有可能减少逆境带来的损失,增加顺境中的有利因素的。
布鲁诺在《驱逐趾高气昂的野兽》里,让命运极其优美的论述来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所有的人都在此埋怨命运采用原则不明的方法来奖赏那些无功受禄的人。但这些埋怨毫无根据。假如奖惩的原则不明或有人无功受禄,那并不是命运本身的过错。命运的作用仅仅在她从名签盒里抽出一个名字而已。在名签盒里所有的名字都一律平等,因为命运是盲目的,她无法顾及社会、种族或经济上的歧视和不公。要是中签的人不配领赏,那么应该归罪于人类名签盒里的德性不足,没有在那里记载下许多德高望重的人名,或者说是由于人类的智慧只将极少数的智者列入其中。在一个有一百个人名的名签盒里,若只有两个有德性者和一个智者,那命运怎么会偏偏抽中这两三个人而不是其中的97个呢?相反,假如名签盒有97个是德高望重者,而只有两三个是无为之人,那么抽中无功受赏的人的概率就低得多。所以就不是命运的过错,而在于配得上荣誉的人太少了。只要人类不产生有德性的人,我们就随时有可能受到名不符实的人的管制,就有可能让人无功受禄。
人类应当选择获得德性的道路来拯救自己。闲散、呆滞、无所事事只能使我们接近动物。而劳动、生机和行动能使我们变得神奇,成为永远有能力征服新的未来的英雄。
从哲学的角度看也同样如此。在这方面布鲁诺也明确地指出了应该与其斗争的敌人。在思想领域里我们也能辨别出在不动和行动、在封闭的宇宙和无限的宇宙中的对立来。布鲁诺尤其力图摧毁两种哲学: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怀疑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无所不知”和怀疑论的“不可知”只能产生一种僵持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人无法与求知建立起一种有益的关系。自以为无所不知和否认任何知识都只能意味堵塞探索之路,只能意味着放弃所有的文化原动力。布鲁诺认为知识不可能存在于封闭的、单一的、静止的、与不断求知相距甚远的世界里。
在这个意义上说,宇宙无限的理论完全和求知无边、永远在发展的论点相结合起来。布鲁诺明确地肯定这样一点:对一个真正的有识之人来说,无论他多么博才多学,也还是总有局限性;没有一个人能在某一天夸耀自己无所不晓。探求真理需要这种坚定,这种自知之明。真正的有识之人懂得,每当我们发现一个真理,在我们面前便又打开了其他的探求途径,其他把我们引向获得真理的道路。真正的有识之人懂得,探索没有止境,没有终结。探求真理与经历接近地平线的假象相似,我们在孩童时期有多少次曾经以为极为遥远的地平线就是一个终点。可是那个终点是不存在的,因为它随着我们移动,无论人们怎样朝着它推进,它依然并继续无限渺茫。
这个唯一客观的真理似乎与这个寻求真理的过程不断相吻合,与一个不断引出新的认识事物、发现新的真理的无限过程相吻合。在《论单子》的一段令人难忘的文字里,布鲁诺在对待人不满足所发现的真理、不满足探求事物的实质和形式时也用了以上这个观点。这两种情况都不能使人达到最终的结果,物质在它聚集和分离的过程中永远无法停止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形态中;人也一样,人永远无法仅满足于获得部分真理,因为人一旦发现这个真理,便会立刻发现获得真理的可能性。
寻求物质“永恒形态”的痛苦和人在寻求“全部真理”中的痛苦体现出自然界一个的完整形象。哲学、生活、文学、物理、道德讲的都是同一种语言:讲的是宇宙的多变、它的无限性,讲的是它的深奥性。
布鲁诺关于认识的共性的观点在今天具有极强的现实性。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了两种文化的剧烈冲突:自然科学(它们不断地与法律、客观性、可逆性和普遍性相连)和人类科学(它们的本质与多变概念,与事件性、时间、历史等概念相关)。它们之间互相隔离,并由此而产生分裂和互不理解。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那些博学多才、能够提供绝对把握、能够只用客观概念和数学来解释世界的人是至高无上的。
但是,最近几十年来,一些科学家清楚地意识到,一种万能科学的观点对未来的预见往往最终失去对人和自然的真实视野。只有上帝能从他的位置俯视一切:过去,现在,将来。而人的知识永远无法完满,因为它产生于一个多变而不稳定的世界。今天许多科学家愿意用一种新的、承认存在局限、能够抛弃自以为有绝对把握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一种建立在理想化和绝对化基础上、非常接近神学世界观的思维方式。
布鲁诺在他的意大利文和拉丁文著作中均反复强调:在一个无限的宇宙里,知识也不得不是无限的。只有无知的人才不力求智慧,因为他们自以为有智慧。相反,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热爱智慧,而且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致力于获得智慧。但是他也同时知道,这种追求永无止境,因为人是无法占有全部知识的。尽管如此,对知识的热爱会使求知的欲望在其追求中永不衰弱。
承认这个世界观,意味着承认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和真理的局限性,意味着懂得与其他真理共存,用其他观点来检点自己;意味着接受这么一个事实,即世界上有许多与我们自己不同的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与我们不同。而容忍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容忍并非指忍受异己,忍受“危险和令人不快”的事物。容忍首先是认可自己的观念有变化,有它的暂时性。这种变化和暂时性使我们更易于理解和接受他人,也帮助我们把差异和多面性看作一个巨大的财富,看到它们所具有的必要的积极的价值。
不了解布鲁诺这些哲学思想的核心,就很难认识到他斗争的意义。他对发现新大陆的无情抨击准确地推翻了众人、包括直至本世纪初的大多数人在内所坚信的观点;他认为哥伦布的远征不应当被简单地理解为人类获得了新的知识。那些第一次踏上美洲土地的欧洲人并不是一批渴望求知的航海者,而是一群受低级本能驱使的无耻海盗。在文明的名义下,在天主教的名义下,在西班牙君主国的名义下,土著人被虐待、掠杀、抢劫,被剥夺全部的自由、全部的财产。没有人去想,这些土著人也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传统,有他们自己文化的多样性。
在哲学家和文人完全屈从于君主和罗马教会的时代里,极少有人敢于持有这些大胆而明智的观点。正是以这种明智,布鲁诺预见到宗教战争对欧洲文明社会的威胁。在天主教和新教之词,以及在天主教内部和在新教内部的斗争将导致人间和平被破坏,将不可逆转地阻碍欧洲的文明进步。布鲁诺指出,在不容异己、自以为拥有绝对真理并将其强加于所有其他人的过程中,种下了只能引起仇恨和暴力的种子。
冲突和内战不仅削弱了社会基本结构,而且对追求真理的途径产生了灾难性的作用。不需要几年,就可以把人类多少世纪以来通过无数人辛勤劳动和努力而建立起来的东西全部摧毁。文明轻易地坠入野蛮深渊的危险近在咫尺。
在这个聚会中,由于时间所限,我无法详尽而准确地回顾布鲁诺的一生。但只要稍微审视一下他一生最重要的经历,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一生与探求真理之间的深刻关连。这个持宇宙无限论的哲学家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他从一个官廷到另一个宫廷,从一个大学到另一个大学,因为他认为只有在不断的移动中,他才能确保自己哲学论述的自由。布鲁诺知道进行批评是有代价的:自由地表达一种不同意见,反对一位王子、一个宗教派系或一个强权,意味着失去优惠待遇,意味着时刻准备面对流放和迫害。为此,布鲁诺放弃了那不勒斯,日内瓦、巴黎、牛津、伦敦、符腾堡和其他许多欧洲城市。
接受多样性的丰富和容忍的重要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正是由于这些观点和信念,布鲁诺选择了死于罗马,在鲜花广场被活活烧死。可惜我们没有许多关于当时行刑的记载,特别是没有关于他最后时刻的记载。但是不难想象,而且许多人已经认为,布鲁诺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放弃自己哲学最关键的核心。在他受审的开头阶段,有迹象表明他曾经愿意妥协,愿意承认自己在理解宗教教义方面有错误。但一个是宗教——向芸芸众生传授道德和文明的工具,另一个是哲学,没有任何宗教教义能够迫使他否认自己关于宇宙无限和维持万物生机的原动力同一的观点。
几个月以后,将近2000年2月,布鲁诺去逝将有四百年了。在意大利和全世界将举行许多纪念他的活动。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布鲁诺的哲学是希望的象征,它让人放弃仇恨和种族歧视,放弃不容异己的狭隘偏见;让人抛弃消费主义给人带来的幻象,抛弃金钱和物质的欺骗性;让人去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弱者将受到保护,老弱病残者将得到帮助,贫穷地区的儿童将不会死于饥饿。
我认为,在这个大学内相聚——如今全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促进教授和学生日益频繁的交流,把这一天献给布鲁诺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教育工作者们对更加年轻的晚辈具有重大的责任。对我们来说,布鲁诺的启示尤其明显:缺乏热忱就无法传授知识。假如我们自己不热爱所教授的内容,就无法向我们的学生传播这种热爱和热忱,就无法传授哲学和文学的巨大价值。
为了达到教学目的,我们的教学必须建立在一种信念上:人类的团结和文明不是建立在商品、经济交易和庞大的市场中。人类的共同根源处于文化之中,处于哲学、文学和艺术之中。“真正的哲学家四海为家”,布鲁诺在《论原因》中这么写道。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说法使一个非凡的事件可以在全世界发生,使得鲁迅有可能不再仅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欧洲许多国家的读者,他们由于阅读他的作品而感到自己是那个遥远大陆的公民。于是,我这样寄希望于你们这些阅读布鲁诺中文译著及其他许多欧洲经典著作的人们,你们将能永远地跨越亚洲的边界,而拥抱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文化。
(N.ORDINE VITA CIVILE,TOLLERANZA E UNITA DEI SAPERI IN GIORDANO BRU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