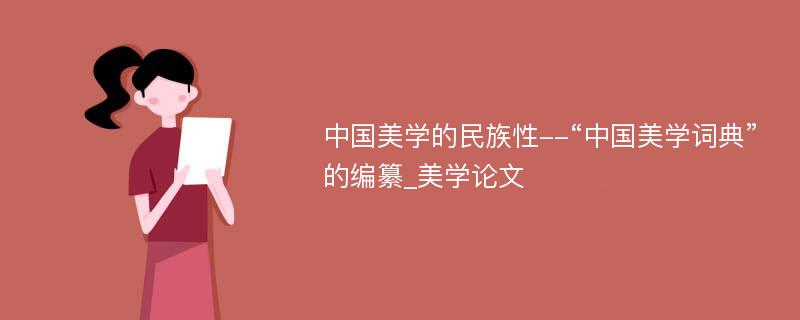
中华美学的民族特色——应编一部《中华美学大辞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美学论文,民族特色论文,大辞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2)01-048-09
中华文化中处处讲审美,事事有美学——但本无“美学”其名,也未为之立一专学特科。“西学”东渐之后,始有“美学”之概念与名目。因此,讲论美学的人士,往往以欧美的美学理论为师,从启蒙到归属,总不离西方色彩。这也是历史的形成,自然的理数。
但是,以西方理念为本的“美学”搬来硬“套”中华的文化精神活动,从内容质素到形态表现,都会发生多层次的问题和误解,中华美学应是民族的,不能“向西方看齐”,拉向人家的特点而强求附会。所以,我们应当特别重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特色,注意寻求我们传统上的无其名而有其实的“美学”遗产,异样的珍宝财富。
笔者以为,讲中华的美学,应从自己的汉字语文的理解认识开始,汉字语文中所包涵的种种美学理念与形态,丰富之至,重要无比。为此,我主张学术教育文化各界,必须“补课”——补古来十分重视的“小学”课,即文字学训诂学。多年来这桩大事被忽视甚至废掉了。“读书”与“识字”断了血脉联系,这本身是个“笑话”,可惜历久而习以为“常”了,久忘“读书必先识字”的真理要义。
比如,“文章”一词,目今好像只在“……写篇文章(其实也不是‘文章’本义,只指非文艺性的通常叙记文字了)”还在用它,古之所谓“文章”,却只说成“文学作品”了——那是洋话literary works的译语,中华人本不那样说话。然则,我们原先的“文章”又是何义呢?难道这可以完全不讲不懂,就能撰出高水平的“中国文艺美学”的大作来吗?
从训诂上讲,事情并不“麻烦”,倒很明白:文,是五色所组构;章,是五音所配含。这意味着什么?就十分耐人作深长思了。
五色,赤黑青黄白。五音,宫商角徵(zhǐ)羽。一方面是视觉的,一方面是听觉的。它们的巧妙组配,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大美。
五色的美,后来用“文采”这一文艺标准代表而进化了。五音,又即是后来诗词讲究“韵味”的根本源头。
中华文学的美学,应由此而研究讨论之——然后再议其它。
又比如,中国画叫做“绘画”。绘画又是何义?粗分可以认为:画是今之所谓“线条”的事,即“勾勒”之法;而“绘”就是色彩运用配合之道了。
中华诗圣杜少陵《丹青引》赠画家曹将军(霸)首次提出:曹姓氏族文化,如从魏武来看,他的政治事业虽已成为历史,但“文采风流今尚存”(曹霸为之艺证)。是则“文采风流”四字即是中华美学的一个典型命题。
在此,“采”属于文的事情,如不晓文字训诂学,不知“文”本五色,遂觉奇异难以索解,甚至“批评”古人“不科学”了。
杜诗《冬至》云:“刺绣五纹添弱线”。何为“五纹”?正是文包五色的一个义类佐证。中华文事,要讲“有文采”。“文采斐然”,“斐不离文”。
在此,就会有致疑者,问:“文”一经用“字”写成,就只剩了“白纸黑字”,怎么还会有什么“五色”可言呢?
要知道,中国书画也讲“墨彩”。墨不但不可黯滞而无光泽,而且还讲“墨分五色”。难道这都是无谓的胡云吗?
在中华大艺术家目中看来,“字”不只有声有义,还更有色有韵。
例如,东坡咏海棠云:
东风袅袅泛崇光
香雾霏微月转廊……
这儿并无色彩字眼。然而“崇光”之中正含有很美的色质在。正因如此,中华伟大作家曹雪芹才由东坡句中“开发”出“崇光泛彩”这一美学名句。
至于“风流”又是何说?
这就触及了中华美学上的一层超越“视听之娱”(王右军书圣《兰亭序》中语)的、无有形迹可资“捉摸”的“风骨”“气韵”的重大课题。
对此,仍然需要从文字训诂讲起。
“风骨”,六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以之命篇——也是学者讨论最为集中热烈的一处核心问题。
“气韵”,则又正是同时代中华绘画理论之祖谢赫的《六法》论中的居首之法。这儿,一个“风”,一个“气”,都不再是视官与听官所能为力的了——文学艺术家须具备的“第六官”:“感官”,只有它方能感受与感悟到这种“无形美感”, 夐乎不落于一般“生理官能”的限度之内。
这个“关”过不了,是无法也不必来讲什么中华美学的。
“气质”一词,说明了我们民族对于审辨“虚”、“实”的特高天赋能力。是故魏文帝曹子桓(丕)首先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根本性命题。
还要举杜少陵,他题赠李白的名句云: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所谓“不群”,所云“清新”、“俊逸”,是什么?不是别的,就是气质,就是风骨。
关于“气”、“风”的关系,可参阅拙文《中华文论[艺论]三昧》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为节省篇幅,暂且将“气”的含义略说一二。
“气”的表面“字义”不难懂,文化内涵却极其复杂深邃。西方科技家的“气”,大抵指氢、氧、氮等等“元素”和“空气”、“天然气”等几个分类。“西学”入华后有了“电气”一词,可知这一类的“气”是指“能源”的“动力”。
中华的“气”则不尽然。中医讲“元气”和“气血”。天文讲“气候”、“气象”(气象一词今日预报气候还叫“气象台”),就是农民也知道“二十四节气”。占卜家讲“气数”、“气运”,俗话还说“运气”。养生家讲“气功”,即道家的“导引”法。……如此举之未易罄尽。归到此刻本题,中华为何绘画也要“气韵”?文赋也要“以气为主”?——这里的“气”又是什么?
原来,要理解中华文艺美学,必须先懂得一个大前提,即:“活”字当头。
活,是“死”的对面,在中国审美的心目中,一切诗文书画艺术品,都与其作者同样是一个“活人”,而非一件“死物”。每件经“活人”创造出来的艺品,都是一个“活物”。或许可以说:真正的不朽文艺品,就是因为由那作者将他的精神生命“分给”(赋予)了它!
因此,那艺品也有生命、生机、生趣(性情意态)。它也有气质、气味、气象、气度……我们的审美,不只是“线条”、“光线”、“位置”……等等一套“死法”。
气,是生命的运行,器官“运作”的动力。不只是“肺活量”能吸多少“氧”的问题。医家讲阳虚是气亏,即机能动力不足。(阴虚是精血亏损之症)
所以,中华文艺美学把“气”放在第一位,并非什么“玄虚”、“神秘”、“不科学”。它比“皮相”、“以貌取人”要深刻、科学得多。
可是,“气”虽略能说解,还又剩下一个“气韵”的“韵”。这又是什么“东西”呢?
这儿有几层意义可表——
第一,“韵”是“均”的后起“会意”字。韵、均都是音乐学(包括汉字学)上至关重要的一大关目。
据专家考定释明:均是中华古乐的一种定音的标准器,一切乐器制作的发音(高低合律)都以“均”为定规。所以无论丝竹管弦百人千人大合奏,均能达到一个“和”的美妙效果,成为“乐”的无上高境界。
[附说:和,本字作龢。右为音符,左为乐器的象形:屋梁上悬者是一组(以“三”代表)编钟或编磬;下边是一件排箫。二者代表了金石丝竹诸般乐器的主脑。]
至此即可晓悟:由“均”达“和”,众乐既谐,其音乃悠扬而长,而余音袅袅不绝。
此种效果,即是“韵”的本质与效应。
由于汉字语文本身一大特点是它的音声带有“乐律性”(最粗的分类是“四声平仄”),所以诗文一经诵读,即生音韵之美。韵律一生,则又发现了“韵味”的“味”字这一课题。
那么文学史上的常识还有一个“神韵”。这又如何理解?难道是说“鬼神大合奏”吗?
这儿,又要转到先讲“神”。
神,是中华本土受到崇信供奉的“三类”(神、仙、佛)之一。佛是古天竺传入,修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者。仙,是修炼以期于“长生不老”而常以“法术”著称者。后二者俱与本文主题无涉。而神,则大有关系。
中华的神,可分两类:一,大自然山川万物之神。二,人之神。
何谓人之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庸常者“与草木同裔”,谁也不记得;其有立大功德事业而造福于民族国家百姓者,其品格精神,不随人之躯体消逝,永垂不朽,万民历代总还怀思奉养者,方是我们常说的“神”。例如,民间的“关公”、“武圣”,药王华佗、孙思邈……以至上古圣帝“三皇”——伏羲、神农、黄帝,皆是神位。治水定土的大禹,也称“神禹”。不必多举,其义已明了。
综而言之,佛、仙、神,都是有成有就的特等超常的人物——与怪异妖魔之类了不相干。
至于天、地、山、川……万物皆有神以为之司掌,这种“多神论”,俟后文专节另论之。
至此,已然可知:
一、韵——众音和谐而达到的美,名之曰韵。韵则“三日绕梁”——正是形容余音袅袅不尽之义。
二、神——形死而精气不灭者,皆有其“神”圣性,故列之于神位。
——结论:中华诗,特讲“神韵”,是说真诗之作,必能具有不灭与无尽两层超越“视听”的审美体性。
这个重要的中华美学理念,到了宋代高人,乃以创“新”而实述“旧”的方式重加表述。
其词曰:
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含无尽之意见于言外。
这实在好极了!——然而一核实际:上句即言“精神不灭”——唯其是重“神”而轻“貌”,所以才发生“难写”之问题。景而难写即不在具体形貌色相,而在神情意态,是无法“言传”的精微所在了。下句谓须有超乎言辞以外的意致,这正是“不尽”之韵的又一效应。
所以,要讲中华美学,不先弄清这些基本道理,是不行的——而这些道理,入手处不能离开中华汉语文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声律学。这是一条原则真理,它产生于民族语文的本身,而非“外加”、“移用”。(故只用西方美学概念条例来“解”中华美学,是非科学的思维与实践)
说到“难写之景”,需要略加申解。
苏东坡有一首小诗,人所习闻:
湖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别的慢讲,只这“潋滟”形容晴波,“空濛”形容雨岚,便有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的神理——令人正像置身于晴湖、雨岭之间。
这个“神”,是靠什么传达的呢?原来就是那两个汉字连绵词。
只看这“潋滟”——不要说“外文”里查不到“对应词”,就在《汉语词典》里也只这一个!
这就又引出了“中华美学来自汉字特点特色”这个命题的根本性的探讨工程。
中华的这种“形容词”,绝无仅有,正因为它本身就是民族审美的感受与表现,而不是“大家(各民族)都差不多”、“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事情。
比如,杨柳何以“依依”?孟夏何以“滔滔”?春寒何以“料峭”?东风何以“骀荡”?……这种感受度与表现法,你能在别处发现一二吗?太多了:我总爱举“迷离”、“苍茫”、“依稀”、“飘渺”……外文只有一个“不清晰”。烟雨凄迷,霜风凄紧。庭院萧条,山川寂历……你用外文译译看,这都怎么办?
至此可悟:这一切,归根结穴,要理解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诗心”和“诗语”。她观照宇宙万物,感受是皆有生命精神、性情灵慧——而且是与“人”皆有交通交感的。
这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另一诠释。懂了这一要义,同时也就再次明白为何中华的文家艺匠都把他们的“作品”看作是“活人”而非“死物”一件了。
中华美学的一切来龙去脉,原始要终,咸在于此。
我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到清华大学去拜访钱钟书先生,谈文论艺是我们惟一话题。一次,说到“神韵”,钱先生说:“有人认为神韵不存在,太玄虚。其实不是不存在,而是有人感受不到——比如我的servant就不知道什么是神韵,这不能就是没有神韵的证明。”
当时还只是因诗而论神韵一“案”,今日想来,钱先生一席话已然说到一个根本问题,即:他的servant(仆役服务者)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文化教养修养,所以他无法领受神韵的存在,这不等于神韵本身是“无”的,是人为的假说和想象的。
所以,讲神韵,不但是要明白“不灭”、“不尽”之本义的事情,还必须认识这是一种中华大文化上的高层灵慧和感受能力的根本问题。
上文讲的“韵”是音乐之事,而音乐和奏乐、聆乐者则必须是文化水平造诣至高至深之义,所以才发生“曲高和寡”的交感共鸣上的冲突矛盾。要想到:一则“高山流水”的佳话,又一则“手挥目送”的美谈,却恰恰都是古琴奏赏的典故,那些相涉的人士都是中华文化史上头流的高人——他们本人就具有人格和品德素养的神韵。
所以,问题的根本又不在、不限于音乐之事之理。因此,“韵”在实际上早已不只是“谐”、“和”、“押韵”悦耳的狭义概念,已经早就延伸到人物和艺术的广义涵量上来了,“俗不可耐”,问题何在?无神少韵、粗蠢野犷、言语乏味、面目可憎……这是品人的贬词,也正是审美评艺的反面镜鉴。
呼唤一部《中华美学大辞典》
这部宝典,应结合文献学、文字学、训诂学、笺注学、音韵学、乐律学、《雕龙》学、古今诗词话学……汇为一座艺术宝库,构筑一座最辉煌的文化艺术殿堂。
第一步,摘录“四部”书海中所有有关的词语。从先秦到清代,几千年相承习用的传统汉语华言。
第二步,加之训诂笺疏。训诂不只是一味“考古”,是“通古今之变”。正如以大师段玉裁之注《说文》那样的研究注疏法所示之良例,即可悟出一种今之辞典又当如何继承发展的体例做法,应当注重哪些方面。
第三步,搜罗近、现、当代有关学者的有价值的研论文章,作为“词条”释义以下的“附说”。不同见解,可以并列,以供采择。
第四步,如果可能(而非强求附会),可以附加“比较”项的简注,内容是沟通中外,或理论相似,或义类相从,或会心不远,或悬殊大异,或似是而非,或宜加审辨……
我想,如能初步做到这四层工作,纂成一帙,勒为善编,那么我们中华美学的真面貌真精神,方可望得到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况——外仪内美,丰神命脉,灿若列眉。
有了这个总基,为学人提供继续探研的便利,实在功德无量!
必如此,方可望中华美学的研究能以较大步伐向前推进。
若能这样,也就可以避免一种倾向:不懂自己,只将双目盯住“外来品”的美学研究兴趣与做法。
在这部辞典里,我们将能查到诸如下列的词条——
高华、韶秀、跌宕、潇洒、闲雅、悲壮、俊逸、遒媚、铿锵、顿挫、舒卷、收放、擒纵、巨丽、娟净、哀艳、婉约、豪放、朗润、清畅、茂密、沉郁、苍劲、峻厉、沉着……无数的中华美学概念、艺术标品。
这座里程碑,是否就由南京师大的学术力量承担起来?有关方面应为此提供协助、创造条件。
近来,文艺报刊上的论文标题最常出现的是“生命的×××”。这原非不好。但也要说明提醒:“生命”在大自然中是十分残酷野蛮的(弱肉强食,生死搏斗……)。一味强调生命就容易忘掉同样重要的一面,即必须伴以文化。有文化的生命才是造化的赐予,宇宙的奇迹。而文学艺术的美学并不是“单纯生命学”的事情。
到此方知:中华美学讲“神韵”,其体会感受最为深刻而高明。“韵”是高文化的水到渠成之境界。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只是比较“人物性格”、“描写手法”等等技能问题;要比较的还是美学观念概念的异同深浅。舍此而事它,即难望探骊而得珠——却易流于刻舟以求剑、胶柱而鼓瑟了吧。
前文粗举,如“高华”、“韶秀”……以致“沉着”、“痛快”……皆当于“词条”著录,这并非说只限此种二字联词方入辞典。凡二字以上,或脍炙人口的文学艺术史上的“公案”、“话头”(此借禅宗用语),内含美学义蕴者,皆为最好的入录词目。
例如,“山抹微云秦学士”的佳话,“明朝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传颂万口……这类都非美学“界外”之事例。盖中华美学,不一定是某一名人大师正式提出什么流派思潮、新说主义,而常常反映在读者赏者论者的“聚焦”点上,那些警策精彩的文词笔致,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审美要求和评定。
这一类的文献资源,实际上丰富得很,只不过是如珠如玉,散落在诸子百家之间,须待有心有识之士去蒐辑罢了。
中华美学,宝贵无比。中华美学,亟待建立。散兵游勇的状态,不可长久认为“力止于此”、“无事可做”,或者总是目光朝“外”,拾人牙慧,而不知宝山就在家门。
文献也有另一面的开发,如沪上传出,发现一批古竹简,对《诗经》的文本与理解都提供了崭新的材料。如孔子曾有“诗不离志,乐不离情,文不离言”的“三不”论,何等可珍可震!新文献未必只此一例。诚望早日能见研究成果正式发表。
复有一例,讲中华美学者亦所当知:
比如音乐,是以音声为艺术,人耳受之,以得领略赏会之美。这应无可“外”延,是“科学”规定。然而,试举三例,请君一思——
第一例,“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乐之大美,是孔子用“耳”闻得的,这无疑问,可是他闻后,并不是听官发生了异常感受的大变化,却是在“味官”上出现了异相。《韶》之大美,使他食肉而不再觉味——或者是解读为三月不思饮食之享。不管如何,这都表明音乐之美学不只是“生理科学”的事,它的作用效应是高层灵慧境界的精神活动,绝不同于一个简单的“耳朵”的功能。
第二例,《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无尽意菩萨请问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而得是名号?佛答: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这儿是众生称菩萨名号时,菩萨立即“感”到了这种心声,是“观其音声”,而不是“闻”的事情——但“观”是视官之事,何以又能“看声”?又为何不名之为“听人声菩萨”而单单用这一“观世音”之称法?可悟“观”不只是目“见”。佛经明明白白规定“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受纳“六尘”(色、声、香、味、触、想)各自分明不紊,然而同时出现了“观音”这一“观念”,岂不耐人寻“味”?梵文原本我不懂,至少古代高僧译经,是以“华言”沟通佛语的,那就说明:在译者的理念和语文造诣中,“五官”只是常人俗事的范围以内的概念;若到精神文化的高层次上讲,“视听之娱”便非探本追源之胜义了。
第三例,《石头记》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人人皆背得烂熟了。如今要问,作者开卷第一回正文首句是“列位看官”。写小说是给“列位”用眼“看”的,可是“看”的结果是“味”的问题。
这“味”,就是“舌”之所司吗?“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末三字岂能“科学化”而必须改“在舌头”?
这类例子多得很。讲东方中华美学,也不能只盯住“视听”而不解其它。
——至此,似可归结到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中土美学必须从汉字训诂等“小学”基础做功夫。汉字本身不是“符号”,是形、音、义、意、感、悟、表、现的高级灵智的综合创造,是中华文化的历史“档案”、“信息”财富宝库,美学的一切“消息”都可以从这里追踪蹑迹,意会言传。
说欲研中华美学先须懂汉字训诂,如“文”本义为“五色”之组成,“章”乃“五音”之协奏……即从汉字色彩而言,岂不大与美学有关而宜一究其蕴乎。且看,有“丹青”一词喻指绘画,这就重要之至了。
粗讲第一步,此词表明中华先民作画着色以红、绿二色为主,为什么?民族审美目光抉择能力所决定也。至今也还可以听到看到“红花绿叶”、“桃红柳绿”、“穿红挂绿”……这些成语熟词,就是良证。但为什么“红绿”或“青红”不能代指画艺?就要明白丹、青都是矿物性颜料,古画用之朱砂、石绿石青,其色极为深厚沉重,迥异于“水彩”、“油色”。
然后再思索汉字中的“红系”字与“绿系”字,看看中华审美对色彩的分析鉴赏能力如何——
红系:红、朱、丹、赤、绯、降、茜、紫、赭、頳……
绿系:绿、碧、翠、青、苍、黛、玄……
这些字,在诗文中用起来是意味声容大有差别而并非可以随便调换代替的。比如“红颜”与“朱颜”涵意不同(极个别互代例只见一、二)。韩退之(愈)咏榴花,说:“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苍苔落绛英。”你不能给他改成“落赤英”。再则若要写桃花、海棠之落红,也不能说成是什么“落绛英”。
碧,审美情绪与“翠”大大不同。“寒山一带伤心碧”,总难乱改为“伤心翠”。碧落、青空、苍穹,所传达的审美因素也是似同而各异。“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儿也绝不可换成“绿海蓝天夜夜心”。其余可以类推而自悟。
这证明汉字音义之外,还有心理色彩,亦即审美内涵。
“五音”的问题,难以在此细讲。如今但说一个“平仄”的课题——这是今日大部分“文化人”已不懂的“平常”道理了。
平仄是单字或“音组”的两大“声类”的交替配合联构的音律美。比方说,一个七言诗句,是由三个“音组”联构而成,“一片——飞花——减去——春,风飘——万点——正愁——人。”音律即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其第二、四、六字的联次,总是平仄二声交替轮换。只有这样才达到了汉字诗文的音声格律的至美圆满之境。不合此律的听起来就十分别扭。(但今日百分之九十几的报刊“七字仿诗标题”是违律不懂汉字声美的!)此非“人为”的“枷锁”,而是从上古实践直到六朝末期方才达到这一美境——即悟知其规律的。如若连这也还不通而侈言“赏诗”,岂非欺人自欺的谰言一段?
所以,中华美学必须包括汉字音韵之学。
我说“平仄”律就是中华哲学的“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总道理的一种体现。其实,刻印讲“阴文”、“阳文”(即白文朱文之分),剪纸讲“实地”与“剪空”,也都正是阴阳交替大道的艺术运用佳例。
若说到此,也就明白:论到了“终极”,即:讲中华美学也需要理会中华民族的感受高度、认识高度、思维高度——然后达到的审美高度。
若明此义,则音乐美学也可贯通无碍。民族乐、佛乐中的管乐,笙、管、笛三者为阴阳配谐之道,三者音质音色各有其美,非常“个性突出”。在节奏上,又加上鼓钹的间歇与暗联(间歇不等于“中断”、“破碎”)。而洞箫是独奏擅场,另成一格。如“箫声咽(yè,入声),秦娥梦断秦楼月”,一个“咽”字点睛。而到了东坡《赤壁赋》,则出现了一段“传达”洞箫的审美感受——
“客有吹箫者,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这种至美之文,是中华美学范围内的瑰宝——它不以“理论”面目示现,而是以文艺为载体。
一切都不要忘记中华美学是民族个性的,天下独一无二的。
还有两类中华文艺审美上的重要考究,也不能忘记:一是笔法讲波澜,二是意态讲“鼓立”。杜少陵尝赞曹子建,谓“文章曹植波澜阔”。又于一诗赞之,诗篇曰:“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这就足以为证了。
杜老又有一句,说是“字向纸上皆轩昂”。在文艺美学上看,这话尤为吃紧重要一义。
这是因为,无论文章还是字画,其笔法、笔意、笔致,都切忌平、缓、松、散、塌、蔫。中华文艺高品要表现为“遒举”——此即杜老所言“轩昂”之意。
如换成“大白话”,就是说中国的文、字,都是“站”在纸上,而不是“躺”在那儿“睡懒觉”的!那一片精气神,是振作、是奋发、是骏迈、是鼓舞、是行进。
说到这里,回顾前文,为什么自从汉魏六朝,逐步的中国文艺美学理论提出而强调这个“风骨”、“气韵”来了。
遒举、轩昂、骏迈……统统是“气”的内在运行的精微而又确切的感受和领会。那种平、缓、松、塌等等大病,正是没有“气”、缺乏“韵”的后果。
这是我们中华美学的根本理论,是很科学的观照、思考、实践的结晶,绝不可与什么“玄虚”、“神秘”混为一谈。
以上种种,悉皆中华美学的民族特色。西方若有相同、类似的理念,再好没有——但要科学比较,不可生拉硬扯,牵强附会。西方若无,那就更需要我们自己考论清楚,然后介绍交流,促进了解。舍此以外,空言这“化”那“化”,未必真有实际意义。
庄子早就提出:凡精微至极的技艺之“灵魂”,都是无法靠语言文字传出来的,庖丁、轮扁之喻,莫非如此——凡能用“话”说出来的,记下来的,不过皆为“糟粕”而已。糟粕,是粱米酿成酒浆、精华已尽,所剩“渣滓”。(庄子的“糟粕”本义是说,凡精微之极的道理只能意会,语文记叙只能是一种“渣滓”废物。至近世以此词专指应该扬弃、批判的“坏作品”、“毒素”……已是另一回事,切勿相混。)
本文所言,实在是很粗劣的“剩物”,往精微处讲,深愧无能为役。尚希方家学者鉴其大旨,而谅其粗劣,是为至幸。
壬午正月廿九日写讫于挥媚轩
[附记]
一、本人目已濒盲,引用书文,只凭记忆,不能检列详细书卷、篇目等细节。阅者谅之。
二、孔子谓“诗不离志,乐不离情,文不离言”,可印“诗言志”之古义;志与情有合有分,志包括意愿、向往、取径……有理智因素,与纯情不同。至陆机《文赋》,始言“颐情志于典坟”,然亦二者分论,不相混同。“文不离言”者,并非今人所谓“作文就写话”——即主白话而弃文言之意;孔子原话是说:撰文的目的,是“立言”,有意义的言论,而非文字游戏,消闲玩弄。
三、关于“波澜”、“轩昂”二义,不妨参看今贤启功先生题拙作背临《兰亭序》所赋《南乡子》词:“蚕纸入昭陵。《定武》欧临隔壁听。但爱元人摹本好:精能。无限波澜笔下生。
大作富先型。纸上如闻战马声!书苑自今添胜迹:飞腾。大展鹏图万里程。”此词将笔法、笔姿、笔意的跳宕飞动、不平不塌等要义,已经用极经济而又生动的词句喻写鲜活了。(见《永字八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又,本文用意只在拈拾示例,举一反三,故多为提端引绪,而非“系统”、“全面”。即如只一位杜少陵,若就他的美学观而略略深思而言,那就还有很多应“补”的了。例如咏宋玉“江山故宅空文藻”,藻与“藻绘”合看(如“藻井”彩绘也)。是与“文采”同义的。如他强调的“凌云健笔”的“健”字,“下笔如有神”、“书贵瘦硬方通神”的“神”字;“瘐信文章老更成”的“老成”之再见。诸多不一。至于杜老是格律诗的集大成而又锐意创新之先进者(字法、句法、章法、笔法、意法,无一不是突破拓展之独创新格),但他却单单是“晚节渐于诗律细”。这就是因为他是个大艺术家,具有天赋过人的“音乐耳”(感受力),愈到后来愈悟音律才是中华汉字诗的大美之“灵魂”,必须从“细”考究。而今日却有些人宣传抛弃汉字本身特点之一的平仄阴阳大律,面对古代高智慧者的终生实践而得的教示,无动于衷,一反谆谆语重心长的嘉言至意,岂不令人感到:中华美学之整理发扬,也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吗?
至于中华的文质艺境,又有“高明”与“厚重”之两大分驱,或以为不过是作者“性格”的不同表现,那就又失之简浅了。盖此二者,来源仍然是我们民族的宇宙审美观:“天”表现为“高明”,“地”感受为“厚重”,“天高地厚”之俗语,亦即此一理念之通俗化。换言之,高明也是“阳”美,厚重亦即“阴”德。
凡此种种,俱在中华美学之广大范围中,宜加讨论而入于典则。
古历壬午二月朔日再记
收稿日期:200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