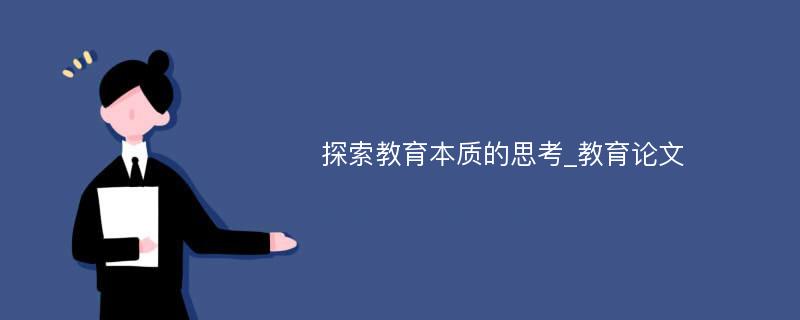
教育本质探讨思路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1999)05-0047-04
教育本质问题是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疑难症。关于这一问题的论争似已陷入了疑无路的境地。[1]有人感叹,教育本质讨论了10余年, 至今不知“本质”为何物,听起来似是天方夜谭,令旁观者难以置信。并认为这种讨论呈现模糊——清楚——再模糊——更清楚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此时的“模糊”或许比“糊涂的清楚”更好些。[2] 这种观点足以反映了研讨的艰难。实际上,教育本质的研究不止10多年,从1950年5月《人民日报》创刊号上发表过《教育是什么? 》开始至今40多年,特别是近10多年来,发表了近300篇论文,洋洋洒洒200余万言,林林总总20余说。但所有这一切,远不能令人满意。各说虽力求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几乎均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2]这种局面, 是教育本质探讨的“黑洞”,它使任何对教育本质探讨的新见解都消融于其中。探讨教育本质已变得意义不大,充其量,这种探讨不过是为林林总总的几十说再加新的“说”,为洋洋洒洒的几百篇文章再添新的“篇”。
在今天,重要的不是教育本质的探讨,而是对这种探讨思路的探讨。若思路错了,越探讨离教育本质就越远。尽管人们对教育本质看法不同,但却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思维定势: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是关于“教育是什么”和“教育应该是什么”的认识。这条探讨思路是毫无唯物辩证法哲学根据的,奇怪的是竟然无人对此质疑。一探讨教育本质,就把脚踏在这条路了。
将教育本质问题变成“教育是什么”,教育本质问题的研讨就陷入一个悖论:人们不知道“教育是什么”竟然能研究教育的本质。认识本质必须从现象入手,不知道“教育是什么”就无法判断什么是教育的现象,什么不是教育的现象,教育本质研究也就根本无入手处。而研究一个无法研究的问题,就必然会走上越研究越糊涂的宿命的道路。
要想从这个悖论中走出来,有必要分清两种对教育的知:一种是知性的知,它是在感性具体基础上对教育形成的抽象概念,是对“教育是什么”前辩证思维概念的认识。一般的教育者都具有这种认识,它使得教育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者能知道“教育是什么”,他们即便没有参与到教育本质讨论中去,也能心安理得地从事教育工作,而不会将它与计划生育等工作混同;另一种是辩证理性的知,对教育形成辩证具体概念,以此揭示教育本质。准确地说,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和探讨不是对“教育是什么”的认识,而是对“教育是什么”的辩证理性认识。“准确”在这里是十分重要的,不然不仅无法理解对教育本质的研究,而且会贻笑大方,搞教育的人不知道“教育是什么”这会成为“天方夜谭”中最滑稽的故事。这样,谁还会去尊重教育,尊重教育者呢?
将教育本质问题变成“教育应当是什么”更令人费解。这反映了人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七十年代水平:以价值判断代替对本质的客观描述。强调政治,教育就是上层建筑;强调经济,教育又成了生产力;认为政治与经济都重要,于是教育既是上层建筑又是生产力;强调主体性,教育本质又成了宏扬人的主体性。教育本质象手艺人掌中的一块随意捏的“泥”。无论后来有多少关于教育本质“应当”的认识,在思路上与七十年代教育是上层建筑的观点一模一样。历史上教育成为某物的附庸、其独立性丧失的教训人人皆知,但根子恰恰在对教育本质认识的“应当”上,这个教训似乎并未吸取。
将教育本质变成“教育应当是什么”,违反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常识,即本质是客观的。这样,在讨论中就出现了“教育是什么”和“教育应当是什么”两大类本质,一类为真实存在的、客观的东西;另一类为应当存在的、带有规范性、价值性的、主观的东西。这使探讨人为地复杂化,且背离了唯物辩证法。
提出教育本质包含着“应当是什么”的根据是认为教育有理想追求。这根据本身是毫无根据的。若某人想成为超人,能说他的本质就是超人吗?不能以人的理想定义人,同样,也不能以教育的理想定义教育本质。当然,这并不否认,在研究教育本质时可以考察教育本质实际存在的好的方面,但这必须在本质是客观的辩证认识前提下进行,不能用价值判断代替客观描述。这也不是说“教育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不重要,不需要加以研究,而是说不应将它归入到教育本质研究的范畴。否则,会使教育本质定义显得随意和无穷无尽。因为“应然”包含着“想当然”。每个人对教育都会有不同的价值评判,这就足以把教育本质的定义的数目增至无限,使教育本质定义成为人言言殊、飘忽不定的东西。这样,感叹不知教育本质为何物就不足为怪了。但这种感叹本身是不必要的,既然本质属于应然的,就规定了本质是无穷无尽的“想当然”,再要求探讨得出一个大家共认的本质概念是自相矛盾的。
谈本质必须有哲学依据,探讨教育本质必须按唯物辩证法的思路进行,唯物辩证法“装”不下二类本质。唯物辩证法探讨本质有三个“一”:本质一类、方向一致、思路一条。
列宁说:“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3](p.278)这种无穷无尽不同于“想当然”意义上的无穷无尽,它首先要求达到一个初级本质的认识。而这个初级本质不存在于探讨者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客观事物中。无论有多少级的本质认识,本质只有一类,它是客观存在的。探讨的方向也是一致的,首先达到初级本质,然后,沿着初级本质不断深化。
探讨教育本质的认识路线有一条,即“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p.751)北大哲学教授张世英曾举过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这条认识路线。这里权且用笔者的语言述其大意:认识是一个整(完整的表象)——分(抽象的规定)——合(思维具体)的过程。譬如,一个乘飞机到南京旅游的游客,当飞机在南京上空飞翔的时候,这个游客从飞机上往下看南京,这时南京对游客来说是一个完整的表象、混沌的整体。当游客下飞机后开始游玩南京,去了中山陵、雨花台、玄武糊、新街口、夫子庙……等等,这时便处于“分”的阶段,是对南京各个部分的认识。游玩结束后,游客乘飞机离开南京,再在飞机上往下看南京,还是这个南京,但这时已不是混沌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对南京各个部分的认识、规定的整体,达到了思维具体。这个例子是辩证认识路线的形象化的注解。这种整——分——合的方法应该是教育本质探讨的方法。
以下笔者沿此思路对教育本质试作分析。探讨教育本质首先要从完整的表象出发。我们对教育有一个完整的表象,典型的教育是学校教育,有教室、课桌、教师、教科书、直观教具、学生、笔记本、钢笔、日光灯、上课铃声……。“它(指表象)对于对象还没有省略掉任何东西,而且让对象整个地、完整地呈现在它面前。”[5](p.63)接着, 我们对感性认识进行思维加工,形成抽象的规定。这种抽象必须掌握好度,不是漫无边际地抽象,而是要抽象出反映事物本质的规定性,这些抽象规定性为教育者、教育手段、内容和教育对象,这些是教育的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的知性概念。然后,综合上升到思维具体:教育的本质是教育者、教育手段、内容、教育对象相互作用的流程。肖前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给本质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即“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构成一事物的各必要要素的内在联系。”[6](p.288)尽管该定义在教育本质讨论中受到质疑,但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它正确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本质。正是以上教育诸要素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才构成了教育本质,舍弃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成其为教育。教育的双重属性、多重属性、培养人的活动、文化传递、教育使人社会化和个性化等等都是在诸要素互相作用中才显示出来的。
这种本质观可以抓住教育这个事物的全体,由诸要素相互作用构成了完整的教育。认识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仿佛又回到出发点的意义上,它与完整的表象相对应,好像是向感性具体的复归,但又高于感性具体。如果抛开这一完整(非穷尽性)的概念,说教育是生产力,是上层建筑,或是其他的什么等等,都难以让人理解教育是什么,因为它们与人们生活中的感性具体不对应,没有一点仿佛复归的感觉。
以教育者等定义教育本质可能会有循环论证之嫌,可将教育本质定义为:“增进人们的知识技能、影响人的道德性格陶冶的信息传播者、传播手段、内容和信息接受者相互作用……的流程(信息不等于知识,也不仅仅是语言、文字)。”这个流程是一条奔腾不息的赫拉克利特的河流。省略号标志着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教育本质定义,这是教育的初级本质。列宁说:“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能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3](pp.309—310)无限丰富的具体的多样性以胚胎的形式存在于初级本质的认识中,随着对教育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分析、抽丝剥茧,具体的多样性就会逐渐“生长”、成熟起来,愈来愈丰富,由一级本质发展到二级本质……思维越来越具体。
对教育本质定义还要再加二点说明:其一、抽象出来的教育者不仅指人,而且指物,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从事物中受到的教育。教育本质定义应该包括一切教育现象,因此,它也要包括事物对人的教育。其二、教育本质定义是中性的,能容纳坏的教育。把坏的教育排除在教育本质之外,无法使人们认识和杜绝教育的负向功能,也无法使人们全面、客观地认识教育。全面、客观地认识教育,是教育独立性的前提。尽管这种认识不能提供教育理想,但至少能使人明白是“什么东西”的理想,而不至于将理想当教育,把教育消解在理想之中。
教育本质的探讨应该定位在这种初级本质的探讨上。虽然这种本质是客观存在的,但对本质的认识必须靠辩证理性去把握,它决定了人们并非一下子就能真正找准教育的初级本质,得出一个人人共认的教育本质定义。所以笔者只是试作探讨。但只要思路正确,即使一时找不准,至少会大致接近。总不会出现两大类(客观的和主观的)本质,从而使研究哲学的人对教育理论者的哲学基础知识质疑。
收稿日期:1999-0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