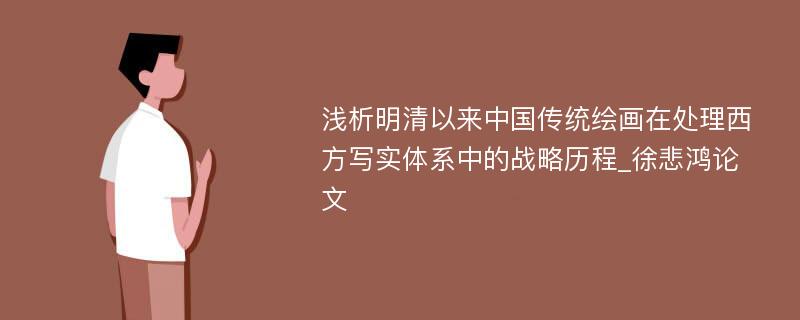
明清以来中国传统绘画应对西方写实体系之策略历程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历程论文,体系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之际西画东渐,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开始受到触动,有人加强了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对西画采取摈弃的态度。也有人开始对传统绘画进行加以西法的嫁接与折衷的探索。具体而言,当时主要问题应当是明暗写实技法和中国画传统笔墨的结合,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法写实关系的探索成为一种艰难的精神之旅。
岭南画派和徐悲鸿可以说是明清之际这段历史的余绪和继续发展,前后两个时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提供有趣的对比。例如,如果说在明清之际中国绘画主要是初步的防御性的反应和有限范围内的借用西洋写实手法,而后来的两者在被动之余,则是有意识地借取西法写实。又如清初沈铨在中国被评为品位不高,有趣的是他在日本却大行其道,更有趣的是后来岭南派又去效仿日本画的道路。再比如徐悲鸿的早期绘画正是从郎世宁入手的,不同于明清之际的曾鲸、陈洪绶等试图结合写实技法与传统笔墨的合笔画中充满了与现实的割裂感的文人理想[1],也不同于郎世宁屈从于宫廷趣味撮合之下,力图融合笔墨与写实时的身不由己,徐悲鸿以科学主义①为依凭,主动地探求素描与笔墨的结合,对形、神等在概念及其操作层次上作了新的阐释。而其融入西法改革中国画的设想,触及了创作主体和画体的层面,实际上从反面揭示了中西传统绘画的深层文化差异。
同时,“中国画”概念的逐渐产生和演化也是在这两个时期。从与异质视觉文化相接触时的一些视觉文化表层形式的传通②以及内层观念碰撞,到蕴含着应对性的文化策略在内的“中国画”概念的逐渐产生,在这两个时期,在许多理论认识及相应的实践方面可以发现寻求“中国画”特定样式的努力。针对西方写实体系③,中国画家的文化策略可分为三种,④一是与西方比较、区别,如早期的邹一桂⑤、吴历,乃至后来的许多人强调笔墨和中国画的传统原则;一是折中西法,以皇帝趣味指导下的郎世宁为代表。另外,岭南派绘画也属于折衷画体;再一种便是融入西法⑥,所谓“可采者融之”,以徐悲鸿为代表,笔者认为这种融合企图仍然难以摆脱两种绘画语言的内在矛盾,因而仍然是折衷性的,其中包含着把以文人绘画为主的中国传统绘画形态与异质美术的科学象征图像相对接的企图。而无论哪一种策略,研究都表明中西视觉文化表层某些共通的可能性的背后是巨大的文化深层差异。同时作为对徐氏的切实把握,我们不应忽视他与前期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动意和与“文人理想”的联系。
下面以前后两个时期中国传统绘画结合西法写实的策略为重点,试对这两个时期和三种策略加以历史的分析比较。
一、明清之际:归属与折衷
将中西绘画进行比较、区别之后并归属民族传统的策略者,他们主要出自一种文化上本能的、直接的带有防御性的反应,有的直接以中国传统绘画的品评标准对待西画。如邹一桂说西画“虽工亦匠”,确含有在中国文化深度上评判的内在玄机。实际上只要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就有着充分的自足性理由,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包含“非艺术”因素的国际文化环境让这种优越感难以继续保持。
以人物画为例,在折衷的立场中,明末人物画对于人物面部画像式的写实的世俗感与文人理想中的古雅格调之间的矛盾,采用了如李日华所言的一种策略来加以调和,即人物面部用相对写实的画像手法,而以文人的笔墨画衣纹道具等,以体现仰慕高古的文人气格。所谓“……正以像既恭谨,不能不借此以助雄逸之气耳。至吴道子以描笔画首面肘腕,而衣纹战掣奇纵,亦此意也。”[2]
而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画像只表现人物的面部特征而无对像的个性可言,因为中国的人物画谱总结了各种类型化的观察和表现的程式。真正传达内心情感的是对于一些程式化的景物、道具、衣纹和仪态的选择,如《葛一龙像》中的书和衣纹等。李日华的方法看似有效,却从深层上暴露了问题,画面表现出的是一种奇异的割裂感,“生命形态与古雅的格调谐调,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得以解决,它预示着对后世的诅咒:不进入形式主义,就可能陷入自然主义。”[3]
郎世宁的作品体现的是皇帝的旨趣,他通过降低明暗去掉阴影等方法以讨好皇帝,却仍不能令皇帝满意,于是有了与院画家和宫廷文人画家(翰林画家)合作的宫廷合笔画——郎世宁画人物、马等,唐岱等画山水树石。与之类似的又如工西法写真的莽鹄立画人物面部,蒋廷锡补景的《允礼小像轴》等。这里关键在于皇帝在喜欢写实技法的同时,又强调传统笔墨的文人文化导向的作用。这种折衷画体之所以在宫廷呈一时兴盛,却没在中国大范围流行,原因一是满洲贵族对西画的纪实功能的功利性的需要,二是洋教士在宫廷参与的绘画种类有:油画、工笔重彩、院体写实,而文人笔墨为主的作品较少。郎世宁的西法更多地与工笔重彩和院体绘画相结合,如众多的御容、人马图、花鸟、宫廷仕女等。而有时也与高其佩、唐岱这样的被皇帝抬举的院画家和文人画家(翰林画家)合作,宫廷翰林画家称西画“虽工亦匠”,内廷文人画家即或奉旨与其合笔,也是同床异梦,合作也不是很情愿的。 [4]其影响局限于宫廷是可以理解的。
这提示我们,中国传统绘画不同的体裁、题材的认识和表现方法是不同的,这种个别对待正是中国绘画体认与表现对象的方法的特点,不同的体裁与题材与西方写实体系的相似关系是不同的,其中人物画是一个关键的类别,也是矛盾的焦点,而其中工笔人物画与写意人物画又有所不同。人物面部写实手法与周围环境衣物的传统笔墨的协调是当时的一个难题。
而面对这个问题,当时的中西画家都感受到巨大的审美心理隔阂,从而产生对自身所属文化的归属感,陈洪绶如此,郎世宁等洋画家亦如此。
而实际上,可以说问题集中在“形神”和“笔墨”上。明到清初,中国绘画的形神表现和笔墨有趋于视觉表现性的倾向,例如浙派、江夏派的劲拔外露、清初对写生的重视、“宋法元格”的没骨法、干笔皴擦、指头画等等。在这些基础上,事实上许多画家对西法颇为参酌一二,且有中西两种风格的画家的合笔画,如高其佩和郎世宁,蒋廷锡与莽鹄立等合作的作品。之所以没能发生类似日本圆山四条派和后来的竹内栖凤等在社会上影响广泛的折衷画体,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典型主义文人文化抑制了这种折衷的倾向。而在中国被视为院体的沈铨在日本的盛行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二十世纪岭南派又学习日本画,明确提出“折衷”口号,其“折衷”性已有许多学者论及,本文不再详细分析。[5]253谨对影响较大的徐悲鸿的策略加以分析。
二、二十世纪:徐悲鸿的策略:从形、神、笔墨到创作主体和画体
徐悲鸿立足对文人画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改造,试图从西方写实体系中为中国绘画的写实找到合乎科学的基础,这种基础仍然是主要针对形神和笔墨的。徐氏选择融入西法写实的个人原因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政治气候,以及其“唯科学论”的出发点是有关的,林木已经做过详尽论述,[5]309此不赘述。在此重点看他的操作策略。
首先看形神方面。他提倡基于西方观念的“由形似到神韵”的理论——“有人喜言中国艺术重神韵,西欧艺术重形象,不知形象与神韵,均为技法;神者,乃形象之精华;韵者,乃形象之变态,能精于形象,自不难求得神韵”(1947年《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而实际上,中国传统绘画的形、神的具体概念与西方写实绘画的类似概念有极大的差别,早有人指出欧洲没有能和中国的形、神对应的概念。⑦它们在中西绘画中的操作顺序和相互关系也极为不同。因此这里存在概念的混淆和西式观念的导入,此“形象与神韵”在此已不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概念,而是暗中采用了西欧艺术的标准,却也被用于评判中国画。尽管明清之际出现如恽南田对于写生的重视,邹一桂也突出强调构图的重要性,出现重视创作性及其操作程序的倾向,邹一桂还说“未有形不似而神似者”,但是形和神与西方类似的概念仍然是极为不同的。
中国古来虽多有形与神的分辨,但未有在训练程序上明确先后逻辑,形在中国也不能等同于西画中的形的确定含义。徐氏这样一种观念的引入,是为引入素描和西画个人风格的表达语言:笔触、对形的处理等,以与中国既有概念“写形”与“写神”相对接。其“心手相应”最终是处于“未尝违背真实”这样的一个带有西式固定观察和表现方法的框架之内(1920年《中国画改良论》)。把他所谓的“真实”作为标准,这是一立足于科学主义的理论。
其次就笔墨而言,画马标志着徐悲鸿在国画融入西法领域的最高成就。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形”与“笔墨”结合在共同的玄学根基上,事实上徐悲鸿在他画的马上显示出对此较深层的把握,形与笔墨结合得很好。固然这是因为他是在娴熟掌握马体解剖和大量画稿的基础上的,然而重要的是,他又回归了中国玄学精神的笔墨贯通之下对形的把握。他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超越了历史上的郎世宁等的折衷,具有较深的民族文化涵义和绘画类种上探索的深层意义。而且徐氏笔墨所显示的也不是像徐渭、陈洪绶的笔墨那种表现性的某种冲突感,而是立足于由科学认知立场向中国古典认知方式回归之基础之上的精神性表达,侧重于寻求科学认知立场、中国古典认知方式和艺术家情感的艺术表现三者的某种内在一致性。
应该说,中国传统笔墨中除了独有天地的精神意味外,其运笔的体验性在西方油画的笔触中也存在,其中如力度与质感。然而不应夸大二者的共同点,关键之处在于笔墨含有水墨与宣纸互动的自然有机过程的随机性与艺术家性情的互动感应,而油画笔触更多体现主体意志的控制和视觉美感。这里表现出材料的独特作用,“笔、墨、宣纸也是画家创作的热情的合作者,他们的自由品质使笔墨的必然与偶然并显,兴会所至,机趣横生,画家不断取得生动的形象,并受激发产生新的意象。同时他们又是不易对付的对手。”[6]这样材料的选择形成了一个小宇宙的有机抽象存在,可在此体验有机自然主义的奥义。可见笔墨和笔触也是深度不同的。
然而,这种由科学立场向中国古典绘画的认知、表现方式与精神的回归在马这种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民族长期图腾上是卓有成效的——对象毕竟是相对类型化的寄情言志的动物。但在近代化的个性化的人物画方面则不是一回事了。过去人物画的笔墨书写性是建立在对类型化的图式的娴熟笔墨把握(如“高士策杖溪桥”之类的预成图式)与凝结了文化成见的简化笔迹的基础之上的,而在转化了情境的近代个性化人物肖像上则失去了传统的依恃,加上解剖结构的要求,于是笔墨与形象颇见冲突。
然而徐悲鸿的探索更为深入。他对中国画的深入探索可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可以与西方写实绘画对应的对视觉真实性表现的重视,即独立于文人图式与趣味的视觉性画体的成立;其次是专业创作性的问题,主要是指艺术家身份从文人中独立。而这二者是紧密联系的。
以下试析这两个方面所潜在的矛盾。
大体上可以说以文人绘画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绘画的象征性主要对应着一种文化的成见和被赋予的社会功能,其“用”直接联系到其“体”的成立,所谓“为人生的艺术”,也是这个意思。有趣的是徐悲鸿改革中国画,在追求视觉真实性的“体”的同时,也求其“用”,但这是回归中国文人纯洁道德传统的“经邦济世”之用,与后期文人的渐趋偏重个人化的独善其身、自娱自乐的“用”有所不同。徐悲鸿虽然反对文人画的非专业性和以书画自娱,但他本身却具有真正的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承当精神。[7]
徐悲鸿的文人理想体现在关注现实,并有民族历史文化动机。他在发掘历史题材上的倾向受文艺复兴以来之影响,同时集中发掘中国古典题材,他比蒋兆和要更富于象征性与古典的理想主义,具有更深的民族文化动意。而其古典的取材又是同现实结合的,如《徯我后》、《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等。在精神上徐氏与陈洪绶和任伯年有共同之处,就是对绘画及其功能表现出一种纯正的儒家道德,反对明清以来的浅层次的文人趣味。
陈洪绶以儒家道德为根基,批评欺世盗名的伪文人画:“今人不师古人,恃数句举业饾丁,或细小浮名,便挥笔作画,笔墨不暇责也。形似亦不可比拟哀哉!欲微名供人指点,又讥评彼老成人,此老莲所最不满于名流者也。然今人作家,学宋者失之匠何也?不带唐法也。学元者失主野,不溯宋源也”。[8]陈洪绶的启示是,当“文人画”作为文人的策略而大兴时,或许从根基上偏离了儒家的道德。
而任伯年立足民间的立场,鄙视欺世盗名,可以看作传统美德在民间意味上的复苏。在人物画的题材取向上,他以民间与典故的题材居多,技法上则恢复民间肖像传统的“写生”,而又参以西法。徐悲鸿本人就出身民间画师家庭,对任伯年颇为推崇。在绘画本身的发展上,任伯年以中国传统造型观念为依托融入西法,对后来的浙派人物画以传统笔墨为本处理造型问题的路线有影响。而徐悲鸿正是由于反对“舍弃其真感以殉笔墨”,笔墨往往被放到次于西法素描的位置。任徐二人对比陈洪绶也可见近代民间立场与传统文人立场对中西画法的融合态度有所不同。
我们可以把他们同徐悲鸿对文人画的批评联系起来,徐氏思想中也隐含着一种对文人道德(儒家)的复归,自然,他立足的情境已经不同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徐悲鸿所追求的文人理想道德之“用”,是借用了西方的古典科学写实体系。科学的重要立足点是对单纯的“实在”世界的自然主义观点,西方艺术史中存在表现真实世界的自然主义理想(所谓普林尼——瓦萨里——罗斯金传统,认为艺术发展是注重再现技术的进步以图真实地表现客观世界的观点),即要再现世界“是”什么。而中国文化中特别是文人文化缺少这种自然主义的理想为根基,有的似乎是恰恰相反的倾向。
更重要的是,“实用只是科学的副产品”。[9]贡布里希说:“……要是我们把科学的好奇心只看作是创作‘照相式的’形象所用的附属工具,那么就低估了科学对西欧艺术的重要性。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对过去的东西所持的自豪态度、带批判性的叛离态度和相信进步的可能性的态度。”[10]在西方现代艺术对传统艺术造成冲击的时候,徐悲鸿只取科学有用的外层,强调其写实的用处,而遗其精神,可谓折衷,这也许并非其本意。从长远看矛盾仍然存在。
科学的另一深层精神在于不断的试错与证伪,科学在一个阶段的世界图景能为中国绘画中的“常形”、“常理”所体现的“有机自然主义”[11]的“自然合理论”的玄学精神提供辩护吗?这种玄学精神认为,我们在日常生命中所体验到的事物与自然整体的有机联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存在的合理性,不是通过机械论的分析和从固定视点出发进行逻辑推理来加以规定的,而是主要通过生活体验和圣人的教导。也许二者能够在视觉表面接近,但在文化深层的差异是很大的。
书法也有类似的情况,而文人画的核心笔墨是以书法为基础的。陈振濂认为古典的文人士大夫的书法观念的标志是独善其身——“为了书法家的这个身,书法是一个最好的点缀。但再好的点缀终究不过是点缀,若要让书法家在人生幸福与艺术创作中选择,则必然选择人生而不选艺术。”[12]以书法为根基的中国文人绘画,同样如此面临着“体”与“用”的问题,即脱离文人象征性图式与趣味的视觉性画体的成立以及相应的艺术家身份从文人独立这样的问题。而西方历史上艺术家从工匠走向“美”的代言人,乃至现代时期波希米亚人式的艺术家,往往有其独立的身份而存在,这是与以书法为根基的强调笔墨的文人画家不同的地方。文人画家不但鄙视职业画家和工匠,而且如徐悲鸿所指出,使绘画失去其学术独立的地位(笔者理解徐悲鸿此处所提倡的专业性的画家是有科学写实专业训练的画家,但不是作为波西米亚人的或为艺术而艺术的画家)。在这种情况下,文人画的象征性不能脱离其传统文人文化的意趣,难以走向更广泛的视觉性象征(文人画可称“拘泥的象征”),从而难以确立独立的真正“普适性”的视觉性的画体和艺术家身份。
从画体方面来看,需要把中国传统绘画的象征性与西方绘画视觉的象征相比较。中国绘画的象征性在文化成见之下,同追求视觉象征理想的西方古典绘画相比,其象征是拘泥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非形而上学性的术数玄学精神和经验性,使它远离了纯视觉的象征(欧洲写实绘画的视觉象征理想暗含了一个形而上的基础),而包含了对笔墨材料、物象及创作主体的玄学自然观和社会观的东西。形、神和笔墨就是这种差别的集中体现。并且即便认为其有一定的视觉象征性的同时,中国古代绘画的象征性,充满功能性的文化成见以及文学性典故的引用暗示。中西相差甚远的两种视觉文化的接近企图,早期是以皇帝(康熙、乾隆)的意志为指导的,而遭到大部分文人士大夫的反对,包括吴历、邹一桂这样的对中西美术之不同有所认识的人。第二个时期则大致以康有为为发轫,可能受老师康有为的影响,徐悲鸿早期的绘画就是直接从郎世宁入手的,详细分析可以表明徐悲鸿从中国文化秉承了文人理想,包括从其绘画的选题,创作目的等思想。而正是因为它是应对历史挑战的策略者,采取的是把中国传统绘画的概念用西方绘画概念暗中置换的策略(包括他对形象与神韵的解释及其训练顺序,还有笔墨与笔触的嫁接)。
结论
鉴于明清之际以来这段时期中国绘画状态之改变含有文人对异质文化的策略性反应(徐悲鸿也主要是针对文人画的改造,并且其艺术的社会理想与文人理想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将涉及文人绘画在中国本土性绘画中的地位。文人绘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视觉体现形式,但它却不强调单纯的视觉性表现及技术。文人的地位使他们有操作其策略的条件,笔与墨在中国虽也是一种普遍的书写工具,但仍然有非传统笔墨与传统文人笔墨之分。[13]由于隶变而产生的文人笔墨是一个社会功能集团所特有的工具与操作环境下的产物,并被这个社会集团赋予哲学、美学的,根本上是伦理的功能含义,这个意义上中国文人绘画功能性大于对普遍“存在”的象征反映或者说缺少单纯的“存在”的概念,可谓体用不二。
即便是中国民间的经验式肖像画与西法写实比较,在某些表面相似的底下,也有深层的文化差异。因为民间画像实际上与文人画分享着共同的中国文化荫泽,不过或许含有一些素朴的前科学的经验而已。
这两个时期围绕着形、神、笔墨、创作主体和画体的探索体现出探索的深入过程和历史连续性。然而由于文人化了的玄学自然观和社会观与西方科学文化的深层差异,折衷或融入西法与传统绘画都难以融合无间。尽管有如岭南派的某些激进革命思想,策略者立足于其社会身份,在不同的时代与“文人理想”仍然有着许多的联系。
注释:
①科学主义(scientism)一般指在非科学领域不恰当地运用科学方法,或者以科学的名义推行某种观念,本身是有违科学精神的。
②现代传播学把传的行为叫做“传通”(communicate),用来与人建立共通的关系。参见洪再新《传通与归属:十八世纪欧洲与中国美术交流叙要》,1987年第4期《新美术》。
③吴甲丰将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500年间的西方写实绘画称为“西方写实体系。”见吴甲丰《论西方写实绘画》第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④本文主要探讨以文人画为主的传统中国绘画与西洋写实画法的结合策略,主要针对西画现代主义和中国绘画非文人传统的林风眠当另作探讨。
⑤通过与西方科学文化形态下的写实绘画的基本概念相对接,为“中国画”概念谋求合理性则是一种文化的应对策略,这特别是指后一个时期。早期的吴历曾经在一些形式层面把中西绘画加以对比(吴历《墨井画跋》),邹一桂则强调了用笔和笔法在传统中国绘画中的意义,他还带有对于传统文人文化归属的优越感。
⑥本文所说“结合”,具体指以中国传统绘画为主体对西法的采用,“折衷”也是一种结合方式,而“融入”指更为深入和更具主体性的结合,找到内在一致性之意。陈传席指出徐悲鸿并不提倡“中西结合”,也是强调了徐氏采西法而为中国绘画所用的意图。参见陈传席《徐悲鸿并不提倡“中西结合”》,《美术观察》2004年第5期。
⑦这个问题早有学者广泛论述,如陈代湘指出,在中国传统绘画里,“形”具有特殊的含义,与现在一般所理解的“形”大不相同。见陈代湘《以形写神新论》,1990年第11期《美术》杂志(总第275期)。
标签:徐悲鸿论文; 文人画论文; 郎世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视觉文化论文; 明清论文; 艺术论文; 折衷主义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化论文; 美术论文; 国画论文; 陈洪绶论文; 西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