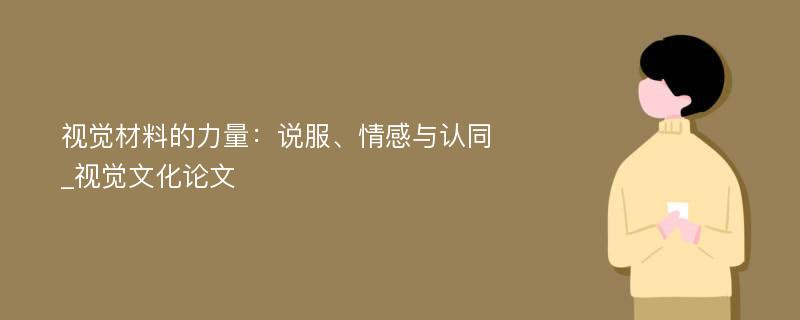
视觉资料的力量:说服、情感与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觉论文,力量论文,情感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媒体反复灌输被选来吸引其受众注意力的视觉资料。图像不但被用来阐述新闻和突出风格,还被用在试图劝导其目标受众改变态度和行为的广告与活动中。这些包括健康、安全和慈善活动。
在这一背景下,人们也许会认为有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考察了视觉资料是如何影响公众对一条或另一条信息的理解的。然而,在社会科学中鲜有关于其效果的经验证据(多姆克等,2002年)。对视觉资料的研究被边缘化了(拉德利,2002年)。重新激活对图像的兴趣的倾向正在日益增强,本文即为这一倾向的一部分。本文的目的特别在于消化吸收现有的探讨图像的说服力量的文献,并提出关于受众如何理解信息以及这可能如何与它们的效果相互作用的问题。为此,本文利用了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对图像的研究。图像的情感力量构成了本篇评论的焦点。
图像的性质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视觉资料的性质以及受众如何理解它。这些研究在视觉与口头/文字资料之间进行了隐含的(并且有时是明确的)对比。它们倾向于强调一个核心的层面:视觉资料激发情感的能力。
文字/口头信息与视觉信息的相对效果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别涉及它们的情感效果。图像被认为是令人经由情感的路程,而文字/口头资料使人处于一条更为理性、合乎逻辑和线性的思维路径。例如,艾弗和奥尔德梅多(2006年)发现,看到取自全国性报刊的肯尼斯·比格雷绑架案的视觉资料的人比那些从报纸的文字中阅读到绑架案的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感到更加恐怖。不仅是恐怖,图像还能激发参与感和关注。博霍尔姆(1998年)发现,在对跨越5个欧洲国家的切尔诺贝利10周年纪念的新闻报道中,视觉内容与文字相比在受众方面引发了更强烈的情感参与,并使议题浸透了更强烈的个人关注。博霍尔姆将此部分地同“拥有强大的能力使远离日常经验的风险表现得具有个人相关性”的视觉图像联系起来(第127页)。他推测这使对其内容的认同成为可能。
视觉资料似乎尤其令人难以忘怀,而且这带来的突出性可能令其尤其具有说服力。这与视觉资料的逼真性质相关。关于社会认知的心理学文献充斥着人们借以理解他们周遭世界的心理策略。一个发现是,人们有着系统化偏颇的观念,他们据此而高估作案不多的“鲜活”的杀手(并且低估频频作案的藏而不露的杀手)。信息是根据它的逼真程度被认为是逼真的:感情上引起关注的;激发意象的;以及在感觉、时间或空间方面具有接近性的。
虽然这种“逼真效果”本身也许并不强大(见泰勒和汤普森,1982年),但两种相关的心理策略却被发现是强大的。“突出性效果”假定,当人们的注意力被特别地引向环境的一个部分,他们倾向于在做出随后的判断时记起那一部分并将其置于首位。这可能与可获得性启发相关(特沃斯基和卡纳曼,1974年),这一社会认知的基石假定,一个事件是根据其事例能够被从记忆中轻易唤起的程度被判断为是经常发生的或可能的。因而论点是,视觉资料的情感性质增强了其逼真性。生动的图像留下一道多彩而强烈的记忆痕迹,在那里不那么生动的信息将会消失。这建筑了它所描绘的事物的显著性。
这一经验发现支持博霍尔姆的假设(1998年),即图像能够在观者的想象上施加一种“定位力量”,观者的想象可能会抵制质疑它们所产生的感受的评论。图像以一种未经媒介的方式被轻易地接受,因为观者通常不会像在涉及口头资料时所发生的那样,被挑动去对其进行思考或解构。关于一场争论中哪一方是“正确的”,媒体常常安排辩论来解决(例如在关于腮腺炎、麻疹和风疹的组合疫苗接种是否会导致孤独症的争论方面)。然而,类似的关于图像的“辩论”是不可能的。这与图像的另一个性质相关联:即它能够证实被讲述事件的真实性(格雷伯,1996年)。图片(移动的或静止的)这一新闻媒体中突出的图像类别,确定了某一事件的“真实价值”。此处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某人已经亲眼见到了所指对象,它赋予了这样的感觉,即已经为所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事实证据(巴尔特,1977年)。这一性质消解了任何有关图像以及图像之间“辩论”的机会。
然而,虽然可以证明辩论在本质上是口头的/文本的,但却可以将图像并置,并让人们自己去对争论进行“解读”。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将2001年阿拉伯世界的人欢庆美国双子楼倒塌的图片放在处于震惊之中的西方人的照片的旁边。这些图片中的人依照他们各异的身份而对同一视觉事件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反应,这一观点证明了图像所需要的阐释作用。这使图像具有多义性。处于不同群体中的个体对同样的图像可能有不同的反应,这可能取决于如他们对受害者的同情这样的因素。①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这开启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据称是由图像所引起的对受难者的情感参与和认同将依照此类差异而产生变化。
基于图像的这些性质——即激发感情、以未经媒介的方式被接受、逼真和难以忘怀,以及“证实”了所描述事件的真实性——图像会被认为是在塑造说服性信息方面尤其有效。
说服和基调
通过利用关于健康、安全与慈善活动的文献,说服与视觉资料之间的联系在此得到了强调。一种有力的论证思路提出,说服是通过将受众带入一种情感状态而得以实现的。在活动方面,那些充斥着文本的教育型活动已经为充斥着图像的社会营销所取代。这一转变反映出,有大量证据表明,仅有信息并不能吸引人们足够的注意力来引起活动所希望达成的变化。更准确而言,他们必须被引诱进来,并且视觉资料为此而得到利用。
激发恐惧与幽默的活动的说服效果是大量经验研究的主题。商业广告的历史上几乎见不到利用恐惧来说服受众,而旨在改变健康与安全相关的行为的努力却经常含有具备威胁性质的资料。在学术界存在着在支持和否认恐惧的说服力量之间来回摇摆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一项对激发恐惧的、旨在增多对安全带的使用的活动的重大研究表明,这种活动并未对安全带的使用产生如此的效果(罗伯逊,1976年)。这促成了一种转而支持强调采取健康与安全行为的益处的趋势。当激发恐惧随着预防艾滋病运动席卷全球而在20世纪80年代强力回归时,再一次有趣的是,在效果方面,关于其成效的证据微乎其微。相反,被普遍认为是最有成效的瑞士的预防艾滋病运动(见科克,1992年)并没有利用恐惧,而是聚焦于使用安全套对生活质量的益处所在。
在英国的健康与安全领域,对激发强烈恐惧的利用是显而易见的。从有即将死于肺癌的人参与的反吸烟运动到反对在马路上超速行驶的“三思,减速”运动,恐惧被用来说服人们采取健康和安全的行为以及劝阻他们不要有被视为不健康和不安全的习惯。虽然对这类当前运动的长期评价研究尚在进行中,但有人可能会指出它们忽略了这样的证据,即恐惧即干扰了注意力,也妨碍了记忆(拉扎勒斯,1980年),并导致观者不忍目睹(盖勒,1989年)。另一方面,很多证明激发恐惧的运动的负面影响的经验研究已经过时。当前的研究表明了恐惧的实用效果,尤其是当其伴有关于预防性行为的功效的信息时(威特与艾伦,2000年)。激发恐惧的图像主导着惊悚、恐怖和动作电影类型,它们都对观众具有吸引力。而且,据称由恐惧所引发的“不忍目睹”可能更确切而言是与厌恶的感觉相关。
厌恶,这一令人惊讶地并未得到充分探讨的感情(柯蒂斯与比朗,2001年),同恐惧、快乐、悲伤、愤怒和惊讶一起并列为普世的、基本的情感之一(见扎伊翁茨,1998年)。“基本的”情感之所以是基本的,是因为它们不是由任何其他情感复合而成。厌恶是通过看见(或接触抑或吞咽)体内废物和其他人体物质而得以最强烈地激发出来。“厌恶刺激”还包括死亡和恶劣的卫生状况(罗赞与法伦,1987年)。对它的反应包括窒息、作呕、畏缩和生气。由于许多当代的健康与安全运动以及那些表现灾难的活动都利用了激发厌恶的图像,本文转而对它的说服和劝诫效果进行探讨。
当代的健康运动大量利用激发厌恶的资料。英国媒体在过去几年中的反吸烟信息已经将香烟表现为渗出胆固醇/脂肪的动脉,并展示了一颗冒烟的人类心脏。其意图似乎在于让人们去观看扭曲的人体物质,以此将他们带入厌恶的状态。就像过去将吸烟者的嘴表现成烟灰缸的反吸烟信息那样,当代的运动展现了一位在嘴的周围有着深深皱纹的年轻女士,附加的文字将她的嘴明确解释为“烟蒂”。另一个描画了一位本应是有魅力、但有着非常污迹斑斑和参差不齐牙齿的年轻女士。再次同过去的运动一样,吸烟者还被呈现为濒临死亡的病患。就那些设计活动的人而言,这样的描述似乎反映出如此的信念,即引发厌恶将阻止吸烟者吸烟并/或阻止非吸烟者开始吸烟。
如果厌恶导致不忍目睹,它为何被希望吸引观众的新闻媒体和希望使人们对关于他们正在对自己造成的伤害的信息有所关注的健康运动参与者如此大量地使用?答案的一个方面在于令人厌恶的对象“在心中挥之不去”或铭刻自己的能力。为了理解这一点,可以对罗赞和法伦(1987年)关于人们如何对某些食物感到厌恶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某些“令人反感的物体”(例如一根毛发,一片指甲)变成了“污染物;也就是说,如果它们仅是短暂地接触到了一份合格的食品,它们也会把那份食品变得不可食用”(罗赞和法伦,1987年:23)。换言之,合格的食品与令人厌恶的物质之间的物理接触导致了对那合格食品的拒绝,并且这被归类于污染。这与内梅罗夫和罗赞(1994年)的魔力扩散的概念相联系。超出食品的领域,一种像吸烟这样的行为当被死亡和其他引起厌恶的联想所污染时,就变成了一种受到污染的存在。利用厌恶的说服性信息不仅作用于身体内部层面的反应,还作用于不可思议的思维领域。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厌恶的感觉持续存在,并可以对先前能够接受的事物造成影响。因此对那些希望说服和劝阻的人而言,它是一种潜在的有力工具。
引起厌恶的图像的力量在基青格(1995年)对英国艾滋病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说明。艾滋病的早期媒体形象强调了一种特别的“艾滋病外观”,即它所造成的身体的衰败或“严重虚弱的视觉表现”(第62页)。患有艾滋病的普通人和名人的“患病前”和“患病后”的照片被展示。有吸引力的男同性恋尤其成为“患病前”照片的特色;在“患病后”的照片中,他们已经变成了形容憔悴、“行尸走肉”类的角色。
基青格将早期的艾滋病报道描述为被损毁的“艾滋病外观”时期。她提出了媒体为什么强调此类形象的问题,并回答说它们利用了一种独特的摄影流派,吸引眼球的企图在此通过对疾病的怪诞后果的强调而得以实现。在艾滋病的个案中,这一流派被用来阐明(并警告人们)与艾滋病相关的“异常”生活方式的后果。在此,“对身体折磨的描绘同罪恶、惩罚、天谴和忏悔的概念纠结在一起”(基青格,1995年:53)。通过对一种摄影和恐怖电影流派的利用,这些形象利用了一种文化剧目,在这些剧目中表现异样会令一个人显得邪恶和危险。它们还将受害者呈现和非人化为“植物人”和“行走的骷髅”。
基青格认为,不仅是媒体,公众也采纳了这些形象。她利用了一项大规模的以专题小组访谈为基础的研究,发现怪诞的或“恶心”的照片是那些最多被记住的。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它们是那些表现艾滋病的照片。人们明确表示,这些形象来自媒体。根据其研究被试的说法,此类形象被夸大的显著性源自它们的“令人厌恶”和“恐怖”的性质。基青格的发现强化了这一论点,即令人厌恶的图像印刻自己并感染其所描绘的事物。
在说服的过程中,什么是媒体图像与世俗理解之间特有的相互作用?基青格对此进行的概念化包含在更为复杂的对媒体与其受众之间关系的解释之中。对她而言,媒体对其受众的说服力量在于“令人作呕的”图像,它们由于与其俘获媒体的想象力相同的原因而俘获了世俗民众的想象力。这些图像尔后通过它们在日常互动中的使用和重放而被进一步烙印在受众的记忆之中。例如,她访谈小组中的一些被试描述玩一个“辨认艾滋病罹病者”的游戏,在游戏中他们猜测他们周围的人是否感染了艾滋病毒。一些人表演出面孔扭曲、流淌口水等“艾滋病外观”。他们对重现这些形象的热衷说明了他们对令他们厌恶的事物的痴迷(另见约菲,1999年,关于这一主题)。基青格报告说,她访谈小组中的一些人认为这样的形象会说服人们采取措施预防艾滋病。其他人推测该形象会让人感到害怕和不忍目睹。
令人厌恶的图像,就像那些在英国的反吸烟和艾滋病运动中所利用的,也可能意在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说服和劝阻。它们可能想要将行为包裹在厌恶之中,以使其在社会环境中背负恶名。使用按照戈夫曼(1963年)的方式对耻辱所下的“社会污点标志”的定义,那种行为因而成为了一种社会耻辱的标志,对以如此方式行事或想要这样做的个体施加影响。因而,经由厌恶的说服和劝阻可以间接地操作。
虽然知道激发厌恶的图像会导致畏缩,但为什么那些说服性信息的幕后操手还要对其加以利用?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回答就是此类图像可能不会导致畏缩。拉德利(2002年)提出,图像迫使人们投入他们自己的情感。在对更开放地展示手术后的身体这一趋势进行分析后,他假设观看将改变人的情感状态——无论那是厌恶、恐怖还是/或害怕。观看还是被带入一种同所看对象之间的新的关系之中,并可能因此克服一个人对其的厌恶和恐惧。这里的假设是,可怕的和/或令人厌恶的刺激源是迷人的,正如一系列电影流派和新闻图片所证明的那样。
说服与内容
超出情感基调的领域,关于说服的很多当代观点来自探讨说服观者向与所描绘的那些人相关的慈善团体捐款的图像类型的研究。本文转而探讨不同类型视觉资料的说服力量。
当人们被要求为一个他们已经获得了某些个人信息的个体捐款时,他们会比在被灌输了统计数字的时候多捐出超过两倍的钱(斯莫尔等,2005年)。有趣的是,一旦向“单个被确认的受害者”中加入更多的人,甚至只是多一个人,同情与怜悯就会减少。对一位得到确认的个体受害者的刻画似乎在情感上具有高度煽动性,并且这可能会引起悲痛并因此刺激捐款(见科格特和里托夫,2005年)。
在国家与国际问题方面,图像的力量需要被置于人们被强行灌输了统计数据并患有数据疲劳症的背景之下(斯洛维奇,2006年)。统计数字的问题是,它传达的关于它所表现的人的信息是那么少——他们有什么感受,他们的声音和样貌。因此,图像往往比数字在感情上更加打动我们就不令人惊讶了。在某种意义上,图像为统计数字提供了对照——尤其是在特别诉诸感情的方面——在那里文字和数字支持更为理性的思考路径。没有感动,信息就缺乏意义(扎伊翁茨,1998年),并且不会被用来进行判断和决策;因此,感动是决策中的一项关键因素,例如决定是否向一场特定的灾难拨款。
在说服人们向慈善团体捐款时,除了“单个被确认的受害者”的照片起到的作用之外,“受害者”的类型也发挥了作用。埃尔斯和埃利斯(1990年)对与残障相关的慈善海报活动和观看它们的人之间的互动进行了仔细观察,证明人们在看到表现儿童而不是成人的海报时倾向于捐出更多的钱。残障儿童的形象可能激发特别的情感,例如可能对捐款意向产生作用的悲痛(见科格特和里托夫,2005年)。
至此,使视觉信息具有说服性的若干性质已经被发现。然而,观者群体内的差异却没有得到关注。是否存在不同的方式来说服不同的群体向慈善团体捐款?关于慈善海报活动,拉德利和肯尼迪(1992年)表明,来自较高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群体的人对激发同情的形象不以为然,而是更喜欢对残障人士平等权利的促进。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被激发同情和触动个人心弦的海报所打动。这令对定位和认同如何能在视觉信息被“解读”的方式方面发挥作用的研究得以进展。因此,并非仅有情感基调的性质和图像的内容是其说服效果的决定因素,而是还有观者的定位与认同。这将会通过对英国人的埃博拉病毒表征的研究成果得到进一步说明。
说服效果、情感基调与认同:对埃博拉病毒表征的研究
既然我们从图像、文字以及有时是声音的方面综合体验媒体,就不能对图像部分单独进行研究。想到这一点,这里不妨将对英国报纸中刻画埃博拉病毒的图片和文字进行研究的成果公布于众。埃博拉病毒是按照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埃博拉河命名的,在诸多次已知的爆发中,第一次是1976年在那里爆发的。它通过体液传染,对它没有良药或疫苗,而且它往往迅速导致死亡。埃博拉病毒于1995年在刚果的爆发得到了英国媒体的大量关注,并开始了一项研究,来调查在该病毒表征的构建中这一媒体资料与英国世俗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媒体文章及其插图得到了内容分析,伴以对英国读者的采访的主题分析,在采访中他们被要求谈论当听到“埃博拉病毒”一词时他们脑海中出现了什么。研究(约菲和哈尔霍夫)调查了埃博拉病毒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蔓延之时,英国的全国性报纸在世俗思想中培育了什么样的关于埃博拉病毒的社会表征。
结果显示,在报纸的文字和读者的议论中,埃博拉都被定位成一种非洲疾病。当通俗小报(“低眉”报纸)及其读者集中关注被视为是那广义的地方——非洲——所固有的、他们将其与正在发生的灾难相联系的内在特征的时候,大开本报纸(“高眉”报纸)及其读者倾向于谈论非洲的结构性特征(如卫生系统、贫困、战争)是如何助长了埃博拉的传播。
这一部分地为媒体和受众所共有的关于起源的描述,可以与媒体同世俗观点在情感投入方面的重大差异形成比照。报纸将来自埃博拉的风险大肆渲染和全球传播,并进而向受众保证西方对其进行控制的能力。读者的言论完全是超然的,明确提到遏制、自我限制以及埃博拉远离自己所在的空间。
在得到分析的文章中,有刚刚超过1/4伴有一张或多张插图:那些阅读通俗小报的读者看到的主要是穿着密封服到扎伊尔进行埃博拉病毒采样的西方人团队的照片。那些阅读大开本报纸的人最可能看到的是病毒的医学类照片,有时是由穿着防护服的西方科学家举在手中。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死者或濒死者身体的照片,但有少数下列照片:死于埃博拉的西方人——尤其是一位修女——的照片;非洲的地图;以及两个面露恐惧的人的照片(仅在大开本报纸上)。
虽然在报纸文章的文字中并未直接提到科幻小说,但那些阅读有插图的文章的人所看到的密封防护服可能已经将某种思考埃博拉的方式烙印在读者的头脑中。的确,许多被试谈到他们看到过描绘埃博拉的科幻小说类的图片。图片中的医师看上去就像执行太空任务的宇航员。而且,调查样本可能已经看过在当时广泛放映的电影《极度恐慌》(Outbreak),电影以科学幻想的笔触描绘了一种类似埃博拉的病毒。表征埃博拉的视觉符号可能在世俗之人表达的对埃博拉的超然感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仅埃博拉是“远在”非洲并可以被西方科学所控制,那也是科幻小说所虚构世界的一部分。
就关于图像性质的文献而言,埃博拉的图片在塑造样本所表征的埃博拉方面可能有着一种“定位力量”或首要作用,但在说服性传播中,图像往往伴有某些形式的文字。可以假设它们对文字信息“做了什么”。它们可能强化了某一特定特征并导引读者达至其显著性。关于埃博拉的研究表明,当文字以一种轰动效应的方式谈论一种“末日”疾病的全球蔓延以及对其进行遏制的可能性时,最流行的图片载有正在对抗埃博拉的西方宇航员式的疾病控制团队。当被问及埃博拉,许多读者将其看做是一种科幻小说类型的疾病,言外之意即它是一个虚构的领域,因此它所激起的为他们自己所感到的恐惧和对其受害者的同情都微乎其微。
不仅图像在塑造表征中有着“定位力量”,观者的认同——大体而言,就像白种英国人对侵袭非洲的一种疾病的反应——似乎也对他们的超然态度起到了部分作用;图片资料造成了距离感,而不是关于图片的文献所预设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因此,图像的内容与基调似乎与认同相互作用而产生了参与感和关心或超然与冷漠。
心理学研究一直聚焦于认同性,而非认同。关于对特定群体(如一个人的国家、像“西方人”和甚至是性别群体这样的类别)的认同程度的文献尚待开发。一个人对视觉资料的认同如何影响被激起的关于它的焦虑以及从它建构出的意义,需要对此进行研究。如果一张照片中所表现的病患看上去就像某人自己,这是否会增强一个人对他或她的同情?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对人们使自己与视觉资料疏离或认同并将这种视觉资料与说服效果联系起来所凭借的机制有更深入的理解。
关于埃博拉的研究揭示出媒体与观点之间联系的许多额外的层面。第一,接近媒体的受众并不是等待被烙印上一个或另一个观点的白板,而是有着“既有知识”(见基青格,1998年)。媒体的“信号”是根据人们现有的观念被吸收的。受众已有的知识引导着他们对在大众媒体中见到的观点有选择地进行强调、反对或重新建构。第二,并且与第一点相关,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去看待或反映事物的动机源自除了其他功能之外的身份保护的需要(莫斯科维奇,1961年/1976年)。那些为群体间广泛共有的表征的功能是一种共同应对威胁的方式;人们以保护自己和内群体的方式表征威胁(见约菲,1999年)。就艾滋病、埃博拉以及许多由媒体带入人们视线的其他潜在的变化而言,与风险相脱离形成了防御,因为它带来了对威胁的免疫。
本文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内形成的关于视觉资料的说服效果的文献进行了整合,强调了情感与认同问题。在大众媒体曾深深依赖文字信息的地方,它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向对视觉资料的使用。这不仅在新闻媒体中,而且在试图在社会上操纵人们在信仰、态度与行为方面改变的健康、安全与慈善活动中也是十分明显的。随着此类图像越来越多地出现,一个更为情感化的媒体环境到来了,人们发现他们自己被迫参与、并在某些情况下脱离那个环境。
注释:
①可能有人会辩称,对文字注释的反应也会依据阅读或听到它的个人的定位而有所不同。
标签:视觉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