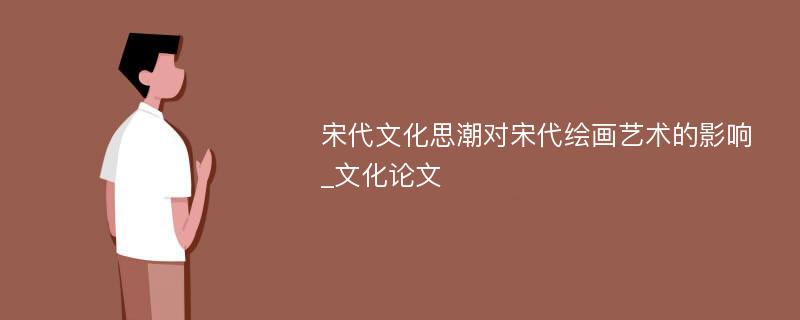
宋代文化思潮对两宋绘画艺术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宋代论文,艺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绘画史上,两宋绘画所呈现出的个性特征十分明显,这一时期既出现了“文人画”的萌芽,同时又因为两宋画院在创作中的主流地位,而表现出绘画题材与情趣上的“俗”的倾向。过去,我们习惯于从绘画本体去关注这一独特现象,而较少认真分析宋代文化思潮对其产生的直接影响。本文拟想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文化”是个复杂的概念,我们对它的解释与理解都具有一定的虚拟性,[1]文化思潮自然也因文化的复杂而复杂起来。作为构成文化结构最重要的因素——艺术,对它的认识必须还原到对应的文化结构之中。所以,即便文化思潮再复杂,为探讨不同时期的艺术现象还得去对它作以梳理,不过我们可选取与艺术直接相关的因素加以关注。艺术既然作为文化结构中的一种因素,我们在关注文化思潮时就不该将其抽取在外,这似乎是个悖论。文化的这一现象造成我们在解释中只有缘于客观的因素作以主观阐释。
两宋文化思潮有着延续的传统,虽然在北南宋也存在时段上的变化,但总体特征并没有大的起伏,所以我们在梳理两宋文化思潮时,应从北宋推演而下。在梳理中,为避免其复杂性的纠缠,我们只侧重于对艺术发生直接影响的因素加以探讨。
一、“宋学”的文化观念
“宋学”的概念是对两宋哲学思想的最好概括。[2]尽管在思想界许多学者对两宋的学术有过多种称谓,我认为这些称谓只不过是对“宋学”不同视角的理解。比如:“新儒学”是侧重于儒家学说的新建来看“宋学”的:“理学”则是产生于北宋,活跃于南宋的“宋学”一分支。[3]
“宋学”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求突破前代儒家们寻章摘句的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二是怀有经世致用的要求。[4]具体而言,“宋学”立足于传统儒学,又从佛道两家摄取,偏重于义理和心性修养等方面因素,所以也可把它称为“新儒学”,它与汉唐儒家们对经书的注释繁琐章句之学有着本质不同。
两宋出现的“宋学”自然有着它多方面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根源。[5]但出现以后它便对两宋文化观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宋学”的核心是“新儒学”。儒学复兴表现为“崇儒”和“释儒”。崇儒,即以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基,文人学士当然也以儒学为正学;释儒,是指以儒学为本,特别是那经世致用的原则,然后再援佛道两家入儒,尤其偏重于义理和心性修养方面。这种思想的上新气象,必然也带来文化观念的新变化。
“宋学”要求文人自觉地让“心念”成为文化基础。“宋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对“天理”的自觉意识。这就是说,宋人重于把价值的终极基础从宇宙的外在、可见及形式上的理,转向存在自我之中的完整和协调的过程。说句通俗话,宋人似乎在告诫自己:“要学会自己做主。”
这种文化观反映在制度上,便使文人可以断言,学者能够独立于政权来悟“道”。正像有的学者所论述的:“它以此创造了一种纽带,来联系社会和政治以及作为社会基础的自我赓续的地方精英和自我限制、不积极有为的政府。”[6]这一现象也便导致了宋代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7]
“宋学”在两宋的突出地位,自然难以抹杀它对艺术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文化观反映在艺术上便是人文精神的张扬,它有着两方面明显倾向:
第一,是重艺术家主体精神的表现。宋代艺术重视主体精神的表现,虽然这种主体精神还有着许多因素的限制,但相比较于前代确实有着较大程度的拓展。李成就说:“吾儒者,粗识去就,性爱山水,弄笔自适矣。”[8]李成画山水完全是主体精神表现的需要,是“性爱山水,弄笔自适”。李公麟也有:“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情性而已,奈何世人不察,徒欲供玩好耶?”[9]宋代画论更是重视这种主体精神的表现,无论是《图画见闻志》、《林泉高致》,还是《宣和画谱》等都明显表现出这种倾向。
第二,艺术功用得到进一步拓展。此前艺术的功用主要体现在它的社会政治价值上,具有“宣教”之功。[10]宋代也崇尚艺术的“宣教”功用,但这种功用又结合了艺术的形象化语汇来获得。所以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1]被宋人所重视。[12]这“游于艺”一个“游”字道出了“心念”的意味。进一步,宋代画学注意到画有着“心印”的功用,郭若虚说:画“系乎得自天机,出于灵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13]黄山谷说得更清楚:“夫吴生之超其师,得之于心,故无不妙。张长史之不沾他技,同智不分也,故能入神。夫心能不牵于外物,则其天守全,万物森然出于一镜。岂待含墨吮笔,槃礴而后为之哉。故余谓臻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14]有着这种“得妙于心”的艺术,我们便不难想象为什么宋代会出现长于抒情的文人画萌芽了。
我们在谈论“宋学”对艺术的影响时,似乎关注更多的是士夫文人。其实,在宋代,艺术既是士人们的行为,更是普通文人诸如画院画家的一种行为,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创作的主体是后者而非前者。所以,我们往往从大多数宋人绘画作品中看不出“宋学”的直接影响有多大。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宋学”对画院画家的影响也还是存在的,这里有二点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自徽宗朝设立“画学”以来,画院画家开始对自身修养普遍重视起来,而他们加强学习的内容也为儒家之学,这是“宋学”复兴儒学的直接影响。南宋设立画院之后,虽然没有了北宋画院的“画学”系统,但大部分画家也都在宣和画院时期受过“画学”教育,他们思想观念上存有儒家文化的因素是必然的,这种思想观念一直在南宋画院中保持着。
第二,在画风上,北宋开始重视荒寒萧疏境界的表现,水墨山水画畅行,及至北宋神宗朝又有一次的画风变化,改变黄氏程式,花鸟重境界,重幽情逸趣,多画败荷雪雁,枯槎寒禽,弱柳幽雀,远离尘俗。这与王安石变法有一定联系,但更多表现为“宋学”的文化辐射。到了南宋,更加强调这种“淡逸”画风,追求“形”之外的“理”,变“繁琐”为“整一”,改“呆滞”为“灵动”,从重“形似”到重“意趣”。这一切都不能说与“宋学”的文化观毫无关系。
二、“格物致知”的文化途径
“宋学”在确立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时,特别强调“天理”的重要性。那么,“天理”究竟为何物,在学术界尚有争论。[15]不过它是宋学家们力求抵达的彼岸,其途径就是要“格物致知”。通过“格物致知”的修身实践,以达到“天理”的标准。所以有学者也将“宋学”的核心概括为:“关于人的学问,它所讲的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和自然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发展的前途和目的。”[16]
何谓“格物”?《二程遗书》中有:“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17]由此,“格物”就是“穷理”。那么“理”又为何物?二程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18]也就是说,理在自然为不可违抗之“命”,理在社会为规范行为之“义”,理赋于人为先验之性,理寓于身为主宰之心。这样看来,理即一切,一切即理,理在人的心外,它又在人的心中。由此,“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它可以类推。”[19]归根结底,“格物”就是要通过众物之理与人心中之理发生契合,触发出人的自省与觉悟。
“格物”不是最终目的,“格物”还是为了“致知”。二程说:“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烛理明,自然乐循理。”[20]先求知以明理,后循理而乐行。朱熹对“格物致知”总结得最明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21]这是将儒家伦理规范转化为文人内在主动欲求,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
从文化的立场上看,宋学的“格物致知”要求文人士夫多学多识,所谓:“人之蕴蓄,由学而大”。[22]学的对象既是古圣贤之言与行,所谓:“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23]又是“物之理”,所谓:“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24]“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人有见一物而悟者,有终身而悟之者。”[25]这种因学的对象不同,似乎本身就构成了矛盾。[26]其实也并不矛盾,朱熹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27]那么,学的方式“物之理”毕竟与“古圣贤言与行”不同,对“物之理”的体察应重在行动上。所以,“格物致知”的文化途径也就有着各自的不同。
表现在艺术上,艺术家也同样十分重视内在修养的提高,格物的途径,重视琴棋书画、诗礼弦歌的方式,从而获得调息养气,宁静自适的内在充实。另一方面,艺术表现内容既重视文人士夫“格物”的对象,如绘画上的山水、花鸟题材,又重视生活风俗,如界画、风俗画形式。艺术表现手法趋向于对象精神的写实,这种精神写实并非只注重对象的外形,而是努力表现对象内在之性、之理。苏轼的“常形”与“常理”之分辨最能反映这种不同之处。[28]
三、“右文”的文化政策
有些学者对两宋的文化政策表现为“右文”性质颇有微辞,[29]但我认为即使宋代没有因“扬文”而“抑武”,但“扬文”却是在不自觉中成了自觉,这是不争的事实。
宋代“右文”政策的推行,首先是由皇帝重视所致。宋代自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就特别重视“文治”天下的重要性,打天下时他是一介武夫,治天下时他成了尊儒重文之君,享有“性好艺文”之称。[30]自此之后,宋代皇帝没有不重视文化的,[31]皇帝也逐渐变成了文人学士中的一员。
宋代的“右文”政策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在古代中国,文化专制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秦之焚书坑儒:汉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魏、北周、晚唐、五代发生的“三武”“一宗”毁灭佛法的事件:明清的文化酷政……。相比较而言,宋承唐制,在文化上基本坚持兼容并包的政策。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即并“宋学”畅行,也是援佛道入儒的产物。在官方的科场考试中,也并非纯以儒书为限,多杂出于老庄之书。对于应考的答卷,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也都不做任何规定和限制,这对士夫文人的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科举取士更加扩大。科举制度创始于隋唐,目的在于选拔俊杰、网罗人才。宋与唐相比,无论在科举制度操作上,还是人数上,都较唐代有很大变化。宋代科举更加严格,避免了科场舞弊。[32]宋代科举人数之多更是让人不可思议。在太平兴国二年科举考试中,一次就取109人,难怪宰相薛居正着急了:“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但太宗却说:“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33]科举制度的改革和人数的扩大,提高了庶族出身文人的数量和实力,这样一来原居于社会下层的人群也有了较多的取仕机会,人们一旦丰衣足食,便要令子弟去读书应考,社会的文化素质普遍获得提高。
第三,礼遇文人士夫。宋代的“右文”政策还表现为国家的权威与社会秩序依赖于文化与教育的支持。“只有由知识阶层表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系统,才能有效地建构着政治与伦理的秩序,而一个庞大而有影响的知识阶层的舆论,对于国家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34]因此,宋初开始,朝廷不仅礼遇文人士夫,也重用文人,[35]后来一直效仿。这一重文士的皇家取向,很快造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人阶层,使宋代文化氛围高涨起来。
第四,文化传播更加广泛。刻版印书创始于宋代,也昌盛于宋代,造纸技术在宋代也日益得以提高,这都使得书籍的流通量成倍扩大,图书的刊行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传播。而且宋初朝廷还专门组织文人修撰大型图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及至真宗朝,经版由宋初不及四千,增至十余万。[36]宋代这种编撰风气一直不衰,高宗南渡后,因前朝图书文献散佚迨尽,编撰力度更大。[37]
宋代文化传播还表现在教育的昌盛。这种昌盛包括了官学和私学共同繁荣。在宋廷右文政策下官学发达已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宋代私学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宋代之前,私学是被禁的,而宋代私学甚为普遍。《宋史》道学传、儒林传、隐逸传以及《宋元学案》中都有多处关于私学的记载。书院在两宋也特别兴盛,尤其是南渡之后,地方州县学日趋凋落,而书院却大为发展,这与理学倡行,理学家到处聚徒讲学有很大关系。[38]
宋代的“右文”政策对艺术有什么影响呢?它也同“宋学”的文化观相类似,主要侧重于宏观影响,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翰林图画院的设立以及画院画家地位的不断提升。翰林图画院在徽宗朝设立“画学”,用传统经典作为画院学生学习白勺科目,也反映了“右文”政策的直接影响。到了南宋,全国上下凡知名画家没有不被宫廷所重的,所以南宋画院几乎云集了所有有成就的画家。宋代“右文”政策还为艺术向多极发展提供了优良环境,与前代相比,宋代艺术门类最齐全,风格最多样。南宋时期,象梁楷这类亦颠亦疯的文人也为画院所接纳,[39]不能不说这是宋代文化政策的宽松。这种宽松的气氛必然使艺术走向极至,风格变体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四、雅俗并举的文化风气
“宋学”的畅行,尤其是宋廷的“右文”政策,为宋代文比繁荣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宋代文化成就自然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40]在这种文化繁荣的局面中,既有士夫之气的雅文化,也有市井特色的俗文化,雅俗并举共同将宋文化推向极至。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论及的“雅”与“俗”具有着较大的相对性,而且两者电没有褒贬之分。所渭“雅文化”,主要是指它的创作者多为具有传统文化知识的文人士夫,其文化中较多地体现出佛道儒的精神,也就更能适合传统文人的欣赏口味。而相对的“俗文化”,具有“通俗文化”的意思,它的创作主体虽也为文化人,但其身份多为市民,所以也更能适合市民的欣赏口味。宋代文化雅俗并举的特征并没有孰主孰次之分,只不过古代中国士夫的身份永远高于市民,所以“雅文化”也就显示出它的优势来。
宋代“雅文化”在艺术上的反映,不仅有相对应的文学成就、音乐成就、书法成就。[41]而且绘画艺术成就也十分突出。绘画中的文人画理论和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写意画的出现,以及在水墨山水和工笔花鸟上的杰出贡献,都明证了这一点。但宋代“雅文化”又有别于前后,正象前面我们所提及的,它有着一定的相对性,也就是说宋代“雅文化”中也渗入了许多“俗文化”的成份。比如说宋问,它就不象唐代的诗歌那样,长于儒稚端正,言志咏怀。宋词的产生与市井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初写男女之情,后来才为文人士夫抒情而用。宋代绘画也是如此,宋代具有突出影响的画院绘画,多数画家来自民间,因丹青一技而被召入画院,他们接受过正统教育,其作品也多倾向“雅文化”,但其“俗”的成份还是存有明显痕迹,或许这俗还是艺术家们的有意追求。如有些风俗题材,虽然出于画院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画家之手,[42]但其题材就决定了它“俗”的倾向。
宋代“俗文化”更是古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高潮,这是与北宋中后期城市商业的繁荣而带来的文化发展分不开的。这种“俗文化”观念在宋代推广的原因,不仅表现为宋代士夫文人多为庶族出身,而且宋代“党祸”以及不宁的战事,使得文人们经常与平民为伍,客观上也促进了“俗文化”对“雅文化”的渗透。更重要的是,自从中国文化史上凸现出“俗文化”之后,它就不断地向成熟的境地发展着,它在吸引社会广大民众的同时,也吸引了士夫文人的目光,它的新奇生动、俚俗浅显、活泼恢谐的独特品格都为中国文化注入一股新的血液。而且这种稚浴交融在南宋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可能因为北宋灭亡,大批文人流落民间,一旦他们重新获得身份之后,在他们的知识与视野之中,他们的文化表达形式上也便就有了更多“俗”的成份。在宋代,可以说后世一切通俗文艺品种几乎都产生于此时,如小唱、鼓子词、诸宫调、词话、讲史、说经、杂剧、南戏、傀儡戏、影戏、版画、招贴画、话本、剧本、词曲本、小泥塑……[43]应有尽有,这正是宋代市井文化的一种折射。
在中国画领域便是大量风俗题材与风俗情结的表现。风俗情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与处于社会基层的农民、城市市民以及手工业者、商人连接在一起的,并与这些阶层有着普遍的认同感。宋代绘画创作的主体在画院,画院画家由宫廷向社会民间招募,因为其身份决定了被招的对象与民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他们就是其中的一员。虽然宫廷绘画中也有一些文人参与,那是迫于皇帝的隆恩,而且即便参与绘事,也不会改变他既有的文人身份,象大小李将军、阎立德阎立本兄弟、赵伯驹赵伯骕兄弟等均属于此类。来自社会基层的画院画家们尽管有着丹青一技,但其生活的环境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怎么也抹不去那世情风俗的影响。
画院画家属于宫廷“御用”文人,这种文人的意义到了两宋才有所提升,但他们在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心目中,其“工匠”的性质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考工记》所汜的分工是如此的明确:“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显然画院画家也应列入“百工”之中。这从身份性质上就将画院画家与活动民间的工匠们混在了一起,来自民间的画院画家自然有着民间百工的趣味倾向。
但是宫廷是个特殊的场所,传统向来就有宫廷好尚细腻、雅致和威严庄重的趣味,而这正是风俗题材中缺少的。宫廷画家被招募入宫廷,主要是完成宫廷的图绘任务,诸如:大型石窟、陵墓以及宫殿、庙宇的壁绘、装饰性绘画等,而且这种创作多是奉命而为,有着种种的要求和限制,基本属于按样作画,画家所能发挥的特长也只是其造型能力和对绘画中风俗程式、样式的掌握,他们的绘画必须合乎礼法。因此这些画家毫无著作权可言,连其姓名也不能有文献留传下来。[44]宋代宫廷画院在性质上有着较大变化,绘画作品作为观赏性功能获得了提升,因此有些专画民俗风情但又有观赏趣味的风俗画,在宋代画院中开始流行起来。
而且,宋代有着风俗绘画的极好基础,这是由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特征决定的。社会需要风俗绘画,人们接纳风俗绘画,风俗绘画成了宋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从事风俗画创作的画家和优秀作品不计其数,所表现的内容几乎涉及宋代风俗画创作的各个方面,有了这样的文化环境,宫廷画院中出现风俗情结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宋代画院有许多画家专以表现风俗题材而得名,最突出者有张择端、刘宗道、杜孩儿、苏汉臣、李嵩等,[45]也有一些画家虽不以画风俗而名世,但也常涉猎风俗题材,如燕文贵、李唐、朱锐、阎次平等,[46]更多的画家在作品中多少都会流露出与现实民情民风有联系的趣味性,尤其是在南宋画院,除了极少数作品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之外,几乎南宋画院画家的作品中部有着不同程度的风俗情结。就是南宋院体山水画,虽以山水为题材,但其形态和趣味中所透露出的民俗情结也是明显的。
两宋绘画在宋代文化观念、政策与风气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文人绘画的出现与画院的鼎盛,其绘画史上的重要意义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文人绘画作为绘画史上的新现象,它的出现虽然也有绘画自律性因素的影响,但其主要原因还是两宋文化思潮的直接作用。一般而言,魏晋时期文人就开始参与绘画,但那只是身份的特征,在绘画观念上文人的气息还得就范于绘画本体的需要。也就是说,画家更多的是关注所表现对象的本身,在宋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画家们在关注对象本身的同时,也开始逐渐关注自身的感觉,并由此进入自己的情感世界的直接表现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花鸟似乎先行了一步,因为梅、兰、竹、菊四君子从来就是文人们青睐的象征之物,自古有之,当这些诉诸于视觉的形象进入画面之后,便成了他们抒情达意的最好载体。在宋代文人绘画观念的影响下,元明清几乎成了文人绘画的一统天下。需要说明的是,文人绘画的出现与发展虽然是历史之必然,但其在美术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正反掺半的。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绘画形式的确定,为画家直抒胸意开拓了更为快捷、更为直接明了的最佳方式。但与此同时,人们在关注抒情达意的同时,便不自觉地疏于对造型客观化的留意。但这一现象并非完全出现在宋代,甚至元画家还是力求在写实绘画的统摄下来寻找更为方便的抒情形式。但由于苏轼等士大夫的文化影响,更重要的是元代之后对一种所谓标准笔墨的过份偏执,致使文人绘画在重抒情的同时,只留意于对笔墨形态的传达,而于客观对象关注越来越少,最后画面上仅存一些形的躯壳。这种失缺绘画造型本体的写意,致使文人绘画在明清的必然式微。
宫廷绘画几乎伴随着朝代的更叠自汉代就有着特定的影响,但画院的正式出现却是在五代,两宋是其鼎盛与繁荣期。两宋画院在美术史上是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不仅表现在画家人数之巨,精美作品之多,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由于皇亲国戚的参与和倡导,从而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风气,极大地推动了美术事业的发展,并使人们的视觉审美能力普遍得到提升。从教育的角度讲,两宋画院有着比较完备的建制,具有教育型制的范式,这是中国美术史上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难怪有人称之为“皇家美术学院”,似乎确有几分道理。这一现象的出现,正是缘于宋代文化环境而使之然。并且,两宋画院在风格上直接承传了唐五代画风,在趣味上则暗合了绘画发展从客体走向主体这一必然势趋。宋代开始,画家重于在画面中表现自身感受的诗意之美,这为元代绘画完全转向表现画家之情起到了很好的过渡作用。
标签: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宋代绘画论文; 风俗文化论文; 南宋论文; 宋朝论文; 国学论文; 画院论文; 画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