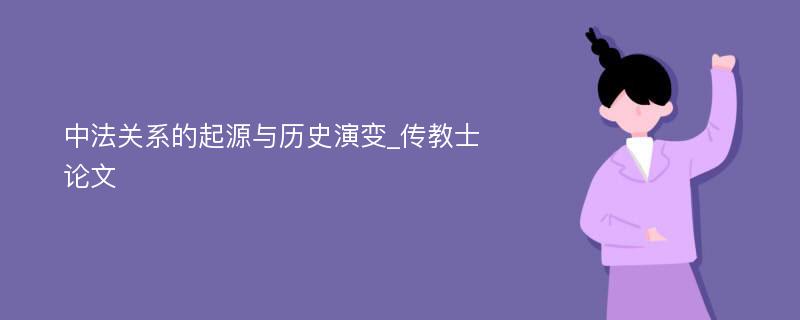
中法关系的缘起及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起论文,中法论文,关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一位研究中法关系的学者曾妙笔生花地写道:“试图寻找中法两国的共同点是徒劳的,一切都使它们格格不入:其疆域、其历史、其经济结构、其传统、其文明。历史上,孤芳自赏的‘中央帝国’从未对远在天边的‘蛮夷’小国法兰西产生过兴趣。而高卢雄鸡国目光又是如此短浅,
根本不可能想像到中国的重要和富有”。
(注:AllainClaisse:Les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 1945 —1973) .In:Notes et Etudes documentaires,No.4014—4015,septembre,1974.)然而,历史的发展却打破了一切地域界线, 中法两大文明必然地接触了,碰撞了。今天,中法关系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两国的关系经历了跌荡起伏的历程;既有震动全球的高潮,也有濒临破裂的低谷。研究中法关系的历史,无疑有助于理解中法关系的现实。
一、早期中法关系:法国传教士与商人在中国的梦想及失落
尽管考古证明早在古罗马时期中国商品就辗转到了欧洲,但中国与欧洲有据可考的人员往来实始于公元十三世纪。当凶猛彪悍的蒙古帝国大军横枪跃马于欧亚大陆、所向披靡时,欧洲教皇和君主们恐于蒙古的强悍,也出于联合蒙古配合十字军东征伊斯兰异教徒的动机,数次谴使前来修好。这种谴使的第一次,是在公元1245年至1247年之间,法王路易九世谴使前来蒙古地域考察,其使者未能见蒙古大汗而归。1248年,路易九世再次谴使东来,并携带了给蒙古大汗的友好信件及宗教礼物等。谁知使节带回欧洲的,是蒙古大汗以征服者的口吻写给路易九世的信件,称“汝宜每年贡我以甚多之金银,则吾人可永敦友谊;若不愿从吾言,则我将悉屠杀汝之人民,如我向日对于反抗我者之所为”。如此骄横之信函,更增加了路易九世的恐惧,1252年路易九世再次谴使谒见蒙古可汗,力陈友好,但使者带回的是一封措辞更为强硬的信,“汝若愿服从,宜更谴专使来此,证明汝等臣服之意。倘汝轻藐吾命,不听劝告,妄挟信念,自恃山高而峻,海阔而深,敢于抗我,当知我固有力能使极难之事成为极易,且能使彼远隔之国,成为逼近,终无所逃。我之所能,汝当熟晓矣!”(注:束世徵:《中法外交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2页。 )蒙古大汗的狂妄态度,使欧洲君主们却而远之,且死了联合蒙古共伐伊斯兰异教之心。束世徵先生在其《中法外交史》中把路易九世的这几次谴使作为中法关系的开端,其实并不准确。蒙古灭宋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是在1279年,在此之前法王与蒙古可汗的往来,很难称为中法关系。法王使节所到之处,也大部分是今天中亚诸国的地域。(注:张雁深:《中法外交关系史考》,北京史哲研究会,1950年,第1页。)这种接触, 只能算是法国人与“中华文化圈”的最初接触。
蒙古大汗定都北京之后,称北京为汗八里(Khan Baliq)。第一个到达汗八里的法国人当属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尼古拉。尼古拉是作为教皇派驻汗八里的第二任大主教来到北京的。(注:教皇派驻汗八里的第一任大主教是意大利人蒙德可维诺(Ioannes de Monte—Corvino), 他于1293年来到北京,1307年被任命为首任驻汗八里大主教,约1328年逝世于北京, 教皇乃于1333 年任命尼古拉为第二任驻汗八里大主教参见Henri 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Tome Ⅱ,P.425。)1368年,明兵攻入北京取代了元朝。在此巨变之下,尼古拉大主教与教皇失去了联系,下落不明。教皇认定尼古拉大主教已命断战乱之中。 乃至1370 年任命巴黎大学另一位神学教授纪尧姆·德· 普拉多(Guillaume de Prato)继任尼古拉为驻北京大主教,但当时欧亚海路尚未开通,陆路交通又战乱不休,普拉多一行踏上征程后便音讯杳无。于是教皇暂时停止了向中国派遣使者。尼古拉虽是法国人,而且驻北京长达三十余年,但他是作为教皇的代表来到北京的,他所建立的与中国的关系,实际上只是罗马教廷与中国的关系,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中法关系。这种不完全的关系,至尼古拉之后也中断了二百多年。
至十六世纪,欧亚海路交通已经开通,欧洲传教士通过海路来到中国,再度活跃起来。其中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经过努力,在北京确立了天主教的地位。协助利玛窦进行这种努力的,有几位法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虽系教皇所派,但却致力于建立中法两国政府间的直接联系。在他们的鼓动下,法王路易十四于1685年首次直接向中国派出了5名传教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张诚(Jean FrancoisGerbillon)、李明(Louis Le Comte)、刘应(Claude de Visdelou)、白晋(Joachim Bouvet)。他们来到中国供奉于朝廷,在整理历法、修理火炮等方面成效显著,时值中俄尼布楚战争,法国传教士在中俄谈判中担任翻译,受到朝廷欣赏。为表彰他们的功业,清朝康熙皇帝在紫禁城接见了法国传教士代表,接受了他们带来的法王路易十四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如八音盒、时钟之类,并委托他们转交给法国国王的礼物如丝绸、瓷器等。此后康熙皇帝于1692年下旨,命令发还明初以来没收的教堂,允许“西人”在华行教,康熙皇帝还特别赐给法国传教士一块地皮,允许他们在靠近皇城的地方修建一座天主教堂。(注:康熙所赐的地皮位于中南海边的西安门蚕池口,在此基础上建造的教堂已高出紫禁城太和殿许多,皇帝感到有损“天子”尊严。经多方交涉,至光绪时期,该教堂迁至西什库重建,即今天北京的西什库教堂。)可以认为,五位法国传教士的受命来华及他们与中国皇帝的晤见标志着中法两国政府的首次接触。
法国传教士对中法往来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麻烦。康熙皇帝对西方传教士持和善宽容的态度,但传教士是带着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信念来到中国的,即首先让中国的大众信奉上帝,继而通过这种信仰上的归顺扩大政教合一的法国国王的统治范围。然而中国与传教士们到过的许多地方不同,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惊讶地发现,远在他们到来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久远的文明历史和发达的社会政治经济,中国的三大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已牢牢置根于人民大众。因此对于西方传教士来说,他们要做的不是开化仅具有原始图腾崇拜的部落人群,而是从中国已有的宗教派别中夺取信徒,使他们背弃原有信仰而信奉上帝。在这里,中西文化在碰撞的过程中产生了很难调和的矛盾。在西方传教士眼中,中国官宦阶层所必信的儒教,中国社会的祭祖习俗,甚至中国语言对基督教“上帝”一词的称谓,都是与基督的教义所格格不入的。面对这种现实,基督教不同的派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耶稣会士们认为,“正面冲撞中国的社会、政治、宗教根基是相当危险的,重要的是要慢慢地改变中国人的习俗和精神”,(注:引自Jacques Gernet:Chine et christianisme,Action et Réaction,Paris,Gallimard, 1982,P.248.)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耶稣会士们采取了迂回作法,在发展中国教徒时,先不强迫他们放弃祭祖祭孔习俗,而是强调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中某些似乎类似的东西,如“神”,“天”之类。利玛窦等人的成功正在于此。但对于圣方济各(Saint—Franciscains)和圣多明我(Saint—Dominicains)等教派来说,中国的祭祖祭孔礼仪是正统的基督教徒所无法容忍的,他们对中国的礼仪习俗口诛笔伐,声称:“所有你们认为具有天使般和真正上帝般先知先觉的所谓土地神、圣人和贤人,所有你们的祖先,都不可能是上帝的朋友。然而你们却以最崇高的礼仪来祭祀他们,向他们鞠躬就如同向上帝鞠躬一样。这是多么荒唐!多么盲目!多么迷信与不恭!”(注:同上书第249页。 )圣方济各和圣多明我教派严禁他们发展的中国教徒继续祭孔祭祖,向中国传统习俗公开挑战。传教士对中国传统习俗的攻击自然引来了中国传统的猛烈反击。十七世纪初叶,中国民间就流传着专门批驳西教的《破邪集》,指出传教士“散布谎言,蛊惑人心”,其目的是教唆人们成为“逆子刁民”。(注:同上书第250页。)
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宗教界就中国的传统文化问题掀起了一场著名的“礼仪之争”。利玛窦于十七世纪初叶在中国去世后,他所代表的耶稣会士在争论中败下阵来。谴责中国习俗的观点在欧洲宗教界占了上风。教廷先后三次(1704,1707,1715年)公开谴责中国礼仪习俗,并于1742年断然禁止中国的天主教徒继续祭祖祭孔。教廷的决定在中国社会上激起了反洋教的浪潮,康熙皇帝在看了传教士所写的攻击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后,愤然批注“谎谬至极”。(注:同上书第252页。 )晚年的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他重新下旨禁止传教士进行宗教活动。康熙的继任雍正皇帝干脆下令禁止所有西教,没收西人教产,与西人的其它往来也被削减到了最低限度。至此,在非武力的文化冲撞中,法国教会在中国的努力宣告破产。
法国人前来中国的另一个动机,是开拓中国市场。然而,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努力也同样付诸东流。与英国对华贸易相比,法中贸易的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注:张天户先生对鸦片战争前英法来华商船数的统计与比较能充分说明这一问题。)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国与英国、荷兰等国家竞争中的失利。与英国、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相比, 法国商人到达中国市场要晚得多。 葡萄牙人早在1514年就发现了通往中国的海路,英国人1620年即踏上了中国海岸,荷兰人1622年为了进入澳门甚至与葡萄牙人兵戎相见,而法国人由于社会动荡、内战连年、经济衰败、对远航缺乏兴趣等原因,派出第一艘商船到达中国已是1698年。英国人早在十七世纪初就在远东建立了扩张基地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即设在印度的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法国由于与英国竞争的失利,在印度所占地域微乎其微。只是在两个世纪以后,法国在远东扩张的基地才真正建立起来,即法属印度支那。在此之前英国人利用东印度公司给对华贸易提供的各种便利,法国人自然是望尘莫及。其二,法国的早期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给法中贸易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为拓展对华贸易,法国先后成立过三个“中国公司”。第一个中国公司成立于1660年,但因荷兰人拒不向该公司提供承诺建造的远航船只,该公司未能向中国派出任何船只便宣告破产。继而成立的第二个中国公司于1698 年向中国派出了第一艘商船“安菲特里特号”(L' Amphytrite),“安菲特里特号”的第一次中国之行非常成功, 从中国运回了满船的茶叶、丝绸、瓷器、景泰蓝等。但“安菲特里特号”的第二次中国之行却不成功,运到中国来的法国商品没有市场,第二个中国公司也因此而倒闭了。1712年成立的第三个中国公司向中国先后派出了三艘商船,易货贸易兴隆。但当大量中国商品、特别是中国生丝及织品运抵法国、对法国纺织业形成竞争时,法国国王为保护本国纺织业,竟在1709至1716年之间四次下令烧毁从中国运来的纺织品。1713年,从中国归来的“王太子号”满舱绫罗绸缎在法国著名的海港城市圣·马洛被付之一炬。第三个“中国公司”也因此而破产。此后法国对华贸易更如雪上加霜,每况愈下。法国对华贸易不景气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性,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相适应的。中国皇帝从来没有感到对外贸易的必要。在与周邻藩属有限的物资往来中,皇帝体会到的是“天子”受贡的尊严,因而皇帝回送各国礼物的价值往往高于对方“贡物”的价值。当西方商人通过海路来中国进行实质性贸易时,清政府的反应可以用乾隆皇帝那句名言来概括:“天朝物产丰富,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注:乾隆皇帝1793年致英王乔治三世信中所语。)然而西方商人来中国海岸进行的贸易越来越具有强迫性。1757年,乾隆皇帝敕令在广州成立“公行”,一切外人与中国的贸易只能通过把持“公行”的“行商”进行。对此,西方商人自然不满意。法国人为促进法国商品在华销售,于1776年擅自决定在广州派驻一“领事”,但这个不受中国朝廷认可的领事在广州只能偷偷摸摸地活动,对促进法中贸易于事无补。至1801年,法国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秘密领事灰溜溜地离开了广州,1804年,在广州的“法国洋行”也租给了一位英国商人。至此,“法国在中国的影响实际上已告完结”,(注:Henri Cordier: Histoire g én éralede la Chine,Tome Ⅲ.P.378.)“法国多年经营之对华贸易美梦,尽成泡影”。(注:张雁深:《中法外交关系史考》第20页。)诚然,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性拘束外贸对所有国家都是同等的,但由于法国与英国竞争失利及法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原因,法中贸易受到的影响显然大于别的国家对华贸易。法国对华贸易萧条的第四个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法国由于未能控制当时的鸦片产地印度,在“获利甚丰”的鸦片贸易中没有多少份额。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是以中国的大量出超为特点的。当中国的茶叶、丝绸等在西方市场上畅销的时候,用惯了土布陶碗的中国农民对欧洲的洋布、玻璃、染料等却不屑一顾。由于西方商品在中国没有市场,因此来华贸易的西方商人都需携带大量白银用于购买中国商品,
“运往中国的大部分是银子”。(注:HenriCordier: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Tome Ⅲ.P.375.)一些西方汉学家经过研究后惊呼:“十八世纪的中国成了欧洲货币的坟墓”、“从‘新大陆’开采的贵重金属半数流通到中国后即停止了流通”。(注:Deveze,Michel, L'impact du monde chinois sur laFrance,l'Angleterre et la Russie au XV Ⅲ ème siècle. In: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la Missionfrancaise de Pékin aux XV Ⅱème et XV Ⅲème si ècles.Paris.1976.P.9.)在纯贸易性质的往来中, 欧洲商人在自给自足的中国市场前束手无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西方商人竟然干起向中国输入鸦片、让中国人染上烟瘾后被迫用中国商品换取鸦片的罪恶勾当。由于当时世界鸦片产地主要集中于英国控制下的印度,英国人几乎垄断了鸦片贸易,并利用鸦片迅速改变了其对华贸易的入超状况。法国由于不控制鸦片产地,对鸦片贸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当英国对华贸易处于可耻的兴旺之中时,法国对华贸易却进一步衰落。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事实是,在鸦片战争前中法两国的和平接触中,法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在中国的梦想都化为了泡影。意识形态色彩的浓厚和贸易关系的薄弱是早期中法关系的基本特点,直到现在,我们仍时时能感到这一历史因素对中法关系的影响。
年代 英船来华数 法船来华数 年代 英船来华数 法船来华数
1787 62 31826 85 2
1788 50 11828 73 3
1789 58 11829 72 2
1790 46 11830 72 5
1791 23 41831 93 1
1792 39 21832 90 3
1802 38 11833 107 7
1803 43 11834—每年约每年约3
1844 100
1825 61 1
资料来源:张天户:清代法国对华贸易问题之研究。 载《外交月报》1963年6月号。
二、近代中法关系:不平等条约的深深烙印
不论是想在华传教也好,想与华通商也好,应该说这都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而产生的正常需求。但同样正常的是中国经济文化受到外来碰撞时产生的自卫性反应。问题在于,当西方国家在经济文化的和平碰撞中未占上风时,它们想到了诉诸武力,正如传教士们所言,“如果我们不给中国人来点硬的、不让他们屈服于士兵之前,那我们看不到使他们归顺基督的任何希望”,“如果欧洲君王们不要相互分裂和争吵,而是致力于扩大基督的统治、迫使中国君主允许传教士宣传教义并允许当地人倾听真理,那么使中国人归顺基督将是轻而易举之事”。(注:法国传教士Ribora和Melchior Nunez 1596 年的信件, 引自Bernard:Les missionnaires du XV I ème siècle,P.85.)然而, 当西方传教士和商人跟在刺刀后面重新返回中国时,他们的在华使命就牢牢打上了殖民统治的烙印,它们的在华存在也就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平等条约和中华民族屈辱的标志之一,它们从中国大地被扫地出门也就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当法国传教士和商人面对中国一筹莫展时,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鸦片战争硝烟弥漫之际,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向中国派来了“真盛意使团”(Mission de Dubois de Jancigny), 该使团的任务有二,其一,获取远东中英纷争的确切情报,其二,在中国海域的英国舰队中体现法国的存在。真盛意来华后,以调停中英纠纷的斡旋者面目出现,他企图让清朝两广总督相信如果英国拒绝法国的调停,法国舰队将参加对英国作战。并称法国愿意帮助中国建造军舰大炮,要中国派团到法国考察。对这种异乎寻常的建议,连笃信“以夷制夷”的清朝统治者都不敢轻易相信,真盛意使团空手而归。当中国朝廷屈服于武力,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后,法国政府于1844年再次派来了使团,这次使团由喇鄂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率领, 由八艘军舰护航,气势汹汹而来,使团的主要目的是迫使中国政府给予法国“与英国相同之商业利益与相同之保障”。(注:1843年11月9 日法国外长训令第一号,参见张雁深:《中法外交关系史考》第27页。)当时清廷上下都处于鸦片战争后“惊恐未定”之中,喇鄂尼没费多少功夫,甚至没经过真正的谈判,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这一条约使法国享受到了清政府给予英国的各项通商特权。然而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在与清政府特派大臣交涉时,喇鄂尼又竭尽威胁之能事,提出了所谓“解除教禁”的问题,清政府虽对天主教解禁顾虑重重,但唯恐法国“别生枝节”,只好承诺解禁。《黄埔条约》签订后,道光皇帝批准了天主教开禁,在喇鄂尼的威逼下,道光又于1846年2 月通谕全国,明令不许各地官吏查禁教堂,要求各地发还过去没收的教产。“护教条款”使法中文化往来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康熙前期,允许西人在华行教是皇帝对传教士的“恩惠”,到了雍正时期,传教士的活动被严格禁止,《黄埔条约》签订后,保护西人在华传教成了清政府必须履行的义务,这种“恩惠”—“禁止”—“条约义务”的演变过程,准确地反映了清帝国的衰败及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护教条款”对中国社会关系的演变也发生了微妙的影响。在此之前,农民与朝廷在抵御外来文化渗透方面是一致的,但《黄埔条约》签订后,朝廷被迫承担了保护天主教在华活动的义务,然而农民对自己的故土文化却依然眷念,对洋教在华活动依然抵触,尤其是对于以占领、经营土地为特点的天主教更为反感。过去中国皇帝和农民与基督教文化的矛盾现在演变成了中国皇帝与农民在西方传教士问题上的尖锐对立。由于法国是天主教在华保护国,因此,“护教”成为法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宗教纠纷也成为中法关系的重要特点。
《黄埔条约》改变了西方在华传教运动的性质,也改变了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行为。由于有了自己国家的武力作后盾,传教士们一改过去谨小慎微的习惯,变得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在法国政府保护下的、以经营土地为特点的天主教在土地购置方面巧取豪夺,与以土地为生的中国农民矛盾越来越大,在很多地方,农民反洋教的情绪越来越针对法国。英国著名的汉学家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研究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时注意到,《黄埔条约》签订后若干年内,“针对英国教会的暴力行为很少,而针对法国保护下的天主教会的暴力行为却日益频繁和严重”,马士断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兰西民族、法国人以及罗马天主教在中国受到憎恨”。(注: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18,V.Ⅱ.P.23.)这种憎恨的两次重要表现,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重重两笔的“马神甫事件”和“天津教案”。
《黄埔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通商之五口行教,超越这五个地方的传教行为从理论上讲就是非法的。但是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法律置若罔闻,擅自深入到中国内地活动的事情屡屡发生。自《黄埔条约》签订后至“马神甫事件”发生前,发生了多起法国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活动被擒事件,大部分被抓获的传教士都依“护教条款”规定交还法国领事馆,但也有个别法国教士在与中国农民的冲突中伤亡。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教士马奥斯多(Auguste Chapedelaine )是其中之一。 马奥斯多1853年深入广西活动,与当地村民多次发生冲突,1856年被处死于广西西林县境内。马神甫被处死以后,法国教会上书法国驻广州代办,大肆渲染马神甫被处死时的惨景,耸人听闻地描绘马神甫如何被缚于柱上,如何被一刀一刀地片去身上的肉,刀口上被抹上盐,他那还在跳动的心脏如何被切成薄片,如何放进猪油锅中煎熟并下酒食用等等,要求法国军队对中国动武。法国代办随即向广州及澳门附近的法国海军作了布置,并将这些布置报告了法国外长。这一事件与所谓“亚罗号事件”一起,成了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使节得以常驻北京,西方传教士也获得了在中国全境自由传教的权利。然而依仗不平等条约而深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们只能激起中国民间的更大反抗。
1870年,天津发生了多起儿童失踪案,被抓捕的拐骗犯招供他们把被拐儿童卖给了法国修女。有人潜入法国教堂后院基地,发现了大量儿童尸骨。消息传开,愤怒的人群涌向法国教堂。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Fontanier )气势汹汹地来到清政府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府第,要求崇厚派兵弹压示威群众,而崇厚认为只需派官员向人群作解释,劝说他们离开。丰大业对此不满,竟然拔抢向崇厚射击。从崇厚宅第出来时,丰大业见天津知县刘杰正欲进见崇厚,竟破口大骂,并向刘杰开枪,将刘杰的随从打成重伤。丰大业的暴行将示威群众的愤怒推到了极点。人群沸腾了,丰大业被群众当场打死,法国教堂和领事馆被焚毁,愤怒的人们呼喊着“先杀法国鬼子,再杀别国洋鬼子”,(注: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Ⅱ,P.246.)满街追杀法国人。结果,14名法国人,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 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和三十多名在法国教堂工作的中国教士被杀死。自然,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事件很快被清政府镇压。20名中国人被斩首,25名对事件“处理不力”的地方官员被发配边疆,被斩首的中国人首级被挂在天津城墙上示众多日。清政府向法国政府赔偿五十万两银子,并派从丰大业枪口下侥幸逃生的崇厚作为专使到法国巴黎向法国国王陈致歉意。被焚毁的法国天主教堂很快被新建起来,那座建筑于天津人心目中圣地的望海楼遗址上的教堂,与修建于两广总督府旧址上的广州天主教堂和修建于皇宫边上高傲俯视皇宫的北京天主教堂一起,似乎构成了法国保护下的天主教在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然而在中国人民心中,这只能增加对外来压迫的仇恨。
对于天津儿童失踪事件,法国教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天主教堂的名声不佳,天津居民很少把孩子送往法国修女开办的育婴堂。据法国史书称,为了搜罗更多的孩子,法国修女奖励把孩子送到育婴堂的人,每当有人送来孩子,修女们就付出一些报酬,这种做法实际鼓励了歹徒拐骗幼童。一些法国修女又特别愿意给孩子进行“临终洗礼”,鼓励人们把临死的孩子送到教堂受礼,而1870年6月天津流行瘟疫, 更增加了死亡儿童的数量,死去的孩子埋在教堂后院墓地,被盗墓人发现后引起轩然大波。(注:Henri Cordier: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1860—1900,Paris,Felix Alcan,1901,P.384.)但当时在天津市的传言是:法国修女杀死幼童,挖出幼童的心脏和眼睛用于制造“魔药”。这种传言显然属夸大其词,(这种夸大其实并不甚于法国传教士对“马神甫事件”的夸大),但就是这种夸大之词,却激发了如此猛烈的反洋教运动。让人深思的倒不是这些传言有多大的可信度,而是这个事件本身揭示了在中国民间反洋教(在天津是反法国教会)的情绪是多么强烈。意识形态冲突始终是中法关系的一个鲜明特点。
十九世纪中法关系史上的另一重大事件,是中法两国在越南的冲突。 历史上的越南由东京(Tonkin )、 安南(Annam )和交趾支那(Cochinchine)三部分组成。在成为法国殖民地之前, 安南与中国保持着藩属关系,安南皇帝每四年向中国皇帝进贡一次,中国皇帝则回赠以厚礼。首批到达安南的法国人还是传教士,但法国传教士在安南遇到了与在中国遇到的同样困难,宗教纠纷也屡屡发生。1858年,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以护教为名向安南派去了海军舰队,以武力征服。其后,法国以武力强迫安南国王签订了三个条约,即1862年、1874年和1883年的三个“西贡条约”。通过这三个条约,交趾支那的大部分变成了法国殖民地,安南和东京变成了法国的保护国。法国在越南的活动引起了中国朝廷上下的巨大震动,各地方大臣纷纷上书,分析利害,指出如果越南被法国所占,而中国束手旁观,则整个藩属体系将土崩瓦解;与中国云南广西接壤的东京若落入法国人之手,后患无穷,法国不是唯一对中国心怀叵测之国,越南也不是中国唯一藩属,失去越南将不仅危及边疆,而必将祸及全国。(注:关于各地大臣的上奏原文,参见《清光绪中法交涉史料》,第二卷第3页和第17页。)民间请战情绪也强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从战场局势看,法国军队并不占优势,然而畏敌如虎的清政府却与法国签订了承认法国在越南权利的停战协定。中法战争后越南被法国完全占领,然而中越之间人文经济往来并不可能随之而中止,中法在越南的矛盾成为以后几十年内中法关系的核心问题。越南被占揭开了中国藩属瓦解的序幕,中法战争后短短十几年内,中国的藩属纷纷被列强所占,中国本身也进入了被瓜分的危机时期。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中,法国又获得了新的殖民利益:在华租界得以扩大(天津、上海、广州、汉口法租界)、广西和云南成为法国禁脔、广州湾被法国强租99年等等。中法关系再次被打上了深深的殖民烙印。
三、民国时期:中法之间的折冲樽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五·四”运动为发端,饱受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凌辱的中华民族开始了觉醒的过程。而英法等主要殖民帝国虽以战胜国的身份重新瓜分了殖民地势力范围,但在世界大战中它们的实力遭到削弱,战后亚非民族独立运动开始兴起,对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从发展趋势看,各殖民帝国已进入了没落阶段。中国地位的相对提高与法国实力的相对削弱使中法之间有了进行某种交涉的可能。然而,法国虽然实力受到削弱,但仍力图保住其在华既得利益,法国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无不体现这一基本特点。而中国虽以理论上的战胜国身份跻身战后国际关系舞台,但从总体上仍未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历届政府出于与帝国主义各国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处理对法关系时,虽有在民族觉醒背景下要求废除特权、维护主权的要求,但更有各种各样的交易与妥协。这是民国时期中法政治关系的基本格局。
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民掀起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利权为目的的“修约外交”运动。“修约外交”的具体目标是寻求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撤退外国军队、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等。列强对中国“修约外交”总体态度是消极的,但由于其各自在当时国际关系的不同地位,其在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又有所区别。德国与奥匈帝国战败,失去了发言权;俄国发生了革命,新政府在资本主义特权问题上有新的看法;美国因对“凡尔赛体系”不满而在远东问题上与英法保持距离;英国在中国北伐革命反帝浪潮冲击下态度有所收敛;日本力图取德国而代之,乘机扩大在华特权;而法国由于在一战中损失惨重,总想从战后世界安排中攫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在对华“修约外交”问题上,“法国不做任何满足中国民族主义政府要求的事”,(注:Morse,Hosea Ballou: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oston,New York,etc,1931, P.755.)“法国执行的是对中国‘不说、也不做’的政策”。(注:同上书第776页。 )特别能说明法国政府立场的是所谓“金法郎事件”。
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的规定,华盛顿协定批准生效后三个月内,协定签字九国将在中国召开会议,讨论中国提出的“关税自主”问题。而法国以中国在“金法郎事件”中未满足法国要求为由不批准华盛顿协定,使关于中国关税自主问题的会议迟迟不能召开。所谓“金法郎事件”, 纯粹是因法国提出的无理要求引起的。 根据1905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有关各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清政府应用对方国家的货币来偿付的“庚子赔款”,为有别于银本位置的中国货币,金本位置的法国货币法郎被称为“金法郎”。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郎贬值,法国政府不再接受用法郎纸币支付赔款,居然提出要中国政府用金币按战前汇率来支付赔款。这种折算方式给中国带来巨额损失,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直到中国政府在其它西方国家压力之下作出让步,法国才同意批准“华盛顿协定”,“关税自主”会议才得以召开,而这时离华盛顿协定签字已是三年半之久。在取消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问题上,法国的立场是能拖则拖,最好能保持现状。在“修约外交”的年代里,中国由于各种原因从德、奥、俄、比、英等国手中收回了十块租界,(注:参见:Ge Mingyi:《租界问题之研究》南京,1940年,第17页。又见P.Wou,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a Chine depuis 1919,la révision de traités sino—étrangers,Paris,1932,P290.)但与此同时,法国在华租界却完好无损,甚至有所扩展(如天津“老西开”)。正如马士所概括:“在取消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的问题上,法国的立场是尽可能久地保持现状,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法国与日本的关系有关”。(注:Morse,Hosea Ballou: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oston,New York,etc,1931,P.776.)确实,法国因其实力的相对不足和在亚洲利益的脆弱性,在与后来居上、咄咄逼人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交道时比其它西方殖民帝国更富妥协性。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法国在华利益基本上处于日本侵占地区,法属印支也逐渐受日本控制。在欧洲战场上,法国1940年6 月战败后成立了效忠法西斯德国的维希政府,由于德国与日本的轴心关系,维希政府在远东只能执行与日本协调的政策。虽然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宣布成立了“自由法国”政府,但是在中国和印支代表法国行使权利的却是维希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维希政府都采取了不利于中国抗战的立场。维希政府断然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在印支联合抗日的建议,甚至声称“要与日本联手对付中国”,(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电报,1940年9月22日。 )继而又在日本压力下中止了滇越铁路运输,不仅截断了中国抗战物资的重要通路之一,而且导致大批待运的中国战略物资被日军截获,其后竟与日本达成协议,将法国在印支军事设施交日军使用,允许日本飞机从印支机场起飞轰炸中国南方城市。特别让重庆政府耿耿于怀的是,法国驻华大使馆1943年2月派代表到南京与汪精卫傀儡政府谈判,于5月和7月与汪伪政权签订了所谓“放弃法国在华特权”的两个协定。 维希政府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南京政府, 其驻华大使亨利·科斯摩( Henri Cosme)有意回避,与汪伪政府谈判时只派去了其驻华大使馆的一秘罗伯尔·博瓦松(Robert de Boissezon), 并自认为“派去的是法国驻整个中国的代表,放弃特权也是向整个中国放弃的”,(注:维希政府外交部政治司亚洲处上呈文,1943年7月23日。 )意即派去谈判的并不是汪精卫政府的外交官,所作的承诺也不是向汪精卫政府作出的。然而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段又能骗得了谁呢?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维希政府“放弃”特权的举动是日本对中国盟国英美的外交总攻势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汪伪政府谈判签约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外交承认。对此,重庆政府作出了强烈反应,宣布废除中法之间关于法国强租广州湾和法国在华租界的有关条约,并中断与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此后,重庆政府才认真与“自由法国”的代表接触。然而“自由法国”并不控制法国在亚洲的代表机构,这种接触更多的只能具有政治上的意义。(注:关于蒋介石政府与“自由法国”政府关系的演变, 参见法国戴高乐研究院编:DeGaulle et l'Indochine,1940—1946,Paris,Plon,198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与法国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方面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虽然中国和法国对战胜国际法西斯势力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但由于在战争过程中两国都有半壁河山被侵占,两国都出现过与法西斯合作的傀儡政权,因而在战后事务安排中两国都受到排挤,两国的“大国地位”都受到怀疑。其次,在国内政治中,战后初期法国的戴高乐政权和中国的蒋介石政权都面临着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问题。由于这样的原因,戴高乐政权与蒋介石政权同病相怜,在中法之间最棘手的印度支那问题上各取所需,很快达成了妥协。根据战争期间大国协议,印度支那由英国和中国分区占领,接受驻印支日军投降。战争结束时,中国与英国按照大国协议分别进驻了越南“十七度线”南北地区,卢汉将军统帅的“滇军”还在越南海防地区对法国军队登陆北越的企图进行了武力抗击。这样,法国若想“重返”印支,就必须取得中英两国的同意与配合。英国由于自己也有恢复战前殖民地统治问题,对让法国重返印支似乎没有太大的反对。而在战争期间,蒋介石是坚决反对法国在战后再度统治印度支那的。在1943年1 月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曾明确向罗斯福总统表明:法国统治印支百余年,对印支只取不予,战后印支不应再交还法国。(注:参见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台北传记出版社1972年, 第183页。)但越是接近战争末期,蒋介石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就越软化。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在抗战中获得了大发展,战后与共产党作战需要大量兵力,无法拿出更多的军队长期派驻印度支那。在这种背景下,战争刚一结束,蒋介石就派宋子文访问法国,与戴高乐会谈,在对印支问题处理和对共产党政策等方面取得了原则共识。(注:参见Charles De Gaulle:Mémoires de Guerre,le Salut 1944—1946, P.494.)1945年11月至1946年2 月进行的中法谈判从总体上说比较顺利。法国同意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同意中国利用越南海防自由港免费中转货物,同意放弃在滇越铁路中国段的权利作为对战争期间中国战略物资在印支被日军扣押的赔偿。而国民党政府则同意将驻越军队撤出越南,将北越完全移交法国。对法国政府来说,放弃“治外法权”只是对现实的认可。如前所述,1943年重庆政府就宣布废除中法之间有关租界租借地的各种条约,抗战胜利时中国也已从日本军队手中收回了这些租界及租借地等权益。法国在1846年2 月的中法条约中实际上只是在法理上表示了法国合法政府对这一既成事实的认可。而“收回”印支,撤回驻印支军队既满足了法国的要求,又适应了在内战中的急需。被牺牲的,只是越南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权利。
国民党军队从印支撤出后,法国即开始在印支进行全面殖民战争,蒋介石也在中国国内全力打内战,顾不上在印支发生的事情。然而中法之间仍然风波迭起。首先是中国海军在西沙群岛主要岛屿上 (IleBoisée)建起了主权碑,并宣布:“中国政府已经收回了西沙列岛,中国国旗重新飘扬在西沙岛上”。(注:见1947年1月9日《民国日报》。)然后法国也向西沙群岛派去了军舰,并向岛上的中国守军宣称“你们位于法国领土之上,我们奉法国政府命令将你们带离此地,将把你们交给中国驻越南总领事”。 (注:法国外交部档案亚大司中国卷,
1944—1955,西沙群岛专档:致总督报告,1947年2月3日,西贡。 )中国守军拒绝了法国军舰的无理要求,法国军舰即转往占领中国军队还来不及驻防的西沙第二大岛(Ile Pattele)。当天晚上, 法国驻华大使馆和法国外交部同时收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法国驻华大使梅里耶(Jacques Meyrier)还被中国外交部告知, “如果不是由于外交部的劝阻,中国的海空军就已经出动了”。(注:同上)此后几天,中国报刊对法国对西沙群岛的觊觎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有的报刊甚至话中有话地写道:要知道尽管中国人民非常同情越南人民的解放战争,但目前在法越冲突中仍保持中立,这仅仅是由于中国非常珍视中国与法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注:参见1947年1月21 日《申报》时评:“西沙群岛与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驻华大使馆认为鉴于法国在印支的战争离不开中国的配合,因此应竭力避免与中国的冲突。法国外交部研究了西沙问题,认为可以将中法争端付诸国际仲裁,并认为在当时国际仲裁机构的组成情况下,法国有胜诉的把握。但法国提出的仲裁动议被中国拒绝。几个月后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通过了决议,责成政府“在必要时以武力逼迫法国从西沙撤出军队”。(注:参见Alain Claisse:Les relations Franco —chinoises( 1945 —1973),in Notes et Etudes documentaires,No.4014—4015,1973.)但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对政协决议束之高阁,事情只好不了了之。
西沙事件一波未平,法国军队在印支伤害华侨生命财产一波又起。法国殖民军队在对越南民族独立力量狂轰澜炸中,对旅越华侨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伤害。华侨的强烈反应对国民党政府形成了压力,国民党政府向法国政府提出了大额赔偿要求,并声称:“如果中国政府得不到满意答复,法国将对中国政府在外交领域和其它领域采取的一切措施负完全责任”,(注:引自1947年4月30日法国《战斗报》(Le Combat).)“中国政府将通盘重新考虑中法关系问题”。(注:Alain Claisse: Les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1945—1973), in:Notes etEtudes documentaires,No.4014—4015,1973.)为了平息事态,法国政府一方面决定向中国付出一千万元法属印支货币(Piastres)用于对受伤害华侨的赔偿,另一方面,通过法国驻华大使于1947年11月18日向蒋介石本人颁发了“军事勋章”,以表明法国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良好愿望。法国政府是在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之后作出这样的决策的。法国政府分析的结论是:“毫无疑问,蒋介石政府已因其内部困难而被削弱,但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无政府状态中,仇外宣传也总能团结起中国民众。而在这一方面共产党人的立场也决不会有丝毫软化。出于对印度支那的考虑,我们显然只能在合理的限度内继续支持南京政府”。(注:法国外交部档案亚大司中国卷,1944—1955,亚大司致外交部长报告,1947年6月11日。)然而, 在这种所谓“合理限度内的继续支持”中,南京政府却很不争气地土崩瓦解了。不管法国政府愿不愿意,它都必须与它所不寄予任何希望的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中法关系必须在这种新的背景下重新展开。
政治家、外交家在谈到中法关系时,总爱提到两国关系的“悠久历史”。固然,在这个还算悠久的历史中,两国交往确实不乏辉煌的篇章,但更有冲突与矛盾。两国对各自意识形态的执着、两国经贸传统的淡薄,都是中法关系脆弱、易于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双方清醒地认识这些消极因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增加相互理解和往来,也许更有利于双边关系的长期发展。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主旨。
标签:传教士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蒙古军队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路易九世论文; 基督教论文; 天主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