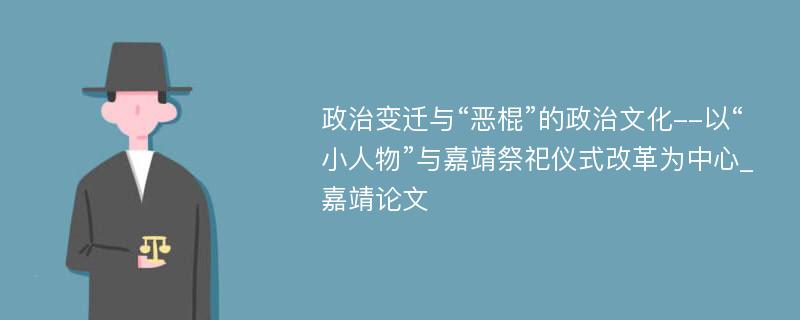
政治变动与“小人”政治文化——以“小人”与嘉靖朝的祀典改制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人论文,政治论文,嘉靖论文,变动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嘉靖朝大礼议的演进,在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中,君子小人之辩贯穿始终,实是明朝其他时期较为少见的现象。君子与小人本是对立的道德判断,但往往与一定的语境相结合,其特指含义才会更加显现。与其他历史时期君子小人之辩多是由政治纷争引起的不同,嘉靖朝的小人众生相是与“大礼议”以及祀典改制中议礼两派的纷争相关的。希哲师有云:“研究嘉靖朝政治,有三件事不能忽视,一是嘉靖初年大礼议;二是明世宗迷恋于建醮祷祀,好长生术;三是明世宗为‘猜忌之主’,颇护己短……前两点成为嘉靖朝政治上的敏感物,变成了衡量大臣是否‘忠君’的试金石。”[1]149大礼议及由此引起的祀典改制是明代中期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由议礼引发的对议礼两派的评价、明代中叶皇权及阁权的演变、政争以及嘉靖新政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的是关注议礼两派中的领军人物,如杨廷和、张璁等,而忽视那些在议礼活动中诸多“小人”对大礼议及祀典改制推波助澜的作用。①事实上,正是这些“小人”的奔竞与投机,才激起了明世宗对祀典改制的不断推演,进而影响了嘉靖初政的实施。孟心史评大礼议时有言:“君之所争为孝思,臣之所执为礼教。”[2]209但是很显然,这些“小人”在议礼中的目的不完全是为“礼教”,因此,这些“小人”就不能忽视。他们既是考察嘉靖朝大礼议及相关祀典改制的一个新视角,也是进一步研究嘉靖朝中前期政治变动的一个立足点。
当然,对这些“小人”的考察,既不是按《宋史》中辨君子小人以“取象于阴阳”,也不是沿袭过去的君子小人、忠臣奸佞的二分判断,更不是将所有在议礼中支持世宗的人都视为“小人”②,而是结合嘉靖祀典改制中诸小人的言行、得失,来考察嘉靖朝政治中“小人”的政治文化。因为诸如百户聂能迁、署丞何渊、给事中陈洸、百户随全、闲住光禄寺录事钱子勋、闲住教授王价、厨役王福、千户陈升、广平府教授张时亨和主事丰坊等人,他们在议礼中的表现、动机及作用与张璁、桂萼等根本不同,无法相提并论。
“小人”的推手与祀典改制的异常演进
嘉靖朝围绕“大礼议”而展开的祀典改制的起点,应是世宗即位后对其生父兴献王的尊崇,结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十一月祧仁宗而同时祔孝烈皇后于太庙。尽管学界不少先贤将嘉靖十七年(1538年)献皇帝称宗祔庙看做是祀典改制的结束,尽管将孝烈皇后祔于太庙是出于世宗本人的考虑,而非本文要着力研究的小人们的鼓动,但世宗之所以将孝烈皇后祔于太庙,正是出于世宗此前将其生父兴献帝祔庙,且独占一室,害怕他自己死后,后世以兴献帝从没有真正做过皇帝而将其祧迁,让孝烈皇后为自己预占太庙的位置,则可先将仁宗祧出,进而保证以后太庙祧迁时,其父不被祧迁。用心可谓良苦。故明人王世贞有云:“睿考入太庙非中外公论,恐千秋万岁后所祧主或非仁宗而睿考,遂下阶定议,欲以孝烈先祔。”[3]卷16《大学士徐公阶传》,596徐阶和诸大臣议于朝堂,诸臣认为应该先将孝烈皇后祀于奉先殿,只有礼科给事中杨思忠认为应速祔孝烈皇后,后徐阶虽在综合诸臣意见时“婉其辞”地表达了祔孝烈皇后于太庙不妥,但在世宗的暴怒之下,徐阶“皇(惶)恐谢罪”,“不获终守前说”。至此嘉靖皇帝对其父兴献王的尊崇活动最终完成。不过,考察整个过程,可以不难发现,尽管“大礼议”以及由此引发的祀典改制是“帝自排廷议定大礼”,并“以制作礼乐自任”的结果[4]卷196《张璁传》,5178,但其间诸多奔竞小人的推波助澜实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嘉靖朝“大礼议”的发生,实在是不可避免的。小宗入继大统,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特殊现象,在宗法礼制传统下,入继大统者对原来小宗的表孝道及祭祀等是势必要发生的。世宗朱厚璁的入继情况更加特殊。世宗入继时,他本人已没有其他兄弟可以承继其父兴献王的爵位并对兴献王进行独立的祭祀,因此由武宗遗诏中所定的“兄终弟及”而“嗣皇帝位”的世宗,在承嗣皇位以后,处理继承来的大统和自己原先小宗的尊崇问题就变得尤为突出了。其实,这个问题在即位前的相关礼仪选择上就已经出现了,如厚璁在自安陆到达京城外时,是否以皇太子礼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还是由大明门入而登极的争论以及在即位之初世宗就诏令礼部拟议其父兴献王的尊崇礼仪及称号等,都属于此。过去学界在论及此事时多将这些礼仪的提出归结于世宗的年少英聪,事实上,“从龙”的王府长史袁宗皋的作用实不可忽视。
初步议礼的结局可能是新立的世宗皇帝绝没有想到的。以杨廷和为首的议礼诸臣三议三上,且都为六七十余人的附议,坚持应以汉定陶王、宋濮王事为例,称应“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母”。廷议三上,或命再议,或为留中,或为不从。此间针对杨廷和等人的反对意见,首有时为礼部侍郎的王瓒和观政进士张璁指出的“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与汉哀、宋英不类”[5]卷50《大礼议》,734结果王瓒被劾,杨廷和恐其挠议,遂授意吏部将王瓒调官南京吏部。后有张璁独自上疏,主张尊兴献王为帝,母为兴献皇后。尽管张璁此议得到“方扼廷议”的世宗的支持,但世宗手敕杨廷和等按张璁之议议礼的要求,还是被杨廷和封还了,张璁本人也以“干进”为名被给事中朱鸣阳、史于光、御史王溱、卢琼等交章弹劾。面对杨廷和等人强大的反对力量,世宗的议礼要求表现为一定的无奈、无助,“朕受祖宗鸿业为天下君长,父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朕于罔极之恩何由得安,始终劳卿等委曲折中,为朕申其孝情,务加追尊美号,于安陆立祠,以为永久奉养,使朕心安,而政治、父神有所依倚”。[6]卷6正德十六年九月丙子,261过去学者们对这条史料关注不够,世宗对杨廷和等人提出的“务加追尊美号,于安陆立祠”的请求,并不为过。设身处地地想,其父兴献王“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世宗如何能心安?如果世宗的这个要求能得到议礼诸臣的支持,使其可以“申其孝情”,那么,以后是否还会有世宗进一步的议礼要求呢。事实是,杨廷和等议礼诸臣回绝了世宗这个最低的请求,这为以后张璁、桂萼等人的助大礼提供了空间,也为诸小人的投机钻营提供了机会。
对“大礼议”过程的详细考察不是本文的主旨。在嘉靖三年(1524年)底以前争考礼过程中,世宗在张璁、桂萼等人的鼎力支持下,几经反复,排击反对派,去“本生”二字,顺利实现了争考礼。至九月,大礼之议定,并颁诏布告天下,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王为献皇帝,兴献王妃为章圣皇太后。至此,“正名定分,父得为父,子得为子,兄授位于弟,臣授位于君,大伦大统,两有归矣。奉神主而别为祢室,于至亲不废;隆尊号而不入太庙,于正统无干。尊尊亲亲,两不悖矣”。[6]卷43嘉靖三年九月丙寅,1113应该说,世宗此前要求的“名”得以正了,“分”得以定了,其所言“务加追尊美号”的要求完全得以实现。如果按照这样的结果推演,于安陆立庙祭祀,也不会有任何障碍了。这样,世宗当时的议礼要求都已实现,嘉靖初年的议大礼本该到此结束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礼议之初,即有人指出大礼之议可能的结果。时为福建提学副使的胡铎言:“考(献王)不已则宗,宗则入太庙,入太庙则有祧,以藩封虚号之帝,而骤夺君临治世之宗,义固不可也。入太庙则有位次,将位于武宗上乎?位于武宗下乎?生而为之臣,死不得跻于君。”[7]卷1《胡铎》,101胡铎之言既指出了大礼议可能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指出了如此发展潜在的更麻烦的问题。本来“追尊美号”和“安陆立祠”是世宗皇帝申其孝情的两个基本要求。当然,这两者关系上,前者是根本,后者是基础,都是必须达到的,而安陆立祠实际上还是有进一步变更的可能的,正如胡铎所言的称宗入庙。如果说,此前“追尊美号”的争大礼是世宗皇帝申其孝情与张璁等人据情据理推演的结果的话,那么,后来世宗放弃“于安陆立祠”最初的议礼主张,逐步推进为立庙京师、称宗入庙、欲迁显陵于天寿山等,则完全是何渊、随全、钱子勋等干进小人的“凿空妄议”,一步一步怂恿鼓动、推波助澜的结果。
立庙京师是世宗放弃安陆立祠后第一个达到的目标。何渊等干进小人的不断推演是直接原因。本来,立庙京师是张璁首先提出的,他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一月所上的《大礼或问》中提出了“为兴献王别立庙于京师”。[6]卷8正德十六年十一月癸酉,307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礼科右给事中熊浃也提出“兴献王宜尊以帝称,别立一庙”。[6]卷10嘉靖元年正月己酉,362当时争大礼的主要目标还不在于是否要另立庙祭祀,至少世宗的议礼要求还是在争皇考、去“本生”二字的争考上,因此,立庙问题此时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这也是后来桂萼和方献夫在争考礼中相继提出献帝当别庙而祀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张璁、熊浃、桂萼和方献夫等提出别庙而祀的问题,都不是孤立提出的,而是在争皇考、去“本生”过程中,按照他们的主张自然推演出来的,是他们争考礼合乎逻辑地推演的结果。即便如此,张、桂等人别立一庙的奏请还是遭到礼部尚书汪俊等议礼诸臣的坚决反对。而吏部听选监生何渊于嘉靖元年九月所上立庙京师,“不必远祔安陆”的奏请,本身并不是争考礼演绎下的必然结果,而是对世宗原本主张的“安陆立祠”的超越。[6]卷18嘉靖元年九月己巳,555在张、桂、何渊等人的奏请下,嘉靖三年七月,世宗将其父的神主迎至京师,安奉于观德殿。至此,立庙京师得以实现。不过,观德殿并非祀献帝的专庙,乃是由奉先殿的西空室临时修葺而成,尽管在观德殿祀献帝时,所用乐舞世宗特旨仿太庙用八佾之制,但仍属内殿奉祀,在礼制上与太庙之祀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将献帝祀于太庙就成了以后其他小人钻营的方向了。
应该说,立庙京师已经远远超越了世宗当初的“安陆立祠”。尽管后来世宗本人以制作礼乐自任,在张璁、夏言、严嵩等人的帮助下,通过皇后亲蚕、弃配社稷、分祭天地、罢太宗配祀、祧德祖等一系列复杂的祀典改制,基本为世宗进一步推演尊其父而申其孝的祀典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中允廖道南提出的“都宫之制”,为世庙排于诸庙序埋下了伏笔。世宗谋求为其父称宗祔庙,只差关键时刻有人为他提议了。而在世宗等待这个关键时机时,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扬州府同知丰坊,因其“家居贫乏”,遂“思效张璁、夏言片言取通显”,向世宗建言“建明堂事,又言宜加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世宗得疏大悦。[4]卷191《丰坊传》,5071尽管礼部尚书严嵩认为“配帝当如奏,称宗则未安”,更有户部左侍郎唐胄上疏反对,结果唐胄被严旨切责下狱,严嵩被要求再议时遂“改口奉命,进献皇为宗,一如坊议”。[8]卷2《献帝称宗》,45至此世宗又实现了为其父的“称宗入庙”。丰坊被时人认为是“素有文无行”,其“入都献谀,距其父殁时尚未小祥也,不忠不孝,勇于为恶”,因此,世宗对献帝的称宗入庙又是丰坊之小人献谀与推演的结果。
在整个嘉靖祀典改制过程中,怂恿世宗迁显陵于天寿山是小人干进、献媚推演最突出也是最拙劣的表现。嘉靖三年八九月间,正值左顺门事件后大礼更定之前、议礼两派因议礼而起的政治斗争最酣的关键时刻,锦衣卫革职百户随全、光禄寺革职录事钱子勋希旨言“献皇帝梓宫宜改葬天寿山”。[6]卷43嘉靖三年九月甲子,1110事下工部议,尚书赵璜以为“皇考体魄所安,不可轻犯”,“山川灵秀所萃,不可轻泄”,“国家根本所在,不可轻动”,并举太祖定都南京不迁仁祖陵、太宗迁都北京不迁孝陵例,反对随全、钱子勋之议。而曾经“与事显陵”的五官灵台郎吴升也上疏反对随全的建议。尽管如此,世宗仍令礼官集议,实际上此举已经表明了世宗属意于迁陵。数日后,礼部尚书席书集廷臣意见:“显陵先帝体魄所藏,不可轻动。昔高皇帝不迁祖陵,文皇帝不迁孝陵,随全等谄谀小人,妄议山陵,宜下法司按问”,几乎完全重复了赵璜的意见。然而世宗并未就此罢休,以“先帝陵寝在远,朕朝夕思念”为由,令礼部“再详议以闻”。席书再次集议后仍“极言不可”,世宗方暂时放弃了迁显陵于天寿山的念头。
但诸奔竞小人的钻营并未就此结束。明人沈德符对此有详细考察,可见一斑:“迁奉献皇之说,始于百户随全,继以厨役王福等,又继以千户陈升、缘事监生詹啓等,屡请屡不行。至听选官王维臣等被重谴,而此议遂息。至十四年四月,上恭谒诸陵寝,并营寿宫于西山,于是京师遂有讹传迁陵者。时顺天府儒士潘谦、锦衣军匠金桂,各上疏请迁显陵于天寿山,盖预为希恩地也。旨下礼部参看。尚书夏言等奏……潘谦等望风进言,必有奸人主使,希冀非望,宜重惩治。上深然其言,下锦衣送法司讯治。于是议者益晓然知上意,无一人言及矣。至十七年十二月,章圣太后崩,上忽下诏,迁显陵梓宫改葬于北,六飞亲阅,得吉壤于天寿山之大峪……大学士夏言、尚书严嵩等,各具献皇梓宫启行图,及奉迁仪注上呈矣。上忽颁谕,谓奉藏体魄已二十载,启露风尘,摇撼远道,朕心不宁。于是嵩等又会议从上圣意,停启攒三使不发,别遣锦衣指挥赵俊者往视,而迁事中辍。……已而赵俊自承天还,言显陵玄宫有水,于是众啧啧又谓显陵当北迁。……工部郎中岳伦上言:梓宫南祔,未足遂陛下孝思之诚,请坚北迁之举,勿惑群臣之议。上怒,命锦衣逮讯,已而褫职,永不叙用。盖犹祖迁陵之说以媚上,不意其拂旨也。……三数月之间,陵寝大事,或南或北,或行或止,更改数番,一惟圣意自裁。宰执大臣惟唯诺奉行,不复设一谋出一见,如傀儡之受牵,可恨亦可哂矣!……章圣后南祔显陵已竣事矣,次年五月锦衣千户李拱辰上言:圣母南祔之后,灾异屡作,乞迎二圣梓宫俱葬天寿山。上斥其狂悖庸愚,下镇抚司逮治”。[8]《补遗》卷1《大峪山用舍》,796-797自嘉靖三年随全起迁显陵之议,至十八年(1539年)李拱辰因再议迁陵被治罪止,时历十五载,中间反复无常,甚至张璁、夏言、严嵩等宰辅大臣也不得不左右其间,更不用说是一心想为其父争得尽可能荣宠的世宗本人了。这些奔竞小人十几年的迁陵之议,最终并没有得到世宗皇帝的认同,这也是嘉靖年间小人们怂恿世宗祀典改制唯一没有成功的一次。不过,没有成功并不意味着小人们的迁陵之议对世宗没有产生过影响。
嘉靖朝祀典改制视阈下的君子小人之辩
其实,在嘉靖朝的祀典改制中,还有其他一些奔竞干进的小人,如建言考兴献王的山东历城县堰头巡检方濬、致仕训导陈云章、革退儒士张少连、教谕王价、南京通政司经历金述,又如力请迁显陵于天寿山的温州武举杜承美、除名兵马周密、致仕佥事宁河、湖广璧山县听选官王维臣等,他们和上文中提及的那些干进小人一起构成了嘉靖朝祀典改制中的小人众生相。不过,在嘉靖朝祀典改制下的君子小人之辩,并非完全单指他们。其时议礼双方互指对方为小人,这是嘉靖朝祀典改制下的一个特殊现象,与历史上的因政治纷争而起的君子小人之辩有很大区别。
在嘉靖朝大礼议及后继的祀典改制中,几乎任何一个阶段中,大凡站在世宗一边助世宗议礼者,都被反对者视为小人。争考兴献王是大礼议的起点,也是议礼双方礼争的焦点。张璁最初提出考兴献王,此论让“廷臣大怪骇,交起击之”,甚至欲置其于死地。后与桂萼由朗署入翰林,骤至詹事,诸翰林耻之,不与并列,“举朝士大夫咸切齿此数人”[4]卷196《张璁传》,5176,至有乔宇言其为“内降恩泽,先朝率施于佞幸小人。若士大夫一预其间,即不为清议所齿。况学士最清华,而俾萼等居之,谁复肯与同列哉”。[4]卷194《乔宇传》,5133甚至连“为人和易,好推毂后进”的费宏,也以“安能与小人相齮龁,祈赐骸骨”。[4]卷193《费宏传》,5109-5110诸多中下级官员如修撰杨慎、张衍庆等36人也连章表明“不能与之同列”。在前期争考礼中,举朝数百之人反对世宗与张璁、桂萼等人的议礼,特别是“左顺门”杖责以后,大批议礼官员被杖死、夺职或夺俸,被当时舆论视为正人者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而附和世宗的张、桂等人却得以升迁。这对此后的祀典改制以及后人对此事件的评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故清人赵翼言:“嘉靖中大礼之议,天下后世万口一词,皆是杨廷和而非张璁等。”[9]卷14《大礼之议》,238
与张璁、桂萼的冒死坚守大礼不同,争考礼告一阶段后,诸多奔竞小人活跃起来,朝中因争礼而起的对抗,集中转向了对这些奔竞小人们的抨击。陈洸是“左顺门事件”后第一个跳出来的奔竞小人。左顺门杖责后的血腥还没有散去,受杖官员的伤痂还在流着脓血,此时陈洗上疏世宗“主事张璁等危言论礼,出于天理人心之正,而当道者目为逢君,曲肆排诅,且群结朋党,必欲陛下与为人后之仪”,并直接点名攻击吏部首贰官乔宇、夏良胜是“用舍任意,挤排豪杰”。[6]卷42嘉靖三年八月癸巳,1087陈洸此时上疏,目的特殊,行为的意义特殊。陈洸在议礼之初任给事中,和大多数朝臣一样也是反对世宗考其父的,但在大礼议最激烈之时,他“奉使回籍居二年”,躲过了议礼中最激烈的君臣冲突,左顺门事件后,“复命,在道,已闻升湖广佥事,犹以旧衔上疏”。尽管是职位迁升,但毕竟是被放为外官,陈洸此举的目的非常明显,即以附和张璁、讨好世宗、攻击反对派来获得在京内迁升。陈洸的投机,即刻为一些朝臣坚决反对,并连章弹劾。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洗已外补,犹冒旧衔,假以建言,紊乱国典,宜行究问,以绝他觊。”[6]卷42嘉靖三年八月癸巳,1088何孟春的弹劾尤其值得注意。其一,何孟春对陈洸的弹劾时机是在世宗刚刚镇压左顺门的抗议者之后不久,何氏并不畏惧世宗可能对他进行再次打击;其次,何孟春明确指出陈洸是个投机钻营的小人,故意用旧衔上疏以期让世宗也像对待张璁等人一样,授他美职;最后,何孟春还指出陈洸的行为可能引发其他人的效仿,并建议世宗“宜行究问,以绝他觊”。此外,礼部官吴一鹏也上章弹劾陈洸并提出同样的建议:“若不痛惩,窃恐人人效尤,大礼之议,更无虚日,而圣聪亦不胜烦渎矣”。[6]卷42嘉靖三年八月庚戌,1100在对奔竞小人的抨击时,这些反对者无不关注到了小人们投机行为的效仿效应。
立庙京师及建世庙的倡议,是诸奔竞小人表现最为集中的,也是君子小人之辩较为激烈的时期。如前文所言,立庙京师的倡议本是张璁、桂萼等首先提出的,但他们提出此议是和争考礼相一致的,也是争考礼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也是对世宗原本要“安陆立祠”的巨大超越。继之者是小人何渊,他不断地上疏议及立庙事,此论一出,即刻遭到礼官的强烈反对。大学士石珤抗疏言其非礼,“但知希合取宠,不复为陛下体察”。[4]卷190《石珤传》,5048立庙京师以后,何渊被授以平凉县主簿,但他上任后屡为上官笞辱,遂自陈请改内职,世宗破格迁其为光禄寺署丞,何渊遂“请立世室,崇祀皇考于太庙”。[6]卷50嘉靖四年四月戊申,1257何渊请立世室,祀献帝于太庙,比原先张璁、桂萼和他自己所提出的“立庙京师”的主张大大向前迈了一步。此前,世宗曾因其父“不得享于庭”而耿耿于怀,何渊之请,正中下怀,故世宗立即将何渊之奏下部众议。不想廷议全面反对何渊之议。张璁斥何渊为“妄肆浮言,破坏成礼……上干九庙之威监,下骇四海之人心”。[10]卷2《庙议第一》,43礼部尚书席书会众臣议后指出,此前“奉迎安陆神主于大内,祀以天子之礼”是“大伦既正,大统以明”,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家庙之祭不可缺”,而此时众臣不敢认同何渊之议是因为“献帝未为天子,天统之正不可干”。[6]卷50嘉靖四年四月戊申,1257并指责何渊之论是“以私逞小智,妄为谀词”,并奏请“乞断自宸衷,正何渊之罪而寝其议”。[6]卷50嘉靖四年四月戊申,1260世宗不听众议,并让中官传旨“必祔庙乃已”。张璁再议反对何渊:“臣等愚昧,徒知皇上孝心无穷,犹未知皇上审处者复何在也,若曰请入献皇帝主于太庙者,援古之礼经,揆今之制度,均为有碍。臣等万死不敢以此误皇上也。窃念典礼方成,不可遽坏,公论方定,不可复摇。”[10]卷2《庙议第二》,45廷议的意见也基本相同。当时之情形,有如一年前杨廷和等反对议礼之势,“部臣如吏部尚书廖纪等,勋臣武定侯郭勋等,六科给事中杨言等,十三道御史叶忠等数十百人,咸以为大礼已定,不宜再更”。[6]卷51嘉靖四年五月己巳,1277-1278面对数十百人的反对,最后双方各自妥协一步,“观德殿规制未备,宜圣心未慊也,须别立庙,不干太庙,尊尊亲亲,并行不悖”。[5]卷50《大礼议》,755-756立世庙,既是何渊之议得以实现的表现,也是世宗君臣在入祀太庙上相互退让的结果。此后,在世庙建立地点,是否要别开神路,是否要与太庙同门等具体问题上,何渊更是多次迎合世宗,提出当时其他大臣都坚决反对的建议。世庙之立,特别是它与太庙同门,也为以后的小人再提进一步的要求埋下了伏笔。因此,清人夏燮说“世庙与太庙同门……为献皇帝异日入祀太庙张本”。[11]卷52,1401不过,尽管张、桂等人强烈反对何渊之议,但很少有像其他朝臣那样,动辄指其为小人。
与争考礼及立庙京师礼中某些重要的礼臣参与其中协赞世宗不同,迁显陵于天寿山之议几乎全是一些贱役杂流鼓动的。诚如黄景昉所言:“凡阿附议礼,多出于录事、巡简、教谕、县丞、千百户、监生,一种无耻杂流,意欲何为。”[12]卷6,344其实,黄景昉又真的不明白这些无耻杂流阿附议礼的真正意图吗?不过,面对这些杂流小人的阿附,面对不断引发的迁显陵于天寿山的妄议,当时的朝臣们却少有像前期争考礼、争立庙京师那样的坚决反对并严君子小人之辩。只有随全、钱子勋二人最初提出迁陵之议时,礼部尚书席书指其为“谄谀小人,妄论山陵,宜下法司按问”,及光禄寺厨役王福、锦衣千户陈昇上疏请迎显陵梓宫,葬天寿山之议再起,才有礼部尚书李时斥指其为“以屠宰贱夫,剿狂悖之说,以感激皇上哀慕之衷,而昇因希图宠荣,风闻附和”,并提出“若福等之议得行,无籍小人莫不各鼓挟诐词,摇惑国是,莫可谁何?乞敕法司将福等逮治如法,以为小人横议者之戒”。[6]卷129嘉靖十年八月己亥,3072缘何诸贱役小人提出迁显陵于天寿山时,朝中大臣,特别是礼臣没有像以前争考礼、争庙礼那样激烈反对,严君子小人之辩呢?窃以为,其一,随全、钱子勋等人提出的迁陵之议是希旨,且世宗对此议的初始态度也是很欣赏的,因此前所有反对世宗议礼的结局都是失败的,此次激烈反对恐怕亦会招致世宗的打压。特别是《明伦大典》颁行以后,公开激烈反对议礼的已很少见。其变化如范守己所言:“自甲申夏月以前(左顺门事件——引者注),建言者直拾衮阙,至此(嘉靖四年四月)为之一变云。然引咎自列,犹有古讽谏风,至邹公守益等之蒙斥,疏体为之再变,然丁亥后(颁《明伦大典》——引者注),荏梁之习成矣。其张胆朝堂,数及辅贰者,亦不多得。”[13]卷5,60其次,尽管有诸小人的多次提议,但迁陵之事是“屡请屡不行”,甚至还有倡议者听选官王维臣等被重遣,迁陵之议多有息歇之势,反对迁陵之议者也不会因这种可能并不十分准行的事和这些奔竞小人们发生激烈冲突。再者,反对迁陵者,除赵璜、李时外,诸如张璁、席书、夏言和严嵩等人,他们自己在整个议礼中不能说完全是出于对礼的遵循,干进之心不说一点没有,他们又怎能严君子小人之辩呢。
但张璁等议礼派对杨廷和等反对势力的反击,并不是以小人视之,而多以“权奸”、“党附”视之。以张璁为例。张璁认为,争考礼“两论相持,三年不决”,以孝宗为考者,“其始变于奸权大臣一人而已,礼官附之,九卿科道附之,初不顾事体之大、礼义之非者也”;[10]卷1《正典礼第七》,38“臣初叨进士,尝再上议,及著为问答,论辩其非。但言者不顾礼义,党同伐异,宁负天子,而不敢忤权臣,此何心也”;[10]卷1《正典礼第三》,28“今日典礼之议,以皇上与为人后者,礼官附和执政之私也”;[10]卷1《正典礼第四》,30“今臣等朝见,尚有二三权奸大臣,先行风示大小官员,俱不许与臣等往来,且又浮言恐吓,必欲使臣等变其初说,务相和同,以掩己之罪也”。[10]卷1《正典礼第六》,34所指“执政”、“权奸者”、“党附”均为杨廷和及在争考礼中附和杨廷和的其他朝臣。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在反击时也多持此论,而不是像杨廷和等视他们为小人那样对等视之。当然张璁、桂萼对何渊等小人在议礼上的奔竞也是鄙视的。“自是希宠干进之徒,纷然而起,下至失职武夫、闲罢小吏,亦皆攘臂努(怒)目,抗论庙谟。即璁、萼辈亦羞称之,不与为伍。”[11]卷52,1405
嘉靖朝的君子小人之辩,并不是像历史上其他时期因政治斗争而起的,而是在嘉靖初年世宗为显其孝尊其父的议礼过程中,议礼双方因争礼而起的,尽管它后来的发展与嘉靖初年的政局相关联,但在嘉靖朝祀典改制的视阈下,君子小人之辩的意义也因此超越议礼之争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这对明代后期及清代学者评价嘉靖初年礼议之争中不同官员的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直接彰显了明代中期政治演变时“小人”的政治文化。
嘉靖朝祀典改制中“小人”的政治文化
以奔竞钻营为特征的小人现象在嘉靖初年的祀典改制中十分突出,这在明代的其他时期都是少见的,它不仅引发了嘉靖初年祀典改制不断越制地演进,并进而成为当时政局演变的间接推手,在世宗强化皇权、影响仕风等方面都有着特殊的作用。与学术界经常关注的世宗皇帝、议礼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不同,小人现象的政治文化内涵实在不能忽视。
明清两代的学者对整个祀典改制中赞礼者的评价,是小人政治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对赞礼者的评价中,尽管对张璁、桂萼等人持批评意见者居多,但他们大多能将张璁、桂萼与何渊、聂能迁、随全、丰坊等人在议礼中的表现分开来看,少有将他们一并地视同为奔竞小人。嘉靖后期的范守己有论:“夫人谀势而佞权,恒情也,于是时秉臣执国是矣,矻然不移,而璁以孤议独衡其间,言出而抨抶随之,力孰与秉臣兢也。顾么么如渊、浚者,俱从而比其说,岂真是所在执与权莫之能勉耶?”[13]卷1,10沈德符也有言:“若锦衣之聂能迁、寺丞之何渊,初以附永嘉得进,后睹其暴贵,又劾永嘉以自为地,此皆诸公所引为同志者,至此得不汗颜浃背乎?至其后也,则丰坊者起而疏请宗睿皇入太庙,天下皆恨其谄,使张、桂而在,亦必谏止。然则何渊之世室未可尽非,而即帝即考之后,事体愈重,上意已定,即百张、桂安能救正也。贵溪之分祀四郊与亲蚕诸改创,皆本之永嘉,而更成水火,永嘉虽甚恨而屡攻之,终无如之何。最后则孝烈皇后之先俯太庙,并徐华亭亦不敢诤,乃知典制一越,侵寻日深。此实永嘉辈为之俑,至于末流,不复可障遏矣。”[8]卷25《弇州评议礼》,628-629清人之论,可能是隔代之后无所顾忌,对张、桂等持恶语批评者多,遑论何渊、丰坊辈。如王士禛言:“张孚敬、桂萼因得乘间抵隙逢迎,以售其说,而躐取大位。然杨文忠以下凡得罪者,其心不忍负孝宗,皆君子也。张、桂、方献夫、霍韬之徒,侥幸干进,志在逢迎,皆小人也。曩史馆开局时,诸人尚有纷纭之论。”[14]卷2《宋濮议与明大礼议》,39
平心而论,确不可将张、桂之徒与渊、坊之辈等而视之。清人赵翼言:“世徒以考兴献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立论之是非,折衷于至当,此岂得为笃论乎?”[9]卷14《大礼之议》,239-240在帝制时代,为忠难为奸更难。在嘉靖大礼议中,杨廷和可以“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与世宗对抗,附和者不得其志时,也可以以多种方式示忠,甚至冒死于左顺门哭谏,铁骨铮铮的忠臣在争礼中显而易见,这也是后世史家津津乐道的原因。殊不知,张璁等人面对的境况更加险恶,要面对举朝一致且掌控朝政的考孝宗派的反对、讥讽、打击、报复,甚而贬官、打杀的危险,如果说他们在此境况下还是抱着干进之心的话,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谈迁言:“永嘉议礼,能以辨博济其说,即论星历,亦援据不穷。其见知于上,非偶然也。”[15]卷53嘉靖六年十月乙巳,3364虽然谈迁没有进一步说明“非偶然”是什么样的原因,但冒死而干进是不太可能的。而清人梁章钜则更坦言道:“永嘉之议大礼,出所真见,非以阿世,其遭际之盛,亦非所逆料。”[16]卷5《张文忠公》,325可正是张璁在遭际世宗赏识超擢之后,何渊提出立世室、列祀太庙之时,张璁连上数疏,坚决反对,斥其为小人,并指出“典礼方成,不可遽坏,公论方定,不可复摇”。[10]卷2《庙议第二》,45假设张璁为干进小人,他又何必在何渊提出立世室、列太庙时不顺水推舟呢?何必此时逆世宗之意?相反,在整个祀典改制中,诸小人的各种越制提法不断地出炉,在目的上哪一个是为了真正地争礼?哪一个不是为了升职或为了免于降职等眼前的利益?诚如余珊所说:“自大礼议起,凡偶失圣意者,谴谪之,鞭笞之,流窜之,必一网尽焉而后已。由是小人窥伺,巧发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为主,顺之无不合,逆之无不怒。由是大臣顾望,小臣畏惧,上下乖戾,寖成暌孤,而泰交之风息矣。”[4]卷208《余珊传》,5498
嘉靖朝祀典改制中小人政治文化还表现在影响了仕风,造成了奔竞与献媚之风。小人们在祀典改制中的每一次献议,无不得到世宗皇帝的奖掖与提拔。何渊首请追献皇帝尊号、立世室之议时为国子监生,因议礼而除陕西平凉县主簿,后因屡受上官榜笞,再上列献皇帝于太庙之议,世宗破格迁其为光禄寺署丞。聂能迁,武宗末年附钱宁冒功得官,累官锦衣千户,世宗即位后汰为百户,“后附璁、萼议大礼,且交关中贵崔文,得复故职”。[4]卷197《黄绾传》,5219锦衣卫革职百户随全、光禄寺革职录事钱子勋以“张、桂辈以议礼骤贵重”,创为迁奉献皇之说,并陈乞升职,于是聂能迁、致仕带俸南宁伯毛良、致仕教授王价亦假议礼希复求用,世宗以“诸臣各建议效劳,(毛)良如部拟,(聂)能迁升副千户管事,(陈)纪、(随)全各加一级,(王)价以京职叙用,(钱)子勋复原职致仕”。[6]卷70嘉靖五年十一月乙巳,1595嘉靖四年(1525年),《大礼集议》书成,席书奏请奖掖参议熊浃、侍郎胡世宁、先任给事中陈洸等16人。[8]《补遗》卷2《考察官议礼不纳》,855《明伦大典》颁定以后,礼部尚书方献夫又以“襄府枣阳王祐楒、楚府仪宾沈宝、代府长史李锡,前给事中史道、陈洸,郎中黄宗明、同知马时中、百户随全、陈纪,巡检房浚,皆尝建议。郎中毕廷拱、经历金述、生员秦镗、儒士张少连、叶幼学皆尝发明,并及先大学士席书子尚宝司丞席中,俱应颁赐。上从之”。[6]卷96嘉靖七年十二月壬申,2235如前文所及,这些奔竞小人之奏请,并非如同张、桂等人之议,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迁升,且那些反对他们提议的官员无不受到世宗的打击,轻则夺俸,重则夺职,甚或治罪下狱。这种顺昌逆亡的情实,尽管对忠正之臣影响甚微,但对大多数的官员来说,争先献媚带来的好处却是显见易得的。这就是嘉靖初年即形成的献媚之风。
对于此股献媚之风,时人多有批评。都御史王廷相言:“古之君子难进易退,宁自守以俟时,无宁毁道以求进,故足以康济世务,风励时俗也。今士风与此殊异,一登仕宦之途,即存侥幸之念,谄谀贿赂,无所不为。遇一官缺,必有数人竞争,于是京师有讲抢攘之谣,而廉耻埽地矣。夫恬静,君子也;奔竞,小人也。奔竞进则恬静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无君子矣。其为世道不祥,莫大焉。”[17]卷17,312“嘉靖大礼之议,自张、桂倡之,至称宗,至入庙配上帝。以至奉迁显陵,下至厨役王福、随全等贱隶,亦尤而效之。然士君子无一人以为可者……奈何阿谄成风,即一时号为正人,亦献谀希宠,有中人所不为者。……士风披靡,即贤者不免,谓非张、桂作俑不可。”[8]《补遗》卷3《名臣一事之失》,891-892奈何祀典改制中形成的献媚之风并没有随着祀典改制的结束而结束,此后世宗好修玄崇道,一时“群小托名方技希宠,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俱以炼药贵显,而隆禧又自进太极衣为上所眷宠,乃房中术也。原任吏部主事史际建醮祝圣寿,进尚宝少卿;尚书赵文华进百花仙酒……其大臣献瑞者,巡抚都御史汪鋐首献甘露,继之则督抚吴山、李遂、胡宗宪辈,进白鹊、白兔、白鹿、白龟等,尤不可胜纪。……当时谄风滔天,不甚以为怪也”。[8]卷21《士人无赖》,541不能不说,嘉靖朝的媚风之盛,与大礼议中诸小人的奔竞献媚不无关联。
祀典改制中小人政治文化隐性的表现在于对嘉靖初年政治与政局的影响。关于大礼议的政治影响,学术界已多有论述,不再赘述,在此只就小人奔竞的影响略作铺陈。首先是世宗在祀典改制中皇权的意识得到了强化。尽管张璁等人在大礼议中对世宗的支持成为世宗强化皇权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但何渊、丰坊、随全等奔竞小人在祀典改制中不断地提出超越当时礼制的要求,既不断地刺激世宗为其父争礼的欲望,也渐次成为世宗提升其皇权意识的机会。因为诸小人的每个议礼要求,无不遭到举朝一致的反对,像入祠太庙礼,甚至张璁、席书等议礼新贵也极力反对,但世宗不为所动,除迁陵之议世宗没有采纳外,诸小人之议都为世宗所采纳并落实。也正是这一次次的争礼及实现,世宗的皇权意识在力排众议中不断地得到强化。其次是世宗借助小人的奔竞打击了异己、构建了亲己力量。在祀典改制中,小人们每一次议礼要求的提出,都有朝臣们的强力反对,世宗都是通过强力打压的手段使反对者屈服,甚至借小人之手屡兴大狱,如陈洸案、李福达案等,因此《明史》言其“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4]卷18《世宗本纪》,250世宗正是利用这些奔竞小人之手,实现了对武宗朝旧臣杨廷和等的全面清洗,实现了对附和杨廷和等议礼派的分化瓦解,实现了对科道官的钳制,实现了对翰林官的改组。在打击异己力量的同时,世宗也顺利实现了对内阁及重要朝官新陈代谢的绝对掌控。晚明人杨鹤云:“肃皇帝由藩服入继大统,此君之变局也。公(张璁——引者注)以一书生抵掌而取相印若寄,又相之变局也。君臣之变局,则朝局自不觉与之俱变。”[10]《杨鹤序》,9杨鹤将嘉靖初年政治及政局的演变归结于张璁一人,没有考虑到诸奔竞小人之影响,又是否是中允之论呢?
注释:
①关于学界对大礼议中诸小人的研究,只有胡吉勋在其《“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零星提及,但胡氏只将研究内容限定在嘉靖七年前后,对大礼议后续的祀典改制中诸小人的推波助澜很少涉及。另,氏著《从陈洸案看明世宗对文官系统之渗透与操控》一文对陈洸的小人行径有所涉及,但文章也不是立足于对小人行径及其政治影响而展开的。
②对学术界在以往研究“大礼议”中将议礼两派视同君子小人之辩的观点进行猛烈批评的田澍先生认为,不可将在“大礼议”中坚定支持世宗的张璁、桂萼等一概视为小人并加以批判。详见氏著系列文章:《大礼议与嘉靖朝的人事更迭》(《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3期)、《杨廷和与大礼议——中国历史上人事成功更迭的典型案例》(《学习与探索》2011年5期)、《断裂与重塑:大礼议的政治功能》(《明代国家与社会学术研究会会议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12年6月)。笔者以为,田澍先生的这种批判具有建设性,对以后的相关研究也有一定的指导性。但应将张璁、桂萼与其他的诸小人分而视之。
标签:嘉靖论文; 杨廷和论文; 明朝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大礼议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北京太庙论文; 历史论文; 张璁论文; 安陆论文; 专门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