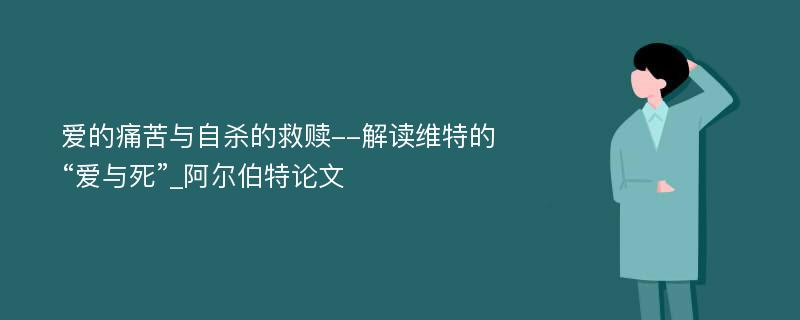
爱的受难与自杀的救赎——关于维特爱与死的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与论文,维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再一次看完《少年维特的烦恼》,〔1 〕纠缠住我的一个问题是:维特为什么非要自杀不可?难道仅仅是因为无望得到他所深爱的绿蒂?还是另有更实质性的原因?
或许以下的三点值得注意:
1.维特在自杀前已确信了绿蒂对他的爱;
2.维特在其信中(尤其是最后两个月的信)透露出一种阴郁而持久的自杀意绪;
3.维特深切地体验到了世界的虚幻与生存的虚无。
这三点为我们探究发生在维特之精神领域深处的变故提供了启示和线索。无论如何,自杀总是个内在性事件(用维特自己的话说是一种“精神性死症”),只有当人内在的纯然性、完满性遭致破坏、裂变,以至再没有其他有效的方法使之恢复、整合时,自杀的发生才有可能。本文针对上述3个问题,所探研的是:
1.爱之意念在维特的心中发生了怎样的裂变;
2.自杀意向是如何促成了维特的死以及在该意向中呈现出怎样的死亡景观;
3.虚无和虚无感在维特的爱与死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二
五月,维特进入瓦尔海姆。在此,“进入”伸展为一个过程。它既是告别、出走(过去),又是接纳、构造(将来),而在两者之间,是一片朦胧、飘渺的虚无。
维特的过去交织着纷扰和诡诈,痛苦和寒栗,它们在他的心中投下了道道阴影。但瓦尔海姆抚慰了他。这是个“乐园一般的地方”,草木中闪耀着造物主的精神,空气里流溢着博爱天父的嘘息。岑寂的美景正好是医治他这颗心的灵丹妙药。一种奇妙的欢愉充塞了他的整个灵魂。维特情不自禁地写道:“我真幸福啊,朋友,我完全沉湎在对宁静生活的感受中……”〔2〕维特在其中读荷马的诗,作他的画, 古代宗法社会的情景宛如再现在眼前,天使的精灵在他周围飞舞……
诗和画构筑起了一个审美的世界,这里没有痛苦纷扰,没有欲念追求,令人恬然忘忧,浮生若梦。
然而,这个审美的世界坚实牢靠吗?它真的能给人一个忘忧的梦乡而使人恒居其中吗?
其实,这个审美世界只是一种感性主观的虚构。它是眼睛的织物,感觉的幻相,它“更多地依靠预感与朦胧的渴望,而不依靠创造与活力”。〔3〕
“一切对于我的感官都是游移不定的;我也如在梦里似的,继续对着世界微笑。”〔4〕
因而,这个感性主观虚构的世界注定是短暂的、虚幻的。它没有根基,不能给人提供安身立命的道德基石和价值屋宇,也不能提供相濡以沫的血肉慰藉和情爱依托。在杳渺虚无的空气中飘忽的只是些闪烁游移的诗的断片,画的幻彩。在这里,连上帝、圣灵等神圣神秘形象也失去了其神意蕴含,而幻化为一种可观可感、怡情悦性的审美意象。上帝一旦被审美化也即被虚无化,终将沦为幻像。
或许,审美世界的最大价值在于肯定个体感性生命的存在,达到一种适性得意、恬然忘忧的逍遥境界。
这确是一个虚无审美化的过程。它虽充溢着无限的可能性,但也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性。主观构想的审美世界随时可能幻灭、碎落,人由此坠入深渊,被虚无感吞噬;或者他不得不构架另一价值的形式来代替审美形式,而这同样可能面临着被神圣化或被虚无化的危险。
三
维特的爱证实了这一点。
爱从虚无的深渊悄然崛起,把无限的可能性凝为一个观念的铁球与维特的头脑相撞,审美的世界砉然碎落。
爱情的伟力在于,它既具有审美形式的感官愉悦、激情浪漫,又具有审美形式所不具的相磨相厮的血肉慰籍和情感交汇。同时,它更赋予生命和世界以意义和价值。缺乏爱的世界是空虚的。在维特心中,爱被推崇备至,它超越一切,至善至美,神圣纯洁,自由无碍。这种对爱之完满性的确信无疑也支配了维特的爱情实践。
维特在见到绿蒂前,就已经知道她已“许了人”。然而,与绿蒂相会后他还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从6月19日到7月26日的信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维特迷醉于爱情中的狂喜之情。按他的观念来讲,爱情犹如艺术,无拘无束,自由不羁,应冲破一切束缚。于是,绿蒂已订婚这一事实就被不加考虑地悬置起来。
然而,阿尔伯特回来了,理想与现实、爱情与道德第一次发生了碰撞。维特立刻被击倒了。他发现,爱情并不能超越现实,爱情就是现实!而在现实中,阿尔伯特是绿蒂的未婚夫,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
维特和阿尔伯特之间爆发的一场争论,更使两人的分歧增大。在这场争论中,阿尔伯特强烈地谴责了自杀者的怯懦、愚蠢、罪过,而维特则毫不迟疑地为之辩护。他举了一个为爱而死的少女的例子,她的投入、忘我、以身殉情深深地感染了他,他为之颤栗、同情、甚而赞美。但阿尔伯特却视之为酒醉、发疯、眼光狭隘。维特所衷心向往的爱情景观在阿尔伯特眼中竟然毫无意义,反而是一种被嘲弄、被诟病的行为。神圣遭人诽谤,至爱受人贬斥,爱情骤然失重,维特只能发出无奈的感慨:
“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真难于相互理解啊。”〔5〕
更糟糕的是,现实中,他自身的爱情经历却证明了阿尔伯特的合理性!受制于道德、伦理、舆论、法律等等的爱,注定是不能自由、不能超越的——维特永远也不可能与绿蒂结合!爱情在取代审美的同时,道德的谱系也随之而来,维特根本不考虑这种现实,所以他被抛入了一个纠缠着情欲和伦理的漩涡中。他第一次窥见了生命的卑渺和存在的无根。
他不得不离开瓦尔海姆。
维特的出走,是其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碰撞的结果。现实世界之所以看起来现实,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最大众化或最理性化的观念,某一种观念如果与之不合,就要被现实世界排斥出去,游离于外,自成为一个世界。正是对这个非现实化的观念世界的过分信任,使维特与现实世界之间出现了冲突和裂变。维特的出走,既是对他的观念世界的据守,也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让步,其中当然也包含着想调和这种冲突的企图与尝试。
结果自然是令人失望的,在一家公使馆里工作,维特目睹的只是形形色色的丑剧:诽谤、算计、斤斤计较、追慕虚荣等等,这一切都与维特的性情格格不入。最后,在一个贵族男女的聚会上,他触了“霉头”,受尽奚落与难堪。一切的努力和希翼均告破灭,他不得不返回瓦尔海姆。
“如今,我从广大的世界上归来,我的朋友啊,可希望已一个个破灭,理想也尽皆消亡!”〔6〕
可能性消失了。
虚无的气息从缺了口的意识地平线悄悄涌起,在不设防的心灵中渗透、弥漫。
那么,维特所据持的观念世界呢?他所信守的爱情景观呢?它们还构成维特的信仰根基和价值向度吗?还有他对绿蒂的爱感意向呢?
爱之理念在现实中的受挫,并不一定表明它的虚幻性,也可能反照出现实的缺陷与不合理。维特认定的是哪一种呢?
四
当维特在爱的迷谷里徘徊低索时,有两位青年,他们的残酷经历对维特的心灵产生了剧变性的震荡。
青年一:一位因爱而发疯的“幸福的不幸者”。〔7 〕本是绿蒂之父的秘书,因恋慕绿蒂而丢了差事,最后发疯。在一个冬日的中午,维特在峡谷深处遇见他。他正在荒凉的岩石间寻找野花,说要送给他的“心上人”。
青年二:一位长工,他爱上了他的女东家——一位寡妇,求之不得被解雇。他在愤懑难抑的心情下杀死了寡妇后来雇的长工,被判死罪。维特竭力救助而不得。
这两个人的遭遇撕破了爱的神圣面纱,使维特直面爱的残暴和恐怖。
爱情难道不是神圣纯洁的吗?追求爱情不是要打破一切清规约束吗?为爱而做的一切不都是合情合理的吗?维特向来肯定并激赏这些。然而,突然间他却看到了由这种思想所导出的一个令人愕然的结果:发疯或凶杀!这无论如何是个悖谬!爱情本该是幸福的,然而只有发疯后才能得到幸福(维特之问:“天堂里的上帝,难道你注定人的命运就是如此:他只有在具有理智以前,或者重新丧失理智以后,才能是幸福的么?”〔8〕);爱情本该是圣洁的, 然而它却绽出了邪恶的血花(编者评述:“爱情与忠诚这些人类最美好的情操,已经蜕变成暴力和仇杀。”〔9 〕)。这两位善良的青年曾经象信徒般虔敬地膜拜过他们的爱人,孜孜追求过他们的爱情,最后却不得不走向发疯或杀人!所有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可思议,然而却真真实实地发生了。
维特本能地感到,这两人和他有着天然的亲近、关切之情,他立刻就理解了他们。对“青年一”,他同情他,敬慕他,为之哀痛(而阿尔伯特却“无动于衷”);对青年二,“他觉得他太不幸了,相信他即使成为罪人也是无辜的。”“因而产生了无论如何要挽救那个人的强烈欲望”〔10〕。然而,阿尔伯特和法官却断然否定了他的辩护和请求。
问题就在这里,维特突然间觉得发疯和杀人都是可理解的,都是合理的,正如那个失恋少女的自杀一样,它们都是为了爱——一种神圣的价值追求!
导致这种理解的原因在于,他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复杂的心理冲突:一方面,他竭力表白爱(特别是他对绿蒂的爱)的圣洁性、纯一性;〔11〕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情欲冲动,想以某种暴力的手段占有绿蒂,甚至希望阿尔伯特死。〔12〕在临死前写给绿蒂的信中,维特写道:“呵,亲爱的,在我这破碎的心灵里,确曾隐隐约约出现过一个狂暴的想法——杀死你丈夫!——杀死你!——杀死我自己!”〔13〕
维特以理解自己的方式理解了那个青年长工,所以他才决定去为他作辩护。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他缺乏理智。当维特刚看到那被人抓获的青年长工时,他脱口而出的就是:“瞧你干的好事,不幸的人呵!”〔14〕这句话中,由谴责到同情、由道德(理智)到情感的语气转换非常明显,也非常快,它显示出维特之独具的思想构成之复杂,情感意蕴之强烈。所以他才要赶着去为那个青年长工作辩护。但是,“他一踏进房间,发现阿尔伯特也在场,情绪顿时就低落下来”。〔15〕在此,阿尔伯特实际代表了一种清醒而冷漠的社会理性(道德感)。这种理性告诉他:“杀人是有罪的,你不得作辩!”理智与情感的起伏轮换,显示出维特生存之两难,也预示了爱之信念在维特心中的颠覆:一种导致荒诞(发疯)和罪恶(杀人)的爱还具有神圣性吗?
维特为青年长工作辩,实际上是在为自己作辩,为他内心骚动不息的“邪恶”冲动作辩,为爱中蕴含的悖谬性(罪恶性)作辩。然而,法官和阿尔伯特断然否决了他的辩护和请求!而他,无疑也接受了这种否决。
当日,维特绝望地写道:“你没有救了,不幸的朋友!我明白,咱们都没有救了!”〔16〕
“维特为救那个不幸者所作的无望的努力,是一股行将熄灭的火苗儿的最后一次闪动;自此,他便更深地沉浸在痛苦与无为中。”〔17〕
神圣的爱导致不幸的结果:发疯、自杀或杀人,这是爱之受难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们不妨追问一下,这种爱的神圣性中难道没有虚假的成分?它是上帝的赐予还是人的虚设?
爱源于人本身的某种匮乏。对人而言,它永远是一种有所求的境界。两性之爱尤是如此。它既追求肉体上的合一,也寻求精神上的交汇,并体验由此带来的迷狂般的喜悦。它是一种如此强烈地寻求合一、独占的向往,以致不能谦让他人。“对相爱的人来说,只能是两者合为一体,两者以外的人对这美满和睦的世界来说只能是多余的。”〔18〕因而,这种爱是自私的,排他的,它在“本质上就含有罪过”,“就是嫉恨其竞争者”,“对自己的向往的所有阻碍者,它都报以强烈的敌意和忌妒”,〔19〕发展到极端,就导致情杀和为爱犯罪等悲剧。另一方面,这种从爱中喷薄出来的力量如果因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外泄,则要反激回去,戕害自身,产生发疯、自杀、爱的病态等悲剧。所以,有时候爱“比什么都更容易成为纷争的发端,罪过和灭亡的起因”。〔20〕
维特的悲剧在于,他把这种事实上包孕着恶的爱看得太神圣、太纯洁、太完美无缺,或者说,他自己构想了一种至善至美、至高无上的爱,并把它作为一种信仰本体,成为他所追求的唯一价值。最后,当爱的残酷性(发疯、杀人)在他眼前一一展现,爱的邪恶性(破坏、占有)在他心中交突冲撞时,他才感到了绝望。
对语言神圣性的过分执持和期待导致了虚无,对爱之信念的动摇、怀疑和否定,最终促成了维特的自杀。
五
维特自觉到了爱之理念的虚幻性,那么,现实是否就合理、完满呢?就算维特屈从于道德、法律的绳束,放弃对绿蒂的追求,阿尔伯特和绿蒂是否就能保持完美和谐的关系呢?
在旁人看来,这是确定无疑的。阿尔伯特稳重严肃,勤谨能干,而绿蒂则温柔善良,美丽可爱,两人正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的一双。但维特却并不如此看待。
维特承认,阿尔伯特是“一位十分善良,十分高尚的人”,〔21〕但又认为,他过于理性化常态化了:“任何常理都容许有例外。可是他却太四平八稳!一当觉得自己言辞过激、有失中庸或不够正确,他就会一个劲儿地对你进行修正、限定、补充和删除,弄得到头来什么意思也不剩。”〔22〕他决不走极端,爱恨有分寸,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而这一切,都是维特所反感的。
无疑,阿尔伯特是近代以来理性化的市民社会的忠实臣民,他一丝不苟地遵守、履行并守护着这个社会的法则、制度和秩序。对任何超出常规的行为,如发疯、自杀、杀人等,他一概深恶痛绝,因为那是一种反常,一种破坏。所以对“青年一”和“青年二”的不幸遭遇,他无动于衷,冷漠苛刻,与维特截然对立。
阿尔伯特和绿蒂的婚姻也是这个理性社会的合理产物。在市民社会式的法律中,在守护婚姻之爱的美名下,爱被固定下来,物化为家庭。它“既不是创造什么的力量,也不是为什么而奉献自己的力量,它变成了受到保护的游戏,失尽了其伟大之处。”〔23〕实际上,这种爱只是被看做“男女在家庭中乃至在家庭的映象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24〕如身份、地位、荣誉、财富等等。爱的温情被忘却了,爱的崇高形象消失了,爱实际上已随着双方的结婚而告结束了。
阿尔伯特自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他也不可能承认这一点。然而,绿蒂却终于意识到了。她了解丈夫对她的爱和忠诚,“也打心眼里倾慕他”;而且他对她和她的弟妹也是座“永远不可缺少的靠山”。〔25〕但是,另一方面,她也感到,正如维特所指出的:“他这人缺乏敏感”,“在读到一本好书的某个片断时,他的心不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当我们(维特和绿蒂——引者注)发表对另外某个人的感想时,情况同样如此。”因而,他的爱,他们的爱总缺少点什么,“他不是那个能满足她心中所有愿望的人。”〔26〕从这方面讲,维特之于她是如此可贵。“从相识的第一瞬间起,他俩就意气相投;后来,长时间的交往以及种种共同的经历,都在她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27〕她直觉到,她已经“离不开他”,而维特则更是离不开她,“维特没有了她,便没有了一切”。〔28〕
事实上,绿蒂处于一个更尴尬、更矛盾的处境,她所可能遭受的心灵痛苦和折磨绝不会比维特少。只是,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尴尬和矛盾还没有成为一种明晰的意识,最多只是一种朦胧的情绪,所以,绿蒂处理得较为轻松。但是当后来,她面临着非此即彼的两难抉择时,这种处境就骤然成为一个问题尖锐地凸现于她的面前。问题已是一种明晰的意识,而问题的独特性更在于它是一种意识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当意识出了某种差错时,问题才会出现。而问题一旦出现,就会持久地存在,并发生作用,直至问题最终被解决。对绿蒂而言,当问题呈现于她的意识中时,她和阿尔伯特的裂痕就不可避免。因为她看出了阿尔伯特的缺陷,看出了他们的婚姻的不完满,而且看出了她和维特之间更有着一种内在的共通性和吸引力。然而,她又不可能离开阿尔伯特,因为道德、伦理、制度等等的限制,也因为阿尔伯特是她和她的弟妹“永远不可缺少的靠山”。所以,她不可能、也不允许留住维特。维特只能去死。正是她亲手把自杀的手枪交给了维特的仆人。她已直觉到了死亡悲剧的不可避免性,但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维特去死而无力制止。当维特自杀的消息被证实后,她一下子陷入了生命的危机。这种突如其来的意识觉醒所带来的摧残性、毁灭性后果就在这里。可以想见,她和阿尔伯特的婚姻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阿尔伯特与绿蒂的婚姻是理性化的市民社会的一个典范。在这种社会里,一切都要按照既定制度的机能发挥作用。爱由此物化为家庭,男女在其中扮演既定的角色,完成既定的任务。丈夫被要求庄重严肃,勤奋多劳,挣钱养家;妻子被要求温柔贤淑,端守妇道,持家教子。一切都是被要求的,在被要求中构成一个一个固定的单位,在其固定的位置上发挥固定的功能。爱因此逐渐萎缩、死亡,这是爱之受难的另一种形式。
维特其实早就看出了阿尔伯特和绿蒂之间的情隙。尽管他承认阿尔伯特是个好人,也承认他专心一意地爱着绿蒂,“但这样的爱尽可以获得任何别的报偿啊!”〔29〕再后来,他更是确信,“阿尔伯特夫妇之间的和谐关系已遭破坏”,已变得“更加可虑、更加暧昧了”,为此,他“还暗暗地埋怨身为丈夫的阿尔伯特”。〔30〕
相比之下,维特和绿蒂之爱更具有中世纪骑士之爱延续下来的那种舍命以求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近代市民化的社会中,“处于婚姻状态的爱不是人本来的爱,于是才出现了浪漫主义,以把在这种制度中动辄便会失去的人类之爱所固有的冒险欲望幻化成梦,投射到婚外之爱上。”〔31〕然而,时代已经不是中世纪,在理性化、技术化的社会中,“超越已经确定框子的至爱之情只能是例外的事了。而对机器来说,例外就是故障,是脱轨。”〔32〕这种爱只能酿成悲剧:疯狂、自杀或杀人;或者“变成精神之花在梦幻的世界中继续开放”。〔33〕
维特已意识到了他与绿蒂之爱的虚幻性(非现实性),也意识到了他自己的爱的矛盾性(邪恶性),还意识到了阿尔伯特和绿蒂之爱的扭曲性(异化)。现实性与可能性,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这双重层面上的可能性都已幻灭。神圣者不再神圣,他所赖以栖身的观念世界轰然坍塌,而现实世界则距他更远。维特只有一条路可走:自杀!
然而,自杀不是复归于虚无,被虚无吞噬,与虚无同一吗?维特不是一直在逃避、抗拒虚无吗?
阿尔伯特们决不会理解维特的自杀,我们呢?
六
死亡的意向在维特面前伸展为一条长长的路。
在维特来到瓦尔海姆之前,他有一位最亲密的女友死了。他看着她的棺木放进墓坑,看着咚咚直响的“土块落在那可怕的匣子上”,“响声越来越沉闷,到最后墓坑整个给填了起来!这当儿我忍不住一下子扑到墓前……心痛欲裂,号啕悲恸,震惊恐惧到了极点;尽管如此,却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会出什么事……”。〔34〕
死亡的印象如此悲怖,维特怎么会选择死呢?
当维特与阿尔伯特争吵,竭力为自杀者辩护时,他饱含激情地描绘了那个自杀少女的绝望情景:“她四肢麻木,神智迷乱,站立在深渊边上;她周围一片漆黑,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安慰,没有了预感!……她看不见眼前的广大世界,看不见那许许多多可以弥补她这个损失的人;她感到自己在世上孤孤单单,无依无靠。被内心的可怕痛苦逼得走投无路了,她唯有闭起眼来往下一跳,以便在死神的怀抱里窒息掉所有的痛苦。”〔35〕
维特几乎以一种移情式的体验肯定了自杀的确然性。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自杀是一种迫不得已被动接受的解脱之道。
维特会甘心受迫于这种冷漠残酷的确然性吗?
必须指出,在此之前,死亡对于维特一直是个非切身的外在事件。死亡的巨幕向维特紧闭着,神秘、阴森、冷漠、可怖。
然而,随着爱的不可能性在现实和理念两个层面的相继展开,随着虚无感越来越深地浸渗、扩张,自杀的念头终于象闪电一样击中了他。黑暗的帷幕隐隐启动,自彼岸吹来的气息飕飕泛寒,一个朦胧幽昧的死亡景观若隐若现。但是,一道幽暗翻腾的激流横亘在眼前,泛着惨白的月光,裹着呼啸的狂风,滚滚冲向一个幽深莫测的深渊(见12月12日的信)。而在半张开的幕后,隐现的只是一片“我们一无所知的黑暗和混沌”。〔36〕
在这里,意识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死后的世界。尽管它还黑暗、混沌,但很快,它就会向维特敞开,向他许诺一片美丽的风景。
自杀之念频频闪耀。“维特终于和这个阴郁的念头一天天亲密起来,决心便更坚定、更不可改变了。”〔37〕“我要去死!——这并非绝望,这是信念”〔38〕!信念总是有所信的东西,正是在他的所信中,自杀的意义生成了:
自杀是一种赎罪。维特致阿尔伯特的遗信:“我对不起你,阿尔伯特,请原谅我吧。我破坏了你家庭的和睦,造成了你俩之间的猜忌。别了!我自愿结束这一切。呵,但愿我的死能带给你们幸福!”〔39〕
自杀是一种牺牲。维特致绿蒂的遗信:“绿蒂啊,只要能为你死,为你献身,我就是幸福的!……唉,人世间只有很少高尚的人肯为自己的亲眷抛洒热血,以自己的死在他们的友朋中鼓动起新的、百倍的生之勇气。”〔40〕
自杀是一种期待。“在即将进入坟墓之时,我心中更豁亮了。我们会,我们会再见的。”“呵,绿蒂!我要先去啦,去见我的天父,你的天父!我将向他诉说我的不幸,他定会安慰我,直至你到来;那时,我将奔向你,拥抱你,将当着无所不在的上帝的面,永远永远和你拥抱在一起。”〔41〕
而在这诸多显现的意义层下还蕴蓄着一种恐怕连维特自己也不愿承认而又确实存在的更原初的意向力:
自杀是一种谴责。它首先是针对绿蒂的。在维特的信中,他感谢她把手枪赐给他,提醒她记住他的不幸,把他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希望她常到他的坟茔上去……在这些哀婉凄厉的语句中蕴含的是一种强烈的谴责情感:她应对他的死负责!他是因她、为她而死的!而且,这种谴责力还指向更深、更远:它指向阿尔伯特、阿尔伯特所代表的道德、理性及婚姻制度等等。
现在,死亡的巨幕已完全揭开。来自彼岸的光耀亮了维特的路。险恶可怖的激流深渊消失了。维特怀着强烈的炽情走向了死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维特丧失或缺乏了理智。我们可从他表达的自然流畅,从他对往事的细致回忆,对后事的周密安排(甚至连一些细微之物,如一张剪影画,一个蝴蝶结也不疏忽)及对死后的期待执信中看出他的心很冷静。
“时候到了,绿蒂!我捏住这冰冷的、可怕的枪柄,心中毫无畏惧,恰似端起一个酒杯,从这杯中,我将把死亡的香醪痛饮!是你把它递给了我,我还有什么可犹豫。一切一切,我生活中的一切希望和梦想,都由此得到了满足!此刻,我就可以冷静地无动于衷地,去敲死亡的铁门了。”〔42〕
叶芝说,是人创造了死亡。在此,我不得不惊诧于人的意识构造能力之强悍之奇崛。在维特的意向活动中,死亡如此明晰地显现为一个由远趋近、由隐蔽至澄明、由可怖到亲密、由此岸向彼岸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死亡的意念不断地被复现,被叠加,被赋予意义、形象、光彩,直到构成一个确信无疑的意义景观。由此,死亡祛除了神秘的面纱,消散了恐怖的气氛,并最终战胜了虚无。死亡里萦绕着意义和真理的光环,充满着期待和允诺的喜悦。趋向死亡的自杀遂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自由选择。它是一种由此岸向彼岸的引渡,一种“向死而在”的救赎。
七
死亡竟然成为一种救赎,这难道不是荒谬透顶吗?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它只是发生在意识活动中的一种意向性努力的结果。而且,在这意向化的过程中,始终凸现着一种死亡与复活、必然与自由、遮蔽与去蔽的剧烈冲突与强硬张力,它所加诸个体身上的是一种远非个人所能承受却又非要个己加以承受的巨大痛苦和折磨。正是这一点显出了此种救赎的力度。正如死亡一样,救赎有着无可替代的个己属性。然而,问题是,这种个己属性能否向他人敞开,或者说,是否每一濒临死亡的个体都能构拟一种向死而在的救赎景观?如果不能,则所谓的救赎岂不又是一种虚妄?
当然,这已不是维特所“意向”的问题,也不是本文所想涵盖的内容。我只想指出一点,在维特殚精竭虑的意向性努力中,我们有幸看到了一种可能性的涌现,一种真理的发生过程。这才是维特的自杀所能给予我们的最有益的价值。
收稿日期:1997—09—11
注释:
〔1〕杨武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2〕〔3〕〔4〕〔5〕〔6〕〔7〕〔8〕〔9〕〔10〕〔13〕〔14〕〔15〕〔16〕〔17〕〔21〕〔22〕〔25〕〔26〕〔27〕〔28〕〔29〕〔30〕〔34〕〔35〕〔36〕〔37〕〔38〕〔39〕〔40〕〔42〕,同上,第3、9、9、51、78、100、99、106、107、117、107、107、108、109 、41、46、119、81、119、133、81、105、130、50—51、112、112、116、136、137—138、137页。
〔11〕见“7月29日”、“9月3日”、“12月14日”等信。
〔12〕见“8月21日”、“10月10日”、“10月30”等信。
〔18〕〔19〕〔20〕〔23〕〔24〕〔31〕〔32〕〔33〕分别见今道友信《关于爱》第49、49、48、81、81、83、81、83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41〕同〔1〕,第131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上帝的形象有了改变。它由一位审美化的上帝变成了一位禀有爱意,倾听哀告并能满足要求的神意上帝,即信仰中的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