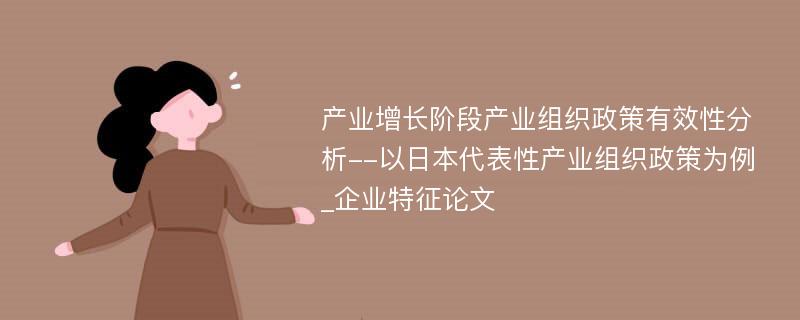
产业成长阶段的产业组织政策有效性分析——以日本代表性产业组织政策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论文,组织论文,政策论文,日本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8)04-0087-04
一、有关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及评价标准
在号称“产业政策大国”的日本,有关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从“产业政策”一词被提出后就没有停止过。极端的表现为“产业政策礼赞派”和“产业政策否定派”的存在。前者以美国政治学家Chalmers Johnson为代表,认为有效的产业政策是创造日本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后者则以Kent E.Calder和三轮芳朗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一些所谓成功的产业政策,不是来自于政策本身的成功,而是来自于包括政策对象产业和企业在内的民间经济主体的作用。[1]更多的学者,像小宫隆太郎等认为,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因每一项具体政策而异,也取决于很多条件。[2]青木昌彦等人还据此提出了“市场扩张见解”,认为产业政策只是一种协调手段,并不一定总是有效的。[3]
国内学者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很有限,大多是探讨产业政策为何会失效,如张许颖认为存在多个博弈主体的产业政策,在其运行中因为缺乏利益协调机制,政府行为有限性的约束等会发生失效的情况。[4]齐孝福认为,存在多重利益关系、政策实施机制不健全、企业主体缺乏应变和持续发展能力等问题是导致我国产业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
本文将产业组织政策成功的标准设定为其运行效果是否达到了政府制定该政策的初衷。如此设定的理由是因为政府作为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它评判一项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标准就是看政策是否按照其预想的方向发展。但因为政府并不总是恪守公共利益的理性主体,即便是成功的产业政策也并不总是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因此,将面临一个基于社会整体福利视角的理想的产业政策问题。
二、基于产业成长阶段的产业组织政策类型
产业成长一般会经历幼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而产业组织政策也存在两大类型,即竞争促进政策和促进规模经济政策。
1.幼稚产业的激励型和单纯型保护政策
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一般被看做是典型的产业结构政策,但实际上它也带有产业组织政策的某些特征,因为实行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往往会采取限制国外产品进口和直接投资的做法,这等于是切断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的竞争渠道,具有限制竞争色彩。同时,幼稚产业保护政策的实施一般都有特定期限,保护政策一旦撤销后,国内企业必须面对国外企业的竞争挑战。因此,增强产业和企业未来的竞争力应该是幼稚产业保护政策的根本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又带有促进竞争的特点。
在日本曾经大量实行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中,既有以保护促发展的激励型保护政策,如汽车业;也有以保护求保护的单纯型保护政策,如水泥业。从政府的角度看,该项保护政策显然没有达到其初衷,是失败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是具有促进竞争的激励性质,还是限制竞争的单纯保护性质,不是由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本身,而是由政策对象产业的产业组织特点决定的。像汽车业这种具有竞争型特征的产业,大多能够充分调动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中的竞争激励因素,与政府在一定期限内实行的保护措施相得益彰,并取得良好的政策效果。而像水泥制造业这种具有协调型特征的产业,企业则会利用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中的竞争限制因素,并以社会已经付出的高昂成本为博弈砝码,寻求政府事实上的无期限保护。如果以是否达到政府的政策初衷来判断政策成功与否,对具有竞争型特征的产业实行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很容易成功,而对具有垄断型特征的产业实行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则大多是失败的,但如果以是否达成了企业意愿来判断成功与否,则两类政策应该都是成功的。
2.成长性产业的市场功能促进型和市场功能抑制型政策
对成长性产业内的企业而言,不断增加的市场需求预期可以充分调动企业的扩张发展本能。因此,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成长性产业的基本特点。以成长性产业为对象的产业组织政策,如果具有促进竞争特征,就可以称之为市场功能促进型。反之,如果具有限制竞争特征,就称之为市场功能抑制型。如果针对成长性产业实行市场功能抑制型的政策,因为与企业之间相互激烈竞争的行为取向并不吻合,因此大多是失败的。如果针对成长性产业实施市场功能促进型的政策,如研发扶持等则大多是成功的,日本对半导体产业所实行的研究助成计划即是典型一例。
虽然这项政策表面上也是把产业内的主要企业划分成几个技术合作小组,政府对技术合作小组发放研发补助金,鼓励企业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创新研究,并且分享技术创新成果。这似乎与成长性产业内企业的竞争型行为取向不符,但因为技术合作研究可以提高每个企业的技术开发创新能力,增强每个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与国外企业竞争的能力,因此,这种政策从根本上还是市场功能促进型的,且与企业的发展意愿相吻合,所以大多能够成功。同样就政府而言,有成功有失败的针对成长性产业实行的产业组织政策,在企业看来,大多还是没有违背其自主意愿的。
3.成熟和衰退性产业的现状破坏型和现状维护型政策
对进入成熟和衰退期产业内的企业而言,未来可以预期的市场需求扩张很小或几乎没有。因此,保持当前的市场份额,维持或提高价格等扩大当前收益的行为是这一阶段的企业普遍愿意接受的,而可能带来更多变动和不确定性的竞争,对这时的企业已经不具有很大吸引力。据此,以成熟和衰退期的产业为对象的产业组织政策也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尽量限制和排除企业间协调合谋行为的反垄断政策,本文称之为现状破坏型产业组织政策;以及限制和削弱企业间的竞争程度,促进和维护企业间协调垄断行为的现状维护型政策,主要包括大型企业合并政策、卡特尔合法化政策等。对处于成熟和衰退期的产业而言,现状维护型的产业组织政策更符合企业的自主意愿,因此,大多能够成功。而现状破坏型的产业组织政策因为与企业的自主意愿相悖,往往很难顺利推行。
如果以政策作用结果是否达到了政府的初衷来判断政策是否成功的话,上述基于三个产业发展阶段的六类产业组织政策,恰恰是政策初衷与企业的自主取向与意愿相吻合的政策,即这些政策大多能够成功。反之,政策初衷与企业的自主取向相违背的,则大多难以推行或中途搁浅。这样的结果预示着产业组织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主导力量似乎来自于企业,而非政府。即便在所谓成功的产业组织政策中政府显示出很强的主导性,那也是企业判断政府的政策目标与自身的行为取向相符时采取的一种“示弱”姿态,一旦政策目标与企业的自主行为取向不符时,“软弱”的企业会变得异常强大,政策结果也就很难达到政府的政策初衷。
三、日本代表性产业组织政策的案例剖析
1.汽车产业的“集团化发展构想”惨遭失败
经过幼稚产业保护已经初具竞争力的日本汽车产业,在日本先后加入OECD和IMF后,开始直面国际竞争。这种情况下,1961年6月,通产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前身)发表《针对汽车产业的施策方针》,提出为了增强本国汽车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需要确立规模化生产体制,把国内八家企业改组为大批量车、特种车、微型车三大集团,这一计划遭到除丰田和日产外所有汽车企业的强烈反对,没能实施。然而这一结果并没有打消通产省重组汽车企业的念头,1963年3月,通产省向国会提交一份《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置法案》,指定在轿车、特殊钢、石油化学三个产业实行企业合并和生产专门化、集中化政策,并试图以国会立法的形式保证政策的有效推行,但该法案直至次年3月,三次提交审议均未获准通过,成为废案。[5]即便如此,通产省仍然执著于汽车产业的重组计划,但一些企业不顾通产省慎重对待与外资合作的劝告,1969年三菱重工与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1970年五十铃与GM达成合作意向,与此同时,国内企业间的合并合作趋势也明显加强,并形成了由日野、丰田、大发组成的丰田集团和由日产引擎、日产、富士重工组成的日产集团。然而,这两大企业集团并没有像通产省所设想的那样,不同集团生产的产品各有侧重,而是每个集团都拥有从大型拖拉机到轻型轿车的全系列产品,集团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最终通产省这一煞费苦心的汽车产业组织政策以失败而告终。该案例证明了对成长性产业内有强烈竞争取向的企业实行压抑竞争行为的产业组织政策,终会因遭到企业的猛烈反击而流于失败。
2.大型企业合并政策的成功产物——新日本制铁的成立
钢铁产业作为日本重化学工业的支柱产业,一直是政府产业政策的重点之一。20世纪50年代日本钢铁产业实施的限制新企业进入政策曾因民间企业的强烈反对而搁浅。但进入6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对直面国外企业竞争压力的钢铁产业又实行了一项以扩大企业规模和提高市场集中度为核心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并在1966年发表的《关于今后钢铁产业的方向(中间报告)》中,明确表明希望通过大型企业的合并联合,避免“过度竞争”对产业竞争力的危害,确立企业间关于设备、价格等的自主调整体制。[6]1968年5月充分领会了通产省政策意图的两大钢铁企业,八藩制铁和富士制铁联合发表《合作意向书》,8月通产省明确对两家企业的合并意向表示支持。虽然公平取引(交易)委员会因为担心两大寡头企业的合并可能引发垄断而持反对态度,以及经济学家们关于合并可能使市场竞争效率遭受损失并扭曲资源分配的讨论,使合并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但还是没能阻止两大企业的合并步伐。1970年3月,由八藩制铁和富士制铁合并而成的新日铁宣告诞生。从此,新日铁不仅成为日本钢铁产业的巨头企业,而且一跃成为世界钢铁产业的第二大企业,这似乎达成了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初衷。但实际上,经济学者通过计量分析得出,新日铁成立后的1971-1975年间,抑制设备投资的效果虽有所显现,但并不明显,反而在价格方面,合并在提高钢铁产品国内价格的同时,出口价格得以下降。[7]
八藩制铁和富士制铁之所以能够冲破重重社会压力而成功合并,除了通产省等经济官僚机构的极力推进外,产业内其他寡头企业的默认也是原因之一。合并后成立的新日铁,理所当然的成为产业内的领导型企业,其他寡头企业在维护新日铁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彼此之间的竞争色彩也日渐稀薄,直至钢铁产业在70年代逐渐走向一个卡特尔组织,这与产业进入成熟期后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取向高度吻合。由此可见,企业在产业组织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主导力量非常强大。
四、产业组织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关系的理想模式
如果以是否有利于促进竞争来评判基于产业不同成长阶段的产业组织政策,那么幼稚产业的激励型保护政策、成长性产业的市场功能促进型政策,以及成熟和衰退产业的现状破坏型政策是值得采取的。
从日本的实践看,前两种类型的产业组织政策,因为政策目标与企业的竞争偏好型发展取向相吻合,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形成力量同方向的作用机制,即便是事实上的企业主导型,表面上看也是产业政策的成功,这时政府和企业关系的理想模式很容易确定,即政府和企业齐心协力,共同推进产业政策朝向既定目标。但对成熟和衰退产业实行的现状破坏型产业组织政策,因为与企业的自主行为取向不相符,即企业更希望获得垄断的特权,而产业组织政策目标却是促进竞争,政府和企业的目标相左,这时如果还是企业占据主导权,会使政策很难达到政府的预期目标。但从促进竞争、增进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又需要这样的政策作指导,这时就需要政府表现出“强势”,抑制产业和企业的反竞争本能,同样对具有垄断和协调特点的幼稚产业实行保护政策时,也需要政府表现出“强悍”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竞争增进社会福利。
同理,对成长性产业实行的市场功能抑制型政策,因为既与企业的自主发展意愿相违背,又具有反竞争的特点,不仅会遭到企业的极力反抗,而且会引发社会舆论的不满,即便付出巨大政策成本,从政府角度看也大多以失败收场。不过这种政府角度所言的失败恰恰可能是效率与社会福利角度所言的成功。因此明智的政府应该抛弃试图对成长性产业实行市场功能抑制型政策的企图,让市场功能和企业的自主取向发挥根本性作用。对成熟和衰退产业实行的现状维护型政策情况又不同,虽然因为政策目标与企业的自主意愿相吻合,很容易达成政策目标。但因为政策自身所带有的反竞争特点,这种对政府和企业而言的成功,从增进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却是失败的。因此,恪守公共利益的政府,同样不应沉迷于这类政策所谓的成功。
概括而言,在产业组织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关系的一种理想模式应该是,当产业处于幼稚期和成长期时,只要市场组织结构不具有协调型寡头垄断的特点,就应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必要时辅以一定的推进措施,如研发扶持、信息提供等。而对进入成熟或衰退期的产业,以及即使处于幼稚期和成长期,但具有协调垄断型产业组织特征的产业,政府必须发挥强势主导作用,实行与企业自主意愿相违背的产业组织政策,在产业组织政策的类型选择和实施过程中,单一的政府主导型和单一的企业主导型都不是理想模式。[8]
五、对我国制定产业组织政策的几点启示
近年来对产业政策的某些反思性研究对我国慎重、合理运用产业政策提出了警示。但对待产业政策在谨慎的同时也不能因噎废食,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合理运用产业组织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1.准确判断某一产业所处的成长阶段及产业组织特征是政策制定的前提
虽然对我国产业组织政策的实证研究并不像日本那么透彻,但一些产业发展现象表明,企业的自主力量十分强大,在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同博弈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还很严重,因此才会出现“小钢铁”、“小煤窑”的屡禁不止和一直提倡走集团化之路的汽车产业类竞争主体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的现象。既然处于不同成长阶段或具有不同产业组织特征的产业内企业的自主发展意愿是不同的,政府制定产业组织政策时首先就要准确判断该产业所处的成长阶段和产业组织特征,然后再进一步判断产业内企业的自主发展意愿是否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如果是,只需采取一些顺应性的政策,或是无为而治;如果不是,就需要政府采取政策对企业的自主发展意愿予以纠正,并以相应的制度设计保证实施,而不是为企业的自主力量所左右或陷入政企勾结的境地。
2.从产业链整体而非产业链的终端状态出发制定产业组织政策
现代产业所呈现的链式发展特点决定了产业之间的竞争是产业链与产业链之间的竞争,而非仅仅是产业链终端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往我国制定产业组织政策时往往只关注产业链终端的状态,所以认为很多产业都存在“散”、“乱”、“小”等问题,增强规模经济也就成为我国产业组织政策的一个主题词。在提高规模经济这一政策导向的笼罩下,我国的中小企业政策相当滞后,使得作为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基础的中小企业在我国总体上缺乏竞争力,也使我国的产业链基础相当脆弱。可以设想,如果我国的汽车组装企业形成了三大集团的发展格局,但零部件大部分依靠进口或国外企业在我国的合资及独资企业生产,那么该产业的发展基础依然薄弱,从增进社会福利的角度看,政策效果也不会理想。因此,从产业链整体着眼判断竞争是充分还是不足,以及在哪些环节要促进规模经济,在哪些环节要促进竞争,据此来制定分层次的产业组织政策是必要的。
3.充分运用间接政策手段实现产业组织政策目标
目前,运用产业政策手段的总体趋向是直接干预手段渐趋弱化,间接诱导手段逐渐增强,除了反垄断政策会运用阻止兼并、拆分等直接手段外,其他大量运用的是间接手段。我国以往实行产业组织政策时,更习惯于运用直接手段,如“拉郎配”式的兼并重组,因为缺乏企业间自主意愿的现实基础,要么不了了之,要么流于形式。如何通过诱导性的间接手段,让政策目标与企业的自主意愿相契合,并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是对政府运用产业组织政策能力的一种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