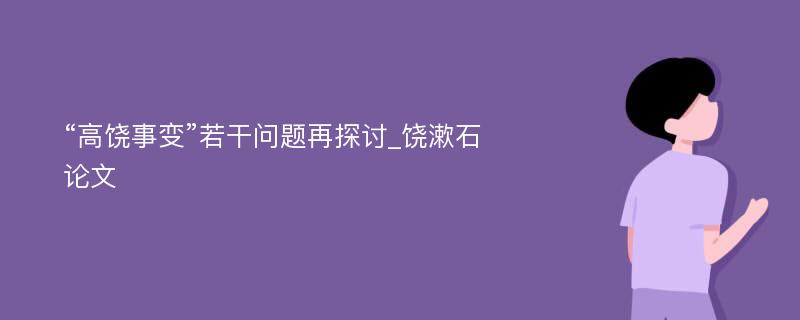
关于“高饶事件”几个问题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发表的《对“高饶事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简称《考察》)一文,分析了“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论述了“东北一党员”的来信与“高饶事件”的关系,考证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识破和揭露高、饶分裂党的阴谋的时间,为全面、准确地认识“高饶事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和观点。
不过,我们认为,《考察》一文关于“高饶事件”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和党对这一事件的认识起点和揭露时限的认定,尚不够充分和准确,有进一步分析和考证的必要。故提出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以期促进对“高饶事件”研究的深入。
一、分析“高饶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应忽略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体制性因素
《考察》一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共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从根本上说,是高、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极度膨胀的恶果。”“第二,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人事安排,要进行大的调整和变动,高、饶视其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可乘之机。”“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初,在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问题上,党内存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这本来是正常的,但高岗、饶漱石利用这些分歧,大做文章,推波助澜,乘机实施其阴谋活动。”(注:见《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44~45页。)
“高饶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所发生的第一场党内斗争,这场重大的党内斗争之所以发生在建国初期,确实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考察》一文中虽然分析了三个方面,但这三个方面的立足点主要是一个,即高岗、饶漱石的个人主观因素。然而,高岗、饶漱石的个人错误固然是“高饶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但高岗之所以能够“把东北地区看作不受中央领导的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而且又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以后,自称是组织了‘经济内阁’,同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相对抗”(注:“高饶事件”出现后所揭发的高岗“十大罪状”中的两条,见《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1954年2月)。),并非是仅仅靠其主观的意愿就能够达到的,而是与建国初期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密切相关。
其一,过渡形态的大区行政建制与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易于助长“独立王国”的倾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的。按照当时的临时宪章——《共同纲领》的规定,新中国是一个由若干行政区域组成的单一主权国家,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适当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地方行政建制有大行政区、省、县、区、乡五级或大行政区、省、县、乡四级。大区行政建制则有1948年8月成立的东北人民政府和华北人民政府,1949年12月成立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政委员会。
从六大行政区成立的时间和名称即可看出,大区行政建制并非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统一实行的一级地方行政建制,而是延续了革命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政权体制。东北人民政府和华北人民政府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是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其他四个大区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但它们的前身也都是解放战争时期所属解放区的最高行政单位。因此,大区行政建制虽然是地方行政建制中的最高一级,但实际上具有过渡形态的性质。它的实行与中国革命所走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特殊道路有关,但这并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与地方的理想行政架构。它带有浓厚的战争年代色彩,既是权力机关又是行政机关,而且既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又是地方一级政府。所以,它不但实行地方政权的职能,而且还以中央政府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使所辖地区易于成为独立性较强的“国中之国”。而且,上述大区行政首脑的权力还只是当时所实行的党政军三位一体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部分。
高岗是在1949年8月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在此之前,高岗已于1949年3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局书记。在此之后,高岗又于1949年11月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这样,高岗就集东北地区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了。
其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两级制”及由此带来的政务院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平级的行政架构,是“经济内阁”出现的体制性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行政管理实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其下辖的政务院两级制政府体制。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与《共同纲领》同一天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作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政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以及各部的部长、副部长等,都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
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中央人民政府暂行国家最高权力,国家行政管理暂行中央两级制政府体制这种特殊的权力结构,是由当时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但是,这种特殊的权力配置状况与当时执掌权力的具体人员交织在一起,就出现了上下级关系不清、部门职责重叠的复杂状况。高岗当时不但集东北地区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因此,当他于1952年10月奉调进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时,由国家副主席高岗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周恩来担任总理的政务院是一种什么关系就成了一个很难摆子的问题。
按照1952年11月15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的决定,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责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编制国家长期和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也就是说,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不归政务院领导,它实际上是同政务院平起平坐的国家经济建设的最高执行机关,这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这次会议同时任命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主任,邓子恢、李富春、贾拓夫任副主席、副主任,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张玺、安志文、马洪、薛暮桥等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一章第五条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只组织国家最高政务执行机关政务院、国家最高军事统辖机关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国家最高审判及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及人民检查署,并没有组织国家经济建设最高执行机关的规定,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职责实际上是由政务院担任。政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等4个委员会和三十几个部、委、署、院,有关经济建设的部委都由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如果不是实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其下辖的政务院两级政府管理体制,而是政务院享有后来成立的国务院拥有的职权;如果高岗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而是同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等一样,只是各大区的负责人,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就非常有可能设在政务院内,不会成为与政务院平行的机构,所谓的“经济内阁”自然也就无法成立。
也正是因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不归政务院管辖,实际上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最高执行机关,才有了在“新税制”风波后的政务院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调整,才出现了政务院20个部中主管经济的8个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由此可见,虽然“高饶事件”起因复杂,但在大解放区基础上产生的大区行政建制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两级制”,为“高饶事件”的出现留下了体制上的空间。
二、“‘东北一党员’的来信是认识和揭露高、饶问题的起点”的论断,缺乏史实论证。也与此后高岗的被重用相矛盾
《考察》一文的第二部分是论述“东北一党员”的来信与“高饶事件”的关系。在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东北一党员”来信的经过和内容后提出:“从我们党认识和揭露高岗问题的全过程来看,‘东北一党员’的来信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引起了我们党对高岗问题的注意,是认识和揭露高、饶问题的起点。”“可以说它是我们党对高岗问题从开始关注到发现直至识破这一全过程的起点。”
“东北一党员”的来信在揭露高岗问题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据此就认为它是“认识和揭露高、饶问题的起点”则无法令人信服。“东北一党员”来信发生于1952年1月,而高岗是1952年10月奉调进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的。如果认为发生于1952年1月的“东北一党员”的来信是“认识和揭露高、饶问题的起点”,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发现了高、饶的问题后反而还要更加重用高、饶。
《考察》一文之所以把“东北一党员”的来信说成是“认识和揭露高、饶问题的起点”,主要依据有两个:一是“‘东北一党员’来信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北存在的问题,使毛泽东等人了解到了高岗及东北的另一面。”二是毛泽东在1953年8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就此事质问过高岗,而且在高、饶反党分裂阴谋被揭露后,“东北一党员”的来信曾经印发给在京的有关领导,成为揭露高岗问题的重要材料之一。但是,历史研究是不能“倒推”的,是不能把事件后的结果作为事件前的原因的。不能把“东北一党员”的来信在高、饶反党分裂阴谋被揭露后所发挥的作用与它提出时的作用混为一谈,也不能因为“东北一党员”来信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北存在的问题就夸大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
实际上,署名为“东北一党员”的信,是在“三反”运动中写出的,信的内容也主要是向毛主席反映东北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的情况,并非完全是针对高岗个人的。而党在建国初期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恰好是从东北地区的“三反”运动而逐步推向全国的。毛泽东虽然后来对高岗“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十分反感,但他当时对高岗在东北率先开展“三反”运动还是十分赞赏的。1951年11月1日,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11月20日,毛泽东亲自在中共中央转发这份报告上批示:“各中央局,并转发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军区,并转告中央和各部门首长,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十一月一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个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注:毛泽东在中央转发高岗三反斗争报告上的批语(1951年11月20日)。)12月13日,毛泽东就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致电各大区领导人时,再次肯定了东北局率先开展“三反”运动的功绩。电文中说:“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注:毛泽东在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报告上的批语(1951年12月13日)。)
在这种时刻,仅仅是一封署名反映东北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情况的信件,就能够成为党中央和毛泽东“认识和揭露高、饶问题的起点”吗?
实际上,党中央和毛泽东何时发现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是一个并不需要再重新阐述的问题,《考察》一文在论证另一个问题时也引用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
本文转述《考察》一文中的论述如下:
“毛泽东曾讲到:‘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其标志就是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对饶漱石的调查了解(找陈毅、谭震林等人了解饶的情况)、会上不点名地警告并建议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邓小平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也讲到,‘中央政治局在1954年2月上旬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这以前,即在1953年6月到12月期间,党中央书记处即已逐渐发现了高岗和饶漱石所进行的反党活动。”(注:见《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49页。)
既然在同一篇文章中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这段论述作为论证问题的论据,又把“东北一党员”的来信说成是“认识和揭露高、饶问题的起点”,是否存在逻辑上的不清呢?
三、弄清揭露高、饶分裂党的阴谋的时间是必要的,但“识破”与“揭露”高、饶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截然分开
《考察》一文的第三部分,是论述“高饶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是何时被识破和揭露的”。提出:“笔者认为,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识破了高、饶分裂党的阴谋,但此时还没有公开揭露。”“从发现到揭露经历了一个过程,不能把识破等同于揭露。”“高、饶问题被揭霹是在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
认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高饶事件”“从发现到揭露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就此事件而言,发现和揭露高、饶问题并没有截然分开。能说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点名地警告高岗搞地下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仅仅是发现而不是揭露吗?而且在这次会议之前的12月19日,陈云“受毛泽东委托,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注:《陈云年谱》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页。)。这难道不属于揭露而仅仅是发现吗?
实际上,高岗阴谋分裂党的活动,主要是在1953年6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进行和暴露的,毛泽东也主要是从此时“强烈地感觉到”的。1954年3月26日,毛泽东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谈话时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老觉得党内外有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就像一场大地震即将来临一样,觉察到这儿震动一下,那儿震动一下,但就是不知道震中在哪里。在去年的6、7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的会议上,这种感觉尤其明显。不久,在1953年7月到9月间,我强烈地感觉到党内存在两个中心,一个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但是另一个却隐而不现。震动开始变得越来越剧烈。12月24日在政治局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后之后,事情变得明晰起来。”(注:此件摘自尤金1954年3月31日的日记,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执行总主编沈志华教授提供。)
此外,《考察》一文在最后部分中的“几点思考”中提出:“高、饶问题暴露后,中央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
我们认为,这个断定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研究“高饶事件”的人都知道,1955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专门讲述了对于高岗、饶漱石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还是“无情斗争”的问题,明确指出:“在我们同错误作斗争的时候,必须分别清楚两种不同的情况,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那就是如同四中全会决议所说的,一种是‘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另一种是‘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高岗、饶漱石的活动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既然这个反党联盟已经有系统地进行分裂党、颠覆党中央的活动,已经暴露出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改造党和国家,而且他们的阴谋如果得逞,前途就是亡党亡国,既然如此,他们的错误性质还能算是党内的一般性质的错误吗?尤其像高岗那样,在党已经揭露了他的全部阴谋的时候,还公然采取与党对抗的自杀手段,当然就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最可耻的叛徒!”(注: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1955年3月21日)。)
标签:饶漱石论文; 高饶事件论文; 中央人民政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政务院论文;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 毛泽东论文; 高岗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