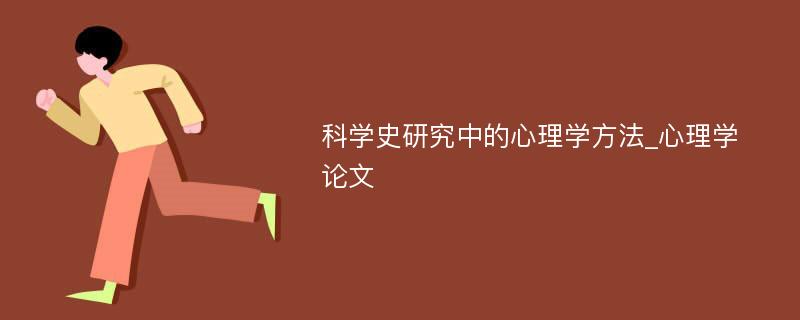
试论科学史研究中的心理学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心理学论文,史研究论文,科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学以过去的事件和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一般来说,这些人物即是所谓的“伟人”(great men)。在本世纪历史学的发展中,心理学理论被引入和应用于历史研究,形成了自6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学派。虽然各种不同的心理学理论对历史学均有渗入,但心理史学的主流却是精神分析学说与历史研究的结合。[1]在这些研究中,对“伟人”的传记研究又占了绝大多数,故又有“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或“精神分析传记”(psychoanalytic biography)之称。由于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泛性理论,注重童年的经历及无意识的重要作用,因而弗洛伊德将此工具用于历史研究时,无论研究方法还是得出的结果都与传统的史学研究大相径庭。
本文将结合科学史的研究,对有关问题作简要述评。至于精神分析理论本身,因国内已有较多的介绍与研究,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一
现代心理史学的创始人也正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而心理史学(或者说心理传记)的发轫之作,又恰恰是以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人物——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和科学家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为研究对象的。1910年春,弗洛伊德完成了他的这部著作其最初的英译本名为《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例性心理学的研究》,后来的译本更名为《列奥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2]对弗洛伊德本人来说,这一研究不仅是他第一次,而且也是他最后一次在传记领域中的长途跋涉。
达芬奇是一位极有特色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中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3]关于他的工作、生活和性格的许多方面,不权在现代人来看多有费解之处,即使在其同时代人的眼中,也同样地不可思议。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有趣的人物引起弗洛伊德的兴趣。为了系统地研究,他曾浏览了当时手边所有有关达芬的著作,众所周知,在精神分析理中,研究对象的心理发展与其童年经历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在记载中,人们对达芬奇的童年却所知甚少,只知达芬奇是公证人塞·皮罗·达芬奇与一位名叫卡特琳娜的农村姑娘的私生子。出生后不久,他的双亲就各自结了婚,以及他在5岁时成为塞·皮罗家族中的一员。不过,弗洛伊德还是在达芬奇有关飞禽的科学笔记中,找到了这样的一段插入的文字:
“我似乎注定要与兀鹰有缘,因为我回想起我最早的一段记忆,那时我在摇篮中,一只兀鹰向我飞下,用尾巴撬开我的嘴,并一次次地撞击我的嘴唇。”[4]
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所讲的:
如果一部传记研究真的打算要达到对其主人公精神生活的理解,那就一定不能象在大多数传记中那样,由于谨慎或假装正经的结果,略还不谈其主人公的性活动或性的个人特征在这方面我们对列奥纳多所知极少,但这极少的内容充满了重要性([2],P.488)
弗洛伊德正是将达芬奇对童年的那段回忆作为这“极少的内容”,并以此作为他分析的出发点。他首先指出,这段离奇情节的回忆不可能是真实的回忆, 它应是在后来才形成并被转换到童年时期的一种幻想。但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这种幻想有其起源。在随后的分析中,兀鹰的尾巴撬开并撞击幼年达芬奇的嘴唇被解释为象征着用嘴吸吮阴茎的性活动,这种幻想来源于幼年在母亲的乳房上吮乳以及被母亲亲吻的记忆,但这种记忆却被隐藏起来。此外,在此幻想中,兀鹰取代了母亲,这还可从另一方面来论证。(由于本文在后面将谈到的问题,在文献)[2]中,此论证被编者略去,这里的转述参考了文献[5]。)因为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是以兀鹰为形象的,而且在古典文献中有记载说,兀鹰系母亲之象征,世上只有雌兀鹰存在,它们“在飞翔途中,张开阴道 ,受孕于风”。一些教会神父用此传说来为感孕辩护。弗洛伊德认为,达芬奇无疑是知道这些说法的。至于为什么在此分析中阴茎和母亲联在一起的问题,弗洛伊德则借助精神分析的幼儿性欲理论予以解释,即小男孩最初相信所有的人均有阴茎、后来发现女孩没有阴茎时产生的被 阉割恐惧,以及仍相信其母亲也有阴茎等等。
由此,弗洛伊德认为,可以通过对兀鹰幻想的分析来“填补列奥纳多生平中的空白”:它告诉我们,达芬奇“在他生命着急的最初几年中,不是在父亲和继母身边,而是在他可怜的、被遗弃的生母身边,因而他有足够的时间感到缺少父亲。”([2].P.458)而且,单独与母亲呆在一起的最初几年,“对他后来内心生活的形成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正象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弗洛伊德为19世纪的机械自然观所支配,追求事物间的因果联系。[6]在对达芬奇的研究中,弗洛伊德确实体现出这一倾向。关于为精神分析所“揭示”的“幼年经历”对达芬奇后来生活的“决定性的影响”方面,弗洛伊德讨论最多的是其“同性恋倾向”问题,认为正是达芬奇幼年同母亲的关系,导致了他后来特殊的性心理发展。由于压抑了对母亲的爱,他把这种爱保留在无意识中,以致于只追求男性,远离导致他对母亲不忠的女人。由此,弗洛伊德来说明达芬奇只招收漂亮但并列才华的男孩为学生,以及不厌其烦地为学生的开销记帐等 行为。当然,弗洛伊德也并未肯定达芬奇与其学生之间有实际的同性恋行为,而是作为某种“易动情的态度”来描述。
对达芬奇艺术杰作的解释也是弗洛伊德的中心论题之一。联系到兀鹰幻想中母亲的亲吻,象《蒙娜·丽莎》中的微笑,也是源于其生母的深层回忆,虽然在长期压抑下无法再期望从女人嘴唇上得到这种爱抚,但却可以用画笔来再现这种爱抚,并将它赋予所有的绘画作品。
遗憾的是,对于在达芬奇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科学工作,弗洛伊德却讨论不多。达芬奇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科学家,不迷信权威和古人,并热衷于研究和观察自然。弗洛伊德对此的解释,又牵涉到了达芬奇的父亲的作用,一方面是他不在达芬奇早年时的身边,另一方面是他后来的出现。弗洛伊德认为,古人和权威对应于他的父亲,而自然则成了曾哺育他的母亲。归根结底,达芬奇而独立的科学研究,是由其不受父亲约束的幼年的性探索所决定的,也是带有性成分的这些探索的延伸,当然,除了上述内容之外,弗洛伊德还讨论了许多其它内容,对此,本文就不再一一转述了。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这种研究方法,与近来在西方开始兴起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在一些女性主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弗洛伊德相信,精神分析的传记将使传记的撰写更富有人性,并认为他对达分奇的研究是精神分析学者征服文化的一个新阶段。因此,这部作品成了他的得意之作之一。从现在来看,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开创了心理史学的先河。随后,对此著作的批评也就纷至沓来。其中最致命者(当然也有些人不这样认为),是有人发现在弗洛伊德分析的关键“兀鹰的幻想”中,他依据的德译文误将“鸢”译作了“兀鹰”。更有人指出,即使在达芬奇本人的概念中,兀鹰的形象也并非如弗洛伊德所想象那样,如斯坦纳德,从史学角度对此传记的多个方面进行了反驳,认为“就弗洛伊德论战的三个基本阶段而言——幼年史、成年性生活和以后绘画特征,我们实际上找不到任何一个阶段的证据。即使有连贯的因果推断关系,每一阶段各自都经不起推敲。”([5]P.40)此外,他还着重提出了这类研究在论据问题上、在逻辑问题上、在理论基础问题上以及在对当时文化的理解上的严重缺陷。
二
尽管有种种异议,但是自弗洛伊德之后,心理史学还是发展了起来。50年代末,历史学会主席甚至号召会员将动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历史视为所有历史学家的下一项任务。这种热潮在70年代达到了极盛期。虽然此间涌现的著作水平参差不齐,但其中也有象艾里克森(E.Erikson)对青年路德的研究那样的力作。可是,正象在历史学的漫长发展和浩如烟海的著作中,科学史研究只有短暂的历史并只占很小的比例一样,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也大多是政治领袖、宗教名人、著名作家和艺术家等等。但结合本文的主题,在极少数涉及科学家的研究中,我们可再举出两个较典型的例子。
一个例子是曼纽尔(F.E.Manuel)的《艾萨克·牛顿的肖像》一书(参见[7][8])。它是一部动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伟大科学家牛顿的心理传记。曼纽尔也是以牛顿幼年的经历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牛顿在未出生前,父亲就已去世,他出生时非常瘦弱,在他3岁时,母亲再嫁,牛顿被交给外祖母抚养,如此等等。在曼纽尔看来,牛顿的性格与天才实际上是其幼年两种体验结合的产物。这两种体验就是他与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的关系,以及他与母亲的关系。母亲再嫁后,牛顿失去了他曾一度完全拥有过的母亲,从而产生了极度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 。渴望再次见到母亲,就象在幼年时期那样,这成了牛顿一生都在徒劳地追求的幻想。在对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的追求中,地上的父亲也就是天父上帝,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择,并有一种负罪感。这种双重体验的结合,便使得任何要夺取或占有其智力成果的企图都会引起牛顿的狂怒。在少年时,他不可能不受惩罚地伤害他的父兄,但他成年后却可以摧毁对手和敌人。这导致了他与胡克和莱布尼兹等人的冲突,而这些人实际上成了使他失去母亲的继父的替代者。晚年在铸币局的职位,则使他可以以社会所认可的方式来发泄其愤怒,来处罚作伪者。至于他的历史和神学研究,乃至科学争论,都是为提供可接受发泄的心理需要。同样地,曼纽尔对牛顿的科学工作论述不多。曼纽尔提出了有趣的二项新论:一是牛顿在1666年以及1678年的重要发现,均与他故乡伍尔兹索普即与其母亲有关系;二是他的光学实验解释为为了再次享受与母亲“亲密的视觉交流的愉悦”。
对于曼纽尔的著作,研究牛顿的著名学者、科学史家韦斯特福尔(R.S.Westfall)认为它最令人感兴趣的,但关键点在于是不是真实的。而这却难以肯定,因为不可证明,除了指出曼纽尔提出的与伍尔普索普相联系的科学发现在科学史细节上的错误之外,象对牛顿光学实验的解释,也被认为是一种“没有规则、没有结局、任何人都能 玩的游戏”,因为自中世纪发明了暗箱以来,与牛顿的实验相似的光学介光学研究的普遍内容,难道所有的研究光学的人都是为了追求与母亲亲密的视觉交流的愉快?总之,韦斯特福尔认为:“我所反对的——而且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科学史家完全有权反对的,是他这样的一种倾向,即认为他能以精神分析优越地位撰写科学史”。[8]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学者福伊尔(L.S.Feuer)在其《爱因斯坦和科学的世代》[9]一书中,用精神分析的观战来研究现代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家科学气质的心理根源。福伊尔认为:“可以说,没有一个科学家曾发现或构想出他所不喜欢的假设。在心理学意义上,假设是一种目的论的原理,对它的利用是这样的一种期望的投影,即这个世界将证明是某种与科学家最深层的潜意识渴望相一致的类型。”[10]关于福伊尔的方法与观点,可举他书中对马赫和玻尔的讨论来说明。
对马赫有关风车以及有关在实验室一支蜡烛在装满水的烧杯中燃烧的梦,福伊尔都赋予了性的含义,认为是马赫无意识要从对父亲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并涉及到马赫对物理定律的看法。这种解释在讨论马赫的反原子论观点的根源时达到了极至。神福伊尔称对马赫为说似乎成了父亲支配的象征,他把原子称为Stones(砖石),而这个词又出自《圣经》对丸的隐喻,因而马赫是在追求一个没有Stones的世界,追求一种非家长化的、作为一个整体从父亲的威胁下解放出来的实在。马赫在其物理论中投射了一种最基本的、神话中的对父亲的反感。([9]PP.26-41)在谈到玻尔时,福伊尔也是基于类似的理论,强调玻尔与其父亲的心理学关系,认为玻尔的哲学教师赫弗丁对玻尔的影响“部分地是一位教师的影响,而在一位造反者眼中,这位教师用一种新颖的态度和学说代替了一位父亲。”他指出,“足够有趣的是,尼耳斯·玻尔‘科学’创造性的伟大爆发是在他父亲于1911年逝世后的不久。”福伊尔还用这种父子冲突来说明玻尔对物理学研究课题的选择,如此等等。
对于福伊尔的这些研究,同样也引起了传统科学史家的严肃批评。克拉夫(H.Kragh)指出,事实是,在19世纪末反原子论是常见的,马赫的态度恰 恰是基于恰当的、科学的理由。而象那种对述语的象征含义的揭示,却并无进一步的证据。“对于马赫使用‘Stone’这一术语不那么人为的解释就是这样的:马赫的所想到的是物质的最小建筑砖石(Bausteine),而不是 丸。”([11],P.173)丹麦学者福尔霍耳特(D.Favrholdt)在其对玻尔的哲学背景的研究中,也根据确凿的史实一一批驳了福伊尔的观点,并措词激烈地指出那些诊断“全都是胡说八道。”[12]
三
如前所述,关于利用精神分析理论对科学史进行研究所得的成果,在传统科学家中并未被认同。这里所涉及的实际上也是历史学研究中的许多基础性问题,在范围更广的一般历史学界,争论亦同样激烈。除了象心理史学家应接受什么样的训练这样一些一般性的之外,也有人试图要否定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整个精神分析学说。[5]不容否认,在应用此理论时,对性问题及其在解释中的地位的过分夸大,也是使传统史学家抵触的原因之一。象这种涉及精神分析理论本身的正确与否等更深刻、更不易有统一结论的争论,本文不拟讨论。但正象心理史学的倡导者也承认的那样,心理史学真正区别于其它学科的,正是其方法论。[13]可以说,这种差异,是造成鸿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体现在:第一,心理史学方法依靠理论特别是依靠精神为理解和解释历史,对于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并不是按其本来的情况来加以理解和让人理解,而主要是以心理学理论来加以理解和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不是来自历史往事本身,而是理论模式的产物,简言之,与其说将模式应用于过去的历史,不如说将过去的历史应用于模式更为准确;第二,心理史学家在依靠理论时,也用现在的事情作证据,以证实他们的解释。[14]这就涉及到“证据”在在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问题。
就传记研究而言,因为要应用精神分析理论,对伟记主人公童年是不要假定些什么,就是核心的问题之一。心理史学的赞成者认为,“认为对于任一给定的童年,对于伟记主人公在童年时期对重要人物的感情,很少有足够可信且可得到的证据但精神分析理论能够使传记作者在考察童年生活时看到他,否则就会对之视而 不见的行为。”[15]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证据,传统史学家当然无法接受。另一方面,因为一般说来,近来的各种心理史学均是弗洛伊德以前的探索的变种,[6]其中了渗透弗洛伊德式的因果观,即人的童年经历与后来心理发展的因果联系。而联接本身就成为问题的“证据”与后期发展的因果链,却又是精神分析理论所惯用的、带有相当非理性的随意解释,这双重的问题也使传统史学家望而却步。针对科学史而言,由于已有的这类研究还不多,或许其发展还有待观望,但至少对宽容些的科学史家来说,也是在承认这是一种“困难的、充满陷井的艺术”的同时,保守地认为“只有当这些事件似乎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释,即不能在理性的基础上来解释时,才应考虑心理学的资料或精神分析的推理。([11]P.173)既然使如此,可以说,能为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史家共同体较为认可和接受的以科学家为对象的心理史学研究,到目前为止似乎仍未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