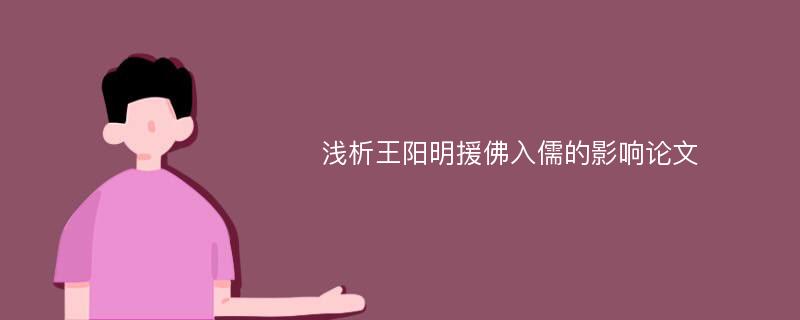
浅析王阳明援佛入儒的影响
蔡晓阳
王阳明援佛入儒在中国思想史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不但在儒学角度上促进了王门的佛学化,还在佛教角度上推动了佛学的儒学化,共同推进了儒佛两家的合流,进而结束了长期存在的儒佛之辨。
一、对儒学的影响:王门的佛学化
王阳明以援佛入儒的方式构筑了包括心本体论、“知行合一”论与良知论在内的心学思想,不但使得阳明思想融入了浓厚的佛学思想,而且为王门后学开出儒入佛、援佛入儒之先风,进而引出个体性与普遍性、存在与本质、本体与工夫等二重性的内在紧张。而这种二重品格从心学伊始便预示着其后世演变注定不是单一的“照着讲”,而是多向的“接着讲”。
关于王门后学的分化,古今学者持有不同的论点。明代黄宗羲为梳理师承脉络将王门按地域区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以及泰州王门共七大流派。今人牟宗三分王门为浙中派、泰州派、江右派,冈田武彦、杨国荣、劳思光分之为现成派(左派)、归寂派(右派)、修证派(正统派)。而更多的学者,如葛兆光、钱明等人,根据王门后学对心与理、心体与性体以及本体与工夫的理解不同而归纳为良知现成派与后天致知派,前者以王畿、王艮、李贽等为代表,后者以罗洪先、聂豹、邹守益、刘邦采等为代表。综合各家立论,笔者赞成多数学者的观点。不过,较之于王阳明援佛入儒思想,良知现成派与后天致知派均体现了对佛义领悟的深化,揭示了王门的佛学化是一种不可违逆的历史趋势。
(3)There exists complicated interaction when high sound intensity effect and grazing fiow effect are present simultaneously,and the SPL effect can be greatly inhibited when grazing fiow is present,while the grazing fiow effect can be reduced partly as well at a relatively high SPLSP.
基于王阳明援佛入儒思想,良知现成派则直接采用禅宗明心见性、“我心即佛心”的佛性哲理与参禅静悟的修行方法,将普遍之理囊括于一人之心、一人之良知,强调“良知”即现成自知,重在自“悟”本体。良知现成派不仅推进了王门佛学化的深化,亦推进了浙中王门、泰州学派的“风行天下”。对此,《明史》记载:“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三十二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风行天下”是指王门的影响与势力,而“渐失其传”是指王畿、王艮近似“禅学”之风。
继王畿之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作为良知现成说的承继者与发展者,他“出入二氏”,其学颇具佛禅“不立文字”之风,“主于自得,不落于言语文字之诠”。他坚持现成“良知”说,主张“格物”在正己,倡导以“安身”立本,将高高在上的“道”融入百姓日用之中。在良知说层面,他特别继承王学“良知人人皆有”的论点,着重汲取“佛法在日用处,行住坐卧处,吃茶吃饭处,语言相同处,所作所为处”的“平常心是道”的佛禅哲理,使得其良知现成说具有“百姓日用是道”的平民化色彩。他说:“良知天性,往古来今,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与“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的良知说相联系的工夫论即为“淮南格物”论。王艮指出:“物格知至,本也;诚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贯,是故爱人治人礼人也,格物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也。大人之学也。”所以,“格物”“知本”不是向外探求的认识论,而是强化内在修养的修行论。
作为良知现成的首倡者,王畿与佛教尤其是禅宗关系密切,一方面他喜好丛林交游,与云栖祩宏、玉芝法聚、苇航、小达摩及风自然等高僧大德相交甚笃;另一方面,在佛教认识上,王畿不同于王阳明将佛教视为异端邪说的主张,重视从义理上来解释儒佛同源,认为“良知”具有“虚实相生而非无”“寂感相乘而非灭”的特点,遂以“良知”为“范围三教之宗”。王畿从道德践履与主观修养的工夫论上阐释三教的兼容并蓄,强调要顺应良知准则以尽作圣之功。王畿的良知现成论以王阳明的良知本体为根基,在本体与工夫上都离佛禅更进一步:在良知本体上,他将其与佛禅观念进行比附,借惠能的《坛经》以明良知不离“流行”而显其“主宰”之义,认为现成良知的宗旨与佛禅“自性”等同。他说:“良知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自然明通公溥,无邪之谓也。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恶;却又不断百思想,此上乘之学不二法门也,若卧轮则为声闻之断见矣。”在工夫论上,他强调“自证自悟”,倡导君子之学“一念之几”。他说:“圣狂之分无他,只在一念克与妄之间而已。一念以定,便是缉熙之学。一念者,无念也,即念而离念也。故君子之学,以无念为宗。”“无念为宗”是《坛经》所揭示的佛禅宗旨,在此,王畿不但将其与君子之学进行比附,而且实质上采用“不着一念”的佛禅义理。尽管王畿以阳明心学思想为根基,但以禅证儒是其思想的主要特征,“狂禅”之称实为王畿所助推。
王门学者坚持以实用主义的原则看待佛教,在佛教历史、佛教经典与佛教义理方面做出了儒佛相融的积极努力,促进儒佛深层次的衔接,推动了佛学的儒学化。
儒佛融合作为宋明时期的一个历史命题,如何把儒学与佛学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是每一个时代学者的核心任务,而王阳明及王门后学亦不例外。在王门学者中,儒佛融合主要体现在佛教历史观、佛教经典观与佛教义理观中。
相较于良知现成派的“狂禅”化,后天致知派虽然注重与佛门交游,如胡直随圆宁、邓鲁习禅修静,王时槐“殚精佛学”,邹元标与无念深有、憨山德清、紫柏真可等禅僧友善,但却不认同良知现成派的佛禅化趋向,坚守儒学传统底线。他们认为“自来圣贤论学,未尝有不犯做手一言,未有学而不由做者”。为悟得良知本体与坚守儒家传统,后天致知派尽管强调工夫的重要性,但亦对佛教的修行观多有借鉴。其中,归寂派主要借鉴禅定的佛教修行论,以归寂为致知的工夫。如罗洪先主静归寂的修行观始于他与王畿的“楚中习静”事件,这一学佛事件使他认同了佛教主静无欲的“无滞无相”。再如,聂豹借用佛禅“心镜”的拟喻强调“离感而守寂”的静修论,他说:“鄙以致虚守寂充满乎虚灵之体为致知,感而应遂通天下之故为格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与明明德于天下相照应。”同一时期,修证派则借鉴了“定慧等持”“渐顿双修”的佛教修行观,认为良知虽是先天本体,但其展现却无法离开后天的工夫。如邹守益将戒慎恐惧视为保养良知的工夫,注重去欲、慎独,“以独知为良知,以戒惧谨独为致良知之功”,他说:“圣学之要曰,一者无欲也”“果能慎于独知,视无形而听无声,日用人伦庶物三千三百,不敢以纵弛离之,即此便是自得,即此便是悟,别无一种机窍也。”再如刘邦采“致虚”“致实”的工夫论充分体现了其儒佛相融的特点,他说:“心之为体也虚,其为用也实。义质礼行,逊出信成,致其实也;无意无必,无固无我,致其虚也。虚以通天下之志,实以成天下之务,虚实相生则德不孤。是故常无我以观其体,心普万物而无心也;常无欲以观其用,情顺万事而无情也。”在这里,刘邦采借佛教修行论以达到不为世俗所累的“无相无我”之境,借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道德以“成天下之务”,超越了王阳明以儒为本、以佛为用的援佛入儒思想。
与良知现成派由先天本体走向现成良知的趋势不同,后天致知派将个体之理还原成普遍之理,且为抵制良知现成派直心率性的道德弊端,尤为注重道德践履的工夫论。然而,纵使后天致知论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王学向禅学的彻底转变,但他们的工夫论或多或少地融摄了佛教顿渐双修、定慧等持以及对“无滞无相”境界的追求,从侧面反映了王门佛学化的进一步发展。
由上可知,王门后学承继王阳明援佛入儒思想,从不同的角度统摄佛教义理与方法,如良知现成派在良知本体与“自悟自证”的方法论方面对佛教心性论与主悟论进行统摄,后天致知论在致知工夫的主张中融入了佛教顿悟与渐修的修行论以及超脱出世的境界论。两派之中,良知现成派主张“良知”乃现成自有,并且“在先天心体上立根”,但却拉大了与儒家原始宗义的距离,有陷入“狂禅”之端倪;后天致知派主张培养工夫以“悟得良知”,如聂豹言“归寂”、邹守益言“戒慎恐惧”,尽管坚守原始儒家的底线,但在理论论证与实践过程中,多有借鉴佛教的修行观。
与阳明思想相比,两派均进一步强化了王门佛学化的程度,暗含了佛教义理对王门学说的深化。在王阳明援佛入儒思想的启迪下,王门后学纷纷对佛教义理及方法进行研究与吸收,有的如良知现成派一样过度汲取,有的如后天致知派一样严守儒家底线,有限度地援佛入儒,因此,王门的佛学化进程可谓是阳明心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系统通过精准的车位信息采集(车位探测、视频监控等)和高度整合的运营平台以多种形式为车主提供实时、准确的车位信息并进行城市交通诱导,缓解交通压力,同时,通过顶层平台深度挖掘并充分提炼高度汇集的海量信息,以数据报表等形式为政府决策部门的城市交通规划工作提供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撑[2]。
在佛教历史观上,由于阳明心学倡导人人皆有良知与自我圣化的理念,导致王门学者的历史权威意识淡薄。因此,他们更多地基于实用主义来对待佛教传统思想资源。如杨复所认为“秦、汉以远,不复知道为何物,而佛之教能守其心性之法”,要求诸生借佛明儒、以禅明心,“儒生学士从此悟入,然后稍接孔脉”。这显然是以历史实用主义为出发点,承认并利用佛教对辨明心性的助推作用,对中晚明的佛学儒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借助王门佛学化这一点可知,王阳明援佛入儒是宋明理学在援佛入儒思想进程中的终结点。与先前理学家相比,王阳明是援佛入儒以创新说的杰出者、彻底者。对于王阳明之后的儒学家,他们均是在王阳明思想的前提下对援入儒佛的不同判断,良知现成派主张继续加深儒佛结合的力度以促使儒家更好地发展,而后天致知派认为在援佛入儒的同时要注重儒佛之防。因此,王阳明援佛入儒的终极目的在于维护儒家正统,并且促使儒学深入发展,赋予儒家以适宜的时代性,为后世奠定儒家正统。
二、对佛学的影响:佛学的儒学化
倘若王门学者是从外部儒家视角推动佛学的儒学化,那宗门禅僧则是从内部佛学角度致力于佛学的儒学化。鉴于阳明心学思想的广泛影响及王门学者普遍的丛林交游,晚明佛教界的焦点便集中在阳明学说的儒佛相通之处。对于阳明思想的认同与否,佛教界主要分为以赞成为主的以佛释儒者与以否定为主的出儒释佛者。
总之,良知现成派将天赋良知归入现成本体,不仅将普遍之理归入个体之心或个体之良知,而且以先天之知勾销后天之致,致使修行工夫的内在性佛禅化。这是对阳明心学有根性、先验性与简易性的赓续,亦是从不同方面对王学思想进行推进与创新。确切地讲,良知现成派工夫消解的发展进程不仅是王门援佛入儒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王门佛学化程度趋于深化的过程。
第一,健康教育宣导。护理人员可利用医院相关宣传册、黑板报、网上视频教学等宣传手段让孕妇充分了解妊娠的具体过程,并使孕妇及其家属充分了解整个孕期中孕妇所应注意的各种问题。同时,护理人员应注意将相关分娩知识教予孕妇,让孕妇对于分娩过程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以提高孕妇顺利分娩的成功率,缓解孕妇的紧张和焦虑。此外,护理人员还应对孕妇及其家属进行血糖控制知识教育,避免并发症的产生。
一个完整的直播流程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数据编码、数据传输、解码数据和视频播放等五个部分:数据采集部分包括视频/音频的采集、图形处理等;数据编码和传输涉及视频/音频压缩、CDN推流、控制信令等;数据的解码和视频播放部分涉及视频/音频解码,拉流、即时通信等技术。对于部分高校来说,从零开始搭建一个直播平台,要求的技术难点较多,实现较为复杂。云服务平台能够提供稳定的底层构架和API接口,能够帮助高校较为轻易地实现搭建属于自己的微课直播平台。
在佛教经典的考辨上,王门学者注重以禅解经,尤其善用以《六祖坛经》《传灯录》及《传法心要》为主的禅宗典籍。如耿天台借助追溯《坛经》原旨,强调倡导众生皆有佛性的禅宗“不特诡于吾道”,“俾尽此性以绍法弘化,即所以报父母恩也”。
在佛教义理观上,王门学者大多坚持以儒家思想为基本理念,同时亦认为佛教中存有“正法”“人道”。如在性体论上,王畿认为,“良知者,性之灵,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范围三教之枢”,而以良知范围三教的实质则是儒佛具有同一的性体论,因而性体论是中晚明王门后学主张儒佛融合的理论基础。在工夫论上,王门学者继承宋儒张九成“学佛然后知儒”的传统,将儒佛提高到等同的位置,如王时槐重视真修的“实悟”与见闻的“解悟”,他说:“由真修而悟者,实际也;由见解而悟者,影响也。”其主旨是倡导把佛教空性与参究悟性相结合,以达到彻悟性体的目的。
在王畿、王艮“良知现成”论的基础上,李贽提出“童心说”,即“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他借“童心说”延伸古代思想界少有的平等观,并将佛禅中人人皆有佛性的佛性论与王阳明人人皆可以成圣的良知说融合为一,“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尝不可使之知也”,以此说明人人生而知之、皆可成佛的平等观。
王阳明心学思想对佛教义理、修持、境界等方面多有摄取,拉近了儒佛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中晚明及后世佛学的儒学化。因此,关于佛学的儒学化及复兴,一方面得益于王门学者儒佛融合的努力,另一方面得益于宗门禅僧中以佛释儒者、出儒释佛者的理论注解。
2000年代,由于提高了农药效率,农民转而使用需要剂量小并更有效的化合物,农药销量开始下降。2007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召开会议制定了一项为期5年的环保计划。通过环保主义者、农业工会、杀虫剂制造商和其他有关方之间的反复协商和谈判,最终促成了“生态植物”计划的出台。该计划包括重大的政治让步,“如果可能的话”,将达成50%的使用削减目标,这意味着计划的实施大部分以自愿为原则。
至此,方向机单元软件升级操作完成,故障代码“B200500记录无效”记录可以删除。接下来需要写入参数,对方向机进行参数化操作。
本研究主要介绍了组合可调式Halo -骨盆固定支具的设计及初步临床应用结果,仍存在一些不足:①样本量少,尤其是针对结核性脊柱后凸畸形方面需要进一步积累临床病例;②缺乏与其他类型脊柱牵引技术的对照研究;③Halo -骨盆固定支具刚性牵引作用力大,容易导致盆针切割及变形,盆针的穿针方式、牵引策略及器材设计有待进一步改善。
以佛释儒者认为阳明心学与佛教义理有相通之处,心性一如的佛性论与真妄同证的修行解脱论互有共通。憨山德清认为,儒家“惟精惟一,以精一为宗,而有人心、道心之别,此亦(佛教)真妄之分”,儒家的复性工夫相当于禅宗的渐修工夫,从而在心性论与修行论上打通了儒佛两者的隔阂。与德清注重义理辨析不同,紫柏达观基于佛教对性的理解,阐释心、性、情三者之间的关系。如紫柏充分运用《大乘起信论》中性、用、相三分法解释宋儒“心统性情”论,通过真实参悟以达到“情即心”“心即情”“情亦性”“心亦性”“性亦心”,这表明了紫柏以禅法诠释宋儒性情论的思想立场。紫柏说:“佛法者,心学也”,这不仅是紫柏对儒佛交涉的基本主张,也构成了以佛释儒者对儒佛相融的基本认识。
出儒释佛者主要从佛教与阳明学的不同之处入手,对阳明心学及儒学持批判观点,从侧面推动儒佛交涉的发展。如云栖祩宏主张佛教真知不等同于阳明良知,因为真知是“自然之知”,良知是“造作之知”“涉妄已久”,佛教的无念之知本然地有别于良知的善恶属性。对于儒家知行与佛家静悟的关系,祩宏指出:“儒家之悟与佛家之悟,虽则无异,然根本枝叶自有深浅。”其意指儒家之悟与佛家之悟好比树根与枝叶的关系。再如,永觉元贤认为,佛教之知是清净之真心本体的的体现,属于纯粹本觉的先验之知,“灵光独露,迥脱根尘,无待而知觉者也”。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则“知待境起,境灭知亡”,实际上属于佛教中的妄念之知。综合云栖祩宏与永觉元贤的论述可知,出儒释佛者多以禅化儒,故无儒而非佛。
质言之,无论是王门学者的以儒解禅、以儒化禅,还是宗门禅僧以禅解儒、以禅化儒,两者分别从外部与内部推动了佛学对儒学思想与观念的整合交互,促进了佛学的儒学化。而这既反映了佛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过程,还奠定了儒家与佛教在中国思想界中分别占据的主客体地位。
王阳明通过援佛入儒不但构建起心学的思想体系,还对后世儒学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王学的佛学化使儒家提升了心性本体的精致性;另一方面,佛学的儒学化又使得佛教从出世转向入世。儒佛合流扩大了儒佛两家的交集,促使儒佛两家的发展趋于一致,儒佛之辨呈渐衰之式。不过,王阳明援佛入儒的初衷本是利用佛教对儒学的改造,使改造后的儒学能够充分利用佛教的义理,与佛教相互融合,最终巩固儒家本位、佛教非本位的后世思想界格局。皇权专制主义后期,儒佛之辨的式衰、儒佛两家的合流,实际上也借力于王阳明援佛入儒思想。
[作者简介] 蔡晓阳,济南市文化馆(济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见习生。
[责任编辑:祝莉莉]
标签:王阳明论文; 儒佛之辨论文; 心学思想论文; 中国思想史论文; “接着讲”论文; 佛学化论文; 儒学化论文; 知行合一论文; 济南市文化馆(济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