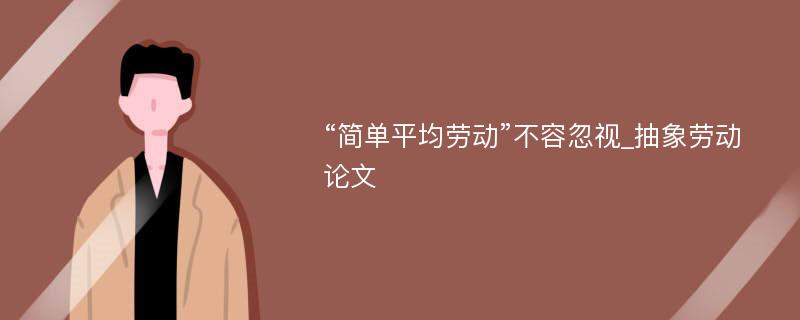
“简单平均劳动”不容忽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容忽视论文,平均论文,简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原理由两个范畴组成,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对抽象劳动范畴,马克思又作出两个规定:一是“一般人类劳动”,二是“简单平均劳动”。这是层次分明、缺一不可的系列规定。但多年来我们的辞书及大多数经济学论著说明了抽象劳动范畴的第一个规定,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第二个规定。
《政治经济学辞典》对“抽象劳动”如是界说:“具体劳动的对称。又称一般人类劳动。指撇开各种具体形态的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商品生产条件下,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的一个方面,它形成价值。”(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册,第345页)《辞海》中“抽象劳动”的定义,除了指出“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人的脑力、体力等在生产中的消耗”外,与上述解释一样。(《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681页)
马克思对“抽象劳动”虽未下过定义,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对之是“较详细地加以说明”了的。(《资本论》第一卷,第55页)紧接着,转入对商品价值的抽象,他指出:“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资本论》第一卷,第57~58页)此间简单平均劳动。
马克思讲得很明确:“人类劳动在这里”“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全部分析,并不是撇开了劳动关系中的自然物质因素,把人们的视野引入纯粹人的领地,指出价值只是体现人类劳动以后,便到此终止了,而是再加以抽象,俯瞰全部人类劳动,直到其“极卑微”的领地,将人类劳动最终归结为“简单平均劳动”。马克思在上述引文的末了特意交代:“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资本论》第一卷,第58页)这一交代很重要。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抽象劳动范畴的内涵是这样两个规定:首先是“一般人类劳动”,或称“人类劳动”;在此之下,又抽象出“简单平均劳动”,或称“简单劳动”。而前引辞书的“抽象劳动”定义,正确诠释了第一个规定,却只字未提第二个规定。
“简单平均劳动”的含义是什么呢?所谓“简单”,就是指在一定社会的全部劳动中,抽取出“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劳动;所谓“平均”,就是指再把每个这样的人的劳动耗费都加在一起,然后除以此基数所得的商。
我们现在要着重分析的是,马克思为什么要在作出一般人类劳动的规定之后,又进一步作出了简单平均劳动的规定呢?后一个规定的地位和意义何在?
首先,可以从“简单平均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的比较中认识这一规定在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中的地位。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阐明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无疑,在商品生产上只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唯有它才直接决定价值实体。马克思又明确指出:“简单平均劳动”是形成商品价值的“各种劳动”的“计量单位”,“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资本论》第一卷,第58页)这就是说,形成价值实体,被抽象为价值实体的基点、原子、细胞或最小颗粒,是简单平均劳动。而包括社会必要劳动在内的其余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都不过是自乘的、多倍的简单劳动。可见,只有“简单平均劳动”,才具有最基本的意义,才是马克思“用抽象力”代替“显微镜”所得到的最基本的研究成果。因而可以说,只有“简单平均劳动”,才揭示了价值系统中最低到最高各个层次之间的连贯性,才使几千年的人类智慧在价值方面的探讨有了真正的结果。
其次,我们再从不同角度把抽象劳动范畴的这两个规定较详细地加以比较,以便加深对第二个规定的认识。
先从抽象劳动范畴本身内容出发进行比较。“抽象劳动”首先作为“一般人类劳动”,固然是在考察商品价值时得出的规定,然而如前所述,它又与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相承接,直接是对一切不同自然属性的具体劳动的抽象。据此,对这一抽象,借用某些学者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劳动抽象。而“抽象劳动”进一步作为“简单平均劳动”,则更侧重于对形成商品价值的社会劳动本身的抽象,亦即对价值实体的抽象。据此,对这一抽象,应确切称之为价值抽象。(这里所说的价值抽象,仅为上述劳动抽象的特定对称,实际上是对通常相对于价值形式所说的价值抽象的进一步抽象)这就是说,“抽象劳动”既是劳动抽象又不仅仅是劳动抽象,还是价值抽象。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主要是劳动抽象,作为“简单平均劳动”主要是价值抽象。
劳动抽象,是对劳动的永恒规定;价值抽象是对劳动的历史规定。一旦价值随着商品的消亡而消亡,那时抽象劳动概念虽然在第一个规定的意义上仍将可以被保留,但作为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二重性这一学说所涵定的形成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将不复存在。即是说,在商品及其价值消失以后,一般人类劳动规定仍可留留,简单平均劳动规定因其丧失了存在的历史必要而消失。(消失的根据将是:“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到那时已不复存在)可是,只要还有商品,还有价值这个充分条件存在,那么,形成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就全然不会被扬弃;与此同时,价值抽象也就是必然的存在。因此说,简单平均劳动规定这一价值抽象,与抽象劳动直接同一,它是抽象劳动的本质规定;而一般人类劳动规定这一劳动抽象,则只是抽象劳动的先决条件、必要条件。这就是说,第二个规定比第一个规定更重要。
第三,从《资本论》的整体结构出发来认识这两个规定,以及后一规定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既然《资本论》的出发点不是劳动而是商品,既然抽象劳动范畴不是研究人的劳动的结果而是考察商品价值的结果,既然价值不是小前提而是大前提,那么,抽象劳动的全部内容规定就处处离不开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上衣和麻布不仅是价值,而且是一定量的价值。”“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饮食的劳动量”。(《资本论》第一卷,第58、59页)诚然,撇开价值形式中的物化因素,把价值归统于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是必要和必须的,舍此便不能把万千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化为相同质的东西,从而使它们在逻辑上能够比较。然而,一般人类劳动规定的意义也不过如此。它还没有说明价值物之间如何比较,以什么单位来比较。因而它只是初步地解决了价值的质的问题,还没有进一步地解决价值的量的问题。而一旦从价值实体中最终抽离出“简单平均劳动”就确立了比较的单位,从而解决了价值的量的问题。既统一了各种劳动之间相互比较的量,也确定了每一种劳动本身的量。这一比较单位决非无关紧要。假如以最复杂劳动为基本比较单位,虽说不会得到相反的价值比例,但那样一来,也就很难确立各种劳动尤其是“极卑微”劳动本身的量,人们也许就永远不会知晓,至少不会精确知晓,价值增殖过程是怎样的,剩余价值从哪里来、是多少,资本积累的基因在哪里,商品堆积的社会本质是什么,等等,人们对资本的全部研究都将陷入迷途。由此可以窥见,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原理的系列规定中抽象出“简单平均劳动”这一计量单位,实在至关重要。
如前所述,一般人类劳动是价值的质的规定,简单平均劳动是价值的量的规定。这两个规定的统一,就是价值的质和量的统一。价值的本质意义是一定的量,量又以质为前提,因此说,“一般人类劳动”是价值的前提,“简单平均劳动”则与价值的本质意义直接相联。二者各自的地位互不可代,二者也不可缺一。由此我们看到,对抽象劳动范畴,在作出一般人类劳动的解释之后,还必须作出简单平均劳动的解释。
在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曾指出,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抽象方法,一种是越蒸发越稀薄的方法,一种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如果对价值的抽象不是彻底的、不以简单平均劳动的“颗粒”为终点,而仅仅界定到一般人类劳动的“云雾”为止,那么,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就找不到价值创生的基点,找不到社会财富积累的起点,那也就不能由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而与现实具体归于同一。这样的抽象,很难说是科学严谨的抽象,而是近于越蒸发越稀薄的抽象,笼而统之的捉摸不定的、越来越“抽象”的抽象。对抽象劳动范畴及其本质规定的诠释和理解,实际上从一定程度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两种根本不同的抽象法,两种根本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质言之,抽象劳动范畴中,只有“简单平均劳动”才称得上人类抽象思维的一个最优秀成果,只有“简单平均劳动”才科学地揭示了商品时代价值立足的基点,只有“简单平均劳动”才是抽象劳动范畴的本质规定。因此,这一规定决不容忽视。
商品经济发展到当今,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比例的愈发扩大,随之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初步实施,在客观上都始终丝毫不会削弱“简单平均劳动”的核心指导意义。
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劳动,始终不过是自乘的、多倍的、自我凝聚的简单劳动。马克思创立劳动二重性原理、提出抽象劳动范畴的时代,已经是科技革命取得空前成就,从而不到一百年的人类劳动创造出大于以往人类劳动成果总和的时代。而且,马克思比一般学者都更重视科学技术的伟大作用。他曾说,蒸汽机对反动统治的威胁,要大于布朗基,科学技术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是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但是,马克思经济眼光最根本的着眼点,仍是“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简单劳动。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是对立的统一。可以说,正是复杂劳动的高度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产生的社会条件,使马克思得以站在人类劳动的最高点,俯视人类劳动的“极卑微”领地,从而作出“简单平均劳动”的规定。
当今经济愈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往往简单劳动也愈充斥于市。这种现象的因果联系值得研究。总的说来,“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尖端始终以底端为根基。叶茂固然促使根深,但根深才能叶茂。事情总是由简单到复杂,复杂也总要表现为简单。显赫迷人的金字塔,总是由不显赫不迷人的底端建起和组成。有了简单劳动的量的积累,才有复杂劳动的质的飞跃;复杂劳动的质,最终也要靠简单劳动的量来实现。如果压抑和限制了普通人的简单劳动,那么,科学技术也就只是科学技术,不会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就象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四大发明那样。在当代社会,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依赖引进先进科学技术设备获得经济发展的成功,相反,都是失败的。普通劳动者自身素质的提高,自身积极性、创造性的焕发,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保证。也就是说,当今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立足点,仍是“简单平均劳动”。因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人类劳动大舞台,始终并非像它表面上显示的那样,是将军或银行家、元首或科学家等等重要角色的扮演,而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马克思这一独具慧眼的揭示,体现了他旗帜鲜明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也体现了他旗帜鲜明的哲学历史观,亦即,归根结底,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
但是,树立马克思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很难,付储实践更难。一旦在这样的观点指导下再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较长期存在的农民负担过重,工人负担过重,普通劳动者积极性不能有效发挥,以及近几年出现的下岗职工及其再就业等等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无疑极为重要。但是,自己的特色不突出,一味跟在别人后面前进,永远不会超过别人。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经济的突出特色,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自觉发展的经济。本文所述简单平均劳动的规定,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基本原理的最基本规定。在最基本的理论上,容不得半点忽视。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