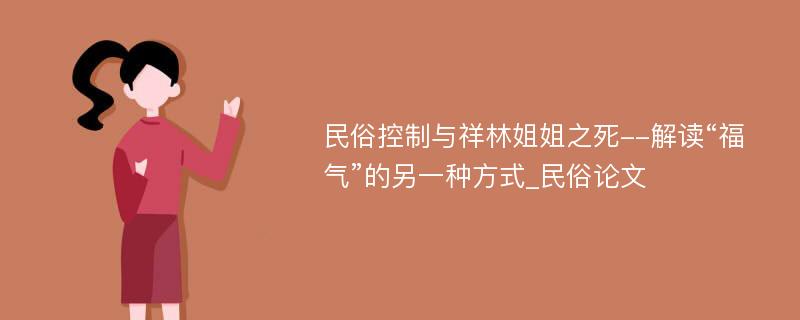
民俗控制与祥林嫂之死——对《祝福》的另一种解读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死论文,民俗论文,方式论文,祥林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03(2007)01-0111-4
一、引言
对于祥林嫂之死,正如陈方竞所说,“这确是一个老而又老,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1]。在过去,人们从四大绳索、文化吃人、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等角度进行了多种阐释。毫无疑问,这些解释都具有合理性。但众所周知,文化杀人更多的侧重于文化对“真的人”(《狂人日记》中语)的精神虐杀;而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又未免笼统,因为以此来说明鲁迅小说中孔乙己(《孔乙己》)、阿Q(《阿Q正传》),甚至魏连殳(《孤独者》)、狂人等也并无不妥之处。的确,《祝福》中紧紧威慑着祥林嫂的不是罪恶的个别人,而是由“‘多数人’构成的社会力量——鲁镇上‘咀嚼赏鉴’着她的痛苦的人们,那‘又冷又尖’的‘笑影’,那似笑非笑的‘嘲笑’”[2]。对于祥林嫂之死,围绕在她周围的每一个人——信奉理学的鲁四老爷、善女人柳妈等等都脱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说恰是“我”这个与鲁镇格格不入的新派人物对灵魂有无的解释,给了祥林嫂最后那致命的一击——从这里看,《祝福》在小说意义结构上与鲁迅其他乡土类作品并无不同。然而当我们将几篇小说比较而读,就会发现《祝福》与《孔乙己》等有着明显的区别:小说中的人际环境也即祥林嫂周围的人们——从鲁四老爷到普通百姓,与孔乙己周围的人们相比,他们给读者的感觉是更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祥林嫂是在丈夫死后以寡妇身份到鲁镇打工的。寡妇,在过去中国的许多地方,在民间信仰中,“人咸目为不祥人,以为其夫主之魂魄,常随妇身,又娶之者,必受其祟,故辄弃置不顾,无人再娶”[3]。(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也有“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之语)但尽管如此,鲁镇人还是接纳了初到鲁镇的祥林嫂。鲁四老爷尽管皱了皱眉,但对她并没有太多禁忌,祭祀时福礼的准备、桌子上供品、用具的摆放等,祥林嫂可以样样参与。周围人们对祥林嫂的态度显然也是和蔼的、热情的——这从祥林嫂二到鲁镇时人们态度的转变可以推断出来。因为对鲁镇人而言,只要我不娶你,就沾不上你的鬼气;你不改嫁,就是从一而终的节妇。而穷苦人家的寡妇出外打工,是为人们所接受的[4]。更何况祥林嫂的安分和“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自然赢得人们的好感,而祥林嫂也在这种看似其乐也融融的人际环境中,尽管劳累,“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5]。而且,即使当祥林嫂背负不贞、不洁、不祥的罪名二到鲁镇时,尽管鲁四老爷认为她伤风败俗,但依旧录用;四婶听完她悲惨的故事“眼圈就有些红了”;而初听她故事的人大多也会陪出眼泪。由此我们可以说,《祝福》中的人际环境与《孔乙己》等明显不同。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鲁镇人的和蔼与温暖逐渐变为讥诮与又冷又尖的嘲笑,并且,也正是这些当时充满同情心的人们最终使祥林嫂陷入绝境!何以有这种变化,或说善良的鲁镇人们怎样变成“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6],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在鲁迅乡土小说中,《祝福》无疑是最具民俗色彩的作品。我们不必细说小说中涉及的祭祀民俗(祭灶、祝福等)、婚姻民俗(小女婿婚——绍兴称为养媳妇、抢婚——绍兴称为抢亲等)、信仰禁忌民俗、社会制度民俗、服饰民俗、语言、交通民俗等等,就小说整体而言,我们通过开篇祭灶的鞭炮和结尾隆重的祝福礼,就可以看出,在鲁迅笔下,鲁镇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具有较强稳定性和维系功能因而也就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俗文化系统。
每一种较为成熟的民俗文化,都有较强的教化功能和规范功能,对其俗民个体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在民俗学看来,“民俗控制在习俗环境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俗民群体依据习俗规范的约束,有具体意向地要求俗民成员无条件遵守,如有违规越轨行为,就会受到惩罚;如能模范遵守就会受到表彰奖赏。另一类是由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违背了这些民俗的约束,立即在俗民的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作为一种自我惩罚或超自然力的惩罚”[7]。民俗对俗民个体的控制类型有六种:隐喻型、奖惩型、监测型、规约型、裁判型和禁忌型民俗控制[8]。由此我们来考察祥林嫂一生的遭遇,可以发现隐喻型和奖惩型民俗控制集中体现在祥林嫂一生遭遇中,也决定着她在鲁镇这一民俗文化区内必然的结局。
二、隐喻型民俗控制与祥林嫂的贞节观念
在《祝福》中,最为人注目的情节之一,是祥林嫂被迫改嫁时与众不同的反抗。这种反抗毫无疑问是出于对自身贞节,也即“从一而终”观念的拼死维护。然而在感叹祥林嫂反抗之出格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祥林嫂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山村女性,这种强烈的贞节意识从何而来?或说是谁教育或灌输给她这种思想?进一步而言,与祥林嫂处于相同社会地位的鲁镇人们(除了读过书的鲁四老爷等)的种种相关意识从何而来?为什么大家对祥林嫂有着不约而同的评价或态度呢?——这也许正是我们探索“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形成原因的重要途径。而从卫老婆子的叙述看,祥林嫂的反抗并非唯一,“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我们见得多了: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觅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闹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连花烛都砸了的也有……”。显然,祥林嫂的拼死反抗绝非“因为在读书人家做过事”,这种对自身名、贞节的维护,或说寡妇守节其实是一种人人恪守的习俗惯制。
对已婚女性要求“从一而终”起源已久。《周易·卦三十二·恒》中就有“恒其德贞,妇人吉;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语。在《序卦》中又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9]。《礼记·郊特牲》中也说“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至汉,刘向的《列女传》和班昭的《女诫》使这种观念进一步强化。但从历史资料看,尽管此后历朝统治者均有此类规限,此后又有唐·宋若莘(一作若华)著《女论语》,更有宋朝程颐在《近思录》中提出著名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但从总体讲,女性再嫁并未受到严格限制,“从一而终”的伦理观念在当时还未能“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10],也即还未能进入为广大俗民所认可、恪守和传承的民俗系统。
南宋以后,女性贞节观念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至明清际,这种观念的强化达到极致,走向宗教化、民俗化。
在理论上,明仁孝文皇后撰《内训》一书,明成祖将此书颁赐臣民,使之广为流传。不久后王相将《内训》、班昭的《女诫》、宋若莘的《女论语》和自己母亲所著的《女范捷录》合成一部《女四书》,传遍四方,影响极大。在政府具体举措上,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就颁布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又令“巡方督学,岁上七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于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家有节妇,不仅有精神上的表彰,更有经济上的诸多收益,自然使“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以至于民间出现将寡妇守节年龄弄虚作假统治者不得不进行制裁的事情[11]。由此,烈女节妇日渐成为民间崇尚之风。从当时的民谚“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就可见一斑。清政府沿用了明朝政策,并在节烈范围和表彰力度方面予以扩展,这极大推动了节烈观念在民间的影响,使之完全走向宗教化[12],成为规范人们(主要是女性)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从而纳入到世代承传的民俗系统。从明、清正史中所收数以百计的各类离奇的节妇烈女故事中就可以看出,民间对贞节的崇尚真是达到只有迷信,不顾事实,不讲理性的程度,无形中成为人们信奉的宗教,成为控制人们心理、言行的民间风俗。
一种民俗一旦形成,它就依民俗自身规律来纵向传承,横向播布,并不断在传播过程中丰富、发展自己。通过隐喻型、奖惩型控制等手段教化、规范俗民行为,使俗民耳濡目染从而成为它的文化创造物。
隐喻型民俗控制“是民间约束俗民行为进行先期防范性控制的类型。它通常贯穿在习俗化过程的早期民俗教养的实施中。所说的隐喻,实际上指的是用虚拟的或纪实的人物形象作比喻,展开叙事情节的母题进行行为的预警教育,从而达到控制行为人的目的。这种控制类型主要表现在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及其中的寓言、笑话等民俗文艺活动中”[13]。在鲁迅作品中,属于隐喻型民俗控制的内容并不少见。如《二十四孝图》中的孝义故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美女蛇、《五猖会》中的善恶报应等等。这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神话传说等,在传播过程中都对俗民的心理、言行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预警作用。在《祝福》中,善女人柳妈所讲冥间对再婚女性的残酷惩罚,也是典型的隐喻型民俗控制,它对祥林嫂的心理和言行产生极大影响。
贞节、从一而终观念对祥林嫂的预警教育,无疑是在她到鲁镇打工之前就已基本完成。尽管在小说开始时作者着重点出鲁四老爷“是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书房案头摆放着《近思录集注》,但这仅仅是为祥林嫂的鲁镇生活渲染一种民俗文化氛围,为她的悲惨遭遇设下伏笔。作为短篇小说,作者不可能为我们详述祥林嫂的成长、教育等过程——而这种内容的“缺失”和祥林嫂作为“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恰好说明隐喻型民俗控制潜移默化的预警作用之可怕。但尽管如此,我们从相关资料和小说的潜在信息,依旧可以看到隐喻型民俗控制对祥林嫂等的预警教育。裘士雄等在《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中介绍说,“过去,绍兴主要城门外,都有叫行牌头的地名,那里贞节牌坊林立。在乡间路旁或成立台门口,还有旌节石碑,甚至有的台门口挂有‘奉旨旌表’的巨幅匾额。”“绍兴古贡院附近还有一个专门为寡妇设立的‘清洁堂’,把寡妇送进这暗无天日、举目无亲的‘清洁堂’去守节。‘清洁堂’门口有两个女人管着,既不让外面人进去,也不让里面人出来,一直把这些守节的寡妇关到死为止”[14]。这些贞节牌坊和“清洁堂”毫无疑问对广大女性在心理上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而从小说传达的潜在信息看,祥林嫂“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是死后阎罗大王对她这个失节妇女的残酷惩罚,而贞节意识,显然通过历朝历代各种各样的烈女节妇故事的广为流传也即民俗的隐喻型控制,早已牢固的植根于祥林嫂这些山村女性的意识中,控制着她的言行和心理,使她成为“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忠实一员,监视着他人,更严格规范、要求着自己。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祥林嫂是“被封建和迷信逼入死路。鲁迅与其他作家不同,他不明写这两种传统罪恶之可怕,而凭祥林嫂自己的真实信仰来刻画她的一生,而这种信仰和任何比它更高明的哲学和宗教一样,明显地制定它的行为规律和人生观”[15]。很显然,没有民俗的隐喻型控制——妇女贞节意识的预警教育作用,祥林嫂就不会有这种成为她“行为规律和人生观”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她的生和死的“自己的真实信仰”,她也就不会在内心深处因自己名节丧失而产生深深的耻辱——由此,我们才能说明祥林嫂的贞节意识从何而来,才能明白她被迫改嫁时对自身贞节的拼死维护,明白她再到鲁镇后那种“讪讪”、“局促”的动作与眼神以及捐门槛后那种“坦然”的样子。也由此,我们才会进一步理解“文化吃人”的深刻内涵。
三、奖惩型民俗控制与祥林嫂之死
奖惩型民俗控制是指对俗民个体“行为后果所给予的评价或评判,这种评判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对立态度。一种是表彰奖励的,而另一种是斥责惩罚的。通过两种对立态度和方式引导人们循规蹈矩”。“在村社环境中,俗民们对违规破俗者往往也采取歧视疏远的态度,或者传播嘲讽的笑话,编唱讽喻的民谣,传播嘲弄的绰号,甚至对违规越轨者的困难也不予帮助,群体娱乐活动也不欢迎越轨者参加”。而且,“这种群体反应机制不一定有权威人物主持或支持,它是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这种势力或构成对违规者的压力,或构成对守规者的动力,从正反两方面发挥民俗控制的作用”[16]。
祥林嫂二到鲁镇的遭遇,正是这种奖惩型民俗控制的最好说明。
如果说初到鲁镇,祥林嫂仅仅是个不祥之人的话,那么二到鲁镇时,她已背负着不贞不节不洁不祥伤风败俗的诸多罪名,正是一个典型的民俗的违规越轨者。她是个再醮再寡的寡妇,不仅身上带有两个死鬼丈夫的不祥之气,更可恶的是,她“畏死贪生,至于失节,则名虽为人,实与禽兽无异矣![17]”用柳妈话说,“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但祥林嫂没死,而且又来到鲁镇打工。尽管她的失节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但“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18]。因此与初到鲁镇相比,“她的境遇却改变的非常大”。我们不妨看看鲁镇俗民们是怎样对待这样一个越轨破俗的妇女的——
与第一次的爽快相比,鲁四婶面对是否再次录用祥林嫂变的“踌躇”了。
鲁四老爷“照例皱过眉,……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在听了祥林嫂的悲惨叙述后,“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何谓宽恕?显然你有罪你越轨了才需要被宽恕。
“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显然鲁镇的俗民们面对这样一个越轨破俗的妇女,与她要保持着一定距离,有意的或厌恶的在疏远她。
但对越轨破俗者的惩罚并未到此为止。
“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祭祀,这回她却清闲了”。作为越轨破俗者,作为伤风败俗的失节妇女,她已经失去了参与这种重大活动的资格。
她的悲惨故事“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即使有意提起,也是“又冷又尖”“似笑非笑”带着极大的嘲弄与讥讽。当柳妈这个“善女人”把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疤”故事传扬开去时,这成了鲁镇俗民群体再次大肆传播的对祥林嫂嘲讽的笑话。
对祥林嫂的这种俗民群体的反应机制,没有也无须权威人物(如鲁四老爷)的主持或有力的支持。它是鲁镇民俗传统的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鲁四老爷和柳妈等都只不过是这习惯势力中的一分子。这习惯势力使生存于鲁镇的人们失去了人类应有的最起码的同情心和对弱者的理解、怜悯,更不用说温馨的关心与帮助。在这种民俗势力氛围中,鲁镇俗民们已不再是“真的人”!祥林嫂只有“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那伤痕,默默地跑街,洗菜,淘米”。她认为唯一救赎自己的希望就是捐门槛,“赎了这一世的罪名”!但她不明白捐门槛只是“免得死了去受苦”,而活罪,在“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的中国,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清的。“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19]。祥林嫂已成为人们“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
正是在鲁镇俗民们对越轨破俗者无意识的似乎又是自觉的歧视、疏远与讥讽嘲弄中,祥林嫂一步步走向绝境。
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祥林嫂这个遭受命运重重打击的生命“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后,鲁四老爷家的短工那“淡然的”、“简捷的”对“我”问话的回答和他无表情无感觉的漠然态度!我们也就明白了鲁镇人们的和蔼与温暖为什么变为讥诮与又冷又尖的嘲笑,鲁镇这些充满同情心的人们怎么就变成“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使祥林嫂最终陷入绝境。
祥林嫂终于在人们的唾弃与漠视中死了。但民俗控制对她的惩罚并没有随之结束。因为她恰恰死在鲁镇俗民们正“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时候,“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可以说,对祥林嫂这个越轨破俗者的惩罚,对鲁镇任何一个已婚或守寡的女性来说都是一个警示,她们自然会更加循规蹈矩。对于那些未成年未出嫁的女子来说,又是一个眼前的活生生的隐喻型民俗控制的反面教材。因此,对于祥林嫂的死,对于一个曾与大家朝夕相处的生命的结束,在鲁镇没有激起任何人的反省与痛惜,反而使鲁镇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俗文化系统更加稳定,并不断丰富、传承和播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