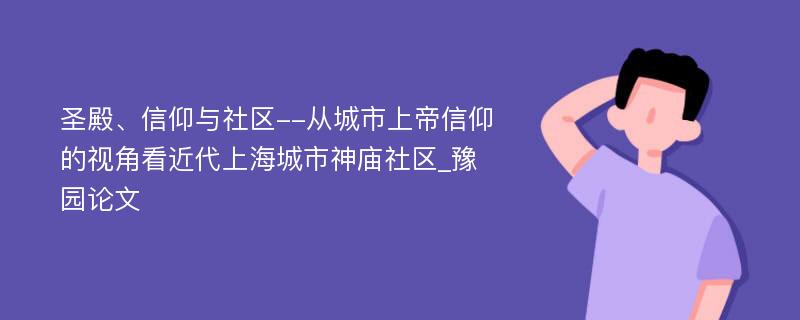
庙、信仰与社区——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隍论文,城隍庙论文,社区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1—0063—11
“上海城隍庙的风景,在很久以前就享着盛誉,许多来上海逛逛的人,大半都要到邑庙去观光一下,因为邑庙是上海市的名胜之一,它不但是善男信女奉神的所在,而且还是南市中最大的商场和游乐场。”① 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段话语,恰如其分地定义了上海城隍庙的内涵,时至今日,我们的描述仍无出其右。城隍庙社区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城隍信仰的功能变迁。至迟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隍庙已超越单一的信仰空间,成为商场、娱乐场甚至整个城隍庙社区的代名词。
以城隍庙为象征实体的城隍信仰,在上海城隍庙社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的原动作用。那么,它是如何将城隍庙社区塑造成以信仰为内核、集商业、娱乐、文化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城隍庙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里,我们将视线集中在晚清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这个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期,源于传统的城隍信仰如何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城隍庙社区互动,显然是解读这一社区发展的重要视角。
一、上海城隍庙社区的沧桑沿革
中国的城隍崇拜可以追溯到汉代,而上海之有城隍庙,起于南宋。当时的上海,只是松江府华亭县下辖的一个镇,原永嘉路12号的淡井庙②,就是华亭城隍行殿。元至元年间(1264—1295),上海升格为县,淡井庙成为上海的城隍庙。明永乐年间(1403—1424),上海知县张守约在“县西北长生桥西”③ 的金山神主庙④ 中增祀上海县城隍秦裕伯⑤,成就了上海城隍庙近600年来“前殿为霍、后殿为秦”一庙二城隍的格局。留存下来的“明代上海三志⑥”和《康熙上海县志》记载了上海城隍庙的早期情况:天顺元年(1457),知县李纹重修庙宇,殿前建仪门并刻诰文于石;嘉靖十四年(1535),住持募集财帛扩建山门并建牌坊一座,由新任知县冯彬题字“保障海隅”;万历三十年(1602)和三十四年(1606),知县刘一爌和李继周相继重建庙宇。至此,经历代修葺扩建的上海城隍庙,终与上海县署隔浜相对,成为上海县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公共空间。城隍庙社区基本形成以庙(包括建在城隍庙两侧的祀祠)为中心,南濒方浜,北接豫园,东为士绅宅邸、社学,西为府馆、演武场的格局。
当然,城隍庙社区真正繁荣是在清代。据乾隆、嘉庆和同治《上海县志》记载,有清一代上海城隍庙近旁的祀祠,除明朝留存下来的群忠祠、三李公祠、仁寿祠,增加了弥罗阁、鄂王庙、刘猛将军殿、许真君殿、药皇殿、罗神殿、斗母阁、花神祠、鲁班阁、三官殿、施相公殿以及新江、长人、高昌、五路四司神殿等。与此交织的是地方对城隍庙及近旁祠堂的频繁修扩。《同治上海县志》和庙内外的碑文记载着从康熙到道光年间,上海历代官府和民间修缮邑庙的详细记录⑦,充分彰显了城隍庙作为邑城信仰中心的地位。
城隍庙的屡次修建,体现了邑庙在邑城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地方绅民也在不断致力于城隍庙公共空间的构建。康熙四十八年(1710),乡绅集资在庙东鸠构“东园”作为城隍庙内园,每逢新年、重阳等节,官吏士绅祭毕城隍,便入东园“登高望云物”、“宴罢此中闲”⑧。乾隆二十五年(1760),邑城绅、商又集资买下庙北荒废的豫园,“仍筑为园,以仰答神庥。先庙寝之左有‘东园’,故以西名之”⑨。整顿一新的西园,“百数十年名胜湮没之区,俨然复睹其盛”⑩,逐渐成为士绅商贾开展社会活动的场所。从康熙年间到开埠前,先后有7 家执沪地传统产业之牛耳的行业公所入驻庙园。豫园的新生是地方士绅重构城隍庙格局的结果,特别是各业公所的入驻,使城隍庙社区在政治、信仰功能之外,又添经济功能,为后来城隍庙社区突出的商业性奠定了基础。
从各类史料来看,城隍庙商市概成于清初。每逢庙会,许多摊贩和卖艺者齐集景物荒废、隙地较多的豫园,兜售货品、娱乐民众。这时的商市仍带有明显的节会性质。西园建成后,为方便士绅商贾的活动,园内开设了一些茶肆、商铺(以书画笔墨骨董业为主),于是,“凡四方之山人墨客及江湖杂技,皆托足其中”(11),渐渐有了市廛的雏形。道光二十二年(1842)到咸丰十年(1860),城隍庙社区三遭兵燹(12),庙园屡遭破坏。然这一时期,庙园的商业气象有了长足进步:除法国驻军“惟许设书画笔墨骨董等铺”(13),曾为上海人熟悉的几家老店均于那时开设,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创设的素以酒酿圆子闻名的老松盛,咸丰五年(1855)创设的朱品斋和永生堂梨膏糖店(14)。建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湖心亭,原为青蓝布业议事场所,也于咸丰五年改为茶馆。而王韬笔下的庙园,俨然已是一个大商场:“园中茗肆十余所,莲子碧螺,芬芳欲醉。夏日卓午,饮者杂遝……茶寮而外,设肆鬻物者又百余家。隙地虽多,绝无一卉一木,堪以怡情,园林幽趣,荡然泯矣。”(15)
历次兵燹过后,城隍庙社区亟待整修。同治七年(1868),上海县署颁布公告:“缘庙园公产向来列入官字图捐纳粮赋,现办清漕业等,理应各归各业……于同治七年分起,各自永远承粮。”(16) 将西园的修复工作交由园中21个行业机构承担,一并出让的还有土地使用权。于是,各业在修复园景的同时,纷纷把多余的地产造屋出租,使城隍庙社区的商业空间进一步膨胀。1872年8月17日刊载于《申报》的《豫园杂咏》描绘了修缮一新的豫园风光,“名园点缀不寻常,不数当年绿野堂”是对庙园商业气息浓郁的感慨。应该说,这时的庙市已与西园连成一片,形成了集古玩书画、文房用品、茶楼小吃等为一体的市场。刊印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申江百咏》中提及:“沪江邑庙皆花园,古玩书画铺多借庙中之亭台为之,故人游其中犹不知其为庙也”(17),从中已经可以窥见城隍庙社区功能的转向。
“光绪十九年(1893),知县黄承暄募捐头二门、大殿、戏楼、鼓亭、辕门等。宣统元年(1909),知县李超琼募捐重修大殿、寝宫并旗杆、墙壁。”(18) 整顿一新的城隍庙不但香花瞻拜、络绎如织,更成为邑人游观登眺、相叙行乐的场所。“城隍庙内去烧香,百戏纷陈在两廊。礼拜回头多买物,此来彼往掷钱忙”;“豫园热闹在春秋,士女纷纷结伴游。随意品茗看戏法,湖亭行过又登楼”(19)。1906年刊稿的《沪江商业市景词》浅显却真实地反映了人们来城隍庙烧香、品茗、看戏、购物和游览的情景。光绪三十二年(1906)和宣统二年(1910),城隍庙前后的方浜路和福佑路填浜而成(20)。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指南》卷二首页就记述:“上海城垣作圆形而略长……租界环城之北,黄浦绕城之东,交通便利,故东门、北门之市……商贾市廛,鳞次栉比,而尤以城隍庙为荟萃之所。”辛亥革命后,不少地产商乘地价飞涨之机在城隍庙周围租地造屋。终于,一座店铺林立、摊贩栉比的市场形成了。上海城隍庙开始了以“市”兴“庙”的历程。
民国成立后,国货之声日盛。素以手工制品闻名的城隍庙左右街弄,遂成国货的集中作坊,尤以顾绣、玩具、乐器、古董、文具、花爆以及木竹丝带等日用制品闻名遐迩。于是,城隍庙社区成了这些手工作坊的地域象征,庙市也成为手工艺品集中展示的舞台。无怪乎到了20世纪20年代,城隍庙社区成了华界的“永安先施新新三大公司。同一为集中商品地点,而城隍庙之佳处固又在商品之多国货”(21)。
1922年到1924年间,由于管理不善等原因,城隍庙三遭祝融之灾,特别是1924年农历七月十五的大火,几乎使整座庙宇化为废墟。1925年8月, 整理豫园委员会成立,翌年12月,上海邑庙董事会成立,后者的宗旨是“保持庙宇之庄严,扶助商业之发达,汇集公益之收入”(22),当然,头等大事是城隍庙的修复。1926年7月,沪上闻人黄金荣、刘鸿生、张啸林、杜月笙、程霖生、苏嘉善等合捐5万元重建大殿,“以钢铁为骨干,以水泥为材料,不用一砖一木,而彩椽画栋,翠瓦朱檐,仍沿古神庙之仪制”(23)。1927年12月18日的开光日,“进香男女,络绎不绝,直至晚间九时,犹见香烟缭绕,红烛高烧”(24)。
这次邑庙重建的意义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不仅使庙貌得以长久完好,更实现了城隍庙社区的彻底商业化。首先体现在信仰上。上海城隍庙历来由正一派道士管理。邑庙董事会获得管理权后,享有特权的黄金荣等帮会分子想出了“承包神像”的敛财方式。一时间,城隍庙的殿阁廊台上挤满了千奇百怪的作为敛财工具的神像,导致包括城隍信仰在内的各类民间信仰的畸形化。1936年的《上海市年鉴》对城隍信仰这样定义:“其他如城隍庙……等处之住持虽多为道士,然其庙宇根本不属于道教。此等道士,乃巫祝之变相矣。开埠以后,假迷信以觅食,自称为道教,而混迹于市廛者……是则不得与于道教之列。”(25) 这多少也是这次“改制”的负面影响之一。其次体现在商市上。“小东门外城隍庙,在甲子年(1924)秋,曾遭回禄,以致宫殿焚如,遂有城南热心公益者,鉴于商业之骤落,殊非佳象,因特组织豫园委员会及邑庙董事会,筹款重建。”(26) 可见,无论是整理豫园委员会还是邑庙董事会,其创立初衷是为了复兴城隍庙社区的商市。事实上,重建之后的“邑庙市场”确实迎来了全面繁荣。
二、近代上海老城厢城隍信仰的表现及特点
中国的城隍信仰,经历信仰对象从自然神到社会神、信仰范围从地方到全国、信仰受众从民间到官方的过程,在明初实现制度化,并随着明清城市的发展而广具影响。明清(晚清以前)统治者把城隍神作为国家正祀的对象,赋予其保城护民、督官摄民的“神职”,于是,在官吏士绅心目中,城隍信仰是正统的“礼制”。但对于民众而言,城隍信仰的意义未尽于此。中国人信仰中的功利性和近地性,加之城隍信仰中鬼神信仰的成分,使民众的城隍信仰带有浓郁的民间信仰倾向,且随着国家行政干预的减弱,其民间信仰的成分愈加突显。于是,矛盾由此产生。赵世瑜曾言:“城隍庙……是正祀,普通百姓也去崇拜,但官绅按照规定的仪式进行祭祀,就符合礼,百姓在这里搞得宗教实践活动(游神)逾礼越分,使它实际上成为‘淫祀’,但在制度上它还是正祀。”(27) 城隍信仰背后,存在官方与民间两种异质的文化系统。要如何将它们放在同一平台论述?赵世瑜给出了他的观点:“也许,从探讨信仰和仪式入手,比较容易陷入那种二元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们从寺庙——无论它是属于哪个宗教的——这个空间或场所入手,观察在其中和周围发生的一切,是否可以把思考深入一步?”(28) 从历史上来看,城隍庙是提供地方朔望拈香、宣讲乡约和祈祷晴雨的官方活动场所,同时也是大量民间信仰活动的集中地。从城隍庙着手考察,显然能够发掘城隍信仰的二元一体及其合理性。而这里,我们要采用一个逆向视角——正是城隍信仰的二元一体,给城隍庙社区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环境,使其成为各阶层民众共同活动的多功能空间。这里,我们就以上海老城厢为例,看看城隍信仰的这种特性如何作用于清末民初上海城隍庙社区的发展。
以下两份历史资料向我们展示了清末上海地方官员对于祭祀,特别是祀典颇多的城隍祭祀的重视。 《六十年前上海官场的接印仪节》描述了晚清(光绪三年,1877)上海道台上任当天的活动,包括查库、点卯、谒庙点香、拜会领事、 考录代书、悬牌放告等(29)。这里的“谒庙点香”便是拜祭城隍,显然,这是行政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另一份史料,叶廷眷知上海县时(同治十一年七月到光绪元年四月,1872—1875)的衙署账簿,记有知县每年参与的祭祀活动:除了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国家祭典,“每月朔望两天,知县老爷例须恭临城隍庙拈香”,“正月有祭海的典礼……二月初三日祭文昌,初四日祭吕祖,十九日观音诞拈香,二十一日城隍神诞拈香……还有文庙、武庙、天后宫、社稷坛、神祗坛、风坛、龙神、土地祠、群忠祠、黄婆祠、周太仆祠、袁公祠、吉公祠和陈公祠,都是择日设祭的。二月底到三月初,先农坛和城隍神墓;也有照例的祀典。三月十八日的龙王诞,二十八日的城隍夫人诞是只要拈香不必要设祭的。四月仅有十四日的吕祖诞拈香,二十四日的雷祖诞要祭祀。七月无事。八月所祭的和二月完全一样,而且都是择日祭司……九月只是十九日的观音诞要拈香和月底的祭扫城隍神墓”(30)。城隍庙与城隍墓的祭扫相当频繁。
然而,事实并非没有矛盾。《同治上海县志》的“祠祀”部分下设两目,“其每岁动支公项致祭者曰秩祀,其民间崇德报功自行致祭者曰私祀”。将上文提到的祭祀与志书对照后发现,上述祭奠绝大部分是“秩祀”,而“城隍庙”却位列“私祀”第一位。作为“私祀”的城隍庙,却由知县带头“司朔望拈香、宣讲乡约并祈晴祷雨”(31),充分体现了城隍信仰的内在矛盾。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知县虽每月朔望拈香并亲往祷祝城隍神、城隍夫人的诞辰,却没有循例参与一年三次的城隍出巡(32)。且据各种材料显示,正是同治年间的这位知县叶廷眷,对沪城“三巡会”的种种风气实施严禁,以至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版的《上海乡土志》“岁时”一栏虽有其它神诞纪念,却不提“三巡会”(33)。
明初以后,除京都为“二祭”,各地城隍于每年清明、七月半、十月初一举祭厉坛,赈济幽孤。这一官方明文规定的仪式,民间称其为·三巡会’。据其初衷,“三巡会”理应是城隍信仰的核心内容,除鬼神信仰的成分,兼有代表世俗官员巡察民情的含义。缘何热衷于城隍祭祀的叶知县,对同为城隍信仰内容的“三巡会”如此忌讳?要弄清其中原因,不妨先来看看几个时期的沪城“三巡会”情景:
乾隆十五年(1750)的《上海县志》,在“风俗”篇中说道:“三月清明……城隍神至期诣厉坛,仗卫整肃,邑民执香花拥慕者甚众,至晚复以华灯迎归,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皆如之。”
道光十九年(1839)的《沪上岁时衢歌》也记有“三巡会”:“清明报赛到城关,毂击肩摩拥阓阛。五里羽仗人静肃,路由岁岁掣红班。”案语中也把“三巡会”描绘为“舆马骈集,旌旄灿然,亘四五里,俨然宪卫也”。
《同治上海县志》对“三巡会”的描写较简单:“三月……清明日祭邑厉坛,悬牒城隍神诣坛赈济各义冢幽孤名祭坛会,舆从骈集,亘四五里。亦名三巡会,以七月望十月朔皆有此举也。”王韬的描述就要细致得多,且提及“三巡会”的弊端:“沪人于每年清明日、七月望、十月朔,例以鼓乐奉城隍神出诣北郊,坛祭无祀鬼魂。仪仗舆从,骈阗街巷,马至数百匹。妓女椎髻蓬发,身着赭衣,锒铛桎梏,乘舆后从,谓之‘偿愿’。间有徒步于市者,轻薄少年指视追逐以为笑乐。是非敬神,直酿淫风矣。”(34)
光绪九年(1883)出版的《淞南梦影录》干脆指出了“前邑尊叶顾之观察出示严禁”的原因:“小家碧玉,狭巷娇娃,艳服靓装,锒铛枷锁,坐无顶小轿游行其间,谓之女犯。既可媚神,又能炫客,诚一举而两得焉。”(35)
一般来说,传统社会的庙会,不论乡村还是城市,主要面向一般民众,甚至是平时饱受禁忌的妇女和社会底层。而庙会期间使用的服装道具等象征物品、夸张怪异的行为、极尽铺张的场面,也是对传统社会规范的反操作。显然,上文描述的日益“无序”的“三巡会”形象,消解了城隍信仰神圣严肃的成分,其中一些“非礼”的内容,是以维护地方礼教为己任的知县们所不愿看到的。“迎神赛会乃邑中糜费之大端,其最盛者,莫如高昌会、瞿真人会、大王会、三巡会等。每次举行,不惜巨费。若台阁、花十景、臂香、阴皂及芦架解犯各种,为浮糜惨酷谬妄之举动,于民智颇有关系,近已禁止,殊可破迷信而节糜费矣。”(36) 从“破迷信而节糜费”的角度,我们也能理解叶知县对“三巡会”的冷淡。
同时,我们还要从信仰层面分析官方和民间视野中的“三巡会”。如上文所言,城隍信仰存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官方推崇城隍信仰,因其对应世俗的行政关系;而民众更多地将自身对于“鬼神”的敬畏寄托其中,热衷“三巡会”正是这种需求的表现。开埠以后,原本享有至高威望的城隍神,在西方势力的入侵面前束手无策,而它的世俗对应——地方官员的懦弱自保进一步破坏了城隍信仰正义威严的一面;相反,对西方势力(“洋鬼子”)的危惧和试图“驱鬼”、“恤鬼”的心理,提升了民众对于城隍信仰中鬼神信仰的虔诚,表现为“三巡会”的日益盛大。而在地方官员眼中,声势浩大的“三巡会”是对官方信仰甚至官方权威的挑衅,通过行政命令对其限制,才能扭转城隍信仰进一步民间化,重新控制民众心理。
然而,这种尝试总体来说并不成功。成书于光绪二年(1876)的《沪游杂记》提到同治年间的沪城“三巡会”,“旋经邑侯禁止,此风稍息”(37),《淞南梦影录》也言“此风遂绝”(38)。可到了光宣之际,不少竹枝词披露了“三巡会”依然盛况不减的事实(39)。可见,民间对“三巡会”的热衷终究不以官方意志为转移。
应该说,晚清上海老城厢的城隍信仰,表现了突出的“二元性”——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在信仰生活中对峙着。然而,随着晚清封建官僚系统的弱化,后者在信仰生活中逐渐占据主导。进入民国以后,城隍信仰中象征封建官僚体系的层面随之落没,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对立趋于缓和,取而代之的是日益显著的信仰商业化趋势。
这里也以“三巡会”为例。1919年8月10的《申报》以《三巡会复活》为标题报道民国成立后首次“三巡会”的准备情况。此后,沪城“三巡会”因战争、政治气候等原因时断时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类迎神赛会一度禁止,不久,以城隍庙为首的一系列巡会又死灰复燃(40),并持续到抗战前。
仔细考察这一时期的“三巡会”,我们发现,传统意识中的城隍信仰已逐渐从仪式中流失。无论是活动初衷,还是整个组织过程,包括组办机构的人员构成,越来越趋向商业化和另类化(41)。
导致邑城“三巡会”与城隍信仰偏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清中后期。豫园在清乾隆年间归属城隍庙后,逐渐划归各业公所使用。这些公所,鉴于使用城隍庙园中的亭台楼阁,多在行业神之余,祈求城隍庇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显示,钱业晴雪堂、布业得月楼和豆业萃秀堂中均供有城隍神像。不仅如此,各公所还积极承担城隍庙改扩建的费用,甚至将买地出租所得和罚没所得用于城隍祭祀,并在后期开始参与“三巡会”的活动组织。由此,城隍神被人为地赋予行业神甚至财神的职能,在吸引各大行业的同时,还引来大量没有行业神的手工业者的朝拜。又因城隍驾下四司中有财帛司,于是,出现了在“三巡会”中迎财神的热闹景象,“士女填街塞巷时,委员弹压路三歧。年年三节城隍会,第一雄观财帛司”(42)。城隍信仰的“福祉”开始普及商业。
进入民国以后,城隍庙社区突出的商业娱乐氛围,进一步“感染”着“三巡会”,加速着信仰的商业化转向。抗战前夕描写“城隍出巡”的竹枝词写道:“青天白日照堂皇,迷信神权忒也狂。百业萧条不景气,居然求教到城隍。”(43) “三巡会”俨然成了为商业祈福的仪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能看到上海老城厢城隍信仰和城隍庙社区发展的关系:晚清以后,上海城隍信仰经历了“亦官亦民”到“日益大众化”、“信仰一元”到“信仰商业化”的过程。这一信仰现象折射出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信仰文化与商业文化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博弈与重构。然而,一旦这些在信仰、仪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多元因素归结到同一象征点——城隍庙,便会呈现一种空间性的整合,使城隍庙社区成为具有传统气质的公共活动空间。
三、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上海城隍庙社区
同中国各地的城隍庙一样,传统时代的上海城隍庙,除信仰中心,还是地方集会的公共空间。邑庙“西园‘三穗堂’,居园正面,巍然高耸,内极宏敞。绅士每于朔望宣讲圣谕,令众集听,凡道县朝贺万岁及有大事,皆以为公所”(44)。康熙十年,上海全邑组成二百余人的进京团,要求朝廷留任深得民心的朱知县。七月二十六日,绅民在城隍庙演戏祀神,为进京团送行(45)。“光绪戊申之夏,邑中耆老集千龄曾于豫园,与斯宴者皆年达七十以上齿德俱尊之士。筵开北海,颂上南山,诚盛事也。”(46) 城隍信仰的官方内涵使城隍庙社区成为官方集会的最佳空间。进入民国以后,城隍庙在民众生活中的传统影响力使得不少宣讲活动选择在城隍庙园中开展:五四运动前后,“东吴第二中学及通俗演讲团,在邑庙摇铃演讲商界罢工之原因及今日之大局。淋漓尽致,多为泣下”(47);五卅运动期间,数百名学生冒雨在豫园各处演讲,“要求市民援助被捕学生并与外人经济绝交”,还在庙园各茶肆分发传单,“演讲此次工潮经过情形”。规模盛大,前后历时20小时(48)。然而,当华洋矛盾取代满汉冲突成为民国政治的潜台词,上海政治生活的重心不可避免地从老城厢转移到了租界。城隍庙社区的政治功能被消解了(49),留存下来的是政治空间的遗痕——传统文化。
上海城隍庙的风光,曾被传统时代的文人反复描摹,只因他们丰富的个人体验。一个传统时代的文人可以因为信仰,也可以因为信仰之外的原因去往城隍庙。从每年定期的看戏、登高、观花会,到一时兴起的游园、品茗、购书画,城隍庙社区足以满足传统文人的各种精神需求。从清代的文人笔记来看,寓居上海县城内外的士绅文人,几乎都在城隍庙园留下足迹,尤以“海上狂人”王韬与庙园的渊源最甚。携带一身“狂”气的王韬是晚清中西文化冲撞中的弄潮儿。在他和他的同道好友身上,纠结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徘徊于中西间的矛盾与彷徨,邑庙的茶馆酒楼见证了他们“掷杯挥剑”的狂态和怀才不遇的伤感。从王韬的日记来看,西园的群悦楼、凝晖阁、绿波廊等茶馆,都是狂士们“饭罢无事,聚众剧谈”的佳处。在那里,他们拓宽着交友圈,也交流着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看法。
这些茶馆中,备受中外人士推崇的要数湖心亭茶楼。以画佛闻名的万佛楼主钱化佛说:“湖心亭设炉卖茶,我们同道的一班书画家,在南市的,大都集在亭中,品茗谈艺,很自优游快适哩。”(50) 湖心亭里还常出现一些陌生的身影。“各国的作家凡是来到上海的,总要踏进它的门喝这么一碗茶,或者吃那么几杯酒。西班牙的易本纳兹,在上海停留了三十六个钟头……他的足迹就印上了这家茶馆的阶沿。”(51) 20世纪20年代,前天安堂主教达文德游览城隍庙时,也专程去访湖心亭(52)。“在这个古老的茶馆中,我们不难会见一两个有学问有身份的中国人。他们一面喝着香茗,一面神游故国,追念着这古老的大中国的过去的光荣,一面向往着凤凰的再生。”(53) 湖心亭之所以吸引来自中外的目光,是因为它身上有租界中渐渐消失的传统的“中国意蕴”。
同宣年间,不少国画团体在豫园活动,丰富了城隍庙社区传统文化中心的内涵。位于庙园荷花池南岸的飞丹阁是著名的书画店兼画家俱乐部。当时频繁进出飞丹阁的,有后来蜚声海内外的任伯年、吴昌硕等国画大家。宣统元年(1909),城隍庙西园又产生了两个著名的书画组织——位于放鹤楼的“宛米山房”和位于得月楼的“豫园书画善会”,以后者的社会影响更大,因其成员在进行各类创作交流活动外,还很重视社会慈善和书画界同仁的经济互助。《豫园书画善会缘起及章程》中明文规定:“所收之润,半归会中,半归作者”,“应纳之润,半储会中,存庄生息;遇有善举,会议的拨,聊尽善与人同之意”,故深得时人赞誉(54)。晚清上海各书画组织往来频繁,共同创新了“上海画派”。国画研究者多评价“海派”商业气息浓,事实上,在他们身上同时留有传统文人的“济世情怀”,这种情怀最能在城隍庙这类传统积淀浓厚的空间释放。
与书画社比肩的是扇笺书画店。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邑庙中的扇笺书画业仍然繁盛,具名者有22家(55)。这些店铺“非但出卖楹联幛轴之类,而且收罗的名家书画也着实不少。所以文人墨客来游邑庙,也常在那里徘徊”(56)。
邑庙中另一个引人逗留的地方是旧书摊。“邑庙内的旧书摊,非常之多,重要而普遍的书籍,大概可说是规模粗具”(57),其中又以“国粹”为强,后期也有西文书籍。不少后来的大作家、大学者都曾在城隍庙的书摊旁消磨时光。在他们眼中,“有很大的古董铺、书画碑帖店、书局、书摊、说书场、画像店、书画展览会以至于图书馆”的城隍庙,“不仅是百货杂陈的商场,也是一个文化的中心区域”(58)。难怪有着新文学家之称的郁达夫“无聊之极便跑上城隍庙去”,常常是“独自一个,在几家书摊上看了好久。没有办法,就只好踏进茶店的高楼上去看落日,看了半天,吃了一碗素面,觉得是夜阴逼至了”(59)。从王韬到郁达夫,城隍庙社区作为文人墨客野游之地的传统保留到了民国,正如其作为老城厢商业中心的地位延续至今。
城隍庙社区是上海早期同业公所的汇集地,尤以庙园中的公所最为密集。据碑刻资料显示,康熙年间,沪地布业就以豫园得月楼为议事场所。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到开埠前,青蓝布业(湖心亭)、肉庄业(香雪堂)、钱业(东园晴雪堂)、京货帽业(飞丹阁)、饼豆业(萃秀堂)、花糖洋货业(点春堂)先后入驻庙园。到同治七年(1868),邑庙中的同业公所又增加了鞋业(凝晖阁)、旧花业(清芬堂)、酒馆业(映水楼)、羊肉业(游廊)、铜锡器业(游廊)、银楼业(游廊)、乡柴业(挹爽楼)、铁钻业(世春堂)、沙柴业(可乐轩)等(60)。从少数特权阶层享有的私家园林,变为大宗进出口货物交易买卖的场所,城隍庙社区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是庙园空间开放的直接结果。同时,同业公所的云集也影响着城隍庙社区的发展。
各类公所的空间延伸是庙园中的茶馆。开设于光绪年间的春风得意楼,初开时,因烧香妓女出入频繁,“似关风化,就在光绪二十四年的元宵节前,被保甲总巡封闭”(61)。重开后的得意楼,改变经营方向,依仗庙园中各业公所麋集的优势,招徕商贾在茶馆中交易论市,称为“茶会”。从此,每日清晨的得意楼中,布、豆、钱、糖等业的商贸经济人不断进出,“每至午申人毕集,成盘出货约期忙”(62)。不同于公所的严肃气氛,茶馆空间使交易多了几分变通和人情,于是,茶楼作为交易空间的优势得以体现。那些“终日托迹茶肆品茗纵谈,一遇机缘即四处钻营冀达成交目的”(63) 的房地产掮客,也纷纷来到春风得意楼。当然,邑庙内的茶楼还常开“鸟会”。每月初十、二十、三十及周日,鸽笼“陈列在大殿前右偏月台上(东楼茶馆外——引者注),任客观看。不论卖出买进,或转卖买回,只要双方同意,便可交易。东楼也不取分文佣金的”(64)。这类鸟会在得意楼、桂花厅、赏乐楼也出现过。
城隍庙社区历来是商人们觊觎的风水宝地。各业公所享有造屋出租权后,城隍庙社区逐渐成为县城商业的荟萃之所,以庙园为中心的邑庙市场,更成了“国货”的买卖中心。比起大机器生产的近代意义的“国货”,邑庙市场的“国货”带有更多传统色彩:有明清上海县志中提到的金鱼、蛇、蟋蟀、天竺,水仙等地方物产,也有清末民初被收入县志的全新物产,如豫园内的象牙雕刻品、笺对,豫园养素轩出品的治疗咳嗽的肺露,邑庙西辕门隆顺馆的素面和邑庙大门内的酒酿(65)。1928年出版的《上海城隍庙》为我们列举了“邑庙出品”(象牙、图书石、骨牌店、镀金饰物批发所、镌业、耍货批发、传神、点痣、刀枪、班鼓店)、“邑庙特产”(梨膏糖、海礳石、油面筋、扯铃、蛇胆、弹弓),从中,我们能清晰感到邑庙市场的独特之处。而放眼城隍庙的特色小吃,酒酿圆子、平望面筋、素面、糖炒栗子、徽州饼等,哪样不是传统口味?在“洋货”充斥中国市场的当时,“传统”隐含在“国货”中成为振奋人心的话语,于是,城隍庙社区的商业地位被人为拔高:“今日之改良,以后之设法,能多着力,则此集中国货之地点,自不难将来成为极大之劝业场,于全国有莫大之关系。此为曾到城隍庙观察者之所公认者也。”(66)
如果说庙园一度是文人雅集的所在,民国以后的邑庙市场则展示了它大众化的一面。1919年,邑庙中的大小摊头已达二千余处(67),一些大众化的传统物件往往依托摊头交易,正是这些摊头和摊中物件赋予了邑庙市场独一无二的特色。民国以后,邑庙市场小商品交易已颇具规模,可以说,城隍庙小商品市场的传统从那时就已形成。
“邑庙游客,半数无事忙。”(68) 于是,娱乐是城隍庙社区的另一大功能。
从各时期的县志来看,城隍庙社区是上海岁时年节活动的最大承办地。这种节庆空间的形成源于城隍信仰,却又超越信仰进入到民俗层面。晚清以后,城隍庙社区的岁时活动,无论形式还是参与对象更趋大众化。“城隍庙内园以及萃秀点春诸胜处,每于朔望拔关,纵人游览。正月初旬以来,重门洞启,嬉春士女,鞭丝帽影,钏韵衣香,报往跋来,几于踵趾相错,肩背交摩。上元之夕,罗绮成群,管弦如沸,火树银花,异常璀璨。园中茗寮重敞,游人毕集。”(69) 原属士绅阶层风雅活动的游园和观花会,到同光时期也逐渐演变为大众娱乐。不少寓沪文人提到豫园花会:“二月在船舫厅者为兰,三月在内园者为蕙”(70),届时“湘江佳种,罗列满堂。别其种类,品其高低……其有得居手镯者,同人咸啧啧称为状元。如是者凡三日,三日中男女老少,负贩肩挑,鳞集麇萃,汗气熏蒸。竹屋纸窗,无异鲍鱼之肆。”(71) 而王韬在提及九月中旬设于萃秀堂外的菊花会时也以为“佳者殊鲜,所集之人,率皆市侩,罗腥膻,杂丝肉,以夸宴赏。渊明有知,定当捧腹”(72),反映出的正是送菊参赛者和观赏者的大众化(73)。《上海县续志》抛弃原有的风俗节日,将豫园花会列入“岁时”,是对城隍庙公共活动空间的再度认同。
不提茶楼,城隍庙的娱乐中心地位便不得成立。“茶寮每有说书人,海市蜃楼幻作真。一扇一瓯聊佐讲,偷闲争听味津津。”(74) 拥有众多茶馆的城隍庙社区是沪地书场的集中地。庙园中的春风得意楼、柴行厅、群玉楼、四美轩等有着悠久的“书场史”。晚清以来,有名的评弹艺人,如苏州光裕社、润余社的艺人大多先被网罗到城隍庙的书场,而那些初来乍道的艺人,只有在邑庙书场被老资格的听众认同了,方能走红沪上。所以,称邑庙书场是“弹词家的发迹地”毫不为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期间,光裕社和润余社先后发起义务说书以捐助各类革命运动,柴行厅等邑庙书场成了他们的活动基地(75)。
楼阁中有传统的戏剧艺术,楼阁外有大众化的民间杂艺。“在桂花厅的面前,有一方空地,常有卖艺的北方人,设场在这里……文有大小套之中西戏法,武有各种柔软工夫。此外还有走绳索,耍花坛,与扬州女子的唱小调,倒也杂以丝竹锣鼓的交响乐……有时候,场里还有奇禽猛兽陈列在那里。”(76) 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滑稽戏,正是在这种雅俗交融的环境中形成的。与王无能、江笑笑并称“滑稽三大家”的刘春山,出生在老城隍庙。他的少年时光就是在九曲桥畔桂花厅前的说书摊旁度过的。据说,他也曾在永生堂梨膏糖店学生意,“小热昏”卖梨膏糖的口技自然也被融入滑稽戏的表演中(77)。后来的滑稽巨星韩兰根、程笑亭等也都从城隍庙社区汲取过艺术经验与灵感。
将这些娱乐功能融于一身的是诞生于1918年的“小世界”。这个一度经营不善的劝业场,经“大世界”创办者黄楚九的妙手,一跃成为仅次于租界“大世界”的沪南“小世界”。多少南北曲家从这里开始了他们曲折的艺术生涯,京剧名伶孟晓冬、申曲名家丁少兰、丁婉娥,都曾在此粉墨登场。1922年11月13日,路过上海的爱因斯坦游览了城隍庙,到“小世界”观看昆剧也是日程之一,可见“小世界”在当时老城厢的娱乐中心地位。1928年的《上海城隍庙》打出广告“中国第一游戏场”小世界:“有京戏、有新剧、有说书、有滩簧、有魔术、有电影、有三弦拉戏、有奇禽怪兽、有百货商场、有新鲜空气、有清雅布置。总之,是城南最广大,最完备,最清雅,最有价值的公共娱乐处。”口气虽大,却是无可厚非。
当然,在这样一个多功能的公共活动空间中,也会充斥着社会的另一面。大殿前替人看相的,茶馆里兜售假药的,隐秘处伸“第三只手”的,最“壮观”的是遍布各处“吃百家饭”的。《上海轶事大观》的作者陈伯熙“偶游邑庙,见道旁乞丐男者、女者、老者、幼者、残废者、聋哑者纷呈眼前,或坐地乞怜,或纷随要索,甲去而乙来,乙得而丙至,苦缠不已,环视四周,殆无处无乞丐”(78)。上海丐帮以城隍庙为大本营,同治七年承粮庙园的21家行业公所中就有“花神楼丐头”(79)。乞丐的聚积,从侧面印证了该社区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属性。
伴随城隍信仰的功能嬗变,近代城隍庙社区经历了大众化、商业化的过程。这一社区氛围的形成是各种时空因素的交汇与互动,最终呈现出一种独特且多元的空间气质。然而,随着商业文化的日益强势,主导城隍庙社区发展的力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再度易手。正如火雪明在《上海城隍庙》中所言:“到城隍庙来烧香,果然是名副其实的分内事,但只有烧香客在那里兜圈子,怕也不能造成这么热闹的大场所。所以造成热闹的肥料,只属于商店和摊头,可以占到大半的力量。换句话说:城隍庙假如没有商店与摊头,也会像南京路上的虹庙一般清淡。”(80) 上海地区日益浓厚的商业文化席卷城隍庙社区,削弱了信仰在其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终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提出:“故不问现代宜否神道设教,而尽力从事于整理,变陈旧为新颖,变狭陋为壮观,非仅仅如普通之点缀,其意亦曰:‘我齐将以吸引更多之游客,如先施等之有屋顶花园也。谁能谓为无意识!’城隍庙果可以能吸引更多之游客而归功于商场乎。”(81)
然而,信仰真的远离了吗?
城隍信仰不再是城隍庙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但作为原动力的“信仰”并没有远离社区发展。1995年春节,上海城隍庙中断了30年的香火重又兴旺,从除夕到正月初三进庙者4万多人,全年更达40万人次(82)。10年来,城隍庙社区日新月异,庙与信仰在其中的贡献不容忽视,而随着各类民间信仰活动的回暖,庙、信仰和社区之间的互动,必将成为更具现实意义的课题。
收稿日期:2006—10—11
注释:
① 沈善昌:《邑庙风光》,1946年版,第13页。
② 因庙有井,水味淡而不咸,故名。
③ 《弘治上海志》卷四。
④ 金山卫城隍霍光在上海县的行祠。
⑤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诏封天下州县城隍。相传,上海县城隍秦裕伯由他亲点,未见正史,惟秦氏后裔据族谱所记认定,后人多认为确实。
⑥ 即《弘治上海志》、《嘉靖上海县志》和《万历上海县志》。
⑦ 参见《同治上海县志》卷十。庙内外碑文还记载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和道光十三年(1833),邑人分别重修庙殿、班房等事迹,见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3页。
⑧ 曹一士:《小灵台四首》,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豫园》,1962年版,第26页。
⑨⑩ 乔钟吴:《西园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豫园》,1962年版,第12页。
(11)(13)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8、37页。
(12)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十一日(公历6月19日),英军占领县城,驻城隍庙五日;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以城隍庙园为司令部,前后占据十八个月;咸丰十年(1860),苏松太道吴煦请英法军队进城协助防守太平军,驻扎于城隍庙,庙园严重被毁。
(14) 上海豫园办公室编:《上海豫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41页。
(15)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16)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页。
(17)(19) 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86、94页。
(18) 《上海县续志》卷12。
(20) 《光绪上海县志》卷2。
(21) 吴灵园:《上海城隍庙》序2,见火雪明《上海城隍庙》,青春文学社1928年版。
(22) 《申报》1926年12月7日。
(23) 《民国上海县志》卷二。
(24) 《申报》1927年12月19日。
(25) 上海市通志馆年鉴委员会编:《上海市年鉴S宗教》,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5页。
(26) 《申报》1927年10月25日。
(27)(28)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1—82、82页。
(29)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557页。
(30)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534页。
(31) 《同治上海县志》卷10。
(32) 1839年的《沪上岁时衢歌》“三巡会”条目下还提到“邑厉坛,令宰有举祭之典,每岁于三元节遵行之”。
(33) 胡祥翰等:《上海小志 上海乡土志 夷患备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34)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5) 葛元煦等:《沪游杂记 淞南梦影录 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111页。
(36) 胡祥翰等:《上海小志 上海乡土志 夷患备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页。
(37)(38) 葛元煦等:《沪游杂记 淞南梦影录 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111页。
(39) 刊印于1906年的《沪江商业市井词》和撰成于1909 年《上海竹枝词》中都提到“三巡会”的情景。见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95、425页。
(40) 参见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神会”一诗的案语,第278页。
(41) 1927年邑庙重建后,“三巡会”的组织操办多由黄金荣等帮会分子把持,彻底偏离了“三巡会”的原旨。
(42)(43) 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4、437页。
(44) 王韬:《瀛壖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45) 姚廷遴:《历年记》,《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46) 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19页。
(47)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81页。
(48) 《新闻报》1925年6月2日。
(49) 城隍庙社区在进入近代以后,逐渐丧失政治公共空间的功能。这与老城厢地区的整体边缘化有关,也与社区大众化、商业化的趋向有关。当然,城隍庙园公所、商铺遍地,缺乏开阔的空间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50) 钱化佛口述,郑逸梅撰:《三十年来之上海》续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
(51)(53) 爱狄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包玉珂编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版,第30—31页。
(52)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513—515页。
(54) 黄可:《上海美术志札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
(55) 它们是笔花楼、丽云阁、二雅堂、艺兰堂、瑞芝阁、九经堂、黄仁昌、翼雅堂、漱墨斋、青莲室、蔡仁昌、萃华堂、十二楼、得月楼、丽华堂、耀华堂、萃新阁、益锦堂、槐荫堂、堃华堂、饱墨斋、椿华堂。
(56)(57)(59) 火雪明:《上海城隍庙》,青春文学社1928年版,第75、74、40页。
(58) 阿英:《城隍庙的书市》,载倪墨炎编《浪淘沙——名人笔下的老上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60) 参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附录:清代上海主要会馆公所一览,第507—511页。
(61)(64)(68) 火雪明:《上海城隍庙》,青春文学社1928年版,第50、36、18页。
(62) 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
(63) 陈炎林:《上海地产大全》,1933年版,第376页。
(65) 《上海县续志》卷8。
(66) 吴灵园:《上海城隍庙》序2,见火雪明《上海城隍庙》,青春文学社1928年版。
(67)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58页。
(69)(72)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
(70)(71) 葛元煦等:《沪游杂记 淞南梦影录 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119—120页。
(73) 大众化也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这类活动。《沪竹枝词》(1874年)中有“豫园花会更翻新,士女嬉游到点春。行过湖山桥九曲,弯环恰遇意中人”,《沪江商业市井词》(1906年)中有“假山矗立点春园,每届花辰始启门。裙屐翩翩来此地,登高风月细评论”等。见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74) 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75)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1页;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00页。
(76) 火雪明:《上海城隍庙》,青春文学社1928年版,第52页。
(77) 上海市文化局史志办公室编:《上海滑稽戏志》,1997年版,第152、169页。
(78) 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79)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4页。
(80) 火雪明:《上海城隍庙》,青春文学社1928年版,第40页。
(81) 吴灵园:《上海城隍庙》序2,见火雪明《上海城隍庙》,青春文学社1928年版。
(82) 张化:《上海宗教通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