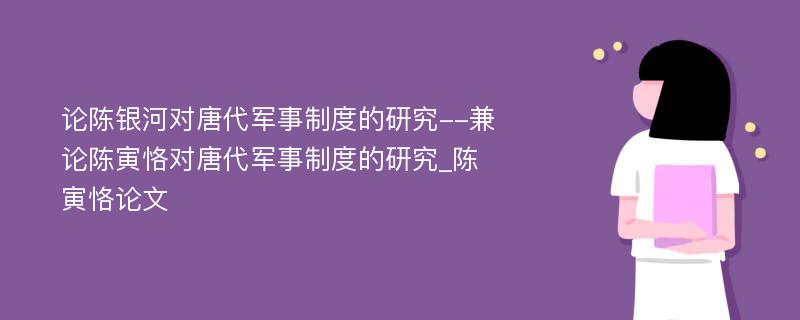
论陈寅恪对唐代兵制的研究——Eyes on Chen yinke#39;s Research on Military Institution in Tang Dynasty,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兵制论文,唐代论文,陈寅恪论文,Chen论文,Eye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成书于1979年的《剑桥中国史》第三册隋唐篇(上)之绪论中,道出唐朝“这个复杂的时期”,对无论中国学者、日本学者、西方学者都自有其吸引力;而尤称重陈寅恪对“解释这时期政治及制度史有重大贡献”。本文遂拟就通过探讨陈氏对唐代兵制之研究,见其研究方法及成就。
1937年,陈寅恪发表《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此文后收入1946年出版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1957年,陈氏发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其中论点,颇引起学者不同的讨论:王树椒、杜洽、岑仲勉、谷霁光、贺昌群、章群等诸家均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的讨论,更有利于分析陈寅恪对唐代兵制之研究。诸家之不同意见,计有下列三项:
一、府兵制是否出于鲜卑兵制?言府兵制最详之《邺侯家传》中所谓“六户”、“六家”二词定义为何?
陈寅恪云:
府兵之制,其初起时实摹拟鲜卑部落旧制……为部酋分属制。 〔1〕其因则出于宇文泰承当日鲜卑族反对汉化之风气,遂杂糅鲜卑部落制与汉族周官制,以笼络其部下之汉族,与高欢对抗:
北魏晚年六镇之乱,乃塞上鲜卑族对于魏孝文帝所代表拓跋氏历代汉化政策之一大反动,史实甚明,无待赘论。高欢、宇文泰俱承此反对汉化保存鲜卑国粹之大潮流而兴起之枭杰也。宇文泰当日所凭藉之人材地利远在高欢之下,若欲与高氏抗争,则惟有于随顺此鲜卑反动潮流大势之下,别采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笼络其部下之汉族,而是种汉化又须有以异于高氏治下洛阳邺都及肖氏治下建康江陵承袭之汉魏晋之二系统,此宇文泰所以使苏绰、卢辩之徒以周官之文比附其鲜卑部落旧制,资其野心利用之理由也。苟明于此,则知宇文泰最初之创制,实以鲜卑旧俗为依归;其有异于鲜卑之制而适符于周官之文者,乃黑獭别有利用之处,特取周官为缘饰之具耳。八柱国者,摹拟鲜卑旧时八国即八部之制者也……而宇文泰既思提高一己之地位,不与其柱国相等,又不欲元魏宗室实握兵权,故虽存八柱国之名,而以六柱国分统府兵,以比附于周官六军之制。此则杂糅鲜卑部落制与汉族周官制,以供其利用,读史者不可不知者也〔2〕。王树椒则认为兵众并非柱国所私有,故不能谓府兵制为部酋分属制:
六开府所领为一万二千人,则一军为二千人,二十四军共为四万八千人,《邺侯家传》所谓共有众不满五万,是也。盏盏五万之众,分属诸六柱国,则一柱国所统才八千人;且无事则兵散为农,即此八千之众亦不为柱国所私有。谓之部酋分属制者,非也〔3〕。而王氏别提一说,谓府兵制乃来自北魏番戍制,而非鲜卑兵制〔4〕。此外,谷霁光亦有相近之见解,认为府兵制之主要渊源,并非鲜卑部落之制:
陈寅恪先生以为府兵兼采鲜卑部落之制及汉族城郭之制,其说法尚欠全面。封建兵制应该是府兵制的主要渊源和内涵,鲜卑部落兵制只是某些遗留因素和影响,二者结合后形成为具有新的特点的府兵制。过分强调鲜卑部落之制,是不适当的。陈先生着重从八部及赐姓等方面探索鲜卑部落之制,太多地着眼于形式,其实八部与八柱国只是一种偶合,有如汉置八校,南齐置八镇、八安,强相比拟,不足以阐明问题的本质,其实除陈先生所提出的部族色彩外,番役自备资粮和番第的规定,亦属府兵制显著的特点。鲜卑兵制从部族、资粮、番第三个方面给予府兵制以重大影响,却没有也不能压倒作为主流的封建兵制,封建化是拓跋族进入中原后的基本趋向,府兵制亦不会逾越这一轨辙。〔5〕陈氏自然是知晓“封建化是拓跋族进入中原后的基本趋向”,其谓:
北魏晚年六镇之乱,乃塞上鲜卑族对于魏孝文帝所代表拓跋氏历代汉化政策之一大反动,史实甚明,无待赘论。〔6〕即是。六镇之乱,正是六镇人极度不满拓跋族进入中原后不断封建化的表现。而单单强调府兵制之后期趋向封建化,实不足以否定府兵制之前期实具有部落兵制之色彩。
所以,谷氏在修正陈说之同时,亦罗列出鲜卑兵制对府兵制之具体影响。另一方面,谷氏认为八部与八柱国只是一种偶合,是其直接否定陈氏“宇文泰特取周官为缘饰之具”说,即对陈氏“关中本位政策”不以为然,是二氏治史各有通则也。
另一方面,岑仲勉虽同意府兵制源出鲜卑兵制,却不同意陈氏的解释:
又近世出土墓志,发现北齐许多兵府名号,如非东,西魏同承北魏,无缘两朝制度甚相类。由是知陈氏称宇文泰别采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异于高氏之系统,不尽合于事实。〔7〕
《邺侯家传》乃言府兵制最详之唐人著述,所称府兵之选拔,出“于六户中等已上”家,“六户”一词,颇有歧义。
陈寅恪释“六户”为中等以上富豪之家,即《文献通考》“六等之民”之谓:
《邺侯家传》所谓“六户中等以上”者,此“六户”与传文之“六家”不同,盖指九等之户即自中下至上上凡六等之户而言,《文献通考》一五一兵考作“六等之民”,当得其义。〔8〕
王树椒则认为“六户”是指“六家才取一人”之意:
此谓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六户而选才力者一人以充府兵也。《文献通考》兵考三改为“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材力之士以为之”,失其义矣。〔9〕
岑仲勉释“六户”为“六坊之户”:
现在要来试探“六户”是什么户了。考《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记北魏末年情况,曾论:“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及)万人,余皆北徙。”又说及“(北齐)文宣(高洋)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都以“六”为数,似乎不是偶然的。魏末,葛荣领着六镇人南下,葛荣失败后,其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显即《隋书·食货志》所说北徙之众,他们屡次抗拒,被斩杀者半数,普泰元年(公元五三一年)高欢欲图尔朱兆,诈言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以激众怒。这些六镇人既离开镇地,分散各处,已无属籍,势不能不设法安置,于是仿东晋南迁按照相随渡江民众原日的州籍在江南特设“侨州”来安置的事例,在他们流落的地面,按照他们原日的镇别,分设六坊来管理他们。由这来参悟,毫无疑问地,六坊之人就是六镇南迁之人,“六户”就是六坊之户,六坊之户有“中等以上”、“中等以下”的区别,是自然不过的,选兵必先向六坊之户着手,也是自然不过的。〔10〕
王树椒认为“六户”是指“六家才取一人”,大概是因为《邺侯家传》中有“六家共备”一语。陈寅恪则主张“六家”实指“六柱国家”;并非“六户”之意:
又《邺侯家传》“六家共之”之语,“共”若依通鉴作“供给”之“供”,自易明了,惟“六家”之语最难通解……鄙意通鉴采用《邺侯家传》已作“六家”,故“六”字不得视为传写之误。然细绎李书,如“六家主之”及“自初属六柱国家”等语,其“六家”之语俱指李弼等六家,故其“六家共备”之“六家”疑亦同指六柱国家而言也。《北史》云:“甲槊戈弩并资官给”,李书既以府兵自初属六柱国家,故以“六家供备”代“并资官给”,观其于“六家共(依通鉴通作供)备”下,即连接“抚养训导,有如子弟”之语,尤足证其意实曰六柱国家。〔11〕总之,府兵制源出鲜卑兵制之说法大概可信,虽则或说明各异,惟异议意亦非峻,不过是程度问题罢了。
另一方面,陈氏以为“六家”即“六柱国家”,宇文泰“以六柱国分统府兵,以比附于周官六军之制”〔12〕,此即陈氏所谓:
此宇文泰之新途径今姑假名之为“关中本位政策”,即凡属于兵制之府兵制及属于官制之周官皆是其事。〔13〕而“关中本位政策”又是陈氏治唐史之系统之一。见陈氏虽释“六户”一名词耳,是注意到此释义必须先与其“自成一家之言”之系统扣紧,前后照应,并非只就个别事实考证,亦是陈氏史法特色之一也。
二、府兵制究竟是“兵农合一”抑或“兵农分离”?施行二百年间曾否增损?
陈寅恪云:
府兵制之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部酋分属制,为特殊贵族制;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君主直辖制,为比较平民制。其前后两期分划之界限,则在隋代。〔14〕是其认为府兵制由兵农分离至兵农合一,是实经增损者;并又指出其主张府兵制未曾增损之原因,是由于隋以前有关府兵制之史文缺乏,而唐人之言,又未堪足信之故:
府兵之制起于西魏大统,废于唐之天宝,前后凡二百年,其间变易增损者颇亦多矣。后世之考史者于时代之先后往往忽略,遂依据此制度后期即唐代之材料,以推说其前期即隋以前之事实,是执一贯不变之观念,以说此前后大异之制度也,故于此中古史最要关键不独迄无发明,复更多所误会。夫唐代府兵之制,吾国史料本较完备,又得日本养老会之宫卫军防诸令条,可以推比补充,其制度概略今尚不甚难知。惟隋以前府兵之制,则史文缺略,不易明悉,而唐人追述前事,亦未可尽信。〔15〕王树椒与岑仲勉俱主府兵制行之二百年未曾增损,无根本之变迁。惟王氏认为府兵制始终是“兵农合一”,而岑氏则认为府兵制始终是“兵农分离”。辩府兵制中之兵农关系,应自《邺侯家传》“郡守以农隙教试”一语开始。
陈寅恪指出,《邺侯家传》不过是依唐时兵农合一的情况推想唐以前事耳,所言未可尽信:
据《北史》六十“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及“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等语,则《邺侯家传》所谓“郡守农隙教试阅”者,绝非西魏当日府兵制之真相,盖农隙必不能限于每隔十五日之定期,且当日兵士之数至少,而战守之役甚繁,欲以一人兼兵农二业,亦极不易也。又《北史》谓军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则更与郡守无关,此则《邺侯家传》作者李繁依唐代府兵之制,以为当西魏初创府兵时亦应如是,其误明矣。李延寿生值唐初,所记史事犹为近真。温公作通鉴,其叙府兵最初之制,不采《北史》之文,而袭《家传》之误,殊可惜也。〔16〕王树椒则直信《邺侯家传》之记载:“《邺侯家传》谓‘郡守以农隙教试’。《文献通考》兵考三谓‘刺史以农隙教之’,府兵盖以三时务农而暇日教以攻战,其兵农不分与北魏番戍兵旧制同”。〔17〕是王氏认为早在唐以前,府兵制已是“兵农不分”,甚至“兵农未分”〔18〕。
另一方面,岑仲勉虽然同意陈寅恪辩“郡守农隙教试阅”之误〔19〕,却不同意陈氏认为府兵制是由“兵农分离”演至“兵农合一”。岑氏认为府兵制是始终的“兵农分离”〔20〕。对于陈寅恪引《通典》证府兵制已推广及于设置军府地域内全部人民说不大为然:
陈氏《述论稿》又引《通典》六龙朔三年七月制:“卫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军,仍免庸调”(陈引误为“每年放还,令出军”),谓八等指户籍等第,“然则此制与其初期仅籍六等以上豪户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广及于设置军府地域内全部人民之确证也”。按六“户”非六等以上户,已辨见前节;府兵之家既不免征徭,自然有户等之别,从何见得府兵制普及于军府地域内之全部人民?且全部人民包含各种阶级,就让一步而言,只能证为“兵民合一”,不能证为“兵农合一”。〔21〕王氏既有“华夏之民,征发以为兵,又北魏之旧制”〔22〕,且视北魏兵制乃府兵制滥觞之见,则陈寅恪以周武帝改民籍成兵籍,藉此扩大府兵至最终“兵农合一”之说,必不获王氏认同无疑,是亦两家对府兵制之兵农关系各有所见也。陈寅恪云:
又最初府兵制下之将卒皆是胡姓,即同胡人,周武帝募百姓充之,改其民籍为兵籍,乃第一步府兵之扩大化即平民化。此时以前之府兵既皆是胡姓,则胡人也,百姓,则夏人也,故云:“是后夏人半为兵矣。”〔23〕王树椒引《隋书·食货志》:
或据《隋书·食货志》:“建德二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以为在此以前,兵人悉为胡人,斯亦不然”。〔24〕是王陈二氏对改兵籍为民籍之辩。至于陈寅恪谓改兵籍为民籍,乃周武帝时事,杜洽与岑仲勉均不表赞同。杜氏云:“今据现存史料所载,周武帝建德二年改军士为侍官事,实为府兵成立以来第一次之改革。当时充府兵之百姓,犹除民籍,隶属于军。可知武帝之改革,反使府兵制较前扩大而已,于府兵制本身,实亦无大变更。建德改制,时距隋文化周仅八年,此八年中史籍无改革事,疑后周府兵制至周亡仍存兵民各籍之制也。”〔25〕岑氏则由于以“六坊之户”释“六户”,则所见不同更远甚:“抑入关之六坊,不满万人,而西魏府兵将达五万,其间显曾取汉人为之扩充,非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云始自周武”。〔26〕
陈寅恪认为周武帝时,改兵籍为民籍,“乃第一步府兵之扩大化即平民化”,而陈氏据高齐河清三年定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27〕。遂“疑北齐当日实已施行兵民合一之制”〔28〕:“盖后期府兵之制全部兵农合一,实于齐制始见诸明文,此实府兵制之关键也。但当时法令之文与实施之事不必悉相符合”。〔29〕岑氏却认为高齐“兵农合一”之说并无根据,盖所谓“二十充兵”的“兵”是指“力役”,不是指“府兵”〔30〕。由于对“兵”字定义不同,陈岑二氏对北周保定元年三月“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一令遂有不同理解。胡三省以“境内民丁”释“丁兵”,陈氏以为胡氏“绝不一及兵字,其意殆以为其时兵民全无区别,与后来不异,则疑有未妥也。”〔31〕陈氏言下之意,北周府兵为兵民分治,还未演至后来“兵农合一”。岑氏既主“兵”即“力役”,与“丁”无异,则北周保定元年三月“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一令,“皆属于庸役之制,于府兵无关”〔32〕,“陈氏误会以为改制”而已〔33〕。
对于隋代府兵的情况,陈寅恪以为较诸北周、隋代府兵制是进一步的“禁卫军化”及“兵农合一化”。〔34〕岑氏则指出:“若以为‘隋代府兵制变革之趋向,在较周武帝更进一步之君主直辖化即禁卫军化’,则不知‘门栏陛戟,警昼巡夜’,称作侍官,魏、周时已是这样的了。”〔35〕至于陈氏说明隋代府兵制是进一步的“兵农合一化”,是取北周保定元年令文胡注中“境内兵民合一”之义以解释开皇三年及十年之令文,以此陈氏来说明“兵农合一”成于隋世:
隋文帝开皇十年诏书中有“垦田籍帐悉与民同”之语,与《北史》所载府兵初起之制兵士绝无暇业农者,自有不同。此诏所言或是周武帝改革以后之情状,或目府兵役属者所垦,而非府兵自耕之田,或指边地屯垦之军而言……隋文帝使军人悉属州县,则已大反西魏初创府兵时“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即兵民分立之制,其令“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及“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隋书》二四食货志)。虽实施如何,固有问题,然就法令形式言,即此间略略记述或已隐括北齐清河三年规定受田与兵役关系一令之主旨,今以史文不详,姑从阙疑。但依《通鉴》至德元年之胡注,则隋开皇三年令文与周保定元年令文“八兵丁”及“十二丁兵”显有关系。而开皇三年令文《隋书》所载有“军”字者,以开皇十年前军兵不属州县,在形式上尚须与人民有别,故此令文中仍以军民并列。至《北史》、《通典》以及《通鉴》所载无“军”字者,以其时兵民在事实上已无可别,故得略去“军”字,并非李延寿、杜君卿及司马君实任意或偶尔有所漏明矣。
由是言之,开皇三年令文却应取前此保定元年令文胡注中境内兵民合一之义以为解释也。夫开皇三年境内军民在事实上已不可别,则开皇十年以后,抑更可知,故依据唐宋诸贤李、杜、马、胡之意旨,岂可不谓唐代府兵之基本条件,即兵民合一者,实已完成于隋文之世耶?〔36〕
陈氏的上述观点曾引起几次讨论:
(一)关于开皇十年诏书中“垦田籍帐悉与民同”一语,陈氏以为“史文简略,不能详也”,所谓“垦田”,或是府兵自耕,或是雇人代耕,或是指边地屯垦之军。岑仲勉则指出开皇十年诏书中有“坊府”之称,而当时兵制,唯府兵系统才有“坊府”之称,故是针对府兵而言,与边地屯垦军无关〔37〕:“其所以误认为兵民合一者,无非先误解‘垦田’为府兵自耕之田,作出隋时府兵有暇业农与西魏时府兵无暇业农的错误对照。”〔38〕从而认为开皇十年的命令“对于府兵地位,毫无变更”〔39〕,强调其一贯主张府兵制未尝兵农合一,施行二百年间亦未尝有所增损之见解。实则陈氏并未确定“垦田”为府兵自耕,反而道出由于史文简略,故不能详之语。
(二)关于开皇三年的令文,《隋书》载有“军”字,《北史》、《通典》、《通鉴》均无“军”字,文称:“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40〕岑仲勉认为《北史》、《通典》、《通鉴》不记“军”字,是一书误脱,他书承之使然。岑氏指出由于军民俱可受田,而“成丁”又是受田的年限,是故成丁年龄之改定必须军民并提。史书行文相承失察,根本并无暗示府兵制“兵农”关系之意〔41〕。
(三)陈寅恪以为“开皇三年境内军民在事实上已无可别”〔42〕,却又云:“开皇三年令文《隋书》所载有‘军’字者,以开皇十年前军兵不属州县,在形式上当须与人民有别,故此令文中仍以军民并列。”〔43〕似乎陈氏对开皇三年或十年之说,颇为游移,故岑氏讥之尤甚:“明明‘军’与‘民’分掌,陈氏竟解为‘境内兵民合一’,是陈说已内在矛盾。如果开皇三年军与民已无区别,又何需如陈氏所解释至十年而特令合一。”〔44〕杜洽亦不信开皇三年之说:“陈寅恪先生断其始在开皇三年,似尚不足信,而开皇十年以后,则已成合一之制。”〔45〕至于开皇十年后军人的籍属问题,陈氏既有“开皇十年前军兵不属州县”之语,意即开皇十年后军兵籍属州县,亦即其所主兵民合一、兵农合一之意也;另方面,岑氏亦本其府兵制未尝兵农合一之见云:“开皇十年以后府兵只编入民籍,领导仍属于军府而非属于州县。”〔46〕惜岑氏此论点并未援引证据以证明,真不知何所据而云矣。
总之,岑仲勉是反对府兵制曾“兵农合一”之说,盖岑氏以为点兵之家不尽是农家;陈寅恪引魏征“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之语推证唐人身兼充兵务农二业,岑氏的意见是:“按唐代无论士农工商都可受田,既享受田的权利,自然应尽纳租赋的义务,点府兵之家不见得定是农家,尤其纳租赋之家更不尽是农家,拿未充府兵时须纳租赋的条件来断定兵农合一,恐说不过去吧。”〔47〕是岑氏贯彻其“军民从来有别”之说也。较之汤承业之“府兵制之后期所谓‘兵农合一’者指‘平时’也,‘兵农分离’者指‘战时’也。”〔48〕未知何如?
另一方面,岑氏对“农”之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较有“土地与人民结合”的意思〔49〕。贺昌群就认为言兵农关系,不能不联结土地而言:
用兵民分离或兵农合一的框框来看汉、唐间土地关系与封建军事的关系,不能说明这段历史时期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发展的过程,原因就在于不能说明这里的“兵”是什么样,“农”是什么样的阶级地位。
如果把汉、唐间自由民的身份和封建依附的从属身份区别开来认识“兵”与“农”的阶级地位,那末,皇帝的近卫兵从来就不曾与“农”分离过……反过来说,如果把汉、唐间自由民的身份和封建依附的从属身份区别开来,那末,汉、唐间始终不曾有过“兵农合一”的事实……,直到唐玄宗时代安史之乱前后,公田制形态起了变化,近卫兵制由招募而不由征选,成立所谓彍骑,这种自由农民与土地相结合的军事制度(即汉晋以来的羽林、虎贲等,北朝的八柱国、六柱国等,总结而为隋唐的府兵),才大体告一段落。
……安史之乱前后,唐的中央政权已不能掌握大量的公田,土地转入于大土地主之手,这些大土地主,就是藩镇、节度使庄园主等,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这样,府兵就逐渐脱离了土地,失去其存在的积极因素……离开了他们和土地的关系,而泛言“兵农合一”或“兵农分离”,是没有历史内容的说法……而今天却有人用超阶级的兵民分合的观点来看府兵问题,便不对了。〔50〕。如果从土地角度看问题,则陈寅恪从文化种族观点而析出的、以府兵制为最主要的“关中本位政策”〔51〕面貌了,贺昌群云:
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说:“在‘关中本位政策’犹未完全破坏以前,凡操持关中主权之政府即可以宰制全国,故政治革命只有中央政治革命可以成功,地方革命则无论如何名正言顺,终归失败,此点可以解释尉迟迥、徐敬业所以失败,隋文帝、武则天所以成功,与夫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卒丧邦家,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迨玄宗之世,‘关中本位政策’完全改变,所以地方政治革命始能成功,而唐室之衰亡实由于地方政治革命之安、史、庞勋、黄巢等等起事。”……我以为唐统治者内部的中央政变和地方政变的成功与失败,应当从社会经济基础去理解,那末,这段话就比较明白了,便是说:建都于长安的西魏、北周、隋、唐的封建政权,由于在关中畿内掌握了大量的公田,施行均田制和计口授田,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府兵制,府兵的政策是强杆弱枝,重内轻外,把重兵置于关中,因而中央一旦政变,如李世民(太宗)玄武门之变,李隆基(玄宗)之平韦氏等,都由于迅速在长安宫廷取得了全国军政大权,便很快控制了全面,直接号令全国,这是隋末唐初百年间中央政变所以成功而尉迟迥、徐敬业地方政变所以失败之故。及至开元、天宝之际,两京国有土地——公田逐渐为大土地占有者所兼并,中央政府不能握有大量公田,内重外轻的形势倒置,均田制与府兵制亦随之渐次解体,安、史之乱便促成唐王朝内部的分裂,藩镇割据。〔52〕
三、府兵战斗力之估计及蕃将问题。
陈寅恪于1957年发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53〕,最先注意到唐代蕃将的问题〔54〕,惟亦引起后世学者有不同之论。章群的《唐代蕃将研究》可说是最全面讨论陈氏对唐代兵力观点的著作。兹集中于府兵的战斗能力及唐用蕃将的演变两方面的商榷。
先商榷府兵的战斗能力。
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引《贞观政要》记魏征的话而谓太宗时之府兵实不堪攻战〔55〕,是故在贞观四年以前,实以“山东豪杰”集团为其主要兵力〔56〕。章氏则观乎贞观四年以后的多场战役,认为府兵仍有其战斗能力:
从贞观五年到二十三年(631-649),因战争或备边,发各州兵者五次,唐代的地方兵,不外乎驻屯与征调两个系统,征调系统指各地的折冲府而言,而驻屯的军城守提之兵,实际上仍来自轮戍的府兵。贞观十九年(649),发各州兵以备薛延陀,以江夏王道宗所发者为例, 有朔、并、汾、箕、岚、代、忻、蔚、云九州之兵……请问这些所发之兵,非府兵而何?或者说,既是备边,并不能证明其是否能作战。试以同一年(649)的高丽之役为例,参与者有折冲都尉曹三良, 果毅马文举及傅伏爱(《通鉴》198卷第6222-6230页)。此役虽有小挫, 大体上可称全胜,足以证明府兵的作战能力。〔57〕其实,陈氏之所谓府兵“不堪攻战”,不过是相对于善于骑射之蕃兵而言耳。陈氏云:“蕃将之所以被视为重要者,在其部落之组织及骑射之技术。”〔58〕府兵演变至后期已“兵农合一”如陈氏说,农家安土重迁、且兵事业余耳,整个社会组织既非部落之组织,战斗力自非以骑射为善,却并非代表全无战斗力之可言也。章氏以649 年高丽一役证明府兵之战斗能力,适足说明府兵在面对非善骑射之族如高丽确仍有其战斗力,陈氏所称府兵“不堪攻战”,不过是指府兵之骑射术不若部落组织之蕃兵而已;对付非善骑射之高丽族,仍是有其作战能力的,一如章氏所言。
再商榷唐用蕃将的演变。
陈寅恪云:“至于蕃将,则世之读史者,仅知蕃将与唐代武功有密切重要关系,而不知其前期之蕃将与后期之蕃将亦大有分别在也。今请先论李唐开国之初至玄宗时代之蕃将。玄宗后之蕃将问题,则本文姑不涉及。”〔59〕
又云:“太宗所任之蕃将为部落酋长,而玄宗所任之蕃将乃寒族胡人……太宗既任部落之酋长为将帅,则此部落之酋长必率领其部下之胡人,同为太宗效力。功业成后,则此酋长及其部落亦造成一种特殊势力,如唐代中世以后藩镇之比。至若东突厥败亡后而又复兴,至默啜遂并吞东西两突厥之领土,而建立一大帝国,为中国大患。历数十年,至玄宗初期,以失政内乱,遂自崩溃。此贞观以来任用胡族部落酋长为将领之覆辙,宜玄宗以之为殷鉴者也。职此之故,玄宗之重用安禄山,其主因实以其为杂种贱胡。哥舒翰则其先世虽为突厥部落酋长,然至翰之身,已不统领部落,失其酋长之资格,不异于寒族之蕃人。是以玄宗亦视之与安禄山相等,而不虑其变叛,如前此复兴东突厥诸酋长之所为也。由是言之,太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所统领之诸种不同之部落也。”〔60〕
陈氏以为“部落酋长”与“寒族胡人”之定义,前者在率同部落,后者则属个别投募。章氏则认为,个别投募的蕃将,不一定是塞族胡人:“陈氏只看到有部落与无部落之分,而不知有边族蕃与西域胡之分。西域胡入唐为将,本无部落,陈氏也不知道安禄山本是西域胡,而又将之与部落酋帅比观,遂以为安氏是寒族胡人”。〔61〕陈氏有《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62〕,称安禄山为杂种胡,即中亚昭武九姓胡,是陈氏“知道安禄山本是西域胡”;而哥舒翰之例,诚属个别例子,却不足以言陈氏不观蕃将问题之演变。讨论演变而又扣紧系统,必须先立乎其大者。陈氏论唐代蕃将止于玄宗朝,并非忽略蕃将问题之“演变”,而是扣紧其治唐史所称“关中本位政策”之系统而出之。府兵制既是“关中本位政策”之最主要者,又与此政策相始终于玄宗朝;而用蕃将戍边又是府兵制破坏以后的事〔63〕,即是“关中本位政策”崩溃之后事。故以“关中本位政策”为系统讨论唐史之陈氏,其言蕃将问题于止玄宗朝,断不能视为忽略演变之说也。
何况,从另一角度言,陈氏言蕃将问题之演变,是一本其种族文化释史之观点分析:
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而安史以蕃将之资格,根据河北之地,施行胡化政策。恢复军队部落制,即“外宅男”或义儿制。故唐代藩镇如薛蒿、田承嗣之徒,虽是汉人,实同蕃将。其军队不论是何种族,实亦同胡人部落也。延及五代,“衙兵”当是此“外宅男”之遗留。读史者综观前后演变之迹象,自可了然矣。寅恪尝谓欧阳永叔深受北宋当时“濮议”之刺激,于其所著五代史记特标义儿传一目,以发其感愤。然所论者仅限于天性、人伦、情谊、礼法之范围,而未知五代义儿之制,如后唐义儿军之类,实源出于胡人部落之俗。盖与唐代之蕃将同一渊源者。若专就道德观点立言,而不涉及史事,似犹不免未达一间也。〔64〕
陈氏释唐代军力,是不离其所谓“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65〕之史观。
总括上述三项,陈氏讨论唐代兵制之特点有三:
(一)从演变之角度观察。府兵制源出鲜卑兵制,六镇之乱正道出此种部落兵制曾经汉化之演变,终由“兵农分离”演变为“兵农合一”。府兵于“兵农合一”后不善骑射,故面对北族善骑射之辈,终至不敌而崩溃;至晚唐五代部落兵制遂告复活而有“外宅男”或“义儿制”,以应付形势之演变。
(二)从社会组织、社会集团着眼。陈氏以有无部落分类蕃将,实从社会组织角度讨论兵制。杨志玖云:
陈先生在其论文中指出,唐太宗所任之蕃将为部落酋长必率领其部下之胡人同为太宗效力,质言之,此蕃兵即为部落兵。此一由部落组成之军队,由于将领与部众之间“本为血缘之结合,故情谊相通,利害与共”,因而其战斗力“远较一般汉人以将领空名,而统率素不亲切之士卒者为优胜。”这一从社会组织角度的分析方法,非常可贵。〔66〕不同的社会组织,自有不同形态之兵制;不同形态之兵制,自有不同之战斗力。此所以谓府兵“不堪攻战”当不得实解,只相对善骑射之蕃兵而言,故面对非骑射之高丽族,府兵亦能发挥其所擅之战斗方式。例如侯景善战,盖其为北族;李自成望满洲兵而溃逃,以南人身份,不无惧与北族人战故。此亦因社会组织不同而有不同的兵制及不同的战斗力也。
至于陈氏讨论唐代兵制从社会集团着眼,众所周知,陈氏所谓“关中本位政策”乃“关陇集团”所行而以府兵制为最主要者。陈氏从社会集团之盛衰研究兵制,故有“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67〕之说;故其讨论蕃将问题亦止于玄宗朝。凡此种种,均见陈氏研究兵制之法,实属有机之组合法,并非单纯考证个别事例者。
(三)兵制实与社会其他制度互为联系。陈氏谓府兵制破坏后,“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68〕,实因科举制度兴起有以致之:
……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故科举制之崇重与府兵制之破坏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其时代之符合,决非偶然也。〔69〕
他如田制,陈氏亦不无着墨处,要之归结到文化种族之观点,盖“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70〕与持片面的经济史观者如谷书及个别事例考证如岑书,所论兵制,自属不同理解与演绎。
注释:
〔1〕〔2〕〔6〕〔8〕〔12〕〔14〕〔15〕〔16〕〔23〕〔27〕〔28〕〔29〕〔31〕〔34〕〔40〕〔42〕〔4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第131、126-129、126、 132、132-133、129、140、124、133-134、136-137、138、138、 138、137、139、139、135、139、13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 其中“兵制”一章,乃陈氏《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一文增订而成。
〔3〕〔4〕〔9〕〔17〕〔18〕〔22〕〔24〕王树椒《府兵制溯源并质陈寅恪先生”,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
〔5〕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出版。
〔7〕〔19〕〔20〕〔27〕〔26〕〔32〕〔33〕〔44〕岑仲勉《隋唐史》下册,第205、206、216、216、206、208、207、209页,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10〕〔30〕〔35〕〔37〕〔38〕〔39〕〔41〕〔46〕〔47〕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第19、26、35、37、39、39、42、42、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
〔13〕〔51〕〔65〕〔67〕〔68〕〔69〕〔7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5、18、1、18、22、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
〔25〕〔45〕杜洽《唐代府兵考》,《史学年报》第3卷,第1期,1939年12月。
〔48〕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第263页, 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年出版。
〔49〕〔50〕〔52〕吴泽主编《贺昌群史学论著选》第448、390-391、426-4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53〕〔55〕〔56〕〔58〕〔59〕〔60〕〔6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64-276、265、267、268、264、268、2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54〕〔57〕〔61〕〔63〕章群《唐代蕃将研究》第368、244 -245、246、246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出版。
〔6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52-53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66〕杨志玖、张国刚《试论唐代蕃兵的组织和作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40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