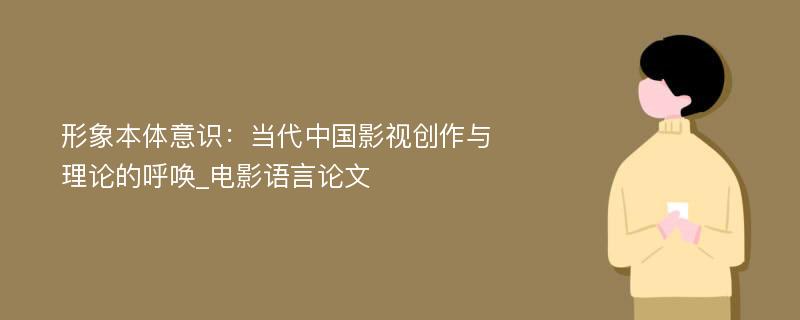
影像本体意识——中国当下影视创作与理论的召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中国论文,影像论文,意识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当下的影视创作与批评中,存在一种极普遍的显在或潜在的认同:电影是一门最接近于文学的艺术种类。基于这一“公理”,影视评论家惯于以文学批评的一套话语对影视本文“绳之以法”:剖析一部影视无非从结构安排(以文学结构为准绳)、情节对主题的倾向性暗示、细节对人物的“工笔”作用入手,甚至于以文字语法去解释影像“语言”(在西方,这种以语法学研究影像的方法盛行不久,便被符号学研究方法取代)。而与这种理论形成交流关系的影视创作实践,也一直把影视艺术的本体——影像(声音与画面),仅作为一种翻译文学细节、情节,以达到塑造人物,凸现主旨的工具。这一影视理论与创作的“文学化”倾向,势必遮蔽了影视艺术的真正本体——影像。而影像本体意识的缺席只能使影视艺术沦为文学的奴仆,一种缺乏卓然独立的审美品格的艺术种类。
其实冷静下来,也不难看到影视与文学毕竟是两门泾渭分明、绝然异质的艺术种类:一个是以抽象的文字去询唤读者头脑中的经验储存,一个是以逼真的视听“语言”去撞击受众的感官系统,两者是以完全异质的话语方式言说创作主体的审美感知和审美意识,因而两者的思维方式、叙事策略、本文结构皆相距甚远。(影视的这些要素还得受播放给予的特殊的接受状态的内在规定。如接受的不可倒逆性、接受的一次性、接受的连续非中断性等接受的被施暴状态的制约,另外,作为最终的审美实现,文学艺术基本落在文学能指层之后;而作为直接诉诸感官的视听艺术的影视,视听快感本身就是完成其审美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我们不仅要放弃影视评论中那套文学批评或者说是准文学批评的话语,更亟待建立一套尊重影视艺术本体——影像,或者说以影像研究为核心的影视理论体系。这既是理论纠正或者说建构的必需,也是中国当下影视艺术发展的召唤。
基于以上这些认识,本文试图提出影视理论的核心问题——影像意识的问题,以引起理论与创作的某种关注。
一、空间意象的营构:时间叙事的空间转换
影视作为叙事艺术,一般来说都要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故事的因果链条首先是在时间中展开,所以我把影视的这种讲述故事的线性叙事特征称为影像艺术的时间性属性,简称时间性。这种特征在电影的初始阶段便在实践中予以肯定并延续至今。不过成熟的影视艺术与非成熟的影视艺术在处理时间性的方式上却迥然有异,低劣的影视作品只能用一组组画面交待性地呈现情节发展,最终目的是把故事讲清楚;而高超的影视艺术,却善于在线性叙事的链条中寻找营构空间意象的一切机会,制造强有力的空间造型,来把故事讲得富于情绪感染。也就是说,善于把时间性叙事转换成富有视听冲击力的空间性叙事(兼有叙事能力),从而有效发挥非视听艺术不可能具备的感官震撼。这种影像意识的觉醒,在中国首先发生在以张艺谋、陈凯歌为首的“第五代”电影导演身上。
电影《红高粱》远不是以画面翻译莫言的原著,而是创造性地营构了那一片火红如血(通过滤色镜使象意象化)、高大蔽日(仰角拍摄的表意性)的红高粱的空间造型,既产生能指的感染力,又富于所指意蕴(对人文环境和主旨的暗示)。而且这一空间造型,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这也是影视影像与照相影像的差别所在),因而兼有叙事能力(用高粱渐次成片倒下暗写我爷爷和奶奶的“野合”)。这种空间转换叙事既具视觉冲击和情绪感染,同时暗写的空灵召唤着观众想象的参与而使之获得叙事的张力和反常规叙事的陌生。
张艺谋是一位善于摆脱语言思维的人(实际上,图像思维是人的天性,却被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语言思维所抑制),在“第五代”导演中也是最早发生影像意识自觉的人。他敢于且善于以电影思维大胆改写小说原著。我们不妨看看电影《菊豆》,对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的改编。小说中的大染缸在银幕上变成了大染池;小说中那些普通不起眼儿的染布,变成了高达丈余、悬挂而下、色彩艳丽、遮天蔽日的长布的屏障。这种着眼空间造型的改写,也是为后面一系列的空间化叙事提供了可能:以染轮飞速旋转、血色染布迅速泻入庞大的染池,隐喻天青与菊豆挣脱心理羁缚后性爱的奔放和欢腾;以菊豆在楼上晒布(实际是向楼下的天青倾斜长达丈余的红色染布),暗示菊豆对天青倾泻性欲的幻想。张艺谋对改编小说的选择主要是从视觉造型的角度考虑,以是否易于完成空间意象造型作为选材的主要标准之一。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分别以高粱地、手工染坊、江南的旧式宅院这些极富地域文化特征的具体小环境诱发着张艺谋的创作欲望(具体而言,是一种造型欲。这种以空间造型为侧重点的原著改编,表面看是对原著的细节偏离,而深层里,这种尊重影视内部规律的改写,实际是对原著的真正负责(从效果上负责)。由此我们也联想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搬上电视,得失所在的一些根源。说到底,大部分改编不如原著效果,关键在于没有充分调动影像手段,以为原字原句地空间译解是对中国灿烂的文学遗产的尊重,这实则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实际上,刚好相反,不去尊重影像艺术规律的对原著机械性的空间翻译而形成的效果落差才真正是对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的一种损害(损害名著积淀在老百姓心中固有的艺术想象)。
影像叙事的最基本元素还是影像造型,因而影像本体意识的自觉最先应该呈现为空间造型意识以及利用空间造型进行叙事(时间叙事的空间转换)的自觉。
二、空间的展示——经验的拆解和重构中的表意性
影视的空间造型,不要狭隘地理解成一个静止画面的造型如同照相视效,它指的实际是一组连续的互为补充(互文)来共同完成在观众心中塑造事物整体印象的镜头。对一个空间的展示,不排斥以一个长镜头完成的可能(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惯用技法),但长镜头和蒙太奇结合造型则更为自由,也更为惯用。这也是电影的空间展示与绘画的空间展示的差异处,就如W ·本杰明概括的:“画家提供的形象是一个完整的形象,而电影摄影师提供的形象则是一个分解成许多部分的形象,这被分解的诸多部分按照一个新的原则重新组合在一起,因此电影对现实的表现,在现代人看来就是无与伦比地富有意义的表现。 ”(注:W·本杰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董学文、荣伟主编《现代美学新维度》,第190页。)也就是说,电影表现空间经验, 是把对空间的(整体而混沌的经验拆解<细致化>成多个局部经验,然后选择部分经验,按自己的表意需要去重构一个对空间的新的经验(实际是创作者的空间体验)。这一新的空间经验因为经过了拆解和重构的主观化过程,因而能传达出一定的主体意识。这里面实际包括两个步骤:一是选择哪些局部经验进入影像本文,这实际上反映了创作主体对具体空间的一种注意方式。如果有的较关注整体轮廓,那么就可能较多地使用全景;如果有的人对形式感较强的东西比较敏感,那么他就可能注重独特视角的选择;有的人习惯以联系方式观察对象,那么他就可能惯用遥、撂等运动镜头来表现物与物之间的空间关系。选择哪些空间经验进入本文,从更高层意义上说,就是如何拆解分割主体对空间的整体经验,如何像母亲给婴儿喂饭似的一口一口把它嚼烂,然后喂给小孩。拆解是一个很细致的步骤,它涉及到创作者对经验凸现的意识甚至无意识;而第二个步骤重构经验,即对进入本文局部经验的顺序的排列,则是创作者在空间展示中完成表意的继续,尽管可能有意传达,也可能更多是无意识传达,就像本杰明说的:“而摄影机借助一些辅助手段,例如通过下降和提升,通过分割和孤立处理,通过对过程的延长和收缩,通过放大和缩小,便能达到那些肉眼觉察不到的运动。我们只有通过摄影机才能了解到视觉无意识,就像通过心理分析了解到本能无意识一样。”(注:W· 本杰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董学文、荣伟主编《现代美学新维度》,第193、194页。)空间展示的艺术,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已发展得极为成熟。《泰坦尼克号》中沉船一段是全片的高潮,表现出不同人对待死亡的行为、态度。这是一段庞杂而极易表现混乱的空间展示,但导演巧妙地运用声画对位和声画错位的蒙太奇方式,把有力凸现主旨的一组分割镜头有机地融合一起:海轮即将沉没,想逃生的人已拥上甲板,这时镜头聚焦于一群正在安然拉琴的流浪艺人。随着人群向船舷涌去(争着上救生船),其中有一人提议撤走,然而做四散之后,却有一人又转身留下继续那段未了的音乐,于是其他艺人也跟着放弃了逃生的机会,一齐面对死亡作平静而安然的小提琴协奏。情绪随着音乐走向高潮。这时导演采取了声画错位的剪辑:让琴声延续,插入一组平切镜头:白发染鬓的老船长在驾驶舱安然而徒劳地掌着舵,海水破窗,呼啸而来——呈现了老船长特殊的生命告别仪式;一对相濡以沫的老人安静地躺在铺位上互相抚慰着一起迎接死亡的来临——暗示一种虽不同生却共死的人生宽慰;一位慈祥的母亲轻轻拍打两个孩子,讲着那个古老的故事——以回到遥远的生命起点的心态去对待生命的终结。这一段表现“死亡意识”的空间展示,以恰到好处的经验重构方式——平切,取得一种集中、概括的效果(把对死亡的同类反应集中到一起);而声画错位中小提琴音乐的延续,则起到了一种疏通镜头脉络的主题点染作用,使各个分散的局部经验成为有机的整体。而声画错位中,复合声给现场声的留位,则起到了或增强视力冲击——保留海水声增加海水破舱铺盖船长的气势;或丰富叙事——保留母亲给儿子讲故事的内容(因为故事内容本身暗写了一种对生命终结的态度)。同时,因为有了声画错位前声画对位(艺人拉琴的声画同步)对后面声源(声画错位中小提琴声的延续)的交待,使音乐有了声源依据而获得一种纪录感。(强调声源依据是纪录片音乐运用的风格,而无端音乐,如主题曲、插曲,对本文叙事则是一种他者的声音,一种自外而来的主观介入。)
可见,在这短短几分钟的一组镜头中,导演已煞费苦心地将经验选择(对沉船大场景中,局部场景的有意识选择)和经验结构(选择蒙太奇方式)的表意性发挥到一种淋漓尽致的程度。
另外,充分调动经验拆解和经验重构中的表意性,不仅能强化情绪情感,还原主观体验(而非客观经验),暗示叙事所指,而且还可以成为一种具体的叙事策略,一种可见可触的叙事手段。在这一方面美国电影《本能》呈现出一种经典范例的姿态。这一部侦破题材的艺术片,极擅长依靠运动镜头、特殊拍摄视角和景别的有意识组合来构成一种叙事悬念(这是侦破题材最为强调的一点)。开篇的第一个镜头极为新巧:画面出现一对男女的俯拍做爱镜头(因为俯拍让平躺床上的男人的脸出场),在一阵剧烈的动作后镜头拉开下摇至真实的床上,落幅与起幅起到互文效应,言说了本体与镜像的倒错关系,奠定了虚虚实实、扑朔迷离的全片叙事基调。而接着出现的“下文”:从女人背部所取的视角和手的特写(女人的手缚男人的手于床头栏杆,女人的手紧握冰锥频频扎向男人的脖颈),以对女人(凶手)面部的回避,弥漫起一种浓重悬念和神秘气氛。就如一部音乐作品的主旋律一样,开篇这一组镜头的运动、视角和组接的范式在“后文”中不断得到仿制(有所变动的近似重复),本文中间段落出现的每一次性行为凶杀都是以这一类似的镜头分割和组接来叙述的。只出现从女方背部拍摄的小全,男人的近景及特写,女人手的特写:缚住男人的手,紧握冰锥扎向男人脖子的手(“冰锥”特写,是鉴别真凶的线索暗示,因为这一极其特殊的作案工具显示作案人特定的生存环境和内在气质)。悬念的递增是靠与开篇类似的分割镜头和组接方式来完成的,而片尾悬念的解开也是通过与片头相辉映的镜头分割组接方式来实现的。我们看《本能》的结尾镜头,首先出现男女主人公做爱的正面叙写(视角变化是与开篇的唯一不同),然后出现手的特写:女人把男人的手缚在床头;女人仿佛从身后拾起什么,然后扑向男方,手却落在床头——空的,接着以有力的一“笔”结束全片——镜头从女方空着的手摇向地上,落幅为冰锥的特写,这就以影像的特有“语言”方式交待了谜底——凶手是谁。而与开篇类似的镜头分割和组接,开始给人以明确的期待视野(使观众设想凶杀又将如何发生),然而随后的叙述又猛然打破读者的期待(手拾起什么,扑向男方,然而这次手却是空的)。这种故意制造的与开篇镜头的类似和突然的错位(这次手是空的)。获得了一波三折、惊心动魄的整体叙事效果。而结尾与开篇辉映的“摇”镜头(片始镜头从房顶玻璃中的镜像下摇至镜像的本体床上的做爱,片尾镜头则从床上摇至地上的冰锥),完成了影像叙事的整体开合性,使全片结构完整,一气呵成。同时这个“摇”镜头不仅以影像的方式解谜,更以影像的方式升华主题——通过空的手和地上的冰锥的特写景别(特写本身有强调、写意作用),言说了女主人公最终对杀戮的放弃,凸现了人在社会化中获得的社会性一面(爱情),对人的原始本能的最终胜利的主旨。
可以说,在近几年的好莱坞大片中,《本能》是把影像叙事作为一种叙事策略而发挥到某种极致的一部出色影片。导演以摄影叙事一波三折、扑朔迷离的视觉效果,有力证明了影像艺术在空间经验的拆解和重构中巨大的表意潜能。
三、影像意识的当下趋势:对影像能指的倾斜
影像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差异在于,它是通过机械复制手段,以逼真的声音和画面还原我们对世界的视听经验(而视、听经验是人对于世界的最主体经验),机械复制的声光效果显示了电影对世界的一种独特观照方式——物质化观照。而作为影像“语言”的声音和画面的能指——声光效果体现了电影的物质属性,这也是与文字艺术不同的。“……在词语语言的领域中,‘能指物质的多种变异,从某方面说,总具有想象性,因为人们实际接触到的唯一东西只是语言’,而在电影中,‘形式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却表现得很明显,因为观众面对着彼此有明显区别的物质。”(注:〔法〕罗杰·奥丹《语法模式、语言学模式及电影语言的研究》,《世界电影》1988年第1期,第19页。)更确切地说, 文字艺术是唤起读者的经验(能指物质是想象性的),每个读者的经验储存不一样,才形成“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接受张力场,影视艺术则是以逼真的声音、画面震撼观众(一种不容想象的感官施暴),让观众从震撼中获得感动,从感动中接受本文的意义传达。因而要尊重影视艺术的特质,就必须发挥影像的物质性优势,进行能指倾斜(相对于文学而言)。从世界电影发展史看,对影像物质性的关注,实际是一个漫长的摸索过程之后的结果。在电影的发轫阶段,其创作基本上没有摆脱舞台戏剧的影响,把摄影机架在摄影棚里记录一场近乎戏剧的表演,这就是电影。不久,爱森斯坦提出蒙太奇理论,划时代地发现了电影的一种极其重要的表意方式。然而蒙太奇理论把影像的能指作为意义寄寓的扁平符号,而忽视了声画能指的独立价值。到40年代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才觉悟到影像能指的重要性(之前的英国纪录派电影也有朦胧的意识),这一批电影人充分认识到声画逼真的重要意义,他们把摄影机扛到街头,采用偷拍和长镜头,让演员穿行于真实的大街小巷,从而获得声画的真实和生气。正如他们的代表人罗西里尼提出的宣言:“尤其重要的是,今天的摄影机已经完全可以自由操纵,我们无须事先作任何思考,我所关心的倒是观察的敏锐性,我只根据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注:〔日〕冈田晋《现代的电影与影像问题》,《世界电影》1988年第3期,第79页。 )之后的安德烈·巴赞则把新现实主义强调能指的观点赋予纪实美学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电影的物质在于以其声音和画面的逼真性带给观众其他艺术不能企及的真切感受。这一走出学院式思辩切入当时电影实践的理论给予影像“语言”的物质性以合法地位。
而今天的世界电影(以好莱坞为中心)一方面在继续探索着影像叙事策略、影像的表意功能。另一方面更注重以巨大的资本投入和高科技等手段,制造电影前所未有的逼真,富于冲击力的视听震撼——即不惜血本地制造能指的诱惑。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接受的考虑,许诺现代观众对本文平面化要求和刺激阈的不断扩张(市场流通必须充分考虑观众);另一方面,从本文角度考虑,对能指的强化也是发挥影像艺术独特魅力的必需。因为电影擅长的是以强烈的视听效果将观众置身于故事现场,以一种梦幻似的身临其境(所以有人把电影称为梦幻艺术),奠定观众进入审美的基础。因而一方面能指本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视听美感本身是电影美感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对能指的强化也是进入深层审美的基础,是观众抵达深层审美接受的桥梁,从而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泰坦尼克号》所讲的那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沉船事件,之前也曾有数部影片表现过,但却都没有《泰坦尼克号》的巨大震撼力。这主要得益于《泰》片中高科技电脑制作和对阵容、服装、道具的巨额投入所取得的视听效果。那极其逼真的声音和画面,使观众完全置身于灾难降临的紧张气氛(产生面临这种空前劫难的幻觉状态),从而在这种紧张中充分感受和理解主人公露丝和杰克面对死神生死与共以及那种把生的希望给予对方,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的崇高真情。也就是巨额制造的逼真能指效果,极易使观众进入一种感同身受的无间离接受状态(忘我境界),从而最大限度地吸收创作主体借文本发送的情感信息和审美意义。反过来,我们也不难设想,如果《泰》片中没有海轮与冰山的猛烈撞击、海水撞碎玻璃扑进船舱、巨轮断裂、船尾迅速栽入黑色的大海等系列空间造型的极具逼真的视听效果,是不可能形成一种“空谷足音”的接受状态,而使这一并不新鲜的爱情故事(贵族女性反叛等级与平民青年相爱的模式)还显示出勃勃生机,在观众心中成为“永不沉没的真情”。
中国电影在能指制造方面,应该说还一直处于滞后状态。中国电影从儿童期直至“第五代”导演出场前,还缺乏影像意识的自觉,既不能在影像叙事、表意上进行开拓,更忽视了制造电影能指的魅力;“第五代”导演的崛起过程,实际是中国电影影像意识复苏的过程,以张艺谋、陈凯歌为首的“第五代”导演关注的是影像的表意能力和传统意义上的形式审美(注重画面的构图、光效),却不能顺应当今观众对强节奏和视听快感的心理期待。结果他们大多数影片制作的唯一意义,似乎是走出国门捧回几个大奖。(相反,也许对中国观众并不陌生的那些风俗、仪式、文化环境的泼墨式叙写、铺陈,对西方观念倒可能因为距离而散发着能指的魅力。)
中国影视(尤其是电视)对影像能指的忽视,归根溯源,大约是受中国戏剧虚拟性造型(时空虚拟和动作虚拟)的潜意识影响。强调影像“语言”所指的“语言”观,把对影像能指的强化视为满足观众生理快感的庸俗的商业化行为(把个别现象视作普遍),这一滞后于世界电影发展趋势的传统观念,导致了中国影视始终不能发挥其独特优势而居于文学之下。电视剧《三国演义》远没有小说给我们的传奇感受,其中之一,就是影像造型无力。像众人皆知的“三英战吕布”这样的经典场景,就在四个人迟缓无力(没有速度对力量的体现)的刀、枪、剑、戟的顶压中,在简单的几个马腿的打转中,浪费掉了。而视效证明,几个戏剧化的动作、表情,戏剧化的以点代面的虚拟,是永远取代不了对速度、力量和气势的正面实在的铺写和表现的。也正是中国电视人对这一观点的初悟,才使之后的《水浒传》呈现了风格的进步。最明显地表现在精心的武打设计上:鲁智深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威猛和直率(拳直来直去,以力量取胜)流露出他个性的豪爽和痛快;林冲则以动作的标准、规范、精到暗示出他从小所受的正统式教育;武松则以其刁钻、巧妙、随机应变的醉拳反映出这位侠士豪爽中的机智。这些精心制造的影像能指,在制造令人悦目的视听快感的同时,具有刻画人物性格的所指意义。然而这一尊重影视规律,发掘影像优势的对原作的创造性改编却被某些古典名著研究专家,以文学的知识加以鞭挞。如不满意,将鲁达痛打镇关西的三拳两脚改成长达数分钟的武打场景,认为这是歪曲人物性格(三拳两脚说明镇关西经不起鲁达的神力),是追求商业化的表现。以此为例,否定电视剧武打设计的发挥。殊不知,两种艺术存在不同的表现手段和接受方式。小说中“三拳”的描写以镇关西对“三拳”的感受渲染了鲁达的力量,而这种感受是不可能搬上银屏的(描写心理活动和感受是影视的短处),于是只能进行视觉转化。若这时仍译解为电视上的三拳两脚,则会因丧失原著对感受的铺写所取得的对动作的渲染作用,而显出处理的简单(没有足够“笔墨”表现人物的力量)。反过来说,也只有对动作的视觉效果的着力渲染(如拳头穿过凳子将人打飞,人飞出后落地的渲染等等),才给人以鲁达神力的印象。
总而言之,影视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以影像(声、画)传达创作者对世界的审美感知和审美意义,因而我们可以说影像艺术的本体是影像,那么,如何充分意识影像在影视艺术中的本体性地位,如何开掘、发挥影像表现的潜力,尤其是在高科技引入电影,丰富电影“语言”的今天。这既是一个理论上亟待研究的课题(尤其亟待作影像思维、影像叙事、影像接受等直接融合中外影视发展现状的研究),又是中国当下影视创作摸索并借以摆脱其他兄妹艺术(尤其是文学的小说、戏剧)的潜在羁缚而走向独立、成熟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