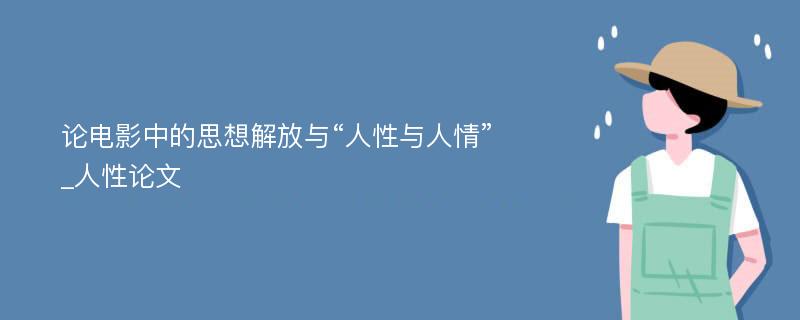
论思想解放与电影中的“人性和人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人情论文,人性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鸟瞰色彩斑驳流向歧异的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最为喧哗、最为睿智,因而也最有创新力度的莫过于新时期,创作、理论、批评三军骚动,潮汐滚滚涌来,后浪推前浪,形成最为壮观的电影现象景观。回眸辉煌历程,我们发现无论是战争题材影片还是由“伤痕文学”发端的暴露“文革”黑暗的影片;无论是改革题材影片还是文化反思电影,在一片喧哗与骚动中,始终活跃着“人性与人情”的浪花。中国电影开始有意识地把人从“阶级斗争链条上的一环”还原成具有独立个性的人,它反映了电影艺术家对人的价值、尊严的热烈追求与对人的本质力量全面实现的憧憬。
叙事艺术最根本的原动力是情感。但文革刚刚结束时,电影要表现世俗生活却步履维艰。《大众电影》杂志封底一幅王子与灰姑娘拥抱亲吻的剧照竟横遭指责,电影创作的境遇可想而知。习惯了以阶级斗争编织矛盾冲突的人们,对世俗生活的海洋望而却步,或者潜意识里拒绝趟涉。在当时的社会主流话语中,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人性与人情被禁锢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档案”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腐朽思想。政治话语制约文艺的格局,使得“禁区”的存在超出了文艺思潮的范畴,在这种格局下,电影艺术家与理论家只能在政治话语限定的活动空间内斡旋。所以,欲要打破这块坚冰,必先进行思想解放。思想领域内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解放思想运动,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确认,为广大电影艺术家与理论家冲破人性与人情“禁区”扫清了障碍。
一
文革结束后,亿万人民一下子从话语营造的虚妄跌落到满目疮痍的现实。语词建构的虚假帷幕一旦被撕碎,漂亮文饰下的残暴就昭然若揭。社会话语中堆积着厚重的极“左”观念,而电影艺术家还面临着政治话语形构与艺术话语形构强制关系,即历史地形成的政治制约艺术格局使得“阶级斗争模式建构叙事中的矛盾冲突模式”和“塑造英雄典型人物”的人物典型论压迫着电影创作。“人性人情被人从花园里放逐到荒凉的纱漠”(注:王愿坚:《人·人性·人情》,载1980年第9期《电影艺术》。),其理论根据是“要求文艺要表现人情和人性,这要求本身就反映着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反映着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用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阶级论的反动思想。”(注:见《管见集》:《残渣的泛起——略评部分电影文学剧本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本文转引自《论电影中的人性和人情》,载1980年第5期《电影艺术》。)就连“人情味”也成了一个批判用语,似乎只在“批判”地主资产阶级或封建残余的腐朽生活时能派上用场,英雄典型形象一身“光”到底,寡情无欲,成了“一丝不挂”的圣人。在这种压力下,艺术家艰难地翰旋于“阶级斗争”模式的缝隙,遇到表现世俗生活场景、人物情感和普遍人性时往往捉襟见肘。
正如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讨论为旗帜开路一样,电影以及整个文艺领域的思想解放要用现实主义的“复归”作为冲刺的旗帜。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理论诸要素中最基础的要素。电影人清楚欲要打破僵化的“观念化”模式,必先恢复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借助“真实性”的威力使万马齐喑和影坛万马奔腾起来。而这与政治思想领域正在进行的摆脱“两个凡是”的障碍,恢复实事求是精神,步调一致,在那种格局下运行起来稳妥可靠。于是乎,咀嚼着人性遭受话语戕害的悲剧,艺术家自然就将视角投向滴血的心灵,世态炎凉中的人情悲欢与人性在“文革”狂澜中煎熬就成为电影艺术家关注的焦点。《泪痕》、《牧马人》、《小街》等影片相继问世。电影编导潜入生活底层,正视淋漓的鲜血。编导在真实地再现活生生的人物命运的创作实践中,自身主体意识觉醒起来,挣脱了旧观念、旧模式的束缚。跟着人物走了这一程,我们才明白,影片的创作者着眼于写人物命运,并不是对命运有什么偏好,也不是为了写命运而写命运,而是艺术构思的需要。”(注:王愿坚:《人·命运·心灵》——学艺笔记之一,载1980年第5期《电影艺术》。)所以,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深化为创作主体思想上的解放,人物从“一丝不挂”的“高大全”变成欲情双全的血肉之躯。人情与人性的浪花从创作主体的心灵雀跃于银幕之上。改革最初阶段的电影就是这样从“观念化”向“世俗化”演变。《小花》、《今夜星光灿烂》和《归心似箭》这三部战争题材影片最能反映这种倾向。影片《小花》改编自小说《桐柏英雄》,但是编导舍弃了小说的主线——描写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时刻的战争形势发展及有关交战双方矛盾冲突的内容,把战争事件推到背景,只撷采其中一朵“小花”加以发挥——兄妹、母女、父女间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成为影片再生故事的中心。“影片中的‘情’成为很重要的表现手段。寓理于情,以情动人——我们想这应成为这部影片区别以往我国战争片的主要特征。也只有大胆地触及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才有可能使这部影片出现新的突破,给观众造成一点新鲜感。”(注:黄健中:《〈思考·探索·尝试〉——影片〈小花〉求索录》,载1980年第1期《电影艺术》。)《今夜星光灿烂》的编剧开机前向导演阐述创作剧本动机时也说,没想着力描写战争的规模、军事战略思想、将领的才智及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基于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典型人物的
塑造,作用于人们的灵魂,简单地说是写战争中的人——主要是人的灵魂。”(注:白桦:《〈由衷的、有感而发的歌唱〉——〈今夜星光灿烂〉拍摄前和谢铁骊同志的谈话》,载1980年第7期《电影艺术》。)所以,编剧有意识地设置在叙述中一个村姑作为视点人物,让其目睹在摧毁旧制度的战斗中一群与她同龄的年轻战士,及她与其中一位之间爱的浪花。而影片《归心似箭》做的更绝,硝烟战场被编导推到银幕之外,我们能够感知的叙述中,是一位负伤的抗联战士遇到一位年轻的寡妇,两颗心撞出火花。这些看似简单的创新,虽然恢复的是五六十年代巴人等人所倡导的“通情”、“达理”。“通的是‘人情’,达的是‘无产阶级的道理’”,及“应该有更多的人情味,并且使作品中的阶级战士闪耀着更多人性的光辉”。(注:巴人:《论人情》。)但在迷信盛行、“观念化”模式依然根深蒂固的当时,此举颇有杀出一个黎明的意味。回顾一下此前刚刚发生的“水晶鞋”风波,情形可窥一斑。
一九七九年第五期《大众电影》介绍了英国影片《水晶鞋和玫瑰花》,并在封底刊登剧照——王子与灰姑娘拥抱接吻。很快,编辑部收到新疆某农场一位姓问的党员来信,说他看那幅剧照非常气愤,“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那些洋大人们腐朽的爱情,那些搂搂抱抱、亲亲吻吻的爱情,……我看这类狗屁不如的艺术,不适合中国现代的国情。”且由此引申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被篡改了。当时《“歌德”与“缺德”》、《向前看呵!文艺》等文把一大批反映与“四人帮”斗争的作品划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大众电影》编辑部考虑到这封信超出了对那幅画页的责难,不是孤立的个别现象,就将此信刊登在第八期《大众电影》上,展开争鸣讨论。一时在电影界引起轩然大波,文艺界其他方面的艺术家、理论家及广大读者也积极参与进来,各抒己见。这就是当时所谓的“水晶鞋事件”。几乎,就在这个讨论进行的同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筹拍《无情的情人》时又碰上“人性”的钉子而胎死腹中。这个剧本发表于1959年11月份的《电影创作》上,获得许多推崇,但是不久就被扣上“一部宣扬人性论的作品”的帽子而遭受批判。当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之际,北影厂希望重拾旧题,把这个剧本搬上银幕,原来存在的对人性和人情问题理论上的偏颇,再次浮现出来,成为一个前进中的绊脚石。那么,如何对待电影作品中的人性和人情就成为一个亟待探讨的话题,也是阻挠电影界进行思想解放的一个大门槛,必须在理论上进行澄清。于是,《电影艺术》发表了文章《电影中的人性和人情》,并邀请了一些电影艺术家和文艺评论工作者举行专题座谈会。(注:《电影中的人性和人情》载于1980年《电影艺术》第5期;同年5月31日编辑部召开了专题研讨会。)该文及这次研讨会在坚持“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的人性和人情,不同阶级又有共同的人性和人情”,否定抽象的人性或完全超阶级的普遍人性的存在的前提下,比较系统地清理建国以来被极左思潮“蒙昧化”的“人性论”,提出区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人性和人情与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和人情。这实际上是通过恢复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性观”(注: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打破僵化思想设置的“人性”禁区,把极“左”思潮弄乱了的“人性和人情”问题再次澄清(注:周恩
来1961年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里谈到文艺作品中的人性问题时,责备那些极左派是把已经解决的问题又“都弄乱了”,“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分析来看问题,而是从唯心主义看问题。)
事实上,在人性和人情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究竟有无“共同人性”及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很快,作家梁晓声等人著文对“共同人性”、“超阶级的普遍人性”和“带阶级人性”提出异议,认为这三个概念的并存,虽然能够瓦解存在多年的“人性”禁区,为电影创作争得一个宽松的表现空间,但其理论上的“很不彻底”性造成“自身包含的混乱”,必将最终导致无法彻底打破极“左”思潮的“人性”桎梏(注:其争论的观点分别见梁晓声文:《浅谈“共同人性”和“超阶级人性”——与陈剑雨同志商榷》,载1980年第9期《电影艺术》;未泯、萧飒文:《漫谈人性与阶级性——兼及人性在新时期电影中的反映》,载1981年第4辑《电影文化》丛刊;叶式生文:《略论超阶级的人性》,载1981年第4辑《电影文化》丛刊。)。电影界的这场关于人性和人情的讨论与争鸣同整个文艺界所进行的人道主义讨论步伐一致,其热点基本接近,尽管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是两个概念。这个讨论之所以在八十年代初能够达到高潮,除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积淀的结果。所以,要对这个讨论进行回顾,我们必须回顾它自身的历史进程,唯此才能考察这些概念形成的历史根源。而电影创作中的“观念化”倾向与“世俗化”倾向,说到底是如何对待作品中的“人”,是现实的人还是观念的人。
二
在中国,文艺对人、人性和人情的热情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漫长的封建专制造成以宋明理学为基础的“话语板结”,它反作用于人,束缚着人。在那种社会话语下,人的精神受到压迫和摧残,人的价值遭受蔑视和践踏。于是,五四先驱们针对“存天理灭人欲”高举起“人文”的旗帜,寻求人性的复归,他们倡导“人的文学”,用以反对封建“非人”的和“吃人的”文学。首先提出“人的文学”口号的是周作人,他主张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而排斥“非人”的文学。“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都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个人主义(它的较悦耳的代名词,就是人的发现,或发展个性),原是资产阶级的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故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封建思想开始斗争的‘五四’期而言,个人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要态度和过程,正是理所当然。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亦即在此。”(注:茅盾:《关于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艺术家们觉悟到社会运作的阶级性,发现单凭“个性解放”未免空洞,人的解放首先应该是被压迫者的解放,于是,把人的解放具体地从“个人主义”式的解放发展为被压迫者整个阶级的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还没有到来,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队伍的条件尚不成熟,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的是,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关系的文艺,他们首先强调的是现实主义理论——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列宁所处的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建立自己的文艺队伍、确定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方针。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所以艺术家们更多地继承和发展了阶级倾向。人作为个体生命、人性的解放发展到被压迫者共同的解放事业,毫无凝问,在中国文艺史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当“历史的观点”被借鉴、中国化的同时,“美学的观点”被忽略了,其结果是在“左翼”创作与批评中政治倾向性淹没了文艺审美原则。也就是夏衍所说的,“我们最早提出无产阶级文学口号的‘左联’,受苏联‘拉普’的影响,本身就带有‘左’的色彩……由于‘左’的思想作崇,对政治和艺术怎么摆法,根本未加考虑。”(注:夏衍:《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1980年第1期《电影艺术》;其中“拉普”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
电影由于其自身的商业性与通俗性,在它诞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结合,而是更多地借鉴通俗文化的力量,题材多是从文明戏、鸳鸯蝴蝶派、武侠神话和历史演义移植过来的,它们本来就有广泛的市场和读者群,所以,深受欢迎。这个时期,电影正当童年,天真未凿,随俗浮沉的人生命运多于“力图挣脱牢笼”的斗争锋芒。就这个历史根源而言,电影与文学的区别在于,文学经历了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时代而后进入以“阶级斗争为本”的“左翼”革命文学时代;电影则没有经历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的时代,几乎是一夜之间,随俗浮沉的市井文化渗透进入阶级斗争的血液。随着党的电影小组的成立,夏衍把一批“左翼”进步艺术家带进电影界,同时王尘无等“左翼”文艺评论家成立了“影评小组”,这样“左翼”势力从创作到影评都渗透进去,电影原来单一的格局被打破了,随俗浮沉的市井文化与倾向明朗的“左翼”文化一下子涌进同一条江河,又各自遵循自己的“方向”泾渭分明地继续流淌。《狂流》、《春蚕》、《渔光曲》等进步电影作品的诞生,使电影与其他文艺品种、与整个时代脉搏频率一致起来,而《一夜豪华》、《小女伶》、《浪淘沙》等“脱离时代脉搏”的影片也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
但是,这种随俗浮沉的市井文化与激进的革命文化的合流不同向之奇特组合,当时虽能够本能地平衡人伦世俗与阶级倾向,然而缺乏人性的旗帜,使成长中的中国电影从理论到创作、到评论都先天性“缺钙”。加之,“左翼”文艺思潮在形成期就受到国际上‘左’倾文化思潮影响,在幼年时代就表现出过左的倾向。忽视电影本身的内在规律,特别是美学规律,用政治倾向代替文艺审美规律甚或电影批评。如对费穆导演的三部影片《人生》、《天伦》和《小城之春》(注:影片《人生》、《天伦》的编剧是钟石根,分别为1934年、1935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小城之春》的编剧是李天济,文华公司1948年出品。)及桑弧导演的《不了情》、《太太万岁》和《哀乐中年》(注:《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编剧都是女作家张爱玲,文华公司1947年出品;《哀乐中年》为桑弧自己编剧,文华公司1949年出品。)等影片的批判,就流于简单偏颇,从中反映出理论上的欠缺。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反映“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而是将视角投向个体生命,“只是摭拾一些人生的片断,素描地为人生画一个轮廓”(注:费穆:《〈人生〉的导演者言》,载《联华画报》第3卷第4期,1934年1月21日出版。本文转引自《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第348页。),描述缠绵悱恻爱情、家庭世俗生活及人物内心的哀愁与欢乐。于是,它们就被进步影评家简单地批评为“逃避现实斗争,纠缠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纯粹家庭、爱情的小圈子中,渲染没落阶级的情调。”(注:见:《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卷第270页。)甚至连费穆在导演艺术上善长于渲染气氛和刻画人物内心世界,也被说成“这些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处理,在这样一部灰色消极的影片里,除了加深片中没落阶级颓废感情的渲染,扩大它的不良作用和影响外,”“实际上是起了麻痹人们斗争意志的作用。”(注:见:《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卷第371页。)所以,从那时起,由于“左翼”批评者就走向偏颇,人性与人情的表现如果不结构进“社会矛盾斗争”格局之中,或者说影片所表现的人性和人情若不通过社会矛盾的激流荡涤而出,就被这种理论视为消极颓废。这种批评是用政治倾向代替艺术批评。对此,亲身经历这些文艺思潮形成过程的夏衍感悟颇深,“其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由于历史条件、社会条件造成的。”(注:夏衍:《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1980年第1期《电影艺术》;其中“拉普”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溯其远因,则
自中国新文艺运动以来,思想就不够解放……”(注:夏衍:《在电影导演会议上的讲话》,载1980年第3期《电影艺术》。)“由于‘左’的思想作祟,对政治和艺术怎么摆法,根本未加考虑。”(注:夏衍:《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1980年第1期《电影艺术》;其中“拉普”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这种“倾向性”在极“左”思潮的驱动下,导致了其后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使“人性论”和“人情味”成为责难的靶子,进而成为批判某部作品或某位艺术家的“棍子”。
到了五十年代,当随俗浮沉的市井文化被历史荡涤出影坛后,原来依靠本能平衡的格局被颠覆之后,只剩下一支独流时,艺术家们终于发现自身的偏颇已经演化为教条,形成理论上的“话语板结”地带。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也囊括了全部的人性内容的时候,巴人、钱谷融等一批明智之士试图用“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来救助“机械的”“阶级论”(注:巴人:《论人情》。)和把文艺作品中人仅仅当作“反映整体现实”的“工具”(注: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提出“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注: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和“能‘通情’,才能‘达理’。通的是‘人情’,达的是‘无产阶级的道理’”(注:巴人:《论人情》。)但是回应他们的是政治上的迫害,而不是文艺观点上的论争,姚文元在《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一文中,说巴人“为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注:原文载1960年第2期《文艺报》。)此后,人性和人情以及人道主义便屡遭批判。六十年代,枪毙一些影片时也是以“人性论”为幌子,《革命家庭》是“充满了人情味”、《五更寒》是“充满人性论”而《柳堡的故事》是“利用了人情味”。于是,电影中的人性和人情彻底销声匿迹了。电影以及整个文艺和现实生活不约而同地重演了一次“非人”和“吃人”的悲剧,直到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电影界涌动起“回归”现实主义的浪潮。
三
随着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事求是”的旗帜高扬起来,政治制约文艺的格局被打破了,身心疲惫的电影艺术家在宽松的政治气候下,终于能够摆脱“阶级斗争模式建构叙事模式”及“塑造英雄典型人物”理论的压迫,回归现实主义传统。于是,真诚奉献贴近现实生活、反映触目惊心的“文革”浩劫、揭示灾难对人物心灵的戕害,一度被电影艺术家奉为圭臬。
在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下,电影艺术家通过回归现实主义传统,试图恢复被极左思潮阉割了的现实原则,用“真实性”瓦解政治需要驱使下的主观意志论,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论瓦解“高大全”式的“英雄典型人物”论,以此突破“三突出”的僵化模式。所有这一切都以文革前的理论格局为回归的目标。也就是说,要塑造真实可信的人物、真切感人的形象,那么,就得把普通人身上都有的“世俗性”还给影片中的人物。人性和人情的问题自然就被提出来了。《电影艺术》引发的那场讨论,无论是陈剑雨的文章还是研讨会上的发言,其观点都没有突破五十年代的理论深度,可以说,是想通过旧话重提来瓦解蒙昧主义束缚下的人性“禁区”,拯救危机中的电影创作,但是,这次情形不同于五十年代,有思想解放运动开创的宽松气候,有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不再横加干涉”的庄严承诺,于是,思想睿智的艺术家和理论家就试图沿着五十年代开创的道路向前跨一大步。陈剑雨的文章发表不久,作家梁晓声即著文对把“共同人性”与“超阶级的普遍人性”对立起来,且断言“共同人性”是存在的而“超阶级的普遍人性”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悖论予以否定,指出“共同人性”与“超阶级的普遍人性”同属于一个范畴,承认前者而否认后者的存在是不符合逻辑的。(注:梁晓声:《浅淡‘共同人性’和‘超阶级人性’——兼与陈剑雨同志商榷》,载1980年第9期《电影艺术》。)这一步迈得很有意义。之后,叶式生沿着这个线索又向前推进一步,指出“带阶级的人性”总是与“共同人性”同室操戈,誓不两立,只要你承认前者的合理地位,后者就无法立足。“‘人性’本来就是‘超阶级’的”(注:叶式生:《略论超阶级的人性》,载1981年第4辑《电影文化》丛刊。),超阶级的“人性”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是一种普遍的因而自由的本质”(马克思语)。“多年来,‘超阶级的人性’总是被同‘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连在一起,完全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曲解。”“把‘超阶级人性’拱送给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荒谬的,把它同‘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一齐反对更是十分有害的。”(注:叶式生:《略论超阶级的人性》,载1981年第4辑《电影文化》丛刊。)到此,笼罩在“人性和人情”问题上的神秘面纱终于在思想解放运动强大动力推动下被完全撩开,人性和人情作为美好的字眼重新在社会话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随着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新发现而引发的整个思想领域与文艺领域对人道主义的广* 泛讨论,无疑是对当时电影创作中朦胧进行的人道主义的艺术描写给予极大肯定,同时也弥补了自左翼文化运动以来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化过程中,承继偏颇的一次有意义的“补钙”,在理论上突破了“人”的禁区,容纳更为深邃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内容。然而,这次不彻底的讨论,在含含糊糊中落下帷幕,使已经撩开了面纱的“人性和人情”仍然忸怩作态。当人们看到银幕上的爱情与自己“观念”中的想象不一样时,仍旧粗暴武断地视其为“不健康”,所以,中国电影一度产生这样一个怪圈,艺术家因为刚刚挣脱了“人性和人情”的桎梏争相演绎爱情场景而许多不愿接受此道的观众却用“不健康”予以否定和责难。而那些表现个体生命意识的影片,那些反映改革时代人自身觉醒的影片,那些揭示民族生存意识的影片,更是每有推出必见挞伐,揭示人性超深刻其受责难的程度就越激烈。但是,坚冰既已打破,航船既已启程,前进的航程不可逆转。有胡耀邦的“继续解放思想,坚持繁荣”的政治承诺,有邓小平的“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政治原则,(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强调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而胡耀帮同志在“人道主义”讨论之后多次针对文艺问题的讲话中都饱含对艺术家的理解,主张“继续思想解放,坚持繁荣”的方针。)有关人性和人情以及人道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一如既往的向前推进,更为深化、更加走向明朗化。
实际上,扭转人道主义讨论含糊落幕的是有关“主体性”的探讨,把关注的焦点从“人物”身上发展到“作者—人物—读者”三个不同的主体身上,进而也把作品中“人性和人情”的探讨深化为对“人”的探讨,确定了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艺观,荡去了以往机械反映论忽视主体的偏颇——即用环境决定论取消人物性格自身的历史,用抽象的阶级性代替活生生的个性和用肤浅的外在冲突掩盖人物深邃的灵魂搏斗。就人性和人情这个话题而言,这个理论发现最深刻、最精彩之处在于,否定了把共性解释为阶级性,把个性解释为共性的具体形态,解释为阶级性的形象演绎。借此理论,就很容易除去强加在人性头上的那些定语,使揭开了面纱的“人性和人情”不必忸怩作态。正是由于理论上的进步,约在八五、八六年前后,影片《小城之春》才引起电影界的重视,电影艺术家像从考古中发现稀世珍宝似的谈论这部曾经遭到苛刻批评的佳作,理论家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它是最能代表东方美学的曲范之作。与此同时,《野山》、《红高粱》和《老井》等充满东方人性风采的影片震撼着国人,吸引着国际。“人性和人情”的桎梏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最后一道绳索终于也被剪除了,尽管这个代价太大了。
然而,电影理论自身并没有经历主体意识觉醒,事实上,人道主义讨论之后,有关“人性与人情”话题研讨在电影界暂告一个段落。电影艺术家与理论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电影观念与电影语言特性上,即“电影是什么?”这个理论话题。创作与理论界都把热情投入到电影与戏剧、文学的区别,确定电影作为一门艺术自身的“个性”,优秀的欧美影片及西方电影理论被介绍进来,令人目不暇接。于是,发端于人道主义讨论的关于“主体性”的研讨被电影理论忽视了。电影对这一理论成果的享用得益于它与文学的血缘关系,懵懵懂懂中通过改编成熟文学作品延续“人”的话题。尽管如此,还是产生了一个含糊点,导致人物淹没在事件中的“错位结构”毒瘤继续在电影创作中蔓延。近年来一些历史影片写事不塑造人物,是这种错位结构的延续,“精品”缺乏个性鲜明的人物、艺术睿智不高,娱乐性不强,只剩下一个重金堆积的宏大场面和新闻舆论包装下的皮囊。那么,电影观众流失就在情理之中。
人是一切艺术的中心。思想解放运动以来,“人性和人情”的话题经历了通过拨乱反正恢复五十年代理论成果来打破极“左”思潮设置的人性和人情“禁区”,通过历史反思、寻根追源弥合历史造成的偏颇及随着人道主义探讨的深入进一步深化的“人本”中心论,即主体意识的觉醒。
(本文系第七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改革开放20年的中国电影”学术研讨会论文)
标签:人性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电影发展史论文; 小城之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