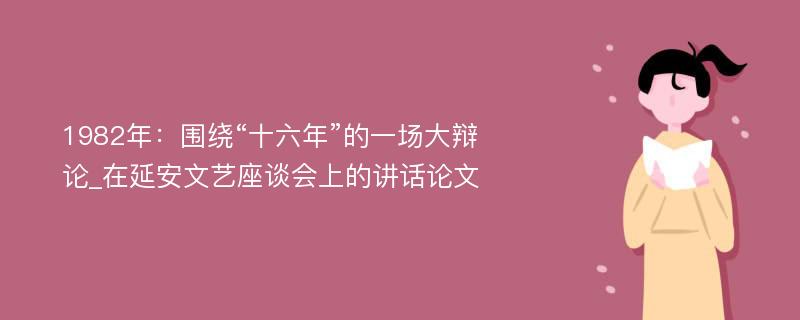
1982:围绕“十六年”的一场大辩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辩论论文,十六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来是半月刊的《文艺报》,自1982年起改为月刊。自1981年评《苦恋》以来,在一些基本的文艺观点以及对文艺形势的估价上,《时代的报告》与《文艺报》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代表两种文艺观、并屡屡公开对阵的刊物。《苦恋》问题已成过去,在如何对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论争。这次新的论争,是因《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2期的《本刊说明——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起的。全国很多文艺刊物和人文学术期刊,都先后参与了这场实际上是围绕着对《讲话》是否“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和是否退回到“十七年”的大论战。因此,这场大论战,与其说是《时代的报告》与《文艺报》两刊的论争,毋宁说是新“左派”与党中央领导下的主流文艺观之间的一场斗争。 “十六年”论一出笼即遭批评 《时代的报告》(月刊)1982年第2期发表《本刊说明——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化大革命”十年与“文化大革命”后新时期文学的六年连接起来,统称“十六年”,把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专制的“文革”十年与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新时期六年混为一谈。该刊同期还发表了两篇文章:《加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引导——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点体会》(作者燕铭)、《试论〈讲话〉对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作者张晓生)。 针对着《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2期发表的《本刊说明》,安徽省文联所属期刊部分编辑举行座谈,并在《文艺报》1982年第5期发表雨东写的长篇报道《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安徽省文联所属期刊编辑部部分同志对〈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2期的一组文章及其〈本刊说明〉提出疑义》,对《时代的报告》发表的《本刊说明》提出了质疑。 《读书》杂志发表文摘说: 《文艺报》八二年第五期发表署名雨东的文章《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代表安徽省文联所属期刊编辑部的部分同志对今年第二期《时代的报告》的一组文章及其《本刊说明》提出质疑。 这些同志认为,《本刊说明》中的一些提法很难令人理解,如:“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六年中,《讲话》也曾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歪曲或篡改。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用极‘左’的办法,把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文艺,演变成为林、江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文艺。粉碎‘四人帮’后,有些人则又把《讲话》当作框框来突破,结果不能不使自己陷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 雨东认为这提法的问题在于: 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均有清楚的划分和明确的阐述,党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也均无“十六年”的提法,“不知这里为什么要创造出‘十六年’这个特殊概念?” 二、十年内乱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时期,“把二者混为一谈,无异抹煞了三中全会在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意义。” 三、在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过程中,历来都存在着两种思想、两种倾向的斗争。而《本刊说明》偏偏只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来论证问题,似乎“文革”以前什么斗争也没有,而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则又只存在右的“自由化”倾向。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否认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斗争是反“左”,就可能导致否定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继续拨乱反正以及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等等。 四、该刊同期的另一篇署名文章,不加分析地重提“文艺工作者仍面临着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这一首要问题”的口号,这里所说的改造思想是专指文艺工作者而言,“这与党中央一再明确指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政策精神,和有关不提‘改造思想’的口号的意见,是相违背的。这种提法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歧视、批判和排斥另一部分人的情况。” 文章还指出,“要继续注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也要警惕‘左’的东西的干扰。”① 同时,吉林省白城地区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绿野》第2期发表了黎兮的《〈本刊说明〉说明了什么?——对〈时代的报告〉的一个提法的质疑》。接着,《文艺报》第6期发表辛旭的《“十六年”无差别吗?——评〈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就《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中所提出的“十六年”问题进行商榷。《安徽文学》第6期发表《对“十六年”提法的异议——本刊编辑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发言摘要》。沈阳市文联主办的文艺刊物《芒种》在该刊第6期上发表了东子今的《关于克服“自由化”倾向的思考——兼评〈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 在发表了《本刊说明》遇到了《文艺报》署名文章的批评之后,《时代的报告》以攻为守,于第6期发表了胡乔木的《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它》,意在把《文艺报》等刊物置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境地。接下来,《时代的报告》于第7期在《重新刊登〈本刊说明〉请读者评说》的总标题下,加编者按语,集中发表了一组文章:薛亮、方含英的《一篇玩弄诡辩术的奇文——我们对〈文艺报〉〈原则〉一文的看法》;彭泽、严汝的《应当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郑显国、文正的《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是新时期的优良作风——与雨东同志商榷》;梁军的《也和〈文艺报〉争鸣》。第8期又发表一组反击文章:徐夕明的《对〈文艺报〉批评〈本刊说明〉的异议》(读者来信综论);高洁的《为什么要在“十六年”上大做文章?》;邓斌的《也谈十六年的产别问题——评〈文艺报〉第6期辛旭文章》;豫林的《〈文艺报〉批“十六年”的文章不能自圆其说》。 紧接着,《文艺报》第8期发表了关林的文章《分清是非辨明真相——评〈时代的报告〉第7期的反批评》,对《时代的报告》第7期发表的《重新刊登〈本刊说明〉请读者评说》的编者按以及一组集束炮弹式的文章给予回答。一场文艺问题大论战就这样开始了。 一些外省刊物也陆续参加到这场论战中来。除了动作较早的安徽、辽宁、吉林等地的几个刊物编辑部的座谈报道和批评文章外,上海师范学院主办的《文艺理论研究》于第8期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峡》(文学季刊)在第3期上发表了余如的《〈本刊说明〉说明了什么?》;福建文联主办的《福建文学》(月刊)第9期发表了鲁人的《到底“说明”了什么——评说〈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安徽省文联主办的大型文学季刊《清明》第3期发表了周云泥的《果真是“十六年”一贯制吗?——与〈时代的报告〉编者商榷》;辽宁文联主办的《鸭绿江》第11期发表了陈深的《必须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也与〈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商榷》。 就全局而论,思想解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导的思潮,但《时代的报告》提出并宣扬“十六年”论,在继承和保卫毛泽东《讲话》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合法旗帜下,以“左”反右,让“左”的思想死灰复燃,也是有适宜的土壤的。针对着《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及其他一系列文章所宣传的观点,我所供职的《文艺报》对之采取了不妥协的斗争和说理批判的方针和态度。副主编唐因于本年度6月15日在长沙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学会1982年年会上,就“十六年”的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对其“左”的面貌和实质予以揭露和批判;编辑部副主任、文艺理论家陈丹晨在本刊发表了《“十六年”无差别吗?——评〈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②。 《人民日报》的报道给予支援 7月21目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闻一《〈文艺报〉发表文章评〈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的综合报道: 1982年第七期的《时代的报告》,在《重新刊登〈本刊说明〉请读者评说》的题目下,发表了一组“读者来信来论”,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说: 今年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本刊为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于今年二月号特辟“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栏,并附《本刊说明》。该栏目开辟以来,蒙文艺界人士惠赐鸿文佳作,颇受读者欢迎。不意《文艺报》今年五月号发表署名文章,以《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为题,指责《本刊说明》“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一语,认为“十六年是一个新奇、怪异的提法”,“无异是抹煞了三中全会在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意义”。《文艺报》给我们扣上这样吓死人的大帽子,实在令人大惑不解。为了使广大读者、特别是一些不明真象的读者了解情况,现将《本刊说明》重新发表,以便于大家共同鉴别,一起进行讨论,其中是非曲直,广大读者幸垂察焉。 这一期《时代的报告》刊登的来信来论有:薛亮、方含英的《一篇玩弄诡辩术的奇文》,彭泽、严汝的《应当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郑显国、文正的《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是新时期的优良作风》,梁军的《也和〈文艺报〉争鸣》。这一组文章对《文艺报》今年第五期发表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提出反批评。薛亮、方含英在文章中说:(一)《本刊说明》中的“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提法问题。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虽然提到“建国三十二年来”,但不能把“三十二年”当作提法而只能当作时间概念一样。如果说,六中全会《决议》说了“三十二年”并没有“抹煞了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那么,为什么《本刊说明》说了“十六年”就“抹煞了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呢?!(二)《本刊说明》中说:“有些人”“把《讲话》当作框框来突破,结果不能不使自己陷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应当指出,“有些人”突破《讲话》搞自由化,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原则》一文蓄意把“有些人”扩大成整个“文艺界”,从而将这个说明引申为“否认”文艺界的“巨大成绩”,以及把两个历史时期“混为一谈”等等。这样的“扩大”和“引申”,确实是罕见的怪事。(三)《原则》一文既不谈对《讲话》基本原则的坚持,也不谈在坚持《讲话》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发展,只是一味强调修改。试问:如此修改下去,难道还能坚持《讲话》的基本原则吗?!在《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之际,《文艺报》居然发表《原则》这样的奇文,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我们觉得,《文艺报》近几年来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发表《原则》这样的奇文,一方面固然要把自己说成一贯正确的好汉,但另一方面,恐怕也很难说没有其他用心。薛亮、方含英的文章最后说:“从《文艺报》等所发表的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消息看,他们是要动员舆论,组织围攻,把《时代的报告》打成极左刊物,并把它置之于死地。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极为巧妙的。但是,就在他们巧妙的行动之中,已经露出破绽,表明他们尽管口头上拥护三中全会,但事实上却用自己的行动在践踏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路线。”彭泽、严汝在来信中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有些人一看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像西班牙斗牛时牛看见红布一样激动起来,立即斥之曰:‘你们这是在反对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的方针,否定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说穿了,这是借维护三中全会路线之名,行维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实。”郑显国、文正在文章中说:“事实证明: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在对待《讲话》的问题上存在着‘左’和右的歪曲和篡改,这是合乎实际的,正确的。而雨东同志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文章,不仅论点站不住脚,而且论据也是不能成立的。说穿了,这是一种文过饰非、十分蛮横的非科学的态度,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打棍子、乱扣政治帽子的恶劣作风的一种流毒的表现。”梁军的文章在谈到文艺工作者是否仍然面临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的问题时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如果还带着由于历史的错误而形成的偏见,固执地反对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这样一个对于文艺工作者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不仅是十分不应该,也是十分错误的了。”③ 一个月后,8月2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闻一的题为《部分报刊陆续发表文章就《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展开争鸣》的后续报道,报道上海、北京、安徽、辽宁、湖南等省市一些报刊对《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的争鸣文章和座谈。报道全文如下: 今年第二期《时代的报告》“本刊说明”发表后,上海、北京、安徽、辽宁、湖南等省市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座谈会发言摘要,对“本刊说明”的某些提法展开争鸣。 狄英在《对一个提法的质疑》(1982年4月23日《文汇报》)一文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的提法,是一个古怪而有害的提法,它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粉碎“四人帮”后的六年混同起来,相提并论。这提法“无意中否认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界一直进行着两条战线的斗争。如果有所侧重的话,那末前一阶段主要是拨乱反正,荡涤极左余毒,批评‘两个凡是’观点;近两年来,则是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在继续批‘左’的同时,着重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如果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只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好象‘左’的影响就不存在了,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安徽文学》1982年第六期发表了《对“十六年”提法的异议——本刊编辑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发言摘要》。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说:今天存在的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是局部的、个别的问题,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文艺界的整体,更不是文艺的指导思想。及时指出和严肃批评这种现象,是应该的,必要的。但绝不能把局部的、个别的文艺现象当作一个历史时期总的倾向,更不能把它当作指导思想与林、江的反革命阴谋等量齐观。 1982年第八期的《文艺报》,发表了关林的《分清是非 辨明真相——评〈时代的报告〉第七期的反批评》一文,并加了编者按语。 按语说:1982年7月号的《时代的报告》上,发表了薛亮、方含英等同志的文章,对《文艺报》今年5月号发表雨东的报道《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对于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进行讨论和争鸣,以辨明其中是非曲直,是完全必要的,正常的。但是,在薛亮、方含英等同志的文章中,离开对问题实质的探讨,却说什么:“《时代的报告》今年2月号提出要‘重新学习’《讲话》之后,《文艺报》即召开座谈会进行指责。”仿佛《文艺报》是反对学习《讲话》的;又说:“尔后又在某地产生了一个所谓‘情况汇报’,这个‘汇报’一出来,《文艺报》奉若至宝,即作为内部情况向各地‘通报’,以组织围攻。”甚至说《文艺报》“是要动员舆论,组织围攻,把《时代的报告》打成极左刊物,并把它置之于死地”。必须指出:这类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以为,虚构出什么“开座谈会”、“‘通报’”、“组织围攻”等等情况,不仅无助于问题的澄清,而且助长了一种不正的文风,为正常的争鸣所不取。我们诚恳地希望在争鸣中不要采取这类方法。至于是非如何,广大读者自会有正确的评断。 关林在文章中说:一、《时代的报告》第七期的一篇文章写道:“我们用不着多费笔墨来描绘前一时期文艺界那种乱哄哄的局面。”另一篇文章说:“就来自‘左’的干扰而言,莫过于林彪、江青一伙横行的十年;就来自右的干扰而言,则又莫过于粉碎‘四人帮’后的近几年。”近几年来,确有少数人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但这不代表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党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时代的报告》把十年内乱期间指导思想的问题和近几年的问题相提并论,都说成空前严重的极端错误,根本不讲这几年党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二、《时代的报告》的反批评文章竭力把这场争论说成是要不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争,是很奇怪的。党中央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以来,文艺界的多数干部群众是拥护中央的批评,积极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的。问题在于: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怎样估计当前文艺领域的自由化倾向?不能把纠正毛泽东同志的个别失误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把整个文艺的局面看成自由化的局面。人们批评“本刊说明”,是不同意它抹杀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的巨大成果,把拨乱反正的局面说成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局面。这就是分歧的根本点。三、围绕着《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出现了一场争论,这反映了人们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态度上的分歧。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我们的态度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但近几年来,也存在着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是借口我们的文艺工作犯过“左”的错误,借口毛泽东同志晚年有过失误,否定革命文艺传统,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甚至把文艺领域种种“左”的错误不公正地归咎于《讲话》。另一种则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承认毛泽东文艺思想有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向前发展的必要性,不承认在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基本原理的同时,也需要改正毛泽东同志文艺言论中的个别失误。《时代的报告》今年2月以来在“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栏目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提出的观点是很值得研究的。譬如今年第六期的一篇文章,对“文艺从属于政治”问题大发议论。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这个口号利少害多,但他们却认为指出这个口号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是“太偏激”了。这就不难看出,他们对待三中全会以来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是很不合拍的,持一种评头论足、怀疑否定的态度。 1982年第八期的《文艺报》,还发表了李何林的文章《我不同意〈文艺报〉和〈文艺动态〉的解释》。文章指出:《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明明只是提出《讲话》的遭遇这一个问题在‘十六年中’前后有‘左’的歪曲利用和右的反对;前十年、后六年分得很清楚,并没有‘混为一谈’;也没有把‘十六年’当作一个‘历史时期’,说‘十六年时期’,而是说在‘十六年中’”。“《本刊说明》不是在对‘十六年中’的文艺作全面的评价,更不是对后六年的文艺界的成绩作全面的评价……只是说《讲话》受到的‘左’右两种遭遇,不涉及其他问题。为什么就是不全面或否定成绩,甚至和《决议》不一致了呢?这不是‘我说东,你偏说我没有说西吗’?何况《本刊说明》只是说‘后六年’‘有些人’反对《讲话》,‘陷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并未说很多人都是如此,这也符合我们六年来文艺界的实际”。 今年8月号的《时代的报告》,发表了署名为余一卒的文章《兴师动众为何来?》,对《文艺报》第五期雨东同志的文章《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反批评。各段小标题如下:一、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二、“十六年”一词错了吗?三、目前对文艺上两条战线的斗争究竟怎样谈为宜?四、思想,还要不要改造?五、症结何在?这真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该期还在“读者来信来论”专栏里附了四位读者的来信,对《文艺报》今年第五、六期发表的雨东、辛旭的文章进行反批评。④ 论争自有终局时 由《时代的报告·本刊说明》引起的文学界的大论争,一度扑朔迷离,多所曲折,并非如我们今日看到的简单地直线发展。到1982年10月,事情总算出现了转折。中央书记处决定《时代的报告》停刊,另办一个报告文学刊物。 10月8日和12日,《文艺报》编辑部两次召开组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副主编唐达成传达中央宣传部关于《时代的报告》的决定。根据我笔记本中的记录,中宣部部务会议“决定”的大致内容是:根据中央常委的意见,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对《时代的报告》的错误作出决定。《时代的报告》今年第2期在一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前面,编辑部撰写的《本刊说明》提出了“十六年”的问题,混淆两个不同时段的性质。第6期公开发表文章,批驳经中央批发的邓小平同志关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同期,发表文章,反对经中央批发的胡乔木同志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论述。会议指出,《时代的报告》的错误是原则性的;一些兄弟刊物发表了批评文章后,又拒绝检讨,性质是严重的。“决定”指出:一、《时代的报告》的问题早已发现,因涉及的面比较宽,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加以慎重的解决,现在条件成熟了。二、在刊物上发表与中央精神相对立的文章是不能允许的。三、在纪念《讲话》时提出所谓“十六年”的提法,把性质不同的前后两个时段混淆起来,且强词夺理。《时代的报告》还要办下去,但要改为以发表报告文学为主,别的文章就不要发表了。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要实事求是,不要散布悲观主义。对文艺工作及其他方面的意见,不要公开发表,可以报送中宣部。杨尚昆同志指示,军队的同志要退出来。军队同志从编辑部撤出后,挑选对报告文学有研究的同志担当。黄钢同志不再担任主编和编辑了。四、希望公安部党组领导与作协、文联领导融洽共事,不要形成门户之见⑤。 贾漫在《风雨十年——记新时期的贺敬之》一文中这样描述整顿《时代的报告》的情况: 1982年10月,接替王任重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找贺敬之谈话,传达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让《时代的报告》停刊,交地方另办一个刊物,刊名为《报告文学》,由人民日报领导,田流任主编。此事交贺敬之负责落实。贺敬之对此事的态度是:《时代的报告》确有和中央精神不相符的明显错误。但纠正它要防止走向另一片面,不能为《苦恋》的错误翻案。书记处决定的几条措施他愿意照办。但也提出应当全面看待《时代的报告》和主编黄钢等几位老同志,以利团结。他的这些看法经中宣部部务会讨论同意之后,由他出面约集《时代的报告》的几位负责人和人民日报的田流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他的谈话中肯定了刊物的成绩,说它发表过不少好的报告文学,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方向是对的。同时指出它的严重失误。贺敬之特别指出,批《苦恋》是应该的,但要实事求是,不能以“左”批右。刊物的主编是为党的文艺工作奋斗多年的老同志,写过许多影响巨大的好作品。黄钢同志坚持报告文学必须真实,旗帜鲜明地反对虚构,这是完全正确的。《时代的报告》的负责人毕竟是几位老同志,他们遵守党的纪律,服从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的决定。⑥ 对于贾漫的这段记事,徐庆全在《与这场风波相关的几个材料》中写道:“贾漫的叙述,有一处事实上的失误。《时代的报告》改由田流主编后,并没有马上改为《报告文学》,而是继续以《时代的报告》刊名出版。在田流任主编后的1983年第1期上,编者作了一些说明,可资参考。”⑦ 如前所说,《时代的报告》落得这样的结局,绝非仅仅《本刊说明》这一件事情。徐庆全这样描绘了它所以有这个结局的前因后果: 《时代的报告》创刊于1980年,是部队和地方一些老同志合办的报告文学刊物。部队的参与者主要是黄钢、魏巍、姚远方等人,地方上穆青、康濯、杜宣、梁斌等人,虽然开始名列主编,但大致是挂名的,不参与实际工作。1980年和1981年的实际工作,事实上是由黄钢具体负责的。有材料显示,在创刊号出版后,即被勒令停止发行,但后来还是解禁了。 《时代的报告》创刊以来,当然发表过一些好的作品,但是,由于编者有着“我们是在战争威胁的条件下进行四化建设的”心态……大约就是这样过高的警惕性,使这个刊物对文艺领域的一些作品进行上纲上线的指责。……在发表专批《苦恋》的增刊后,该刊还对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提出质疑,并对粉碎“四人帮”六年来的文艺形势作了令人反感的消极估计。 诸如此类的文章,自然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在“左”的思想路线支配下,不断绷紧的阶级斗争神经和不断膨胀的“革命”行为,导致了这场围绕着“十六年”而展开的文艺论争。这场规模不小的文艺论争,就这样结束了,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花絮。 注释: ①《读书》1982年第7期。文质摘。 ②丹晨:《“十六年”无差别吗?——评〈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载《文艺报》1982年第6期;收入所著《艺术的妙谛》,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③闻一:《〈时代的报告〉重新刊登“本刊说明”以及与〈文艺报〉商榷的读者文章》,载《人民日报》1982年7月21日。 ④《人民日报》1982年5月28日。 ⑤见笔者在《文艺报》工作时的笔记本第18本。 ⑥《文艺理论批评》1999年第3期。 ⑦徐庆全:《与这场风波相关的几个材料》,见《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43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标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文艺论文; 原则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