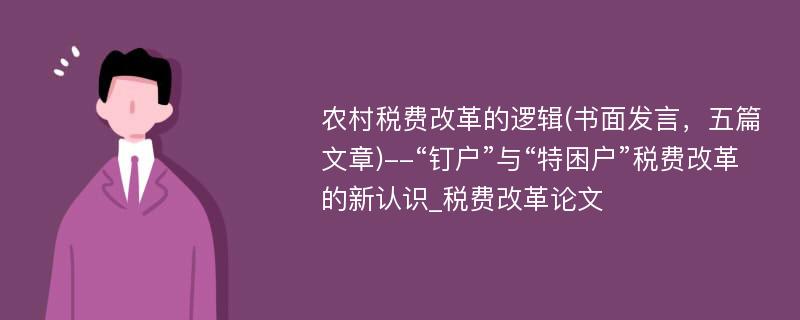
农村税费改革的逻辑(笔谈,五篇)——在“钉子户”与“特困户”之间——重新理解税费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困户论文,笔谈论文,钉子户论文,税费改革论文,农村税费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0年中央发出《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开始,农民负担问题正式重新进入了国家政治和乡村治理领域,此后,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主导整个1990年代乡村治理变革的关键因素,甚至直接决定了新世纪初期的一系列重大涉农政策的出台。税费改革承接了1990年代以治理农民负担为表征的乡村治理变革,并开启了世纪初以免税为主要表征的“后税费时代”。因而,理解税费改革对于窥视最近二十多年来的乡村治理变革,具有重大意义。
为什么要进行税费改革?从既有的研究来看,税费改革的主要动因在于中央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让基层政权“从收粮收钱中解脱出来”,而进一步解释的话,这两个主要动因其实来自于两种解释理路:前者归结于治理基层政权的“恶”,换言之,基层政权是造成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税费改革有利于“规范”基层政权的行为;后者则归结于调整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冲动,在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情况下,基层政权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从而客观上造成农民负担加重。这两种解释尽管大相径庭,但背后的逻辑却如出一辙,即认为税费改革是宏观政治结构所导致的结果,只不过,对这种结构的“不合理”解释不尽相同,前者归结于地方政府行为的错位,后者则归结于中央的责任。在这两种解释路径之下,税费改革一度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含义,以至于上升到了与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第三次农村革命”的高度。
但是,一旦这样解释,可能就无法解释为何在税费改革只实行了两三年的时间就宣布免征农业税。如果顺延这种解释,免税就是对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的确符合中央政府的政治逻辑,但是,却不符合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换言之,税费改革和免税实际上有质的差别,前者的主要取向在于完善征税制度,如何更好地向农民索取却又让农民负担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后者则明显是加速征税制度的消失。如果说税费改革交织了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治逻辑和地方政府完善税费征收制度的治理逻辑的话,那么,免税则纯粹只有中央“惠农”的政治逻辑,而将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放置一边。也正因为此,就有可能把税费改革理解成是中央政府“倒逼”基层政权变革的一种手段。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从税费改革到免税的跳跃,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突然,但从围绕税费征收工作的基层政权的治理技术变革上去考察,这种跳跃顺其自然。在中央于1990年出台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之时,已经预示了基层政权的税费征收工作开始陷入了困境。那么,为什么会陷入困境?分田到户以后,尽管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瓦解,农业税费的“平摊税费”的特征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征税单位却发生了改变,农业税从人民公社时期的分摊到生产队改变为分摊到户,而人民公社时期的公积金、公益金以及义务工等则变革为乡镇统筹和村提留,同样分摊到户,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税费的征收单位从之前的“队为基础”转变为一家一户。当分散的农户成为农业税费的基本征收单位时,基层政权的征收成本就会急剧加大。从微观治理成本的角度上看,基层政权在面对分散的小农时,得面临如何治理“钉子户”和“特困户”的问题。
在一定的税费负担下,总会出现“特困户”,但却是有限的。换言之,“特困户”本身并不会影响整体的税费征收工作。并且,建国以后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也要求各级政府“关心”贫困农户,对“特困户”的关照甚至融进了乡村道德传统。如此,对于“特困户”,基层政权普遍采取了消极的态度,“特困户”是不能治理的。问题在于,一旦出现“特困户”,并且,“特困户”可以在税费征收过程中获得不言自明的道义优势,逃离负担,就有可能出现“攀比”现象,由此,“钉子户”得以产生。在熟人社会当中,“钉子户”和“特困户”在技术上的区分是比较容易的,村庄里面的人都清楚谁是真正的“特困户”,谁是“钉子户”;但是,在税费征收的技术上,村民的区分却并不起关键作用,因为“钉子户”的逻辑不在于税费负担的轻重与否,而在于“攀比”,如此,只要“特困户”存在,“钉子户”也必然产生。19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分田到户的政治效应带来了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税费的征收工作并没有受“钉子户”的影响而陷入困境,如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基层政权在治理“钉子户”问题上的消极行政。然而,19世纪80年代初的消极行政,使得“钉子户”的数量大大增加,以至于开始影响税费征收任务的完成。为了治理“钉子户”,基层政权就必然采取一定的措施。采取措施的实质在于不断加大税费征收工作的力度,从负面的角度上看,税费征收的成本不断加大。到1990年代末,全国各地的税费征收工作基本上呈现了两个特征:一,开始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于“钉子户”,一方面实行奖惩制度,以调动农户积极性,另一方面,采取强制手段,甚至动用专政工具;二,乡村两级组织都完全陷入了税费征收工作,并最终使农业税费的征收成为大部分地区的基层政权的“中心工作”,“清遗留”成为常规工作程序。
仅仅从治理技术上来考察,这种税费征收技术的变革的确把“钉子户”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相应的,农民的负担水平也相对比较平稳。但是,如果考虑到1980年代中后期农民的增收水平已经放慢,而1980年代后期的负担又肯定会比1980年代前期重,农民的负担感会增加,而中央也会持同样的看法。最关键的可能还不在于此,而在于一旦基层政权动用强制手段甚至专政工具来进行税费征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就难保不出现意外,在判断“钉子户”和“特困户”上出现问题,以至于出现恶性事件。意外事件一旦发生,加剧了中央对农村形势的误判,其逻辑变为农民负担过重,“特困户”增多,归根到底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而基层政权显然更清楚,真正对征税工作造成挑战的不会是“特困户”,而是“钉子户”,在一定负担水平下,“特困户”总是有限的,而对于“钉子户”,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就会不断增加,最终让税费征收陷入困境。19世纪90年代前期的几个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尤其是1993年措辞严厉的文件,基本上把基层政权于19世纪80年代末形成的“硬”的手段堵死了,一旦没有这种手段,等于“软硬兼施”这一关键的工作机制就难以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权必须寻找替代手段。替代的手段有两种:一是提高农民的税费负担水平以填补“尾欠”(“遗留”)造成的财政空缺;二是启用乡村社会中的“恶人”,用非正式的“硬”手段代替正式的“硬”手段,控制“钉子户”。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少有地方仍然采取正式的强制手段,比如极端的专政工具,而更多地采用这两个替代手段。
提高农业税费对于解决因为“钉子户”和“特困户”所带来的基层财政问题,具有关键的意义。简单地说,本来是人均10元的负担水平,最后却可能演变成人均13元的负担水平,增加的3元,可能是这样分布的,其中1元用于激励工作人员(包括吃喝),还有1元用于补足因为工作量增大(“做工作”)的征收收本,另1元则用于填补最后仍然无法完全解决的“钉子户”和“特困户”造成的农业税费的缺额(“尾欠”)。从人均10元到人均13元的负担水平的转变,可以发现,这种替代手段是相当没有效率的,并且,还为滋生腐败创造了“合法性”条件。从治理技术上来看,这种手段仍然无法在事实上控制“钉子户”,更为可怕的是,还容易造成恶性循环。换言之,一旦采用这种手段,农民负担会在事实上增加,而农民负担一旦增加,“特困户”会随之增加,“钉子户”也会不断增加,如此,反过来又造成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如此,就有了“钉子户增加-农民负担加重-钉子户进一步增加-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的恶性循环。既然这种替代手段并不能解决税费征收困境,基层政权就会采取第二种替代手段:启用“恶人”。启用“恶人”,进行“恶人治村”有两个好处,一是熟人社会里面的“恶人”很清楚谁是真正的“特困户”,谁是真正的“钉子户”,由此,“拔钉子”相当准确;二是可以借用其“恶”的威慑作用,制服那些“钉子户”,甚至部分“特困户”,却又可以避免采用中央严令禁止的专政工具。如此,“钉子户”可以被治理。但是,一旦采用“恶人治村”这个手段,对基层政权产生的负面后果几乎是毁灭性的。它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进一步加剧了基层政权的腐败,形成了乡村利益共同体,二是进一步毁灭了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使得治理基层政权成为中央和社会各界的共识。
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三农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基层政权在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压力下所采取的两种治标不治本的税费征收手段,其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两种手段使得农民负担具有了实质性的增加,换言之,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以农民负担加重为核心的。围绕着这个核心,乡镇机构膨胀、基层政权腐化、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集中爆发。“三农问题”被看成是农村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而从爆发的逻辑来看,税费征收过程中基层政权治理“钉子户”的困境是一个关键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理解为何税费改革会提升到“第三次农村革命”的高度,其直接指向在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而深层次的指向则是为了解决治理“钉子户”的困境,包括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在内。2000年开始,中央开始在安徽进行税费改革试验,并很快于2002年左右全国推广。但是,当中央一旦进入税费征收的治理技术领域,却发现,“钉子户”的逻辑而不是“特困户”的逻辑主导了税费征收工作,即便是实行了税费改革,税费征收工作并没有减轻,“让基层政权从收粮收钱中解脱出来”并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判断“农民负担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如此,“深化”税费改革就成为必然选择:最彻底的办法是免税。
至此,税费改革和免税实际上采取的是“釜底抽薪”的方式。“釜底抽薪”并不仅仅在治理基层政权上有意义,而且,在治理“钉子户”上有意义。从后一个意义来看,免税实际上仍然只是遵循了“特困户”的逻辑,让“特困户”少一些,甚至消灭,但却回避了治理“钉子户”的问题。免税实际上替代了以“费改税”为特征的前期税费改革。而回应1990年代末的“三农问题”,免税也不是从解决“钉子户”问题的角度来审视乡村治理问题。换言之,免税没有回答分田到户后国家和基层政权重新面对分散的农户时如何治理“钉子户”的问题,从税费改革的逻辑来看,其政治逻辑是建立在基层政权如何治理“钉子户”的治理逻辑基础上的,正是“钉子户”的治理逻辑主导了1980年代以来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农民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问题的实质并没有根本改变,治理“钉子户”仍然是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