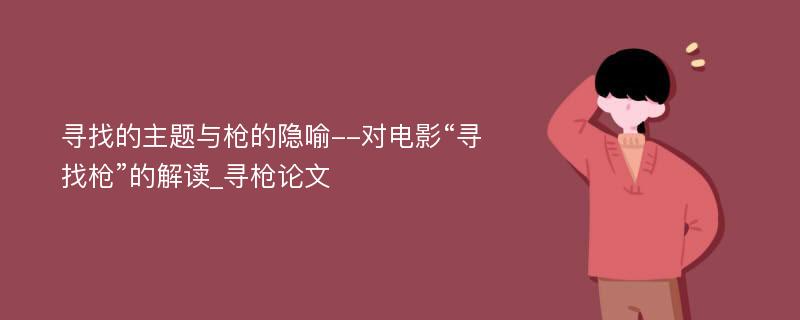
寻的母题与枪的隐喻——解读影片《寻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影片论文,寻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新导演陆川推出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寻枪》,这也是他的处女作。因为好 看,所以我认定陆川很有电影的气质与才华,接下来,他会有更好看的电影奉献给观众 。
好看的电影不寂寞,《寻枪》刚在大学生电影节推出,最新一期的电影刊物上就纷纷 发表评论文章,但读过以后,总觉得对《寻枪》的评价多停留在电影的表象上,如抓住 “悬疑”——“枪在哪里?用‘老树精’的话说是,找!于是情节如剥竹笋一样层层铺开 ……”,或是干脆不知陆川要表达什么:“我们无法概括影片到底要说明一个什么样的 主旨……但我们可以在人物的机智同时也实在导演的机智之外,感受到一份壮美。这份 壮美会让我们忘掉去辨别马山到底有多大的功过是非……”,甚至批评陆川作品真正触 及心灵的镜头太少:“《寻枪》作为陆川的处女作,从开始就走得这么隐,语言精致却 没有新意,少了处女作应有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等等。(注:以上引文均见《电影 评介》第251期38页至41页文章。)只有一篇文章略点到了主题:“他(陆川)表现的是所 有人的状态,是对于理想的追寻,是人类底层的焦虑……”但即便写到这儿,也没有能 对自己的观点再做深入的探讨。
引出几篇文章的观点,是想分析一下当今电影评论的“软骨”——理论准备的不足, 于是在文章中只能发布一些感想式的东西。《寻枪》当然好看,因为就故事的表层层面 而言,《寻枪》至少是数年里我看中国电影少见的那种“看了前面,实在不知道故事后 面将会怎样发展”的电影。但它又并不以情节取胜,它的故事实在很简单,一个乡村派 出所的警察赴婚礼吃醉了酒,醒来才知道自己的枪丢了,而且枪里还压有子弹,“要晓 得中国是禁枪的,偷枪的一定是要拿它去杀人,枪里有几颗子弹,那就是几条人命”的 话,让观众背上抽紧,于是和马山一起踏上寻枪的路,找啊找啊,突然就找到了:“局 长,枪和犯人都交到你的手里了”,悬疑虽设,但并不大;惊险虽出,但并不深;刺激 虽有,但又觉浅。然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陆川很好地把握了镜头语言——快速移动 、静态焦灼、客观追查、主观幻像、机位长跟、急促摇甩、所有演员表演到位,川话口 语透出乡情,观众被精致的镜语吸引,因而说明陆川懂电影,知道怎样把电影拍成电影 ,而不是把自己捆绑在情节上使镜头成为故事的附庸。时间长度仅有90分钟的电影,能 使观众既深深沉入那个胆敢“偷枪”的客观世界中思考,又不断追随“寻枪”者的主观 情绪而有所感受,不管对观众还是对市场,都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的应该是电影评论者来分析、研究这部电影的成败得失,或是挖掘出它的深层 含义,以供电影创作者从中获取经验教训,同时也通过对评论的阅读不断提高观众的鉴 赏水平。
分析一部电影,可以从多个层面入手,但一定要看清评判的对象,检点自己的评判利 器,有取有舍,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比如,《寻枪》这部电影,我们对它的道德层面的 审定,就只能置之空缺:偷枪者原来是卖羊肉粉的结巴刘,但他偷枪的动机在于要为被 假酒夺去生命的亲人和众多喝假酒致死的冤魂复仇。这是该由法律解决的事情,制造假 酒的元凶周晓刚已被法律监控,只是还为证据不足而暂时逍遥法外。陆川导演原本就不 想纠缠于此,否则本片就会演绎出一个公安部门侦破假酒大案的“九命奇冤”式的故事 来,或者也不必追究“政府失察”、“法律失控”等等有关的社会道德责任。而且马山 究竟与李小萌之间有怎样的感情纠葛,周晓刚与马山之间因李小萌又有多大仇情恨愫, 以致为什么参加妹妹婚礼竟使马山醉得人事不省,周晓刚一定要送马山防弹背心等等, 都不应是研究者对《寻枪》所发问的方向。我曾为马山的妻子韩老师追问马山“李小萌 的死你是不是感到难过”,马山坦率承认后,韩老师向马山道歉说:“我不该吃你的醋 ”一个细节感到困惑——这个道歉在暗示生活中的哪一处细节”,后来终于明白这个细 节表现的是中国妻子的美德——内疚于因自己的“吃醋”使丈夫承受精神压力而铸成丢 枪大祸。这个细节在电影叙事中只能算一个旁枝,是人物情感丰富化的辅助手段而已。
对《寻枪》要下功夫的,是它的文本层面,它的意义与价值都出于文本。前述的评论 文章都误于没有对文本下功夫。中国古语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当然百遍也绝 不是机械阅读,还应该有阅读的方法、评论的武器。
《寻枪》导演陆川在影片中最用力经营的,包括情节,包括镜语,包括音响,包括表 演,一切手段都为之努力的,就是“寻找”,“寻找”成为影片的立身之本。没有“寻 找”,也就没有了《寻枪》。“寻找”,自古以来就是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母题(motif ),加拿大文艺批评家N·弗莱更进而把“寻找”确定为神话中的最中心的故事。从古希 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对金毛羊的寻找,到民间文学中大量类似《找幸福》类型故事 中或是幸福或是宝物的寻找,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和中国 新新人类电影(?)《十七岁的单车》中同样对自行车的寻找,都是“寻找”母题的具像 化。“寻找”是人类千百次不断重复的动作,也就成为文学艺术中不断出现的意象。“ 寻找”是表层的,表象的深处则是对“寻找”客体的潜意识欲望,这种客体必然会改变 寻找者的命运:找得到会改变,找不到也会改变,所以非找不可,甚至有时主观上并不 明白为什么要去寻找。(注:由于儿童深受童话影响,很适宜成为“寻找”母题作品的 阅读者。1958年我国第一部中法合拍的彩色儿童电影《风筝》,就是以寻找风筝的主人 为叙事主线的电影。电影并不解答法国儿童比埃罗等为什么要寻找风筝主人的理由,而 只是暗示寻找的结果是得到了“友谊”。同样,侦破片的母题也是“寻找”——找出作 案的元凶,因此,这类影片便也成为一大部分影迷的“童话”。)而“寻找”母题向文 本与观众两方面的延伸,即表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主题、组织原则和要求观众把握的 中心意识,则是对秩序的追求与重建。具体到《寻枪》,便是马山的战友——他的上级 对马山的要求,他的朋友老树精等人积极而不得法的介入,以及他的妻子韩老师、儿子 马冬包括妹妹、妹夫等人对他的无言或有言的鼓励。当然从生活常理以及叙事逻辑两方 面都要求导演陆川必须如此设置,但更重要的一条是:“寻找”母题以及它背后深藏的 原型(archetypes)——重建秩序,也恰恰是观众对马山的行动请求。导演与观众在一个 母题上很容易取得相通的价值趋向,在古老的潜在的原型上很容易产生作者与观众在情 绪上的共鸣。这便是《寻枪》容易得到观众好口碑所使用的高超技巧。
所谓原型,N·弗莱解释得最精湛:“原型是一些联想群(associative clusters),与 符号(sign)不同,它们是复杂可变化的。在既定的语境中,它们常常有大量特别的已知 联想物,这些联想物都是可交际的,因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很熟悉它们。”(注:N 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 p.102.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 71年版。笔者手中暂无中文译本。本文也不想在概念上作过多纠缠,只是引进它们以便 更准确地把握《寻枪》。)那么《寻枪》中就有了两个原型意味的联想群,一个是上文 所叙述的“寻找”,另一个就是作为警察的马山反复念叨反复追寻的目的物——那把暂 时丢失的枪。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枪在文化意义上的象征都在指涉权力。《寻枪》并没有枪符 号化——单纯作为政治权力对待,而是尽力把它原型化,从而使枪具有多种相位(phase s)(注:在弗莱《批评的解剖》艺术中,对文学的象征表现做了五种相位的划分:文字 相、形式相、描写相、神话相和寓意相。在每一相中,象征分别成为叙述、母题、意向 、原型和单子(monad)而出现。单子是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在 他的著作《单子论》中提出的关于宇宙万物构成的哲学命题。)的表现。用中国文化熟 悉的思想方式,我们可以发现来自镜头语言中的多种原型相位。
第一个相位:马山是在被妻子愤怒地从窗上叫起来,阅读儿子的“流氓”作文后要好 好教训儿子一顿时,才发现枪丢了。找不到枪,不仅顿时使做父亲的威风完全消失,而 且迅速把马山拖入到无尽的恐慌与焦躁之中。在这个相位中,枪象征着父权,有枪就可 以向儿子发威,没了枪父亲也就无法再成为父亲——李小萌被杀,马山因嫌疑最大而暂 时被拘留,儿子马冬前来探望,探望也许是父子关系的表露,但马冬一席话却鲜明揭示 枪与父权的象征关系——“我知道你把枪丢了,我正在积极想办法帮你找枪,也有了一 点线索,但是今后我要和你做个约定: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怎样都不许再打我,也不许 再骂我”——马山只能无奈地点头接受。后来证明马冬并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探望”一场戏的意义并不在探望,而在于马山的父权因丢枪而丧失。
第二个相位:马山丢了枪,除发疯地寻找以及在想象中向所长承认之外,他有很长时 间向自己的妻子韩老师隐瞒。而当他不得不向妻子说明真相后,妻子因为与自身的利害 关系开始同情他,并在一个晚上把儿子打发到楼上睡觉,想通过和马山做爱暂时解脱一 下马山的焦虑情绪时,马山表现出了性的无能。生活中因情绪波动而导致如此状态的情 况常有,但电影的叙事则不是全为了加点“作料”。这也是一个象征,是枪对夫权的隐 喻——影片结束处,马山终于把偷枪者铐在自己手上,并寻回了枪后,他唯一想做的事 情就是让自己的灵魂来到儿子就读、妻子工作的小学校,看看自己的儿子与妻子,这是 马山的潜意识——我寻回了枪,我就又是你们值得骄傲的好父亲、好丈夫!
第三个相位,是周晓刚追着马山要送他防弹衣的情节。按情节推论,周晓刚是知道李 小萌是被谁打死的,因而也就知道偷枪者是谁。假酒的事与偷枪的事相比,因自己也处 在死亡危险之中,因此后者的严重性一定大于前者,但周晓刚不去积极揭发偷枪人,反 倒追着送马山防弹衣,这绝不是有自己弟弟和马山的战友之情所导致,恰是对没有了枪 的警察的一种蔑视性的哀悯——于是,枪在这里又成了国家权力即王权的象征,甚至那 个偷了枪的结巴刘,在日常很有威风的马山面前也变得不结巴起来,原本做抹稀泥、和 浑水的瓦匠现在也敢在警察面前高声叫卖“羊肉粉”了——什么是羊肉粉?无非是“挂 羊头卖狗肉”和“粉”状的稀泥软蛋而已。没有了枪,你马山就再也不是王权的代表。
马山终究是机智的,他在观众无限的猜测中终于化装成周晓刚,用自己的肉身引出了 偷枪人。他的伤看来不轻,所以有了一段出窍的魂灵飘荡到学校的镜头。他也终于在闻 声赶来包围偷枪罪犯的警察中站了起来,但影像的三次晃动使我们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 挺过来、活下去,结局只能在马山仰天大笑的定格中结束。但我们可以说:枪找到了、 罪犯抓住了,只是马山智慧的胜利,是马山牺牲精神的胜利,而不是我们观众已经早已 习惯的父权、夫权以及王权的胜利,所以很多观众看过电影以后,只记得扮演马山的姜 文,而不记得《寻枪》所能给观众的教诲意义是什么,从而导致有一位评论作者,竟然 说出陆川只是把单人旁三点水写得有模有样,看陆川像看有希望的孩子那样可爱的让人 丧气的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