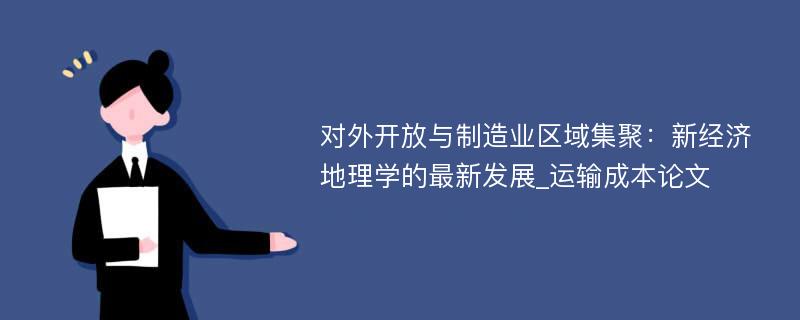
对外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集聚: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对外开放论文,新经济论文,制造业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0)03-0062-09
制造业在一国内部空间分布的不均匀一直是学术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研究的重心在于决定制造业区域非均匀分布的因素分析。对于产业空间分布的研究属于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空间经济学发端于德国的古典区位理论,该理论的奠定者当属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Von Thunen)。冯·杜能在其1826年的著作《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创立了农业区位理论,并探讨了工业在大城市形成集聚的七大原因,这恰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的向心力[1]。20世纪初叶,德国经济学家兼文化社会学家韦伯(Weber)创立了产业区位论,其1909年的著作《工业区位论》探讨了工业在地区间迁移的原因,并将影响工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分为区域性因素(regional components)和非区域性要素(non-regional factots)[2]。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了“中心地理论”[3]。之后的另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勒什(August Losch)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在其1939年的著作《区位经济学》中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之市场区位理论[4]。上述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理论构成了古典区位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古典区位理论的研究视角是孤立的区位,尚未触及到区域间的贸易问题。而且上述传统理论都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定前提下研究产业空间分布问题,这种分析方法所具有的同质性空间的非凸性特征无法同时支撑贸易均衡和区位均衡。因此,要想建立一个用于解释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和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必须要采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20世纪90年代,以藤田(Fujita)、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Venables)等为代表的学者在规模报酬递增与不完全竞争市场为特征的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引入了运输成本、外部经济、要素流动以及路径依赖等因素,来研究产业集聚与扩散,并最终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创立,则标志着区位理论向主流经济学的回归。新经济地理学将区位理论与新贸易理论有机整合,成为迄今为止研究产业集聚的主流经济学理论。
然而如若仔细推论便不难发现,无论是克鲁格曼、Fujita和Venables的早期努力,还是后来别的学者的研究,都撇开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即分析所涉及的区域经济对外开放对该地区内部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后期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国际贸易与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主题。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一国或地区内部的制造业集聚在贸易政策自由化乃至加入经济一体化组织前后发生了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表现也不同。有的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集聚被对外开放打破(Rosen and Resnick[5];Hanson[6]),而有的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则因对外开放而进一步强化(Armstrong[7];Sala-i-Martin[8];Puga[9])。由此引出了一个新的论题,即对外开放或贸易自由化对一国内部制造业原有集聚模式的影响。多年来围绕这个论题的研究络绎不绝,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个层面属于理论的,就是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放作为重要的外生变量引入到“核心—外围”模型中,来考察对外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集聚的关系。另一个层面属于实证的,就是从国别找出对外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集聚之间的联系。
一、对外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集聚:理论模型
对外开放与一国内部制造业集聚关系理论分析的开拓者当首推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在与人合作的一篇题目为“贸易政策与第三世界都市区”[10]的论文(Krugman and Elizondo)中,首次把对外开放纳入到“核心—外围”模型之中,将新经济地理学原有的核心—外围两地区模型拓展为三地区模型,主旨在于分析对外开放与一国国内制造业集聚之间的关系,由此引发了对这一论题的理论研究兴趣。
多年来围绕这个论题的研究络绎不绝,按照模型得出的结论,可将它们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对外开放会导致原有制造业集聚格局的打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Krugman and Elizondo[10]和Behrens et al.[11];另一类则认为对外开放会导致制造业区域集聚,较有代表性的是Alonso-Villar[12]、Monfort and Nicolini[13]、Paluzie[14]、Crozet and Soubeyran[15]以及Brulhart et al.[16]。
(一)对外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重构
Krugman and Elizondo的理论模型是以墨西哥加盟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制造业中心空间变迁为典型案例,考察发展中国家加入一体化组织的制造业集聚效应。
Krugman and Elizondo模型的结构如下:整个世界由本国的两个地区(地区1与地区2),和国外的地区(地区0)构成。每个地区都只有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和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其中,本国的工人在地区1和地区2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但无法跨国流动。
进一步地,假定城市为线形的,工厂设立在城中心。每个工人拥有1单位的劳动,并需要1单位的土地生活,他们分布在这条线形城市上。对于居住在城外的工人去城中心的工厂工作,需要支付一定数量的用劳动衡量的交通费;对于居住在城中心的工人而言,不需要支付交通费但需要支付同等数量的地租。在这些假定前提下,Krugman and Elizondo模型利用DS的垄断竞争模型以及“冰山”型运输成本构建起一个均衡方程组,并赋予本国对外运输成本三种不同的值来分别代表高、中、低的三种对外开放程度,进而观察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一体化是如何影响劳动力在国内两地区间分布的。
该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对于本国的两地区而言,当对外运输成本较高时(即对外开放程度较低时),制造业全部集中到其中一个地区是唯一稳定的均衡。当对外运输成本较低时(即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时),制造业平均分布在这两个地区是唯一稳定的均衡。当对外运输成本居中时,制造业的集聚与分散生产同为稳定的均衡。因此,由相对封闭经济向面对国际大市场的开放,会导致一国内部原有制造业集聚格局被打破,对外开放与原有集聚中心之间存在某种负相关关系。
Krugman and Elizondo模型得出的结论得到了Behrens et al.的支持。Behrens et al.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四个地区的模型,来同时考察国际贸易和区际贸易对一国国内制造业地理分布的影响。
该模型认为,其他条件不变,降低一国内部运输成本将会导致其国内制造业集聚,这与核心—外围模型的推论一致。但是当国际运输成本降低时,其他条件不变,国内厂商会通过分散生产降低国内竞争来应对国外厂商的竞争。因此,国际贸易开放会导致每个国家国内生产的分散。如果国内市场一体化和对外开放同时进行,那么两者对每个国家内部制造业分布的影响则变得不确定。
(二)对外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集聚
Alonso-Villar将Krugman and Elizondo模型拓展到了包含三个国家的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一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其内部的制造业空间分布还与它相对于周边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若该国的制造业水平较高(在模型中表示为人口规模大),则对外贸易会使该国的厂商在运输成本和拥挤成本的作用下分布在边境地区。若该国的制造业水平较低,而邻国的制造业相对较发达,则对外贸易会促使本国的厂商集聚在内地地区,目的在于规避外国厂商的竞争和失去国内市场的风险。
Monfort and Nicolini构建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四个地区的核心—外围模型,同时考察了区际运输成本和国际运输成本对国内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区际运输成本和国际运输成本均会影响到国内厂商的区位选择。具体来说,随着国际运输成本和区际运输成本的降低,厂商将会在国内某一个地区形成集聚。而且,对外开放会进一步强化区际运输成本降低时所产生的制造业集聚。
Paluzie建立了一个与Krugman and Elizondo模型类似的三地区模型,并引入了农业部门。该模型中的向心力是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离心力是分散的农村市场的需求。在这两种作用力的作用下,Paluzie得出了与Krugman and Elizondo模型完全对立的结论:当对外运输成本较高时,国内制造业的平均分布是唯一稳定的均衡;当对外运输成本居中时,制造业集聚和平均分布同为可能的稳定均衡;当对外运输成本较低时,国内市场就演变成为核心—外围的生产格局。
Crozet and Soubeyran在Paluzie的模型基础上,分别考察了一个国家内部无差异的两个地区和地理位置有差异的两个地区的两种情况。该模型得出的结论为,对于两个无差异的地区,对外开放会使得制造业生产集中到其中一个地区,但是这个地区并不确定。而对于两个地理位置不同的地区,对外开放则会促使国内制造业集聚到靠近国外市场的边境地区。
Brulhart et al.与Paluzie一样,也构建了一个三地区模型并引入了农业部门。该模型针对本国与外国的工农业产业结构相同与不同的两种情况分别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当本国和外国的产业构成相同时,如果本国的两个地区完全相同,那么对外运输成本的降低将会导致制造业集中在其中某一个地区;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不同,那么对外运输成本的降低将会促使制造业集聚在靠近国外市场的边境地区。这与Crozet and Soubeyran的推论基本一致。但是,Brulhart et al.进一步强调,如果内陆地区在开放前就已经拥有较大份额的制造业,那么即使在对外运输成本降低时,内陆地区仍然维持其制造业集聚中心的地位。此外,当本国和外国的产业结构不同时,如果外国的农业份额比本国高(即本国的制造业比重比外国高),那么对外开放将会导致本国制造业集聚在靠近海外市场的边境地区。
(三)两类模型的比较
通过对上述理论模型的回顾可以看出,关于对外开放与一国内部制造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事实上,如若仔细推敲上述模型便不难发现,导致模型结论分歧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二。首先,模型背后的作用力不同。在Krugman and Elizondo模型中,打破国内原有制造业集聚的离心力是原有集聚中心存在的拥挤成本;而在认为对外开放导致国内制造业集聚的模型中,离心力是无法跨地区流动的农业部门。因此,在这两种不同离心力的作用下,上述这些模型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其次,建模策略的差异。强调对外开放导致国内制造业集聚的模型采用的是DS框架和冰川运输成本,而认为对外开放导致国内制造业区域重构的Behrens et al.模型采用的是线性需求函数和线性运输成本。这使得贸易和运输成本在前者的模型中以乘数方式影响产品价格,而在后者模型中以加法的方式影响价格。当运输成本是加法形式时,就不存在价格对运输成本的反馈效应,但是在乘数方式中,却存在着这种反馈效应。因此,贸易和运输成本以何种方式进入模型,也会影响到模型的结论。
二、对外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集聚:经验研究
大量学者针对上述理论模型的推论对不同的国家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也是两面的。一类学者的实证结论表明对外开放程度与制造业集聚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联系。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有:Armiti[17]、Rabellotti[18]、Bhattacharya and Bloch[19]、Bair and Gereffi[20]、Kuncoro and Dowling[21]、Pons et al.[22]以及Crozet and Soubeyan;一类学者的实证结论表明在对外开放程度与制造业集聚程度之间存在负相关联系。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包括:Ades和Glaeser[23]、Hanson[24]、Paluzie et al.[25]、Tomiura[26]、Beine and Coulombe[27]以及Sanguinetti and Martincus[28]。
(一)对外开放促进制造业区域集聚
Armiti对意大利、比利时、法国、英国和德国在加入欧盟前后的制造业集聚程度变化进行了考察。利用基尼系数和Balassa指数计算的结果表明,除了英国外,其他国家的专业化和制造业集聚在开放市场后均有所上升。
Rabellotti以墨西哥Guadalajara地区的制鞋业集聚为例,分析了墨西哥在1980年代以后采用的贸易开放政策对该地区集聚的影响。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认为,对外贸易的开放不仅促进了制鞋业内部厂商之间合作程度的提高,而且国外市场对鞋子的大量需求也为国内制鞋厂商创新、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些贸易所带来的动态利益使得Guadalajara地区的制鞋业集聚程度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而提高。
Bhattacharya and Bloch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澳大利亚102个四位数制造业行业集聚在1978-1985年演进过程,尤其考察了贸易政策对国内制造业空间结构调整的影响。通过对行业的上期集聚程度、市场规模、资本密集度、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程度和进口产品密集度的回归分析发现,澳大利亚的制造业集聚在以每年10%的速度自我强化。此外,行业集聚的调整速度会随着有效关税率的降低而提高,这意味着,自由贸易有助于澳大利亚制造业加快行业集聚的速度,而且这种自由贸易的影响比国内厂商竞争的影响更有力。
Bair and Gereffi以案例的方式分析了贸易开放对墨西哥Torreon地区牛仔衣生产集聚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为,出口外向型的行业发展战略使得Torreon地区牛仔衣生产进入了全球商品链,巨大的国外市场需求推动了当地牛仔衣生产集聚的发展。
Kuncoro and Dowling对1991-1996年间印度尼西亚107个两位数制造业行业的空间地理分布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行业规模经济、资源密集度、进口密集度、人均收入、行业竞争度、劳动力成本、行业出口倾向以及外商投资变量的回归分析发现,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的空间集聚起到了显著性的促进作用。
Pons et al.运用西班牙45个省9个行业1856、1893和1907年的数据分析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和对外开放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通过对空间基尼系数的计算与对比分析发现,国内市场一体化导致了制造业集聚,而且对外开放进一步强化了国内的这种制造业集聚格局。
Crozet and Soubeyan考察了罗马尼亚在加入欧盟前后制造业集聚的变化。通过对罗马尼亚1991-1997年41个地区的分析显示,对欧盟其他国家的开放进一步强化了边境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接近海外市场比接近国内市场对制造业集聚的作用更明显,进而再次肯定了对外开放对罗马尼亚国内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
(二)对外开放削弱制造业区域集聚
Ades和Glaeser对Krugman and Elizondo模型的对外贸易与地区经济集聚负相关的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对85个国家1970、1975、1980、1985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结果表明,贸易依存度与该国最大城市的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而贸易壁垒(用进口关税率表示)则扩大了中心城市的规模。此外,对公元前50年的罗马、1670年的伦敦、18世纪的日本、20世纪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和墨西哥城的案例分析,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观点。
Hanson利用1930-1988年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对墨西哥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在NAFTA建立之前,尤其是在1980年代之前,墨西哥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实行进口替代制造业化战略,严厉保护国内市场,由此导致了产业集聚于首都墨西哥城一带,即远离墨美边境的区域。从NAFTA成立前数年开始,墨西哥一改贸易保护政策而为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到NAFTA成立而实现与北美市场的一体化,由此对原有制造业集聚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导致了墨西哥制造业中心开始由原有中心向美墨边境地区的移动。因此,Hanson指出,贸易政策在地区经济发展格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制造业集聚中心是进口替代战略的副产品,而对外开放则有利于国内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散。
Paluzie et al.检验了欧洲一体化对西班牙50个省30个行业在1979-1992年间集聚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西班牙的制造业行业并没有因为对欧盟其他国家的开放而变得更加集聚。
Tomiura考察了日本1985年日元升值带来的进口增加对国内制造业分布的影响。通过对1985-2000年41个地区21个行业的回归分析发现,进口的增加导致了日本制造业在各地区的分布更加均匀,尤其是进口比重高的行业。他们认为,进口打破了地区投入产出的关联,因此降低了制造业的区域集聚。
Beine and Coulombe运用加拿大10个省1980-2001年四位数制造业行业的出口数据分析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CUSFTA)与加拿大制造业专业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动态回归分析发现,美加自由贸易导致了各省制造业生产的多元化,表明制造业在各省的分布趋于分散化。
Sanguinetti and Martincus以阿根廷为例分析了贸易开放和国内制造业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省际层面1974、1985和1994年四位数制造业行业就业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导致了国内原有生产集聚的分散。
Faber[29]将新经济地理学与比较优势理论向结合,实证考察了墨西哥制造业在1993-2003年间的空间分布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对美国出口比重较高的行业在美墨边境地区增长迅速,而进口比重较高的行业则在墨西哥内陆地区增长迅速。这一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对国内制造业行业地理分布的影响并非完全一致,而是与行业的进出口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关于中国对外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集聚问题的研究
有关对外开放与一国内部制造业区域集聚的论题,近期的研究焦点开始聚集于中国。Hu[30]从理论模型的角度,Fujita and Hu[31]、黄玖立和李坤望[32]、贺灿飞和谢秀珍[33]、Ge[34]、金煜等[35]以及赵伟和张萃[36][37]从经验检验的角度分别对此论题进行了研究。
Hu针对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构建了一个包含三个地区三种生产要素的核心—外围模型,来考察对外贸易和农民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两个因素对中国制造业集聚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结果显示,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集聚的程度不断加强。
Fujita and Hu采用了内陆与沿海制造业总产出比、各省制造业产出变异系数、各行业比重最大的4个省份三项指标测算中国1985-1994年的制造业集聚,发现东部沿海是制造业集聚的中心,而且对外贸易和FDI是促成该制造业集聚的主要因素。
黄玖立和李坤望分别对1985年和1995年中国制造业布局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地区的地理优势、对外贸易、外商投资、自然资源以及市场潜力是影响制造业集聚的主要因素。
贺灿飞和谢秀珍引入了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产业联系、外部经济、产品差异、市场竞争程度以及经济全球化变量来解释中国制造业在1998-2003年的地理集中。回归结果表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及经济全球化是决定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因素。而且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判断出,经济全球化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最重要的因素。
Ge实证检验了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在Midelfart-Knarvik的计量模型基础上,利用1990-1999年省际层面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区域集聚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金煜等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等因素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并运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随机效应和工具变量的回归方法对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以及对外开放等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无论采用何种回归方式,对外开放都是导致中国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显著性因素。
赵伟和张萃[36]利用1999-2003年20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分三个层面实证考察了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中的FDI因素:一般层面之FDI渗透与制造业集聚之间的关联性;行业层面之集聚诸因素中的FDI因素;集聚程度有别层面之FDI集聚效应差异。借助成熟模型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在所有这三个层面,FDI的行业空间集聚效应均明显可鉴。研究还显示,即使在高集聚行业,FDI迄今尚未产生新经济地理学推断的倒U型效应。
赵伟和张萃[37]鉴别出了对外开放促进制造业区域集聚的三个机制,分别为制度转型机制、技术溢出机制和基础设施机制,由此构建了一个机理系统。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现实数据对上述机制进行了经验性检验。研究表明,对外开放主要通过制度转型机制和基础设施机制来对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发生作用,对外开放的技术溢出机制尚未显现。
四、“二重开放”:一个新论题
通过前面对已有文献的回顾不难看出,关于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集聚,经济学长期以来主要关注了区域或一国总体的对外开放,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彼此开放。赵伟等人[38]指出,虽然克鲁格曼等人的新经济地理学涉及区域间贸易开放,但由于其主旨是将空间因素融入主流经济学框架下,单纯考察贸易流动、要素流动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并最终将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融为一体,而非分析区域经济本身,因而未给予区域经济与国民经济以严格的区分。因此,克鲁格曼等人的“核心—外围”模型,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经济格局,也可以用来解释国内区际经济结构①。
事实上,就经济开放的内涵而言,国民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质的差异。通过对先行工业化国家区域经济开放历史考察,赵伟[39]的研究认为,一国的经济开放可从两个层次来把握:一个是国民经济总体层次,另一个是其内部各区域经济个体层次。前一个层次的开放,属于单纯的经济国际化开放,后一个层次的开放,则带有“二重开放”的特征:一重是一国内部特定区域经济面向国外其他国家的开放,另一重是该区域经济面向国内其他地区的开放;前一重开放可以称作“区域经济国际化”或曰对外开放,后一重开放可以称作“区域经济区际化”或曰区际开放②。由此提出区域经济“二重开放”说。
进一步地,赵伟等人[38]的研究指出,一国内部之特定区域经济的对外开放与区际开放之间的内涵与性质,也严格有别。一国各地区经济的对外开放,汇聚成了该国总体经济的国际化浪潮,构成了该国经济国际化的基础。该国内部各区域间的经济开放或区际开放,则促成其内部区际市场(Interregional market)或全国性市场(National market)的形成。而全国市场,则是一个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依赖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的前提条件。简而言之,区域层次的二重开放,既是一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基础,也是该经济市场化的基础。对于一个由众多地区构成的大国来说,区际开放的意义尤其重大。
中国经济作为一种转型经济,其独特的经济转型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一些独特模式,其中在区域经济开放进程上,也呈现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通过与先行工业化国家区域经济开放的比较,赵伟[39]指出,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与一般市场经济的区域开放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具体说,一般市场经济,区域经济“二重开放”同时诉诸两个市场,分别为国内区际市场和国际市场。然而中国的情形则不然,由于中国是在计划经济因而市场荒漠基础上开始转型的,改革开放初期未有国内市场,且国内市场重建要比对外开放困难得多,因而区域经济开放采取了由国际化切入的战略路径,对外贸易与引进外资超长发展而内部市场重建进展缓慢;只是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才开始强调对内开放。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开放路径总体上是先国际化后区际化。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的考察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国内区域间开放滞后于对外开放。在众多的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钟昌标[40]、沈坤荣和李剑[41]、Poncet[42]、陈敏[43]等人。其中,钟昌标通过对中国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现状的分析认为,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不发达,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国内市场自然扩张的延伸,国际贸易迅猛发展与国内区际贸易严重滞后形成鲜明对照。沈坤荣和李剑利用1978-1999年的经验数据证实,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影响,但由于国内市场分割的存在,国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负。Poncet使用边界效应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各省在1987年、1992年和1997年三个时点上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结果证实,中国各省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市场,相反,国内贸易流量的下降则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很低。陈敏等利用国内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构造出度量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程度的指标,测度结果揭示,中国国内市场在总体上是走向整合的,而且对外开放的发展通过改变地方政府决策环境、加速市场竞争、改变观念等渠道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综合上述几个层面的研究,无疑可以归纳出如下结论:一国区域层面的经济开放,带有国际化与区际化并行的“二重开放”特征。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其区域经济“二重开放”同时诉诸国内区际和国际两个市场。然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一种转型经济体,其区域经济开放则是一种先国际化后区际化的独特路径模式。
五、结论与启示
从现有的关于对外开放与一国内部制造业区域集聚的理论模型可以看出,由于假定条件和建模策略的不同,模型结论存在着分歧:其中,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对外开放与国内原有制造业集聚之间存在着某种负相关关系;而Alonso-Villar等学者则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对外开放会导致国内制造业区域集聚。从现有的实证文献来看,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检验,也得出了与理论模型一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从对中国对外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集聚的研究来看,无论是理论模型还是实证检验,均表明对外开放导致了国内制造业区域集聚。
诚然,不管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对外开放与一国国内制造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均不能用一个简单化的结论来回答。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众多文献使人们能够以多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已有的理论,实际上是对对外开放与一国国内制造业集聚关系问题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以西方国家为背景进行的。在这些西方国家中,国内市场的统一远早于对外开放。研究者往往把统一的国内市场因素视为给定的外生变量,从而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对外开放因素对国内制造业区域集聚的影响上。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统一的国内市场并未完全形成,地区间开放程度较低,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区域经济开放是一种先国际化后区际化的路径模式,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巨大差异,这意味着那些以统一的国内市场为暗含前提条件考察对外开放与制造业集聚的理论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现实。有鉴于上述认识,在探讨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发生作用的机理时,如何在对外开放和区际开放同时兼顾的框架下进行,进而揭示出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二重开放与制造业集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收稿日期]2010-04-20
注释:
①例如,“核心—外围”模型既可以用于分析制造业在一国内部两个地区之间的分布,也可以用于分析制造业在不同国家间(比如欧盟)的分布。
②也就是国内市场一体化,即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开放。
标签:运输成本论文; 经济地理学论文; 新贸易理论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