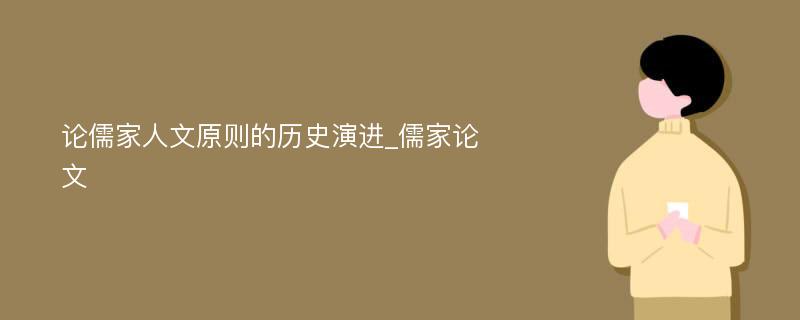
论儒家人道原则的历史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人道论文,原则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年来关于儒学的讨论中,儒学重人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人们似乎没有足够地注意到这一事实与下列事实的矛盾:具有重人道传统的儒学,不仅没有生长出近代人道主义,而且被指责为反人道即“吃人的礼教”。要解释这一矛盾,就要考察儒家人道原则的历史演进过程。
一、先秦:儒家人道原则的奠基和确立
儒家人道原则由孔子奠定,经孟子和荀子而确立。这一过程内含着仁和礼的紧张及其协调。
孔子以“爱人”作为仁的根本规定,主要有两方面的内涵:就人和其它物类的关系而言,前者比后者重要;就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应当互相尊重和友爱。由此奠定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道原则: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
在人和其它物类的关系上,孔子的“仁者爱人”,不仅表现在关心人重于关心牛马这类自然物,而且表现在事人先于事鬼神。他的“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强调有人格尊严的主体(君子),不能将自己混同于其它的器物。这里的含义是,人较之其它物类有更高的价值,就在于不是工具(器)而是目的。
既然每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工具,那么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应当是相互尊重和友爱。孔子之仁在这方面不仅表现为把“恭、宽、信、敏、惠”规定为仁爱之德,也不仅表现为以“忠恕之道”作为人与人之间实行仁爱的方法,还表现为视孝悌为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的基础即“仁之本”。以孝悌为仁之本,一方面是把血亲之爱引伸到一般的人际关系中去,展开为普遍之爱,即由孝悌而“泛爱众”;另一方面是要求普遍之爱的仁应当像孝悌那样以内在的自然情感为基础。孝悌作为血缘关系,具有自然性,其情感内涵无疑也具有自然性。因此,把血亲之爱提升为普遍的爱人之仁,是自然的人道化;而把普遍的爱人之仁与自然情感相联系,则是人道的自然化。这反映了孔子之仁与自然原则的相融性。自然和自愿有一个共同点,即排斥外在的强制。因此,孔子之仁亦和自愿相贯通。这就使得孔子的人道原则具有出于自然而非伪饰、出于自愿而非强制的一面。
然而,孔子的人道原则存在着仁和礼的紧张。孔子维护“克己复礼为仁”的旧观念,礼即周礼的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原则就不能不渗入其爱人之仁。这就形成了孔子之仁的另一面:“爱有差等”,即根据血缘的亲疏和等级的尊卑,实行不同的仁爱。从血缘关系上看,“爱有差等”把亲人手足之爱放在优先和首要的地位,因而儿子可以为其父亲隐瞒偷窃的行为(见《论语·子路》)。从等级关系上看,“爱有差等”对处于不同等级地位的人施以不同的爱,即在下者对上者的爱,表现为顺从,孔子以“无违”(《论语·为政》)来界说儿女对父母之爱的孝;而在上者对在下者的爱,则表现为赐以恩惠,孔子把“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作为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仁爱。
这样,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为仁就存在着矛盾。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爱有差等”的血亲优先抵销了“泛爱众”、忠恕之道的推己及人所蕴含的对人的普遍尊重。就人与其它物类关系而言,“爱有差等”把每个人都置于尊卑等级序列中,而且卑者对尊者的爱就是顺从,前者就成了后者的依属物;尊者视卑者为使用的工具,只是在使用时要施以恩惠。这样,原先把人和其它器物相区别的爱人之仁就流于抽象和空泛,人由抽象的目的沦为现实的工具地位。更重要的是,“克己复礼为仁”隔绝了爱人之仁的人道原则与自然、自愿的联系。礼作为由人订立的制度和规范,具有非自然性,同时孔子又赋予其强制性:“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所以,“克己复礼为仁”具有把人道原则和自然、自愿相分离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一旦成为现实,就会走向人道的反面,即虚伪的做作和强制性的束缚。
可见,孔子之仁虽然奠定了儒家人道原则,但是与其紧密相联的礼阻遏了这一原则。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化解了仁与礼的这种紧张,儒家人道原则得以确立。
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他以性善说为根本,认为仁之端倪是每个人先天具有的内在自然情感即“恻隐之心”,把这一端倪扩大,便形成仁德。内在的仁之端不仅是个人仁德的萌芽,也是社会政治秩序即仁政的基础。仁政以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内涵,因而在其旗帜上写下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是由内(内在的善端)而外(外在的社会政治秩序)来拓宽和深化孔子之仁的人道原则,使其从一般的伦理规范进而为一切社会政治秩序的准绳。由仁扩至仁政,要求对社会成员普遍施以人道,进而提出民贵君轻,无疑削弱了孔子与礼相联的爱有差等之仁对人道原则的阻遏,使儒家人道原则呈现出民本主义的亮色。同时,孟子的性善说强调仁义是将内在的自然情感唤醒,从自发变为自觉。这就使人道原则和自然、自愿有着某种联系,疏通了被孔子以礼所阻隔的这一联系,因而具有更能打动人的原始的人道情感。
荀子着重发展了孔子礼的学说。他以礼为人道的最高准则:“礼者,人道之极”(《荀子·礼论》)。不过,他的礼与孔子之礼有所不同:后者以仁释礼,不重刑政;前者则摄法入礼,礼成为法律和伦理的总纲。因此,以礼为人道之极意味着人道原则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礼)而展现。这是以性恶论为出发点的:人性作为恶的禀赋,与动物的自然本性相差无几,而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形成服牛驾马的社会群体,是因为用外在之礼控制和制约内在的恶之本性,从而消弥了人际间的利益争夺。这就由外(外在的社会规范)而内(内在的恶之本性)来发挥和衍化孔子的人道原则。因为他化解了孔子之礼对其人道原则的排斥性。他指出法的基本特点是公正无私,因此,其所谓的礼尽管包含着等级分界,但摄法入礼就突出了礼像法那样的公正无私:“虽王公士大夫之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同上)。这种在礼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性,对孔子之礼阻遏人道原则的宗法性、等级性有所冲破。同时,荀子认为礼的外在制约最终要通过内在的意志选择而实现,他的“形可劫而使诎伸,心不可劫而使易意”(《荀子·解蔽》),就表达了这一意思。这就把作为人道之极的礼和出于意志自由的自愿相联系,克服孔子之礼对自愿的忽视。
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仁和礼发展了孔子的人道原则,从而化解了这两者在孔子人道原则中的紧张,使儒家人道原则在仁与礼相协调的基础上得以确立。
二、两汉至隋唐:儒家人道原则的曲折发展
两汉至隋唐,儒家的人道原则是在和神学的冲突及其两者的调和中曲折展开的。
儒家人道原则由孔子奠定,经孟、荀而确立,但在现实政治里取得胜利的是法家的暴力原则。在儒家遭受了秦始皇的暴力摧残之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儒学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却又表现出神学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和儒家人道原则是有冲突的。董仲舒的儒学以“天人感应”论为轴心,皆在论证封建统治秩序(人道)出自天意(天道)。他说天道有阴阳两个方面,阳主阴从,君臣、父子、夫妇的尊卑等级正是天道阴阳的表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春秋繁露·基义》)同样,德与刑也是天道之阴阳的表现,“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如此以天意来论证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而天就成了人格神,“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儒学走向了神学化。自孔子、孟子至荀子,在轻鬼神重人事的人道原则的制约下,本来殷周的神学之天逐渐地还原为自然之天。从孔子的“天何言哉”到孟子的高远之天体星辰都可“求其故”,再到荀子的“天行有常”,正表现了这样的趋势,映照出人道原则的伸长。就此而言,董仲舒是偏离先秦儒学的人道原则的。
然而,在神学的外衣下,董仲舒又表现出对儒家人道原则的某种确认。儒家人道原则发韧于孔子之仁,董仲舒借神秘的天意来回应孔子之仁。他指出仁是天意,其表现就是生成万物以“养人”,因而作为天意之仁肯定人的价值高于万物,“最为天下贵”(《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显然,儒家以人为目的、肯定人的价值的人道原则在这里得到了延续。但是,在董仲舒以神学的呓语表达儒家人道原则的同时,神学也内在其中了。这突出地表现在“天命”从此以后深深地缠住了儒家的人道原则。他反复论证人道出于天命(天意),因而天命对主体自由的钳制就渗进了正统儒学的人道原则。在孔孟那里,天命论始终没有被放弃,因而他们尽管重人道,但天命的阴影或多或少地笼罩着人力。董仲舒把孔孟的人道原则为天命论所盘绕的弊端强化和凸现了。这种强化和凸现把儒学裹在神学的迷雾里,从而消蚀了它的人道原则,因为人完全成了天意的奴仆。儒家人道原则被其神学化倾向所消蚀,是汉末儒学危机的重要理论原因,因为人道原则是儒家的基本原则之一。
由儒学神学化带来的危机,显然只能从其以外的思想中寻找解救的药方。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道家。因为它的天道自然无为正是人格神之天的克星。所以,援道入儒是儒学走出神学迷雾的必然途径。首先援引道家来伸展儒家人道原则的是王充。他称自己“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论衡·自然》),实际上是以道家(黄老)的自然之义来拭拂弥漫于儒学的神学迷雾,从而避免了儒家人道原则为这迷雾所吞噬。神学化的儒学是以人格神之天凌驾于人之上为基点的。王充针锋相对地以道家天道自然无为的观点驳斥了人格神之天。他指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论衡·谴告》)天道无为而人道有为,两者不同类,因而毫无感应的可能性。以此为前提,他对于种种天人感应论的鬼神迷信都作了批判。同时,他指出“然虽自然,亦须有为辅助”(《论衡·自然》),人为在自然过程中有其不可否认的作用。可见,在其道家之义背后,伸张的却是先秦儒家(更多的是荀子)的人道原则:以自然无为否定神学之天,还天以自然之本色,反对鬼神迷信,肯定人为的价值。这既不同于道家对人为的全部否定,又融进了道家“道法自然”即尊重自然法则的思想。这一融入丰富了儒家人道原则的内涵:对人为价值的肯定是以人为不偏离自然法则为基础的。
如果说王充的援道入儒主要是对被正统儒学目为异端的荀子的发挥,那么玄学援道入儒的主流则是接续正统儒学。玄学用道家的自然无为否定人格神的造物主:“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王弼:《老子注》);但也没有像道家那样否定人为,而是强调人为要顺乎自然规律。庄子指责穿牛鼻络马首是人为对自然的破坏,玄学则认为“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于天地。”(《庄子注·秋水》)意即穿牛鼻络马首这类人事是有其自然根据的。可见,玄学借重道家,而其所传承的却是体现先秦儒家人道原则的重人事轻鬼神的传统,并向这一传统渗入了人为须本于自然的观点。这和王充是类似的。但是,玄学不像王充那样以道家来批判儒学的神学化,而是将道家与儒学的神学化相调和。这突出表现在玄学论证了“天命无妄”,只是这个“天命”不是以人格神之天的面目,而是以思辨性的自然之“道”的形式出现了。就此而言,玄学传承的是维护天命的神学化儒学的人道原则。
援道入儒的结果,是道家作为儒家的对手而崛起,结束了儒术独尊的局面,衍生出儒道释鼎立的局面。隋唐时期,佛教和道教盛行。它们作为宗教神学,和儒家人道原则无疑是有冲突的,然而它们在向儒家靠拢的过程中,调和这种冲突,使儒家人道原则在其间曲折地发展。
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它在中国发展的过程,是儒学化的过程。它的儒学化从理论实质而言,重要的方面就是调和了其神学和儒家人道原则的冲突,禅宗是其典型代表。佛教作为神学,本来是宣扬彼岸的西方极乐世界,以出世为理想,贬黜现世人生。这与儒家关怀现实人生的人道原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禅宗则认为世俗和天国是统一的,世间即出世间,凡夫即佛;两者的差别只在一念之间,一旦觉悟,西方净土就在足下;因为觉悟是在现世日常平凡的活动中实现的,“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在日用常行中获得精神解脱。这不仅表现了佛教对儒家人道原则的吸纳和适应,使儒家人道原则仍然曲折地得以延续,而且启示了儒家人道原则:如何把现实人生与精神超越统一起来。宋明理学正是受此启示,提出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理想,从而丰富了儒家人道原则。
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本身就表现了与儒家人道原则的调和,可以说是儒家人道原则在神仙世界里的一种回音。道教的根本宗旨是修道成仙。所谓神仙,首先是长生不死;其次是活得自在快乐;再次是性命兼修,即高雅脱俗地生存和享乐,这和禅宗的世间即出世间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此这般的神仙生活,既是儒家人道原则注重现世人生的折射,也是对儒家人道原则之不足即忽视人的自然感性欲求(享乐)的反衬。宋朝理学以后正是意识到了这样的不足,因而就区分了感性需要(饮食)和感性欲求(美味)两个层面(《朱子语类·卷十三》:“饮食者,天理也;美味者,人欲也。”),肯定前者反对后者,使其没有走向极端的宗教禁欲主义。
虽然佛道在宗教神学的形式下一定程度上曲折地维系了儒家人道原则,但是佛道作为宗教,毕竟从本质上抵销着儒家人道原则:对神灵的膜拜,必然贬低人自身的价值,至少使这一价值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儒家人道原则必定要随着儒学的复兴而重振。儒学的复兴是以宋明理学的形式而呈现的,儒家人道原则的重振也与理学的发展相关联。
三、宋元至明清:儒家人道原则的重振和超越
宋元至明清,儒家人道原则的重振和超越,表现为天理既以人道为内涵又压抑人道以及对这种压抑的批判。
理学以上承孔孟道统自居,表明其正统儒学的品格。这就决定了它循着正统儒学的轨道来重振儒家人道原则,其表现就是以“天理”为最高宗旨,由此来伸张儒家人道原则。
理学要高扬在向佛道神灵磕头俯跪里日趋式微的儒家人道原则,因而其天理就以人道为内涵。所谓“理”,是先天设定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即作为“类”的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规定;其内在表现是人的至善本性(性即理),其外在表现是规定人的行为的礼(礼即理)。“理”之前冠以“天”,则是沿续了正统儒学的传统:以天作为人道的根据。由于天理以人道为内涵,因而“存天理”的题中之义是肯定人有高于自然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朱熹:《四书集注·孟子》),这是对先秦以来的儒家人道原则的重申。这种重申由于是在佛道神学弥漫之后进行的,因而就有了重振的意义。
儒家以仁为至善,因而从性即理出发,理学由仁来阐发儒家人道原则:“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上)这样的仁者情怀,就是理学家津津乐道的“民胞物与”。仁,就是爱一切人和一切物,这与孔孟之仁以血亲之爱向外推及的思路一脉相承。但是,孔孟之仁较多注意人际关系的和谐(民胞),而理学之仁则进一步注意到了人与天(自然)的和谐(物与)。正是出于对后者的注重,理学家张载首先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显然,这使得儒家人道原则有了更为宽广的普遍意义。“天人合一”还是一种境界,而这一境界的达到,则是通过日用常行来实现的。这就是理学吸纳佛道而提出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于是,儒家人道原则不仅有关怀现实人生的意义,而且还有赋予现实人生以精神超越的意义。所以,理学使儒家人道原则既不偏离关注现实人生的宗旨,又使其具有宗教那样的精神超越的功能。这是对原先忽略精神超越的儒家人道原则的发展。正是这种发展使得儒家人道原则能够冲淡宗教而重新崛起。
然而,理学家更多的是重振正统儒学的将天命论楔入人道原则的传统。理学承认“人为贵”,但并不由此认为人力是万能的,在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之外的领域就是“命”,即所谓人力尽处即是命。以万物一体为仁的人道原则却不会由于人力之极限而无法贯彻,因为其是天之所命:“仁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可不为之理也。”(朱熹:《论语或问》)这固然赋予人道原则以不可不为之必然性,但把人道原则的贯彻看作是听天任命,天命就内化于人道原则。如此的天人合一,是继玄学之后,天命论进一步趋向精致化。这不仅将人道沦为天命之附庸,而且否定了主体(我)在实践人道原则中的选择自由。因此,理学的天命内化于人道原则,使正统儒学的人道原则越来越走向其反面即反人道。
这在理学“礼即理”的命题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理学视礼为理的外在表现,因而合乎礼就是存天理:“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朱子语类》卷四十)礼是社会规范的总称,理学之礼的要点是通过社会规范来体现贵贱等差的秩序:“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二程遗书》卷十八)。因此,礼即理使得贵贱等差的秩序成为天理的化身。这样的存天理,实际上发展了孔子的仁与礼的紧张:爱人之仁和爱有差等之礼的矛盾,发展为民胞物与之仁和贵贱等差之礼的冲突。天理之“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必然性,“理之所当为者,自不容己”(《朱子语类》卷十八);天理之“天”,又具有自然的意蕴,因而在理学那里天和自然常常交替使用。于是,作为天理之外在表现的礼,既是等同于必然的强制性规范,“孝悌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朱熹:《论语或问》);又是将自然涵盖于其中,“礼即天地之德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前者以不能不然取消了主体的自愿,后者把合于自然消弭在循礼而行之中。这样,在孔子在克己复礼中所显露的人道原则与自然、自愿相分离的端倪,在理学的“礼即理”的命题中成了现实。于是,理学之礼就孵化出了反人道的东西,即虚伪的假道学和强制的礼教。
总之,理学在重振儒家人道原则的同时,也使其朝着反人道的方向走去。然而,与其同时的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和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则对这一走向有所阻遏。他们作为非正统的儒学,在与理学的争鸣中,从另一侧面来展开儒家人道原则。他们在以仁义为人道这一点上,和理学并无差别,但他们力图剔除理学的天命论等反人道因素。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陈亮的不能“舍人而为道”,叶适的“人皆能以一身为天下之势”,都与正统儒学把天命论楔入人道原则的趋向正相反对。他们的这些观点,反对了有人力所不及的天命(天理),反对了有关于人道之上而人道又不得不以其为准则的天命(天理)。他们也反对理学过分强调礼对主体的外力强制作用。王安石说:“礼始于天而成于人。”(《礼论》)认为礼是人为制定的,但却是以自然天性为根据的。陈亮的“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是对“非礼勿视、听、言、动”的突破,因而朱熹告诫他“勿出于先圣规矩准绳之外”(《答陈同甫书》)。叶适的“奉天以立治”,认为礼治以奉顺人之自然天性为立足点。总之,他们强调礼应顺导而不应强制人的自然天性。这无疑是冲击了为理学所强化的礼与自然(自愿)相分离的反人道性。正因为他们对理学的反人道性有所阻遏,使得在佛道盛行之后重振的儒家人道原则呈现出比较健全的面目。
反对理学把儒家专注于正统的偏狭之途,从而全面地振兴先秦儒家的人道原则的趋向,在明清之际的儒家那里成为一种思潮。明清之际诸儒提出“舍经学而无理学”,批判理学,要求重振经学(先秦儒学)。他们正是在反对天理压抑人的过程中,在更高的历史阶段重振了先秦儒家的人道原则。
理学把存天理和灭人欲相提并论,其性即理、礼即理都把人欲看作是性和礼的对立面,要求予以灭绝。这集中体现了理学反人道的性质。明清之际诸儒和理学一样,坚持天地之中人独贵这一儒家人道原则的基本立场;但他们反对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作为人的现实活动的全部内容,强调人欲是主体现实活动的推动力:“有欲而后有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下)。这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就是化“天之天”即自然的存在为“人之天”即人化的存在(《诗广传》卷四),也就是通过人的作用变革自然的存在,从而使之满足人的欲望(目的),“天之所无,犹将有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他把命还原为自然的存在,“天之命,有理而无心者也”,因而化“天之天”为“人之天”的过程就是“造命”(《读通鉴论》)卷二十四)的过程。这样的实现主体欲望的有为造命,是以遵循客观自然规律为基础的,“唯循理以畏天,则命在己矣”(同上)。欲在广义上包含着意志(意愿),明清之际诸儒从批判存天理灭人欲出发,反对天理对于主体意愿的扼制。王夫之指出,人性并非天理赋予,而是人按照意愿“自取自用”所形成的(《尚书引义·太甲二》)。黄宗羲也指出,“豪杰”精神表现为反抗和挣脱“囚缚”(《靳熊封诗序》),即出自于意志自由。戴震进一步指出,如果否弃了自愿,那么天理就会像法律那样无情强制,从而背离人道:“其所谓理,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与某书》)。
明清之际诸儒这种剔除天命论,强调主体意愿的人道原则,显然和荀子、王充、王安石、陈亮、叶适等非正统儒学的人道原则有更多的历史继承关系。当然,同时他们也坚持了自孔孟到理学的儒家一般意义上的人道原则。因此,可以说,他们通过对理学的扬弃来重振先秦儒学的人道原则,实际上是对整个儒家人道原则的总结。
不仅如此,明清之际诸儒还为儒家人道原则注进了一股近代的潜流,即开始批判君主专制对个体的践踏,从而表现出对传统的儒家人道原则的超越。在以往的儒学传统中,突出的是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和义务,而封建君主则是群体的代表,因而个体的权利就被戴着群体面具的君主遮蔽掉了。明清之际诸儒没有丢弃儒学关怀群体的传统,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但他们区分了国家与天下,一姓与万民:国是一姓之君主,而天下则是个体总和之万民,因而“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三)天下之公以确认个体的权利为基础,而封建君主专制恰恰是剥夺了个人的权利。黄宗羲指出,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逼迫天下人放弃自己的权利(自利),因此,“向使无君,人皆得自私也,人皆得自利也。”(《明夷待访录·原君》)顾炎武指出,君主为了剥夺个人的权利,编织了稠密的法网,以确保“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他要求君主发还从每个人手中收去的权利,“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他们的批判,没有明确否定封建君主专制,但却透露出确立个人权利意识的近代人道主义的民主气息。不过,他们却强调自己是对孟子民贵君轻的阐发,而这正表现了对儒家人道原则的超越,即向近代人道主义转换的萌芽。
但是,中国社会没有提供让儒家人道原则实现这一自我转换的条件。自清代康熙年间起,程朱理学重登独尊的宝座,在天理的宰制下,儒家人道原则只剩下表面的空壳,内里却是对人道的扼杀。因此,儒家人道原则也就终结了。
在简略地考察了儒家人道原则的历史演进过程之后,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本文一开始讲到的两个矛盾的事实是可以统一的:儒家确有重人道的传统,然而从孔孟至理学的正统儒学确有反人道的这一面;由于正统儒学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儒家人道原则不仅没有生发出近代人道主义,而且被反人道的一面所吞噬。
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存天理灭人欲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孟子论文; 董仲舒论文; 荀子论文; 理学论文; 道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