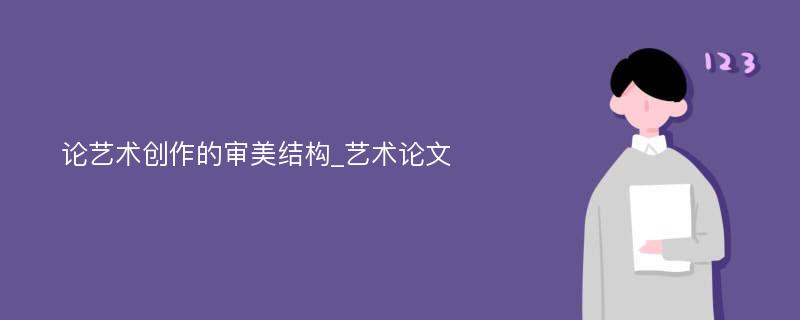
论艺术创造的审美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6-0116-04
一
“诗性主体”作为审美生成的逻辑前提,一个艺术家的资格才得以可能,艺术创造才得以可能。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常人,然而,在美学意义上决不能等同常人。这并非建立在克罗齐的理论上,在他看来,就直觉能力而言人人都是艺术家,之所以没有人人成为艺术家,是因为艺术家之外的常人缺乏艺术传达的能力。艺术家和常人最重要的美学区别在于,艺术家必然是一个“诗性主体”。艺术家“诗性主体”的建构,首先取决于他的心理结构:恋美情结、超越之爱、人类良知。其次,取决于他的发达想象力和奇异的灵感、生命的诗意和智慧以及独特的人生经验和情感路程,最后是他对于艺术形式的天才感觉和传达技艺。罗丹对于艺术和艺术家发表过深切的感悟:“艺术,就是所谓静观、默察;是深入自然,渗透自然,与之同化的心灵的愉快;是智慧的喜悦,在良知照耀下看清世界,而又重视这个世界的智慧和喜悦。艺术,是人类最崇高的使命,因为艺术是要锻炼人自己了解世界并使别人了解世界。”[1](P8)艺术家的心理结构必然存在恋美情结,一是对于大自然之美的迷恋,二是对于“美人”的迷恋。恋美情结往往来自于童年的经验和记忆,所以许多艺术家都酷爱自然,从童年时代就是自然之子,而且潜藏强烈的迷恋“美人”的本能冲动。随着年龄的增长,恋美情结升华为一种“审美信仰”,他把对此岸的美的沉迷转换为对于彼岸的美的乌托邦(Utopia)式的眺望。
这一冲动逐渐加深而激发创作动机。无论人生经历如何沧桑变迁,这种恋美情结伴随终生。弗洛伊德说:“童年记忆经常是这样出现的。同成年时期的有意识的记忆完全不同,它们并不固定在被经验的时刻,又在以后得以重复,而是在以后的年月,即童年已经逝去了的时候才被引发出来;在它们被改变和被伪造的过程中,它们是要服务于以后的趋势的,所以,一般说来,它们与幻想并不能被明确地区别开来。”[2](P58)隐藏在童年的经验和记忆中的恋美情结在后来的岁月不断被“回忆”修改和“伪造”,“回忆”实质上具有了幻想的性质。弗洛伊德又说:“众所周知,伟大的艺术家多么经常地通过性的、甚至赤裸裸的猥亵的画来抒发他们幻想,以此获得快乐。”[3](P49)凡·高和毕加索两位艺术家的生命经历就是典型的例证。从另一个意义来看,既然“生命的经验”意味着艺术家对于大自然的直觉迷恋,那么,艺术家必然地属于“自然之子”,往往经历乡村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双重洗礼。所以,几乎很少伟大的艺术家一生居住于都市而远离乡村,而科学家和学者则不在此限。艺术家的童年的创伤性经验也同样对艺术创造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创伤性经验和记忆成为他一生的压抑性势能,他要借助创造过程和艺术作品释放储存在情感水库里的痛苦。这样,可以体悟为什么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所说“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
和恋美情结相关,艺术家的心理具有超越的爱。第一,艺术家的爱欲一般超出常人,他爱自然和自然中的生命形式;第二,他们沉醉于异性之爱,男性艺术家常常有女性崇拜或女神崇拜的潜意识动向。第三,他痴迷“自我”,具有强烈的自恋情结。所以,艺术作品常常是艺术家的自画像或精神投影。第四,艺术家对精神形式的热爱超越常人。对于艺术、宗教、政治、文化传统等意识形态结构,隐藏着自己坚毅的心灵许诺。这些都促使他以艺术的符号象征得以表达。
“人类良知”对于艺术家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良知不是道德,良知是高于道德之上自觉的、无意识的仁爱与仁慈。可以允许和宽恕一个艺术家在道德方面存在缺陷,正如克罗齐所论:“善良的意志能造就一个诚实的人,却不见得造就一个艺术家。”[4](P213)但是,不能容忍一个艺术家丧失人类良知。艺术的人类良知包括普遍的人性或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它内涵于孔子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普遍道德原则,佛教的慈悲心和基督教的“赎罪”精神与拯救意识。唯有良知,艺术家才可能使自己的艺术创造获得美的可能。
艺术家的生命经验一方面是直接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是间接的存在形式。人生过程中所亲身经历的生命经验只能构成艺术创作的组成部分,它们另外部分就是艺术家依赖知识积累、理性工具等方式获得的间接的生命经验。它们包括读书生涯的知识背景、理性思维的结果等,它们和直接的生命经验一起参与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但是,无论是直接的生命经验还是间接的生命经验,艺术家的心理结构,如孤独感、痛苦情绪、痴狂、无意识的幻觉、宁静恬淡的美感等,有些隐匿在直接的生命经验之中,有些躲藏在间接的生命经验背后,共同构成艺术创造的动力和动机,迫使艺术家通过创造活动获得释放和显现。艺术家直接的生命经验和间接的生命经验促使自己不断获得知识和诞生智慧,它们渗透到艺术创造活动之中。
二
艺术是想象活动的精妙果实。怀疑论美学对于“想象”给予新的阐释,从本体论视界强调想象的怀疑和否定的特性,揭示其对于世界的追问、反思、批判的理性功能。[5](P69)一方面,想象禀赋感性的心理结构,包含幻觉、痴狂、荒诞、本能冲动等非理性内容,以对知识逻辑和日常经验的斥拒为特性。另一方面,想象不是传统哲学中被藐视的低贱的精神活动,而是人类思维的最高级的形态,综合感性和理性的精神形式,上升诗性的本质。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感叹道:“想象活动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活动,它是一种注定要造出人的思想对象的妖术,是要造出人所渴求的东西的;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人才可能得到这种东西。”[6](P192)黑格尔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但是我们同时要注意,不要把想象和纯然被动的幻想混为一事。想象是创造性的。”[7](P357)黑格尔在这里区分了想象和幻想,但是,他忽视了有部分幻想是可以转化为想象的事实,幻想对于艺术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分量和意义。
中国古典美学对于想象非常眷注和推崇。陆机的《文赋》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於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谢朝华於已披,启夕秀於未振。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说:“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想象活动首先在于艺术家创造心理和现象界建立“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对话关系,在古典艺术中,艺术家以万物有灵观(Animistn)的神话思维方式和现象界建立精神联系,或者,艺术家以诗意的直觉和体验把表现对象虚构为自我的投影,就像辛弃疾的词所咏唱的那样“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人与自然建立一种虚拟的审美对话关系。其次,艺术家调动无意识的心理机能,特别是幻觉和梦境的活动,渗透到艺术创造之中。幻觉和梦境尽管不乏杂乱因素,但是它毕竟为艺术的构思提供精神动力。弗洛伊德说:
当一个作家把他的戏剧奉献给我们,或者把我们认为是他个人的白日梦告诉我们时,我们就会感到极大的快乐,这个快乐可能由许多来源汇集而成。作家如何完成这一任务,这是他内心深处的秘密;诗歌艺术的诀窍在于一种克服我们心中的厌恶的技巧。这种厌恶感无疑跟单一“自我”与其他“自我”之间的隔阂有关。我可以猜测发挥这个技巧的两种方式:其一,作家通过改变和伪装他的利己主义的白日梦以软化它们的性质;其二,在他表达他的幻想时,他向我们提供纯形式的——亦即美学的——快乐,以取悦于人。我们给这类快乐起了个名字叫“直观快乐”(Fore- pleasure)或“额外刺激”(Incentive bonus)。向我们提供这种快乐是为了有可能从更深的精神源泉中释放出更大的快乐。[8](P37)
艺术家的幻觉和梦境的心理活动可以参与艺术创造并且可能带给接受者以奇异的美感。据清代著名诗论家赵翼统计,陆游的纪梦诗达九十九首之多。《瓯北诗话》云:“人生安得有如许梦,此必有诗无题,遂托之梦耳。”艺术的梦境可以更大程度上发挥想象力的潜能,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营造虚幻朦胧的审美境界,使表现范围更为广阔,手法更为灵活洒脱。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有着浓丽幽婉的浪漫色调,全剧构造情境优美的梦境,以梦幻的方法酿成几对情人的喜剧冲突,错中错的情节发展,由于梦境的佐助,显得荒唐而有趣味,让欣赏者感受到这是一场无伤大雅、妙趣横生的美妙之梦。在中国将梦境展现在艺术中并获得巨大成功的莫过于明代戏剧家汤显祖。他写了“临川四梦”,在中国艺术史占居第一流地位。汤显祖的美学原则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情是作者的或一般的社会情志,梦是作者的美学理想,也是艺术创造的方法。梦表现情和体现理想,“曲度尽传春梦景”。“四梦”之冠的《还魂记》,写少女杜丽娘因梦感情,因情而死,演出一场哀艳伤情的虚构悲剧,“梦而死”、“死中梦”、“梦中又生”的曲折情节紧扣欣赏者的审美知觉,充分体现了艺术的独创性。在艺术创造中采取梦幻的表现方法,还因为艺术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限制他以直叙的方式暴露现实,露而不藏的写法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这样就可能使艺术家被迫运用托梦而言的创造方式。曹雪芹的《红楼梦》,“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通篇以一个梦幻相契领,演出一幕“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的历史、家庭和个人的悲剧。梦幻在曹氏的艺术构思之中,不仅是悲观虚无的“色空”观念的折射,而且是他形象刻画和心理分析的独到之笔。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认为艺术是一种直觉(Intuition),他认为:“直觉据说就是感受,但是与其说是单纯的感受,无宁说是诸感受品的联想。”[9](P13)如果说直觉是沉默的持续性想象,那么,灵感(Inspiration)则是瞬间迸发的吟唱性想象。灵感是想象的高峰境界,是心灵潮汐的高涨时刻。艺术家没有灵感是不可能创造诗意盎然和富有智慧与美感的经典之作的。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前460-370)认为:“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10](P36)又说:“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之下所作的一切诗句,当然是美的。”[11](P4)柏拉图在《伊安》篇以诗意的语言表述自己的观点:
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递传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科里班特巫师在舞蹈时,心理都受一种迷狂支配;抒情诗人们在做诗时也是如此……抒情诗人的心灵也正像这样,他们自己也说他们象酿蜜,飞到诗神的园里,从流蜜的泉源吸取精英,来酿成他们的诗歌。他们这番话是不错的,因为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12](P8)
灵感是想象力的突然爆发,也是智慧的畅通,类似于佛禅的“顿悟”。灵感的起因有可能是想象活动的时间积累,有可能是外在意象的突然激发,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梦幻活动的直接结果,也可能是生活经验和以往记忆的间接唤醒。当然,也有可能是情绪处于高峰状态的突发体验。总之,灵感是想象力畅通和智慧之光闪现的结果。灵感决定着艺术创造活动的成败得失,衡量着一个艺术家的天才、智慧和想象力。
艺术家的记忆(Remember)和想象存在非常重要的逻辑联系。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艺术家的童年印象构成永久的生命记忆,这种记忆不断被他本人所修改、涂抹、虚构,成为一种想象的精神对象。其实,包括艺术家在内的任何生命个体的“记忆”乃至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在不间断的回首和追忆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被情感和想象力修改和变形。任何记忆都是历史的和想象的感性果实,不是理性和逻辑的事实。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的“希腊情结”,是一种文化崇拜的历史性集体记忆,他们显然以自我的崇拜情感和想象去复活、修改古希腊精神。因此,所有的记忆都必然是不可靠的虚构和想象,尤其是人文领域的记忆。当然,艺术家的“记忆”是所有记忆形式中的最富有想象力的追忆,并且是最唯美或最痛苦的“记忆”,它以夸张的艺术修辞可能走向不同的心理极端。
艺术家的想象类型,可以区分为:一类是合乎逻辑的想象、现实性想象、再现想象、客观想象、非逻辑想象等。这类想象包含一定的理性成分,是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所说的“可然律”和“必然性”的方式进行想象活动,传统心理学的“接近联想”、“类比联想”和“对比联想”的概念可以指称它们。另一类是虚构式想象、创造性想象、非客观想象、无意识想象、梦幻式想象等以非理性为主流的想象。艺术家的想象是以后者为主体的交叉两类想象的创造性心理活动。
艺术是智慧的敞开和结果,而智慧又是想象的延伸和结果,它具有存疑的否定的理性力量。智慧呈现“虚无”、“非逻辑”、“超越语言”、“关注过程”、“绝对自由”、“幽默”等特性。[13]因为智慧和想象的逻辑关联,它们共同参与和引导着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佛学尤其注重智慧的开启,所谓“戒、定、慧”的修行,“开慧”、“思慧”、“修慧”的智慧汲取方式,都重视智慧之于众生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中国佛教哲学对于智慧的阐发丰富而深刻,般若的“心境俱无”说,唯识宗的“心有境无”说,“阿赖耶识”说,华严宗的“如来藏”说,“事事无碍”说,禅宗的“顿悟”说,法性宗的“离言绝待”说等,均从诸种佛学义理,强调和阐释智慧的性质。宋代普济的《五灯会元》,汇辑不同时期的各派高僧有关教义辩论和生活故事,富有趣味地说明了智慧的超越性和否定性。中国艺术精神融入了佛学的智慧,古典诗人、艺术家都不同程度受惠于佛学的智慧熏陶。
三
艺术创造需要艺术家对于特定的艺术形式的精湛领悟、理解和把握,否则他无法把内心的感受和体验转变为现实性存在。艺术家必须具备对他所从事的某种艺术种类或艺术形式的敏感和娴熟的把握能力。雕塑家必然有对于三维空间的形象把握能力,一方面他要一双敏锐的体察物质的空间结构的眼睛,有一种对空间形体进行感觉和分析并且形成审美意象的心理构造才能。另一方面,他要对雕塑的整个技术过程持有精湛的技艺。罗丹(Auguste Robi,1840-1917)感慨雕塑是“塑造的科学”,他牢记一位前辈雕塑家的忠告:“‘你以后做雕塑的时候,千万不要看形的宽广,而是要看形的深度……千万不要把表面只看作体积的最外露的面,而要看作向你突出的或大或小的尖端,这样你就会获得塑造的科学。’这个原则,对于我,是一个惊人的收获。”[14](P30)画家要有一双细腻地分辨色彩、线条、平面和形状的眼睛,对于绘画的某个种类有娴熟的技巧。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这位后印象派画家,对于光线和色彩产生独特的感悟和表达,沉浸在他绘画世界里:
他变成了一台盲目的绘画机器,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就匆匆地完成了一幅又一幅的冒着热气的油画。乡间果园的果树开花了。他产生一种狂热的欲望,要去把它们全都画下来。他不再去思索自己的画。他只是去画。整整八年他所进行的紧张劳动没有白费,终于突然间化成一股巨大的凯旋的力量。有时,他要是在天将破晓时开始作画,到中午这幅油画就能完成。那时他便徒步走回城里,喝一杯咖啡,然而又步履艰难地向另一个方向出发去画一幅新的油画。
他不知道自己的画是好是坏。他并不在乎。他陶醉在色彩中了。[15](P423)
邓肯(Isadora Duncan,1878-1927)说:“甚至于我要追一个绝对真实的动作,费了我若干年的工夫。……自最初我的跳舞便是表现人生。幼年的时候,我跳着生物自然发育之舞;成年的时候,我跳舞便深深地感觉到人生悲哀的暗潮,冷酷的残忍,前进中的挫折。”[16](P3)凡·高和邓肯分别对绘画和舞蹈有着精湛而独特的理解和传达。音乐家对音响、节奏、旋律、和声有着天然的敏感,如同文学家对于文字语言的节奏、音韵、意象的直觉,以及对于隐喻、象征、夸饰、叙事、抒情、描写等技巧的通晓。正如黑格尔所论:
一位音乐家只能用乐曲来表现在他胸中鼓动的最深刻的东西,凡是他所感到的,他马上就把它变成一个曲调,正如画家把他的情感马上就变成形状和颜色,诗人把他的情感马上变成诗的表象,用和谐的字句把他所创作的意思表达出来。艺术家的这种构造形象的能力不仅是一种认识性的想象力、幻想力和感觉力,而且还是一种实践性的感觉力,即实际完成作品的能力。这两方面在真正的艺术家身上是结合在一起的。……艺术家对于他的这种天生本领当然还要经过充分的练习,才能达到高度的熟练;但是很轻巧地完成作品的潜能,在他的身上仍然是一种天生的资禀;否则只靠学来的熟练决不能产生一种有生命的艺术作品。[17](P363)
所以,艺术家对于形式的感觉、理解和运用是从事创造活动的一系列不可缺少的步骤。
艺术家的传达活动需要精湛的“技艺”和“技巧”。艺术(Art)的原初含义就是一种“技艺”。柏拉图在《伊安》篇把艺术就理解为是一种“技艺”(Tekhne)。古典时期,它的称谓广泛,它包含医药、手艺、手工、畜牧、耕种、骑射等专门化的工作。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对“艺术”进行词源学考证,指出“艺术”和“技艺”的密切关联。“艺(藝)”在汉语中,也包含“技艺”的意思。《说文》中作“埶”和“蓺”。《诗经·唐风·鸨羽》:“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抱朴子·行品》云:“创机巧以济用,总音数而竝精者,蓺人也。”《后汉书·伏湛传·附伏无忌》载:“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注云:“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可见,艺术是个包容性广泛的集合概念。艺术家在创造过程的传达阶段,主要依赖于自己的高超而独特的“技艺”。而展现“技艺”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对于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的选择、提炼,美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决定他对于艺术手法的偏爱,天才的富有智慧的艺术家才能表现出自己的独创性。迄今为止,艺术史展现艺术家五彩斑斓的创作方法,诸如现实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主义、新感觉主义、唯美主义、抽象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立方主义、达达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对于艺术家而言,创作方法没有价值差异,只有眼界和运用的差异。艺术家在传达过程,选择自己喜爱和擅长的创作方法,或者以某种创作方法为主体,糅合其他方法而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当然,天才的艺术家可能凭借自己的灵感和悟性,创造出新的创作方法。“方法”是“技艺”的逻辑前提,“技艺”是依照创作方法在具体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实际运用技巧与技法的活动。技艺是一种熟练而精湛、独特而卓越的表现在某种艺术类型上的才能,它是限于某个艺术话语和形式的特殊才智和能力。这一点正是艺术家区别于常人、伟大艺术家区别于一般艺术家的重要标志之一。
收稿日期:2010-0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