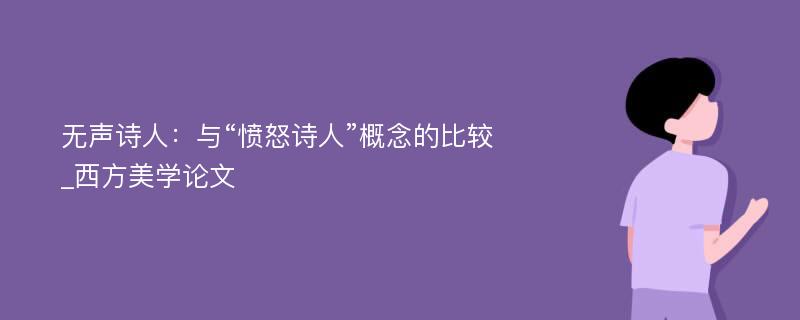
寂静出诗人——兼与“愤怒出诗人”观念相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人论文,相比较论文,寂静论文,愤怒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创作心理及其动因的描述,中国古代历来就有多种说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种是“寂静出诗人”和“忧愤出诗人”。这在西方也大致相通,只不过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有所偏重罢了。可惜的是,对这种独特的轨迹及其理论特点,我们至今还缺乏系统的理解和研究,以至于在理论上显得薄弱零乱,形不成完整的学说。这篇文章就想尝试从一种中西比较的角度,通过对有关文献中一些资料的分析探讨,以求获得一种对中国古代心理美学思想方式的整体性理解,以请教于大方之家。
一
从表面上看,虚静出诗人和忧愤出诗人,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一是强调创作状态首先要求内心宁静,平和,然后才能创作出情致高远的作品;而另一种则揭示出创作与剧烈的心理波动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把心理的压抑和宣泄看作是创作的心理动因。其实,这正好构成了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的阴阳两面,借用刘勰的话来说就是“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构成了一种柔刚并济,阴阳互补的整体状态。
应该说,这种整体性状态不是一种逻辑的和理性的论说,而是一种生命存在状态的显示,所以它是一种描述性的,流动性的,呈现性的,由此向人们敞开了创作美学心理的门扉。这一点它和西方现代文艺心理学有理论形态上的不同。它在概念上和逻辑上没有什么限定,就象庄周之语“深闳而肆”,“其理不竭”,如同人和自然的生命状态一样生生不息。也就是说,艺术创作的根基是人的生命状态,而对于创作心理状态的探讨最终是对人的生命状态的体验和探讨,人们只有在对生命本原的追寻中才能获得它们的秘密。与此同时,更值得探讨的是,随着历史和文化的演进,中国的文艺心理美学中的阴柔一面似乎获得了更充沛的强调和应合,构成了其浓郁的东方特色。
关于“虚静出诗人”,我们最早可以在老子那里找到它的源头。这也是中国文艺美学体系成形的源头,不过,在《道德经》中,老子的理论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提出了“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美无言”的美学理想;另一方面又对一般艺术持否定态度,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在具体的美的表象形态和本原的美的本真存在之间难以取舍,最后不惜以牺牲前者作为代价。也许就老子的体验来说,艺术的本真就不是表象的,而是内在的,它不是表现出来的实体,而是生命能够达到的一种浑沌境界。而这一境界就与虚静相关:
致虚静,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道德经·十六章》
按老子的意思,“静”是体验和理解生命状态的关键,唯独有“静”,才能体验和理解“根”“命”“常”“明”等生命最本原的意蕴。如果说“根”谓之为生命的本原(来处),“命”谓之生命的劫运(去处),“常”谓之为生命的状态,“明”谓之为生命的理性把握,那么“静”自然就是一种对生命毫无遮蔽的体验和触摸了。这时候,人能够和整个宇宙自然溶为一体,息息相通,真正感受到一个运动着的(万物并作)、整体的混沌世界。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大美”,因为它是和那个“寂兮廖兮,独立不改”的混沌世界一样是“不可道”的,所以才有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之说;正因为这种美来自于“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所以不可能用外在表象形式表现出来,而只能通过内在的体验方式来实现。
这在理论上也是说得通的。也可以这么说,老子所追寻的“大美”是一种绝对的本体艺术,它不是语言,不是形体和声音,而是一种生命存在本原的体验;它需要一种超越世俗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在一种不受既定概念和观念束缚的“恍兮惚兮”中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整体存在。同海德格尔的“与神性同在”的终极关怀不同,老子的这种本体论的美学基于个人生命与宇宙存在的同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超越了客体,也超越了主体,而且沟通了意识和潜意识,达到了一种灵与肉浑然一体、自我与自然无法分离的境界。如果换一种说法的话,老子愿意把这种状态比喻为婴孩,因为婴孩不同与成人,他们刚刚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还不能把自己的意识集中于某一点上——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还不能限制自己的意识和思维,用一种意识去排斥另一种意识,是一部分意识处于亢奋状态,而另一部分处于被压抑状态;相反,他们的意识是向所有的方向敞开的,没有任何遮蔽,所有的感觉都包容在意识之中,接纳着所有的外在信息。
老子不喜欢成人的状态,甚至不喜欢集中精力的思维方式,这似乎和后来的庄子有所不同,因为庄子是讲究“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因为从思维角度来说,集中意识就意味着限制意识,一个人越是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家,也就意味着在整体存在方面失去得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通向潜意识的小径不仅是黑暗的,而且是未知的,而思维的混沌状态对于理性来说,它是非理性的;对于逻辑来说,它是非逻辑的。这样很难进入虚静状态——因为有意识的,同时有限定的思维将一直打扰你,不容许你进入。
这也就构成了本体存在的悖论:人不可能离开意识思考认识到自己,但是当你集中思考的时候又不可能获得自己的存在。这也正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悖论。既然如此,就不可能用理性的逻辑的思考方面去接近它体验它和拥有它,而只能通过“专气致柔”,进入一种“惟恍惟惚”“窈兮冥兮”的状态才行。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才能达到一种大美、大象、大音的生命境界。而这才是人本原、本真的存在( to be),是生命的一种大欢喜、大满足。人的精神超越了限定,超越了因果关系,进入了未知,真正从功利的、机械的、程序化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
所以,“虚静”在老子那里是一种生命的艺术状态,体现了中国体验和理解人自身本体存在意义的真谛。这对于在现代生活境况中挣扎生存的艺术是极其可贵的。因为在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的引导下,人们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认识和把握受到了因果关系和目的论的限制,把生命的存在单纯归结为理性和知识,人的意识本身明显地存在着被客观化和物质化的倾向,所以,人丧失了对意识存在的意识,也丧失了本真的自我存在。对此,西方的一些思想大师从上世纪以来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由于理性主义、科学逻辑主义所造成的思想束缚和限定,使他们感到痛苦不已。维特根斯坦在解释历史、文化、语言的方方面面时,用的是一种非常理性和逻辑化的方式,但是到了最后不得不悲叹,“对于一些超越理性范围的东西,是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的,我只能保持沉默。这就是说,不能言说的就无需去说。 ”(That which can not besaid must not be said)。爱因斯坦同样如此。 他沿着理性的道路走到了尽头,最后走向了神秘主义,因为他感到了理性的困局和限定。
这也许就是整个西方理性主义大厦轰然倾毁,一些西方思想家开始转向东方智慧的原因之一。因为试图用理性的方式解释整个生命现象和存在,最后只能是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而一些生命的真谛,存在的意味是无法言说,不能界定的。
二
对此,印度哲人奥修(Osho 1931.12—1990.1 )对老子“虚静”心领神会,进行了积极的理解和发挥。在其著名著作《冥冥虚静——生命极致的艺术》(Meditation:The art of Ecstasy)中,他发挥了“消极无为”(Passive and nondoing)的思想,溶入了印度瑜珈(Yoga)因素,并给予了全新的、积极的阐释,揭示了内在的寂静与创造性的关系,他写到:
由于寂静,一切创造性开始了;寂静孕育着创造。所以当我谈到“寂静”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墓地的死寂,也不是房院的空寂,不,我所说的寂静是饱满的种子,是母亲的子宫,是深扎土地中的根。在这里,一切隐藏着的潜力都将要迸发出来。(注:《Meditation: the
artof Ecstasy》,Rebel Publishing House PVt,LTD,India,p21.)
在这里,不妨对照一下庄子有关寂静的阐述:
圣人之静,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饶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而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为天乐。
——《天道》
也许把奥修的“The art of Ecstasy”译成“天乐的艺术”更为贴切,因为在他的著作中处处可见到老庄的影子。他确实研究过老庄,并且写过多本介绍和阐释老庄的著作,从70年代开始他的思想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毫无疑问,他的思维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古代东方智慧的现代综合和发挥。
当然,作为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性转化,“虚静”是一种内在修炼的过程,所以老子强调不但要“绝圣弃智”,还要“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注:《道德经·第五十六章》。)由此达到衣着生命本真的“元同”境界。作为一种修炼入静的过程,奥修深谙其中的真义。他把“虚静”与日本禅宗(ZEN )融合在一起,用定坐方式来入静,以达到一种窈冥虚静状态。他说:“如果你镇定入坐,人的身体和头脑都进入沉寂不动,就能达到窈冥虚静。”(注:《Meditation:the art of Ecstasy》,p53。)
对这种状态奥修还做了如下描述:
在这种无为的境界,在这种入定境界,宇宙和个体靠近了,它们变得亲密无间,各自都失去了自己的界定,互相重叠融合到了一起,这时候,宇宙的一部分渗透于你,而你的一部分进入了宇宙;两者的界限变得柔软易变,成了流动状。有时候,你会觉得这里已没有界限,也没有意识的存在——一切都没有限定,无始无终。有时候,这种界限以一种透明状态呈现在你的周围。
这种情况会忽隐忽现。一切界限在似有非有,时有时无之中。不过,一切都会变得愈来愈轻松,界限也会越来越趋于消失,然后真正的不可预期的时刻到来了;这个时候的到来是无缘无故和无根无由的。最终你失去了所有的限制和限定,而且不可能再受制于它们。这里开始了一种人类没有任何界限的存在,思想没有疆界,意识毫无限制。这就是浑然整体。(注:同上书,第61—62页。)
这种整体性存在也就是老庄所追求的境界。在《庄子·在肴第一》之中,当黄帝让出天下,住到了一个茅草搭的屋子里,三个月后,他向广成子请教修炼之道,广成子就告诉他:“得道的精义,就在于窈窕冥冥之中,它的极致,也在于昏昏默默之中,你无须耳听目看,精神进入一种虚静状态,外在状态就会到了本原:如果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你的身体和精神清净无为,但是仍然能充满生机。虽然你目无所在,耳无所闻,心无所动,但是你的精神仍然能拥有一切。内在寂寞,外在无为,只要进入窈冥之门,就能达到生命本原存在的极致。”广成子还告诉皇帝说,这将是一个没有界限,没有限制的“无穷之门”,从此可以“以游无极之野”,它是和整个宇宙自然浑然一体的。
还有一则寓言在《知北游·第二十二》之中。当孔子向老子求教至道之术时,老子首先向他谈“崖略”。所谓崖略就是边际,而“至道”的根本就是“其来无际,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到了这种境界,就会“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
由此可见,“虚静”是一种内修内求的心理状态,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开发和修炼,并不依赖于外在的刺激和触动;与此同时,它所追求的也不是外在的表现和呈现,而是内在生命的完整体验,由此获得对自然和宇宙本原的交流和体认。
这种心理状态作为一种诗意的体认,和中国古代“诗言志”观念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尚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就是把内在的“志”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动力的。朱自清对此曾从分析词源入手,指出“志”的“本义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说是藏在心里”。(注:朱自清:《诗言志辩序》。)这就从某种程度上确定了创作的内在性。而对《周易·系辞下》中的“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高亨曾有过如此注释:“易,平也,君子之言,平心静气。”至于在日后人们对艺术创造的体认中,更是经常把“虚静”之说柔人其中,形成了多种意味的说法。
三
例如,中国传统的“中和”艺术观念,就与虚静状态紧密相关。所谓“中”,古人几乎可以运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无不表现出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尚书》中它是一种理想的人格:“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更有进一步的发挥:“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荀子在《不苟》篇中则表达为:“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除此,《国语·虞书·舜典》也有“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德音不衍,以合神人”之语,俨然把它视为一种天人和一的境界。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中”意味着一种平衡状态,能够在多种因素和能量的相互冲突和交叉中获得和谐,而不至于心理偏激和烦燥,情绪趋于极端和紊乱。所以《乐记》中在论及音乐与人的情绪状态时,强调音乐要“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这显然和《论语》中所言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相同的美学理念。
这也就必然要求“和”。因为“中”只是一种选择,而“和”才能最终体现这种选择的魅力;同时“和”又是对“中”的理念的一种必要引展。所以《吕氏春秋》在论乐时指出:“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就要把“心适”和“乐适”统一起来,创造一种“夫乐有适,心亦有适”的音乐。而所谓理想的“适音”也就是符合中和原则的音乐,也就是“衷音之适也”,因为“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也。”在这里,从“中”到“衷”,表达了一种从外在世界向内在心灵的转化过程,而“和”自然是它们趋向的一种完满状态。《礼记·中庸》对此有如此描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了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种完满状态也是一种心态的愉快状态。其实,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快感是一个最本原的价值取向。这在音乐理论中最为明显。音乐的“乐”原本就是人的快乐状态,同时也是艺术起始的源泉。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是一种最好的印证。
如果说“和”在这里是一个多元共存的理念,那么“乐”就表达了一种美感和乐感的要求,它取自于“中”,趋向于或完成于一种“乐在其中”的心理过程。而在这里,所谓“和而不同”,是一种重要的美学观念的表达。在《左传》中有一种“和如羹焉”的比喻,就是把不同的作料“齐之以味”,构成一种新的美味,很有创意。而这种理念在古代典籍中有多种多样的说法,例如,在《国语》中有“以他平他谓之和”之论,指出“夫和生物,同而不继”;《尚书》中言“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周易》中则有:“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而《乐记》中认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万物不失。”《礼记》中则强调:“礼交动于上,乐交应于下,和之至也。”这一些论说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说明了中国古人对于“和”这一观念的重视和发挥。显然,这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人与艺术内在和谐统一的观念,它期望宇宙万物并存,互相谐调,各种情景和因素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这也是艺术给人们带来愉悦和快乐的基本氛围。而对于人来说,最根本的就是内在的和谐,这就必然要探索人的心理世界及其感觉、感情、欲望、理智等多种关系,有时会由心理涉及到生理及其它们的相互感应和影响过程。例如司马迁论乐时就如此谈到:“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
除了“和”之外,“平”则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概念。因为心不平就谈不到“乐”,所以古人常常把平和与中和相提并论。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对于好的音乐和美味羹的评价几乎一样,是“君子听之,以平其心”。而“心平德和”则把“平”和“和”紧密联在了一起。《国语·周语下》中曰:“夫政象和,乐从和,和从平”;《荀子·乐论》中也有:“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但是,尽管如此,“和”在艺术创造中仍然是一个相当模糊和不确定的概念,因为不同的人对于“中”的理解和选择毕竟不同,那么“和”就更会因人而异了。若如《淮南子·本经训》所言:“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那么不同人的不同的心和欲望就成为决定艺术价值的关键因素了。由此后来董仲舒发现了其中的认同关系,即:“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
当然,“中和”和“平和”都不等于虚静状态。但是作为一种对平衡、和谐、愉悦心境的追求,往往和静心交织在一起。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它们又常常互相印证和互为因果的。作为“清净无为”的老庄和勤于进取的儒家在这方面似乎也并不忌讳相互借鉴。例如,庄子在论及“与天和者”时,就“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而荀子在提倡“礼之中流”、“诗之中声”、“乐之中和”时,又特别强调其“虚壹而静”的心理基础,因为心态不宁,烦燥不安,又何以能取中求知、赏心悦目?所以他在《正名篇》中说得好,如果人心不平和宁静,怀有恐惧困惑,就不可能从“万物之美”中获得愉悦满足。而《乐记》中“乐由中出故静”的说法,更是把“中”与“静”溶为一体了。
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儒、道、佛等各家学说之间历来存在许多分歧和冲突,但是对于“虚静”之说却都恋恋不舍,有着某种的共同的体认,特别在文艺美学方面,都承认虚静作为一种艺术状态的价值和意义。例如,阮籍的《乐论》就调和了儒家和道家的理论,认为音乐只有“必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才能有“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的音乐之美;而美的基础就在于调和阴阳,能“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使听之者“入其心,沦于气,心气和洽”,具有“乐平其心”的效果。在这里,虚静与平和实际上是互为条件的。
荀子也是如此,他对于虚静状态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并且由此提出了一个心理美学的重要观念“解蔽”。解蔽,通俗的讲,就是解除心理上的遮蔽,恢复到心理的本原和本真状态。所谓遮蔽,就是心理中存在着各种各样认识和完善自我的偏执和紊乱现象,它们可能表现为焦虑、惊恐、忧郁、狂躁、嫉妒、妄想等病态心理,它们可能来自于欲望的压抑及宣泄,道德的约束与背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荀子认为,人最大的祸患来自于心理的遮蔽,“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不但不能治国平天下,而且也不能感受和欣赏艺术。但是又可悲的是,人心很容易被遮蔽,许多因素都会可能成为“蔽”,如其所说“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无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万事万物都可能为蔽,乃是因为万事万物都有局限性,如果局限于个别的“异”就不可能认识到整体,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而圣人能“知心述之患,见比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
但是,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荀子虽然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但是最终还是要求助于虚静之说,他认为只有虚静才是“解蔽”的最根本途径。他说:
故治之要在于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作之,则将须道者之虚,则人,将事道者之壹,则尽;将思道者静,则察。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
接着,荀子又发出感叹:“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恢恢广广,孰知其极!睾睾广广,孰知其德!涫涫纷纷,孰知其形!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夫恶有蔽矣哉!”
这里不难感受到荀子和老庄的某些共通之处。其实,“解蔽”为荀子所倡扬,但是在老庄那里就有源头。《道德经》中就有“涤除元览”和“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之说。前一句话是说要恢复到婴孩般的本真状态,就要清除内心中的世俗偏见和邪念;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只有心理虚而不满,才能避免心智被遮蔽。对此,庄子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人如果受世俗所累,心不能静,就不能感受和体验到“大美”。他在《庄子·庚桑楚弟第二十三》中提出“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司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要取掉野心,二要解除束缚,三要宽松心境,四要心智通达。庄子对此还作了以下具体论述:
富贵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这四个方面二十四个因素涉及到了人的心理的各个层次和方面。第一层次是外在的社会功利性,太重必然会堵塞人的心智,所谓“财迷心窍”“官迷心窍”就是如此。第二层次是个人的心理修业,太表面化或太拘泥于陈规戒律,都会造成内在的自我冲突和矛盾。第三个层面是人的感情生活,焦虑不安或喜怒无常不仅会心智疲惫,而且也是缺乏恒心的表现。第四个层面是讲人的待人处事,斤斤计较就不可能心理通达。所以庄子把“静”确定为一种特殊的状态。
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
——《庄子·天道》
可见,在庄子那里,解蔽和虚静是互为因果的,最终是要达到“通”的境界。庄子很看重“通”,在著作中屡屡提及,由此把天地、宇宙和自我统一起来。这里试举几例:
道同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齐物论第二》
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神鬼将来舍,而况人乎?
——《人间世第四》
坠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与大通,此为坐忘。
——《大宗师第六》
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避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
——《天道第十三》
在这里,有静才有无,有无才有通,有通才有一,有一才有同,“通于一而万事毕”。庄子也讲“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和消除万事万物的差别,因为“不同同之谓之大”(《庄子·天地第十二》),所以“一”和“同”都是“通”的结果,这正如庄子在《徐无鬼第二十四》中所言:“知大一,制大阴,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解之,大目视之,大均缘之,大方体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定”就是“静”,这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孔子曾有过“求通久也,而不得”的感叹。《庄子》中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公孙龙向魏牟求教庄子之言时,魏牟告诉他,求通不能用“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的方法,那只能是“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这使得本来自以为能“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的公孙龙很惭愧,吐着舌头跑掉了。因为庄子所追求的是一种“大方无隅”的境界,能够“始于玄冥,反于大通”。
庄子很少讲“解蔽”,但是“解惑”却是他一贯的学术追求。而“惑”和“蔽”一样都是通向“虚壹而静”的心理障碍。他在《天地第十二》中感叹:“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至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至,惑者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在这种情况下,“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不至于成为“大惑者,终身不解”。
当然,孔子也讲“解惑”,但是他和庄子有所不同。孔子的解惑多半是属于大脑和知识方面的解惑,教给人们以处事做人的准则和方法,如何学习和获得成功;而庄子所解的惑主要是性情方面的,是对人的本真状态的一种启发和提示。所以在庄子眼中,本来到处跑来跑去为人解惑的孔子,反而总是以“惑”的形象出现,他苦心劳身,宣扬仁义,维护礼乐,不可能意识到本真的存在,所以经常受到有道之人的讥笑。在《庄子·渔父第三十一》中就有这样一段对话: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为真?”
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笑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足,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于人伪,而晚闻于大道也。
可见,庄子要解的惑,就是孔子所授于人的入世的知识和通向有为的务实方法;他所讲的真就是人的性情的本真状态,其方向是通向清净,通向无为,通向物我为一的艺术境界的。
在古代,当然不可能有病态心理学的研究,但是对“蔽”和“惑”的考察和认识无疑具有这方面的意义。尤其在艺术心理方面,这种解惑去蔽的过程,不仅是心灵的一种净化和敞开过程,而且对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开发有着重要意义。因此“静”就有了“净”与“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