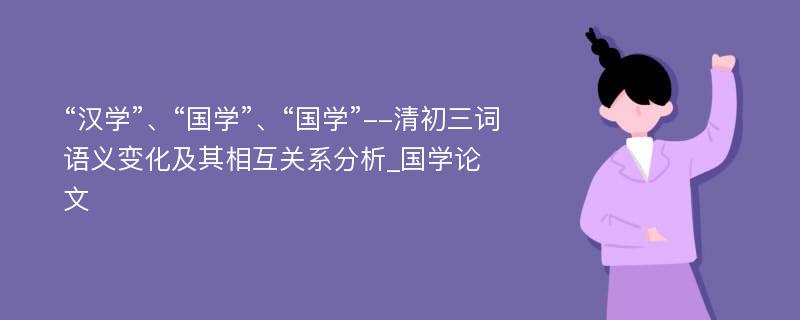
“国学”、“国故”、“国故学”——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故论文,民初论文,语义论文,国学论文,试析三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诚如陈寅恪所指出,“盖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讹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审慎也”(注: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5页。)。清季民初,“国学”、“国故”、“国故学”三词曾一度并行于世,给人们造成了相当混乱。因此,从它们各自缘起和产生语境入手,疏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国学”的由来与涵义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太学相当,二者往往互训。
而近代意义上的“国学”,语义则发生了不小的转变。究其来源,20世纪20年代即有论者推断其为舶来品。何炳松曾追寻“国学”二字“从何而来”,但“在中国书中总是查考不出他的来历”,于是他估计“大概是由西文中翻译出来的”,即“支那学(Sinology)”(注: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汪震、王正己也说:“国学这个观念,大约产自外国,英文为Sinology,意为中国的学问。日本有‘支那学’。”(注:汪震、王正己同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版,第1页。)而曹聚仁在晚年回顾时,则更是详细阐释说:“‘国学’这一名词,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乃是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有些土大夫(精神上的遗老,有如今日海外所谓‘忠贞之士’)只怕‘国粹’给欧风美雨吹掉了,乃要紧紧地保存起来,称之为‘国学’(日本人称之为支那学,欧美人称之为汉学)。到了20世纪初期,他们就在那儿提倡‘国学’了。”(注: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由此看来,在此问题上,近代中国知识界几乎达成了普遍共识。但这种追溯似仅是就“国学”这门学问的起源而言,并未对这一词汇本身如何得名的真实来历细加考辨。
颇有意思的是,在日本,“国学”的涵义也经历过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据竹内理三等编《日本历史辞典》载,日本古代的“国学”乃相对于中央的大学而言,指各国设置的郡司子弟学校,主要传授儒学和医学,在平安后期衰落(注:竹内理三等编、沈仁安等译《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两相参照,除级别稍异之外,中日两国这一概念的古代涵义十分接近,显系日本摄取自中国。不过,日本近代之“国学”一词则与此名同实异,它指的是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弘扬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因其旨在与西学、汉学相区别,故以“国学”为名,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注:桑兵:《国学研究与西学》,《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对于异域学界这一动向,较早的介绍者当是黄遵宪。1887年,他在《日本国志》中就指出日本“近世有倡为国学者”(注: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页。)。
目前所知,国人中最先将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用于中国者乃梁启超。1902年秋,他曾经以创办《国学报》的计划,商之于黄遵宪,并且商请黄氏“分任其事”(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如果说梁启超此番提及“国学”,还仅是作为一个正在酝酿的计划偶见于私人信函;那么,他在数月后所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则屡屡径直称之:“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或是作为回应,1903年2月,《新民丛报》刊登了《游学生与国学》一文,呼吁在会馆内设立“国学图书馆”,以满足留学生研究国学之需要(注:《游学生与国学》,《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2月26日。)。稍后,邓实也在《政艺通报》上发表了《国学保存论》(注: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第3年第3号,1904年3月31日。),对“国学”一词做出了近代意义的阐释,并于1905年初在上海创立国学保存会,公开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注:邓实:《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2年第1号,1906年2月13日。)。至于国学巨擘章太炎,更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
由此可见,诚如有的论者所观察,“‘国学’之名,始自何人,今已无考,然最早出现于光绪末年,可断言也”(注:马瀛:《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版,第3页。)。确实,从它见诸报端的频繁程度以及一系列相关团体的纷纷建立来看,到20世纪初,“国学”一词已基本实现了语义的转换,并被国人普遍接受和使用。
不过,因“‘国学’一名,前既无承”,纯属舶来转借,故“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注: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以至于“此二字虽日日腾于人口,而究之其确诂何若,则几于无人能言之”(注:闻宥:《国学概论》,胡韫玉(朴安)、陈乃乾编《国学》第1卷第3期,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版。)。陈独秀就断言“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注:陈独秀:《寸铁·国学》,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6-517页。)。朱自清也严厉批评说:“我想‘国学’这个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注:朱自清:《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曹聚仁则更是因此提出了“轰国学”的主张,他说:“国学无确定之界说,无确定之范围,笼统不着边际,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故为澄清学术界空气计,不能不轰国学。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如之何其可不轰耶?”(注: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上册,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第92-93页。)此外,何炳松也号召大家“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他问道:“国学两个字的意义,我总觉得它广泛模糊,界限不清,……究竟‘国学’是什么?现在谁能下一个合理的定义?”(注: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
尽管如此,自清末发端,到民初风行,仍不断有人尝试对“国学”一词的内涵外延做出各种诠释。概言之,大致可分为广、狭两义。
狭义者,多有所别择。如邓实曰:“夫国学者,别乎君学而言之。”这便将“国学”与“君学”区分开来(注:邓实:《国学真论》,《国粹学报》第3年第2号,1907年4月2日。)。汪震、王正己则说:“国学为中国固有之学问,盖指我国欧学东来以前之学也。”(注:汪震、王正己同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版,第1页。)这显然是将“国学”的下限界定在晚清甚至明代中叶西学东渐之前。此外,正如蔡尚思所概括,“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一般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注: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上海启智书局,1931年版,第5页。),当时的狭义诠释确实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侧重史学者如顾颉刚,便强调“国学”也就是历史,“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注: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至于注重国文者,则也不遑多让,纷纷迳称“国学者,国文学而已”(注:邵祖平:《国学导读》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与此同时,更多的学人和团体则是从广义的视角来理解“国学”。譬如,章太炎在日本主持国学讲习会,所讲的主要是“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注: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民报》之“国学振起社广告”且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注:《国学振起社广告》,《民报》第8号,1906年10月8日。)授课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亦自我定位:“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注:《公布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布告》,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而清华《研究院章程》也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注:《研究院章程·缘起》,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页。)。研究院主任吴宓还解释说:“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注: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第374页。),他后来更是阐明:“今宓晓以本院所谓国学,乃取广义,举凡科学之方法,西人治汉学之成绩,亦皆在国学正当之范围以内,故如方言学、人种学、梵文等,悉国学也。”(注:吴宓:《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清华周刊》第371期,1926年3月19日。)这些广义的界定,无疑大大扩充了“国学”的堂庑。
除以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学研究机构之外,当时众多学人也持广义的看法。胡朴安便说:“国学二字,作如何解释?即别于国外输入之学问而言,凡属于中国固有之学问范围以内者,皆曰国学。”(注:胡朴安:《研究国学之方法》,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上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5页。)郑奠也以为:“愚谓国学之范至广,凡域内固有之学,无间于心与物皆隶焉。”(注:郑奠:《国学研究方法总论》,洪北平编《国学研究》,上海民智书店,1930年版,第3页。)蔡尚思则有感于诸多的狭义观点“皆仅得其一体,而尚未得其大全”,遂强调指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畸了。……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注: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上海启智书局,1931年版,第5页。)
总之,在近代中国,关于“国学”的定义,始终是见仁见智、难有定论,以至有论者指出“‘国学’其实并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而已”(注: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但总体上说,尤其是从近代“国学”一词在日本肇始的本义和梁启超的转借义来看,应当承认它最初得名正在于力图彰显本国固有学术、与外来文化相区别。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便屡以“国学”一词,与所谓“新学”、“外学”相对举。所以究其近代涵义,在很大程度上即泛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正式开办时就明确声明:“本学门设立宗旨,即在整理旧学。”(注:《研究所国学门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22日。)南京高师《史地学报》在介绍北大《国学季刊》时也表示:“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注:《北大出版之两种季刊与史学》,南京高师史地研究会编《史地学报》第2卷第4号,1923年6月版。)
二、“国故”一词在近代的引申
与“国学”相似,“国故”一词同样也古已有之,而且它在近代也发生了颇大的语义变迁。不过,与近代“国学”涵义纯属舶来转借有所不同,近代的“国故”一词乃是道地国货,它在近代的语义转换,更多的是对传统涵义的引申和拓展。
在中国古代,“国故”一词意味着国家遭受的凶、丧、战争等重大变故。《礼记·文王世子》便说:“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清代学者孙希旦《礼记集解》也引刘敞曰:“有国故者,谓凶、札、师旅也。”到晚清,“国故”又有了一个新的涵义,即“朝掌(章)国故”,用来专指典章制度。如魏源便推崇龚自珍“以六书小学为人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注:魏源:《定庵文录叙》,《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9页。),他同时还揭露科举制度禁锢天下之智慧,“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注: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集》上册,第165页。),从而主张“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注:魏源:《圣武记》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88页。)。
而最早在近代意义上使用“国故”一词者,当是章太炎。他早在1903年身陷西牢作《癸卯口中漫笔》时,即自命:“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8页。)在1907年8月《与孙仲容书》中,他又写道:“方今国故衰微,大雅不作,文武在人,实惟先生是赖。”(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7页。)如果说章氏以上所谓“国故”,在一定程度上仍可理解为“典章制度”,那么他在1910年所著《国故论衡》一书中,则明确地将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学(文学界说、历代散文、诗赋)、诸子学等一并纳入,从而大大引申拓展了“国故”的传统涵义,基本勾勒出近代“国故”一词的涵盖范围。藉其声望,兼之振臂一呼,“国故”一词很快就被人们所广为接受。如钱玄同在1910年便有感于“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遂在《教育今语杂志》章程上标明:“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注:钱玄同:《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然而,章氏虽提出“国故”一词,却语焉不详,因此往往为人任意比附。毛子水就质疑:“什么是国故呢?我们倘若把这个问题问起那些讲国故的人,所得的回答恐怕没有相同的。……国故这个名词,没有很清楚很一定的意义,就可从此知道了。”(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号。)曹聚仁也不由感叹道:“吾人一提及‘国故’,则庞杂纷沓之观念交集于前。若就各观念而一一考订之,则一切观念皆浮泛空虚,枵然无所有焉”,但他人“援用此‘名’,从未计及其实;其意盖以为‘国故’之名,尽人而喻之也”,于是“何为国故?初涉思于此问题,似应声而可解。及再三端详考虑,则解答之困难,随之以俱增进”。究其症结,他指出正在于“‘国故’,‘国学’,‘中学’,‘国粹’,‘国故学’等歧异名词,在近顷学术界已成一异文互训之惯例,笔之于著作,见之于制度,习焉相望,莫知其非也”(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
鉴于“以论理绳之,则‘国粹’一名,当别为解释,与他名相去甚远”(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因此“国故”与“国粹”还较易区别开来。傅斯年后来虽极力反对“国故”一词,指斥“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但他在1919年的态度还较缓和,认为“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注: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新潮》第1卷第5号。)。他这一观点可能还直接影响了胡适。胡适1921年7月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演讲时便说:“‘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注: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杜春和等编《胡适演讲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此后,在1923年1月所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也再次重申:“‘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6页。)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演讲时,胡适又一次强调:“‘国故’这两个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从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注: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胡适演讲录》,第98页。)直至晚年,他还追忆:“‘国故’这一辞那时也引起了许多批评和反对。但是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个名辞。最先使用这一名辞的却是那位有名望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他写了一本名著叫《国故论衡》。‘故’字的意思可以释为‘死亡’或‘过去’。”(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84页。)
胡适将“故”训为“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看法。如曹聚仁就解释说:“‘国故’之‘国’,乃专指‘中国’而言,非泛称也。‘故’之义为‘旧’;以今语释之,则与‘过去’二字相当。”(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汪震、王正己也说:“‘国故’的意义是中国旧有的学问。”(注:汪震、王正己同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版,第1页。)至于毛子水,则更是十分明确指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919年5月,第1卷第5号。)
不过如此一来,则诚如曹聚仁所指出,“习常之目‘国故’,殆与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既然“国故”泛指的也是中国旧有的学术文化,那么它与近代人们所普遍认为的“国学”岂不是没有分别?
其实,章太炎在近代的“国学”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情况下,另外又提出“国故”一词,无疑是别具其一番深意。综观章氏使用的“国故”一词,除具有着“国学”的内涵外延之外,还蕴含了一层“继绝存故”的言外之意。他在致吴承仕函中就说:“仆辈生于今世,独欲任持国学,……今之诡言致用者,……其贪鄙无耻,大言鲜验,且欲残摧国故。”(注:章太炎:《致吴承仕函》,启功等整理《吴承仕藏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7页。)这里“国学”与“国故”二词不惟并称,涵义也各有所指。细加推敲,此处的“国学”一词,主要是在学术研究的意义层面上,指那些作为具体研究内容的传统文化;而“国故”一词,则更多的是在文化传承的意义层面上,意谓着作为中国文化根系所在的文化传统。前者是传统文化,后者是文化传统,二者显然有着具体与抽象、静态与动态的分别。很明显,在章太炎的心目中,以“国故”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虽然是过往的,但是依旧流转不绝,必须竭力予以维系。所以,他所谓的“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方今国故衰微,……实惟先生是赖”等等,无不流露出这种强烈的忧患与拯救意识。
但章太炎的这种苦心孤诣和弦外之音,未必能被新派人士理解与接受。如傅斯年后来就批评说:“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乃太炎尽改其旧义,大无谓也。”(注: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转引自罗志田:《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4期。)至于其他新派人物即使认可“国故”一词,可是在他们身上,章氏那种对“国故”的忧患与拯救意识已不复存在,相反却填充进了更多的批判精神。他们持论的根本立足点便是不仅将“故”释为“过去”,而且还等同于“死亡”。胡适虽然直到晚年才吐露此意、为“故”正式附加了“死亡”的释义,但他早年或许已有此念、只是尚存顾忌而未发。相形之下,一些受他影响的新派分子则远比他激进。毛子水1919年就指出“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然而正如病人的死尸可以成为“病理学上的好材料”,“我们中国的国故,亦同这个死人一样”有其用处;因此,在他看来,“研究国故,好像解剖尸体”(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919年5月,第2卷第1号。)。钱玄同也认为:“研究中国的学术等于解剖尸体。”(注:钱玄同:《敬答穆木天先生》,《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他还辨析说:“过去的已经僵死腐烂的中国旧文化,可以称它为‘国故’(有人称为‘国学’,很有语病)。”(注:钱玄同:《汉字革命与国故》,《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显而易见,新派人士与章太炎对“国故”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不过尽管如此,“国故”与“国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则是双方都认同的。或许也正因此,傅斯年曾观察到:“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注: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转引自罗志田:《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4期。)。
三、“国故学”的肇端
如果说“国学”与“国故”二词,一属外来转借、一属古义引申;那么,“国故学”则是近代国人的新造名词。
第一次揭橥“国故学”概念的是毛子水。在1919年4月撰写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中,他就提出:“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他自己并不是国故,他的材料是国故。”(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919年5月,第1卷第5号。)这一概念及其界定很快地便被胡适所认可。他不仅随即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函中加以运用,而且还在后来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对此重新做了一番诠释,他解释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6页。)
毛子水、胡适此论甫出,立即在当时知识界激起了很大反响。一方面,大多论者肯定了二人所提出的“国故学”这一概念,尤其对他们关于“国故”与“国故学”关系的解说表示赞同。吴文祺即指出:“整理国故这种学门(疑为‘问’之误——引者按),就叫做国故学,国故是材料,国故学是一种科学。”(注: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35页、第41页。)而曹聚仁也指出:“‘国故’与‘国故学’,非同物而异名也,亦非可简称‘国故学’为‘国故’也。‘国故’乃研究之对象,‘国故学’则研究此对象之科学也”(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他并且还以章太炎《国故论衡》为例,批评其“仅能止于‘有组织’,未可谓其有系统也”,由此来论证“吾国前此仅有‘国故’未有‘国故学’”(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很显然,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张大了“国故学”一词的影响。
与此同时,吴、曹二氏也对胡适所谓“省称”的说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吴文祺就针砭说:“近人往往把国故学省称为国学,于是便引起了许多可笑的误会。……所以我们正名定义,应当称为‘国故学’,不应当称为‘国学’。”(注: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41页。)曹聚仁也并批评胡适将“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斯言妄也,胡氏之说,殆迁就俗称而为之曲解耳,抑知‘国故’二字之重心在‘故’,……去‘故’而留‘国’,则如呼‘西瓜’之为‘西’、‘太阳’之为‘太’,闻者必茫然不知所云。故愚以为国故学,必当称为‘国故学’,决无可省之理”(注: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上册,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第90-91页。)。
另一方面,还有论者则根本反对“国故学”一词。作为《国故学讨论集》一书编者,许啸天即曾明确表示:“中国莫说没有一种有统系的学问,可怜,连那学问的名词也还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闹的什么国故学、国学、国粹学,这种不合逻辑的名词,还是等于没有名词。 ……我们中国的有国故学三字发见,正是宣告我们中国学术界程度的浅薄,知识的破产,而是一个毫无学问的国家。”(注: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6页。)他还指斥:“‘国故学’三个字,是一个极不彻底极无界限极浪漫极浑乱的假定名词”。不过,他接着也承认:“我实在是羞死了,气死了!所以在不知不觉中说了几句过激的话。按到实在,这‘国故学’三个字,还算是近来比较的头脑清晰的人所发明的;有的称‘国学’,有的称‘旧学’,有的称‘国粹学’。”(注: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3页。)与许氏的冲动相比而言,马瀛的斟酌则较具理性,他指出:“顾‘国故学’之‘故’字,限于文献,未能将固有学术包举无遗,微嫌含义窄狭,故不如迳称之曰‘国学’为较宜。”(注:马瀛:《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版,绪论第3页。)
然而,相较于胡适显赫的学界地位及其所掌握的话语霸权,这些不同的意见毕竟显得相当微弱。于是在20年代知识界,“国故学”一词仍然基本如胡适所诠释与演绎,纳入了“整理国故运动”的轨道并风行一时。
通过以上疏理可以看出,在清季民初,“国学”、“国故”、“国故学”三词之间,既有不同涵义,却又相互关联。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国学”、“国故”均指中国过去旧有的学术文化,只是“国故”一词相对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而“国故学”指的则是“整理国故”的学问,同时也往往被省称为“国学”。这也就是说,近代所习称的“国学”,有时是作为“国故学”的研究对象存在,有时则意味着“国故学”本身。明乎此,庶几能为恰当阐释“整理国故运动”预先做些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