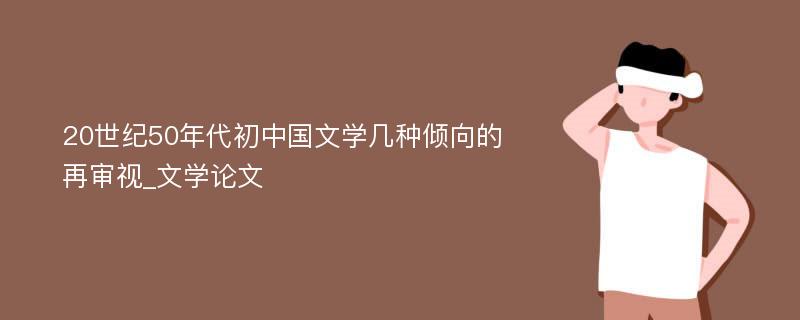
重新审视5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几种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年代初论文,中国文学论文,重新审视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0]02—0089—07
“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转型
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 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明确表示庆贺“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今天的大会师”。这“两个地区”是指解放区和前国民党统治区,他用相同的口吻高度评价来自这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解放区,许多文艺工作者进入了部队,进入了农村,最近又进入了工厂,深入到工农兵的群众中去为他们服务,在这方面我们已看到初步的成绩,在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坚持着自己的岗位,在敌人的压迫之下绝不屈服,保持着从五四以来的革命的文艺传统。”(注: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收《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 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40页。)在会上, 还由周扬和茅质分别作了总结两个地区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但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两个报告人的报告文本和发言态度,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差别。周扬刚开始宣读报告就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注: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同上,第684页。 )而茅盾的报告虽然也是总结斗争经验,但更重要的篇幅是用在检讨前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倾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从理论与创作两方面批评了抗战时期捍卫“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面旗帜胡风和团结在胡风周围的一些进步作家。很显然,两个地区、两种传统在未来文艺发展道路上所处的主次、重轻关系摆得非常明确。当然,能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都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属于“人民需要的人”(注:《毛主席讲话》,同上,第637页。 )(毛泽东语),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崇高的荣誉,因为还有许多在“五四”新文学发展中作过重要贡献的文学家被排除在大会的外面。如创作《边城》的著名作家沈从文,主编《文学杂志》的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以及在沦陷区大紫大红的女作家张爱玲。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预示了即将拉开帷幕的中国文学新阶段将由来自解放区战争实践的文艺传统为发展基础,同时也在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吸收“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战斗力量。这样的新的文艺阵容的组合工作,早在1948年就加紧展开了。那一年,中共领导下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策划的文学理论刊物《大众文艺丛刊》创刊,充满火药味地批判文坛上各种倾向:由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激烈辱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资产阶级”作家,又有邵荃麟、胡绳、乔木(乔冠华)等对左翼阵营内的胡风的文艺理论和路翎的小说进行了集中的清算。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另外几家进步刊物也一起配合对国统区有较大影响的作家创作进行了有计划的批评,被批评的作家有姚雪垠、骆宾基、钱钟书、臧克家、李广田等,范围相当广,相对照的是他们对解放区文艺创作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和肯定性的评价。因此,后来的文学史家有理由认为,1948年的这场批判和“再评价”运动,正是“在为文学史的评价做准备,所要争论(争取)的正是文学史(以及现实文坛)上的主导地位。”(注: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98年,第33页。)可以说,这场批判运动的结果和目的,就是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虽然意味着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已经建立,但是并没有宣布阵营内部的思想斗争已经结束。当代文学的两大传统虽然已分清了主次地位,但两种价值观念、两种美学修养、两种文化实践,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并通过政治运动的形式一再表现出来。50年代初期的文学史是由一系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构成的,到1954年和1955年,毛泽东亲自发起对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对文学理论家胡风及其“集团”的镇压,可以说是这场冲突的顶峰。俞平伯一生研究古典小说《红楼梦》,他的学术成果之所以被挑选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批判运动的典型,主要是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来自于“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胡适的学术传统。40年代末胡适离开大陆远走美国,但他对留在大陆的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具有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但体现在政治立场,更多的是体现在学术研究的思维方法上。胡适一生强调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强调重实验,重证据,不迷信,不盲从等等,在30年代,胡适曾用这种思维方法来劝阻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到了50年代,在当时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的特定革命历史时期要求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抛弃自己的旧世界观,同时焕发出战争时期所有的巨大热情来投入新生活的创造,这套思维方法不能不成为一种消极的障碍,毛泽东抓住俞平伯为活靶,真正目的是掀起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页。)。果然, 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不久,运动就转向了社会科学领域批判胡适唯心论的运动,接着又推动了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而胡风,则是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诞生的左翼文学理论家,他把世界革命文艺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与抗战以来的“五四”新文艺战斗传统相结合,总结出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在鲁迅逝世以后,他自觉继承鲁迅所开创的现实战斗精神的实践道路,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指导和影响文艺创作实践,他通过编辑《七月》、《希望》等刊物和丛书,团结了一大批向往革命的文学青年,在抗战文学运动中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胡风的所有文学实践都是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为出发点的,他强调知识分子应该带了“五四”的战斗传统进入抗战,在接近大众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大众的思维方式、感情方式和认识生活的方式,来更好地引导大众参加抗战并在抗战实践中逐步提高自己,他还坚持对蕴涵于大众中的“精神奴役创伤”进行批判。这些鲜明体现了“五四”启蒙传统特征的思想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战争要求出发强调知识分子自觉改造思想感情,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为工农兵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实质上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于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这些差异还不明显。50年代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全国文艺的总方针时,这些差异就不能不尖锐地表现出来。但胡风本人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差异的严重性,他把它看成是来自解放区的一些理论家在解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时发生的理论偏差,为了让毛泽东直接理解他的理论观点,他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系统地解释自己的理论主张,并逐条反驳何其芳、林默涵等人对他的批判。这就是胡风的长达三十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结果他非但没有获得信任和缓解矛盾,反而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判,最后升级为政治问题,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被强加上“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而受到镇压,这个冤案直到80年代才逐渐平反。
经过批判胡适思想和镇压胡风集团,“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基本内涵已经无法再生出积极的意义,它凡能被毛泽东吸收到自己文艺思想体系去的部分因素,也只能通过毛泽东自己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其他因素,都不能不转化为隐形状态,零零星星地结合着作家的创作实践被表现出来。如1956年的“双百方针”时期,关于干预生活和提倡写真实、人性论的文艺现象中,“五四”传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活。(注:洪子诚《1956:百花世代》,山东教育出版社“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98年,第12页。)在文学创作方面,“五四”的传统仍然断断续续地发挥着影响。一批从“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作家面对新时代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由于三十多年来的文艺道路的复杂的政治斗争犬牙交错地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不同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的作家都不能不带着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与新时代的关系。这里不提已经出奔海外的作家,以留在大陆迎接新政权的作家来说,内心世界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纵情欢呼,有的小心窥视,有的惊惶失措,也有的隐姓埋名,……从那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在一个比较单纯的革命时代里,知识分子的心理世界却是不单纯的。
第一类作家主要来自左翼文学阵营和长期配合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的进步民主人士。他们在新政权的奋斗史和建立史上占有一席光荣之地,一种当然的胜利者的喜悦极大地支配了他们的情绪,尽管在实际的政治生活纠葛中他们也会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烦恼,但在历史与人民的同一立场上,他们真诚地感受到分享胜利的喜悦。他们与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不同,后者经过延安整风的教育,从革命实践中体会到新政权对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除了赋予革命的权利以外还将同时赋予痛苦改造自己旧世界观的义务,而他们则是在左翼文艺运动开始,就一向以唯我革命的姿态激励着自己在艰苦的环境里孤军奋斗,一直在指导别人斗争的人往往忘记了自己也会成为革命和改造的对象,所以,此刻他们自然而然地把新政权看做自己长期追求的理想的实现,高声歌唱新政权。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
第二类作家是一批数量众多的游离政治斗争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坚持独立的理想追求,不满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状,所以对于历史的大变革抱有希望,但并不了解新政权对他们意味了什么?尤其是在“五四”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多少受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他们自知与新的时代要求有一定距离,但希望通过互相谅解达到一种新的契约关系。“五四”一代的重要作家比较多的是持这一类态度,如老舍,最初从海外回国,提出过“不反美”的要求(注: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如巴金,他早期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时发言,竟情不自禁地套用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柏克曼在“十月革命”后回国参加苏维埃建设时的讲演题目:《我是来学习的》(注:[日]坂井洋史《读巴金——违背宿愿的批判者的批判者的60年》,收《巴金的世界》,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第三类作家是指那些曾经在历史上间接或直接地与共产党、或左翼运动发生过冲突,有过并不愉快的回忆,或者虽然没有冲突,但出于阶级或社会关系的隔阂,在感情上对新政权是格格不入的。但他们在时代发生深刻变化的关键时刻,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能够忘掉过去的不愉快记忆,和新政权重新调整好关系。在新时代面前,他们的内心是相当紧张的。沈从文可以说是这一类作家的代表。他在当时因承受不了来自时代的巨大压力,一度神经失常,在狂人般的呓语里表达着敏锐的感觉。他当时写下的这些文献,都不可能公布,成为一种潜在形态的写作,在今天看来,却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真实的精神记录文献。沈从文后来终于离开了文学领域,转向历史文物的研究,作出新的成绩。这类作家大多数都自觉退出文坛,隐居在民间,有个别人也在潜在状态下从事大量的写作,如卜宁(笔名无名氏)在隐居状态下完成了二百万言的巨著《无名书》。
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是复杂的,作家的主观态度和倾向仅仅能决定文学创作的某一个方面,他们所面对的更具体的文化困境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给予作家的表达形式——从思想、感情到审美语言,在一个新的时代环境和革命功利主义的要求下完全失去了呼应时代的能力。除极个别作家在特定条件下(如历史题材)创作出较好的作品外,绝大部分前国统区作家的创作优势都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们的抒情变得空洞无力,他们的写实变成图解时事,这就使他们的创作不仅数量下降,而且艺术质量也失去了生命涌动的魅力。且不说巴金、曹禺、叶圣陶、冯至、臧克家等一代作家均没有创作出力作,即使是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重要作家如茅盾、艾青、丁玲、夏衍、沙汀、艾芜、田间等,也没有创作出可与自己以前的文学成就相媲美的作品。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创作能力的衰竭,而是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的当代文化规范不适应并且不能接受他们的精神劳动。反过来,真正体现出“五四”精神成果的,倒是许多在当时不能发表,也没想到要发表的潜在写作,如被剥夺了写作权力的“七月派”和“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创作、无名氏所创作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无名书》等。(注:《无名书》在40年代末已出版第1、 2卷及第3卷上册,50年代开始,无名氏隐居杭州,继续写作,相继完成了第3 卷下册和第4、5、6卷。80年代全书陆续在台湾出版。 )在今天看来却是那个时代最有特色的文学创作。
胜利者的政治抒情:《时间开始了》
50年代初期是一个旧的文化规范不相适应、新的文化规范正在酝酿的新旧交替时期,思想理论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了一时的风气,文学创作反而相对寂静。这与时代表面所呈现的轰轰烈烈状况成了不协调的对照。在这样的气氛下,胜利者的政治抒情诗创作,成了唯一高昂的声音。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政治抒情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对新政权及其领袖人物的直接歌颂上,这也是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所没有的因素,大约先是抗战环境促使一部分诗人对灾难中的祖国的颂扬,进而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间文艺中出现了对地方政权和领袖人物的颂扬,有些诗人(如艾青、徐迟等)也初步尝试了歌颂题材的创作。50年代以后,“为满足表现‘新的人民时代’的题材与主题的要求,‘颂歌’便进一步发展为诗歌创作的普遍范式。在内容上,它表现为互有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时代——人民革命的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及其主人翁——工农兵群众的歌颂;一是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歌颂。二者同时也就是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歌颂。”(注: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颂歌”样式成为50—60年代政治抒情诗创作的主流,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领袖个人的颂扬达到登峰造极,歌颂的构思方式也日愈模式化。在50年代初期,由于“颂歌”是一种新的主题样式,“五四”新文学启蒙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显然缺乏相应的语言表达能力。最典型的例子是“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自由诗体的创始人郭沫若,竟用古典词赋形式写出了歌颂新政权的《新华颂》,柳亚子等旧体诗唱和也风行一时。用自由诗形式来写颂歌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少,但流于空洞抒情或概念化叙事的粗制滥造倾向也不在少数,总的说来,可能是诗人积蓄在心底的感情急于倾诉,语言上往往表现出“江河不择细流”的泛滥风格,散文式口号式甚至语录式的叙事句比比皆是,泥沙俱下,既粉碎了一般抒情诗歌的规律和节奏,以宏大叙事来重新创造诗歌的“巨无霸”形式,又反映出诗人主观感情的大自由大解放与“颂歌”体的英雄崇拜心理奇妙混合的矛盾,它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诗歌特色。
把这种政治抒情诗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胡风创作于1949年底到1951年初的大型交响乐式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注:本文依据《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胡风创作这部政治抒情诗的心情可能比较复杂,不仅仅是出于对新政权的欢呼,(尽管表现出来的是这种形态),当时胡风的文艺理论已经受到中共具体领导下的有计划的批判,被认为是“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去曲解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方针”(注:萧恺《文艺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大众文艺丛刊》第2辑。), 而且从茅盾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对他的批判来看,他似乎很难从理论角度来为自己作有效的辩护(尽管他一直试图这么做),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用创作来证明他的理论究竟是否有利于新的政权建设,知识分子的“主观战斗精神”究竟能否与新的政权的要求达到一致。《时间开始了》就是一个努力,他用夸张的热情歌颂毛泽东,歌颂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理论与时代的同一性。当然,胡风对毛泽东所怀有的亲近和钦佩也是真实的,特别是1938年曾经他之手最早发表了《毛泽东论鲁迅》以后,一种知遇之感始终洋溢在他的心里。这样两种感情的交融,使他在诗中用饱满的激情大声歌唱:
海
沸腾着
它涌着一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他右手握紧着拳头
放在前面
好像他双脚踩着一个
巨大的无形的舵盘
好像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
各种各样的大小河流
从语言里透彻着个人视角的亲切感,又不失分寸地把毛泽东推上了历史巨人的高峰。这正是胡风诗歌理论的核心:诗人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发酵,诗的情绪的花是人民的情绪的花,诗人的巨大的感情因素必须与时代的精神特质紧紧地结合起来。《时间开始了》更成功的是诗人用相当个人化的语言叙述了诗人与几个先烈之间肝胆相照的动人故事,所谓“个人化的语言”指的是诗中抒情主体既是十分具体的诗人自传形象,又融合了某种庞大的共同性的时代声音,后者是通过前者的真实而不是概念化的感受来表达的。这个叙事特点尤其体现在第四部《安魂曲》,诗人毫不掩饰先烈们曾经有过的灵魂低沉的时刻,以及各种性格上的缺点,尤其是对革命作家丘东平的诗体叙述,简直刻画出一个血淋淋的灵魂。这与诗人一贯主张的要作家写出人物灵魂的痛苦搏斗过程也相一致。
七月派诗人绿原曾高度评价这部诗:“当时歌颂人民共和国的诗篇实在不少,但从眼界的高度、内涵的深度、感情的浓度、表现的力度等几方面进行综合衡量,能同《时间开始了》相当的作品未必是很多的。”(注:引自绿原、牛汉对话录,本文依据《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76页。 )如果把《时间开始了》放在同类政治抒情诗创作之中来考察,这样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这部长诗包容了以颂歌为特色的政治抒情诗的许多必要因素,特别是强烈的抒情主体的塑造,以致后来者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等50年代重要政治抒情诗人的创作都难以达到这样的独创程度;但是也应该看到,当时凡“颂歌”体的政治抒情诗具有的缺点,诸如诗歌语言的不精炼和“颂歌”体的程式化、无节制的主观感情宣泄、以及对领袖人物的狂热崇拜倾向,等等,这部作品都有比较充分的暴露;至于其“巨无霸”式的结构所造成无旋律美感的冗长和重复,如在一个“欢乐颂”后再来一个“欢乐颂”,在描写政协会议中间又插入了党员大会,在叙述纪实性人物时也采取了跟着故事走的自然主义态度等等。这些可能又是这部长诗所特有的缺点。
寻找时代的切合点: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
在50年代初期的文学读物里,不管是哪一类作家,只要他能公开发表的作品,大约都是歌颂性的,许多为“歌颂”而“歌颂”的作品,在今天读来完全失去了具体的感染力。这不完全是因为今天的读者已经不理解那个时代的感情,譬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虽然也夹杂着许多程式化的语言,但诗歌里洋溢着巨大而真挚的感情(主要是《青春曲》里的抒情诗)和对先烈的深切缅怀(主要是《安魂曲》的部分内容),现在读起来仍然相当感人。但是大量来自国统区作家,对新的政权不可能产生理所当然的“胜利者”情怀,他们认同新的时代,并愿意学习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武器,在自我教育的基础上赶上时代的要求。这样的作家在写歌颂性的作品时态度总是比较谨慎,很少将抒情主体扩大为“时代声音”,而是作家通过发扬主体的积极因素来寻找与时代的切合点。“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自身具有强烈的民主性因素,在新的时代里仍然可能结合时代的战斗性要求,使他们对时代的歌颂与主观情感建立切实的联系,使“颂歌”成为一种比较诚实的抒情。如诗人臧克家在1949年底写的短诗《有的人》,在纪念鲁迅这一切合点上接通了时代的精神。还有老舍,他从美国回来后根据北京市民的生活状况,写出了《龙须沟》等一批话剧,在表现北京市民生活变化这一点上,歌颂了新的时代和新政权,主题是新的,但作品的题材和创作思想都有一以贯之的连续性等等。这样的创作在当时都属于比较优秀的创作。本节所要重点介绍的散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注:《巴金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正是这样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
作家巴金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觉醒并走上社会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50年代以后,巴金虽然作为一位有声望的进步作家受到社会的尊重,但他原来的政治理想显然变得不合时宜,事实上他也主动放弃了对信仰的宣传,只是保持了热情的文风,用来抒写对新的政权和新的时代的歌颂。巴金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有官方安排的各种出国访问(包括到朝鲜战场去“体验生活”),然后写出各种游记、随感和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虽然写得不少,但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写作动机下很难发挥他的创作优势,他所擅长的抒情艺术也显得琐碎而空洞。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
这篇散文虽然还是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记录了作家参观集中营的过程,虽然作家基本上是叙述集中营的历史资料而很少主观发挥,但它震撼人心的力量仍然十分强烈。这首先是材料的力量所决定的,在大量的纳粹迫害犹太民族的罪行面前,任何主观抒情都会变得虚伪与不相适宜,重温这段历史悲剧的人,只能屏气息声,静静地沉入历史。作家用纯客观的叙事方式带领读者身临其境地参观集中营,从进入到结束,让历史事实在每个人的眼中和心中流淌,这正是这篇散文最恰当的表达形式;其次,从作家的叙事中可以了解到,作家只是套用参观记的叙事结构,在阅读了有关研究著作和回忆录以后,才精心组织起这篇文章。许多材料不动声色地从作家笔底显现出来,与集中营所展览的内容浑然一体地揉合在一起,达到了完整、丰富、有机的统一。其三,在非常有限的篇幅下,作家还是刻画了一个波兰人阿来克斯的形象,这位从小就在集中营里渡过、父母都死在这里的年轻人竟然担任了参观集中营的接待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残酷的现象,但作家写出了他的冷静和坚强,只有一处,作家这样写他:“平日倔强的阿来克斯现在显得沉静了,他的眼光在各处找寻。他在找寻他的父母的脚迹吗?他在回忆那些过去了的恐怖的日子吗?忽然他抬起头看着我们,过后便指着湿润的土地说:‘这都是烧剩的人骨头啊,这些白色的小东西!’我朝我的脚边看,土里面的确搀杂了不少的白色的小粒。”这样一个小小的残酷的现场有力地衬托了阿来克斯的表面冷静下巨大的内心痛感,他显然不是麻木地职业化地展览自己民族的苦难。
巴金的信仰里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战斗勇气,在20年代反对美国政府迫害工人运动领袖萨珂与凡宰特的斗争中、在30年代反对法西斯军队侵犯西班牙的斗争中,巴金都积极地参与到这些世界性斗争中,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国际人道主义的义务。所以由他来写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恶是最恰当不过的,他的人道主义的痛苦也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能与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有机地吻合起来。散文的结尾写到作家将离开现场,他悲痛地写着:“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感情啊!我的神经受不了这许多。对着那遍地的白色骨粒,我能够说什么告别的话呢?”于是作家依依不舍地站在那里不忍离去。这样的抒情方式与心理描写,与当时高昂的时代战斗精神也不怎么相吻合,若出现在另外一种场合很可能会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表现,但由于这样的国际性题材和反纳粹背景,也就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潜在写作的开端:《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
这是一篇奇异的手记式的散文,写作时间如标题所点明的,1949年5月30日。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的大幕还没有正式拉开, 但北平(北京)城里已经云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人们正在兴高采烈地筹备第一次文代会。可是,30年代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边城》、《湘行散记》的作者沈从文却陷入了异常困惑的精神危机中。1948年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用清算的口气辱骂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注:郭沫若《斥反动文艺》,收《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17页。)。政治上的乌云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摧残了他并不坚强但很敏感的神经系统。四十多年以后,公布了沈从文当时各种文字材料的《从文家书》一书的编者这样说:“1949年,正准备‘好好的来写’一二十本文学作品的沈从文,终止了文学事业,也走下了北大中文系讲台。由于内外原因交互作用,一月起,陷入精神失常。消息传到刚刚解放的清华园朋友中,梁思成夫妇、金岳霖等马上请他去清华调养。朋友的真挚关怀未能缓解起病情,他病了很久很久……”(注:沈虎雏编《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这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注:此文未发表,初刊于《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就是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之一。
虽然这篇手记仅仅是作者在病中的“呓语狂言”,但它富有象征意味地记录了知识分子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里呈现出来的另一种精神状态。病中的沈从文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世界在动,一切在动”,但他真正感到恐慌的不是世界变动本身,而是这种变动中他被抛出了运动轨迹:“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正因为沈从文从来就不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所以他才会对这个变化中的时代既不具备任何敌意和戒心,也不是明哲保身地冷眼旁观,而是想满腔热情地关爱它和参与它,所以才会对自身被排斥在时代以外的境遇充满恐惧和委屈。这种感受多么清醒,多么逼真,哪里有丝毫的“神经失常”?所以他要大声地宣布:“我没有疯”!他还要进一步地反复追问:这“究竟为什么”?作者虽在病中文字仍然充满力量,读完这篇手记,一个善良而怯懦的灵魂仿佛透明似的毕现在读者的眼前,人们忍不住想问: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的到来,难道不能容忍这样一颗微弱而美好的生命的存在吗?
虽然这是一篇随意性极强的手记,其文体却鲜明地烙上沈从文向有的文字特点:文字松弛、内涵丰富、语言有节奏感。沈从文有很高的音乐辨别能力,文章从“静中有声”开始写起,写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远处的鼓声(幻觉),灶马的振翅声,孩子的睡鼾声,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声……,每种不同的声音都唤起了他不同的情绪变化,相当细腻有致。在短小的篇幅里他插入了三段不同时间向度的叙事文字:历史的回忆、现实的抒情和对未来的幻想,其中蕴涵了三个女性:历史上的丁玲,现实生活中的张兆和,和幻觉中的翠翠。他首先从一张旧照片引出了丁玲的故事是意味深长的。青年时代,沈从文与丁玲夫妇是极好的朋友,虽然走的道路不一样,但是在丁玲的丈夫胡也频牺牲以后,他曾冒着危险护送丁玲和遗孤回家乡,可说是有胆有识;当丁玲被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后,他又公开发表长篇散文《记丁玲》来唤起民众对失踪者的关注,可说是有情有义。十九年过去了,丁玲成了新时代的文艺官员和风云人物,当年护送的遗孤已经长大成人,可是他,却“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历史是多么嘲弄人?!对于患难与共的妻子张兆和,沈从文是充满了感激和愧疚。当他的思绪从照片上的历史回到现实时,他用两句话来描写自己的家庭:“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眼看着这样一个在温馨熟睡中的幸福家庭将会因为他的缘故而遭到破坏,他的恐惧和绝望是可以想象的,静夜中小灶马的振翅鸣叫似乎也渲染了这种绝望的心理。最后,沈从文又想到了家乡——他时刻魂萦梦绕之地,这位湘西民间世界的赤诚歌手在社会变动中饱经孤独与冷遇以后,本能地想回到土地的怀抱之中,他本来就是属于那一块朴素的土地。翠翠也许是他小说里的人物,也许是艺术人物的生活原型,也可能是家乡民间世界的一个文化幻想,象征了作家归隐民间的理想。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描述家乡时用的是未来时态(端午快到了)而不是过去时态,隐含了作家对未来道路的自觉选择;虽然他后来没有归隐湘西民间,却以半生的精力流连于民俗文化和历史博物的整理,而自觉远离喧嚣的文坛与社会,在民间岗位上尽了知识分子的职责。
如果说,鲁迅当年以石破天惊的《狂人日记》揭开中国现代文学大幕,宣布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大无畏精神,奠定了以启蒙为特征的现代文学传统。那么,沈从文的这篇低调的新“狂人日记”于5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这篇作品当时不可能发表也不可能流传,但从文学史的眼光来考察,当代文学史上一直若隐若现地流淌着一股创作潜流,许多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知识分子留下大批没有公开发表的私人性文字:日记,书信,札记,诗歌,以及有意识的文学创作,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对时代的感受和思考的声音。这些文字比当时公开发表的作品更加真实和美丽,因此从今天看来也更加具有文学史的价值。而沈从文的这篇手记,应该是这股潜在写作之流的滥觞。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胡风论文; 时间开始了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巴金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作家论文; 文艺论文; 无名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