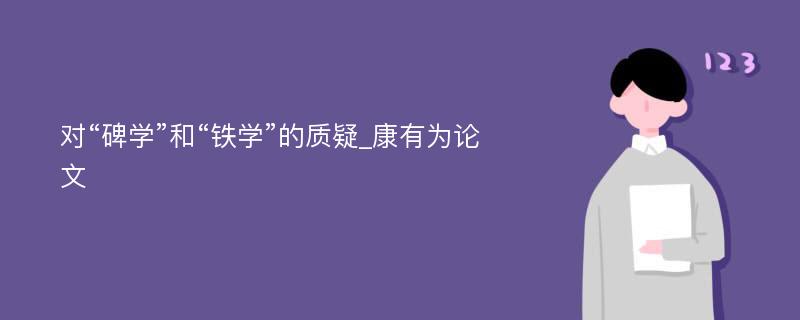
“碑学”、“帖学”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献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描述清代尤其是清代后期的书法发展史时,“碑学”、“帖学”是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两个概念。由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构筑起了清代书法史(甚至有延伸到整个书法史的趋势)的一个基本的写作框架。但遗憾的是,这两个概念在使用中却经常处于混乱状态。
一
先看“碑学”。在有代表性的书史著作中使用“碑学”概念,大约可归纳为三种情形:
一、专指北碑。张宗祥先生《书学源流论》说:“自慎伯之后,碑学日昌,能成名者,赵之谦、张裕钊、李文田三人而已。”(注:张宗祥:《书学源流论·时异篇》,崔尔平选编、点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8月,第888页。)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篇说:“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其提出尊碑的五种理由,也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756页。)沙孟海先生《近三百年的书学》“碑学”一节特加“以魏碑为主”的副标题以限定收录范围。(注: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6月,第52页。)
二、北碑加篆隶。康氏《广艺舟双楫·体变》篇说“今学(即碑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778页。)包括篆书。沙孟海先生《近三百年的书学》把篆、隶分别单列,但在“碑学”一节加上副题后专门说明“通常谈碑学,是包括秦篆汉隶在内的”。(注: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6月,第52页。)现在许多著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碑学”概念的。
三、北碑加唐碑,不包括篆隶。沙老《近三百年的书学》“颜字”一节里,说“就碑帖二字本义说,那末《家庙碑》、《麻姑仙坛记》等等是碑,《裴将军》、《争座位》等等是帖”,“本篇三、四两章所列的碑学、帖学,又是狭义的”,(注: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6月,第67-68页。)然则如果是广义的,则唐碑也就可以包括了。有的著作就把唐碑纳入其中,而把篆、隶摒于其外,如马宗霍先生《书林藻鉴》卷第十二综述中说:“嘉道以还,帖学始盛极而衰,碑学乃得以乘之。……嘉道之交,可谓之唐碑期。……咸同之际,可谓之北碑期。……碑学不囿于唐、魏,而能远仿秦篆,次宗汉分,斯则所谓豪杰之士,固将移俗而不移于俗者。”(注: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新1版,第192-193页。)
用法最混乱的是康氏,分辨得最严谨的是沙老。但不论是用法混乱还是分辨严谨,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和理解存在着严重分歧。
这种分歧必然影响到历史评价。康有为的著述目的是尊碑,则不论怎么界定“碑学”,都是要大力赞扬的。但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碑学”概念的张宗祥先生,评价却不高。沙老在限定了范围后,对所收书家的评价,也可以说是无一尽餍人望。其文共收书家30人,写魏碑的,有邓石如、包世臣、赵之谦、李瑞清、张裕钊、康有为共六人,按比例不算少,但邓、包是前驱,有弱点自不必论,即使晚清的赵、张、李乃至康氏在沙先生的眼里也都不是大方家数。(注: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6月,第52-59页。在“赵之谦”条下,沙先生还带便批评了一位书家:“赵之谦有个同乡叫做陶濬宣,他也是专写北碑——专写《龙门造像》的——写得太板滞了。我以为与其像陶濬宣这般板滞,不如像赵之谦那样流动。好在他于流动之中有勾勒,不至于全没有骨子。”又用括注的方法说:“那时写北碑比较好的,还有孙诒经、李文田。孙浑厚疏宕,方圆并用,确非他人所及,可惜我所见的不很多,李文田似乎太老实了些,故不详论。”见《文集》第55页。即使把陶氏、孙氏再加入进来,此种“碑学”的成就也还是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大。)那么应该说,总体评价是不算高的。在第二种意义上来使用,毫无疑问,评价必然要积极得多,这无需赘言,因为清代复兴篆隶的成就,在历史上已基本得到了肯定。在第三种意义上来使用,首先要面对的还不是如何评价的问题,而是如何区分“碑学”、“帖学”的问题。如果把“唐碑”算作“碑学”的一部分的话,则恐怕这个概念就几乎失去存在的意义了。原因不言而喻:唐以后不受唐碑影响者几人?包括不包括唐碑,对清代书法总体进程的描述和评价,会发生相当大的差异。马先生把唐碑“切割”出来,拼到“碑学”中,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使问题更复杂了,现在看来,接受者似乎不多。
二
再看“帖学”。可以说它同“碑学”概念一样混乱,归纳起来,也可以扼要概括为三种:
一、学晋(人之帖)。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篇首句即说:“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似以“帖学”为学晋人之帖,故后面又说:“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犹不待论。……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754-755页。)
二、写晋唐以来行草、小楷。沙老《近三百年的书学》“帖学”一节标明“以晋唐行草小楷为主”的副题,实际上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沙老又把它分为两种类型:在二王范围内(实际上也包含唐、宋、元、明,因此张照这位学董出身的也得以列入);在二王以外另辟蹊径的。但不包括从北碑中化出行草写法的书家如康有为、赵之谦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沙老把学颜的单列一门,因此这里的“晋唐”是没有颜真卿的“晋唐”。(注: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6月,第44-52、67页。)康有为有“卑唐”之论,在各篇的论述中,也常常把宋、元、明连带批评,当他在《体系第十三》说“近世人尊唐、宋、元、明书,甚至父、兄之教,师友所讲,临摹偁引,皆在于是。故终身盘旋,不能出唐、宋人肘下”(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822页)这种话时,人们不免会把它和他的“碑学乘帖学之微,入缵大统”联系起来,所以在一般人眼里,康氏的“帖学”概念,有时候也等同于“晋唐行草”。和“碑学”概念的作用一样,康氏的“帖学”概念也不那么严谨。
三、学阁帖、甚至主要指学赵、董。马宗霍先生说:“帖学自宋至明,皆所宗尚。”下文并特别指出清帝重阁帖的史实;又说:“宗赵宗董,固自有殊,其为帖学则一也。……至若帖学不囿于赵、董,而能上窥钟、王,下掩苏、米……斯则所谓豪杰之士,固将移俗而不移于俗者,盖亦有人,自当别论。”(注: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新1版,第192-193页。)
这三种意见,对“帖学”基本都持批评态度。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篇说:“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菴,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又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碑学)适乘帖微,入缵大统。”(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754、755页。)马宗霍先生说:“嘉道以还,帖学始盛极而衰,碑学乃得以乘之。”(注: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新1版,第192页。)沙老也说:“有人说,‘碑学乘帖学之微,入缵大统’,这话固然说得过分些,然而清代的下半叶,写碑的人确比写帖的多了。”又认为:“康有为《书镜》里有《尊碑篇》,把阮元的意思推衍开来,说帖学和碑学新陈代谢的情形,很有道理。”(注: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6月,第37、53页。)既承认历史确实发生过这样的变迁,又稍有保留,话比康、马说得委婉、严密,但可以说也是基本赞同的。然而,有趣的是,被一致批评的“帖学”,却是名同而实异,并非同一个靶子。设想一下,如果沙老不把学“颜字”的划走、马先生把他看到的“豪杰之士”算到“帖学”中的话,还能那么一致吗?回答恐怕会是一个问号,看看沙老大著中对翁同龢、梅调鼎的赞许就能明白。
三
需要指出的是,就上面提及的著作而言,不乏有厘清它们的内含、外延,也就是使它们明晰化的努力。特别是沙老,他对每一个类型都有说明、界定,而且在具体的叙述评价中也极为注意彼此间的异同和关联,其写作框架、观点阐述本身都是相当严密的。然而我们也看到,沙老的框架并没有得到较为普遍的接受,因此也就没有根本解决这两个概念使用上的混乱现象。
为什么?
关键就在于“碑学”、“帖学”二分法本身有着先天缺陷,用它们为基础概念来建立书史写作框架,必然导致顾此失彼。本义的碑、帖不过是作品存在的两种方式,晋代以后是长期共存的。唐、宋、元、明各代都有碑,虽然后三代的碑刻不具有代表性,在进行二分法时可以有所忽略,但唐代却没法绕过去。沙老把学颜真卿的划出“帖学(晋唐行草小楷)”圈子,然而没有颜真卿的所谓“晋唐行草”,是不完满的,因而本身是背离历史实际的。试想,宋元明清以来学习晋唐行草的,有多少是不受颜真卿影响的?沙老的这种“切割”法和马宗霍先生对唐碑的“切割”法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很难统一成为一种基本的书史写作框架。
更值得注意的还在于,这种二分法有另一个重大缺陷,就是过分强调了两者的分别,容易导致从写作框架上就忽略清代以来书法的一个重要历史趋向:融铸的道路。清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总结时代,许多领域都出现了涵概古今的大家,构成了一股重要的学术文化潮流。书法领域亦然。许多书家都是多面手,篆、隶、北碑、唐楷、传统行草,兼收并蓄,晚清尤其如此,其例证似乎没有枚举的必要;并且何绍基、刘熙载、杨守敬等还进行了观念上的倡导和建设。宏博精严的沙老,在具体叙述、评价时,很注意点出这种特征,但却没有从写作结构上体现出这一点,根本原因就在于被这个二分法的思路限制住了。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问题太大、太复杂,本不该妄想。但既然已经提出反思,也就不能不有所考虑。一个很不成熟的意见是,与其这样顾此失彼和存在重大的忽略,不如索性取消这两个概念,寻求更合理的方式。初步设想,以沙老的思路为基础,将其具体方法稍加改进:去掉“碑学”、“帖学”的帽子和单列的“颜字”,以取篆隶、北碑、晋唐以来行草小楷作为三种(若篆、隶分开,则是四种)基本的力量;以主要兴起于清代特别是清代后期的、以融铸各派为基本取向的书风作为另一种力量。其长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不会造成某个历史阶段的书法传统被人为分割,其次是能够有效地把固有传统与新发掘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分显现出来。比如何绍基,遍学各种字体、书风,但原来通常被以偏概全地或划为“碑学家”,或划为“学颜字的”,前者忽略了他对晋唐传统的深入学习,后者则忽略了他对新发掘传统的积极吸收,同时还人为分割了晋唐传统。而采用这一框架,何绍基就可以被划入“融铸”的一翼中,这无疑更能揭示他的艺术成长特征和历史发展意义。
这种框架的一个更突出的长处是,对历史的评价将可能更为公正。这一点最主要地表现在对原来所谓“帖学”的评价上。应该承认,由于长期以来人们的研究视野和审美期待视野受所谓“碑学”的制约太严重,研究者对于那些坚守固有传统的书家的重视是不够的,对他们的评价也是不够积极的。然而如果从更大的历史发展视野看,这些书家对固有传统的坚守,实际上是对历史资源的一种有力保持,是对传统书学理念的一种精心呵护;同时,他们对前进在新发掘传统领域内的书家也是一种重要的警示力量和参照系。这一切,都至少在精神传承的层面上具有深远的意义。退一步说,即使只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来看,其中许多人的艺术成就也是相当可观的,起码是不比同时期的一般学碑书家(如李文田、陶濬宣等)逊色。只要把沙老的颜字一翼的部分人(如前举翁同龢)和晋唐行草小楷一翼中的清人合并起来,则所谓“帖学衰微”的结论就不那么好下,马宗霍先生所肯定的“不囿于赵、董,而能上窥钟、王,下掩苏,米”的“豪杰之士”的价值,也就可能得到更多的关注。从而,对于清代以来书法发展的描述和评价,就不会总是把“碑学兴盛、帖学衰微”看得那么理所当然。
在历史写作中,基本框架的确立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它反映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所达到的高度。历史本身是纷繁复杂的,历史写作不可能全部复现它的真面。历史写作的目的,很大一部分在于将这纷繁复杂的现象整理归顺,梳理出脉络,总结出经验,给人们提供认识历史的门径和借鉴历史的镜子。没有框架的流水帐,似乎是要真实无遗地记录历史,实际上不仅不可能,而且根本放弃了历史写作的这一目标,当然不能起到这种作用。然而反过来,不合理、不严密的框架,提供的可能只是一条迷途和一面扭曲的哈哈镜,不仅更加无益,可能还会误导。
当然,历史写作和历史本身一样,不可能一步到位地达到发展的目标,而是需要在不同时代的文化发展基础上,通过不断实践,积累经验,逐步总结出更合理的认识。我们在阅读有关清代书法的一些著作、文章中,得到过许多教益,由此而积累了对清代书法史的基本知识。但是经过思考后,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不揣谫陋,把这些肤浅的想法写了出来,希望有助于深化对清代书法发展史的认识和写作。这类问题很大,关乎全局,前文已经说过,我们的设想也是极不成熟的,权当引玉之砖,恳望大雅方家赐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