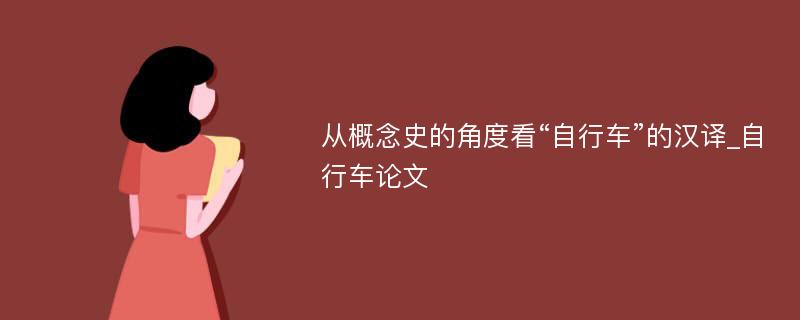
“Bicycle”的中文译名:概念史角度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译名论文,中文论文,角度论文,概念论文,Bicycle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4-0113-07 近代以降,受西力东侵所迫,中国遭遇“三千余年一大变局”,①大至民族国家形态,小至日常器物,皆与传统中国迥然有异。这种变局反映在语言层面,则在历经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国语统一论战、1930年代的大众语论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的语言政策等争论与实践后,传统文言新陈代谢,最终形成现代中国的标准语言即“汉语”。②翻译西文所得中文之词汇,顺理成章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是人类交流的基本行为之一,在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它与语言、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作为社会的动力影响着人类生活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③以自行车为例,自行车技术非一人一国之力所完成,自一开始即是一种跨文化合作而成的交通器械。在其漫长的技术演化进程中,几乎每次改进与创新,自行车都会被赋予一种符合所在民族国家文化的名称:从法国人希布拉克(Comte de Sivrac)眼中的“Célérifère”,发展为德国林务员德莱斯(Karl von Drais)的“Laufmaschine”,再到英国车匠约翰逊(Denis Johnson)的“Pedestrian Curricle”、法国马车修理工米肖(Ernest Michaux)命名的“Vélocipède à pédales”,最后是在英、美等国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流行文化中的“Boneshaker”或是“Penny-farthing”以及“Bicycle”。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行车技术成熟,英文世界“Bicycle”(或简称为Cycle、bike)的称谓亦随之稳定下来。 19世纪60年代,Bicycle与中国初遇之后,如何以中文翻译、如何称谓,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百余年间,Bicycle的中文译名五花八门,学界亦有相关研究,如德国学者阿米尔(Amir Moghaddass Esfehani)的论文《远途跋涉至中国:作为舶来文化技术自行车的挪用,1860-1940年》(The Bicycle's Long Way to China:The Appropriation of Cycling as a Foreign Cultural Technique,1860-1940)④首启这一学术讨论。论文第二章“不断变化中的称谓”(The changing terminology),就是关于Bicycle中文译名的专门研究,作者主要面向西方读者,多用力于分析、解读每一个Bicycle中文译名的拆解汉字的具体含义,对中文译名出现的历史成因未进行文化和社会角度的深入阐释。本文尝试借鉴概念史⑤的研究方法,对Bicycle在近代中国所出现的各种中文译名作一梳理与分类,希冀通过重现东西文明在器物层面上的碰撞痕迹,并由此探讨中国人对新事物的认知策略和水平。 一 Bicycle最早的中文译名 中国人最早接触自行车是在19世纪60年代。1862年,清政府始设同文馆于总理衙门,遣专人学习西方语言,同时亦派人出国采访政俗,视其风土人情。历史的巧合,自行车在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普及热潮(Velocipede Craze)亦在此时兴起。跨出国门的中国人与日渐普及的自行车有了第一次接触,并被记录下来。 1866年,总理衙门派遣内务府斌椿率其子广英、同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等仆从6人前往西方诸国访问,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官派人员出国访问。同年5月7日一大早,斌椿一行抵达法国巴黎,但见“街衢游人,有只用两轮,贯以短轴,人坐轴上,足踏机关,轮自转以当车。又有只轮贯轴,两足跨轴端,踏动其机,驰行疾于奔马”。⑥初到异国,时年63岁的斌椿顿时就被巴黎街头来回穿梭的这种新奇器械所吸引,但是斌椿只是描绘了自行车技术的诸多细节,并没有给其起名字。首位给Bicycle中文译名的人是张德彝。1867年10月,张德彝再次出国呈递国书时,详尽地描绘了他在各国所见自行车技术的情形:“自行车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寸,小者半寸,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左右顾视,趣甚。”⑦两个月后在巴黎,张德彝再次见到“两轮自行车”:“见游人有骑两轮自行车者,西名‘威娄希北达’(法语原词为:Velocipeda),造以钢铁,前轮大,后轮小,上横一梁。大轮上放横舵,轴藏关键,人坐梁上,两手扶舵,足踏轴端,机动驰行,疾于奔马。梁尾有放小箱以盛行李者。出租此车,每一点钟用法‘方’(每方计银二分)又名‘福郎’(今译法郎)者若干,另有铁房为演习乘车之所。”⑧1877年9月1日,此时张德彝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在伦敦的水族馆里,郭、张一行看到了自行车表演的杂技:“二幼女各骑一双轮铁车,英名‘韦娄希贝达’(英文原词为Velocipede),前大轮周丈余,后小轮约三尺,形如口字,女骑当中,手拨关键,高下回旋,侧身扬手,决战争雄,亦陆地之飞仙也。”⑨更为难得的是,张德彝对技术革新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有敏锐嗅觉:“近来街上骑脚踏车者日多一日,亦愈出愈奇。……自有此车,恐将来马车渐稀少矣。”⑩ 张德彝记述所见自行车技术时,使用了“自行车”、“双轮铁车”、“脚踏车”三种中文译名,并附有“威娄希北达”、“韦娄希贝达”英法两国当时对于自行车技术称谓的中文音译。中文音译两词因为不符合中文使用惯习,日后不见在中文世界中使用,而他翻译的三个中文译名皆对后世影响颇深,其中又以“自行车”、“脚踏车”最为流行。 二 Bicycle中文译名的分类 晚清及至民国,Bicycle在中国各地日渐普及,(11)因时、因地、因人之不同,其中文译名亦多种多样。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49年之前,颇为流行的针对Bicycle的中文称谓就有不下20种。下文笔者将对近代文献中出现的Bicycle中文译名作逐一分类梳理,分为五大类别,试以廓清区别,溯本清源。 (一)“自行车”、“自转车”、“单车”等 Bicycle的众多中文译名多不采用直译方法,而取其形意命名之,其中“自行车”、“自转车”、“单车”等可归为一类,其文字涵义为“车主本人单独骑行的车子”。这是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自行车技术普及初期,以当时通行之米肖式自行车为典型式样,车辆并没有稳定的全车结构(三轮自行车不在其列),只能匹配车主一人骑驶。中国人所见之首批引入中国的自行车即为此类式样,故而得此称谓。(12) 以“自行车”之名指代Bicycle,于大众传媒中首次出现是在1868年11月24日出版的《上海新报》中,该报文章开篇便讲道:“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13)这也是自行车传入中国最早的史料证据。1870年,“自行车上海已多,或双轮或三轮,不用骡马,人坐踏足于版(板),其版(板)动而其轮转,即其车自行”。(14)随着最早之中文报刊将“自行车”作为Bicycle的中文译名频繁使用,“自行车”一词旋即在中文世界中普及开来,成为Bicycle译名中使用率最为广泛的词汇之一。 与“自行车”取意相近的还有“自转车”和“单车”。 “自转车”在中文典籍中原指是灌溉农田之水车,清中叶之儒学大师戴震曾著《自转车记》(15)一文详细介绍了自己所发明的这一灌水机械。而日后“自转车”转而指代Bicycle,是受到了日语的“自転車”的影响。(16)“自行车,又名自由车,辞源上叫做自转车。”(17)徐志摩至少在两篇游记中提及自己在英国生活中少不了“自转车”:“徒步是一个愉快,但骑自转车是一个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遍的技术;妇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在康桥听说自转车是不怕人偷的,就为人人都自己有车,没人要偷)”;(18)“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19) “自转车”今日已经很少有人使用,而“单车”却一直延续至今。在香港、澳门、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台湾等地区,Bicycle还保有“单车”的称谓,但并非所有地区都能通行。 (二)“脚踏车”、“踏板车”、“踏车”、“足蹈车”、“钢丝车”等 此类中文译名以Bicycle中最核心之技术、最突出之特征而作为命名依据,其中以其脚力踏板驱动为描绘重点的称谓最多,如“脚踏车”、“踏板车”、“踏车”、“足蹈车”(20),亦有其他译名,如“钢丝车”等: 自行车……习俗叫做脚踏车,还有人颠倒过来叫踏脚车,北方有叫钢丝车。其中最不合理的要算叫钢丝车,其不合理和叫人力车为“胶皮”一样……最相称的还是脚踏车,但踏脚车又似费解了。(21) 除“自行车”外,Bicycle于近代中国最为常见的中文译名要数“脚踏车”了。在近代中国文献资料之中,“脚踏车”的称谓比“自行车”更为普遍,成为Bicycle中文译名中最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种,如《清稗类钞》中就将Bicycle译为“脚踏车”:“脚踏车,即自转车也。两轮前后直立,前轮有柄夹持,可左右以正方向,后轮之侧附以钢链,与曲拐相联。乘者以脚踏曲拐,使链牵转后轮,前轮亦随之而转,以向前进行。虑妨行人,则振铃以告。男子所用与妇女所用者,异其式。又有用汽力者,年少子弟辄喜乘之,以其转折灵捷而自由也。”(22)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三)“洋车”、“自由车”等 西方舶来之交通工具,如汽车、摩托车等,皆曾被称呼为“洋车”,自行车亦不例外。“洋”字除了表明其外来属性之外,最迟至清道光、咸丰年间,“洋”字还成为了人们眼中贵重物品的代名词。(23)整个19世纪,中国市面上的Bicycle亦因其价格昂贵与危险性,并未成为普通人的代步工具,而是富贵之人的玩物,亦不负其“洋车”的美名。 除“洋车”之外,Bicycle在近代中国还有一个凸显其西化之物的名字——“自由车”。 为何叫做“自由车”?一种解释是取其能自由穿行于人群之意(24),而这种解释显然太过于简单。Bicycle之所以称为“自由”车,本身具有一种强烈的西化意味,即能否骑行自由之车是西化生活与否的一种表征和一种姿态。(25) 近代中国,“自由车”的称谓在体育界中最常被使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有“万国自由车”系列比赛、“海格路卫乐园自由车竞赛会”等自行车竞技。何浩华代表中国参加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和1948年英国伦敦奥运会的自行车比赛时,《申报》等中文报纸都是以“自由车比赛”称之,未见其他中文译名混用,可见“自由车”才是民国时期体育界对自行车的通行称谓。 (四)“洋马”、“洋驴”、“铁驴”、“铁马”、“铁骡”等 在传统中国社会,民众主要是借助畜力以达到交通、运输的目的。马、驴、骡子等家畜出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亦成为中国民众最为熟知的动物Bicycle传入中国之后,因其交通、运输等社会属性与马、驴、骡子等家畜相近似,自然而然,中国民众常常将Bicycle这一近代器械类比为马、驴、骡子等家畜,称之为“洋马”、“洋驴”、“铁驴”、“铁马”、“铁骡”等等。 “洋马”等此类Bicycle中文译名在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都有人如此称呼,但似乎在中国北方的乡村社会更为普遍。(26) 1927年6月间,河南省镇平人、在汉口经商的“荣记商行”经理李斌甫“返里省亲,将车(自行车,笔者按)由汉口装船至新野县‘荣记’,稍事休息后,旋即骑车子经歪子、汲滩、黑龙集、张林等地回归故里”。“当时正处三夏大忙季节,在大田里和麦场里正干活的农民,不约而同地丢下干活家具疾走或飞奔路旁观看祖祖辈辈从来未见过的稀奇物。当他入村后,老相识有的抚摸骑车,有的争相问询:‘这叫个啥?’‘一天能跑多少路?’‘从哪里买的?’等等。”“这个洋玩意儿进村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但本村男女老幼来看,邻村群众也络绎不绝前来参观,后来竟聚百人之众。”群众纷纷“夸奖洋车比马好。后来编成顺口溜:‘这洋马,真是好,不吃草,不喂料,不屙屎,不撒尿。’”(27) (五)“风火轮”、“孔明车”等 自行车乃舶来品,对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认知事物。至于如何称谓Bicycle,最可理解的方法就是从自身已有的认知经验中,如《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传统文化典籍中,寻找类似的器物名称为之命名。“风火轮”、“孔明车”等一类译名,即是如此。 “把自行车叫为‘风火轮’,这是从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哪吒脚踏风火轮演绎过来的,形容这种车骑得飞快。”(28)据新华社记者、作家李锦的回忆,在民国时代的江苏省盐阜地区,大家都不习惯称自行车,而叫脚踏车,或叫二人车,老人称为洋车子,父亲说最早叫“脚踏风火轮”: 上个世纪(20世纪,笔者按)30年代末期,黄沙河北的大地主丁七从南通买了一辆“脚踏风火轮”,轰动了兴桥。父亲刚到兴桥不久,都在渡船口等着。一会儿,家丁骑着高头大马,挥着鞭子开路,边喊边跑,说“脚踏风火轮”来了。这时,只见丁七骑着脚踏车来了,两个大轮子转得飞快,比哪吒闹海的轮子还大,不过,没有火,也没有风。当时人们睁大眼睛看着风火轮远去,都说丁七神了。(29) 无独有偶,在邓云乡所著的《增补燕京乡土记》中亦有将Bicycle唤作是“风火轮”的记载:“脚踏车是外国传来的,各地却也有不同的名字。……而且它不但有名字,还有别号呢?五十多年前,常和老词人夏枝巢先生见面,老先生每爱笑着说:‘我比不了你们,你们脚底下有两只风火轮。’风火轮是《封神榜》哪吒的代步,来去自如,极为方便,是古人的想象,与今天的自行车却颇相像,枝巢老人说的多么有趣,又多么生动呢?一时在我们那一圈人当中,‘风火轮’便成为自行车的雅号了。”(30) 与将Bicycle唤作“风火轮”相类似称号还有“孔明车”。“孔明车”的称呼存在地域性,多流行在中国福建、台湾等地。(31) 三 余论 近代中国的西物东渐并非一次简单意义上的科技、工业产品的普及过程,新器物须有新词汇作称谓,西物东渐反映在语言层面,则是在中文世界中产生海量新词汇与之相匹配。如果仅就词论词,尽管也有学术价值,却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称赞沈兼士所作的《“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时曾言道:“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32)以自行车这一舶来器物为例,从Bicycle在中文世界的符号移转可以看出,翻译活动永远都不仅仅是一个语言之间的转换,一个新的中文词汇的诞生是个复杂的过程,无时无刻不体现出文化上的冲撞和影响。 首先,新物命名是一个由多元到同一的历史进程。 汉字属于意音文字而非表音文字,直接简单的音译词汇在中文世界多不成功,Bicycle亦不例外。Bicycle传入中国初期,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社群的中国人对其功能用途的认知迥然有异,故Bicycle中文译名的多元发展亦彼时中国人的多元取向的直接反映。在这个意义上,北方农民眼中“铁马”与上海记者陈冷眼中的“自由车”既是同一个器物,又非同一器物。 “自行车”、“脚踏车”、“自由车”、“洋马”、“风火轮”等不下20余种的Bicycle的中文译名在百余年间的近代中国文化权力场域中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近代文献中,“自行车”与“脚踏车”之间的竞争始终不相上下、尤为激烈。最终,随着1949年新中国新中国成立,“自行车”成为中文世界中最为“普通”的说法,“脚踏车”、“单车”、“铁马”、“自转车”等虽未被淘汰,但已沦为地域性的称谓;而“自由车”、“足蹈车”、“钢丝车”、“风火轮”等译名已不见有人使用。 其次,词物指代关系的确立是一个由混乱至明晰的演变过程。 一物一词,这词物之间准确的指代关系,并非一日之功,往往需要一个由混乱至明晰的演变过程。“自行车”作为一个新生词汇在中文世界使用初期,常有使用混乱的情形发生。晚清的中文报纸中,“自行车”并非全部指代的是Bicycle。1890年,上海虹口有西人“以土累成岛型而筑车路于其上”,取名“飞龙岛”,试行“自行车”,“其车能自行往来,藉汽力、人力”以行。(33)“飞龙岛自行车”开行之后,“游人之往者,每日络绎如织,无不叹为得未曾有”。(34)此处《申报》所刊登之“飞龙岛自行车”显然非今日所共认之“自行车”,而更似游览车、过山车等一类游玩器械;类似情形,屡见不鲜。1898年,《益闻录》载文日:“西国近创自行车一种,法以火油燃火,推动车轮,平地风驰电卷,每下钟行三四十里,需油不过二斤。装人货外,载油十余斤,可行二百里之遥,洵巧制也。”(35)此处所言“自行车”则与今日之摩托车更为相近。可见,“自行车”作为Bicycle的中文译名,名实相符亦需要长时段的筛选与考验,才能取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与认可。 再次,旧词新指:取材古辞,释以新意,是文化自觉的普遍现象。 Bicycle众多中文译名中,如“自转车”一词源自清代戴震的《自转车记》、“风火轮”来自《封神演义》、“孔明车”称谓的流行是缘自中国民间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三国时期诸葛孔明的崇拜,前文已有涉及,不复赘述。时至今日,普及程度高、最为通行的Bicycle中文译名——“自行车”也非清代张德彝的原创。据笔者搜罗典籍,“自行车”一词最早出现于明朝末年王徵(1571-1644年)所著的《新制诸器图说》一书当中。在《新制诸器图说》书中,王徵不仅详细论述了自己发明的“自行车”结构原理,(36)还附有一幅自绘的“自行车”图。由此可见,旧词新指的生命力之强大。 最后,中文译名中“洋”字消失,是其西物东渐成功的重要标志。 有明一代,中国人即对外来国家进口至中国的货物泛称为“洋货”。“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回忆录以及晚明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之后,洋货便开始在中国出现,而且其输入呈稳定成长,这显示出洋货在明代已开始风行与流通。”(37)明清鼎革,及至乾嘉时期,洋货一直维持着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力。(38)19世纪末期,随着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普遍发生,以及中国对外通商口岸的辟设,大批量、各式样的洋货涌入中国,日渐成为普通市民生活中广泛流行使用的日用品,为与国产土货相区别,中国民众开始习惯在本来物品名称之前再加一个“洋”字,以突显其外来物品的属性,如洋布、洋袜、洋灯、洋烛、洋针、洋线、洋小刀,如此等等。 传入初期,Bicycle是摩登器械,非中国本土所产,在国人心中代表着西方文明,代表着先进和富有,故常以“洋车”唤之。然而,伴随自行车在中国各地的日渐普及,其使用群体之社会阶层逐渐下移和扩展,自行车的表征意义和实际作用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自行车渐渐剥离其摩登、西化的外衣,变作人们日常生活交通出行的代步工具。“洋车”渐渐少人称呼,“自行车”、“脚踏车”一类中文译名取而代之。 ①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9,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页。 ②现代汉语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文字则使用简化汉字,即“简体字”。 ③Susan Bassnett,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3rd ed.,2002,p.1. ④"The Bicycle's Long Way to China:The Appropriation of Cycling as a Foreign Cultural Technique,1860-1940,"Andrew Ritchie and Rob van der Plas,Eds.,Cycle History 13.Proceedings,13th International Cycling History Conference.San Francisco:Van der Plas Publications 2003,pp.94-102. ⑤概念史,有人称之为“观念史”、有人称之为“历史语义学”,也有人称之为“关键词研究”。西方学界的概念史研究最少存在三种研究模式:德国史学界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亦即“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 Semantik)、英美史学界尤其是剑桥学派倡导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法国史学界的“话语分析”(analyse du discours)或“概念社会史”(socio-histoire-des concepts)。(参见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页。)中国学界的概念史研究起步较晚,且不论研究成果是否“简陋”,其研究对象集中于所谓的“重要”概念(或称之为“主要”概念、“基本”概念,如自由、民主、阶级等)却是事实。中国学界概念史研究过程中完全忽视物质更新于中国语境的冲击,显然是不够周全的。关于Bicycle译名的讨论自其传入之始即已开启,然而文章多为科普知识一类,并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⑥斌椿:《乘槎笔记》,钟叔河点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9页。 ⑦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43页。 ⑧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1册,第695-696页。 ⑨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51页。 ⑩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4-475页。 (11)参见拙文《自行车普及与近代上海社会》,《史林》2007年第1期;《上海民族自行车产业研究(1897-1949)》,《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A History of The Bicycle and the Chinese Cyclists,1868-1949," Cross-Currents: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B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No.3,June 2012. (12)“自行车”一词,常招致望文生义之人不得其解,妄加评论其“名不符实”。时至今日,仍有文章不解“自行车”等中文译名之真实含义,而将中文之“自行车”,理解为“自行运转之车”,说是与车辆凭借“人力脚蹬驱动”之本质有冲突,从而论说所谓“自行车”是“词不达意”的译名。可见误解之深。参见《“自行车”的含义和翻译》,《青岛晚报》2007年4月29日。 (13)《上海新报》1868年11月24日。 (14)《自行车气行车》,《中国教会新报》1870年第92期,第11页。 (15)戴震:《戴震集》,汤志钧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153页。 (16)在日人川口市太郎(田中久重的弟子)所著的《智慧鉴》中,记载了田中久重重新复制自行车,是日本制造自行车的最早文献,比较西方自行车的发展进程,可以说自行车约1868年时传入日本,日人称之为自转车。参见许正和、邱创勋:《跃上顶峰的台湾铁马:台湾自行车业发展史》,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高雄)2007年版,第27页。 (17)《自行车的名称》,《万象》1942年第2期。 (18)《我所知道的康桥》,原刊《晨报副刊》1926年1月16—25日,收入《巴黎的鳞爪》,转引自来凤仪编《徐志摩人生小品》,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4—46页。 (19)《吸烟与文化》,原刊《晨报副刊》1926年10月1日,收入《巴黎的鳞爪》,转引自来凤仪编《徐志摩人生小品》,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217页。 (20)相较而言,此类中文译名中以“足蹈车”最为少见,据笔者所知仅出现在李大钊191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的文章中。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24页。 (21)《自行车的名称》,《万象》1942年第2期。 (22)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14页。 (23)“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陈作霖:《炳烛里谈》,转引自李长莉:《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 (24)“自由车因为是把脚踏的力量来做发动之原动力,所以最普通的名称,叫做脚踏车。他的构造轻便,运转灵活,动作敏捷,对于驾驶之人,可以运用自有,虽然在车辐纵横的热闹市场里,也能行走自由,所以叫他做自由车。”《自由车杂谈》,《青年界》1937年第11卷,第1期。 (25)以陈冷、包天笑与自由车的关系为例:陈冷早年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1904年春被聘为《时报》主笔,首创“时评”文风,使《时报》一举成名。他身上常有“国际化的气息”,这包括剪掉辫子,身着西式衣服,戴着鸭舌帽,抽着烟斗,在他结婚时上了西餐,当然他还骑着自由车出门。对此,陈冷的好友,另一位著名报人包天笑在其《钏影楼回忆录》中亦有记载。1906年初,包天笑到上海《时报》编辑部初次见到陈冷时,陈冷给包天笑印象最深刻的有二:“一为脚踏车,二为烟斗”。包天笑后来常常笑陈冷“属于动静二物,动则脚踏车,静则烟斗”。包天笑回忆录另外解释道,此时中国的文学家称脚踏车又为“自由车”。见到自由车“又快、又便、又省钱、随心所欲,往来如飞”,包天笑亦颇思学习,讨教陈冷,并租了一辆自由车,选一新开的马路,于每天下午行人较少时去练车。当包天笑练习自由车的第三天,刚刚能够不要人扶持,即一跤跌在路旁一小沟,满身泥污,眼镜几乎跌碎,从此就不愿再学。但陈冷还是不断鼓励包天笑说:“要学习,跌几交,算什么事。”这段在其十七八岁练习自由车的经历,在已74岁高龄时包天笑撰写的回忆录中仍记忆犹新,可见对自由车印象之深刻。20世纪初年,练习自由车成为西化生活之中国文人的一项时髦活动。参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文海出版社(台北)1974年影印本,第409页。 (26)李行健主编《河北方言词汇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07页;吴建生、李淑珍:《三晋俗语研究》,书海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页;朝阳县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朝阳县交通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27)李春有、李光有、丁永章口述,师淼波整理《骑入镇平的第一辆自行车》,林立功主编《百年镇平(1900-2000)》,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306页。 (28)秦若轼:《济南旧习俗》,黄河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29)李锦:《盐阜家谱》上,黄河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30)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下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75-577页。 (31)“话说当日本窃据台湾后(指1895年之后,笔者按),脚踏车也随之出现。台胞看到有人居然能够骑在两个大轮于上飞驰过街,起初惊疑是《封神榜》中的哪吒三太子,踏着风火轮下降人间了。后来听日本人称为‘自转车’,省入学说十分拗口,‘自转’二字也太文雅,不是一般下识字的人容易接受的。于是有人便认为如此巧妙的车子,何异当年孔明制造的‘木牛、流马’,便称之为‘孔明车’。结果因为人人一听便能记能说,遂为脚踏车取定了一个很特殊的名称。”亦玄编著《新编台语溯源续篇》,明报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第283-285页。 (32)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页。 (33)《别开境界》,《申报》1890年7月9日。 (34)《螳臂当车》,《申报》1890年7月23日。 (35)《自行车》,《益闻录》1898年第1751期,第75页。 (36)“车之行地者,轮凡四,前两轮各有轴,轴无齿。后两轮高于前轮一倍,共一轴,轮死轴上,轴中有齿六,皆坚铁为之,即于轴齿之上悬安催轮凡四,名之甲乙丙丁。丁齿二十四,丙三十六,乙四十八,甲六十。甲轴无齿。乙丙丁各轴有齿,齿皆六。甲轮以次相催,而丁催轴齿则车行矣。甲轮之所以能动者,惟有一机承重。愈重愈行之速,无重则反不能动也。重之力尽,则复有一机斡之而上。倘遇不平难进之地,另有半轮催杆催之,若所称流马也者。其机难以尽笔。总之,无木牛之名而有木牛之实用;或以乘人,或以运重。人与重正其催行之机云耳。曾制小样,能自行三丈。若作大者,可行三里。如依其法,重力垂尽,复斡而上,则其行当无量也。此车必口授轮人始可作,故亦不能详为之说,而特记其大略若此云。”参见王徵:《新制诸器图说》(武位中刻本来鹿堂藏本)。 (37)郑扬文:《清代洋货的流通与城市洋拼嵌的出现》,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2010年版,第37-52页。 (38)赖慧敏:《乾嘉时代北京的洋货与旗人日常生活》,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