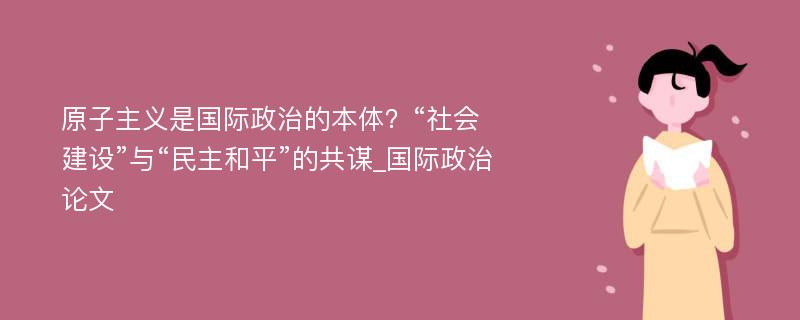
原子论是国际政治学的本体?——“社会建构”与“民主和平”的共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本体论文,民主论文,和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00(2008)06-0029-10
一、引言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译本)一书中,温特开宗明义地写道:“在这本书中,我发展了一个关于国际体系是社会建构的理论。”① 然而,如果国际体系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温特不可回避地需要回答:国际体系是由该社会中的什么行动者来建构?温特说,“由于国家是当代世界政治中具有优势的主体……它们应该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核心,批评一个国际政治的理论是‘国家中心的’,就像批评一个森林的理论是‘树木中心的’,一样没有什么意义。”② 换言之,温特虽然以国际体系的社会性重建国际政治的本体论,但他依然坚守国家中心论。
不过,温特并没有提供坚守国家中心论的充分理由。将树木模拟为国家,而把森林模拟为国际体系,即便这种模拟准确无比,也只能说明树木与森林之间的关系具有某种广泛的社会认知基础,但仍不能说明什么时代或什么人会把森林视为保护对象、汲取对象、生活空间、陌生与危险之所在等。这既无法阐明对树木、森林以及其概念之间关系的种种认知,又无法解释因此而产生的不同情感反应,从而也就不能判断个人会希望借由森林来主张回归自然、人定胜天或是永续经营。结果,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共享国家中心之本体论,让温特不可避免地饱受其他建构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火力集中的批判。③ 为此,温特最近提出了尝试性响应。在名为《自我批判》的文章中,他大方地承认,国家不是本体上的存在,但同时也借用了量子力学的观点辩称,“国家中心论”依然是一种研究国际政治的有效认识论。④
然而,笔者认为,这种作为认识论的“国家中心论”,其实是一种与“民主和平”共谋的“社会建构”,以便在社会效果上达成温特所断言的国际政治终点:即依循目的论发展而成“世界国家”。本文首先将简述在国际政治学中对“国家中心论”的批判以及温特对此的回应。其次,笔者还认为,温特理论的出现有其历史的脉络和有赖于社会建构主义加以统合的国际关系历史背景,对于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适用。最后,通过检验国家安全论述,本文要说明的是,即使是认识论的国际政治学仍富含情感成分,不可能不与思想认知互动而径自抽象存在。
二、社会建构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回应
国际政治学界的国家安全论述,每以国家为前提。晚近国际政治学围绕着“国家是什么”的议题而掀起过一阵热烈辩论。后现代的批判者指出,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有着共谋关系,国际政治学家一方面引导国际政治,另一方面赋予既有的国际政治以某种正当性、合法性;而在实践上,国际政治的运作也引导了国际政治学的发展。批判者进一步将焦点集中于“国际”的提法,指陈主流国际关系如果认为所谓的“国际”即为国家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那么国家就成为不可质疑的基础。⑤ 后现代的质疑因而包括“国家是否存在?”、“是不是以主权疆界加以区隔之后,两个国家的互动便成为国际?”等诸多问题。⑥
依照后现代的叙事,国家之所以在历史上出现,并成为人类行为的单位及制度,这是各种时空因素交错杂汇下的结果。其中,人为意志有之,历史偶然性亦有之。从“国家”这一名词的出现到其后的发展,每个国家的历史脉络均不同,且文化殊异,因此加入国际政治的起点、背景与环境尽皆不同。
面对后现代的挑战,在英语世界的国际政治学界,最新一波的回应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以温特为首的社会建构主义。⑦ 社会建构主义一方面承认批判者所指出的国家之虚构性,另一方面却又回到主流国际政治学,认为国家的存在已属合情合理。温特指出,即便形成国家的历史过程不具本质性,但时至今日,国家业已形成,对于人类世界具有强大拘束力,可以引导甚至规范国际政治的发展,且被多数人接受。也就是说,国家就算在历史上是透过人类实践所建构虚拟出来的,但在今日的国际政治学中仍具备不可动摇的本质性,故国际政治学以国家为单位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开展出以核战、安全为焦点的议程,仍属合理。
为了加强论证以上观点,温特遂以自然科学赋予国家某种正当性。⑧ 他引用量子力学,一方面呼应了后现代对于国际政治生活本质破碎流动的观察,另一方面却又巩固了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正当性。以下我们将介绍温特的后现代转向,再检视温特如何为国家提供正当性基础。⑨
温特引用量子力学指出,亚原子(sub-atomic)现象皆具有不可化约的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 duality),“在某些实验条件下(物理现象)的最适切描述是波,其他条件下则是粒子”。⑩ 量子力学另一项重要发展是海森堡(Heisenberg)的测不准定理(Uncertainy Principle),说明科学家不可能“同时测知一个粒子的位置与动量”。(11) 于是,科学家不可能“测量量子现象而不对其干扰”,任何观察行动皆会改变观察对象的存在,因为测量的过程“无可避免地将改变对亚原子层次粒子的准确描述”。(12) 这对科学本体论意味着什么?温特指出,“测量问题”挑战了另一项古典世界观的假设,即主体/客体的区分,并挑战了真实客观性(true objectivity)的可能性(哪怕是原则上的)。在量子测量时,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共构了单一体系,而非如古典物理学所说的两个体系。主体/客体区分远非既定(given),而是从测量过程中孕生,切分(cut)了先前不可分割的整体状态。(13)
如此,可知观察者与观察对象是相互构成的,无所谓观察者在此、对象在彼,透过工具可把观察对象的客观存在状态反应至观察者认知之中的说法。相反的,观察者只要对对象进行观察,就会改变观察对象的存在状态。量子力学这一震撼性反思所带来的启示是:国际政治学家据以研究、建立、设想国家概念之类的认知活动,会改变国家存在的状态,亦即改变它们号称客观的身份、所要作用的对象与意欲分析的课题。因此,不存在一个可以被研究、被代表的客观国家。社会科学界的后现代主义者及女性主义者诸如福柯(M.Foucault)与巴特勒(J.Butler)的批评相符,而温特则自称为之补上了“量子基础”。(14)
然而另一方面,科学家又发现,这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因互动关系而使研究无法客观的现象,是在一定层次之下才如此的。温特指出:“重要的是,‘量子物理’的发现在宏观的层次上并不必然使古典‘物理’的世界观失效,因为量子状态一般在分子层次以上会‘去相关(decohere)’而成古典状态,这也是日常世界以古典姿态呈现于我们眼前的原因”。(15) 量子物理只在微观层次起作用,古典物理仍“宰制”了宏观层次,故古典物理法则便可以客观适用,观察对象状态稳定、结构井然、易于掌握、独立于观察者之外。(16) 这样的区分非仅在实验室里有效,且在“自然(Nature)”中处处皆是。(17) 如此一来,量子现实总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宏观层次的粒子状态,一个是微观层次的波状态,此二者“不可化约”、“相互排斥”,且“个别不完整”。(18) 于是,温特指向了一个“认识论上的威斯特伐利亚(epistemological Westphalia)”,其中实证主义者(粒子)与诠释主义者(波)相互承认,各安其位,共同组建一个整体的国际理论。(19) 这也呼应了“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合并“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与“诠释主义的本体论”的尝试。(20) 这对国际政治研究有何影响?国家又于温特理论中扮演何种角色?
量子物理的二象性使温特得以一方面大方承认国家身份的矛盾与流动,另一方面仍持续宣称以国家作为行为者的正当性。他指出,国家是“结构的、自我组织的系统”,而其“意向(intentions)”是真实存在,与个人的意向一般。(21) 然而,在国家内部“关于何种意向更为应然”的冲突仍会存在,就像人对自己想做什么有所挣扎一样。毕竟,“宏观(国家)层次”的种种行为会在“微观(个人)层次多元展现”。(22) 如此一来,温特在三言两语之间便巧妙地将“国家以上层次”连接至宰制宏观问题的古典法则,而将“国家以下层次”划归了微观测不准的量子世界。
温特如何处理无以量度的国家内部身份冲突?温特指出,必须检视国内政治。然而,他的社会理论非关“国家身份”,而关乎“国家体系”,“不能被化约为个别国家”。唯一的问题,便只有冲突是不足以“结构化(structured)”进而产生“唯一的集体意向(unitary collective intentions)”。据温特观察,现实世界中国家身份往往稳定,因为身份如果真的“混沌(chaotic)”,国家将“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合理行动,其他国家也无以与之互动”。不依照法则行动的国家不是没有,但被温特指为为数极少的“失败国家”,(23) 不影响国际政治的结构研究。因此,国际体系是一稳定结构,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国家间互动有其法则等国际政治学界耳熟能详的假设,便可一一援用。
综观温特论证至此,哲学上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分明晰可辨。对物理学家而言,就算在本体论层次,量子状态无法被确实掌握观察,但在认识论上,对日常世界的认识可以透过观察分子以上层次而达致,以古典法则便能充分掌握日常世界。对社会建构主义者而言,要本体地了解国际政治,虽须追究至流动纷杂的量子状态,但掌握了分子以上的国家层次便能理解国际体系。无法掌握的国家本体(波)与可以观察的“国际”认识论(粒子),并行不悖。
温特分两个层次来处理国际政治问题,虽然这毋庸置疑,然这两个层次是否为本体论与认识论,却有疑义,此处稍加说明。温特强调物的本体便是二象,貌似在本体论层次便欲包容实证主义与诠释主义。这看似有别于他先前的立场: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温特将其知识体系区分为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与诠释主义的本体论,以社会建构主义作为媒介(via-media),相容本相冲突的二者。然而,细察温特在文中如何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时,其实可知他是在本体论上谈波,在认识论上谈粒子,仍然无法同时观察波与粒子:国家身份的本质是量子,但关于国家间互动的知识,却来自古典法则。国家的本体论层次固然是量子状态,认识论上固然要求一个“认识论的多元主义”以深入理解国家问题,(24) 但只要涉及“国际政治”,所有关于本体论的争论便戛然而止,唯有古典的认识论可以适用。
如是,面对国际政治学,只要掌握国家以上层次的法则就足以让决策者在国家内外进行实践。此即“认识论的国际政治学”:不问宇宙中的构成本体是什么,因其既无法掌握,且试图掌握时,依照测不准定理,也将遭致改变,不如停留在国家以上层次即可。一旦问题停留在国家以上层次,掌握国家间互动法则时,举凡权力平衡、以均权主义原则保护自身利益、即权力累积、遏制其他国家崛起、保护国家疆界等现实主义法则,在此皆可循例引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降,强调国家间权力均衡的现实主义广受批判,因其有利于世界上一部分人,却不利于另外一部分人。批评者相继指出,在追求建立国家的过程当中,强权政治有利于大国、世界市场有利于资本家、国家安全建制巩固了父权、主权疆界支离破碎地切割前殖民地国家各族群。结果,小国、无产阶级、女性、前殖民地人民纷纷在以国家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体系之中牺牲。无论这些批判如何揭穿国家建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但社会建构主义者仍可以宣称,这些都是国际政治学的本体论问题,而非认识论的国际政治学所需要处理的问题。就以多数前殖民地国家为例,其人民目标往往正是致力于建立西化的现代国家,故依然跳不出现实主义的国家前提。国家既然已经运作,受国际体系制约,又何必浪费时间追问已经失去意义的国家来源?社会建构主义者于是把国家重新放进分子以上层次,认定为稳定现象,不论其背后隐藏多少波动混沌,都是本体论层次问题。作为社会科学家,国际政治学家处理的问题自是认识论层次。
面对批评者,社会建构主义以“认识论的国际政治学”回应之。然而,如此响应并非突发于历史真空,而有其时空脉络。以下将从社会建构主义的学科背景及其所巩固强化的国家概念两个层面进行剖析,探问社会建构主义作为国际政治学的分析角度,是否真能停留在古典法则上?
三、社会建构主义的历史脉络
首先,就社会建构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那时社会建构主义的呈现仅是一两篇文章而已,尚未流行;90年代中期之后才蔚然成风,广受学界注目。其中转折,多少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对于解释国际政治现状的相继失败,急需理论加以整合发扬所致。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政治学的主要辩论存在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之间互动受相对权力大小制约,而自由主义则强调国家为了长久摆脱战争的威胁,即使会一时违反当下权力/权利的考虑,仍有可能在国家间形成制度,久而久之成为规范。举例而言,加拿大与美国之间若发生争议,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加拿大既是较弱一方,应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遏止美国,但加拿大素来没有这么做,便使现实主义无法解释美加之间的关系。而人们无法想象美加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认定战争威胁为国际政治主要存在状态的现实主义,因而便遭到质疑。
自由主义者之间遂有民主和平论的滥殇,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发动战争,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必不是由民主国家来发动。(25) 几经修正之后,这番说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民主和平论的面貌推出,不再谈论战争由谁发动,而是强调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但在非民主国家间,或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间便有可能发生战争。言下之意,世上如果都是民主国家,则战争不会发生;如有战争发生,战争责任便必在不民主国家身上。民主和平论来自于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并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战争的发生或民主与否能不能找到一个社会共同认知的标准?能否判断是由谁发起的?(26) 以1984年英国发动的英阿福克兰群岛战役(英阿马岛战役)为例,英国宣称若非阿根廷民族主义威胁岛上利权,便不会有战争。如此,说不清战争起点为何,由谁发动。再如鸦片战争,英国当时是否属于民主国家?若是,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吗?或只是相对于中国清朝更民主?民主和平论所指,是相对民主的国家不会对相对不民主的国家发动战争?还是绝对的民主国家不会对绝对的不民主国家发动战争?(27) 各种各样可能的质疑不仅挑战民主和平论对战争行为的解释,更从中突显出其政治意义,乃在宣判非民主国家的战争责任。美国作为民主国家,其若与非民主国家争战时,责任必然是转移至非民主国家身上。(28)
冷战时,美国全力围堵苏联扩张,和平论拥护者忧心国力受影响从而导致对其他国家相对优势逐渐丧失。日本等经济体在经济上直追,欧洲趁势崛起,似乎都是反映了这样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时,基辛格提出对国际政治的新解读,认为世界有五大强权,五个强权之间形成一种分合的态势,如此美国就不必独自承担国际安全的责任,冷战成本由各国分摊,实际管理责任美国仍继续肩挑。(29) 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力似渐衰退,自由主义者提出挑战,指出现实主义说法有误:观诸时势,美国已衰,日本与欧洲应起而争取霸权,挑战美国,重建国际政治中心,但实际上却无。现实主义者回答,霸权即便陨落,优势消失,其他国家为了维系国际格局,让霸权建立起的秩序继续运作,各国仍会努力维持(美国的)霸权。遂有书名谓《霸权之后》,(30) 该书认为,虽然霸权已不再是美国,却仍是由美国所创造出来的秩序,世界各国为了持续对世界秩序的破坏者进行规训,便编织出霸权,透过标举一个霸权国家,来维系一个霸权秩序。举凡西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东亚各“小龙”,都愿意分摊,撑起霸权国家及其代表的秩序。自由主义者认为,各国在既有霸权之下维系并安于国际秩序,着眼长远,而非短视于眼前。
自由主义者的国际秩序当真得以维系?20世纪9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内战发生了近似种族洗清的骇人行径登上国际舞台,引起各国注意。欧美国家却不介入,导致塞尔维亚穆斯林的危险处境,足以令人怀疑其是否赓续了对伊斯兰的历史性的鄙视。(31) 此类事件反映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态势:世界秩序并没有如自由主义学者所言,因为苏联东欧垮台进入自由主义世界,历史终点杳如云烟,民族主义继续专擅,国家与国家之间依旧战争不断,世界市场也未曾主导人类。社会建构主义便在此国际关系历史脉络下发生,自然具有其历史意义。
社会建构主义提出一个历史进程,(32) 最早在没有霸权秩序之时,国际社会处于权力均衡的丛林无政府状态,是“霍布斯式文化(Hobbesian)”,一如现实主义所言。(33) 发展至次一阶段,国家之间可以建立起自由秩序,以理性态度面对战争,进入了“洛克式(Lockean)文化”,一如自由主义者所言。(34) 不论是现实主义的无政府(anarchy)文化还是自由主义的无政府文化,都被整合在五段式的历史阶段论当中,国际社会终将演化成单一的“合法暴力垄断者”,“世界国家(world state)”这个论述意欲整合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35) 其出现点足以在根本上为民主和平论提供哲学基础。“进步史观(progressivism)”指出,历史终点站终将到来。(36) 温特主张,行为者在现实主义文化之中必须为获得承认(recognition)奋战,故视彼此为“敌人(enemies)”,也因此现实主义文化长期而言并不稳定,终将前进至自由主义秩序。(37) 在自由主义秩序之中,国家相互认可彼此,再非敌人,而是“对手(rivals)”;人与国家不再需要为了“征服”而战,即有战争也是“为了领土或其他利得”。(38) 在此秩序中,人们的“集体身份(group identity)”——即国家——已获承认,为国家牺牲已不像在现实主义秩序中是为己而战,所以人们自然要远离战争,因为理性个人“不喜欢在战争中死亡”。(39) 国际政治学家于是可以期待个人会对国家施压,国家也会意识到“武力使用作为外交手段”的问题,尤其是其中的“战争成本”。最终,此文化中的国家将“整体地扬弃战争,改寻非暴力手段解决外交政策问题”,“至少在同样不愿开战的国家之间是如此”。(40) 如此一来,温特便接合了民主和平论,暗示了某些特定国家间不会有战争的理论基础。他甚至在文中承认了他的理论与“民主和平逻辑”的相似性。(41)
对温特而言,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是个迟早的历史过程。在社会建构主义这样的视野下,现实主义对,自由主义也对,只是有些国家似乎提早进入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有些还停留在现实主义;仍在现实主义秩序的国家,继续遭到战火摧残,需要增加军备来保护,因此战争在已进入与尚未进入自由主义秩序的国家之间发生,也属合情合理。(42) 社会建构主义进一步发现,已经进入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国家,其国家内部本来也是自由主义市场秩序,所以自然而然地接受并进入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何时何地会发生这自由主义秩序无人能推断,但可以确定的是,既然国家是理性的,只要有朝一日进入自由主义秩序,便不肯回到现实主义世界秩序之中。如此,社会建构主义便为民主和平论建立了论述基础。
面对现实主义无法解决霸权为何维系,自由主义却又无法说明霸权秩序出现之后为何仍有各式各样后遗症的窘境,社会建构主义辩称两者都对,只是国际政治学家必须看见其中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最终世界国家的无可避免。如此在国际政治特定的时空情境之中,社会建构主义乃应运而生,补充说明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不能解决的现象,指出了进程,同时提供了历史进化的法则,让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能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框架之内被认可。
四、社会建构主义中的国家与情感
如前所述,在社会建构主义把国家重新带回国际政治学之前,许多批判学者已指出国家论述只是以国家身份为名义来分配资源的阴谋。社会建构主义为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赋予历史阶段位置之后,间接为国家在国际政治学上的位置重新找到基础。国家本身不必再另寻位置或回应批判,因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已经以之为基础互动,也从中找到互动准则。温特甚至赋予国家一种能动性,认为国家不仅如国际关系学者所公认的“像(as if)人一样”,甚至认为国家根本(really)就是人。(43) 如此,国家有自己的理性、身份、利益、信仰,就连何时从现实主义秩序迈入自由主义秩序,也可由国家决定。(44) 至于国家如何做出决定,对社会建构主义而言,这是本体论问题,国际政治学者作为社会科学者无以说明,决定权在国家手上,遂赋予国家一种国际政治学层次的能动性。而社会科学家的无法介入,也就表明国家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稳定的存在,不会因人而转移,于是成为一种客观存在。(45)
国家能不能就此被建构主义当成客观存在?回答此问题,首先要问的是有没有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能与主观认知相分离?反之,有没有一种主观认知,客观上不存在?如果我们要区分国家是主观认知还是客观存在,就必须说明此二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否则事物尽是主客皆具,不必区分此中差异。这样的主客二分引来了我们对社会建构主义的质疑:如何发现国家是客观存在?社会科学家是不是用主观认知来决定所研究的行动者是国家?国家是现实主义的国家、自由主义的国家,抑或是客观存在于两者之外?
温特从认识论出发,把国家当成已经存在来进行研究。这意味着国家存在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人们认知之外,不受认知影响,而是影响着人类认知行动。“人都必须具有一个国家身份”的想法,即便饱受批判,人类行为终究受其牵引制约。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革命家,还是需要面对税赋与警察,思考如何把握国家的位置,才能进行反对。如此一来,国家自然是客观存在的。
细思之,国家的存在如何被行为者认知?在认识论上已经存在的国家为何不能够被推翻?行为者认识国家的方式是透过语言与各种象征,而非来自上帝的本然指引。从太空望地球,并无国家疆界可见,必须看见岗位哨亭,碰上身份检查,人们才得以认知到国家。也就是说,国家是社会的,被人们在成长过程中透过社会学习所认识。如非在现代国家里成长,即便看见岗哨也不了解国家的存在。(46) 透过不断教导与制约,国家乃成认知上无法摆脱的行为思考前提,超越个人,取得客观性与社会性,为人们所共同认知。
然而,对于同一国家的认知显然因人而异,同一人对于不同国家的认识常相去千里,这是因为每一个特定国家标签对每个人所激起的情感尽皆不同。认知心理学家发现,凡认知背后皆有情感附着,情感往往先于认知而存在;接受一项刺激时,情感涌现往往是一刹那,关于其社会意义的认知却要思索以后才能从记忆中召唤而出。(47) 对国家的认知不同,其背后的情感意义也就不同。由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空白的,皆需要被认识,因而必须依赖语言与象征物,情感遂在社会学习过程中自然附着于人们对特定国家的看法之上。
如果国家是社会共同认知的集合,而此认知又满是情感附着其上,则一个客观的国家便不可能存在。温特先用社会理论试图接合本体论与认识论,再用量子物理进一步延续其论点,却始终坚持国家虽有量子/后现代的一面,国际政治学家总能运用法则结构性地观察掌握国际政治。若国家在本质上便无以脱离认知与情感而存在,温特便不能只在本体论或微观层次自我批判,就连其对国家体系互动所具结构性的坚持,也必须全面省思。
既是如此,国际政治学家为何必须稳定国家状态,提供结构法则,说明互动关系?此处,我们提出情感对温特国家理论造成冲击的第二个层面。情感驱使着社会科学家进行研究,在国际政治各种主流学说之中可见斑痕。例如,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对于儒教及伊斯兰教国家的情感明显与对基督教国家不同,认为儒教与伊斯兰教国家将联合对付基督教国家,使文明冲突不可避免。(48) 文明冲突论流露着危机感,故而文明冲突论最终是要以国家的力量来处理代表伊斯兰与儒教的其他国家。这样的情感,是以鄙夷神色面对亚洲及伊斯兰,忧心美国精神之荡然无存。另外,美国的民主党支持者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表示对美国的解构(disuniting)充满恐惧。(49) 自由主义的学者也分享了与亨廷顿相仿的忧心,其中许多在中国尚未崛起之时,就急于预防“中国威胁”。鄙夷作为一种情感,严重影响国际政治学家的理论发展。
社会建构主义学者亦不能自外于己身情感。社会建构主义为民主和平论提供合理化基础已如前述,其中民主与否的标准,是由民主国家来界定;一旦它们所认定的不民主国家表现出要颠覆民主国家之间既存秩序时,民主国家便可以维护秩序为由行动,教训不民主国家。社会建构主义对“民主和平论”的合理化中隐藏的是一种气愤的情感。气愤与鄙夷不同:鄙夷是一种焦虑,带有攻击性,有如面对细菌一般,亟须主动寻找并消灭对象;气愤则是在认知中应有的状况没能出现时,方才以行动教训对象。两种不同的情感所带来的行动也不一样。(50) “民主和平论”理论命题所示虽貌似不涉情感,但所欲处理的对象,却免不了高度情感集中,用以说明教训之必要。循此脉络,遂可见国际政治中将不服美国霸权秩序的国家被称之为“流氓国家”,(51) 后来发现许多国家在霸权规训之下的市场秩序无以约束,便扩而及之,将所有未进入世界秩序者命名为“失败国家”。(52) 福山在《强国论》中,便主张要输入现代国家体制至“失败国家”,使之进入世界秩序。许多批判学者对此感到不可思议。不论是“流氓”或者“失败”,都由民主国家定义,目的是为了维持其彼此之间发展出的秩序,而民主国家之间的秩序又是由其各自国内秩序发展而来。(53)
温特的理论不仅为民主和平论及由其衍生的现实政治提供理论基础,甚且形塑了特定的认知与情感。不论是“流氓国家”,还是“失败国家”,都伴随温特使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合理化的努力,明白挟带进其议程,俨然“流氓国家”与“失败国家”不只是国际政治问题,且是国际政治理论问题。(54) 民主国家视此类国家为国际秩序威胁,且欲积极打击消灭的侵略性动机并非凭空而来。理论说明了何为威胁,何为污染,在民主国家国际政治学者逐步构筑理论话语之际,也塑造了附着其上的情感。过去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对于国际秩序威胁各有其解释,认为威胁来自于武器者便主张裁军,恐惧强权者便强调权力均衡或集体安全制度,具体做法不一而足。而“民主和平论”将威胁界定为不民主国家,视之为战争责任所在,并有输入民主制度之倡议,更是从中可见理论、情感与动机的相互建构。唯有回溯国际政治学家建构客观国家理论的过程,从中解读由理论脉络里孕育而出的强烈情感,方能充分理解。
倘若社会建构主义所言,国家可以在认识论上成为客观研究基础,我们进一步辩称,此基础既由社会建构而来,本体论上本不存在,则国家不可能纯粹客观。国家既需透过语言与象征物方能被熟识进而成为人类行动的基准,自难免于人们夹带于上的情感。(55) 由此可知,国家无法被具体看见,而有助于使国家现形的设计,都带有兴奋或威胁等情感。人们在观察时自需将动员情感,观察不同国家时便带有不同倾向。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宣称已成共识、客观存在的国家并不存在,只存在一种情感丰富、具有倾向性的社会概念。我们怎么看待国家就影响国家怎样存在,国家无法与我们的情感分离,也不可能被模拟成稳定实在的物理状态。整套社会建构主义论述,虽宣称以国家的客观存在为基础,实则让我们在看待国家时盈满情绪,也反映了国际政治学家对既有国际秩序的情感。情感既内在于国际政治研究对象,也全面渗透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从而便凿穿社会科学中任何对于客观、实在、稳定、结构的宣称,使我们看清温特的量子转向终究只是为既有理论重铺坦途的媒介。情感所召唤者,是国际政治学对社会建构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对国际政治学更全面且深层的批判与省思。
五、本体论的国家安全
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安全是一个权力均衡的问题,小国家要结合起来抗衡大国或是自助地建立军备来抵御大国。在自由主义之下,国家安全问题是如何供输霸权,改造“失败国家”以维系秩序。而在综合两者的社会建构主义之下,国家安全是什么,应与国家性质有关,现实主义国家与自由主义国家会实行不同的策略。然而国家性质需要判断,误判便可能产生。以当今中国为例,虽已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努力进入世界秩序,逐渐成为霸权秩序下的国家,仍有论者指出不可轻信。(56) 中国究竟是自由主义国家还是现实主义国家?回答此问题,方能决定如何与之交往,则判断所面对的国家性质为何,便将无所不在地影响己身的国家安全决策,也就进一步影响了国家身份。譬如在“9·11”事件中,本拉登与基地组织被认为是谋划者,但美国却攻打阿富汗与伊拉克——“失败国家”——断定一旦解决上述两国,便解决了恐怖主义威胁。因此,面对“失败国家”,美国的国家安全便是改造其他国家。哪一个国家是“失败国家”?此是而彼非,标准何在?能界定其他国家是失败国家者,俨然并非“失败国家”,故美国也从中确定自己身份。对对方的判断也便等同于对自身是什么国家的判断,国家安全问题最终便决定了自身国家身份问题,于是改变了既有国家身份决定国家安全的单向关系,而使国家安全与身份之间因果关系模糊流动,无法确定。(57)
在社会建构主义之下,若遇国家性质难以确定时,行为者自己的身份问题也将无法确定,则处理国家安全问题时,斗争事实上并不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而存在于自身对一个国家的两种认识之间。如无法对所面对的国家性质产生一致界定,安全问题与己身身份问题无法解决,客观外在一致的国家也就不存在,社会建构主义于焉崩毁。此之所以对付“失败国家”竟是如此重要的国家安全议题,实非“失败国家”摧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是若无“失败国家”作为对象,自由主义国家便无法成其自由主义国家。唯有“失败国家”继续失败,自由主义才能不断自由,民主和平论才能维系,作为民主和平论中已进入自由主义秩序的国家角色才得以扮演下去。国家观念里之所以必须充满情感因素,实因“失败国家”不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是对国家存在意义的根本威胁,揭露了国家在本体论层次上无法存在的事实。如无民主与非民主国家间的现实主义对抗,国家外貌将掌握不住,没有具体对象的量子存在状态终将被全面揭露。
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其他同一时间的大型理论,尽管论证未必一致,仍是建构主义与民主和平论的共谋。像不民主就不和平的这种判断,正是“文明冲突论”能反映或掀起西方国家警觉的情感基础。“文明冲突论”把儒家与伊斯兰视为不可避免的敌人(58),“历史终结论”却散发无限乐观。(59)
“文明冲突论”相当于温特借用现实主义所描绘的霍布斯状态;而“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鼓吹的第三波民主,(60) 虽各有千秋,同属温特借用自由主义所描绘的洛克状态,这在福山用猿猴进化来赞许女人得以加入世界政治的类比下(61),更形同呼应温特。九一一事件后,福山眼见历史尚未终结,又发展前述的强国论,对伊斯兰的所谓“失败国家”提出改造建言,与他之前提倡以信任文化超越儒家关系文化的主张(62),同样是指导国家如何进化。福山与亨廷顿两位主张人为介入国家存在状态,于是揭露出,即使他们与建构主义的科学认识论看似格格不入,但仰赖本体论上的操弄并无轩轾。
六 结论
国家本就不是稳定存在,而更似量子状态。在认识论上宣称国家客观,最终目的是在粉饰国家不能作为客观存在的无能为力。国际政治学需要有国家安全论述,必须区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两种国家安全性质差异,并以社会建构主义包而纳之,是因为若非如此,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同便暴露出来,各据一方,形成两种国际关系,普遍化的国关理论也将荡然无存。所以当现实主义无法解释,自由主义便扶助;自由主义无法解释,再委由社会建构主义来带入历史进程,包容整合。这样的国际政治理论发展,透过解释国家性质差异的历史缘由,容许不同性质国家安全议题的存在,挽救了国家作为看待世界的观念基础,使国家免于成为流动状态、主观问题。于是,社会建构主义便重新让国家脱离学者及领导人的认知与感官,进入抽象,也就解决了国家竟有不同性质,并非普遍、纯粹、单一的尴尬。此即社会建构论的社会效果,或可视之为其动机:解决了民主和平论的困难,也在本体上配合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说明民主国家如何免责于战争;而其整体方向乃在解救国家于消弭,重构国家作为人类行为的基础以及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唯掌握此,我们才能回归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辩论之中继续对话,说明社会建构主义最终目的是对国家概念的维系;也才能鞭策社会建构主义视量子转向为全面自省,而非理论包装。国家概念是情感载体,量子状态终对不同人、不同国家,产生社会科学家测不准的不同效果、不同意义。
[收稿日期:2008-02-17]
[修回日期:2008-04-13]
注释: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ⅩⅢ页。
②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9页。
③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eds.,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London:Routledge,2005.
④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eds.,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London:Routledge,2005,pp.181-219.
⑤ 对于“国际”的多种途径批判,可参见《千年》杂志(Millennium)于2007年9月的专刊号“Theory of the‘International’Today,” Millennium,Vol.35,No.3,2007。
⑥ 代表作之一可参见R.B.J.Walk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其他稍早的挑战例子,可参见Cynthia Weber,Simulating Sovereignty:Intervention,the State and Symbolic Ex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J.Shapiro Michael and Hayward R.Alker,eds.,Challenging Boundaries:Global Flows,Territorial Identiti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David Campbell and J.Shapiro Michael eds.,Moral Spaces:Rethinking Ethics and World Politic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 Krishna Sankaran,“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ronic:A Postcolonial View on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ternatives,Vol.18,No.3,1993;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eds.,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Boulder:Lynne Rienner,1997。
⑦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2,1994; pp.384-396;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
⑧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eds.,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pp.181-219.
⑨ 此处必须提醒读者,事实上,温特以量子物理连接社会科学的尝试,非仅限于本文以上所述的“认识论国际政治学”。在“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一文中,温特试图以量子学说挑战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说,进而援用量子脑理论(quantum brain theory)及量子意识假说(quantum consciousness hypothesis),说明人是一种“量子模型(quantum model of man)”,社会集体作为一种“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也具有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与无意识(unconsicousness),从而为其国家拟人说(state as person)填上自然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内容参见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eds.,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pp.181-219,同时参见该书中笛卡尔对此问题的有关论述。
⑩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191.
(11)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191.
(12)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192.
(13)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192.
(14) 温特在不同脉络下指出量子物理与社会科学批判学者之间的相关性,有关福柯对此论述的部分请参见该书的第202页,巴特勒对此论述的部分请见该书的第198页。
(15)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191.
(16)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p.190-191.
(17)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193。
(18)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215.
(19)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216.
(20)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214.
(21)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205.
(22)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206.
(23)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206.
(24)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p.215-216.
(25) “民主和平论”可参考Michael Doyle,“Kant,Liberal Legacies,and Foreign Affairs,”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2,No.3/4,pp.205-235,pp.323-353; Bruce M.Russett,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26) 来自后结构主义更釜底抽薪的辩论则是:战争在多大程度上根本是一种虚拟?可参考Jean 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Ann Arbor,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James Der Derian,Virtuous War:Mapp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Media-Entertainment Network,Boulder:Westview Press,2001。
(27) 关于民主国家的定义及其背后的历史缘由,可参照Ido Oren,Our Enemies and US: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
(28) Mustapha Pasha and David L.Blaney,“Elusive Paradise: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Global Civil Society,”Alternatives,Vol.23,No.4,1998,pp.417-450;朱雪瑛:《“民主和平论”之分析与美国“推广民主”战略》,载《台湾民主季刊》,2005年第1/2期,第123~158页。
(29) 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chuster,1994.
(30) 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31) 此一视角承接了爱德华·赛立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批判。参见Edward Said,Orientalism,New York:Pantheon,1978。
(32) 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9,No.4,2003,pp.491-542.
(33) 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re is Inevitable?”pp.517-518.
(34) 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p.519-520.
(35) 甚至可见整合“英国学派”的企图,参见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pp.517-519。
(36) 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p.492,虽然温特宣称他的进步史观并非线性,却立刻明白表示就算从较高阶段退回到低阶,“退一步最终将为进两步所平衡”。
(37) 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p.517-519.
(38) 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519.
(39) 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519.
(40) 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519.
(41) 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520,温特看似谨慎地指出“我的故事在单位层次上(unit-level)是否仰赖民主并不清楚”,然又说明民主虽非必要条件,却是充分条件,由此可知,虽然和平不一定来自民主,但有民主必定和平,一旦开战,责任绝不在民主国家身上。
(42) 这也成了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论述基调。于是在当今台湾,民主和平论与社会建构主义就变得很重要。
(43) Alexander Wendt,“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No.2 2004,pp.289-316.
(44) Alexander Wendt,“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p.289.
(45) 温特发现不论学者如何辩论,万变不离其宗的则是,大家必定都会赋予国家某种人性的特质,Alexander Wendt,“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pp.289-316。
(46) 1971年,塔萨代(Tasaday)部落在菲律宾被发现,结束了八个世纪以来的与世隔绝。然而菲律宾政府终得将该族送回丛林深处。这揭露了国家的客观性并非天生自然,却是由驯化而来。
(47) 有关理论请参见George Marcus,W.Russell Neuman,Michael MacKuen,and Ann N.Crigler,eds.,The Affect Effect:Dynamics of Emotion in Political Thinking and Behavio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
(48) 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
(49) Arthur Schlesinge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New York:W.W.Norton Co.& Inc.,1998.
(50) Martha Cottam and Richard Cottam,Nationalism and Politics: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Nation States,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1.
(51) 关于批判学者如何解构作为概念的“流氓国家”,可参见Jacques Derrida,Rogues:Two Essays on Reason,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52) 关于学界如何批判作为概念的“失败国家”,可参考Noam Chomsky,Failed States: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London:Penguin,2007。
(53) Francis Fukuyama,State-Building: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54) 温特对“流氓国家”一词的使用请见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p.520;“失败国家”一词的使用请见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p.206。
(55)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国和越南的边界,为了方便通商往来而建了一条道路,但是在距离越南公路一米处截断,既未相连,就不必设下象征国家存在的岗哨,没有通关问题,更看不到客观的国界。
(56) 诸如白鲁洵(Lucian Pye)所谓的“中国是一个文明伪装成的国家”(参见Lucian Pye,“China:Erratic State,Frustrated Society,”Foreign Affairs,Vol.69,No.4,1990,pp.56-74),或如亨廷顿所说,儒教是威胁,需要被揭穿等此类言论。
(57) Chih-yu Shih,“Does Death Matter in IR? The Possibilities of Counter-Methodology,”Issues & Studies,Vol.42,No.3,2006,pp.227-256; 西方学界相关讨论可参照David Campb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
(58) 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
(59) Francis,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Aron,1992.
(60) Samule Hungtin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
(61) Francis Fukuyama,“Women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Politics,”Foreign Affairs,Vol.77,No.5,1998,pp.24-40.
(62) Francis Fukuyama,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New York:Free Press,1995.
标签:国际政治论文; 认识论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建构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学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原子论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