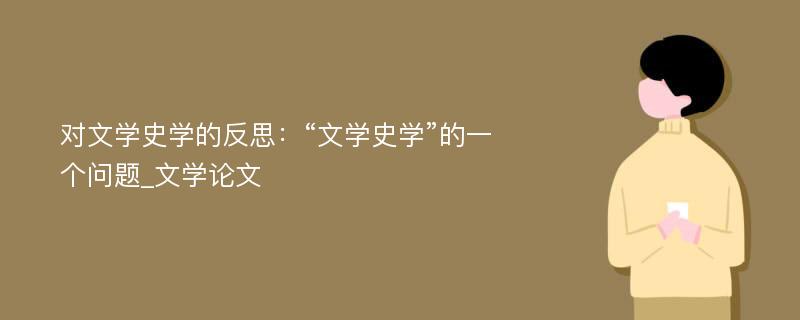
关于文学史学的思考——“文学史学”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文学论文,献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史学”这个名词总令人觉得有点别扭,倒不是由于它听起来拗口,而是由于对它的意义不甚了然。旁观其他历史学科,似乎没有这样一种“亚学科”。与文学史性质相近的学科为数很多:科技史、艺术史、哲学史、史学史等等,但似乎不曾听说有什么“科技史学”、“艺术史学”。哲学史与史学史这两门学科的繁盛程度并不亚于文学史,也未见有人在它们后面再缀上一个“学”字。那么,为什么唯独文学史要派出生一门“文学史学”来呢?是不是文学史具有独特的学科性质呢?
当我们说“文学史”这个词的时候,大概有以下两种意义:一是指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客观的历时性的存在。比如我们说“李白对唐以后的文学史的影响如何”,就是取这种意义。二是指人们关于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论述,是一种主观的叙述、阐释和评价。比如我们说“近百年的文学史著作如何”,就是取这种意义。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第4章中所论述的“文学史”是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的一种研究方式,当然应是指第二种意义而言。那么,所谓“文学史学”是针对哪一种意义的文学史呢?显然,这不可能是第一种,否则的话,如此产生的“文学史学”就是指以文学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也就成了第二种意义的“文学史”。即使这种研究工作偏重于理论的抽绎,也只须称之为“文学史理论”,它仍可被包括在“文学史”之中,根本无需画蛇添足地缀上一个“学”字。所以,“文学史学”就一定是关于第二种意义的“文学史”的,也就是说,它应是探讨如何研究、撰写文学史,或是对已有的文学史著作进行分析、总结的一门学科。然而,对于编写文学史的历史尚不足百年的中国来说,建立这门学科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吗?
从著作的数量来看,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已经蔚为大国了。据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的《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早已超过300种,其中仅属通史性质的即达50余种,真可谓洋洋大观。然而著作数量的积累并不意味着学科水平的提高,草创时期的那些文学史不用说了,因为那时连什么是文学尚不清楚,当然谈不上什么史识和史观。即使在人们对文学史的性质比较清楚以后,文学史著作在学术上的进步仍是步履维艰。而文学史著作往往具有教科书性质这一事实更使陈陈相因成为该学科的整体性缺点,我们试把80年代以来问世的几十部通史浏览一过,便可发现许多声明适用于师范院校、专科学校、电视大学等不同层次的文学史教材,其实都是游国恩史和文学所史的改编本而已。所以真正有资格成为“文学史学”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史,其实寥寥无几。由这么几部著作所提供的学术积累实在是很有限的,许多概念和命题还不够明确,学术规范也不够严格。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一门“文学史学”,是否太忽忙、草率了一点呢?
近十多年来,文学史界有一种普遍的自我反省意识,大家都渴望着在总体水平上有所突破,写出超越前人著作的新著来。由于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理想中的超越,于是便寄厚望于方法的更新,适逢海禁初开,西方现代文艺理论被大量介绍进来,供需双方一拍即合,方法热便应运而生。这种不局限于本土学术的开放心态和谋求理论指导的学术意向本是好事,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有两方面的失误:一是人们往往带着迫不及待的焦燥心情,对西方理论采取了饥不择食、急病乱投医的草率态度,有的甚至只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便自以为已经探骊得珠。二是人们对理论与方法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值,甚至认为只要方法一新便可顷刻点铁成金,势如破竹,而忽视了细致的本文研读和深入的专题研究。结果是不断有人宣称发现了很好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从而可以实现文学史研究的突破了。在一些著作的序言中往往有气壮如山的宣言,可是在正文中却难以找到能体现其宣言的实质性内容。例如有一部《中华文学五千年》在序言中宣称:“今天通行的文学史读本的体系,不仅是陈旧的,也是不科学的,没有光彩的。我写这部书的目的,就是要废除旧的体系,走一条新的文学史研究的路子,建立一个新体系。”这样的宣言无疑是鼓舞人心的,可是当我读了此书的前二卷后,却大失所望。试看其第一卷,共分四个部分,即“神话的时代”、“诗歌的时代”、“散文的时代”(上,诸子散文)、“散文的时代”(下,史传散文)。如此的“新体系”似乎仅仅是旧体系的改头换面,况且此书将《九歌》归入“诗歌的时代”,将《离骚》、《九章》归入“散文的时代”,编排很不合理,在具体论述中对楚辞学、诗经学的最新学术成果吸收很少。如此创新,实在没有多少学术意义。
那么,撇开上述情况不论,或者说假如我们克服了上述失误之后,能不能把提高文学史学科水平的希望寄托于借鉴西方理论呢?
我对此不抱很乐观的态度,原因有二:
首先,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走过的历程是不同的,从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等外在驱动因素到语言、文体等内在嬗变因素,两者都相去甚远。这样,基于一种文学现实的文学理论能否适用于另一种文学,一些重要的概念或术语能否互相转换,是很可怀疑的。例如中国诗学中的意境、格调,西方诗学中的张力(tension)、肌质(texture),用于各自的文本分析时颇为有效,却很难在对方的批评中付诸实用。至于那些对西方文学都缺乏普适性的新奇理论,我们更不能指望它们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起到神奇的促进作用。
其次,西方文学理论的多数体系主要是用于共时性的文学研究的,它们虽然可以运用于文学史研究的局部工作,像细致的文本分析等,但是对于历时性质的文学史自身却并无多大指导意义。高友工、梅祖麟的《唐诗的句法、用词和意象》、《唐诗中的语意、隐喻和典故》可能是运用西方理论分析唐诗的比较成功的论文,但是我觉得如果把两文中所举的作品都换成宋诗(这点并不困难),结论也不会有什么改变。那么,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唐宋诗之沿革异同这类中国文学史的重要问题,恐怕就难以奏效了。
如果我们很谨慎地借鉴西方理论中有关文学史的部分,又努力地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中总结规律,从而建立了比较理想的“文学史学”之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能否由此就出现飞跃呢?
我对此也不抱太乐观的态度。
“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在学术界已经响了好多年了,而且在人们明确提出这个口号之前,重写文学史早已悄悄地开始了。历史学科本来就具有当代性,任何分支的历史都应不断地重写。早在本世纪初期,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提倡“新史学”时就说过“历史时常需要重新编写”,“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常常有所增加,从前的错误常常有所发现,所以我们应该用比较完好的、比较正确的历史,来代替已经陈旧的历史”。话说得平淡无奇,却是不易之论。文学史所处理的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文学,又是一种“诗无达诂”、“见仁见智”的对象,就更加需要不断地进行新的阐释和评价。重新编写文学史,才能体现其当代性和主体性。正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样,一代也应有一代之文学史。在目前的关键时刻,似乎迫切需要“文学史学”为实际的编写工作提供理论指导,然而我认为,文学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提高其学术水准的关键在于实际的操作,理论的探讨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一则任何理论的进步都必须以专题研究的实际经验为基础,二则从理论的认识转化为实际的操作仍有很大难度,几乎可说是“知易行难”,所以“文学史学”的重要性仍是处于第二位的。
从50年代到70年代,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是最流行的、最有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主要是以这三部书为对象的。人们对三书多有不满,主要有两点:一是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背景对文学的影响,有时甚至把这种影响说成文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二是论述大多采取依次罗列作家和作品的章节结构,而忽视了对文学发展脉络也即史的线索的揭示。上述两点也常被简化为“庸俗社会论”和“作家作品论”两句话,对此大家的看法相当一致。几乎可以说,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的“文学史学”倒已经有点眉目了。因为既然已经看清了缺点,那么它们的对立面当然就是应予肯定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努力对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给予更正确的解释。同时应对文化、社会心理等其他文学背景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更应该对文学自身的内在逻辑流程给予最大的关注。我们还应该放弃罗列作家、作品的拼盘式结构,而把理清文学发展演变的线索作为主要的论述方式,等等。然而,正像俗话所云,空说容易动手难,要将这些明白清楚的观念付诸实践,却绝非易事。试以后一点为例。早在40年代,钱基博就已指出:“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到了80年代,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可是文学史的线索不像数学中的曲线那样,可以用图象或公式精确地表示出来。文学史的轨迹是一条乃至数条没有一定规律的,时断时续的曲线,要想用文字把它表达清楚,首先应把一些最重要的轨迹点确定位置,也就是要对重要的作家、作品有充分的论述,并把它们放在文学史上进行定位。然而仅仅有几个孤立的点尚不足以体现曲线的全貌,于是又必须兼顾构成文学整体风貌的次要作家、作品,并理清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即使仅仅在一种文体的范围内已很难兼顾无遗而又主次分明,更何论包含形形色色、互相影响、演变又不尽同步的诸文体的通史型文学史!
再举一例。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是撰写文学史时无法回避的问题。现有的大多数文学史都是按朝代来分期的,大家对此也早已啧有烦言了。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的不满是有充足理由的。文学有自身的发展阶段性,怎么会和封建帝王改朝换代一一重合呢?早在30年代,胡云翼在《中国文学史·自序》中就已说过:“有许多人很反对用政治史上的分期,来讲文学。他们所持最大的理由,就是说文学的变迁往往不依政治的变迁而变迁。”郑振铎等人也写过论文讨论此事。也就是说,就“文学史学”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明确的:我们当然应该依据文学自身的历史而不应依朝代来进行文学史分期。可是直到今天,又有哪种著作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上述几点都是很浅显的道理,在有些学者眼中也许还不具备理论的品格,他们心目中的“文学史学”要深奥、玄妙得多。然而,既然如此浅显的原则都难以付诸实践,那些深奥、玄妙的哲理性原则又怎样运用于实际操作呢?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史教学的教师,我非常希望看到突过前人的文学史新著。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我也非常希望从“文学史学”得到理论的指导。但是我更希望大家不要空谈“文学史学”,而应亲自撰写文学史,至少也应以某些文学史专题为具体对象,再抽绎出理论来,就像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写《普勒的〈大自然的雄伟〉》、伏狄卡写《现代捷克散文的开始》那样。否则的话,那些费尽心力建立的“文学史学”的理论体系也许会成为空中楼阁。
但愿我的忧虑仅仅是杞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