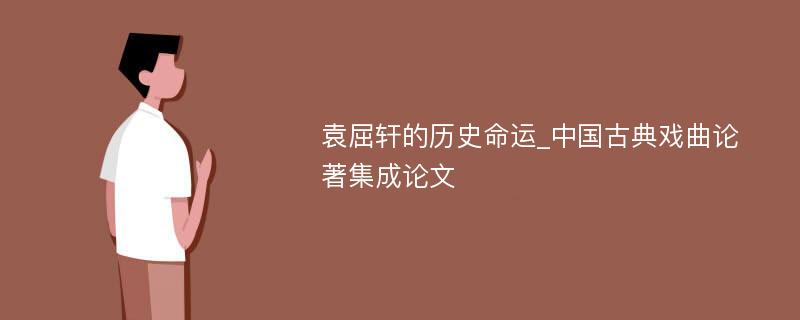
《元曲选》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曲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人臧懋循所编《元曲选》,是一部著名的元杂剧总集,对元杂剧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但晚近不止一位中国戏曲史研究家,对《元曲选》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其间既有前代传统看法的影响,也有当时治学特点的绾摄。
所谓“传统看法”,是指明、清时代的曲学家对《元曲选》的批评。比如郑振铎先生当年在涵芬楼购得的顾曲斋所刊《古杂剧》中发现关汉卿的《绯衣梦》,并决定刊入《世界文库》第一卷时,在他所撰《关汉卿〈绯衣梦〉的发见》一文中,就曾提到清人叶堂对臧氏的“猛攻”:“叶堂氏在他的纳书楹上便已猛攻着臧氏,说他是一个‘孟浪汉’,不知埋没多少好的元曲了”。(注:《西谛书话》19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但最早批评《元曲选》的并不是清人,而是臧氏的同时人,最为学人熟悉的是著名曲学家王骥德在《曲律》中对臧氏及其《元曲选》的评论。后又引出徐复祚和凌濛初对王氏评论的批评,而为臧氏辩护,乃至大唱赞歌。
但晚明的这场围绕《元曲选》的争论,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元曲选》本身,涉及当时曲坛的若干历史背景,涉及著名曲家之间的观点相左,其间也包含有文人相轻的因素。
臧懋循《元曲选》是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开始成书的,该书前序即写于这年春日,第一批出书五十种。万历四十四年(1616)写成后序,随之全书(一百种)出齐。万历时期是明代戏曲传奇的最后辉煌期,汤显祖的“四梦”已问世。被后人称为“吴江派”的曲家十分活跃,沈璟被尊为曲坛盟主,王骥德《曲律》中说他是“词林之哲匠,后学之师模。”臧懋循在主张戏曲“本色”这点上与沈璟是一致的,但臧氏在《元曲选》的两篇序文中,明显地表现了尊北曲而轻南曲的倾向,其间包括尊前代剧作而轻当时剧作的观点。他还批评了包括徐渭、梁辰鱼和汤显祖在内的很多剧作家,他并没有点名批评沈璟,但后序中有一段话对沈氏和他的追随者是很不敬的:
北曲有十七宫调,而南止九宫,已少其半。至于一曲中有突增数十句者,一曲中有衬贴数十字者,尤南所绝无,而北多以是见才。自非精审于字之阴阳,韵之平仄,鲜不劣调。而况以吴侬强效伧父喉吻,焉得不至河汉!此则音律谐协之难。
如果把上述这段话与沈璟的[二郎神]套曲作对比,矛头所向,自是沈璟,沈璟在[二郎神]套曲中写道:
何元朗,一言儿启词中宝藏,道欲度新声休走样。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噪。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
沈璟[二郎神]为论曲之作,或认为其写作动机是针对汤显祖。曲意鲜明,强调“合律依腔”,“说不得才长”。而臧氏序中强调“才”,把“精审于字之阴阳,韵之平仄”,相对地置于次要地位。序中所说的“以吴侬强效伧父”,或许针对沈璟关于作南曲也必须严守《中原音韵》的主张。“伧父”,这里意为中州之音,实指北曲。
臧懋循和汤显祖是有直接交往的朋友,他作《元曲选》后序之年,即是汤显祖逝世之年,但后序写于春日,汤氏去世是为夏时,相距三个月,臧氏在前序、后序中都批评了汤显祖,说汤氏工于北曲而疏于南曲,甚至说他于南曲“绝无才情”,“识乏通才之见,学罕协律之功”。汤氏去世后二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臧氏又删订汤氏的“四记”,并在《玉茗堂传奇引》中攻击汤显祖:“今临川生不踏吴门,学未窥音律,艳先哲之声名,逞汗漫之词藻,局故乡之闻见,按亡节之弦歌,几何不为元人所笑乎!”臧氏自诩“为之反复删定,事必丽情,音必谐曲,使闻者快心而观者亡倦,即与王实甫《西厢》诸剧并传乐府可矣”。(注:《玉茗堂传奇引》,见《负苞堂集》62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但他的删定使后人有“狼藉之极”的感叹,也有“临川之仇”的说法(注:日本学人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说:“臧氏改本,不仅小改曲词使其音律谐和,而且或删全曲,或改宾白,狼藉之极。《还魂记》清晖阁本凡例称之曰:‘如臧吴兴、郁蓝生二种,皆临川之仇也’,宜哉”。见王古鲁译著本231页。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今按:清晖阁本难见,通常只见冰丝馆翻刻本。其中“凡例”今可见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123页,齐鲁书社1989年版。)。
汤显祖既已去世,不可能对臧氏作出反驳,沈璟虽在《元曲选》编成前五年已去世,但沈璟的同乡、王骥德的好友毛以遂却对《元曲选》作了“认真”的评论。关于此事,《曲律》中有所描绘:
若其(指《元曲选》)妍媸差等,吾友吴郡毛以遂每种列为关目、曲、白三则,自一至十,各以分数等之,功令犁然,锱铢毕析。其间全具足数者,十不得一,既严且确,不愧其家董狐。行当悬之国门,毋庸赘一辞矣。(注:本文凡引《曲律》,均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所谓“妍媸”,当是用陆机《文赋》中“混妍媸而成体”意,“差等”是区分等级。毛以遂给《元曲选》所收的每一个剧本区别等级的具体作法是打分,最高分是三十分,结果是,一百种中能得到满分的不到十种,于是王氏誉毛氏为“其家董狐”,类似于说毛氏为藏氏“忠臣”之意。但“董狐”并非是一般忠臣,他是春秋时代晋国的史官,当时赵盾受晋灵公迫害而去国,赵盾的族人赵穿诛杀灵公,赵盾归晋,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因此他曾被孔子誉为“书法不稳”的“良史”。
至于王骥德自己在《曲律》中对臧氏及其《元曲选》的批评,则既有公平之论,也有轻蔑之言。王氏那番话本已为学人习知,但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这里依旧照引如下:
近吴兴臧博士晋叔校刻元剧,上下部共百种。自有杂剧以来,选刻之富无逾此。读其二序,自言搜选之勤,多从秘本中遴出。至其雌黄评驳,兼及南词,于曲家俨任赏音;独其跻《拜月》于《琵琶》,故是何元朗一偏之说。又谓“临川南曲,绝无才情。”夫临川所诎者,法耳,若才情,正是其胜场,此言亦非公论。其百种之中,诸上乘从来脍炙人口者,已十备七八。第期于满百,颇参中驷,不免鱼目、夜光之混。又句字多所窜易,稍失本来,即音调亦间有未叶,不无遗憾。晋叔故俊才,诗文并楚楚,乃津津曲学,而未见其一染指,岂亦不敢轻涉其藩耶?要之,此举搜奇萃涣,曲型斯备,厥勚居多,即时露疵缪,未称合作,功过自不相掩。
王骥德是后人所说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的中坚人物,这一派人常以曲学正宗自诩(实际上确也是曲学里手),所以王氏批评臧氏不习曲学,实有党同伐异之嫌。后世学人尝以为王氏说《元曲选》功大于过是公允之言。按王氏所见杂剧当很多,他曾说:“余家旧藏,及见沈光禄、毛孝廉所,可二三百种”。所以他能判断臧氏所选百种已经收集了向来脍炙人口的上乘之作的十分之七、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承认臧氏选曲“功过自不相掩”。但他笔锋一转,立即把毛以遂(即毛孝廉)为《元曲选》“妍媸差等”事介绍出来。这到底是批评杂剧剧本呢?还是批评臧氏缺乏眼光呢?既然王氏已经承认臧氏所选百种中大部分是“典型斯备”的上乘之作,称赞他多有劳绩(即:厥勚居多),又缘何要把毛以遂抬出来,还说要把他的评判“悬之国门”呢?看来,这种作法未免尖刻。
或许正是对“吴江派”中人露才扬己、轻薄他人的行为不满,徐复祚和凌濛初毅然为臧氏辩护,乃至针锋相对地把臧懋循与沈璟相提并论。结果说徐氏在《三家村老委谈》中虽批评沈璟的《红渠记》“时时为法所拘,遂不复条畅”(注:本文凡引徐复祚语,均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所辑徐氏《曲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但他还是推尊沈氏是“词家宗匠,不可轻议”,那么在对待王骥德的态度上,则不甚客气了。他批评王氏《题红记》“结构如搏沙,开阖照应,了无线索”。他还对王氏《题红记·例目》大张挞伐,实又是引申和歪曲。王氏曾说,自《中原音韵》问世后,元人作曲都“用之甚严”,但像《拜月亭》和《琵琶记》则不同,“始决其藩”。徐氏却引申为王氏推崇“出韵”,并大作文章,说是“夫《琵琶》出韵,是诚有之,《拜月》何尝出韵?且二传佳处不学(举),独学(举)其出韵,此何说也?此何说也?”这一番批评,见出感情冲动,诚有吹毛求疵之嫌,却也表现出徐氏对王氏的强烈不满。至于对待臧氏,徐氏则给予了高度评价:
王茗堂四传,临川汤若士显祖先生作也。其《南柯》《邯郸》二传,本若士(按:应作“若士本”)臧晋叔懋循先生所作元人弹词来(按:此处语意不明豁,疑指臧氏刊行的元人弹词《仙游》、《梦游》)。晋叔既以弹词造其端,复为改正四传以订其讹,若士忠臣哉!晋叔最爱余诸传,逢人便说,且托友人相邀过彼,而余贫老不能往。未几而晋叔物化,负此知己,痛哉!晋叔不闻有所构撰,然其刻元人杂剧,多至百种,一一手自删定,功亦不在沈先生下矣。
由于王骥德批评臧氏对汤显祖评论不当,于是徐氏强调臧氏为“若士忠臣”;由于王氏说臧氏于曲学无所“染指”,于是徐氏强调臧氏虽无“构撰”,却有校定元剧之功。文中所说“沈先生”指沈璟,但沈璟并不曾选刻元剧,所以这里的“功”又是泛指治曲成就。这种褒奖,或属过甚其词,且有投报知己的阿好之嫌,却也表示了对王骥德贬抑臧氏的不满。
无独有偶,明末的另一位曲家凌濛初也是大赞臧懋循,乃至认为他“知律当行”在沈璟之上。凌氏在《谭曲杂札》中说:
沈伯英审于律而短于才,亦知用故实、用套词之非宜,欲作当家本色俊语,却又不能,直以浅言俚句,掤拽牵凑,自谓独得其宗,号称“词隐”。而越中一二少年,学慕吴趋,遂以伯英开山,私相服膺,纷纭竞作。非不东钟、江阳,韵韵不犯,一禀德清,而以鄙俚可笑为不施脂粉,以生梗雉(稚)率为出之天然,较之套词、故实一派,反觉雅俗悬殊。(注:本文凡引凌濛初语,均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所收《谭曲杂札》。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与徐复祚批评王骥德而推崇沈璟不同,凌氏把矛头直指沈璟,说他“短于才”。至于文中所说尊沈璟为宗主的“越中一二少年”,当是指王骥德和吕天成,前者为会稽人,后者为馀姚人。“少年”云云,是轻蔑之词。凌氏评论臧懋循,另有一番口气,他说:
吾湖臧晋叔,知律当行在沈伯英之上,惜不从事于谱。使其当笔订定,必有可观。晚年校刻元剧,补缺正讹之功,故自不少;而时出己见,改易处亦未免露出本相,识有馀而才限之也。
王骥德不是说臧氏“不敢轻涉”曲学吗?凌氏却说臧氏如果从事订谱之业,必有“可观”,因为他比毕生从事订谱事业的沈璟更加“知律当行”。凌氏和臧氏是同乡,都是湖州人,所以文中说是“吾湖臧晋叔”。或许他的评论有回护同乡之嫌,但他指出臧氏“时出己见”,改动元剧,却又显得不是一味回护。
概如上述,晚明曲家就《元曲选》展开的争论,早已越出了《元曲选》本身,不少问题是由臧氏的两篇序文引起的。涉及当时南北曲的写作和南曲作家的评价诸问题。也有意气之争。至于对《元曲选》本身的批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对选目的评估,毛以遂的“差等”之议今已无见,即使他认为臧氏所选一百种中只有八、九种能得到他的满分,即三十分,那么二十分以上的有多少种呢?莫非只有得三十分者才能入选吗?故可置之不论。王骥德肯定臧氏所选百分之七、八十是上乘之作,只是批评他为了凑百种之数,导致鱼目混珠之弊。这种批评实属平常,大凡选刊,总要受到遗珠之讥。再说,这里关及仁智各见,很难取得共识。何况,选录百种,其中七、八十种属“上乘”之作,也就说明这个选本“典型斯备”的基本面貌了。
二是校定问题。王骥德所说:“即音调亦间有未叶,不无遗憾”,当是说原剧中存有未叶现象而臧氏未予订正。凌濛初则说:“补缺正讹之功故自不少”。两家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因王氏也只说是“间有未叶”。
三是窜易问题。王骥德、凌濛初都批评臧氏以己见作改易,王氏着眼点是“稍失本来”,凌氏则从“识有馀而才限”作批评,两者角度有所不同,前者顾及原貌,后者计较改笔的好坏。
明清时代不少曲家,不很重视存真,这有种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要“正讹”,由“正讹”而走向“以己意改之”,也就难以避免。王骥德、凌濛初刊刻《西厢记》,也有此类举动,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注重存真和着意好坏,这是两个角度。明人黄正位选录元剧为《阳春奏》,“凡例”中说:“曲中拆白等语,是皆金元习音,不必求其洞烛,若以己意强解,至或妄为佳句,反失其真矣。”(注:转引自《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452页,齐鲁书社1989年版。)这是切中时弊之言。其实,由不明而强解,不致失真,由不明而妄改,则必失真。
晚近的元剧研究家,很重视存真,这既同清代大盛的考据学传统有关,也同接受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有关。不仅中国学人,即使外国学人,也都从存真的角度批评《元曲选》,这就是我在上文说到的研究方法的“绾摄”。
前面提到的郑振铎在《关汉卿〈绯衣梦〉的发见》一文中批评《元曲选》,就是处在这种治学背景下。他正是从他所作的校阅工作的实际出发来作批评的。他发现了顾曲斋本中的剧本和《元曲选》中有关剧本的不同处,他又把丁氏八千卷楼旧藏的《元明杂剧》二十七种(按:其中十八种实为《古名家杂剧》本),与《元曲选》校阅,发现“其面目亦大不相同”,却与顾曲斋本有关作品差异极小。于是他得出结论:“此可见《元曲选》与同时明人所刊的元曲,其不同的程度是如何的大”。由此,他也就要借用叶堂的话来严厉批评臧氏了。
后来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中批评臧氏“师心自用,改订太多”(注:见《也是园古今杂剧考》151-153页,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也是通过校阅提出来的。他的结论是,今存元杂剧版本可分三类:一是元刊本,指今通行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二是“删润本”,指明人所刊《古名家杂剧》、《元人杂剧选》和《古杂剧》等等;三是《元曲选》本。他认为《元曲选》改动最多:“凡删润之本,校之元刊本,大抵存原文十之七八。懋循重订本,校以元刊本,其所存原文不过十之五六或十之四五”。为此他感叹地说:“嗟呼!安得元本尽出,使世人得一一读原文从而论定其曲也?”无疑这是一种道地的存真观点。
大致与孙楷第批评《元曲选》“改订太多”同时,日本学人青木正儿在《元人杂剧概说》中也论说“《元曲选》改窜得比较厉害”。青木正儿只是把他所能见到的《复元椠古今杂剧》(按:即《元刊杂剧三十种》)、《元明杂剧》(即八千卷楼旧藏本),加上《太和正音谐》中的有关曲文,来和《元曲选》对校。他先是把元刊本和《元曲选》本相重本子相校,当然发现很大相异,但他认为“这样厉害的改窜的痕迹”,并不能只责备《元曲选》的编者,因为他判断在《元曲选》以前,对元剧的改动,早已“与岁月俱增”。《元曲选》和《元明杂剧》重见剧本有十六种,其中有《梧桐雨》、《两世姻缘》和《金钱记》,明初《太和正音谱》中引用了这三个剧本的十五支曲文(其中有一支《元曲选》有而《元明杂剧》无),于是青木正儿将它们相校,得出了以下结论:“就这些曲文,把互见于三书中的异同加以检查,共计有十八处。其中《元明杂剧》与《正音谱》相合者有十五处,《元曲选》与《正音谱》相合者仅有三处。从这一点来推测其全部,那么,《元曲选》改窜得比较厉害,是可以想见的”。(注:《元人杂剧概说》37-41页,隋树森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原名《元人杂剧序说》,开明书店刊印。)
青木正儿“推测其全部”云云,或许并不能使人信服,因为“推测”只是一种可能性的估计。正如有人不敢完全相信《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中关于《元曲选》与元刊本相校只存十分之四五的结论一样,因为这种普遍性的结论缺乏具体论证(至少在书中没有具体论证)。但我在八十年代主编《元代文学史》时,当我围绕《元曲选》所收的重要剧本对元剧作校阅以后,即使我对孙先生的“十之四五”说尚有保留,对他的元剧版本分三个系统的见解是信从的,我认为是大致符合今存元剧版本实际的。
是的,只要我们持客观态度,注意到晚近中外学人通过他们所作的校阅工作(哪怕是局部的),不约而同地得出《元曲选》不同于今存《古名家杂剧》、《元人杂剧选》和《古杂剧》等明刊本的结论,不同于较早的《太和正音谱》和《盛世新声》这些早期曲选曲谱所收曲文的结论;同时再仔细阅读一下吴晓铃等于五十年代所编校的《关汉卿戏曲集》中的详尽的校勘记,更会相信以上的结论。如果从存真的观点出发,那么,由以上结论,也就必然要对《元曲选》作批评甚至是严厉的批评了。同样,如果我们持客观态度,那么,也不能由以上结论简单地把《元曲选》一概骂倒,更不能否定它的传播元剧之功。清陈栋《北泾草堂曲论》中即曾说臧氏“为功词坛,岂浅鲜哉!”余嘉锡《〈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序》也肯定臧氏“表章传播”元剧之功。事实上,上述几位前辈专家,也从来肯定《元曲选》的功迹。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一开头就说:“元人杂剧多赖臧晋叔《元曲选》而存。从前研究元剧的,几以臧选为唯一的宝库。臧选刊于万历四十四年,所选杂剧凡百种。殆为杂剧选中最丰富的一种。”(注:《西谛书话》419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类似的说法,还散见于他的其他论著。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中对《元曲选》作“解题”时,沿用王骥德的“功过不相掩”说作前提,然后再对其体例作批评(注:《戏曲小说书录解题》4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种观点也散见于他的其他论著。
在我看来,从存真的角度批评臧本多有改笔,却又不能走向形而上学,这也是很重要的。那种只要发现《元曲选》与其他明本不同处,立即毫无保留毫无商量地断定是臧氏所改,决不是慎重的态度。如果把元人的改笔也归之臧氏,更属大误。这里不妨介始一则笑话式的“批评”。有一位学人从清人李调元的《雨村曲话》中发现一则批评“俗士”妄改马致远《岳阳楼》剧中的曲文,把“黄鹤送酒仙人唱”的“送酒”两字改成“对舞”。这位学人断定“李氏所谓俗士,即指臧懋循也”。他不知道《雨村曲话》中的这段文字抄自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原来元时已有这种改笔,“俗士”是一位元人,与臧氏了不相涉。这位学人所犯的不只是通常所说的少读书之过,这类毛病,稍不谨慎,人皆会犯。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由臧氏所蒙“恶声”带来的,这位学人也就不免有“先入为主”的片面性了。
自从《元刊杂剧三十种》发现以后,学人发现其中的《楚昭王疏者下船》与《元曲选》中的《楚昭公疏者下船》相比,差异之大几乎无法校读,难道这是臧氏所为吗?待到脉望馆藏本中的《楚昭公疏者下船》发现以后,可见臧氏并未把元刊本《疏者下船》大砍大删,他收录的正是与脉望馆藏本源头相同的一种本子,只是作了若干修饰而已。
有的剧本,现在通常只能见到元刊本和《元曲选》本,如《薛仁贵衣锦还乡》(臧本作《薛仁贵荣归故里》),两者故事情节大异,元刊本写薛仁贵原无妻室,后来招为驸马。臧本写薛仁贵原有妻室柳氏,后又娶徐茂公之女,两位妻子姐妹相称。这都是臧氏所改吗?有一位学人说:“但这些改动并不一定是臧晋叔手笔。经过多年的演出变动,明代各刊本或抄本的元杂剧,内容已较元代演出本有很多变化。臧晋叔刊印《元曲选》时,所用底本恐已是改动过的明代演出本,不能贸然置于臧的头上。”(注:邵曾祺:《元明杂剧总目考略》21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这无疑是有识之见。经我考察,臧本所据改本或出于元末明初,而臧氏又作过若干修改(注:参见拙作《元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校读记》,《戏曲研究》第42辑。)。
实事求是地辨析《元曲选》中《薛仁贵》一剧的本源,却又不能反过来断定它一定比“科白不全”的元刊本为佳。把元刊本中不少富有生活气息的笔墨改去,同时增添不少封建道德气息的明本《薛仁贵》,被选入《元曲选》,并不能证明臧懋循的选家眼光的高超。
还有的剧本,今只存《元曲选》本和其他一种明本,也就是说,今传只有两个明本,如《张生煮海》。如果把《柳枝集》本和《元曲选》本的《张生煮海》相较,可以发现重大差异,前者保持着“旦本”面貌,后者第三折却由正末主唱。《柳枝集》编者孟称舜对待臧氏并不像早于他的明代曲家那样多有尖刻之言,他选录元剧时常有从臧本的现象,只是他选《张生煮海》时却从“原本”,不从臧本,并有“吴兴本改作”这类话。他所说的“吴兴本”指《元曲选》本,因臧氏是湖州吴兴人。他所说“吴兴本改作”云云,可以理解为臧氏改作,但也可释为臧氏所选之本“改作”。经我考察,臧本《张生煮海》“破坏”旦本惯例,或非出自臧氏,但臧氏间有改笔(注:参见拙作《元杂剧〈张生煮海〉校读散记》,《阴山学刊》1992年第1期。)。如果按版本的优劣论,臧懋循所选自较孟氏所选为差,只能以没有识见来批评他。假若我们愿意为他辩护的话,也只能说他或许未见其他版本,却不能说他所选之本就属精当。
著名的《窦娥冤》剧,今存三个完整的明本,其中孟称舜《酹江集》本基本上是按照《元曲选》本重刻的,因此实际只有两个有差异的本子:《古名家杂剧》本和《元曲选》本。前者写蔡婆在胁迫下同意改嫁给张驴儿之父,后者写她未曾改嫁,或者说处在一种敷衍张父的过程中,有一位外国学人说是处在“讨论”中。这种改笔是显出“时代特点”的,在关汉卿当时,理学观念不像明代那样强烈,何况蔡婆是一位商人妇,又是在被迫情况下,写她改嫁甚合情理,故大致可断定《古名家杂剧》本这一情节是接近原本的,《元曲选》本的改动出自明人,殆无疑问。如果从存真观点出发,显然臧本越改越离“真”。但就曲文而论,却是《元曲选》较佳。类似这样的情况,《元曲选》中并不乏见,人们作评论时,切忌片面,也要作具体分析,如果遽下判语,难免欠妥。
《元曲选》所收的第一个剧本是《汉宫秋》,今存明本有四种之多,我曾加以相校,也发现《元曲选》本的“独特”处最为明显。例如常被后世曲家激赏的第一折中的[混江龙]曲,《古名家杂剧》本和《古杂剧》本是相同的,惟《元曲选》本出现不同。孟称舜选录此剧时,对臧本采取从又不从态度,他说:“吾意古本非甚讹谬,不宜轻改。改本有胜前者,始不妨稍从之耳。”他舍弃了臧本中的[混江龙]曲,并有批语说:“吴兴本率多删改,反不若原辞迢递,今改仍旧。”《古名家杂剧》本和《古杂剧》本《汉宫秋》的结尾处汉元帝唱[尾声]曲后下场,此时上场一位丞相,有一段独白,述说番国已送回毛延寿,情愿讲和,皇帝已下令将毛延寿斩首,祭奠明妃,云云。《元曲选》本中却让汉元帝唱[随煞]曲后不下场,再上场一位尚书,报告番国将毛延寿送回和情愿讲和事,于是皇帝发话斩毛祭王。《古名家杂剧》本和《古杂剧》本中都有一首丞相所念的下场诗:“正是,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王骥德《曲律》中曾说:“元人诸剧,为曲皆佳,而白则猥鄙俚亵,不似文人口吻”。上引那首下场诗,虽然是符合格律的五绝,但属俚俗之作,于是臧本中就改为由皇帝念一首下场诗:“叶落深宫雁叫时,梦回孤枕夜相思。虽然青冢人何在,还为娥眉斩画师”。这首近体七绝就文雅多了。孟称舜不采取臧本的结尾,采用“古本”的收场,却用这首较文雅的七绝,代替了那首俗气的五绝。
元剧唱词中常有不甚好懂之句,如《汉宫秋》第四折[叫声]曲末句作“怎做的吾当染之轻”,《古杂剧》本、《盛世新声》和《词林摘艳》均同。由于此曲首句是“高唐也梦难成”,于是臧本就把那末句改作“偏不许楚襄王枕上云雨情”。这当然醒豁了,孟本也就改从臧本。后世注家曾说“怎做的吾当染之轻”句费解难懂,或为臧本更改原由。按“吾当”即“吾”,本剧中不止一见,又《梧桐雨》第一折唐玄宗唱[八声甘州]曲中也有“却是吾当有幸”句。宋以来的小说中也不时可见,但晚明时代的人或已觉不懂,故有把“吾当”改为“吾党”之举。只是臧本《梧桐雨》中依旧保留“吾当”,故此处改句之因或非嫌“吾当”难懂。看来问题出在“染之轻”三字上。我曾疑此句误简,“轻”字或有误,但后来发现郑光祖《倩女离魂》头折[混江龙]曲中有“染之重梦断魂劳”句。那么,可证“染之轻”并不是错句,我的怀疑无非是臆测。当然,对“染之轻”、“染之重”此类话语,用前引黄正位的话说,已难“求其洞烛”,如按黄氏主张,悉存其旧,臧氏则不同,他是要下笔改动的。这里顺便说到,《倩女离魂》是孟称舜激赏的剧本,他在选入《柳枝集》时,对臧本又是采取从又不从态度,他在批语中说:“吴兴本多所改窜,有意旨胜原本者,间亦从之。”又在评[混江龙]曲时云:“絮絮叨叨,说尽儿女情肠。吴兴本于此支删去将半,殊觉寂寂矣。”我曾把孟,臧两本对校,发现大凡臧本改动处都显文雅,也有的是为了对仗,如第三折[醉春风]曲中有这么两句:“一会家缥缈呵如趁扶摇,一会家精细呵使着躯壳。”臧本中把“如趁扶摇”改作“忘了魂灵”,以和下句“使着躯壳”相对。我还曾把《太和正音谱》中所收的《倩女离魂》曲文,来与臧本、孟本相校,发现孟本更接近《太和正音谱》,所以孟氏选剧时常说的“原本”当属较早的本子。孟氏常把“原本”和“改本”相论,所谓“改本”,正是“吴兴本”也就是《元曲选》本的同义语。
臧懋循自己并没有讳言他修改元剧,他在《寄谢在杭书》中说:“比来衰懒日甚,戏取诸杂剧为删抹繁芜,其不合作者,即以己意改之,自谓颇得元人三昧。”(注:《负苞堂集》92页。)他在《元曲选》前序中说的“若曰妄加笔削,自附元人功臣,则吾岂敢。”也不是故弄玄虚,实是自负之言。臧氏是相当自负的,上引《玉茗堂传奇引》中竟说汤显祖之作,经他修改,可与《西厢记》并传。这种自负实属孟浪。清人叶堂是一位吴中老曲师,他在为汤显祖《四梦》订谱时,十分尊重汤氏原著,他以曲律来迁就原词,他在《纳书楹〈四梦〉全谱·凡例》中说:“第欲求合临川之曲”,“特以文词精妙,不敢妄易,辄宛转就之”。从这种尊重态度出发,他也就要在《纳书楹〈四梦〉全谱·自序》中批评臧氏,说:“《邯郸》、《南柯》,遭臧晋叔窜改之危,已失旧观。”(注:转引自《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157-158页。)至于他对《元曲选》的批评,见《纳书楹曲谱正集》:“元曲,元气淋漓,直与唐诗、宋词争衡。惜今之传者绝少,百种系臧晋叔所编,观其删改《四梦》,直是孟浪汉。文律、曲律皆非所知,不知埋没元人许多佳曲。”(注:《词余丛话》引此文,文句有出入。参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九册254页。)这里着重批评的是臧氏的改笔,口气不可谓不严厉,所以郑振铎《关汉卿〈绯衣梦〉的发见》一文中要说这是“猛攻”了。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当年撰著《宋元戏曲考》时,《元曲选》几乎是他的惟一依据,他虽然知道“世多病臧晋叔(懋循)刻《元曲选》多所改窜”,但他误认为臧氏所据都是“御戏监”本,与“坊本”不同,后人执“坊本”而议,“宜其多所抵牾”。他当时以为《元人杂剧选》和《古名家杂剧》等明人选本都已佚失不见,也是园所藏也“竟无一本留于人世”,所以他亟力称赞《元曲选》保存元剧之功(注:见《录曲馀谈》,《王国维戏曲论文集》22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也是园藏本(实即脉望馆原藏)公诸于世时,王氏已去世。但《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发现时,王氏还在世,他为之厘定并作序,虽认为系属“多讹别之字”的坊本,却也惊叹为“惊人秘笈”(注:转引自《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361-362页。)。
王氏《宋元戏曲考》是里程碑式的力作,由于受种种条件制约,王氏对元剧版本的识见存在片面性,这也是事实。王氏如果能看到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大量元剧版本而加以校勘,即使他还会赞赏《元曲选》的佳处,但他大概也不会完全赞赏臧本之改笔。王氏终究也是一位史学家,他不可能忽视“存真”问题。
《元曲选》刊行至今,已有三百八十多年,它之所以成为最有影响的元剧总集,并不偶然。在选目上,连明人也承认它收录的作品绝大部份是历来脍炙人口之作,近人更说它“务取名作”(注: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序》,转引自《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500页。)。这是它功绩彰显的最主要的“内因”。明人的其他元剧选集规模都较小,且在流传中或有散佚,或时隐时显,从而更使《元曲选》长期独显,这是“外因”。但它一出现就遭受批评,而且三百多年来批评不断,其中不少批评符合它的实际。这都是历史事实。这也就构成《元曲选》的历史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