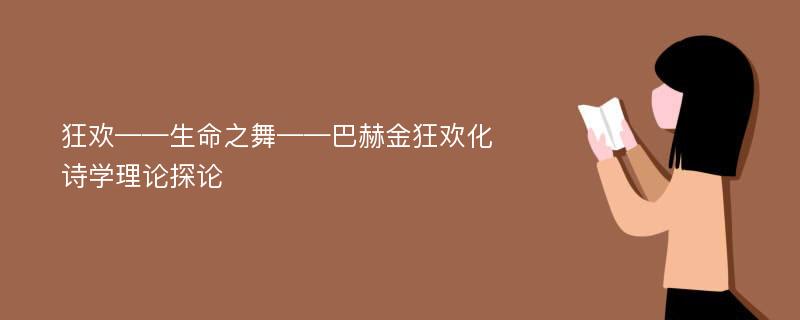
陈登凯[1]2001年在《狂欢——生命之舞》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狂欢是一种全民、欢快、充盈、再生与未完成的世界观、生存态度和生命状态。它把自己的这些生命内涵渗入生活、制度、宗教以及文化的各个角落,以自己所独有勇气与绝决创造了一种与正统官方文化分庭抗礼的狂欢文化及与此对应的狂欢生命与生活。巴赫金一生致力于这种自由快乐的狂欢世界的揭示,认为狂欢与狂欢文化的独到之处就是通过这种表面的对抗表现出生命所固有的永恒延续性。死亡不是终结,而是新一轮竞争的开始;对抗也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它毁灭了旧有的专制文化和呆板生活,催生了新的、自由的狂欢世界,“世界既死又生”。巴赫金所倡导的就是这种对权威化、终极真理、专横话语等进行颠覆的狂欢思维,他要在对旧的话语体系的颠覆中进行积极的创造性的重建,从而建构一个正在形成、欢快、开放、自由的新的话语体系,即狂欢化诗学理论体系。狂欢化源自狂欢节型的庆典,狂欢化的文本使狂欢世界得以再生。巴赫金认为拉伯雷的作品最集中地反映了这一动态的狂欢化过程,是一种复兴人的感性生命的“怪诞现实主义”。通过这些文本的解读,巴赫金引导人们踏入自由、欢快、平等的生命狂欢舞圈。 狂欢化诗学理论体系是一个涉及思想意识、审美观念以及具体文学艺术创作及批评等的文化现象。它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其涵盖面非常广泛。通过它,巴赫金不仅给我们以全新审视文学、艺术及文化的视角,而且构建了一个平等、欢乐、创造、再生的世界,它力图以诙谐的笑、以狂欢的自由力量改变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使人们的意识摆脱僵化的守旧习惯,脱离孤立的独白语境而对话交流。
骆凡[2]2014年在《中国式“狂欢”与清代说书》文中认为说书,又称说话,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伎艺,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则是西方着名的文艺理论,重视民间诙谐文化传统。我们把狂欢化的视角运用到说书领域的研究,即是将说书艺术同它所置身的民间广场与民间诙谐文化联系起来,把它同共同生存的民间诙谐文艺形式联系起来,同它具体的传播环境、传播方式、受众接受联系起来,以此来重新认识说书诙谐艺术所潜藏的文化意蕴。研究分叁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对说书所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行还原,即对狂欢文化进行梳理,从民俗狂欢到狂欢的场所以及狂欢场所中存在着的文艺形式。第二部分是将说书这一传播场域进行考察,力图描述书场传播中的狂欢体验。说书作为狂欢文化的成员之一,身处中国诙谐文化氛围,它存在着笑谑与突破常规的狂欢体验。第叁部分是关于说书诙谐文本的分析,也即文学本位研究。但研究所采用的评价标准不是源于正统文学中艺术水平的高下,而是通过说书的诙谐手法挖掘出它所依存的诙谐文化传统,它所反映出的诙谐文艺中共有的诙谐方式与手法。而这种共性恰好反过去证明了共同的文化土壤,相同性质的传播关系、相同的受众心理对文艺形式与风格的规定性。整个的论证逻辑是由文化到文学,由外部到内部,进而内外互证。第一部分对中国狂欢文化进行溯源。狂欢一词在我国汗牛充栋的典籍中并不常见,但这并不意味着狂欢的缺失,我们稍加识别,便可发现许多虽不以狂欢名之却深具狂欢精神的文献记录。它们是关于我国古代人民生活、劳作、节庆、祭祀、婚姻、丧葬等各种风俗的记载。透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感受到狂欢文化的氛围。《礼记·郊特牲》中关于“蜡祭”的描述便可视作最早记载。我们粗略勾勒出中国民众狂欢生活的基本轮廓:它以节庆为主要依托,欢会中民众聚集,男女同乐、肆意饮食、纵情享乐,歌舞喧哗、百戏竞集。狂欢的发生通常是一种群体行为,须有场所承载,故而巴赫金在其狂欢化理论中把“广场”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提出,认为广场在狂欢节中是全民性的象征。这里远离官方意识形态的笼罩,存活于广场上的各种言语体裁、戏仿文学则洋溢着诙谐幽默的民间情趣,饱含着颠覆与新生的强劲活力。广场的存在为民众的聚集提供了空间,更为各种民间文艺带来了滋生的土壤,使民间文化获得话语权。中国虽然没有没有西方城市建筑中所谓的“城市中心广场”,但是却也有着全民群聚、民间文艺兴盛的中国式“广场”。虽然宫殿庭院式广场与官方意识紧密相依,却奠定了广场与百戏相依的悠久传统。其余的寺庙广场、街市广场、节庆游乐广场、瓦舍类型的商业性游艺场所、茶馆都是属于中国式的民间广场,它们形态各异,但文化特征上显示出高度的同质性。广场中全民聚集,身体与心理的距离都得到消解,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弱化消融;广场中行业汇集,人们各种需求都得到满足,物质、信息、能量在此进行了充分的交换与聚合;而广场中百戏竞集的传统绵延几千年,折析出中国人的观念中,百戏即广场的应有之义。百戏是民间传统文化中最热闹、最芜杂的部分,因而也成为最肥沃的土壤,滋养出中国民间的各种文艺形式,中国的俗文学之渊薮即存于此,民间说唱、戏曲都是逐渐从百戏中分化出来,并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特征及体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狂欢广场同时也是笑文化之渊薮,洋溢着欢乐氛围,诙谐幽默的风格几乎波及广场中的每一种文艺形式。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恰好能够较合理地解释其成因。一方面,广场中民众聚集,等级隔阂弱化消融,人际关系的平等氛围使得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显示出轻松、自由等亲昵化的特征,传播关系的性质对于艺术形式、风格影响明显。另一方面,广场中容纳着众多表演艺术形式,为各种艺术形式的相互借鉴、吸收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性。如果将二者综合起来考虑,那么基于相同的传播场所与传播关系以及受众心理,广场中诸多的艺术形式便会呈现出相对统一的风格,表现手法、内容题材、言说方式也会交融互通。从相同的物质关系所引起的文学形式、风格等意识形态层面的相似,或可为我们重新理解戏曲、说唱领域互渗的现象开辟新视角。第二部分对说书场域存在的狂欢体验进行分析。书场中最标志性的表情就非“笑”莫属,而“笑”也是狂欢体验中最外在化的表征,并且对狂欢氛围的营造有其特殊的作用。狂欢体验的另一来源是反规范性,官方禁令与传统道德对说书的批判中充分彰显出书场中洋溢的狂欢精神与民间立场。说书场域的反规范性体现在全民聚集对等级制度的消解、情色内容对性道德的冲击与对本能的释放、议政干政等叁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广大民众利用民间口头文学批判官方真理,表现自我意愿的狂欢意识。狂欢的体验中还包含着民众的平等交流、高度互动,反对单方独白的权威压制,强调个人的主体价值,处于对话和交往状态中的个体在相互依赖中互相激活。第叁部分对说书文本中的诙谐因素进行分析。分成肉里噱、外插花、狂欢化的语言、文本中的狂欢民俗描写四个方面。“肉里噱”是指内蕴于书中人物性格与情节中的诙谐因素。我们主要针对书中的诙谐人物进行了类型化分析。每一部书都有自己的诙谐人物,大致可以分成书筋、诙谐化的小人物、诙谐化的正统人物叁大类型。书筋是与书胆相随而生的、逸趣横生、寓庄于谐的人物,他与戏曲中的净、丑大体对应,可分为滑稽英雄与机智小丑两类。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书筋与巴赫金关于中世纪狂欢广场上狂欢式的人物的特征描述显示出相当的契合度,这种贯通恰恰体现了人类在获取欢乐愉悦的方式上的同一性,人类思维结构的相似性以及更深层次的原始冲动的无差别性,即民间意识形态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反抗,貌似憨傻的行状和言语中蕴含的真理与叛离意识在笑谑化的手法中合二为一,释放着普通民众在社会道德规范束缚下的冲动,引起中下阶层民众的共鸣,甚至将其作为移情的对象。而对诙谐化的小人物多从生理缺陷、异相着手,通常与戏曲中的小丑类人物相对应,此类笑谑虽然趣味粗鄙、肤浅,却代表了人类初始类型的笑,是我国传统笑话的悠长一脉,他满足了欣赏者自身的荣耀与优越感。第叁类是正统人物的诙谐化,将严肃的历史人物、高大的英雄人物进行笑谑化的改造,从而消除尊崇与恐惧、拉近民众与历史心理距离,在插科打诨中体验到欢乐的自由。外插花是说书艺术中关于诙谐趣味营造的另外一种方式,指说书人结合书情,穿插、点缀在书中的俏皮话、笑话、戏谑、调侃、俳嘲等逗人发笑的部分,相当于戏曲里面的插科打诨。本文从穿插笑话、运用戏曲科范、戏谑化的韵文穿插、现场抓哏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狂欢化的语言是指在狂欢的广场上,以人与人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为基础,形成了广场言语的特殊形式和风格,日常禁语被打破,在插科打浑和讥笑嘲讽中,有吆喝、赌咒、发誓、詈骂、各种粗话和猥亵语言可以脱口而出。说书中的语言呈现出这一特点,本文通过语言游戏、猥亵性语言两个方面分析。说书文本中大量存在的狂欢民俗描写与其存在的节庆广场氛围紧密相关,本文根据这些描写在叙事中的不同作用,分为推进情节的狂欢节俗、诙谐人物塑造与风俗表现相互映衬、参与狂欢、结构关目四个方面,构成说书艺术的狂欢化特征之一。整个文本分析中,说书艺术的诙谐内容体现出与其他民间诙谐文艺形式的高度互动,尤其是与戏曲,如诙谐性的人物设置,书筋中的滑稽英雄、机智小丑分别与戏曲中的花面、武丑对应,诙谐化小人物与戏曲小丑的对应,外插花中笑话的共同采用、戏曲科范的相互借用、语言风格的高度一致以及节俗内容的广泛应用。诙谐手法与风格的一致共同反映了狂欢文化的共同滋养。同时观察到因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等诸方面的差异,中国式“狂欢”呈现出自己的特点:狂欢的不彻底性、宣泄方式的相对含蓄性、狂欢形式的灵活性与场所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 狂欢——生命之舞[D]. 陈登凯. 西北大学. 2001
[2]. 中国式“狂欢”与清代说书[D]. 骆凡. 扬州大学.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