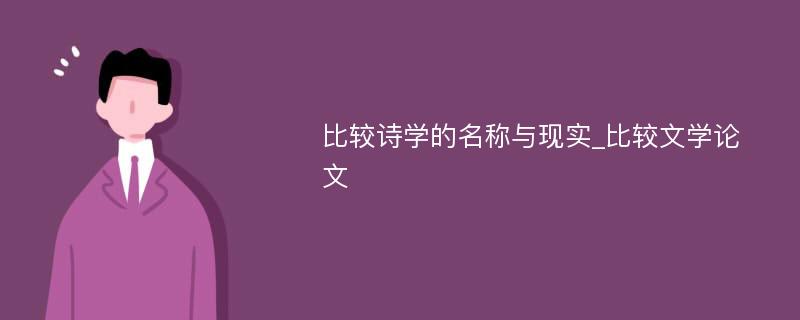
比较诗学的名与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5)01-0108-06
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文学大国。近二三十年来,比较诗学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最大热点。几乎所有的中国学者都承认“比较诗学”的概念来自西方,安田朴(René Etiemble)(注:René Etiemble在中国有多种不同译法,如勒内·艾金伯勒、艾田伯,艾田蒲、安田朴等等,安田朴是其本人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按通例应尊重本人的署名权,故本文中除引文之外,一律使用“安田朴”。)是其首创者。产生“比较诗学”的学术背景是20世纪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争论。
正当一般法国和美国学者还在热烈论争彼此的合法性之时,安田朴却已敏锐地道出了“比较诗学”必将产生的预言:历史的探寻和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式自视为恰好相反,而事实上却应彼此补充,如此,比较文学便会不可抗拒地引向比较诗学[1](P323)。
对安田朴的这个“预言”,由于中国学者依据的版本不同,对内容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所以有多种不同译文,但基本的意义是一致的。
有学者认为:安田朴的“比较诗学”的概念,几乎被我国所有比较文学概论方面的教材所征引,但是几乎遭到了普遍的、有意无意的误解[2](P181)。中国学者是如何“误解”比较诗学这个概念的呢?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
“诗学,指文学理论;比较诗学即对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3](P27)
比较诗学是指在跨文化、跨国度的文学理论之间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Common Poetics)、共同的美学据点(Common Aesthetic Grounds)的可能性,以及用外国的文学理论来阐释本国的文学现象,研究和总结本国的文学思想、技巧和理论的学问[4](P339)。
“虽然‘比较诗学’这个术浯有上述不妥之处,但在比较文学界却已成了通用词。就像‘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准确但又被大家接受使用一样,学术界通常仍以‘比较诗学’来命名各种文论的比较研究。”[5](P197)
读了上述引例,我们觉得中国学者的理解和安田朴的“比较诗学”概念之间的关系,不是“误解”所能解释的。因为误解一般来讲不能是普遍的、有意的,而只能是个别的、无意的。造成中国学者“普遍的、有意无意的误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安田朴的概念以假设为背景,而这种假设很容易被冲破。厄尔·迈纳(Earl Miner)在《比较诗学》一书中,引用了安田朴的“比较诗学”概念之后说:“这种看法有点幻想和玄虚色彩,是以某种未来的可能性为背景的。”此书出版于1990年,比安田朴提出“比较诗学”的概念,晚了27年。所以,他说:“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是针对眼前的情景的一种尝试。这一领域的同仁们也许希望另辟蹊径:意识形态、诠释、翻译、个人、社会—包括文学研究为我们所熟悉的形形色色的途径。正如艾金伯勒所预见的,是研究的目的和目标决定着某一特定的途径能否通向比较诗学。”[6](P44-45)中国大多数学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7]“不管影响研究也好,平行研究也好,比较的结果应纳入或充实所谓‘总体文学’。”[8]总体文学是比较文学更高的发展目标,“揭示世界各国的共同特点、普遍规律,实际上就是诗学或美学。”[9](P8)1983年,迈纳在《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中指出:“近十五年间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专题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10]由此可知,其实迈纳也将各国文学理论的比较理解为比较诗学。
印度的情况进一步说明“比较诗学即对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的理解,具有普遍性。1981年,印度苏里齐·达亚古德(Suresh Dhayagude)出版《西方诗学和印度诗学的比较研究》(Western and Indian Poetics--A Comparative Study)。作者在前言中认为:作为一部比较文学的著作(或者说比较文学理论更为恰当),不同于J.E.施品格恩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批评》等在同一欧洲传统中比较的著作。他说:“为了使研究置于可行的范围之内,我只选取了在印度和西方传统中都比较重要的理论命题加以论述。”“我力图呈现出自柏拉图开始到现代为止,贯穿于前后相继的历史时期的西方诗学中这些经由选择的问题。对于印度的诗学思想的阐述从印度诗学之父婆罗多开始。印度诗学发展演化的持续历史时期,沿循了诸如味论这样一些重要的文学概念。在这种意义上,本书仍然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11](Piv)显然,这位印度同行对“比较诗学”的认识也出现了和中国学者同样的“误解”。印度著名文学理论家纳盖德拉(Nagandra)在《世界文学学构想》一文中写道,构建“世界文学学”(visva sahitya sastra)的可行办法是,从印度和西方文学理论中,找出获得充分发展、有生命力的共同内容。他认为,只要由此出发,建立世界文学学就轻而易举了[12](P4)。综观《世界文学学》一书,盖德拉以《世界文学学构想》作为全书首篇,起总纲作用,其余34篇都是介绍印度婆罗多(Bharata)、欢增(Anandavardhana)、恭多迦(Kuntaka)、新护(Abhinavagupta),以及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朗吉努斯、贺拉斯一直到弗洛伊德等诗学家的诗学观点。显而易见,他的“世界文学学”的方法和目标,和我们理解的比较诗学是相同的,也属于“误解”。既然中国的学者、印度的学者都“误解”,那就应该为这个“误解”正名。按照名实相符的常识,我们应该做出这样的判断:“比较诗学即对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的定义,反映了客观实际,又广为接受,因而是正确的。
比较诗学:实在前,名在后
由于安田朴在1963年提出“比较诗学”这个概念时,用了“走向”(drawn to)这个词,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这是对比较诗学即将产生的“预言”。
许多中国学者,好像是集体无意识,都认为比较诗学是在安田朴做出“比较文学走向比较诗学”的预言之后才兴起的。《比较文学教程》说:“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艾金伯勒在他著名的《比较不是理由》(1963)一文中,为比较文学的发展设计了一个远景规划,其中首次提出了从‘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的设想。”“比较诗学是在近几十年来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13](P89、91)类似的观点,在中国比比皆是。这样,一个新的学术童话宣告诞生:安田朴“预言”比较文学走向比较诗学,于是比较诗学在世界各地兴起来了。
这个学术童话给中国学者带来了逻辑上的尴尬。《比较文学概论》第八章《诗学论》的第一节中说:“7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开始普遍地把文学理论方面的课题当作比较研究的重点……但是,在欧美学者撰写的比较文学原理、导论之类的著述中,比较诗学尚无占有专门的篇章。这一状况在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界却有明显的改观……从而大大丰富了比较诗学的研究实践,并且提高了它在中国学界的学术地位。”可是,在这一章的第二节中又说:“比较诗学的终极目标在于寻求跨文化、跨语言、跨时空的共通规律,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之‘序’中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故申言《谈艺录》之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1](P324、329)
再如《比较文学教程》一书,在《比较诗学》一节里,先讲“比较诗学是在近几十年来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后面又讲“在这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里,中国学者取得了累累硕果。如朱光潜《诗论》、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13](P89、91)作者将《诗论》、《谈艺录》、《管锥编》等视为比较诗学研究领域里的硕果,是非常正确的。正如朱光潜《诗论》重版后记中所说:“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而且他“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14](P311)。钱钟书对《谈艺录》、《管锥编》用心之多,费时之久,以及对比较诗学研究贡献之大,在中外学界众口一词。问题是,《诗论》初稿于1931年,初版于1943年,1948年再版;《谈艺录》出版于1948年,1949年再版,《管锥编》1979年出版,然而这部始笔于1972年的巨著是钱钟书多年积学的成果。这三部中国比较诗学的奠基之作,无论如何都无法归为“近几十年”来即1963年以后的成果。不然,就陷入逻辑的混乱。
印度比较诗学的发展史传递的是同样的信息:比较诗学的实在先,名在后。1981年,苏里齐·达亚古德在《西方诗学和印度诗学的比较研究》的序言中,列举了“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名单:“A.K.左马尔斯瓦米博士的《艺术本质的转化》,伯勒瓦吉温·乔达里博士的《比较美学研究》,K.C.潘迪博士的《比较美学》,K.克里希那拉衍的《诗歌中的暗示义和叙述》,G.哈奴曼吒·饶的《比较美学-东方和西方》。”[11]达亚古德确认上述著作属于比较诗学范畴,而自己的《西方诗学和印度诗学的比较研究》“并不是此类主题的第一部作品”[11]。而以上许多著作的问世时间早于安田朴“预言”诞生比较诗学的1963年。潘迪的《比较美学》之第一卷《印度美学》初版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9年再版时,“增加了关于音乐和建筑的历史和哲学的章节。”[15]此书共13章,前10章分别是《印度美学史》、《新护美学的湿婆派基础》、《新护的美学理论》、《味的种类》、《新护的韵论》、《跋吒对韵的批评和一个回答》、《梵剧的技巧》、《剧种》、《梵剧演出的各要素》、《诗学审美源流》。最后是再版时增加的3章:《音乐艺术》、《音乐哲学》和《建筑艺术》。显而易见,潘迪此书的主体是比较诗学。作者的比较诗学的意识十分清晰。他在《第二版序言》中说:“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两册书的写作主旨,是从印度和西方美学固有的哲学设定出发,予之以忠实的陈述。”[15]
综观印度现代学术,比较诗学和比较文学、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几乎同时出现,而且齐头并进,互为标举。印度学者敬祖重道,高声礼赞传统诗学,在建设比较诗学的进程中,高屋建瓴,俯视西方学术,充满批判精神。难怪美国学者说:“许多印度学者似乎不像日本学者那样乐于接受西方艺术、美学和人文学科的思想。印度今天流行的看法依然是:自己的文化在‘精神价值’上要远远胜过西方几筹,而印度只能学习西方实践性和物质性专题,如工程、卫生和大生产。”[16](P12)
上述中国和印度的情况说明:比较诗学之实先于比较诗学之名,所谓安田朴在1963年预言“比较文学不可违拗地导向比较诗学”的童话并不真实。在安田朴的“预言”之前,至少在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早已有了相当多的真正意义上的比较诗学研究的实践和著作。
比较诗学名实问题引起的思考
比较诗学的名实问题,促使我们产生诸多思考,其中有三点应引起中外诗学界朋友的特别注意。
(一)必须破东方人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但是西方中心主义依然顽强地存在着。这是为什么呢?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作为东方人的中国学者的心里存在着顽强的西方中心主义。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成了我们日常思维的一部分,在我们思考问题时会不自觉地起作用。“预言比较诗学产生”这个学术童话(以下概称“比较诗学童话”)的形成和传播,便是典型、生动的一例。安田朴在1963年只是一种有条件的假设,结果中国学者将其当作了“预言”,并将刘若愚作为首位响应者:“美籍华人学者刘若愚教授赞同艾金伯勒‘比较诗学’的提法。他在1973年完成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强调了‘比较诗学’的必要性,‘考虑到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之间在信仰、自尊、偏见和思想方法方面的差异,我们必须力求跨越历史、跨越文化,去探求超越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文学特征和性质、批评的观念和标准,否则,我们便不应当从整体上去谈文学(Literature),而只能谈孤立分散的种种文学(Literatures),不应当从总体去谈批评(Criticism),而只能谈孤立分散的种种批评(Criticisms)’。”[13](P90)“刘若愚关于‘比较’诗学的提倡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许多美籍华人学者和港台学者赞同这方面的研究并做出了实绩。内地学者也一直提倡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13](P90)
乍一看,一切是那样顺理成章。其实,将安田朴的那段话当作产生比较诗学的“预言”已经勉强,将刘若愚作为实现这个“预言”的首倡者,以及其他美籍华人、港台学者的响应,更是差强人意。待到列举中国大陆学者比较诗学的成就,如朱光潜的《诗论》、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时,就完全自相矛盾了。我们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可以让我们毫无顾忌地编写“比较诗学童话”,当遇到矛盾时,可以不顾逻辑的尴尬,将矛盾吞入肚中。
比较诗学的童话只是众多西方中心主义表现中的一例。此类事例,多到了俯首可拾的地步。不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大声疾呼非将汉字消灭而后快,1929年提出废除中医案;毛泽东长得比斯大林高大,但中国画家却将斯大林画得比毛泽东高大;赛义德的《东方学》完成于1977年,一年后问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大关注,但第一个中文译本一直到1999年才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古人云: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今天我们可以说:破西方人的西方中心主义易,破我们东方人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难。今天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应将重点放在批判我们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说:“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许多中国人并不真正知道中国的文化家底,拿着金碗向西方人乞讨,所以“首在审己”十分重要。有学者指出:“许多西方学者,动辄以西方文论的模式来衡量一切。”“面对这种现况,固然不能置若罔闻、熟视无睹;但如果联系到过去,我们自身也有一定的责任。”[17](P2)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知己知人,心悦诚服地承认并克服自己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只要做到这一点,西方人的西方中心主义就会自惭形秽,自然消失。印度学术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克服我们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我们在历史中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必须在历史过程中消除,不能操之过急,但必须尽快。
(二)左手必须知道右手在做什么
西方有一句名言: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Not to let one's left hand know what one's right hand does.)[18]。尽管这句话的本意和后来的实际意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都不符合比较诗学的要求。我们认为,之所以产生比较诗学的现代童话,重要原因之一是“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所以,我应该将这句名言改为“左手必须知道右手在做什么”。西方人不知东方人在做什么,甚至不知道东方人已经做了什么,那必然会做出错误判断;反之亦然。
安田朴是法兰西的中国学泰斗伯希和(Pall Pelliot)的出蓝子弟,对中西学术造诣精深,对中西文化比较,特别是“中学西渐”的研究,堪称大家。他一生著述颇丰,其中《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是一部800多页的皇皇巨著,“全书洋洋洒洒,纵论上下千余年,横涉文化的所有因子—哲学、史学、宗教、文艺、戏剧、数学、风俗、美学、语言文字、外交关系、情爱、伦理等。此项研究必须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进行,无论对中国学者还是欧洲的汉学家都决非易事。”但是,安田朴的这部著作“令人击节称赏”[19](P4)。他“热爱、崇尚和捍卫中国古老的民族文化,赞同中西文化交流。他经常挺身而出,与诋毁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言行作斗争,因而竟被一些人称为‘中国狂热分子’、‘西方文明的失望者’、‘孔夫子的大弟子’等等。”[19](P4)显然,安田朴不信奉西方中心主义,而且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研究。但是,我们仍然要说,这位知识渊博的汉学家对中国在比较诗学方面的所作所为,具体来说对朱光潜、钱钟书在1963年前的有关著述是不清楚的。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若安田朴知道了《诗论》、《谈艺录》、《管锥编》的具体内容,睿智、机敏的他一定不会在1963年对比较诗学作出那样一个假设。
在“比较诗学童话”的传播中,美国学者厄尔·迈纳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接球手”的角色。他在《比较诗学》一书中说:“正如艾金伯勒所预见的,是研究的目的和目标决定着某一特定的途径能否通向比较诗学。”[6](P45)他的这个“预见”和中国学者的“预言”有着传承关系。迈纳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威望,2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好朋友和引路人”[20]。他对日本文学有深入研究,对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他对中国、印度的比较诗学研究的历史情况是不了解的,甚至可能对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首响之作坪内逍遥充满比较诗学精神的《小说神髓》也不甚清楚。
安田朴和迈纳都是当代著名学者,对东方文学有专业性研究。可是,还是由于“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的原因,他们一个成了“比较诗学”童话的发球手,一个成了“接球手”。国际知名的学术大师尚且如此,对许多中国学者来说,要下的功夫恐怕就更多了。可见,比较诗学是一条艰难之路。
(三)从“知其二”迈向“察其三”
伴随着一门新学科出现的,除了新的研究领域之外,必须还有与之相应的新方法。100多年前,比较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F.Max.Muller),突出和强调了“知己知彼”的重要性,赢得了后人推崇:“缪勒与其同时代的任何人相比,他更为有效得多地使西方世界确信:在宗教问题上,一如在语言问题上一样,‘只知其一者,一无所知’。”[21](P45)缪勒的“只知其一者,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Knows none),是欧洲当时真正具有国际眼光的伟大学者的共识,最早出自歌德之口。歌德作为“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非常重视比较的作用。缪勒说:“当研究比较语言学的人大胆地采用了歌德所说‘只懂一门语言的人,其实什么语言也不懂’这句话时,人们起初大吃一惊,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体会到这句话所含的真理了。”[22](P10)缪勒的一大贡献就是把比较研究作为宗教学的基本方法。“他把歌德的名言‘只懂得一种语言的人,一无所知’,应用到宗教研究之中,提出‘只懂一门语言的人,其实什么语言也不懂’。缪勒认为比较的研究方法是从现象研究转入本质和规律研究的中介。”[23](P2)
比较对于比较诗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我们比较诗学的研究者谁也没有拒绝这个基本方法。那为什么还会出现“比较诗学童话”呢?我们认为,除了上述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这两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满足于A与B之间的比较,缺乏必要的第三者C的参照。能将A与B进行深入的相互比较,显然极大地有利于对双方的本质的揭示,和关起门来进行单一研究相比,是飞跃性的进步。但对A、B双方本质的更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对相关事物的规律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A、B双方互比,往往会出现互相争拗、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这样,非常需要一位第三者。有了这位第三者的参考与比照,A、B之间的许多问题就能不言自明。选择第三者的标准是异质性和影响力,异质性、影响力愈强就愈符合要求。中国、西方和印度,是世界三大独立发展的诗学体系,互相充满异质性和影响力。所以,进行中西或西中比较,印度诗学是最佳第三者;进行西印或印西比较,中国诗学是最佳第三者;进行中印或印中比较,则西方诗学成了最佳第三者。
中国学者在研究比较诗学时,如果能考虑印度因素,了解印度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和在1963年前就出现了许多比较诗学的论著,就可能不会轻言安田朴“预言”和编写、传播“比较诗学神话”了。
进行比较诗学研究,从理论上讲,要求获取的资料越全越好,但从技术能力来讲,不可能做到绝对全面,只能做到相对全面。这个相对全面的最低要求,除了A与B之外,必须还要有第三者C。这个“第三者原则”,是搞好比较诗学研究的最低纲领。我们认为,这是“比较诗学童话”给我们的又一启示,即比较诗学只知其一不行,知其二也不行,还必须迈向“察其三”。这是对歌德和缪勒的“只知其一者,一无所知”的继承和发展。对第三者C,我们可以不作为重点,不必像对A和B那样,做出深入透彻的研究,但对C的总体情况,尤其是对可能影响A、B比较结论的内容,必须进行考察。
综上所述,通过对比较诗学的名与实的讨论得出以下几点看法:(1)比较诗学是指对跨文化、跨国度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意在寻求人类共同的文学规律。(2)比较诗学研究,首起于东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印度等国,比较诗学研究成果丰硕。(3)具有特定含义的“比较诗学”的概念,由安田朴于1963年首次提出。之后,东西方各国尤其是中、印两国,沿着既定方向大力开展比较诗学研究,盛况空前。
标签:比较文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管锥编论文; 美学论文; 诗论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