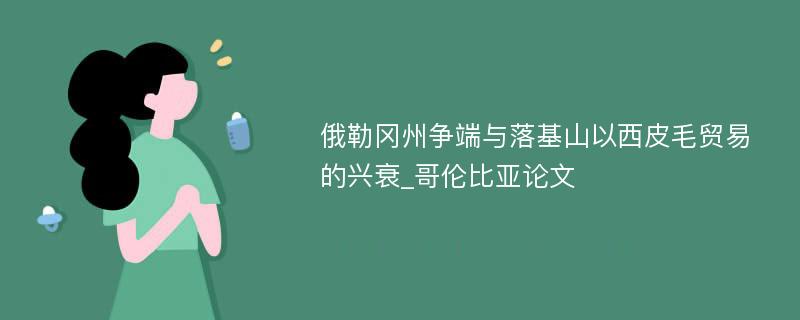
俄勒冈争端与落基山以西毛皮贸易的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勒冈论文,兴衰论文,毛皮论文,争端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早期印第安语中,俄勒冈指哥伦比亚—斯内克河流域。①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英美领土争端最为激烈的时期,则指落基山以西、北纬42度(西班牙所属加利福尼亚殖民地的最北边界)至54度40分(俄国所属北美殖民地的最南边界)之间的地区。②从1792年“哥伦比亚号”船长罗伯特·格雷(Robert Gray)将其命名为哥伦比亚河起,到1846年英美最终划定俄勒冈地区的边界为止,英美在该地区展开了激烈角逐。③该地区的早期历史主要围绕列强对毛皮资源的争夺而展开,英美等国的政治争端对落基山以西的毛皮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术界对英美在俄勒冈地区的政治博弈研究较多,④而对这一争端与毛皮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则重视不足。关于英美围绕毛皮贸易在俄勒冈地区进行的博弈,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英国哈德逊湾公司几乎赢得了对美国贸易商的胜利,缘何最后失去了北纬49度以南的地区?虽然研究毛皮贸易的诸多论著都会涉及俄勒冈争端,但对上述问题并未展开系统论述,也未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⑤本文在大国争霸的宏观背景下,研究俄勒冈争端与落基山以西毛皮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上述悖论形成的原因。 一、海獭皮贸易与俄勒冈争端的缘起 毛皮贸易是北美西部开发史上一种独特的边疆经济模式,与农业拓殖者大规模砍伐森林、驱逐印第安人不同,毛皮贸易商需要印第安人的合作。为了得到持续不断的毛皮供应,毛皮商反对砍伐森林和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改造。⑥但是,毛皮贸易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交换活动。自16世纪末白人殖民者与北美东海岸的印第安人交换海狸皮之时起,它与欧洲列强在北美大陆的殖民扩张和军事争霸就是一对双胞胎。随着殖民争霸势力的更替,毛皮边疆也不断从北美东海岸向西部推进。18世纪末,西北海岸的海獭皮贸易拉开了列强在北美西北部进行商业和殖民争夺的序幕。 与落基山以东海狸皮贸易占据主导地位不同,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主角是海獭。这种动物主要分布在北太平洋沿岸水域,其毛皮是“世界上最好的……甚至可以与王室专用的貂皮相媲美”,⑦“比其他任何已知的毛皮都要华丽和高雅”。⑧早在北美西北海岸的毛皮贸易兴起以前,从亚欧大陆东北地区流入中国的少量海獭皮就受到清朝显贵的喜爱。每张海獭皮在中国广东可以卖到80—90美元,相当于海狸皮价格的30倍。⑨ 其实,北美西北海岸海獭皮贸易的兴起是列强在北太平洋进行地理探险、寻求西北水道的副产品。当时,欧洲人根据地球南北对称的理念,相信北美西北海岸存在一条从太平洋连接大西洋的水道,可以借此便捷地到达亚洲。俄国人捷足先登,为其效力的丹麦探险家维塔斯·白令(Vitus Bering)在1741年第二次探险中,队员在白令岛上发现了成群的海獭和海豹等毛皮动物,并以此为食度过了数月。白令的探险队脱险后,他们把用以取暖的海獭皮卖给中国商人时,居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高价。⑩获利丰厚的海獭皮成为吸引俄国人不断向美洲海岸探险的动力,其势力向南最远延伸到加利福尼亚。从1743年到1800年,俄国人共开展了不下100次探险活动,在北美西北海岸获得了价值800万银卢布的海獭皮。(11)在半个世纪里,俄国人一直掌握着北美西北海岸海獭皮贸易的控制权。1799年,俄国人参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模式,建立了俄美公司,作为在美洲进行殖民和商业探险的领导机构,并宣布其商人涉足的北美西北地区归俄国所有。(12)直到1824年,俄国才最终承认北纬54度40分为其南部边界,从而退出了俄勒冈地区。在此以前,俄国一直是俄勒冈争夺中的强劲力量。(13) 英国商人是向北美西北海岸渗透的第二股重要势力。早在1578年前后,英国著名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就曾经到这里探险。(14)1778年春,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奉命率领探险队对该地进行探险。他们无意间发现:当地印第安人非常愿意用“熊皮、狼皮、狐狸皮、鹿皮、浣熊皮、臭猫皮和貂皮等,特别是海獭皮”,交换船员们随身携带的“刀子、凿子、钉子、小镜子、纽扣、铁器以及其他金属物品”。(15)当库克船队到达广东时,这些毛皮居然卖出了每张120美元的高价,利润率高达1800%。(16)库克的探险把海獭皮贸易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呈现给了世界。 然而,英国人未能充分开发这一商业资源,亦未成为中国与北美西北海岸海獭皮贸易的主角。原因在于:(1)英国当时为了镇压北美殖民地的反抗,正在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进行战争,无暇他顾。(2)英国两家公司在北美西北海岸与中国贸易权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端,南海公司的贸易垄断权虽然包括北美西海岸,但并未伸展到中国;东印度公司虽然拥有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但其权利却没有延伸到北美西北海岸,双方的商船都不能合法地到当地收集毛皮。(17)到1788年,只有约翰·米尔斯(John Meares)和理查德·埃切斯(Richard Cadman Etches)的商船继续在西北太平洋开展海獭皮贸易,其他英国船只则退出,英国人的商机被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扼杀。当1834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这一垄断权之时,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黄金时代早已经过去。 除了俄国人和英国人外,西班牙人是争夺北美西北海岸的又一支重要力量。虽然1783年以后西班牙商人就开始通过马尼拉大帆船把海獭皮运到中国,但他们未能抓住机会成为西北海岸海獭皮贸易的有力竞争者。究其原因,西班牙的主要精力已经投入南美洲更为有利可图的矿产资源开发之中,它在北美西北海岸的利益主要是战略性的,“仅仅是希望维持西北海岸不开发的荒凉状态,以此作为反对外国势力向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渗透的缓冲带,因为那里才是其核心利益之所在。”(18)对于俄国人和英国人在西北海岸的探险和贸易活动,西班牙人一直充满警惕。1789年,西班牙与英国就努特卡湾(Nootka Sound)附近地区的归属问题而发生争端。直到1794年,两国才达成协议,规定双方都有权使用此地,但阻止第三方插足。(19)努特卡湾争端后,英国在北美西北海岸的势力日渐增强,但西班牙并未完全放弃对该地的权利。后来,美国正是借口1819年从西班牙手中继承了其在该地的全部权利,而与英国争夺俄勒冈地区。 除上述三方力量外,奥地利、葡萄牙、法国、瑞典和美国的商人也加入北美西北海岸海獭皮贸易的争夺中。美国商人最终脱颖而出,成为该贸易的主角。独立战争使美国人摆脱了英国的贸易束缚,可以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战争刚刚结束,波士顿商人的“中国皇后号”商船就于1784年2月驶离纽约港,前往中国开展贸易。“中国皇后号”开启了中美直接贸易的新时代,而北美西北海岸的海獭皮贸易则为美国商人指明了发展方向,因为他们正在为找不到输往中国的商品而发愁。 罗伯特·格雷船长早年就在波士顿商人的资助下,前往北美西北海岸收集海獭皮,然后运往广东。1792年5月,他在第二次前往西北地区收集毛皮的途中,航行到一条大河的河口,遂以其商船的名字将该河命名为哥伦比亚河,并宣布该河周围的土地归美国所有。(20)其实,早在1775年,西班牙航海家布鲁诺·德·赫克特(Bruno de Heceta)就曾发现了哥伦比亚河的河口,只是因为船员生病而没有继续探查。1788年,英国毛皮商人约翰·米尔斯曾对赫克特的探查结果进行验证,但未能找到传说中的大河,他因此把河口北岸的岬角命名为“失望角”。(21)罗伯特·格雷的航行不仅为美国人对俄勒冈地区的争夺提供了依据,也奠定了此后美国人同中国进行毛皮贸易的基本模式,即从波士顿购买商品,运到西北海岸同当地印第安人交换毛皮,然后将毛皮运到广东,在中国购买瓷器、丝绸、茶叶等货物,运回新英格兰进行销售。 凭借其吃苦耐劳和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美国商人逐渐排挤其他各国的势力,成为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主角。虽然美国商人运往中国的海獭皮的准确数量难以统计,但据估计,仅1806-1807年,波士顿商人向中国市场输出的海獭皮就达到14251张。随着海獭数量的减少,美国人在西北海岸收获的海獭皮从1802年的15000张,下降到1829年的600张。(22)当海獭皮贸易结束后,美国商人又转向海豹皮。从1793年到1807年,大约350万只海豹被杀。(23)当海豹皮供应不足之时,美国人又把内陆的海狸皮运往中国市场。据估计,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平均每年向广东输送3000—5000张海狸皮。(24) 总之,西北海岸海獭皮贸易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北美毛皮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北海岸的资源开发、印白关系和大国争霸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海獭皮贸易拉开了列强在俄勒冈地区争霸的序幕,俄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该地区毛皮贸易和领土争端之中。美国人虽然脱颖而出,逐渐成为贸易主角,但他们对哥伦比亚河周围领土主权的要求则充满变数,遭到了以西北公司(North West Company)为首的英国毛皮公司的强有力挑战。 二、英美在俄勒冈地区的博弈与对峙局面的形成 西北海岸海獭皮贸易只是整个北美洲毛皮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太平洋与落基山之间的广阔内陆地区,还蕴藏着丰富的海狸皮资源。19世纪初,随着东部毛皮资源的枯竭和毛皮边疆的西移,英国西北公司与美国毛皮商人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的太平洋毛皮公司(Pacific Fur Company)之间,围绕哥伦比亚地区毛皮资源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竞争,最终在俄勒冈地区形成了以哥伦比亚河为界南北对峙的局面。 为了同哈德逊湾公司抢夺萨斯喀彻温河流域的毛皮资源,蒙特利尔的毛皮商人联合起来,派遣商队到西北地区进行毛皮贸易,并最终在1779年建立一个松散的合伙组织——西北公司。(25)该公司曾多次重组,1821年被合并到哈德逊湾公司以前,它是在北美西北地区从事毛皮贸易的主要组织,也是后者的竞争对手,占到西北地区毛皮贸易份额的78%左右。(26)18世纪80年代,哈德逊湾公司每年输往内地的货物价值只有3万英镑,而同期西北公司则有16.5万—24.2万英镑。(27) 以西北公司为代表的毛皮贸易集团,本身就是在不断探索西北地区毛皮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就是扩张,西北公司的探险家不断把北美毛皮贸易的边疆推向西部。然而,面对从蒙特利尔不断往西北延伸的运输线和日益攀升的运输费用,西北公司迫切需要寻找一条从太平洋沿岸深入内地的运输通道。探险家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ackenzie)估计,西北公司差不多将一半费用花费在货物运输之中。(28)此外,为了攫取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收益,西北公司积极推进向西部探险,以期打通从大西洋跨越北美大陆到达中国的贸易路线。按照麦肯齐的说法:“通过连通两洋,在内陆及沿海和各处边界建立贸易站,从北纬48度直到北极,除去俄国人在太平洋沿岸占领的地区之外,整个北美大陆的毛皮贸易都将由我们控制。”(29)西北公司股东邓肯·麦吉利弗雷(Duncan McGillivray)也认为:“如果公司实施这一方案,不仅可以为英国工业品开辟一大片消费市场,而且还将为英帝国增添新的领土和人口。”(30) 西北公司探查落基山以西地区的使命最终落到了戴维·汤普逊(David Thompson)和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头上。1805-1811年,汤普逊对哥伦比亚河进行了探险,是全程探查该河的第一位白人,但却失去了率先到达河口的机会,从而使西北公司失去了优先占领哥伦比亚河口的时机。(31)弗雷泽从偏北方向探查通往太平洋的水道,他的探险队从皮斯河上溯,到达麦克洛德湖(McLeod Lake)后,沿着一条大河顺流而下,并最终在1808年7月1日到达河口。这条后来以其名字命名的河流多急流险滩,很难航行。(32)西蒙·弗雷泽的探险未能完成探查哥伦比亚河的任务,但却意外发现弗雷泽河流域蕴藏着丰富的毛皮资源,从而为西北公司在这一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北公司向俄勒冈地区的扩张,遇到了以约翰·阿斯特为代表的美国毛皮商的强有力挑战。阿斯特力图在北美大陆建立一系列贸易站,构筑横贯东西的毛皮贸易体系,并最终驱逐和取代加拿大人。(33)1809年,他向纽约州著名政治家德维特·克林顿(DeWitt Clinton)寻求支持,以组建美国毛皮公司,表示其目标是在“4—5年内掌控这一贸易,并将其势力伸展到西海岸”。(34)他的方案与美国政府向西部扩张的政治计划不谋而合,受到当权者的青睐。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大湖区到太平洋之间设立一系列毛皮贸易站。然而,19世纪初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圣路易斯毛皮商人的敌视,使阿斯特的这一计划难以实施。 西北海岸海獭皮捕猎的兴起以及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的探险报告,让阿斯特看到了实现其梦想的机会。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对俄勒冈地区觊觎已久,他在给刘易斯和克拉克的训令中,要求他们探查“可资用于商贸的跨越大陆的水路通道”。(35)刘易斯对西北地区的前景也很看好,建议在“哥伦比亚河口建立一个贸易站,开拓与中国的毛皮贸易”。(36)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阿斯特决定首先从西北海岸着手,夺取毛皮贸易的控制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1810年他组建了太平洋毛皮公司。 随后,该公司组织人员分两路前往俄勒冈地区:一路搭乘“汤昆号”(Tonquin),绕道合恩角,从水路前进;另一路由威尔逊·亨特(Wilson P.Hunt)率领,自圣路易斯出发,从陆路前往哥伦比亚河口。1811年3月22日,“汤昆号”率先到达哥伦比亚河口,上溯15英里后,其船员选择河北岸一处地点建立了一个贸易站,命名为阿斯特里亚(Astoria)。为了同西北公司竞争,贸易站的雇员按照阿斯特的既定政策,分兵两路,一路由“汤昆号”搭载24名船员,驶往努特卡湾,与当地印第安人交换毛皮,夺取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控制权。另一路则向东深入哥伦比亚河的支流,建立一系列贸易站,阻击西北公司的势头。(37)美国人终于赶在英国西北公司前面,取得了对哥伦比亚河口的控制权。 不过,“汤昆号”事件和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使阿斯特垄断俄勒冈地区毛皮贸易的努力化为泡影。其一,“汤昆号”船长与努特卡湾附近的印第安人发生矛盾,引起土著人的报复,最后,受伤的船员引爆船上的弹药,与“汤昆号”同归于尽。“汤昆号”的西北之行至此以悲剧结束,也断送了阿斯特夺取西北海岸海獭皮贸易的如意盘算。(38)其二是阿斯特里亚的易手。阿斯特里亚贸易站的设立,是对英国西北公司毛皮贸易垄断地位的挑战,自然遭到了后者的敌视,但西北公司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驱逐美国人。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爆发。虽然该战争含有美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成分,但主要还是英美殖民争霸的延续。假借1812年战争之势,西北公司派遣一小队人马前往阿斯特里亚,要求太平洋毛皮公司的雇员投降。守卫贸易站的大多是原来西北公司的老雇员,负责人邓肯·麦克多基尔(Duncan MacDougall)对老雇主仍然满怀热情,因而不愿意抵抗。加之太平洋毛皮公司的补给船没有按时到达,贸易站的员工最终决定放弃堡垒。1813年10月,阿斯特里亚被正式转手“卖给”加拿大人,改名为“乔治堡”(Fort George),存放的商品和毛皮也被低价卖给西北公司。(39)从表面上看,“阿斯特里亚不是被英国人占领的,而是根据商业协议转让给西北公司的”。(40)阿斯特试图垄断俄勒冈地区毛皮贸易的计划遭遇失败。 阿斯特里亚易手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后,美国政府颇为重视,遂责令其谈判代表团:“你们应该谨记:在战争开始前,美国在哥伦比亚河口有一个堡垒,对整条河流具有控制性作用,该贸易站应该被包括在条约之中,即它也是战争期间被(英国)占领的我方领土。”(41)英美1815年签订的《根特条约》规定:“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本条约签订后,从对方所获取的任何领土,除了特别提到的岛屿以外,一律即交还对方。”(42)但缔约双方对阿斯特里亚的去向并未做出任何特殊规定。美国方面认为它属于战争期间被夺走的领土,英方应该立即归还;而英国方面则认为这是从阿斯特的公司购买来的财产,不是战争期间夺取的敌方领土。因此,当美国方面要求英国交还阿斯特里亚的时候,遭到了对方的拒绝。约翰·阿斯特要求美国政府保护其重返哥伦比亚河口,也遭到了后者的拒绝。美国政府做出如此决策的原因在于:当时它脆弱的海军面临着许多远比收复阿斯特里亚更为重要的使命,如保护地中海的贸易、应对拉美革命、与西班牙的对抗等。(43)阿斯特得不到政府支持,从此对哥伦比亚地区失去兴趣,并退出了这一地区的毛皮贸易。(44)其商业冒险从政府的支持中受益,最终又因为不符合政府的利益而被牺牲。阿斯特退出哥伦比亚地区后,这里的毛皮贸易依然被以西北公司为代表的英国人牢牢地控制。 1817年秋,英美两国在哥伦比亚地区的纠纷出现新动向,双方形成对峙格局。该年10月,美国政府在“忘记”照会英国的情况下,派遣“安大略号”战舰到哥伦比亚河口,“收复”阿斯特里亚。得知此情的英国不仅未加阻止,相反还派员协助美方代表于1818年10月6日在乔治堡举行了一个升旗仪式,美国人重新夺回了阿斯特里亚。(45) 美国人重新占领阿斯特里亚,是它获取哥伦比亚河流域的转折点,英国在这一事件上的立场等于公开承认阿斯特里亚是在1812年战争中占领的敌方领土,而不是西北公司购买而来。1818年,英美就俄勒冈边界进行谈判,美方主张以北纬49度为界。英国则坚持哥伦比亚河以东按照北纬49度划界,以西则以该河为界。有学者据此认为:“英国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占领哥伦比亚河以南地区的可能性,而是坚持以此河为界。”(46)英国方案遭到美方的拒绝,此后,俄勒冈地区进入双方联合占领时期。 总之,经过19世纪初各自政府支持下毛皮商业集团之间的斗争,英美两国在俄勒冈地区形成了以哥伦比亚河为界隔岸对峙的局面。1821年,哈德逊湾公司兼并西北公司后,其贸易垄断权延伸到太平洋,在俄勒冈地区掀起了新一轮的贸易争霸,英美在落基山以西争夺经济与政治控制权的斗争进入新阶段。 三、哈德逊湾公司垄断俄勒冈地区毛皮贸易的尝试 哈德逊湾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以哈德逊湾周围地区为基地,同蒙特利尔的毛皮商人争夺加拿大西部的毛皮贸易。1821年,该公司兼并西北公司,成为加拿大西部毛皮贸易的唯一代表。北美毛皮贸易的形势到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两公司之间旷日持久的争夺,落基山以东地区的毛皮资源已现枯竭的迹象,而落基山以西的广阔地区仍然有待开发。在这种情形下,公司新任总督乔治·辛普森(George Simpson)在借鉴原西北公司贸易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概括来说,这些战略包括:根据不同地区贸易竞争的情况,推行毛皮动物保护或者灭绝式捕杀政策;探索和寻找新的毛皮产地,降低公司开支;鼓励各级商人自我供给和创新;除了毛皮外,寻找其他各种可以出口的商品。(47) 根据竞争形势的不同,哈德逊湾公司对于不同的毛皮产区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落基山以东地区由于此前的过度捕猎,毛皮资源已经大大减少。哈德逊湾公司既已取得贸易控制权,因而对毛皮资源的可持续性进行规划,推行适当的休养生息政策,将贸易站撤出,让猎物能有所恢复。1830年,哈德逊湾公司的会议纪要中记载道:“北方各地区严格限定捕获数量,不得超过公司依据三年的平均收获而确定的限额。”(48)1833年,公司进一步规定:“负责公司毛皮狩猎区域和贸易站的先生们,除了遭到反对的情形以外,应竭力阻止捕捉海狸幼崽和不合狩猎季节的猎捕行为。”(49)而落基山以西地区不仅毛皮资源丰富,而且还面临美国和俄国的经济竞争和政治纠纷,未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哈德逊湾公司在这里推行竭泽而渔的扩张政策,谋取贸易垄断权,力求在竞争到来前尽可能多地占有毛皮资源。 哈德逊湾公司积极向萨斯喀彻温河以外的西北地区探险和扩张。作为西北公司与哈德逊湾公司合并的一个意外收获,哈德逊湾公司获得了鲁伯特地区往西直到太平洋之间的广阔区域。(50)辛普森曾言:“我特别关注麦肯齐河流域的事务,因为那里比其他地区拥有更加广阔的可以开展贸易的空间。”(51)除了经济原因外,政治动因也是促使哈德逊湾公司抢先向西北地区扩张的原因之一。1821年,沙俄政府颁布一项新的法令,宣称从白令海峡到北纬51度之间的地区为俄国领土,外国商船不得擅入。(52)俄国的举动同时损害了美国和英国的利益,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和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共同向俄国交涉。英国的主要目标是:弗雷泽河河口到北纬55度之间对英国人开放;确保从新喀里多尼亚地区(New Caledonia)通向太平洋的任何一条河流在俄国控制区的通行权;麦肯齐河流域不允许竞争存在。(53)1825年,英国与俄国达成协议,乔治·坎宁表面上满足了俄国人控制西北海岸的要求,但却获得了从新喀里多尼亚地区流入太平洋的所有河流的通行权。(54) 正是出于毛皮贸易这种经济形式自身的扩张本性和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哈德逊湾公司开始向西北地区进行探险和扩张。1821-1853年,哈德逊湾公司组织了一系列对西北地区的探险。其中以约翰·麦克洛德(John McLeod)的探险最为著名,1823-1836年,他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多次探险,扩展了世人对西北地区的了解,也为公司开辟了大片新的毛皮产地。(55)通过不断向西北地区探险,哈德逊湾公司不仅有效阻击了俄国人,也为公司添加了大片的毛皮产地,确保它在与其竞争对手的争夺中能够处于上风。 哈德逊湾公司还排挤美国人,控制北美洲西北海岸的毛皮贸易。由于受到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影响,原来西北公司在同美国商人的竞争中一直处于下风。但随着海獭皮资源的枯竭,美国商人越来越多地从内地收购毛皮。到19世纪30年代甚至达到上万张,这令哈德逊湾公司难以容忍。(56)控制西北海岸的毛皮贸易不仅关系哥伦比亚地区的安危,也事关英国在整个北美西部的利益。在总督乔治·辛普森的支持下,哈德逊湾公司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来排挤美国人:(1)在沿海关键地点建立贸易站,高价收购印第安人的毛皮,并提供更好的商品与之交换。1831年,公司在纳斯河(Nass River)河口设立的辛普森贸易站成为西北海岸毛皮交易的一个中心,每年有3000—4000张毛皮在此处交易。1840年,这里的收入达到6964英镑。(57)(2)选派有经验的船长,定期在海岸巡航,同印第安人进行流动交易。哈德逊湾公司甚至还雇佣波士顿人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汽船“海狸号”来执行这一任务。虽然伦敦总部最初对于雇用美国人感到不解,但麦克尼尔很好地完成了公司交给的使命。从1825年到1849年,“海狸号”共收集到109389张毛皮,仅比辛普森贸易站少一些,后者共交易了173452张。(58) 哈德逊湾公司最终击退美国,保持对哥伦比亚地区毛皮贸易的垄断控制。哥伦比亚地区不同于加拿大西北部,这里不仅毛皮质量较差,运输路线漫长,更为重要的是还面临美国的激烈竞争。虽然约翰·阿斯特的美国毛皮公司暂时搁置了建立一条横贯大陆毛皮贸易体系的计划,但圣路易斯毛皮公司和落基山毛皮公司的商人们一直坚持向大山以西推进,试图将势力延伸到太平洋岸边。据说到1822年的时候,大约有1000名来自圣路易斯的毛皮贩子在密苏里河上游活动。(59)以威廉·阿什利(William Ashley)为首的圣路易斯毛皮商人沿着密苏里河不断向大山以西推进,并创建了利用白人猎手直接进山捕猎的山区集会制度。(60) 1824年,约翰·麦克洛林(John McLoughlin)被委任为哈德逊湾公司在哥伦比亚地区的贸易主管后,立即着手制定公司在这里的发展规划。其一,他把原来位于哥伦比亚河口的地区总部迁移到威拉米特河与哥伦比亚河交汇处的温哥华堡(Fort Vancouver)。这里成为哈德逊湾公司在太平洋地区的指挥中心。公司雇员约翰·邓恩(John Dunn)描述道:“温哥华堡是那个时代哈德逊湾公司在太平洋岸边的一个大型市场,也是公司员工和贸易的集会地。从落基山往西直到加利福尼亚之间所收集到的毛皮及其他商品都运到这里集中,然后发往伦敦。”(61)其二,探查和开拓毛皮资源仍然是他们在哥伦比亚地区的迫切任务。在麦克洛林的领导下,哈德逊湾公司以温哥华堡为中心向南方的加利福尼亚和东边的斯内克河地区拓展,与从落基山以东过来的美国商人争夺这一带的毛皮资源。哈德逊湾公司在对公司所垄断地区进行保护的同时,在英美争议地区推行著名的“焦土政策”(Trapping Clean)。乔治·辛普森认为:“一个枯竭的边疆是对付敌方贸易商人包抄我们的最好的自我保护策略。”(62)在辛普森的指示下,哥伦比亚地区贸易主管约翰·麦克洛林每年都派出两队装备精良的捕猎和交易商队,由原西北公司有经验的商人带领,其中一队向南,经威拉米特河到萨克拉门托河谷一带捕猎;另一路上溯哥伦比亚河,到斯内克河流域去收集毛皮。商队的规模一般为50人到100人不等。如亚历山大·罗斯(Alexander Ross)1823年所率领的一个远征队,就由41名来自东部和12名来自落基山以西的成员组成。(63) 由于毛皮资源非常丰富,斯内克河流域一直为美国毛皮商人所垂涎,因而成为哈德逊湾公司与美国商人对抗的最前沿,辛普森认为,斯内克河地区“海狸资源极其丰富,出于政治原因,我们要尽快摧毁它。”(64)从1823年到1829年,毛皮商人彼得·奥格登(Peter Ogden)多次带领远征队深入斯内克河,以竭泽而渔的方式夺取这一带的毛皮资源。根据麦克洛林的估计,从1824年到1846年,斯内克河远征为哈得逊湾公司带来了总共不下3万英镑的利润。(65)而哈德逊湾公司推行“焦土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斯内克河流域的毛皮资源快速枯竭。哈德逊湾公司的远征队在这一带的收获也由1826年的2099张毛皮,减少到1835年的220张,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价值。(66) 随着斯内克河流域竞争的加剧,哈德逊湾公司的眼光转向南方的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河谷、圣华金河谷和科罗拉多河谷都盛产海狸。从1828年到1843年,哈德逊湾公司先后派遣多支商队南下加利福尼亚去收集毛皮。它的远征队大约花了15年,耗竭了这一资源,总共在这里获得了大约1.7万张海狸皮。(67)根据美国人威廉·斯莱卡姆(William A.Slacum)的报告,哈德逊湾公司的捕猎队“踏遍每一条溪流,捕捉他们所见到的每一只海狸,即便毁灭这种资源也在所不惜……而进入这一地区的每一支美国商队都遭遇到失败或死亡的命运。”(68) 总之,通过积极的扩张政策,哈德逊湾公司在俄勒冈地区的商业竞争中成功地排挤美国人,取得了落基山以西地区毛皮贸易的控制权。1834年以前,11家美国公司插足这里的毛皮贸易。1826年,500—600名美国猎手在这一带活动。到1846年,大约只剩下50名美国猎手在此活动。(69)1839年,纳撒尼尔·韦斯(Nathaniel Wyeth)曾感叹:“到目前为止,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在大山以西还默默无闻”。(70)从1821年到1844年,哈德逊湾公司在哥伦比亚地区的毛皮产值由最初的25715英镑,上升到1833年的47619英镑,到1844年依然有40437英镑。其利润从最初的11622英镑,上升到1839年的28165英镑,到1843年依然有17200英镑。(71) 四、尘埃落定:哈德逊湾公司的退却与俄勒冈争端的解决 从1813年到1843年,英国的西北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在与美国毛皮商人的竞争中,几乎赢得了在哥伦比亚地区的每一场商业竞争,成功地将美国毛皮商人堵在落基山以东。但是,哈德逊湾公司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哈德逊湾公司在哥伦比亚地区面临比美国毛皮商人更加可怕的竞争对手,那就是不断涌入的美国移民。农业移民在东部就是毛皮贸易商的死敌,因为移民会砍伐森林,抽干溪水,破坏海狸的生存环境。对哈德逊湾公司来说,不断到达哥伦比亚地区的美国移民是对英美联合控制俄勒冈的严重威胁。 自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就开始对俄勒冈地区的殖民前景表现出兴趣。1830年,霍尔·杰克逊·凯利(Hall Jackson Kelly)到达哥伦比亚地区后,不仅对这里的农业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还四处宣扬哈德逊湾公司虐待印第安人,诋毁该公司的声誉。(72)1832年,在“俄勒冈殖民协会”的创办者纳撒尼尔·韦斯的带领下,21名殖民者向俄勒冈地区进发,最终有11人到达温哥华堡。(73)两年后,韦斯再次率领一队移民跨越大陆来到哥伦比亚地区,这次他代表的是“哥伦比亚渔业和商贸公司”,意图开发当地的渔业资源。(74)1836年,美国政府的代表威廉·斯莱卡姆访问了温哥华堡,并拜访了约翰·麦克洛林。斯莱卡姆回去后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盛赞威拉米特河谷农业开发的前景,呼吁美国占领直到北纬54度40分的全部地区。(75)此后,美国国内掀起了“俄勒冈热”,越来越多的美国移民开始向哥伦比亚地区迁移。当大批美国移民经俄勒冈小道到达哥伦比亚地区后,哈德逊湾公司负责该区的贸易主管约翰·麦克洛林与总督乔治·辛普森的意见发生了尖锐的分歧。辛普森要求全方位堵截美国人的势力,坚决把他们排除在哥伦比亚地区以外。而在麦克洛林看来,俄勒冈地区的毛皮贸易迟早会衰落,这里成为农业开发地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他对美国人在这里建立定居点持欢迎态度,并违反公司的指令,对那些贫困的移民予以资助和支持。(76) 哈德逊湾公司出于在哥伦比亚进行多元化经营的需要,也动员包括雷德河(Red River)殖民地部分居民在内的一些员工及其家属到西部定居。(77)到1844年,这一地区的加拿大人总数在1000人左右。(78)但经俄勒冈小道到来的美国移民在1843年后成倍增长,天平越来越向着美国一方倾斜。1842年从俄勒冈小道过来137人,1843年到达875人,1845年则有3000人到来。(79)1844年,麦克洛林甚至动用公司的资金支持美国移民,结果引起辛普森的强烈不满。麦克洛林因而去职并随后加入美国籍,在俄勒冈定居下来。 除了美国移民的压力外,到19世纪40年代,哈德逊湾公司还面临毛皮资源枯竭的困境。毛皮贸易是一种扩张性行业,其存在的基础就是不断发现新的毛皮产地。虽然辛普森也采取了一些毛皮动物保护策略,但收效有限,整个北美大陆的毛皮贸易正在走向终结。落基山东部的海狸皮资源很早就已经出现了枯竭的征兆。19世纪30年代,到西部旅行的埃德温·德尼格(Edwin Denig)在密苏里河上游注意到:“以前在这些溪流中,海狸数量众多,现在由于印第安人和白人猎手的捕捉,已经变得很少。”(80)山区猎手奥斯本·拉塞尔(Osborne Russell)1840年哀叹道:“海狸和野牛都已不见踪影,是白人猎手离开山区的时候了。”(81)继西北海岸的海獭皮资源枯竭后,哥伦比亚地区海狸皮产量也开始下降。1831年,这里出产的海狸皮达到21746张,而到1846年降至12958张。(82)早在1825年,哈德逊湾公司的高级主管戴维·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就在威拉米特瀑布边叹息道:“这里以前曾被认为是落基山以西最好的毛皮产地,如今海狸已经很少了,我就没见到一只活的。”(83)研究毛皮贸易的专家里奇指出:到19世纪中期,“从公司的主要毛皮产区所收获的毛皮都在持续下降。”(84)毛皮商人弗朗西斯·埃马廷格尔(Francis Ermatinger)1844年也抱怨:“哥伦比亚地区的贸易每况愈下……毛皮贸易必将走向终结。”(85) 不仅毛皮贸易的资源供应遇到了困难,其消费市场也出现了问题。毛皮贸易的基本动力是欧洲市场上对海狸皮制成的毡帽的消费需求,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欧洲的消费时尚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原本用途广泛的海狸毛皮制品被新的产品所代替,由工业革命所带动生产的丝帽成为消费新宠。1834年,毛皮大亨约翰·阿斯特也不得不承认:“我担心除了极好的以外,其他的海狸皮近期都不会好卖,看上去他们现在用丝帽来代替海狸皮制作帽子了。”(86)阿斯特从此退出了毛皮贸易行业。伴随市场需求减少而来的是毛皮价格的下跌,美国市场上海狸皮的价格已经从1809年最高峰的每磅5.99美元,下跌到1843年的每磅2.62美元。(87)流行数世纪的“海狸热”逐渐降温。 面对日益枯竭的毛皮资源和黯淡的市场前景,哈德逊湾公司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第一,在哥伦比亚地区积极拓展其他业务,进行多样化经营,以弥补毛皮贸易的不足。除了毛皮资源以外,当地还有茂密的森林、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鲑鱼资源。辛普森在1837年说道:“哥伦比亚河谷土壤肥沃,气候宜人,适宜耕种。我们正在考虑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有可能很快就能够建立起一个重要的业务部门,出口诸如羊毛、皮革、烟草以及各种谷物等。”(88)哈德逊湾公司随后建立了“普吉特湾农业公司”(Puget's Sound Agricultural Company),在哥伦比亚地区进行农业开发。(89)最初作为公司削减开支和自给供应的一部分,哥伦比亚地区的木材加工、畜产品养殖和鲑鱼捕捞也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公司向外出口的大宗产品。1836年,斯莱卡姆访问温哥华堡时候,发现该贸易站一年生产了8000蒲式耳小麦、5500蒲式耳大麦、6000蒲式耳燕麦、9000蒲式耳豌豆和14000蒲式耳土豆。(90)第二,针对美国人的竞争和毛皮资源衰竭的现状,哈德逊湾公司做出的另外一个重要决策就是战略收缩。在总督乔治·辛普森的要求下,哈德逊湾公司在19世纪40年代先后关闭了北方的多个贸易站,向麦肯齐河流域和育空地区的探险也逐渐停止。在南部,乔治·辛普森对于加利福尼亚的前景表示悲观,在他的要求下,哈德逊湾公司于1846年关闭了在旧金山的商铺。(91) 乔治·辛普森在19世纪40年代做出的最大战略收缩决定,是将公司在哥伦比亚地区的总部从温哥华堡向北迁移到维多利亚堡。1841年,辛普森在结束其伦敦之旅后到太平洋地区视察,考虑到英国和美国在俄勒冈地区的最终边界可能是49度纬线,他决定将地区总部从温哥华堡向北迁移到温哥华岛上,授权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在温哥华岛上选址建立新的地区总部。道格拉斯最终选定该岛南部一处优良的港湾,构建新的贸易中心。1843年,新贸易站建成,被命名为维多利亚堡(Fort Victoria)。(92)维多利亚堡的建立标志着哥伦比亚河谷毛皮贸易时代的结束,它代替原来的温哥华堡成为哈德逊湾公司在太平洋地区的中心。 最终,英美双方在1846年签订《俄勒冈条约》,结束了俄勒冈地区由两国共管的局面。在美国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英国人同意把哥伦比亚河与北纬49度之间的地区划归美国,哈德逊湾公司从此永久失去了49度以南地区毛皮贸易的控制权。自1821年与西北公司合并以来,哈德逊湾公司在北面成功抵制住俄国人的势力,在南面则成功瓦解了美国毛皮商人的势力,把他们赶出落基山以西,取得了哥伦比亚河流域毛皮贸易的控制权。然而,在1846年英美关于俄勒冈问题的谈判中,美国人依然取得了北纬49度与哥伦比亚河之间的三角地区,哈德逊湾公司输在了谈判桌上。理查德·麦凯认为:“哈德逊湾公司赢得了它所涉足的任何商业战争,但却输掉了1846年的政治战”。(93) 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一方面是美国移民和美国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势,另一方面则是英国的战略收缩。其实,即便是早期到来的美国移民,也一直被拒于哥伦比亚河南岸。但随着美国国内扩张主义势力的增强,“俄勒冈热”在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不断升温。面对不断涌入的美国移民,早在1843年,著名扩张主义者约翰·考德威尔·卡尔霍恩(John Caldwell Calhoun)就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在俄勒冈争端中放手,让当地居民决定该地最终的归属:“毫无疑问,推动我国人民从大西洋越过阿勒根尼山到达密西西比河的那股力量,同样会以更为强大的势力跨越落基山,抵达哥伦比亚河谷地,整个哥伦比亚河流域注定要被我国人民占据。这就是我们对这一地区的立场!”(94)1844年,著名扩张主义分子詹姆斯·波尔克参加总统竞选,公然打出了扩张主义的口号:“54度40分,要么就发动战争”,要求美国兼并整个俄勒冈地区。 面对美国的挑衅,英国无意开战,大英帝国有着许多远比哥伦比亚毛皮贸易更为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甚至哈德逊湾公司总督辛普森对这里毛皮贸易的前景也不看好。他在1826年回答英国政府的垂询时就表示:俄勒冈地区所出产的毛皮价值有限,每年仅有3万—4万英镑左右,只相当于曼彻斯特一个工厂的产值,(95)不值得为了一个即将消失的行业同美国开战,况且维多利亚堡的建立已经保证了英国海军在这一带的利益。即便没有落基山以西毛皮贸易的衰落这一外部因素,英国也有可能在俄勒冈地区向美国让步,但毫无疑问,哈德逊湾公司在哥伦比亚地区的战略退却令英国做出上述举动更为顺理成章。对英国来说,在俄勒冈问题上让步,主要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帝国荣誉”问题:“大英帝国可以失去领土,但绝不能失去荣誉和地位。”(96)而对美国来说,虽然国内扩张主义的“天定命运”呼声此起彼伏,来自中西部的许多扩张主义分子为了俄勒冈不惜一战,但对波尔克政府来说,与英国重新开战很难保证不会重蹈1812年战争的覆辙,况且因为兼并得克萨斯,美墨关系已经颇为紧张,因此,美国也不想真的与英国刀兵相见。(97)正是在这种氛围下,1846年,英美两国最终签署了分区占领这一地区的《俄勒冈条约》。条约规定:英美双方以北纬49度为界,此线以北归英国,以南归美国所有。至此,美国和加拿大在北美大陆上的49度分界线最终形成,哈德逊湾公司毛皮贸易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在俄勒冈地区的失败仅仅是哈德逊湾公司毛皮垄断权开始崩溃的第一步。它自1670年以来就拥有的毛皮贸易垄断权受到了加拿大东部政治家的挑战。面对美国随时可能对加拿大西部尤其是雷德河定居区的兼并,加拿大政治家要求尽快把这一地区纳入加拿大联邦的发展轨道。他们把哈德逊湾公司的贸易垄断看作实现自由贸易、移民定居西部和建立横贯大陆国家的阻碍。在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格兰维尔伯爵(Earl Granville)的一手主持下,哈德逊湾公司最终在1869年3月同加拿大联邦政府达成了鲁伯特地区转让协议。根据上述协议,加拿大联邦以30万英镑的价格(折合146万加元)取得哈德逊湾公司的鲁伯特地区。(98)鲁伯特地区的转让标志着哈德逊湾公司毛皮帝国的终结,从此以后,农业移民和边疆拓殖,而不是毛皮贸易成为加拿大西部发展的主旋律。 英美俄勒冈争端是欧洲列强数百年来围绕毛皮贸易而在北美洲进行殖民争霸的一个缩影。从16世纪欧洲殖民者来到北美大陆猎取毛皮的时代开始,毛皮贸易与领土争端就纠缠在一起。对当时的殖民者来说,毛皮是仅次于黄金等贵金属的牟利商品,虽然在北美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对于殖民争霸和控制印第安人却极为重要,以致自17世纪以后的“150年以来,欧洲人对西部内陆地区的兴趣几乎一直仅限于毛皮贸易”。(99)俄勒冈争端也不例外,它起源于西北海岸的海獭皮贸易,也随着哥伦比亚地区毛皮边疆的结束而最终解决。 俄勒冈地区的毛皮贸易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而是具有殖民争夺和大国政治博弈的性质。无论是约翰·阿斯特向杰斐逊和纽约著名政治家德维特·克林顿寻求帮助,还是哈德逊湾公司谋求英国政府的支持,都是利用边界争端这一政治因素谋求经济利益的典型。但是,只有当毛皮公司的经济利益同其本国的殖民利益相一致的时候,它们才会得到政府的帮助,否则就会沦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哈德逊湾公司在哥伦比亚地区虽然击败了所有的对手,但依然输在谈判桌上。与其微不足道的毛皮利益相比,英国更注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因此,俄勒冈争端也是老牌殖民帝国向新兴殖民者妥协的典型案例。 俄勒冈争端加速了毛皮贸易这一特殊的边疆开发模式在落基山以西衰落的步伐。从环境史的角度看,北美历史上的毛皮贸易是一种不可持续的边疆发展模式。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地方的毛皮贸易会随着当地毛皮资源的枯竭而终结。因此,为了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毛皮资源,毛皮商就需要不断探查和寻找新的毛皮产地,这也是毛皮边疆比农业边疆在地理探查方面作出较多贡献的一个原因。作为打击美国这一竞争对手的有效手段,哈德逊湾公司在与美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哥伦比亚河谷地、斯内克河流域以及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加利福尼亚等地,对毛皮资源推行毁灭式的“焦土政策”,力图赶在美国商人到来前捕光这里的毛皮动物,从而达到阻止美国商人插足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哥伦比亚地区毛皮贸易的兴衰是这种边疆开发模式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生动展示。 哈德逊湾公司在哥伦比亚地区的遭遇是北美历史上毛皮边疆向农业边疆转换的缩影。在北美西部开发史上,存在着一种边疆更替现象,即较浅层次的边疆开发会依次让位于较深层次的边疆发展。最初以开发现有资源为主的森林边疆、矿业边疆、毛皮边疆,会随着开发的深入而不断让位于需要较多资本和技术才能操作的农业边疆、城市边疆等,其实北美西部开发的历史就是一部边疆更替的历史。作为毛皮贸易代表的哈德逊湾公司对美国的农业移民采取坚决的抵制政策,但毛皮公司在源源不断涌入的美国农业移民面前不堪一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哈德逊湾公司从哥伦比亚地区的撤退是农业边疆对毛皮边疆的胜利。 ①Vernon F.Snow,"From Ouragan to Oregon,"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60,no.4(Dec.1959),p.441; S.A.Clarke,Pioneer Days of Oregon History,Cleveland:Arthur H.Clarke Company,1905,vol.Ⅰ,p.2. ②Robert G.Winters,Great Britain and the Oregon Question,Master Thesis Paper,Montana State University,1964,pp.1-2. ③俄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都宣称,本国的商人或探险家率先到达俄勒冈地区,这里的土地归本国所有。不过,对俄勒冈地区的争夺主要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展开。虽然双方都宣布对该地区拥有主权,争论的核心却是北纬49度与哥伦比亚河主河道之间三角地带的归属问题。 ④著名西部史学家弗雷德雷克·默克就俄勒冈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俄勒冈争端:英美外交与政治论文集》(Frederick Merk,The Oregon Question:Essays in Anglo-American Diplomacy and Politics,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他的研究奠定了英美俄勒冈争端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霍华德·琼斯与唐纳德·莱克斯特罗合著的《天定命运的序曲:1840年代英美关系》(Howard Jones and Donald A.Rakestraw,Prologue to Manifest Destiny: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840s,Wilmington:Scholarly Resources,Inc.,1997)也对英美俄勒冈争端的来龙去脉和最终解决进行了研究。近年来,关于俄勒冈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詹姆斯·波尔克总统期间美国的对外扩张及英美围绕俄勒冈展开的外交博弈。学界通常对波尔克的战争冒险政策持批判态度,萨姆·海因斯的《詹姆斯·K.波尔克与扩张主义的冲动》(Sam W.Haynes,James K.Polk and the Expansionist Impulse,New York:Pearson Education,Inc.,2006)则独辟蹊径,为波尔克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辩护。 ⑤北美毛皮贸易史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保罗·菲利普斯的《毛皮贸易》(Paul Chrisler Phillips,The Fur Trade,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61)对北美毛皮贸易的变迁进行了细致探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关于加拿大毛皮贸易最经典的著作,莫过于著名经济史学家哈罗德·因尼斯的《加拿大毛皮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论》(Harold A.Innis,The Fur Trade in Canada: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6)。加拿大西部史学家E.E.里奇在毛皮贸易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其《哈德逊湾公司史》(E.E.Rich,Hudson's Bay Company 1670-1870,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61)对哈德逊湾公司的早期活动进行了详细梳理。关于美国毛皮贸易的著作也很多,著名史学家海勒姆·马丁·奇腾登的《美国远西部毛皮贸易》(Hiram Martin Chittenden,The American Fur Trade of the Far West,Stanford:Academic Reprints,1954)对美国西部毛皮贸易的兴衰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成果至今仍为学者们广为借鉴。理查德·麦凯的《大山以西的交易:1793-1843年英国在太平洋的毛皮贸易》(Richard Somerset Mackie,Trading Beyond the Mountains:The British Fur Trade on the Pacific 1793-1843,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97)对西北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为首的英国毛皮贸易商在北美西北地区的活动进行了研究。詹姆斯·吉布森的《海獭皮、波士顿商船与中国商品:1785-1841年西北沿岸海上毛皮贸易》(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2)则是研究西北海岸海獭皮贸易的优秀作品。虽然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毛皮贸易与俄勒冈争端相互脱节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⑥根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雷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边疆理论,美国历史上存在一条从东向西不断移动的边疆。所谓边疆,既可以指“文明”与“野蛮”交界处的一片区域,也可以指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如农业边疆、毛皮边疆、矿业边疆等。本文采用的边疆一词,主要指北美西部开发史上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关于特纳的边疆理论,参见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21. ⑦John Meares,Voyages Made in the Years 1788 and 1789,From China to the North West Coast of America,London:J.Walter,1790,p.241. ⑧Meriwether Lewis and William Clark,edited by Bernard Devoto,The Journals of Lewis and Clark,Boston:Houghton-Mifflin Company,1997,p.326. ⑨Nathaniel Portlock,A Voyage Round the World,but More Particularly to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London:Printed for John Stockdale and George Goulding,1789,p.382. ⑩Peter Lauridsen,Vitus Bering:The Discoverer of Bering Strait,Chicago:S.C.Griggs & Company,1889,pp.177-178. (11)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13. (12)James R.Gibson,"The Russian Fur Trade," in Carol M.Judd and Arthur J.Ray,eds.,Old Trails and New Directions:Papers of the Third North American Fur Trade Conferenc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0,pp.217-230. (13)关于俄美公司的历史变迁,参见P.A.Tikhmenev,A History of the Russian-American Company,ed.and trans.Richard A.Pierce and Alton S.Donnell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8,partⅠ,chapter l-5. (14)John Barrow,The Life,Voyages,and Exploits of Admiral Sir Francis Drake,London:John Murray,1843,pp.132-151. (15)James Cook and James King,A Voyage to the Pacific Ocean,vol.Ⅱ,London:W.and A.Strahan,1784,pp.270,278. (16)James Cook and James King,A Voyage to the Pacific Ocean,vol.Ⅲ,London:W.and A.Strahan,1784,p.437. (17)Nathaniel Portlock,A Voyage Round the World,but More Particularly to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p.4. (18)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18. (19)William Ray Manning,The Nootka Sound Controversy,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4,pp.469-470. (20)H.W.Scott,"Beginnings of Oregon:Exploration and Early Settlement at the Mouth of the Columbia River," The Quarterly of 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vol.5,no.2(Jun.1904),p.103. (21)John Meares,Voyages Made in the Years 1788 and 1789,From China to the North West Coast of America,p.167. (22)Paul Chrisler Phillips,The Fur Trade,vol.Ⅱ,p.57. (23)Benjamin Morrell,A Narrative of Four Voyages to the South Sea,North and South Pacific Ocean,New York:J.J.Harper,1832,p.130. (24)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62. (25)Gordon Charles Davidson,The North West Compan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18,pp.9-11. (26)这里的西北地区是针对加拿大而言,指萨斯喀彻温河流域及其更远的地区。不同于美国历史上的西北地区,后者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俄亥俄河以北、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 (27)Gerald Friesen,The Canadian Prairies:A Histo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7,p.62. (28)Alexander Mackenzie,Voyages from Montreal,on the River St.Laurence,through the Continent of North America,to the Frozen and Pacific Oceans,vol.Ⅰ,New York:W.B.Gilley,1814,p.xxiv. (29)W.Kaye Lamb,ed.,The Journals and Letters of Sir Alexander Mackenzie,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417. (30)转引自James P.Ronda,"Astoria and the Birth of Empire," Montana:The Magazine of Western History,vol.36,no.3(Summer 1986),p.31. (31)David Thompson,Columbia Journals,ed.Barbara Belyea,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4,pp.35-178; George Bryce,The Remarkable History of the Hudson's Bay Company,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1902,pp.134-141. (32)E.E.Rich,The Fur Trade and the Northwest to 1857,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1967,pp.198-199. (33)Elizabeth L.Gebhard,The Life and Ventures of the Original John Jacob Astor,Hudson:Bryan Printing Company,1915,pp.154-155. (34)Paul Chrisler Phillips,The Fur Trade,vol.Ⅱ,p.270. (35)Thomas Jefferson,"To Captain Meriwether Lewis," in George Tucker,The Life of Thomas Jefferson,Thir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vol.Ⅱ,London:Charles Knight & Co.,1837,p.577. (36)Samuel L.Mitchill,A Discourse on the Character and Services of Thomas Jefferson,New York:G.C.Carvill,1826,p.29. (37)Washington Irving,Astoria,or,Anecdotes of an Enterprise beyond the Rocky Mountains,New York:G.P.Putnam,1863,pp.95-105. (38)Hiram Martin Chittenden,The American Fur Trade of the Far West,vol.Ⅰ,pp.176-181. (39)Hiram Martin Chittenden,The American Fur Trade of the Far West,vol.Ⅰ,pp.215-238. (40)H.W.Scott,"Beginnings of Oregon:Exploration and Early Settlement at the Mouth of the Columbia River," p.109. (41)Walter Lowrie and Matthew St.Clair Clarke,eds.,American State Papers,Foreign Relations,vol.Ⅲ,Washington,D.C.:Gale and Seaton,1832,p.731. (42)Walter Lowrie and Matthew St.Clair Clarke,eds.,American State Papers,Foreign Relations,vol.Ⅲ,p.746. (43)Frederick Merk,The Oregon Question:Essays in Anglo-American Diplomacy and Politics,pp.9-12. (44)Washington Irving,Astoria,or,Anecdotes of an Enterprise beyond the Rocky Mountains,Appendix,pp.508-509. (45)Katharine B.Judson,"The British Side of the Restoration of Fort Astoria," The Quarterly of 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vol.20,no.3(Sep.1919),pp.243-260; Katharine B.Judson,"British Side of the Restoration of Fort Astoria-Ⅱ," The Quarterly of 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vol.20,no.4(Dec.1919),pp.305-330. (46)H.W.Scott,"Beginnings of Oregon:Exploration and Early Settlement at the Mouth of the Columbia River," p.107. (47)Richard Somerset Mackie,Trading Beyond the Mountains:The British Fur Trade on the Pacific 1793-1843,p.40. (48)"Minutes of Council,1825," in Edmund Henry Oliver,ed.,The Canadian North-West:Its Early Development and Legislative Records,vol.Ⅰ,Ottawa:Government Printing Bureau,1914,p.654. (49)"Minutes of Council,1833," in Edmund Henry Oliver,ed.,The Canadian North-West:Its Early Development and Legislative Records,vol.Ⅱ,Ottawa:Government Printing Bureau,1914,p.704. (50)哈德逊湾公司在1670年成立之时,获得了英王授予的所有流入哈德逊湾的河流所流经土地的商业和殖民权力,因公司的首任总督是鲁伯特王子,故这片土地又被称为鲁伯特地区。 (51)Frederick Merk,ed.,Fur Trade and Empire:George Simpson's Journal,1824-1825,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04. (52)Alaskan Boundary Tribunal,Proceedings of the Alaskan Boundary Tribunal,Convened at London,Under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Great Britain,Concluded at Washington,January 24,1903,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1903,p.10. (53)Theodore J.Karamanski,Fur Trade and Exploration:Opening the Far Northwest 1821-1852,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3,p.36. (54)Augustus Granville Stapleton,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George Canning,vol.Ⅲ,London:Printed for Longman,Rees,Orme,Brown,and Green,1831,pp.121-125. (55)Theodore J.Karamanski,Fur Trade and Exploration:Opening the Far Northwest 1821-1852,pp.42-51. (56)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62. (57)Richard Somerset Mackie,Trading Beyond the Mountains:The British Fur Trade on the Pacific 1793-1843,p.131. (58)Richard Somerset Mackie,Trading Beyond the Mountains:The British Fur Trade on the Pacific 1793-1843,p.139. (59)Clarence A.Vandiveer,The Fur Trade and Early Western Exploration,Cleveland:Arthur H.Clark Company,1929,pp.200-203. (60)传统上毛皮贸易一般是白人毛皮商人用商品从印第安人猎手那里交换毛皮,而威廉·阿什利则完全抛开印第安人猎手,雇佣白人猎手到西部山区狩猎毛皮,然后公司定期派遣商队进山到约定的地点同前者交换,落基山区的毛皮集会成为西部每年的一个盛事。具体情况参见David J.Wishart,The Fur Trade of the American West 1807-1840:A Geographical Synthesis,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79,pp.121-127; Hiram Martin Chittenden,The American Fur Trade of the Far West,vol.I,pp.264-281. (61)John Dunn,History of the Oregon Territory and British North American Fur Trade,London:Edwards and Hughes,1844,p.142. (62)Eric Jay Dolin,Fur,Fortune,and Empire:The Epic History of the Fur Trade in America,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10,p.285. (63)Alexander Ross,The Fur Hunters of the Far West:A Narrative of Adventures in the Oregon and Rocky Mountains,vol.Ⅱ,London:Smith,Elder & Co.,1855,p.6. (64)Frederick Merk,ed.,Fur Trade and Empire:George Simpson's Journal,1824-1825,p.46. (65)Frederick Merk,The Oregon Question:Essays in Anglo-American Diplomacy and Politics,pp.97-98. (66)John S.Galbraith,The Hudson's Bay Company:As an Imperial Factor 1821-1869,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7,p.95. (67)John S.Galbraith,"A Note on the British Fur Trade in California,1821-1846,"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24,no.3(Aug.1955),pp.258-260. (68)John Forsyth and William A.Slacum,"Slacum's Report on Oregon,1836-1837," The Quarterly of 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vol.13,no.2(Jun.1912),p.189. (69)John McLoughlin,"A Narrative of Events in Early Oregon Ascribed to Dr.John McLoughlin," The Quarterly of 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vol.1,no.2(Jun.1900),p.193. (70)Richard G.Beidleman,"Nathaniel Wyeth's Fort Hall,"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58,no.3(Sep.1957),p.250. (71)Richard Somerset Mackie,Trading Beyond the Mountains:The British Fur Trade on the Pacific 1793-1843,p.252. (72)John McLoughlin,"A Narrative of Events in Early Oregon Ascribed to Dr.John McLoughlin," p.195. (73)John B.Wyeth,Oregon; or a Short History of a Long Journey from the Atlantic Ocean to the Region of the Pacific,Cambridge:Printed for John B.Wyeth,1833,p.10; John McLoughlin,"A Narrative of Events in Early Oregon Ascribed to Dr.John McLoughlin," p.194. (74)W.Clement Eaton,"Nathaniel Wyeths Oregon Expedition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no.2(Jun.1935),pp.101-113. (75)John Forsyth and William A.Slacum,"Slacum's Report on Oregon,1836-1837," p.204. (76)Samuel R.Thurston et al.,"Correspondence of John McLoughlin,Nathaniel J.Wyeth,S.R.Thurston,and R.C.Winthrop,Pertaining to Claim of Doctor McLoughlin at the Falls of the Willamette:The Site of Oregon City," The Quarterly of 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vol.1,no.1(Mar.1900),p.106. (77)John C.Jackson,Children of the Fur Trade:Forgotten Métis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Missoula:Mountain Press Publishing Company,1995,pp.92-111. (78)Neil M.Howison,"Report of Lieutenant Neil M.Howison on Oregon,1846:A Reprint," The Quarterly of 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vol.14,no.1(Mar.1913),p.24. (79)E.E.Rich,The Fur Trade and the Northwest to 1857,pp.280-281; Richard Somerset Mackie,Trading Beyond the Mountains:The British Fur Trade on the Pacific 1793-1843,p.318. (80)Edwin Thompson Denig,Five Indian Tribes of the Upper Missouri:Sioux,Arickaras,Assiniboines,Crees,Crows,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61,p.10. (81)Osborne Russell,Journal of a Trapper,or Nine Years in the Rocky Mountains,1834-1843,Boise:Syms-York Company,Inc.,1921,p.124. (82)James R.Gibson,Farming the Frontier:The Agricultural Opening of the Oregon Country,1786-1846,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5,p.201. (83)David Douglas,Journal Kept by David Douglas during His Travels in North America,1823-1827,London:William Wesley & Son,1914,pp.140—141. (84)E.E.Rich,Hudson's Bay Company,1670-1870,vol.III,p.495. (85)Lois Halliday McDonald,Fur Trade Letters of Francis Ermatinger,Glendale:The Arthur H.Clark Company,1980,p.261, (86)Hiram Martin Chittenden,The American Fur Trade of the Far West,vol.I,p.364. (87)James L.Clayton,"The Growth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the American Fur Trade,1790-1890," Minnesota History,vol.40,no.4(Winter 1966),pp.214—215. (88)James R.Gibson,Farming the Frontier:The Agricultural Opening of the Oregon Country,1786-1846,p.75. (89)E.E.Rich,The Fur Trade and the Northwest to 1857,p.279. (90)John Forsyth and William A.Slacum,"Slacum's Report on Oregon,1836-1837," p.186. (91)Anson S.Blake,"The Hudson's Bay Company i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vol.28,no.2(Jun.1949). (92)相关情况参见Alexander Begg,History of British Columbia:From Its Earliest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Time,London:Sampson Low,Marston & Company,1894,pp.154—166. (93)Richard Somerset Mackie,Trading Beyond the Mountains:The British Fur Trade on the Pacific 1793-1843,p.314. (94)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Public Documents,1s1 Session of the 29[th] Congress,vol.I,Washington,D.C.:Ritchie & Heiss,1846,p.153. (95)T.C.Elliott,"The Northwest Boundaries(Some Hudson's Bay Company Correspondence)," The Quarterly of 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vol.20,no.4(Dec.1919),p.335. (96)Wilbur D.Jones and J.Chal Vinson,"British Preparedness and the Oregon Settlement,"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22,no.4,1953,p.353. (97)Sam W.Haynes,James K.Polk and the Expansionist Impulse,pp.142—153. (98)George Bryce,The Remarkable History of the Hudson's Bay Company,p.455. (99)Gerald Friesen,The Canadian Prairies:A History,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