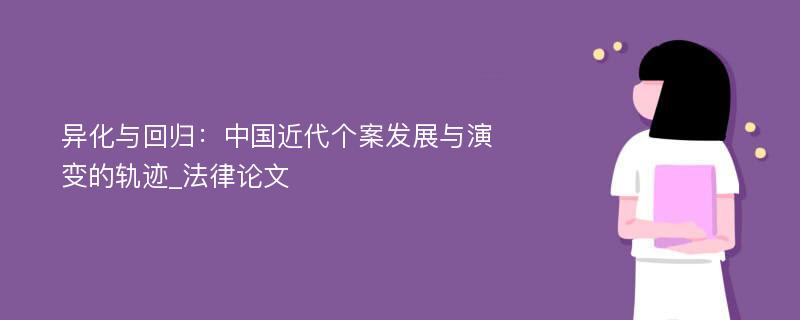
异化与回归:近代中国判例发展演变的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判例论文,轨迹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76(2016)01-0054-11 近代判例制度是我国判例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判例制度构建的初步尝试。学界对此已有所关注,并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既有对近代以来各时段如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判例制度的研究,也有以整个近代判例制度为对象的研究。学界有关北洋政府大理院判例制度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对大理院判例制度的产生原因、特点、功能、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①而有关国民政府时期判例制度的研究则比较薄弱,成果相对较少。②将近代判例制度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乔丛启的《中国近代司法判例制度》及武乾的《中国近代判例制度及其特征》。前文将近代判例制度划分为北洋政府(1912-1927年)大理院时期的初创和形成、国民政府(1928-1949年)最高法院时期的确立和完善两个阶段,论述了民国判例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沿革、作用及历史地位等三个方面的问题。③后文则论述了近代中国判例制度在体裁、汇编体例、适用方式和效力等微观方面的特征。④ 但是现有研究基本上是静态的制度剖析,而对近代以来判例制度初创、发展、成熟的进程以及制度内容从异化到回归的动态变化关注不够。并且,研究对象局限于民国判例制度,即使是以近代判例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两篇论文也仅是对北洋政府时期及国民政府时期判例制度的探讨,而对清末法律确立的判例制度有所忽视。另外,对近代判例制度某些微观层面上的细节问题,现有研究也没有深入挖掘和详细考证,导致对近代判例制度认识上的偏差和误读。本文试图从历史整体的视野考察近代中国判例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揭示近代中国引入和设立判例制度的动因、本旨以及判例制度具体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总结其利弊得失,为我国当前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历史借鉴。 一、清末判例制度的初创及其本原样态 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以成文法为主体。清末移植西方法制,仍是以德国、日本等成文法国家为模范,而未取法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但当时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已出现融合趋势。⑤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日本等法制先进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刊行判例,⑥为各级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提供参考,以统一法律解释。⑦在此世界法制潮流下,清末立法者借鉴大陆法系判例制度,初步创设了中国本土的判例制度。 (一)判例的创制主体 清末改革官制,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大理院者,一国之最高司法官厅也。从其本务言之,即关于法律之适用及解释,接受上告案件,以合议而为裁判者也。”⑧可见,大理院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审判统一法律解释。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906年12月12日)颁布的《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参照日本1890年《裁判所构成法》第48条“大审院裁判,于法律之点所表意见,羁束下级裁判所诉讼一切之事”,⑨规定“大理院之审判,于律例紧要处表示意见,得拘束全国审判衙门”,⑩赋予大理院通过判决解释法律的权力,引入了判例制度。 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10年2月7日)颁布的《法院编制法》第35条规定:“大理院院卿有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之权,但不得指挥审判官所掌理各案件之审判”,(11)明确赋予大理院卿以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权。大理院可通过发布判决录、解答法律疑问两种方式行使该权。“大理院为民事或刑事之判决,通行其判决录于全国之下级审判厅,使供参考;有时下级审判厅提出解释律例上之质疑于大理院,则复以大理院之意见,使供参考是也”。(12)大理院判决录中所载的民刑事判决即是判例。大理院由此取得判例创制权。 《法院编制法》还规定高等审判厅也有上告案件终审权,并准用大理院审理上告案件的相关规定。《法院编制法》第32条规定:“第三十五条、三十七条、四十四条、四十五条及八十条之规定,准用之于高等审判厅之上告案件”。故《法院编制法》第35条可以置换为:“高等审判厅厅丞有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之权,但不得指挥审判官所掌理各案件之审判”。高等审判厅亦有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之权,有权创制发布判例。 清末《法院编制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判例创制权及其配置,仅规定了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之权,判例创制权是隐含于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权之中的。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权被配置给享有上告终审权的大理院及高等审判厅,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权的配置与上告终审权的配置相一致。这是因为上告审为法律审,“上告案件系对于法律点之上诉,以统一解释法律为其目的”,(13)掌有上告案件终审权的司法机关本即具有统一解释法令职能。法律解释的统一则依靠判例的创制、刊行。上告终审司法机关的判决对法律发布意见,成为下级审判机关的模范,实现法律解释的统一。因而,掌有上告终审权的司法机关当然享有统一解释法令权,统一解释法令权当然包含判例创制权。(14) (二)判例的创制程序(15) 大理院民刑事各庭通过普通审判程序作出的判决首次对相关法律发表意见,则该判决即成为判例(或称“成案”)。后来之判决若欲变更判例需经由“总会审判”程序。经由大理院总会审判程序作出的判决如变更旧有成案,也会创制新判例。 大理院总会审判程序在两种情形下启动:一是大理院各庭审理上告案件,如解释法令之意见与本庭或他庭成案有异,由大理院卿依法令之义类,开民事科或刑事科或民刑两科之总会审判之;大理院分院各庭审理上告案件,如解释法令之意见与本庭或他庭成案有异,应呈请大理院开总会审判之。(16)审判总会的具体召开程序为:须有各科推事三分之二以上列席方能开议;由大理院卿总司其事,会长由大理院卿自己担任或命推丞及推事中资深者一人担任;参加总会审判的人员应依次发表意见;(17)总会之决议应由列席推事过半数之意见议决;(18)大理分院各庭推事提出意见书时,(19)应列入决议之数;除该项意见书外,大理院卿应预先征集大理院分院各庭推事之意见书列入总会决议之数。大理院审判总会不公开进行,不允许公众旁听,参加会议人员应对整个会议过程及各人员所发表意见保守秘密。 大理院判例还应系统编纂,以判决录形式刊行。但清末法律并没有规定判例的具体编纂刊行方式,亦未在实践中形成一套固定做法。依当时人的观点,“判决例既非法律,亦非命令,即所谓案件汇览之类”,(20)判例应以编纂成书的案件汇览形式颁行。案件汇览应包括基本的案件事实及判决全文。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判决录应收录判决全文。 (三)判例的效力及功能 根据《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大理院之审判,于律例紧要处表示意见,得拘束全国审判衙门”的规定,大理院判例对全国各级审判机关具有约束力。但《法院编制法》取消了此一规定,判例的效力趋于模糊。既然判例是大理院统一解释法令的形式之一,是大理院卿行使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权的产物,则判例的效力根据应在于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权。(21) 首先,大理院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权的效力是有限的,即“不得指挥审判官所掌理各案件之审判”。各级审判官基于司法独立原则有权依法独立审判,大理院不能干涉各级审判机关具体案件的审判。大理院判例没有强制各级审判官遵从之效力,故大理院判例的效力不是绝对的。但“大理院及分院劄付下级审判厅之案件,下级审判厅对于该案,不得违背该院法令上之意见”,(22)对于被劄付之下级审判厅,大理院的判决意见是有绝对拘束力的。其次,大理院判例的效力是事实上的,而非法定的。“大理院为最高审判衙门,既有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之权,名义上虽不能指挥审判官所掌理各案之审判,然自实际观之,其势力之伟大实有以羁束以下各级审判厅者”。(23)大理院判例所表达的法律意见,下级法院应当参考,否则,其判决即有被大理院撤销之虞。大理院也应遵守自身判例,保持前后判决的一致,如变更判例需经由特定程序。因此,大理院判例具有事实上的相对拘束力,发挥着统一法律解释的功能。 高等审判厅的判例对于其管辖地域范围内的下级审判厅应具有事实拘束力,具有统一一省之内各级审判厅法律解释的功能。但此一高等审判厅之判例对于其他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是否具有拘束力并不明确。而且大理院判例与各高等审判厅判例的关系亦没有相关规定。 二、北洋政府时期判例制度的发展及异化 《法院编制法》颁行不久,清廷即告覆灭,大理院并未实际上创制、刊行判例。(24)但清末初步引入和创设的判例制度却成为近代中国判例制度的滥觞。民国成立后,大理院职掌最高审判权和统一解释法令权,开始创制、发布判例,编纂判例要旨汇览。清末初创的判例制度得以发展,但也开始发生异化,背离了其本原样态。 (一)大理院垄断判例创制权 北洋政府时期,大理院垄断判例创制权。1914年大理院统字第105号解释称:“诉讼通例,惟最高法院判决之可为先例者,始得称为判决例”,(25)其他各级法院的判决皆不得称为判例。虽然北洋政府时期修正后的《法院编制法》依然保留了清末《法院编制法》关于高等审判厅审理上告案件及变更判例准用大理院相关规定的条文,但大理院不认为高等审判厅有权创制判例,判例创制权的实际分配与法律规定不相符合。 判例创制权的集中统一是最高司法机关垄断法律解释权逻辑的必然结果。清末学者即主张由大理院作为唯一之终审机关专任解释,“学者谓终审在法律点,而大理院之设,专为解释法律。故宜用一头制,是亦谋统一之道也”,(26)否定高等审判厅拥有终审权和法律解释权。民国学者也对《法院编制法》将统一解释法令权分配给高等审判厅提出了批评:“所谓统一法令解释之最高法院,除大理院外,又有数十之高等厅公与其事。非仅高等厅已也,地方厅内之高等分厅亦得参加解释法令之意见(参照《法院编制法》第三十二条),不惟解释歧出,法庭之威信有损,亦且保护不一,人民之权利受亏”。(27)根据这种逻辑,若高等审判厅有权发布判例解释法律,则致使解释不一;为维护法律解释之统一,故不允许高等审判厅创制判例。 (二)判例异化为判例要旨 大理院民刑事各庭对法律有所解释、补充的重要判决以及经大理院民事庭、刑事庭或民刑两庭总会审判程序变更旧判例而作出的判决都应是判例。但根据1923年大理院统字第1809号解释:“院判在判例要旨汇览刊行前,未经采入汇览者,即不成为例”,(28)大理院民刑事判决需选编入判例要旨汇览,公开刊行才可成为判例。这不仅缩小了大理院判例的范围,还将本应全文刊行的判例异化为具有抽象规范性质的判例要旨。(29) 章宗祥任大理院长时(1912年7月26日至1914年2月20日)曾令部员“就大理院判例钩玄提要,成判决要旨一书,由《司法公报》临时刊发”。(30)《大理院判例要旨》择取1912年9月至1914年12月的判例要旨勒为成编。(31)此为大理院编辑判例要旨之始。(32)所谓判例要旨是指判决书中具有规范意义的核心字句,编辑判例要旨是为满足当时法律不备条件下司法审判的规范需要。《大理院判例要旨》“凡例”即称:“现在法规尚未完备,判例之刊迫不容缓,为应急需,先辑要旨”。(33)在编纂形式上,判例要旨按照法典章节条文顺序编排,“民律及民诉依有效之现行律及民律民诉草案章节编辑,刑律及刑诉依刑律条文及刑诉草案章节编辑”;在判例要旨上方“加小字眉标,以为旨目”,“并于眉标旁低二格用小字注明某年某字某号某件”。(34)该判例要旨奠定了民国时期判例要旨的编纂体例。 此后,大理院专门制定了《大理院判例汇览及大理院解释文件汇览编纂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以规范判例汇览的编纂形式。《规则》第2条规定,判例编纂体裁分为上下两栏,下栏为裁判原文,上栏为判例要旨及参考。(35)此种体裁虽详备,但操作起来异常繁难。故《规则》第11条规定:“大理院判例汇览得为提前发行起见,暂行省略第二条所列上栏参考门第四至第七之款目”。(36)在规范层面,并未规定可以省略裁判全文,判例编纂体裁仍应包括裁判原文。但1916年大理院判例汇览编辑处按照《规则》所编辑的《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二年度)》,却将裁判原文及参考部分一并省略,仅收录判例要旨及裁判年份、字号,(37)形同法典。 1918年公布的《大理院编辑规则》规定判例汇览编纂格式为:眉批、要旨、年份、号次四部分,(38)不包括裁判原文。1919年大理院编辑处“节取大理院自民国元年改组至七年十二月底之裁判文先例”,编为《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共三卷)。1924年12月出版的《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续集》“就大理院民国八年一月至十二年十二月之裁判成例,节取编辑”。(39)正续两编判例要旨汇览基本按《大理院编辑规则》规定的形式编纂。具体而言,一则判例要旨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为眉批,中为要旨,下为年、字、号。 判例要旨汇览固然简明扼要,易于查阅援引,在法律不完备的历史条件之下,为各级法院的裁判悬以准绳,填补了制定法的缺位。但弊端也极为明显:被抽离具体案情的判例要旨成为抽象规范,“词意简略,事实法律,不便对比,非专研法学者未易了解”。(40)创设判例的本意在于为此后类似案件提供参照,但判例要旨将原案事实、判决理由省略,“或则缩千百言于数行,或则断章取义,截句成章,原意已失,而与本案联络关系,则不可得而睹”,(41)使后来之审判无从比照,背离了判例制度的本旨。 (三)大理院判例效力及功能的异化 理论上,北洋政府大理院判例仅具有事实上的相对拘束力。“大理院以判决解释时,对于本案有拘束下级法院之力”,(42)对其他案件及此后同类案件没有拘束力。“下级审判厅虽下与大理院判决例相异之判决,仍可得完全之效力”。(43)但实际上,大理院判例具有如同法律般的强大效力。《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二年度)》例言称:“本汇览所辑各条,不惟于法令解释足资参考,所采条理、惯例,不啻有法之效力”。(44)当时学者亦称大理院判例“在实际上与法律有同一效力”。(45) 因当时法律不备,大理院判例成为司法裁判的主要或重要依据。“民国肇兴,因各种法律之未制备,司法官审理案件时,每苦无所依据,将援用旧律欤?已为时代潮流所不许;将欲准据新法律欤?然而草案则有之,未足与言法典也。”(46)在此特殊法制条件下,有必要建立一种法律补充机制,“此种不完备之救济方法即所谓大理院判例”,“因彼时既乏法律可以依据,又无成例可以遵循,故不得已每逢一案即成一判例。”(47)大理院判例遂成为司法裁判的主要依据,“当夫诉讼问题发生,执法者类据大理院之判例而解决之”。(48)直隶高等审判厅即称:“本厅对于他案受缺席判决而误向本厅声明控告者,皆援照大理院判例,发回原审判衙门,声请回复原状”。(49)结果,大理院判例获得了形同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此种判例之产生,即不啻大理院之立法矣”。(50)判例制度转而承担起创制规范的立法职能。 三、国民政府时期判例制度的成熟与回归 国民政府时期,法律明确规定了变更判例权以及判例的作出程序,判例创制有了法定依据和程序规范,标志着近代中国判例制度的成熟。但随着成文法的完备、统一解释法令制度的发达及权力分立观念的深化,最高法院判例不复有大理院判例的权威和地位,渐趋回归大陆法系判例制度的本来样态。 (一)最高法院判例创制程序的完备 国民政府时期,最高法院享有判例创制权,(51)判例创制程序已臻完备。最高法院判例产生于两种情形:一是审理无先例可供援引的案件而创设新判例;二是虽有先例可供援用,但认为不适合而变更之,从而创设新判例。以上两种情形下,判例作出程序有所差异。 1.审理无先例可援案件而创设判例 最高法院各庭审理无先例可以援引的案件而作出的判决,是对法律进行创始性解释。该项判决可供以后审判参考,成为判例。1929年《最高法院处务规程》第27条规定:“凡判决无判例可援者,应由庭长命书记官摘录要旨备查,并通告各庭。”(52)1935年《最高法院处务规程》第31条规定:“各庭新判例应由庭长命书记官摘录要旨,将裁判书印本分送各庭庭长推事,并选登《司法公报》”。(53)1948年《最高法院办事细则》第36条亦规定:“各庭庭长认其本庭裁判应著以为例者,应命书记官摘录要旨送交文书科汇辑,并将裁判书印本分送各庭庭长推事。”(54)可见,最高法院各庭可自行作出新判例。 2.变更旧判例而创设判例 国民政府时期,法律明确规定变更判例之权由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院执掌。1928年《司法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司法院院长经最高法院院长及所属各庭庭长会议议决后行使统一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之权。”(55)1947年宪法公布之前的历部《司法院组织法》皆有此规定。1929年《最高法院处务规程》第28条规定:“凡从前有判例可援用而庭长认为不适用者,应由民事庭或刑事庭开总会议议决变更之。”(56)但变更判例之决议须经最高法院院长及司法院院长赞同,才能成为新的判例。若最高法院院长或司法院院长不赞同,则按照《司法院统一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规则》第10条的规定召集变更判例会议。1932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法院组织法》第25条规定:“最高法院各庭审理案件,关于法律上之见解与本庭或他庭判决先例有异时,应由院长呈由司法院院长召集变更判例会议决定之。”(57)1947年宪法颁行后,统一解释法令由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进行,变更判例则仍由司法院院长召集的变更判例会议进行。(58)但实际上司法院的变更判例会议未曾召集过。(59)最高法院各庭可自行召开总会决议变更判例,而无需经由司法院变更判例会议,甚至不需要最高法院院长、司法院院长的赞同。(60) 最高法院除将判例全文登载《司法公报》外,还编纂判例要旨。最高法院判例要旨在编纂体裁上与大理院判例要旨基本一致,无特别创新。1934年最高法院判例编辑委员会将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的判例汇编为《最高法院判例要旨》。1943年最高法院又将1932年至1940年所作判例加以汇集,编成第二部《最高法院判例要旨》,此种判例要旨“仍只系几句抽象的决定,其形式固与法律条文无异”。(61) (二)最高法院判例效力的回归 关于最高法判例的效力,在当时存有争议。最高法院自认其判例有拘束下级法院之效力。(62)有学者亦认为“最高法院之判例,有拘束全国下级法院之效力”,(63)“判例与法典有同等效力”。(64)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自法律观点言,判决例实无拘束下级法院之效力;自理论言,亦不宜使判决例有拘束下级法院之效力;更自立法例言,大陆法系之国家,亦无以判决例拘束下级法院之先例”。(65)但反对者亦承认判例事实上的拘束力,“然非谓下级法院推事事实上即可置判决例不顾。判决例事实上的效力,固亦不容忽视也”。(66)判例的拘束力是相对的,下级法院可以拒绝适用,“如该判例适用不当或违反法律时,下级法院仍可拒绝适用而另依照法律条文判决之”。(67)抛却大理院判例形同法规的强大效力,而承认判例事实上的相对拘束力是向大陆法系判例制度的回归。 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判例可以作为各级法院的裁判依据。1935年江苏兴化县政府依据最高法院判例对“葛夔堂与胡懋森等不动产买卖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按卖方应先尽亲房之习惯有背于公共秩序,不能认有法之效力,经最高法院民国十九年上字第一七一零号著有判例。……而其先尽原告亲房原业先买之旨亦与卖买自由原则有背,更与上开判例抵触。原告主张难认有理”。(68)事实上,“各下级法官仍多因袭最高法判决例而为同类案件判决准据”。(69)1932年《法院组织法》废弃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四级三审制,而实行三级三审制,所有案件都有上诉至最高法院之可能,下级法院倘无更强理由即不遵从判例,其判决被上诉至最高法院时很可能被否定。“苟某下级法官经手之案件,上诉后原判决多遭废弃,于其个人考成上,难免不生影响”。(70)因此,下级法院不得不遵循最高法院判例。 (三)最高法院判例制度功能及地位的回归 最高法院判例不复有如同北洋政府大理院判例的权威和地位。国民政府陆续颁布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宪法等基本法律,形成了以“六法全书”为核心的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无需经由判例立法。学理上,“一般通说,多反对判例法,其理论的依据,在于立法、司法、行政之三权分立,以为适用法律之司法机关,不得制定法律。”(71)随着“五院”体制的确立,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分立,各院分工明确,不容司法机关以判例立法。但最高法院判例的统一法律解释功能受到重视。1932年《法院组织法》取消了最高法院分院的设立,因为“最高法院判决有统一全国法令解释之功用,设立多数分院,易致分歧”;(72)实行三级三审制,“上诉达于最高法院而后已,盖以求法规适用上解释之统一”。(73)判例的功能由立法回归其原本的法律解释功能。 民国时期,判例与解释例并称为“判解”,在一般适用者心目中具有同等地位。在法律文本上,司法院的“统一解释法令权”与“变更判例权”连为一体规定为“统一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之权”,具有形式上的同等地位。但1947年宪法仅规定了司法院的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权,却没有涉及变更判例权。在清末《法院编制法》中同为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权运用方式的解释例与判例,至此已有天壤之别。司法院在宪法授权下创制的解释例获得了法律效力,成为统一法律解释的法定形式,而判例只具有事实上的相对拘束力,在事实上发挥着统一法律解释的作用。判例依靠最高审判权及审级制度发挥统一法律解释功能,是大陆法系判例制度原本的运行方式。 四、余论:近代判例制度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当前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将判例因素引入社会主义法制中,预示着判例制度的复苏。但案例指导制度还远未成熟定型,在理论及具体操作层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完善当前的案例指导制度应从近代中国判例制度发展演变的历程中汲取经验教训。 第一,准确定位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即案例指导制度是着重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还是填补法律漏洞、发展法律?当前案例指导制度严守立法、司法的权力界限,侧重于法律适用的示范和指导,而无规范补充、发展功能。通过指导性案例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确是正当做法,但由立法机关立法并进行解释的做法已为多数国家所抛弃,允许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中解释法律而“造法”有其必要。抽象、固定的法律适用于具体、流变的社会生活,需要判例制度发挥规范补充功能。司法机关以判例补充、发展法律有其合理性。正如民国时期学者所言,“以解释抽象法律及应用于特殊情形上之责任归司法院及其附属机关,确系正当办法,以其较立法者切近事实界也。然则凡法律未规定者,司法院必用判例及解释例之方法补充之,法律不合逻辑不合实际界者,亦必用判例及解释例之方法纠正之,庶几立法与司法两者之间,能声气互通,各尽其事。”(74) 第二,不宜赋予指导性案例以强制拘束力,但应建立起切实有效的指导性案例效力实现保障机制。若赋予最高司法机关判例以强制力,下级法院必须遵守和适用,则各级法院唯最高法院判例是从,法律解释唯一,这将限制法律规范的丰富和发展,违背了判例制度补充法律不足不备、促进法律发展的本意。但为实现指导性案例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功能,应加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并予以制度性保障。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对下级司法机仅具有参考意义上的指导力,对于何种条件下可以违背指导性案例,违背指导性案例精神的司法行为如何处理均未有规定。在我国四级两审的审级制度下,单纯依靠最高法院的上诉审来维护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并不现实。将违背指导性案例原则和精神作为上诉理由,由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违背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进行审查,并报最高司法机关复核,不失为保障指导性案例效力实现的一种可行办法。 第三,要充分尊重各级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不仅将其具有典型性的判决吸纳为指导性案例,还应允许下级法院参与指导性案例的变更。民国时期,最高审判机关垄断判例创制权,其法律解释成为唯一权威解释,抑制了其他各级法院参与法律解释的积极性,不利于法律发展。“最高法院判例,在法律上见解是否允当,原可自由评论。事实审法院亦未始不可加以研讨,与最高法院作歧异之见解。而最高法院见下级审之判例,较为允当,亦可采下级法院判例上之见解,据为变更自己判例之张本。彼此相互贡献,岂不日有进益?”(75)下级法院在判决中表达的法律意见不必与上级法院相同,对于最高法院的判例亦不必一律遵守,如有更强理由,可自行作出具有创见的法律解释来变更判例。我国指导性案例的来源较为广泛,各级司法机关的案例皆可被采择为指导性案例。最高法院应充分注意下级法院对旧指导性案例的变更,及时将其吸纳为新的指导性案例。通过指导性案例的不断更新,实现法律的不断发展,保持既定法律对社会生活的适应和有效规范。 第四,指导性案例的创制、变更及编纂刊布等操作技术应尽快出台规范性文件予以完善。民国最高审判机关的判决经专门人员再三评定,认为确实符合学理、论说精当,才著为判例;判例变更程序有详细的法律规定;设有专门的判例编辑部门选编、刊行判例,判例的编纂体裁有成熟的固定做法。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实行未久,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刊布、变更等的具体程序及方式尚不明确。2015年6月2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规定了指导性案例失效的两种情形:“(一)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相冲突的;(二)为新的指导性案例所取代的”,采取的是自然失效主义,指导性案例的失效并无需特别的变更程序。如何判断指导性案例与新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冲突?由何种主体作出失效决定?新案例取代旧案例是否需要特别程序?以上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明确。随着指导性案例的增多,应及时对失效的指导性案例进行清理,并广布周知,以免出现如民国司法中“亦有不知前例已经后例变更,仍复用前例,以为裁判之者”的现象。(76) 最后,处理好案例指导制度与司法解释制度的关系。近代中国的法律解释制度是双重体制,即判例解释与解释例解释并行。这在世界其他国家并不多见。西方法制先进各国,如德国、法国等,皆是由最高法院及行政法院通过判例形式进行法律解释。“最高法院担任普通法律之解释,行政法院担任行政命令及规则之解释,而其解释行为又不能于争端事实发生前,由某方呈文要求之,其解释结果如何通常非求之判例中不可”。(77)近代中国的法律解释形式除判例外,尚有解释例,且解释例可以在争端发生前,由相关主体呈请解释。最高司法机关针对法律解释请求作出的解答效力强大,异化为抽象立法,而作为法律解释本来形式的判例却与统一法律解释分离。结果,解释例与判例都背离了自身的本初功能。这是我国司法解释制度与案例指导制度进行分工时应注意避免的。 ①乔丛启在《北洋政府大理院及其判例》一文中论述了大理院判例的产生原因、特点、作用以及历史地位。参见乔丛启:《北洋政府大理院及其判例》,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6期。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源盛的《民初大理院司法档案的典藏整理与研究》一文分析了大理院判决例的风格、在法学方法上的运用及历史意义。参见黄源盛:《民初大理院司法档案的典藏整理与研究》,载《政大法学评论》1998年第59期。黄氏的另一篇论文《民初大理院(1912-1928)》则探讨了大理院民事判例的性质、功能。参见黄源盛:《民初大理院(1912-1928)》,载《政大法学评论》1998年第60期。张道强的《大理院判例、解释例——民国初期的司法机关“立法”》一文对民初大理院判例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必然、运作方式及特征,以及大理院判例的立法功能进行了论述。参见张道强:《大理院判例、解释例——民国初期的司法机关“立法”》,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8卷专辑。 ②张道强的《民国判例:功能、必要性与特点——以南京政府刑事特别法判例为例》一文专以国民政府时期判例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国民政府时期判例的法律功能类型、存在的必要性以及与普通法系判例相比较下的特点。参见张道强:《民国判例:功能、必要性与特点——以南京政府刑事特别法判例为例》,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9期。 ③参见乔丛启:《中国近代司法判例制度》,载《法律史研究》编委会、《中日文化交流丛书》编委会合编:《中外法律史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1-457页。 ④参见武乾:《中国近代判例制度及其特征》,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 ⑤当时学者已认识到,“现时则有折衷之势,大陆诸国渐次尊重判决例,英美此时又稍有论难判决例者”。参见[日]矶谷幸次郎:《法学通论》,王国维译,金粟斋译书社1902年版,第32页。 ⑥所谓“东西各国凡最高审判衙门均刊有判决录,以揭示案由,模范全国也”。参见王士森:《法院编制法释义》,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第29页。 ⑦当时各国最高审判机关承担着统一法律解释的职能。“近世诸国皆设上告裁判所,以期解释之一律”([日]奥田义人:《法学通论》,卢弼、黄炳言译,政治经济社藏版1910年,第227页)。“至求法意之统一,则设最高法院使专任解释”(王黻炜:《法律解释论》,载《司法公报》1912年第2期)。法国最高法院有权“撤销下级法院错误适用法律的判决,并有权作出正确的解释”(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德国最高法院“为了法律的正确实施,不但有权审查下级法院的判决,撤销错误判决,作出正确的指示,而且相应地还可以对被错判的案件进行‘复审’”([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日本的大审院“为日本独一无二之最高裁判所,乃得达其法律解释归一之目的”,其判决例所发表的法律意见于诉讼一切事件可羁束下级裁判所(参见吴柏年:《裁判所构成法》,法政编辑社1905年版,第21、49页)。 ⑧边守靖:《法院编制法》,版本不详,第42页。 ⑨[日]菱谷精吾:《裁判所构成法》,熊彦、俞成铣译,长沙政法学社1913年版,第51页。 ⑩《大理院审判编制法》第19条。《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载《东方杂志》190年第3期。 (11)政学社印行:《大清法规大全》,考正出版社1972年版,第1822页。 (12)王士森:《法院编制法释义》,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第29页。沈宝昌在其所著《法院编制法释义》中亦言:“必应处置之权其范围不外二种:(一)大理院以其判决录颁发各级审判衙门,则下级各审判衙门有不能不加以参考之义务;(二)下级审判衙门如有法律上之疑义,质问于大理院之时,则大理院亦有不能不附以意见作为答复之义务。”(沈宝昌:《法院编制法释义》,嘤鸣社1911年版,第66页) (13)沈宝昌:《法院编制法释义》,嘤鸣社1911年版,第53页。 (14)但大理院、高等审判厅有权发布判例以统一法律解释并不必然地否定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的判例创制权。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有权独立适用法律,对法律作出自己的解释,其判决也可以成为供自身或下级审判机关此后审判同类案件的参考。只是大理院、高等审判厅的判例因其上告案件的终审权及统一法律解释权的保障而具有较高的权威和地位。 (15)高等审判厅判例创制程序准用于大理院判例创制程序,在此仅论述大理院的判例创制程序,高等审判厅判例创制程序自可明了。 (16)参见《法院编制法》第37、44条,政学社印行:《大清法规大全》,考正出版社1972年版,第1822-1823页。 (17)资格较浅者先发表意见,资格较深者后发表意见;资格相同者,年少者先发表意见;审判长最后发表意见。参见《法院编制法》第77条,政学社印行:《大清法规大全》,考正出版社1972年版,第1826页。 (18)在进行议决时,如果出现三说及以上均不能过半数时,关于金额者,将各说按照金额之多少排列,居中之说作为过半数通过;关于刑事案件,则将各说按不利于被告的刑罚的重轻为序进行排列,居中之说作为过半数通过。参见《法院编制法》第78条,政学社印行:《大清法规大全》,考正出版社1972年版,第1826页。 (19)《法院编制法》第44条第2款规定“其分院各该推事应送意见书于大理院”,即掌理上告案件审判的大理院分院法官解释法令意见与本庭或他庭意见有异而请求大理院开总会审判时,应出具自身的法律意见书。 (20)《资政院旁听录》,载《申报》1910年12月11日第13595号第18版。 (21)对民国时期判例的性质和效力,学界历来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大理院判例为统一解释法令的形式。章宗祥在为《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二年度)》所作序言中称:“夫大理院为最高法院,有统一解释法律之权,其所平亭比当即为法律之正解,而成下级之楷模。然则此判决录者固全国法官所共瞻式,非但供学者参稽而已”,将大理院创制的判例归为统一解释法令权之行使,刊行判例的目的是统一法律解释(参见大理院判例汇览编辑处:《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二年度)》,京师第一监狱1916年版,第2页)。张正学认为“惟依《法院编制法》第三十五条前段大理院长有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之权,是故大理院解释法令之判决例,经大理院长许可刊布者,固得解为基于大理院长解释权之作用,有拘束下级法院之效力”(参见张正学:《法院判断民事案件适用之法则》,载《法律评论》1928年第249期)。黄源盛认为“大理院解释法令的判例,经大理院长许可刊布者,固得解为基于大理院长解释权的作用,而有拘束下级法院的效力”。(参见黄源盛:《民初大理院(1912-1928)》,载《政大法学评论》1998年第60期。)亦有学者持反对意见,刘恩荣认为“解释文件系大理院司法行政文件,以大理院长名义行之。而裁判书系大理院纯粹司法文件,以大理院各庭之名义行之。若判例有统一解释之权,则各庭侵大理院长之权”(参见刘恩荣:《论大理院之解释与其判例》,载《法律评论》1924年第32-37期)。刘远谋认为解释例与判例“产生之机关与方法,既不相同,固不容强谓大理院之判决例,包括在大理院长法令解释权范围内”(参见张远谋:《论判决例之效力》,载《法律评论》1934年第531期)。但双方都没有追溯大理院判例制度设立的本旨,忽视了宣统元年《法院编制法》将判例作为统一解释法令之形式这一事实。 (22)《法院编制法》第45条,政学社印行:《大清法规大全》,考正出版社1972年版,第1823页。 (23)沈宝昌:《法院编制法释义》,嘤鸣社191年版,第70页。 (24)参见韩涛:《晚清大理院——中国最早的最高法院》,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51页。 (25)郭卫编:《大理院解释例全文》,上海会文堂书局1931年版,第70页。 (26)许世英、徐谦等:《考察司法制度报告书》,《国风报》1911年第15期。所谓“一头制”,即无论初级审判厅还是地方审判厅进行第一审,皆由大理院进行第三审终审。 (27)韩玉辰:《法院编制法私议》,文益印书局1914年版,第4页。 (28)郭卫编:《大理院解释例全文》,上海会文堂书局1931年版,第1043页。 (29)除判例要旨汇览外,大理院判决的刊行方式还有发布判决全文、判例要旨两种。根据1920年《大理院办事章程》第52条的规定:“各庭庭长认案件之裁判为重要时,得商请院长将该裁判文登载《政府公报》,并将副本送交关系公署”,大理院可择取其重要判决全文登载《政府公报》予以公布。《政府公报》设有“判词”一栏,刊载大理院裁判全文。按照192年《大理院编辑处规则》规定,《大理院公报》可登载大理院可成为新例、变更旧例或其他有登载必要的民刑事裁判,而且应将判例要旨及判决全文一并登载。《大理院公报》于1926年创刊后,共发行3期,登载1925年至1926年间大理院民刑事判例147个。但《大理院编辑处规则》同时规定,大理院还应按年编辑判例要旨汇览。 (30)大理院判例汇览编辑处:《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二年度)》,京师第一监狱1916年版,第2页。 (31)该《大理院判例要旨》分为上册民律刑律之部、下册诉讼律之部两册,刊载于1915年《司法公报》第43期增刊3及第47期增刊4。 (32)有学者认为1919年大理院才公布其第一部判例要旨汇编,“1919年12月,北洋政府大理院公布了该院的第一部判例要旨汇编——《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后被称为正集)”(参见武乾:《中国近代判例制度及其特征》,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民国判例集的汇编,最早见于大理院1919年12月刊行的《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参见陈兴良主编:《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这些说法并不准确。 (33)《大理院判例要旨·凡例》,载《司法公报》1915年第43期增刊3。 (34)《大理院判例要旨·凡例》,载《司法公报》1915年第43期增刊3。 (35)参考部分包括7项内容:(1)同例异例裁判号次;(2)现行法条;(3)解释文件号次及汇览页次;(4)惯例;(5)前清旧法及草案条文;(6)外国法条及判例;(7)学说。 (36)参见《大理院判例汇览及大理院解释文件汇览编纂规则》相关规定。大理院判例汇览编辑处:《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二年度)》,京师第一监狱1916年版,书末附录。 (37)与之前《大理院判例要旨》及此后的《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不同,该判例要旨汇览没有眉批部分。 (38)《大理院编辑规则》,载《司法公报》1918年第93期。 (39)《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续集·例言》,载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全书》,上海会文堂书局1932版,第856-857页。 (40)王宠惠:《改良司法意见》,载《东方杂志》1920年第20号。 (41)沈天保:《编纂最高法院判例要旨汇览之商榷》,载《法律评论》1933年第27期。 (42)夏勤、郁嶷编:《法学通论》,朝阳大学出版部1919年版,第49页。 (43)陈承泽:《法院编制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33页。 (44)大理院判例汇览编辑处:《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二年度)》,京师第一监狱1916年版,例言。 (45)郑天锡:《大理院判例研究》,载《法律评论》1924年第38期。 (46)张远谋:《论判决例之效力》,载《法律评论》1934年第11期。 (47)余棨昌:《民国以来新司法制度——施行之状况及其利弊》,载《法律评论》1928年总第244期。 (48)夏勤:《论判例》,载《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5年第2期。 (49)《直隶高等审判厅意见书:陆静泉因赵郎轩股东纠葛声明再抗告由》,载王树荣编:《判决录》,1913年印行,第212页。 (50)余棨昌:《民国以来新司法制度——施行之状况及其利弊》,载《法律评论》1928年总第244期。 (51)根据1932年《法院组织法》,高等审判厅不再具有上告案件终审权和统一解释法令权。最高法院独掌上告案件终审权和判例创制权,改变了北洋政府时期判例创制权实际分配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状况。这也与清末《法院编制法》由上告终审机关掌有判例创制权的配置原则相一致。 (52)《最高法院处务规程》,载《司法公报》1929年第7期。 (53)《最高法院处务规程》,载《司法公报》1935年第50期。 (54)司法院1948年9月公布的《最高法院办事细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三十二)-16。 (55)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页。 (56)《最高法院处务规程》,载《司法公报》1929年第7期。 (57)《法院组织法》,载《法令周刊》1932年第123期。 (58)随着《大法官会议规则》(1948年9月15日大法官会议通过)的施行,统一解释法令由大法官会议进行,《司法院统一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规则》宣告失效,变更判例会议的召集程序无法可依。国民政府迁台后,1952年9月15日又出台了《司法院变更判例会议规则》。 (59)直至国民政府退据台湾之后的1977年6月1日,“司法院”召开判例变更会议作出司法院“例变”字第一号议决,才有了第一次判例变更。需要说明的是抗日战争期间,汪伪政权司法委员会的统一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会议曾对大理院及南京政府最高法院的判例进行变更(参见《司法委员会变更判例》,载《中华法令旬刊》1940年第1期)。汪伪政府成立后,司法院亦曾依据《司法院统一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规则》召开变更判例会议进行判例变更[参见《司法院变更判例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载《司法公报》(汪伪)1942年第57期]。 (60)1935年《最高法院处务规程》第29条规定:“各庭为统一各庭法律上之见解或有其他必要情形,得以推事三人以上之提议开民事庭或刑事庭或民刑事庭总会议决之”。《最高法院处务规程》,载《司法公报》1935年第50期。 (61)阮毅成:《怎样建设中国本位的法律》,载《政治评论》1935年第156-157期。 (62)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编:《三年来之最高法院》,1934年印行,第97页。 (63)江庸:《最高法院限制报章杂志刊载判例》,载《法律评论》1933年第8期。 (64)沈天保:《编纂最高法院判例要旨汇览之商榷》,载《法律评论》1933年第27期。 (65)张远谋:《论判决例之效力》,载《法律评论》1934年第11期。 (66)张远谋:《论判决例之效力》,载《法律评论》1934年第11期。 (67)何任清:《法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73页。 (68)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等编:《民国时期江苏高等法院(审判厅)裁判文书实录》(第5册),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69)张远谋:《论判决例之效力》,载《法律评论》1934年第11期。 (70)张远谋:《论判决例之效力》,载《法律评论》1934年第11期。 (71)刘子崧、李景禧编:《法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7页。 (72)郑保华:《法院组织法释义》,上海法学编译社1936年版,第66页。 (73)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8页。 (74)芮沐:《司法院解释例之检讨》,载《中华法学杂志》1937年第5-6期。 (75)永晖:《判例解释例》,载《新法学》1948年第5期。 (76)永晖:《判例解释例》,载《新法学》1948年第5期。 (77)芮沐:《司法院解释例之检讨》,载《中华法学杂志》1937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