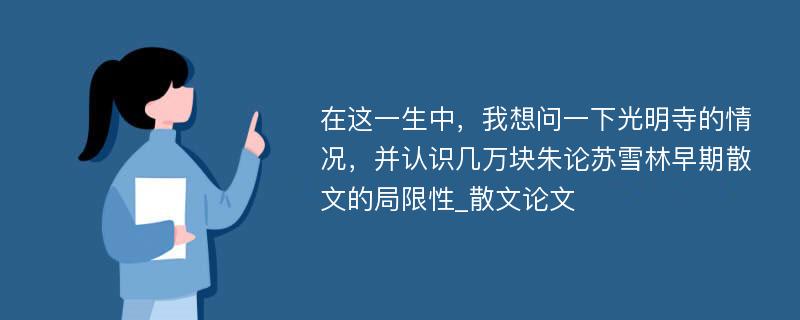
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扉几万重——谈苏雪林早期散文之局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明论文,局限性论文,散文论文,万重论文,知隔朱扉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雪林原名梅,笔名绿漪、杜若、杜芳、天婴、野隼、老梅等,安徽省太平县岭下村人,1897年出生于浙江瑞安,辛亥革命后随家人返回祖籍,先后就学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北京高等女子师范,法国海外中法学院、里昂国立艺术学院,旧国后执教于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安徽省立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是一位集教育、治学、创作于一身的优秀学人。她的散文“细腻、温柔、幽丽、秀韵”(注:阿英《苏绿漪小品序》,见《现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市古籍书店1990年8月版。), 曾为中国现代散文的艺术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过去的许多年里,由于政治的原因,苏雪林的名字很少在大陆文学史上出现,而台湾文学界却称她的创作成就是“后来居上”、“矫然独步”、“首屈一指”(注:陈敬之《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台湾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率先摒弃政治偏见,出版了《苏雪林散文选》,1994年,恰值老人虚年百岁华诞前夕,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四卷本《苏雪林文集》,两书的编者均高度评价了苏雪林的早期散文创作。紧接着,苏雪林以超越百岁的高龄回归故里探亲,传奇般的消息传开之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希望了解苏雪林其人其文,同时也迫切地希望了解对她的创作的中表评价。
为此,笔者认真阅读了这位百岁老人六十余年前的散文作品《棘心》、《绿天》及有关评论,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表达一个真诚的见解:事实上,六十年前以阿英为代表的几位评论家对苏雪林散文创作所作的简约评价是十分恳切的:“苏绿漪的小品文,虽富有田园诗人生活的清趣,然而,在各方面,她是没有什么独创的,她不能代表一个倾向,只能作为冰心倾向的一个支流”(注:阿英《苏绿漪小品序》,见《现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市古籍书店1990年8月版。), “在苏绿漪笔下所展开的姿态,只是刚从封建社会里解放下来,才获得资产阶级的意识,封建势力仍然相当的占有她的伤感主义的女性的姿态”(注:方英《绿漪论》,见《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局1983年版。)。也许这评价不免令人感到遗憾,但笔者认为这是历史的真实,我们对任何一位作家的批评都不应随着政治或其他人的因素随意拔高或贬低。
苏雪林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以老祖母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家教极严,女孩儿们正当的日常功课只是刺绣。与此同时,她的母亲又是一个“自幼在专制压力下长大”,“嫁到杜(苏)家,她又立志要做个好媳妇,相夫教子(注:苏雪林《棘心》,见《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的模范旧式妇女。 这一切深深地影响了苏雪林。尽管小苏梅自幼就是个淘气女孩,为求学肯以性命相拼(注:苏雪林《棘心》,见《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年4月版。),但进入大学以后,即便是在五四时期的女高师这样的环境中,她仍然表现出了封建传统女性的固有特色:面对身边同学们对两性恋爱的热烈追求,她没有任何兴味,“一则呢,她幼小时便由家庭定了婚,没有另外和别人发生恋爱的可能;二则呢,她诞生于旧式家庭中,思想素不解放,同学们虽在大谈并实行恋爱自由,她却从来不敢尝试”(注:苏雪林《棘心》,见《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年4月版。)。身处文学革命的高潮之中,“她这个适在此时此际才开始就读于国文系的‘女学士’,则不仅在讲堂上所接受的仍然是说文的研究与唐诗的格律这一类课程,即是在笔头上所写出的,也依然是‘之、乎、者、也、矣、焉、哉’这一套老调儿。她所以如此,乃是由于她在中国旧文学的窠臼里寝馈日久,熏染甚深,而又一时难于恝然弃置不顾之故。……”(注:陈敬之《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台湾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自称“五四人”的苏雪林,实际上在五四高潮中最多不过是个对新思潮有兴趣的旁观者,既没有如冰心一般每天抱着大扑满走上天安门广场为学运募捐,也不象同班同学庐隐似的“一面试行写作新文艺,一面参加当时种种社会运动,每天忙进忙出,栗六不停”(注:苏雪林《〈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见《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 这就使她的思想与文章从起跑线上开始,已经与冰心、庐隐等现代女作家拉开了距离。
这一距离首先表现在苏雪林反叛封建传统观念时的犹豫和“不忍”中。
与现代许多女性作家一样,苏雪林早期散文以“爱”作为思想核心,“她的作品所表现的,约略言之,可以分作三方面,一是母亲的爱,二是自然的爱,三是两性的爱”(注:阿英《苏绿漪小品序》,见《现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市古籍书店1990年8月版。)。从表面看来, 这种“爱”的倾诉与冰心“爱的哲学”基本一致,都是自然美好的人性的歌唱,然而一旦深入其中,我们就会发现两者的极大差异。同是对母爱的歌颂、对母亲形象的塑造,读过《往事》、《寄小读者》、《南归》的人都会记得,为冰心时时记挂的母亲是一位爱好天然、开明、通达,对新生事物永远抱有极大兴趣的女性,然而,苏雪林所讴歌的母亲,则是一位封建社会里贤妻良母的典范。在婆婆面前,她永远低声下气,“婆婆一生她的气,她便吓得战战兢兢,怒若不解,她便扑通一声跪倒,流着眼泪满口认罪不迭,只求婆婆息怒”(注:苏雪林《棘心》,见《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 对于自己的女儿,她爱之深、爱之切,却不能理解她的海外远游,更不能帮助她解除包办婚姻,最终导致了女儿的生活悲剧。在此,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年青的苏雪林如同鲁迅一样,对身为旧社会的牺牲者的母亲持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但是,当五四时期的众多作家对于这一类旧时代女性都表明了他们的同情哀悯之心,并且从人生人性的角度已经为她们大声呼吁之后,苏雪林仍然将她们作为“贤孝妇女典型”加以介绍,并且提出“大家努力做到此点,国家才能够存在,家庭才能够存在,社会才能够存在”(注:苏雪林《〈棘心〉自序》,见《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 思想就未免显得过于陈旧。目光行于《棘心》的字里行间,我们似乎可以感到作家一方面对于封建礼教的残忍、黑暗表示极大的愤懑,另一方面,又似乎难以割舍对封建力量重压之下的扭曲的人格的欣赏和赞美。因此,她也就不能如冰心一样,真正从本然的人性角度完成对母亲的认识和母爱的颂扬。
此外,苏雪林早期散文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异性之爱”,这又与庐隐的创作题材基本一致,但是,对同一题材的审视与处理,恰恰又显示了两位女性作家思想方法的重大差异。青年庐隐是在用生命追求真爱,因此她敢于以真诚的笔触描写她与的情人的热烈相爱,并且大胆宣称:“我极想抓住你——最初我虽然不敢相信我能,但是现在我觉得我非抓住你不可,因为你,我可以增加生命的勇气与意义;因为你,我可以为世界摒弃而不感到凄惶;因为你,我可以忍受人们的冷眼。在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知己,便一切都可无畏,便永远不再感到孤单”(注:庐隐《云鹏的通信》,见1930年2月14日—4月8日《益世报》。), “吾爱,你不要惊奇,我要死——死在你充满灵光的怀里,如此,我才可以伟大,如此我才能不朽”(注:庐隐《云鹏的通信》,见1930年2月 14日—4月8日《益世报》。)!
与庐隐这般热烈的情爱形成鲜明的对比,苏雪林散文中所表现的异性之爱,只是“夫妇生活的甜蜜。礼教所不容许的爱,她是不肯写的。她只敢在礼教的范围之内,竭力发挥她的天才,抒写她心中的爱”(注:方英《绿漪论》,见《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局1983年版。)。尽管作家与当时许多知识女性同样经受着包办婚姻的痛苦折磨,然而面对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力,她却举步维艰。作为一名热血青年,她当然渴望得到甜蜜的爱情,更何况包办婚姻赐予她的只是未曾谋面又难以言情的“情人”,这不能不使她时时感觉痛苦,可是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又使她恪守婚约、难以逾越。她最终以封建的“理性”,扼杀了“像经了春风吹煦的花儿,大有抽芽吐蕊的倾向”的爱情,并且在《棘心》和《小小银翅蝴蝶故事之一》的结尾处,宣示了这一抉择的正确,他们“结了婚了,而且过得很幸福。……两个天天采百花之菁华,醉众芳之醇液,酿出了世间最甜最甜的蜜”(注:苏雪林《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之一》,见《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若干年后,作者沉痛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美丽的谎”(注:苏雪林《〈绿天〉自序》,见《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 然而透过这个“美丽的谎”,我们却能清晰地看到彼时彼地年青作家的内心世界:这是向着个性解放精神投去凄楚的一瞥之后,重新落入传统怀抱的悲剧,是暂时驻足遥遥眺望一次光明以后,朝着固有目标的继续前行。如果说五四精神此时已成为庐隐的行为动力,那么在苏雪林,它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这个梦不仅遥远,而且苍白,因为它同时缺少一种对于人生的思考力度。苏雪林早期散文在表现人生之爱题材方面的又一种局限,就在于她笔下的母爱、异性之爱,仅仅停留在状写“爱”的自身,表现“爱”的每一个细节,或是由“爱”而生的种种烦恼、种种坎坷。她以大量的篇幅,描写母亲对女儿生活起居无微不至的关照,描写母女离别日撕心裂肺的痛苦和别后绵绵无尽的思念;描写夫婿怎样悄悄为自己定做书架,小夫妻如何双双到草园子里捉蟋蟀,让它们打斗,还有许许多多日常生活中夫妻的逗趣和嬉闹……总而言之,“爱”就是作品的全部。然而在冰心散文中,这种无处不在的“爱”,首先来自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深刻认识。由于清醒地意识到社会的普遍不幸、人生的广泛悲哀、生命的极度脆弱,冰心苦苦思索着人生的根本价值以及超越苦难现实的奥秘。“我想什么是生命!人生一世,只是生老病死,便不生老病死,又怎样?浑浑噩噩,是无味的了,便流芳百世又怎样?百年之后,谁知道你?千年之后,又谁知道你?人类灭绝了,又谁知道你?”(注:冰心《问答词》,见《冰心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面对人生的短暂、惶惑,冰心发出了沉重的慨叹:“这样的人生,有什么趣味?纵然抱着极大的愿力,又有什么用处?又有什么结果?到头来也不过归于虚空,不但我是虚空,万物也是虚空。(注:冰心《“无限之生”的界限》,见《冰心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版。)”为此,她努力寻求自己的回答:“天国和极乐世界,不是超出世外的”,英雄、帝王、杀伐竞争的事业是虚空的,但人和人中间的爱,人和万物、和太空中间的追寻,却正是光明之路所在。(注:冰心《问答词》,见《冰心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正因为如此,冰心散文在充满“爱”的同时也充满着沉郁悲凉的忧患意识,“爱”正是作家苦苦寻求的使人生趋于善和美的答案,因此它也就鲜明地显示出了思想的坚实性,而这恰恰是读来总觉“底气不足”的苏雪林早期散文的缺失。
此外,苏雪林这种拘泥于表现个人情感的早期散文创作,由于所有的哀伤只是一己的,所有的欢乐也仅仅属于一对与世无争的小夫妻,因而也就显示出与时代精神的疏离,从而使读者明显地感到她与庐隐此期散文的又一种差距。庐隐散文同样以自我情感抒发为鲜明特色,但这奔涌的情感大潮气势恢弘,不仅包容了一个小小的我,而且包容了同时代众多青年的心声;她笔下的每一个“自我”都具有鲜明的理性色彩,具有五四人不屈不挠的奋争精神。在《寄燕北故人》中,她语重心长地劝导朋友:“我希望梅姊把个人的价值看得重些,把自己的责任看得大些,象我们这种个人的失意,应该把它稍为靠后些……我们只有推广这悲哀的意味,与一切不幸者同命运,我们的悲哀岂不更觉有意义些吗?”在《美丽的姑娘》一文中,她塑造了一位痴情而又坚毅的理想追寻者的形象,为了祭献这质朴而又辉煌的理想,“他掏出赤血淋漓的心”,呈拜于理想足前。在《云鸥的通信》里,她表达了坚定不移的奋斗决心:“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总未曾忘记过‘自我’的伟大和尊严”,“我热就要热到极点,冷也要冷到冰点,能这样,才配了解人生;如果是半冷半热的,那只是浅肤的生活,不能象征人类的伟大!”两两对照,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人们在阅读苏雪林早期散文时,会“感到里面藏着一种生命的疲乏。基于对生的厌倦与孤独感,似乎没有什么事,能以引起她的特殊的兴味……”(注:阿英《苏绿漪小品序》,见《现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市古籍书店1990年8月版。)1957年, 苏雪林在为新版《棘心》作序时也曾坦诚相告:原本《棘心》“时代气氛并非完全缺乏,不过总嫌其过于稀薄……因而全书感动之力,也就大大打了折扣”(注:苏雪林《〈棘心〉自序》,见《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这实在不是作者的过谦之词, 而是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作家对当年创作的清醒认识。
苏雪林早期散文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作家其时审美意识的陈旧。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人本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于对“情”的高度肯定和热情拥抱。因为在旧的价值体系笼罩下,唯有发乎本性的“情”最能表征人性的需要,最能体现摆脱了各种现实羁绊的人性之真和个性之诚,因此,五四时期众多新文学前驱者均以“求真”作为第一审美要求。无论是胡适提出的“真挚之情感”(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周作人强调的“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注:周作人《平民文学》,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抑或鲁迅“率真行诚,无所讳掩”(注:鲁迅《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的呼吁,都表现着新文学与瞒和骗的旧文学分道扬镳的决心。然而,细读苏雪林早期散文,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除却《棘心》和《棘心》的变体《小小银翅蝴蝶故事之一》的前半部之外,其余篇章均远离了真实情感的倾吐。一切正如作家多年后所说:那时的她“善于画梦,渴于求爱,有时且不惜编造美丽的谎,来欺骗自己,安慰自己”,实际上在最初的两年里,爱情的网“早已支离破碎,随风而逝了”(注:苏雪林《〈绿天〉自序》,见《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4 月版。)。但是正是面对这已然“随风而逝”的爱情,苏雪林“做”出了一篇篇甜蜜的散文:她描绘红尘世界里一对小夫妻的地上乐园,细细刻划笼中鸽儿的相依相恋,写金鱼、写蟋蟀,写一封封荡漾着离愁别绪的情人小札,……这些美丽的篇章因此没有“极度的欢喜或极度的悲哀”(注:阿英《苏绿漪小品序》,见《现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市古籍书店1990年8 月版。),没有五四文学的蓬勃朝气,更似古代闺阁女子闲暇时的舞文弄墨,不求以真实的力量打动人心,唯愿以幽雅清丽之态供人把玩。
这就远离了20世纪中国文学特有的悲剧意识,远离了五四文学传统。我们知道,五四文学思潮滥觞于一个蒿目时艰的社会,传播于一个长歌当哭的时代。悲凉、愤慨、激昂等悲剧性的审美特征就成为文学新思潮的一个重要侧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一方面,是一个历史如此悠久的文化传统面临着最艰难的蜕旧变新,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尚未诞生就暴露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一方面,‘历史的必然要求’已急剧地敲打着古老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产生这一要求的历史条件与实现这一要求的历史条件却严重脱节,同时,意识到这一要求的先觉者则总在痛苦地孤寂地寻找实现这一要求的物质力量;一方面,历史目标的明确和迫切常常激起最巨大的热情和不顾一切的投入,另一方面,历史障碍的模糊(‘无物之阵’)和顽强又常常使一热情和投入毫无效果……这一种悲凉之感,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所特具的有着丰富社会历史蕴含的美感特征”(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见《文学评论》1985年第5 期。)确实,从鲁迅《野草》中的长叹,到茅盾的《疲倦》和《严霜下的梦》里的迷茫,从冰心散文斩不断的乙乙愁绪,到庐隐、石评梅等女性作家散文中哀伤啜泣的泪水,可以说,这个时代真正打动人心的散文篇章无不传递出一种深沉、郁重的悲凉之感,然而,在苏雪林早期散文中,作者面对实际上的悲剧。譬如《棘心》与《小小银翅蝴蝶故事之一》里包办婚姻的苦果,也最终排斥了它们原本具有的悲剧因素,而代之以“大团圆”的结局。“他们现在是互相了解了。从前的事重提起来,只成了谈笑的资料”,他们“结了婚了,而且过得很幸福”(注:苏雪林《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之一》,见《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但是, 正是这样一个结局,使得前面所有的情感倾吐的悲剧力量化为乌有,这样的作品,“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醒”(注: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与胡适这一段话相比,鲁迅对于此类审美选择的评价更为深刻、也更加耐人寻味;“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纵观文学史,确实,“大团圆”式的喜剧从根本上说正是中国国民性的弱点、缺陷在艺术上的一种表现,事实上,只有真实的悲剧、悲剧性、悲剧的观念才能产生思想深沉、意味悠长、感人最烈、发人猛醒的新文学。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半个多世纪以前,阿英指出,苏雪林散文的最大不足,在于她的作品缺乏“深深袭击着读者的心的生命的跃动”(注:阿英《苏绿漪小品序》,见《现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市古籍书店1990年8月版。)。
当然,作为本世纪20年代末期的一位重要作家,苏雪林早期散文确有其独到之处,她的作品文辞优雅、想象奇巧,山川草木、飞禽走兽无不蕴有灵性,与人类的心灵相通,正如阿英所论:“在她的作品里,对于自然描写最多,成就也特别高”(注:阿英《苏绿漪小品序》,见《现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市古籍书店1990年8月版。)。 虽然由于持有一种闺阁游戏的创作态度,她的散文大量采用了“工笔”的写法,不能如冰心一般,“轻轻的抹几笔,便给你一个完全的印象”(注:方英《绿漪论》,见《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局1983年版。),但还是在进一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方面,为现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公正地认识、评说这一点,是我们研究苏雪林早期散文创作时应有的客观态度。
标签:散文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现代十六家小品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冰心论文; 文艺论文; 阿英论文; 庐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