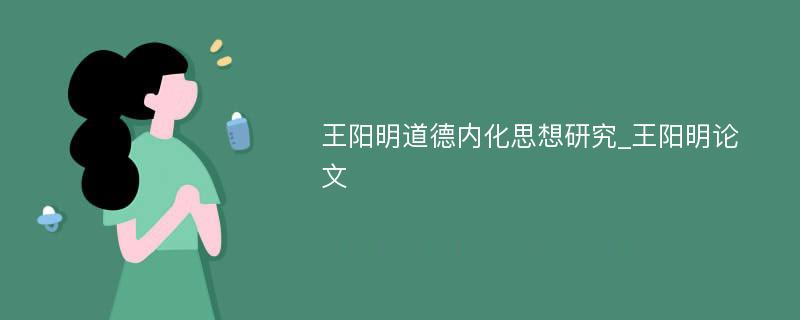
王阳明道德内化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化论文,道德论文,思想论文,王阳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对心性的研究是以成圣为内在的价值基础的。在儒家那里,心性之学构成了论证圣贤之域的哲学根据,他们对心性之学的孜孜不倦的探讨旨在解决圣人德性的养成与发展之道,同时也是对道德内化过程的探究。从孟子到王阳明,心性之辨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演化过程,至王阳明,已臻成熟,其中蕴涵着从主体意识到道德内化的丰富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对心性问题的考察可以上溯到先秦儒学。在孟子那里,凡人皆有四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1]这里所谓心,主要是指道德良心,一方面体现为一种情感、情绪的内在力量,另一方面又包含着理智的善恶指向和价值判断。那么,性又为何呢?孟子提出“四端”说阐明了这一问题。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这“仁、义、礼、智”作为当然之则,就构成了人性的具体内容,而“我固有之”[3]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端构成了“成性”的内在基础。孟子以四心为仁义礼智之端,就意味着肯定了人性与人心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即“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4]孟子认为,人性体现了人的道德本质,人心则表明了人的情意存在。人心所蕴涵的恻隐、羞恶、是非、恭敬等情意,为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而且,由内在的道德情意向道德意识的转化需要一个“扩而充之”的过程,人心的内容决定了这个扩而充之、化人心为人性的过程既包含理性化的过程“思”来实现,所谓“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5],同时又是一个知、智依内心情感而发用,最终实现德性的过程。孟子对心性关系理情并重的阐述包含着合理的思想。在西方伦理学早期,柏拉图把肉体和情欲看作达到理念界的束缚,相形之下,孟子则把融合理智与感性的“心”看作“成圣”的开端和机制,为“成圣”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和健康的实现途径。
至宋明理学,心性之学已经成熟,并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与之相应,道德内化理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其中,程朱理学的心性论是不可忽略的。在对心的理解方面,程朱认为心是身之主宰。程颐说:“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6]朱熹更为明确地指出:“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7]可见,程朱是在实然的意义上来谈论心的。作为实际存在的本然,“心”不仅泛指一般的精神活动及精神现象,兼涉性与情,又与人的感性存在相联系,此之谓“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8]。主于身就意味着心对身的主宰,同时又蕴含着“身”这种感性存在对“心”的渗入。这样,心就成为心与身的统一。而要进一步化实然为当然,就必然涉及心与理、心与性的关系。关于心与理的关系,朱熹认为:“心与理一”,“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9]。也就是说,作为寂然不动的伦理本体和当然之则,理内在于心而主宰心。而包含和体现在心中的理,也就是性,所谓“理在人心,是之为性”[10]。在心性关系上,简而言之就是,性决定心,即“心以性为体”[11]。这就是程朱心性论的核心结论。
这样,程朱通过一个精致的思辨过程,将主体意识分为“性而上”的性与“形而下”的心两个方面。“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是仁、义、礼、智之理而已。”[12]在程朱那里,“性”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外在的社会当然之则,即是指理性的道德规范。因此,理想人格的确立和圣贤品格的完成不过就是把这种当然之则内化入心,实现性对心的本体地位的过程。程朱称之为“化心为性”的过程。“性则是道心”,因而,“化心为性”又是“化人心为道心”的过程。程朱主张“道心常为主,人心每听命”,这就表明了天理不仅规范着外在行为,而且制约着主体的内在意识。化人心为道心,则意味着化除人心的感性因素在内化过程中的困扰和阻碍,促进外在道德权威规则的内化,从而确立天理对人的内在主宰地位。因此,如果说,荀子所强调的礼对行为的规范,主要体现要求外在道德权威对主体的规约,那么,程朱提出的“道心为主”,则进一步强调外在权威要内化于人的主体意识。这正是道德内化理论中“外铄说”观点的发展和完成。
一般而论,人作为道德主体首先是现实的存在,不仅有理性,而且包含着情感、意志等。善的品格的形成固然离不开理性的参与,但程朱把人的道德完满过程仅仅看作是实现人的理性本质,确定理性本体地位的过程,其中,经验、情感、直觉等非理性的因素是没有任何正面价值的。这种以理性的过分扩张从而涵盖一切的趋向使程朱的心性之学不可避免地带上本质主义的特征,这也使它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有效实现道德规范向主体意识的内化。
心性论有着前后相继、逐层提升的内在逻辑。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就体现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心性学逐步从外在的超越性实体(如天理)向心、性与外在实体的同一,最终确定心为最高本体。
王阳明所说的心体,含义比较广泛,指知觉、思维、情感、意向等等,心体的内涵首先涉及心与理的关系。心之所以能成为道德本体,能发出至善的各种条件,主要在于心与理是不可分的。所谓心,王阳明明确指出:“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13]也就是说,作为本原,心并不仅仅是一种感性的存在,它是以理为其内在的规定;而所谓理,主要是指作为先验的道德律或道德规范。这样,理使心具有两重特性:即先天性与普遍必然性。先天性表现心先验的一面,“心,生而有者也。”[14]普遍必然性则是指心融理为一,超然于特殊时空的一面。王阳明将先验的道德律引入心,以理为心之体。在这一点上,王阳明的思路与程朱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但是,在心性的内涵上,王阳明与程朱之间的差异在于,程朱主张以性说心,即用性来规定心,将心完全理性化,把心完全化为具有普遍必然之理的存在,而忽视心的的经验性一面。与之不同,在王阳明那里,心之所以具有主宰性,并不在于它具有先天的普遍必然之理,而是与感性存在不可分。“耳目口鼻四肢,身也,费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吾心则吾身,无身则无心。”[15]可见,心并非隔绝于耳目口鼻等感性的存在,而是包含着具体的感性因素在内的统一体。在程朱那里作为追求目标的超验之理,在王阳明这里甚至成了“理障”,而经验和感性的因素,才是心体应有的规定。
此外,情属于心中的感性经验的层次。王阳明指出:“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16]。情感属于感性经验的序列,王阳明将七情视为人心的应有之义,使先验的心体与经验的内容结合起来,是感性存在在理性世界中获得了合法性。
再者,王阳明还把“乐”规定为心体的品格。他说:“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性之乐,亦不外于七情之乐。”[17]儒家所讲的“乐”,即所谓圣贤之乐,主要是指精神的愉悦。既然讲“乐”,那么就必然包含着情感上的认同。源于仁道精神的精神愉悦,唯有达到“乐”的情感认同,才算趋于完善。
概而言之,王阳明所说的心体既以理为本,又与身相联系而内含着感性的内容。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克服了程朱“以性为体”说的片面性,提出了一种更全面的思路。首先,程朱强调以性说心,实质是把性与心对立起来,以性为体,突出的是理性本体对于个体意识的主导地位,以理性的至上性抑制了感性存在以及情感、意志、直觉等在成圣过程中的作用。相对于程朱的这一弊端,王阳明在肯定心以理为本的同时,还主张以身说心,并将情、意、乐等视为心的应有之义。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王阳明沿袭了孟子情理兼顾的思想;相对于程朱理学,他无疑更多地注意到主体意识多方面的内容,从而使其心性之学更为全面而丰富。
从以上论述可知,在心理关系中,理主要指外在的与个体相对的天道和人道,它总是超越个体的存在,表现为一种外在的社会要求;与之相对的心则是内在于主体的个体意识。那么,如何使社会的普遍要求内化为个体的意识乃至具体行为呢?这成为儒学家们一直孜孜以求的问题。王阳明的心体重建学说构成了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
心即理,首先便意味着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的融合。当普遍的规范仅仅外在于个体并与个体相对立时,它便很难真正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归根到底,理必须要内在于心才能起作用。也就是说,圣人品格必须要经过一个道德内化的过程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王阳明曾经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只是那些仪节求的是当,便为至善,即如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凉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18]还说,“若无真切之心,虽日日定省问安,也只是扮戏相似,却不是孝。”[19]只有扬弃普遍规范的对象性,将其内化为主体意识,才能对道德实践产生实际的影响。
道德内化的本质无非就是如何确证道德规范和主体意识相统一的问题。王阳明的心体论就为道德规范的内在化提供了内在根据:道德内化之所以可能,就在于道德规范和主体意识在本源上就是统一的。王阳明主张价值之源内在于心,没有将“天理”实体化、外在化,从根本上摒弃了道德规范与主体意识的两分状态,克服了程朱赋予道德规范的异己性质。因而,在王阳明这里,道德内化不再是主体被动地接受外在性规范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主体本身的内在要求和潜能与外部影响交互作用,以实现自我道德本质充分发展的过程,是使社会的理想融合于主体意识,并转化为人格内在要素的过程。可见,王阳明的道德内化思想尽管带有先验主义的色彩,但其关于主体自身与道德规范关系的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对道德主体性的彰显,无疑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性。
那么,道德规范是如何内化为主体意识的呢?德性的心理结构包含着知、情、意三部分,王阳明认识到这一点。普遍之理向个体之心的内化,并不是以抽象的理念的形式进入个体意识,而是渗入于主体的情感、意向、信念等之中,并进而转化为主体意识的内在要素。如果仅仅依照外在的理性规范,而未能将一般的理性原则融合与内在心体,就不能实现道德规范的内化。道德原则融于内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普遍的道德规范通过理性的认知,与个体信念、情感相融合的过程。正是通过这种交融,道德才获得了内在的力量。与程朱“性体论”确定的超验理性的当然逻辑在先原则不同,王阳明认为在融理于心的过程中,理智的作用是有限的,知善并不必然会导致善或行善,“凡人之为不善者,虽至于逆理常乱之极,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20]。这就是说,当人为恶时并不是不知道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善恶之知并不能逻辑地导致为善去恶。那么,如何实现由天理向人心的转化呢?王阳明避开了格外在之物的理论思路,强调反求诸己,“诚自家之意”。所谓诚自家之意,也就是要出自真心实意的情感。诚意本质上体现为道德主体内在的情感意识和心理定势。在行为发生之前的善恶判断总是渗入主体的权衡、选择、意愿及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舍自始至终蕴含了情感之维。在道德内化过程中,不仅有理性的分辨,而且有情感的认同在内。相形之下,程朱理学主张化良知为天理,以性统情,又以先验的天理作为宇宙本体,赋予天理以超验性,天理成为道德律令,以定言命令的形式要求人们无条件地遵守,而忽略了个体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自主。这样,其道德的内化完全就成为个体对既定道德规范的机械接受过程,这样的教化思路由于忽视了道德主体的情感、经验、意向等因素,强行灌输,所以无法使道德规范真正内化为主体意识,其结果必然是培养出奴性的或者虚伪的道德。而王阳明却以心即理沟通了普遍之理与个体之心,肯定了普遍之理须通过心的内部活动内化于个体之心,从而突出了个体人格的丰富规定和个体的自主性,心与理的统一在主体意识中具体化为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这样,王阳明的道德内化思想克服了外在规范与主体意识之间的对立,缓解了道德内化过程中理性与情感、社会规范与个体自由之间的紧张,实现了两者的统一。
完整的道德内化过程不仅是指理向心的内化,除此之外,王阳明还提出了外化的思想,即心通过外化而展现天理。王阳明称之为“在物”的过程,即“此心在物则为理”。经过天理的内化,心逐渐获得了普遍的内容,后者又通过践履的过程而进一步外化为道德行为。王阳明所终生探求的“致良知”就是对这一思想的深化。“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21]致吾心之良知之于事事物物,也就是说要化道德意识为具体的道德行为。正是在道德实践中,人伦关系逐渐变得合乎理性的规范,人与人的交往也更趋合理化,理性化的道德秩序由此形成。在王阳明看来,通过新的外化,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行为,从而达到社会人伦的理性化,最终建立实现合乎“天理”的社会秩序。
以心体的重建为基础,王阳明全面地阐发了由良知而德性、由德性而德行的道德思想,展示了道德主体化理入心、化心为行的完整的道德内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洋溢着道德主体的理性智慧,又不乏个体丰富的道德情感;既强调个体的道德提升,又关注社会理性秩序的建立。西方道德内化理论林林总总,但就道德内化的实质这一问题,无论是良心论、道德感论还是自我规定论,归根结底,都在处理外在规范与主体意识和行为的关系时,表现出一定的偏颇之处。相形之下,尽管王阳明以心性之学为基础的道德内化思想还仅仅停留在思辨的层面上,缺乏科学的基础和论证,但它所体现的这种以和谐、统一为取向的思路对我们正确认识道德内化问题无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