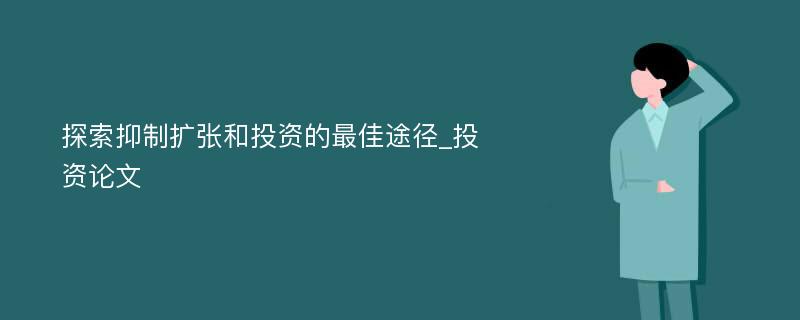
探索抑胀与投资两全其美之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全其美论文,之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这次高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
分析这次高通货膨胀的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我国现行经济体制和现存经济结构上出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产生的后果及效应,辗转反侧,蜿蜒曲折,最终导致增加货币超经济的净投放,结果汇合成为这次高达24.2%(1994年)的物价上涨率。这些问题是:
(一)1992—1993年上半年,股票投机热、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大炒地皮,盛行一时,占压了千百亿资金,成为“死钱”。为了弥补全社会货币流通量之中的这一大窟窿,必然迫增货币净投放。
(二)我国农业不过关,是一心腹大患,是通货膨胀最深刻的根源,粮(及粮食转化物)价不稳是历次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基础。 1993—1994年间的天灾较重,加之农民一度不愿种粮养猪,国家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不得不提高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并支付现金,不打白条。这自然是增加货币净投放的一个重大因素。
(三)我国由于未建立以商业汇票制度为中心的商业信用制度(欧洲商业信用高度发达,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欧美各国的银行信用, 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所谓“三角债”层出不穷,有积重难返之势。企业“三角债”占压的资金何止数千亿。这一部分“死钱”在社会货币流通量中留下的大窟窿,都转嫁到银行头上,而最后都迫使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净投放来弥补。
(四)1993—1994年各地补发中小学教师工资,还有一大片企业和县级以下行政机关,发不起工资,要求银行发“安定贷款”,以解燃眉之急。这些贷款有借无还,留下的缺口,也是增加货币净投放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消费基金的超经济增长。我国实际工资(含奖金及其他形式劳动收入)水平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水平;企业亏损,职工收入照样增长;一部分发不起工资的单位,实际上并不是像口头叫喊的那样“穷”,职工及干部实际收入并不像所说的那样过不了日子。这些人所尽知的事实,说明了我国消费基金的超常规增长的客观存在。而这恰恰是我国发生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
(五)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的贬值,以及外汇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及负效应,使我们在清偿对外债务和对外支付中,按人民币计算,蒙受高达几千亿元的重大损失。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结构(广义)、体制、政策及政策措施上出现的问题,归根结底,引起这次高通货膨胀。我们应针对这些病因,求得诊治良策。
二、令人担心:抑制通胀结局是“滞胀”还是“增胀”
如何抑制通货膨胀?我以为最好办法,莫过于既抑制住通货膨胀,又不致造成经济滑坡。亦即抑制通货膨胀的结果:不会出现“滞胀”局面,争取出现“增胀”或“低通胀增长”的局面。然而,目前令人担心的,也正在此。
什么是“滞胀”、“增胀”或“低通胀增长”?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我认为如果物价上涨率保持在10%以下,而生产不景气、市场滞销,库存积压大量增加,就是“滞胀”。如果物价上涨率在10%左右,而国民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例如百分之十几(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百分之几),就可算是“增胀”。如果物价上涨率控制在6%以 下,而经济增长幅度更大一些,那就是“低通胀增长”,目前在我国也可以看作是基本正常的增长。
由于这次高通货膨胀有多方面深层原因,因之在一、二年内把物价上涨率压低到4%以下是困难的,甚至压到6%以下也难以做到。比较现实的估计,一年内压低10至12个百分点,可能性更大。果真如此,我们应当做的,就是在全力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求得一定的经济增长,力争“增胀”,避免“滞胀”。如何才能避免“滞胀”争取“增胀”局面的出现?我认为,根据1989—1990年市场疲软经济滑坡的沉痛教训,关键在于抑制总需求措施切无过头,实质上即是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切无过头。其数量界限在于:切不可导致投资总量的连年负增长或零增长,而应力求保持全社会固定资产年度投资总量5 %上下(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年度投资实际增长率)的低增长,即使能够保持百分之二、三、四的年度投资实际增长率也好。而这是我国当前经济技术综合实力及发展潜力完全可以办到的。
这次抑制通货膨胀,应高度重视汲取1989—1991年的深刻教训。那一次,为什么会出现市场疲软和经济滑坡的“准滞胀”局面?原因就在于“急刹车”措施太猛,1989年年度投资总量比上年降低22 %, 致使1989—1990年连续二年出现投资负增长,到了1991年才恢复到1988年的投资总量的水平。由于投资负增长,引起生产资料价格下跌,库存超储积压变本加厉,有增无已,结果带动整个市场疲软达几十个月之久,造成社会生产较大滑坡。当时采取的金融政策,先是投放3000多亿元流动资产贷款,企图扶植社会生产的增长,启动市场,刺激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加速。但结果市场启而不动,销售疲软和生产滑坡如故。1991年夏季,国家转而采取增加3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以启动市场。 结果良好,不但很快启动了生产资料市场,而且很快带动了消费品市场的复苏和活跃,使社会生产走出低谷,逐步上升。这次“急刹车”的主要教训之一,是年度投资增长率压低过头,造成连年的负增长。我们这次抑制通货膨胀采取“软着陆”的方针是正确的。但目前已出现了生产资料价格下降3%,基建物资价格下降6%的情况。这是一个重要信号,叶落知秋,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密切注意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控制是过头还是适度,避免重蹈1989—1990年度投资负增长,生产滑坡,市场疲软的覆辙。
三、抑制通货膨胀与投资适量增长可以兼得
抑制通货膨胀,是今年的中心任务。为了抑胀,就必须适当收紧银根,严控货币发行。这一基本做法,世界各国皆然,中国也不例外。其实际后果,必然使信贷及投资的增长大受限制。当然,这样做也是正确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即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期间,是否可以同时保持社会投资的适量增长?我以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乍一看来,抑胀与投资增长似乎是势不两立的,其实并非如此。根本的理由在于:当前的通货膨胀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亦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缓和和解决。抑制通货膨胀,并不排斥反而要求经济的稳健增长,不过要适当降低过高的增长速度。同时,抑制通货膨胀,也不排斥社会投资的增长,只不过要把过大的增幅适当降下来。因此,寻求抑胀与投资适量增长两全其美之策,是完全可能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实现投资总量的适量增长;而且,在控制全社会投资总量的大前提之下,实现投资结构及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
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前提条件下,什么是社会投资总量的适量增长?我以为,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看,所谓“适量增长”,是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社会投资总量, 仍可比上年增长5 %左右, 但是绝不能像1990—1991年那样形成负增长(那次下降了22%),也不可搞零增长。零增长和负增长,是对我国当前综合经济技术实力估计过低所致。5 %左右的实际增长,既符合当前国力已达到的水平,又不致于冲击或破坏“抑制通货膨胀”政策总的贯彻实施和取得成效。我的主要根据如下:
(一)199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28.5%,但物价上涨24.2%,故扣除涨价因素,实际上投资总量仅增长4.3%。1994 年的投资增长率,我以为是合适的,既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又有利于保持稳定,而且并不妨碍抑制通货膨胀方针的贯彻实施和取得成效,甚至可以说是较好地配合了抑胀措施的落实。
(二)我国“六五”时期投资年均增长28%,经济发展较为平稳。这说明28%的年均投资率,是适合我国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的,是合适的。若扣除那五年的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投资增长率也只有20%多一些。这是正常情况下的投资增长率的合理水平。如在通货膨胀高达20—30%的时期,年均投资的实际增长率,自然应当较大地降低。我看至少应降到10%以下较为合适。例如“七五”时期,我国年均投资增长1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只有百分之几,绝对不到10%。又例如,1981— 1990年期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每年平均增长19.6%,去掉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率也只有百分之十几。这个投资增长速度,也充分反映和代表了我国80年代的国力水平。由于80年代最后三年发生高通货膨胀以及不得不大力加以治理,因此,年均投资实际增长率,自然应当比正常发展时期为低,而高于高通胀及其治理时期,故10%以上的增长率是合适的。
(三)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总额, 1992 年比上一年增长42.6%,1993年又比1992年增长58.6%。由于中央采取了有效的稳健的宏观调控措施,尤其是平抑物价、抑制通货膨胀措施收到成效,1994年投资仅比1993年增长28.5%。现在看来,1993年的投资增长率显然过高,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在35%左右。这样的实际增长率显然超过了当前的国力水平。1992年的投资增长率也偏高一些,不如1993年那么厉害。这是因为投资剧烈地高增长,主要是在当年最后一季度出现的,前七、八个月的投资增长速度,总的说还算基本正常。
因此,1992和1993两年的投资增长率,绝不可作为1995年效法的榜样。
四、抑制通货膨胀期间是合理调整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大好时机
我们说抑胀与适量增加投资可以两全,但如何适量增资,却大有文章可作。首先要明确一点,绝不可各行各业各地全面大量增加投资。这样必然会突破“适量”的界限,扩大总需求,与抑制通货膨胀撞车。因此,适量增加投资,必须与合理调整投资结构一同进行。很明显,假如投资的增长,其结果是使生产供给的“长线”部门生产能力扩大,从而使“短线”生产部门生产能力相对缩小,则不仅无益于抑制通货膨胀,反而可以助长甚至导致“短线”产品的物价进一步上涨。而且,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同时,也应看到,抑制通货膨胀条件下合理调整投资结构,不但必要,而且是可能的。抑制通货膨胀期间是调整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大好时机。
近十年来,我们年年高喊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可是,实际上却是年年“调”不动,收效甚微。相反,地方和企业年年大量进行低水平盲目重复建设,使“长线”愈“长”,“瓶颈”愈细。为什么结构“调”不动?究其根源,无非是外无压力,内无动力。现在,全国的首要任务是抑制通货膨胀,核心措施是适当收紧银根。这就为合理地适当地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创造了最有利的时机和最强劲的外部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只要在政策措施上善于引导,外部压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内部动力,从而使结构调整得以向前推进。
五、保农业是调整投资结构的关键
过去有学者断言,我国恩格尔系数大降,人民的“吃饭”问题已经解决了。事实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问题不仅在于我国现在尚有8000万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我国广大农业生产尚未“过关”。所谓“过关”,是指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每年生产的粮食,供给全国人口消费都绰绰有余。美国的典型事例,最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美国自殖民地时期以来,300年间,尤其是独立以后, 粮食年年吃不完,年年有大量出口,长期成为世界粮食市场的一个主要供应国。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美元的币值,在国际市场上屡次下跌和长期动摇的同时,却在国内市场上保持稳定,从不曾对国民吃饭问题构成威胁。我国情况则反是。由于我国农业生产不“过关”,粮价及农产品价格稳定成为整个市场物价稳定和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础;粮价及农产品价格不稳定,动辄影响或波及整个消费品物价的上涨或动荡。改革开放16年来的历史全过程,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抑制通货膨胀、调整投资结构的关键之一,是要较大地增加广义农业的投资,使广义农业投资比重能上升到全社会投资总量的10%左右,而且不止今年一年,应当保持一段时期。过去说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这话是正确的。但是农业科学化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必须大力增加广义农业的投资。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要选择好增加农业投资的重点,不可搞平均主义,无论是地区上还是生产门类品种行业上,绝不应当平均分配投资。我认为,农业投资增加的重点应是:
(一)农业技术推广和技术开发。
(二)有选择地增加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工业投资,例如产粮大省吉林的玉米、东北的大豆、高粱的精、深加工工业,应重点增加投资。
(三)增加支农工业投资,如化肥农药农用机具汽车拖拉机等。
(四)增加农业、渔业水产、林果、畜牧、中草药扩大再生产以及扩大单位面积产量的投资。
(五)增加江湖治理及防洪、水利灌溉设施的投资。
增加广义农业投资,不一定全由国家拿出钱来。国家当然要增加投资,但地方、农村及地县企业、城乡私人均可增加对广义农业的投资。地县乡村还可组织农民以“集体投入劳动”的方式兴修农林水利建设及乡村公路建设。“投劳”实际上不过是“投资”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从节省货币支出的意义上说,“投劳”是最节约的投资。这也应当包含在“增加广义农业投资”的概念之中。
六、调整投资结构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大力加强基础产业投资
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也强调了许多年,能源、原材料紧张势头虽略有缓和, 但交通依然是矛盾的焦点, 其中最突出的是铁路。1950—1979年30年,我国每年平均新增铁路营业里程960公里,而 1980—1991年12年每年平均仅新增520公里, 成为新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低谷期”。1994年全国铁路运输经营亏损达75亿元。今年投资还比去年减少,成为负增长。我认为,即使在抑制通货膨胀时期,什么行业投资都可以减少,唯独铁路投资绝对不应减少。
基础产业方面增加投资比重的重点,首先应放在铁路及公路干线建设上。能源建设应加强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红水河水电资源的开发。其次,钢铁、铜、铅、黄金、稀土、建材、化工原料等工业投资,应得到加强。
这里要强调一点:交通运输建设的加强,不但可以增加“滞后供给”(交通运力增长),而且可以增加“现实供给”。例如,现在山西约有5000多万吨煤炭运不出,不少在露天自燃。东北有300 万吨货物无法运出。河北待运积压物资约值20多亿元。云南出省铁路运力缺口达68.1%。云贵两省磷灰石运不出去,使各省许多化肥厂限产或停产待料。还有许多事例,不胜枚举。所以,增大交通运输建设投资,实质上是增加现实生产供给以抑制通货膨胀快速有力和重要有效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