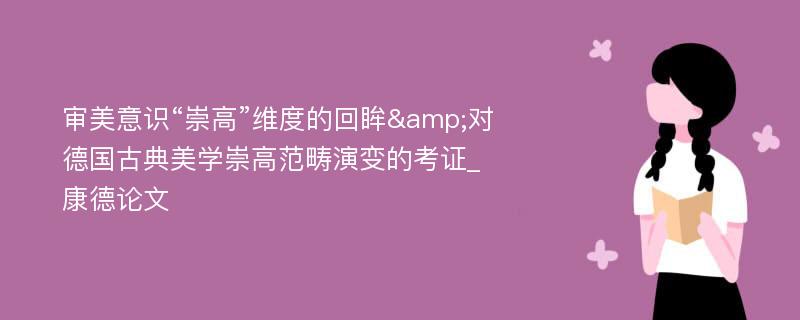
回眸审美自觉中的“崇高”之维———种对德国古典美学中崇高范畴嬗演的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崇高论文,德国论文,范畴论文,学中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4)01-0004-12
在“崇高”的消息早就不再被更多的人所顾念的时下,这里愿借重一段美学史的回味对这一毕竟未可轻弃的审美维度作某种追忆式的探询。诚然,追忆也是一种呼唤,不过其所要唤起的并非只是思古之幽情。
相对于狭义的“美”(优美),“崇高”(壮美)在人的审美自觉或审美反省中是一位迟到者。在西方,倘以“美是什么”的问题的提出为第一次审美自觉的标志,那末正可以说,首先自觉的审美判断是狭义的“美”(优美)的判断;古罗马的朗吉努斯(Longinus)在其《论崇高》中就“(诗文)措辞的高妙”、“结构的堂皇卓越”乃至汪洋大海、火山爆发论说“崇高”,远在柏拉图前后的希腊人寻问“美”(优美)的奥秘之后。与这一情形大体相类,在以“美学”(Aesthetica)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宣布为标志的第二次审美自觉中,英国人柏克(Burke)标举“崇高”为美学范畴的著作《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起源》(1756)发表时,鲍姆嘉通(Baumgarten)以“美学”正式命名他的划时代的著述已经六年了。1764年,温克尔曼(Winckelmann)的《古代艺术史》问世,其中有对审美之崇高感的心理描述的文字;同一年,康德发表了他的论文《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但无论如何,“崇高”被真正触到它的谛趣却不能早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1790),这之前人们所做的一切只是某种注定会向此而趋的酝酿。像是一道不可重现的闪电,从康德到黑格尔,崇高的话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审美自觉的境地显现着人的审美灵魂的深度,“崇高”的探讨者所体悟到的那份人生的崇高感留给人们的是一份永恒的启示。
一、康德:崇高“内在于我们的心里”
康德是第一个为审美视野中的崇高判断寻找先验依据的人,此所谓先验依据乃是一种不为任何经验个人的随意性所摇夺的准矱。他并非一味地鄙弃崇高之维上的审美经验,反倒是这些有待评断和判别的经验使得他不能不超越经验的狭隘或偶然性去对崇高所以为崇高作出“先验的解释”。这解释仍是依照一般判断必得涉及的四类范畴(“量”、“质”、“关系”、“样态”)进行的,并且同对美(优美)的判断的先验解释理趣相通。他指出:
“对于崇高和对于美的愉快都必须就量来说是普遍有效的,就质来说是无利害感的,就关系来说是主观合目的性的,就情况(即‘样态’——引者注)来说须表象为必然的。”(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6页。)
但崇高终究是审美中独立的一维,对崇高的分析并不能全然蹈袭对美的分析。在康德看来,美的发生有待于作为审美对象之表象的“形式”,崇高的发生却在于激起这崇高感的对象的“无形式”;“形式”意味着对象被审美主体有限地表象着,“无形式”则意味着审美主体须得去表象那有限视野中非可全然直观的某种对象的整体。在前一种审美中,表象(形式)与表象者(审美主体)的和谐无乖使审美主体在忘物忘我的情境上产生直接的愉悦,康德称这愉悦为“积极的快乐”;在后一种审美中,表象者(审美主体)因着表象那似乎无限(因而“无形式”)的对象的不可能却又要竭力去表象它而使审美主体在穿透生命遭际的迫力后产生生命力升华的愉悦,相对于前一种愉悦,康德称其为“含着积极的快乐”的“消极的快乐”(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4页。)。前一种愉悦借重于对象的“形式”,使得“美好像被认为是一个不确定的悟性概念”,这即是说,在这里,美“好像”是作为对象的某种“客观属性”被知性(悟性)所表达;后一种愉悦与“形式”无关,因此遂与愉悦“好像”来自对象的“客观属性”这一错觉无关,也便与能够形式地表达“客观属性”的知性无关,却只与理性相系——所以康德说,“崇高却是一个理性概念(唯理性才能把握被知性视为无限的东西——引者注)的表现”(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3页。)。引起美感的“形式”与不能引起美感的“形式”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差别,所以“美”(优美)相系于“形式”的“质”;激发崇高感的“无形式”的对象与不能激发崇高感的对象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在“量”上的非可直观的“大”,所以“崇高”只关涉到这个被视为无限“大”的“量”。康德所谓“在前者(美——引者注)愉快是和质结合着,在后者(崇高——引者注)却是和量结合着”(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3页。),正是在这样的分际上。
与美和崇高的上述差别相应,人在美的鉴赏和崇高的观审中的心意状态也大异其致。美的鉴赏是对一个能够唤起美感的有限“形式”的直观,处在这直观中的人的心意是“静观”的;崇高的观审则是直观一个“无形式”的对象却又必得把这难以整合的对象想像为一个整体,这时人的心意处在对感官尺度的超越中因而是“运动”的。崇高观审中的心意运动或在于想像力(一种心意机能)对认识能力(又一种心意机能)的发动与调整,或在于想像力对欲求能力(心意机能的另一种)的发动与调整,前者把一种“数学的情调”(数量的无限大)赋予对象,后者把一种“力学的情调”(力量的绝对强)赋予对象。于是,“崇高”遂被康德分为“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数学的崇高”突显着“量”和由这量而引致的以不快感为媒介的愉快的“质”;“力学的崇高”突显着人的欲求能力同自然力的抗衡、较量的“关系”及抗衡、较量的“样态”。
“崇高”在语义上被康德理解为“全然伟大”、“无法较量的伟大”或所谓“绝对的大”。这“大”被称述为“绝对”不是在实际量度的数据的意义上,而是在审美中的人的直观感受的意义上。在审美视野中,大海的渺无边际或山峦的绵延不绝,都会使人震撼于一种“绝对的大”;然而,倘作一种实测,则无论怎样辽阔的海域或怎样绵长的山脉,其面积或长度总可以用一个有限的数字作表达。“崇高是一切和它较量的东西都是比它小的东西”(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9页。),当康德这样说时,他实际上已经告诉人们,“崇高”并不能从自然界的某一经验的事物那里去寻找——因为任何堪称为“大”的事物都不可能大到“绝对”的地步。因此,他也如此更准确地阐示他所谓的“崇高”的意味:
“崇高是:仅仅由于能够思维它,证实了一个超越任何感性尺度的心意能力。”(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0页。)
在单纯的直观中,人面对一个其“量”足够大的对象(无论是瀚海、大漠,还是对于一定观审位置上的人说来的埃及金字塔或圣彼得大教堂)时,他总会竭其所能展示他的“构象力”(把事物摄入视野以整全地勾勒它的形象的能力):一方面不断地由此及彼地“把握”(Apprehensio)这巨大的对象的各部分的表象,与此同时则“总括”(Comprehensio aesthetica)那被把握的诸多部分的表象以趣求对该对象的全貌的直观,但这对象的“量”对于直观中的人说来实在是太大了,以致“总括”力在达到它的极限时仍无从窥见对象的整体;“总括”力的极限意味着审美估量的最饱和的尺度,一旦到了这个最高点,无论对部分表象的“把握”怎样继续进行,被“总括”的量都不会再有所添加,它即使“总括”了新的被“把握”到的诸部分表象,也会丢弃在量上相当的前此曾被“把握”的那些表象。于是,“绝对的大”的那种震撼性感受霍然而生,此即“崇高”所由发生的“量”的契机。这“量”之“大”似乎是就那大的对象而言的,但“大”而至于“绝对”决非对象本身如此,而是人的心意机能对超出感官尺度衡量限度的“大”的评判。引动崇高感的契机既然仅仅在于那种“绝对的大”,此“绝对”又只是出于直观中的人的心意的评估,那末,就“量”而言,“崇高”的真正原委便只能追溯到主观。康德说:
“真正的崇高只能在评判者的心情里寻找,不是在自然对象里。”(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5页。)
倘换一种说法,也可谓:崇高不是外物——哪怕是很大很大的外物——的“客观属性”,而是人评判那乍一纳入直观中的外物时的一种内心的情调。
单是心意评估中的“绝对的大”带给人的也许只是压抑或不快,不过“绝对的大”的观念的乍起,本身便意味着超越感官尺度的那种理性的显露。知性永远只能问津有限的东西,对某种“绝对的大”的力图把握所唤起的是理性的使命。恰恰是为想像力所运用的感性尺度的不足使我们“感到我们有纯粹的、独立的理性,或具有一估量大的机能”(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8页。),这机能的把握无限或绝对的使命及其优越性才鼓动着人穿透压抑或不快,并由此而获得愉快。愉快以压抑或不快为媒介,显出压抑或不快及引发这压抑或不快的因素对于愉快者说来的合目的性,此即“崇高”所由发生的“质”的契机。
当自然在人的评赏中被直观到的主要不是数量的“绝对的大”,而是一种难以抵拒的力的威逼时,那被引发的“崇高”被康德称为“力学的崇高”。人对强力的震摄在直观中估量着,人也在其心意中倾其全力与之较量着;这较量含着“崇高”的“关系”的契机。高耸而下垂的危石断岩,滚滚而来的乌云中的雷鸣电闪,飞流直下的悬崖高瀑,撼天动地的火山爆发……诸如此类的自然的“力”扑向人时,人的可能的抵拒的能力显得微不足道。但倘若人处在某个相对安全的观审位置上,这类自然力愈暴烈可怖,往往愈能吸引人的评赏的心灵。依摩德的分析,异乎寻常的自然的力使人“认识到我们物理上的无力,但却同时发现一种能力,判定我们不屈属于它,并且有一种对自然的优越性”(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1-102页。),如此被激发出的超乎自身自然而足以俯瞰外部自然的那种力是以理性为依据的人格的力。这种力量意味着,即使人在肉体上被无情的自然暴力所挫败,人也不应因此降低自己的人格。由人的肉体自然与外部自然的较量所引生的恐怖在被理性的力量解除后,人获得一种从重压下透出的快感——崇高感。
在这里,理性的自由之光投向自然,但这投向自然的自由之光却又是被威力无比的自然调动起来的;那自然由此显出某种合目的性,亦即对人的自由的实现说来的主观的合目的性。如同“数学的崇高”看似在于粗犷的自然,而终究却“只能在评判者的心情里寻找”一样,“力学的崇高”归根结底“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任何物内,而是内在于我们的心里”(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4页。)。数学的崇高透过“绝对的大”拓展人的心量或襟怀,力学的崇高则以对自然力的超胜陶炼着人的滋养于道德理性的生命强度。康德由此也把审美意味上的崇高情调关联于宗教信仰当有的崇高观念:“粗陋的人”对大自然的威烈的一味恐怖(“谁害怕着,他就不能对自然的崇高下评判”(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1页。)),同他们对想像中的狂暴的神灵的迷信和畏惧是可以相互说明的,而“受过文化陶冶的人”直面大自然的强力时那种评赏崇高的情调,则同他们对一个作为“道德的元宰”的上帝的崇敬的心境全然相通。
在康德看来,从战栗于自然威势的“粗陋的人”进到能够在心意中超越自然威力以评赏崇高的“受过文化陶冶的人”,有待于道德观念的演进发展。但他并不把崇高判断的依据就此归结于历史的经验。他认为,对于崇高的判断,“虽然需要文化修养(且超过对美的判断),却并不因此首先是由文化产生出来的和习俗性地导入社会的,而是它在人类的天性里有它的基础的。那就是对于(实践的)诸观念(即道德的诸观念)的情感是存在天赋里的。具有健康理性的人同时推断每人都禀具着,并且能对他要求着。”(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6页。)这即是说,人的天赋的道德情感是崇高判断的先验根据,有了这根据,它才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出于必然。就“样态”而言,崇高判断的契机正在于这见诸主观的必然。比起“量”、“质”、“关系”诸方面的契机来,“样态”上的所谓“必然性”的契机在康德的审美判断(包括美的和崇高的判断)的分析中显然被更看重些。他称它为诸契机中的一个“主要的契机”,因为他认为:
“它正在这些审美判断上使一个先验原理显示出来,而把它们从经验心理学里提升起来,——在经验心理原是它们将埋葬于愉快与痛苦的诸情绪的下面,(只是带着一个无所说明的形容词:精微的情感而已)——以便由于它们的媒介把判断力放置进以先验原理为基础的一类里去,而作为这一类又把它拖进先验哲学里去。”(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6-107页。)
二、席勒:崇高——对“受苦的自然”的“道德的反抗”
有如康德,席勒也把“崇高”作为一个独立而又对应于“美”(优美、秀美)的审美范畴。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美”,自然和理性在人这里便无从协调和沟通,如果没有“崇高”,人就会在“美”中陷落于快感而忘记自己的尊严。所以他认为,“只有当崇高与美结合起来,而且同等程度地培养我们对二者的敏感性时,我们才是自然的完美公民,因而不会是自然的奴隶,也就不会在只能靠理性而不能靠感性来认识的世界中丧失公民权。”(注:席勒:《论崇高(1795)》,见张玉能译席勒文集《秀美与尊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214页。)不过,与康德略异,席勒更多地把对崇高感的培养关联于艺术,尤其是悲剧,不像康德那样只是在“对自然事物的‘大’的评量”或对自然事物的“力”的观照中作“崇高的分析”。
当席勒指出“在美中理性和感性是协调一致的”、“在崇高中理性和感性是不协调一致的”(注:席勒:《论崇高(1795)》,见张玉能译席勒文集《秀美与尊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时,他并没有比康德就美与崇高的差异说出更多的东西。而所谓“崇高感是一种混合的感情。它是表现最高程度恐惧的痛苦,与能够提高到兴奋的愉快的一种组合,尽管它本来不是快感,然而一切快感却更广泛地为敏感的心灵所偏爱。两种对立的感情在一种感情中的这种结合,无可争辩地证明着我们道德的主动性”(注:席勒:《论崇高(1795)》,见张玉能译席勒文集《秀美与尊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则几乎可以说是对康德写在《判断力批判》中的某些句段的转述。甚至,他把康德所说的“美”或“优美”刻意区别为“美丽”(“活泼的优美”)与“秀美”(“沉静的优美”),并相对于“秀美”提出了“尊严”的概念,也未必在美学意义上有多少超越康德的价值。但他毕竟做了康德不曾做的事,在以“崇高”领会悲剧——这是康德从未置评的领域,而且依康德所赋予的内涵,“崇高”也当与整个艺术无缘——的美学契机时,他诉诸所谓“激情”。激情被界说为“人为的不幸”(注:席勒:《论崇高(1795)》,见张玉能译席勒文集《秀美与尊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亦即被悲剧诗人构想出来以之作为调动人的崇高感的重要环节的那种不幸。它像现实的不幸一样能够唤起直面不幸的道德理性,但它被把握在恰当的分际上,不像现实的不幸那样在难以逆料的时间、地点向任何一个可能遭到不测的人猛扑过来,使人无以自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席勒指出:
“激情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之移植,借助于这种移植,命运就剥夺了自己的险恶,而命运的攻击就被引向人的强大方面。”(注:席勒:《论崇高(1795)》,见张玉能译席勒文集《秀美与尊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换句话说,激情乃是被移植到悲剧中借以逼视人的灵魂的深度的命运。没有深彻而强烈的感性的痛苦,无从产生激情,但激情成其为激情也还在于它对人的道德境界的可能尽致的表现的成全。席勒批评那种把真实的自然(本性)约束在朗诵式的冷冰冰的声调中的法国悲剧,而对真切刻画“受苦的自然”的古希腊史诗和悲剧推崇备至。他由衷地赞叹希腊人是真正的楷模:他们坦然吐露切己的自然(本性)的苦痛,但从不为感性的自然所奴役;他们不是以对感性痛苦的冷淡和漠然来显示自己的高卓,而是在感受这种痛苦时从忍受痛苦中寻找人性的荣誉。在席勒看来,“悲剧艺术的第一条法则是表现受苦的自然。第二条法则是表现对痛苦的道德的反抗。”(注:席勒:《论激情》,见席勒文集《秀美与尊严》第159页。)因此,他说:
“在一切有激情的情况下,感觉必须是由痛苦引起兴趣的,而精神必须是由自由引起兴趣的。如果激情的表现缺乏受苦的自然的描写,那么它就没有美学的力量,而我们的心就始终是冷漠的。如果它缺乏道德禀赋,那么哪怕在具备感性力量的情况下它也不可能是激情的。而我们的感觉不可避免地被激怒。受苦的人永远应该由一切精神的自由显露出来,主动的或者能够达到主动性的精神永远应该由一切人类的痛苦显露出来。”(注:席勒:《论激情》,见席勒文集《秀美与尊严》第169-170页。)
在悲剧中,激情为崇高而涌动,而所谓崇高感即是从那感性生命的痛感中透出的精神自由的快感。激情集痛感与快感于一身,其不快之感源于激情的对象与人的情感的关系,其快感来自激情本身与人的道德的关系;对于悲剧说来,从痛感中产生出快感,也就是从情感与道德的关联中引发出那不可抵拒之苦难背景下的同情心来。席勒认为,一切同情心都以对痛苦的想像为前提,而同情的程度则在于那种对痛苦的想像的生动性、真实性、完整性和持久性:(一)想像的生动性,是指对痛苦的想像越生动活泼,所能激起的感情就越强烈,感情越强烈,就越能唤起对痛苦的道德反抗。(二)想像的真实性,是指被想像的痛苦切合人的真实体验,以致能使感受者毫不勉强地与剧中的受难者调换位置,设身处地地为受难者的痛苦而痛苦。(三)想像的完整性,是指凡是使心灵按预定目的活动所需要的一切外部条件必须在想像中全部具备,应当有一系列个别的使人直接目睹——而非间接叙述——的动作或情节安排,这些动作或情节以确定的因果关系构成一个整体。(四)想像的持久性,是指要使剧中人的苦难在感受者心中激起高度的感动,就须设法让痛苦的想像持续不断。依心灵的常态,人们总是急于从别人的痛苦所引起的激情中摆脱出来,一部悲剧的成功却往往在于如何运用各种手段让人们的感受长时间地拴缚在剧中人的痛苦上。由引发同情心的痛苦想像所必要的生动性、真实性、完整性和持久性,席勒对悲剧艺术独特的悲剧感的可能产生的必要条件作了如下归结:
“第一,我们同情的对象必须完完全全和我们同类,而要我们参与的行动,必须是一种道德的行动,也就是说,一种自由领域内的行动。第二,痛苦、痛苦的根源和逐渐推进的程度,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事件,完整无缺地传达给我们;而第三,还必须用感性的目睹的形式,不是间接通过描写,而是直接通过行为来表现。”(注:席勒著、张玉书译:《论悲剧艺术》,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6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98页。)
上承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席勒提出,“悲剧是对一系列彼此联系的事故(一个完整无缺的行动)进行的诗意的摹拟,这些事故把身在痛苦之中的人们显示给我们,目的在于激起我们的同情。”(注:席勒著、张玉书译:《论悲剧艺术》,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6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98页。)他分五个层次对他的这一界说作了阐释,各层次的外延的相当程度的重合,显现出论说者对看似相近的提法的微妙差异的经心。当他说“第一,悲剧是一个行动的模仿”时,他所着意的是以“模仿”把戏剧同那些诉诸叙述或描写的艺术区别开来,由此凸显戏剧“行动”(动作或情节)的可直接目睹性。当他说“第二,悲剧是一系列事件的模仿”时,他是要以“一系列事件”把戏剧这一表演“事件”的艺术同抒情诗一类文学作品区别开来,就此申说戏剧人物的感受和激情的展露须借重接连发生的一起又一起事件。当他说“第三,悲剧是一个完整无缺的情节行动的模仿”时,他是要就“完整无缺的情节行动”强调“一系列事件”的因果关联,提醒人们注意有着确定目的的悲剧事件的整体性。当他说“第四,悲剧是一个值得同情的行动的诗意的模仿”时,他的用心则在于以戏剧当有的“诗意的真实性”区别于“历史的真实性”,而他所说的“诗意的真实性”却不外是指艺术作品如何切实达到“使人感动”、“使人快乐”这一诗意的目的。当他说“第五,悲剧是一个行动的模仿,这个模仿把受苦中的人展现在我们面前”时,他把阐述的重心移向了“人”——“人”是他的悲剧理论的底蕴所在,也是他的哲学、美学和艺术见解相牵相系的纽结所在。“只有在‘人’这个字的全部意义上的人,才能作受苦的对象”(注:席勒著、张玉书译:《论悲剧艺术》,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6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1页。),这说法关联到他论崇高、论激情、论美育的文字显然可以引出更深微的蕴涵,然而当他终于说出悲剧诗人的“理想的主人公正是介乎完全堕落和完美无缺的人物之间”(注:席勒著、张玉书译:《论悲剧艺术》,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6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1页。)时,却不免给人以落于浅尝之感。
席勒对悲剧的题材是看重的,他甚至写过《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这样的专题论文,但他更属意于悲剧的形式。他认为,如果一部悲剧不是倚重题材的功效,而是更多地凭着形式的构成获得成功,这悲剧才真正算得上是理想的悲剧。不过,在他这里,悲剧的精神既然在于激情的崇高,它便必得涉及人生的感性和理性两重界域,而且亦终究以道德理性的主动性为其托底的秘密——就这一点而言,那被属意的悲剧的形式便理应是隐贯了从道德的主动性说起的“崇高”之灵魂的形式。无论是重形式,还是重道德的主动性,都可视为对康德的美学原则的信守,尽管康德本人从未问津过悲剧。然而,席勒确曾说了“人的结构美(亦可谓形式美——引者注)在性质上是理性概念的感性表现”(注:席勒:《秀美与尊严》,见席勒文集《秀美与尊严》第115页。)一类话,这诚然更大程度地是在康德美学的意味上说的,但人们由此或会联想到后来黑格尔对美所作的那个著名界说——“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也并非没有足够的理由。
三、谢林:崇高——“真正无限者”呈现为“相对无限者”
康德学说倚重主体的精神性状一度被费希特以其“绝对自我”推向极致,这时,曾对费希特怀有足够的仰慕之忱的谢林开始回顾被判以“独断论”的斯宾诺莎主义。美与艺术同斯宾诺莎哲学无缘,也并未在斯宾诺莎主义的批判者费希特那里获得当有的际遇——他留下了诸如“审美判断是正题判断”一类不无深趣的话题,却没能就此写下相称于其“理论自我”、“实践自我”之确立的有关“审美自我”的更多文字;反倒是谢林,这个处在康德学说和斯宾诺莎主义之张力下寻求主体与实体、自我与自然之“同一”的人,以“艺术哲学”立论,辟出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又一重天地。
谢林以他称之为“上帝”的“绝对者”(“绝对同一”)托底,建构了融摄“自然哲学”、“先验哲学”为一体的“同一哲学”。新姿态的哲学虽然逻辑进退有致,却处处诉诸理智直观与美感直观,以至这哲学的建构者要分外申说:“客观世界只是精神原始的、还没有意识的诗篇;哲学的工具总论和整个大厦的拱顶石乃是艺术哲学。”(注:谢林著、梁志学、石泉译:《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5页。)推重“美”和“崇高”对于他是极自然的事,而“美”和“崇高”在通向“绝对者”的途中相互间也更多了些亲和感。与“艺术本身是绝对者之流溢”(注:谢林著、魏庆征译:《艺术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上帝……乃是任何美的源泉”(注:谢林著、魏庆征译:《艺术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诸提法一脉相贯,谢林这样界说“美”:
“所谓美,无非是被实际直观的绝对者。”(注:谢林著、魏庆征译:《艺术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他没有像康德那样借助“量”、“质”、“关系”、“样态”诸范畴逐一探究审美判断的契机,但他以一种先验的目的论阐释美感直观,倒略可与康德所谓美感表象“合目的性而无任何目的”的说法相比勘。他指出:自然界的创造活动是无意识地开始而有意识地告终(以有意识的人的出现告终)的,它虽然没有预设的目的,其产物(有机体)却是合乎目的的;美感创造活动是有意识地开始而无意识地告终的,它通过创造者的有目的的追求把某种始料未及、不为意志所左右的结果带了出来——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引发于其自由行动中的有意识因素与无意识因素的冲突,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造就则标志着两种对立因素的相契。这即是说,在艺术创作中,有意识活动(自由)与无意识活动(自然)缺一不可,这两种活动以其无限对立之势成全着美感创造,却终于有可能在其产物艺术作品中臻于同一。“无限对立”的双方在既成的艺术作品中达于“同一”是无意识的,它默示着“美”何以会通向无限事物。由此,谢林从另一个角度界说他心目中的“美”:
“既然这两种活动(即处在无限对立中的有意识活动与无意识活动——引者注)可以在作品中被表现为统一的,那么,这种作品就终于把无限的事物表现出来了。而这种终于被表现出来的无限事物就是美。”(注:谢林著、梁志学、石泉译:《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70页。)
其实,这里所说的“无限事物”正可究元于被奉为“上帝”的“绝对者”,以“被表现出来的无限事物”界说美与以“被实际直观的绝对者”界说美,其意趣亦全然相侔。而且,当美被界说为“被表现出来的无限事物”或“被实际直观的绝对者”时,那“美”既然关联到“无限”和“绝对”,便也已经意味着人们通常所称叹的“崇高”。
谢林讨论崇高是从康德对崇高的理解说起的,不过,在他把这一范畴引入同一哲学或以对绝对者的直观为旨归的艺术哲学时,一切都被重新阐释过。他不否认康德曾论列过的两种崇高,即所谓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前者在于可能大的自然对象对于评量者的感知能力说来的不可计量,后者在于可能强烈的自然威力使出现在它面前的人的感性生命力显得微不足道。他只是指出,那对于人的感知能力和感性生命说来显得绝对地大或具有无限威力的自然景象不过是“感性无限者”或“较为宏大者”,这些“感性无限者”或“较为宏大者”所以可能引致崇高感,是因为它们做了“真正的无限者”或“绝对者”的象征。真正的无限者被认为是崇高的最终依据,但离开感性无限者或较为宏大者——实际上的有限者——真正的无限者却又无从直观。康德要谨慎得多,他从不轻言“崇高者”,而仅仅说“崇高只存在那个关系中,在那关系里感性的东西在自然的表象里被判定能够从事于可能的超感性的用途。”(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7页。)谢林则基于他对“绝对者”或“真正的无限者”的认可,把康德所谓“感性的东西”从事于“可能的超感性的用途”,变换为所谓“感性的无限者”对“真正的无限者”的象征,并以此界说他敢于径直道出的“崇高者”:
“崇高者乃是显现为无限者的有限者(即‘感性无限者’——引者注)之从属于真正的无限者。”(注:谢林著、魏庆征译:《艺术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
换句话说,“崇高者”即是那借“感性的无限者”被直观的“绝对者”。这个关于“崇高者”的界说,同前此的关于“美”的界说——“美,无非是被实际直观的绝对者”——相比,其理路与意指可谓毫无二致。至于“感性的无限者”何以可能成为“真正的无限者”的象征,谢林则认为,那是因为二者皆可喻之以“混沌”。感性的无限者,无论是对于人的感知能力说来其全貌非可尽窥的庞然大物,还是对于人的肉体生命说来其威压非可抗拒的可怖之力,它们在人的直观中固然只是被视为一种混沌,而作为真正无限者的绝对者,其本原形态亦正在于混沌。绝对者的混沌是绝对形态与无定形的同一,它不是对形态的简单否定,而仅仅意味着在这包容一切形态的形态或一切形态的统一中没有一种形态有可能作为特殊者脱颖而出。“混沌”非知性所可推求,惟可诉诸理智或艺术予以直观,“绝对者”的这一绝对形态注定了以确证和彻悟绝对者为务的“同一哲学”更重艺术的直观而不是概念的寻绎。
除开自然中的崇高者,谢林还格外留意崇高者在精神体制中的发生。这类崇高者的范型往往由悲剧所模塑,从谢林对悲剧的见地显然看得出他曾如何步席勒的后尘。他几乎是在逐字逐句地重复席勒的说法:真正的悲剧性的崇高者基于两种条件——精神个体在自然之力下筋疲力尽,同时又通过其心灵体制居于上风。危难和灾祸是悲剧人物的摇篮,而悲剧人物成其为悲剧人物却还在于他直面命运的无情终究会守持一种精神。厄运见证德行,危殆显现勇决;在同苦难的抗衡中,命运的承受者即使遭遇灭顶之灾也能在精神上自拔于险境而不输其人之为人。如同自然中的“感性无限者”,悲剧主人公这一“相对无限者”作为真正无限者或绝对者的象征使精神体制内的崇高成为可能。
把崇高分为“自然中的崇高者”与“精神体制中的崇高者”显然可能留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自然中的崇高者所以为崇高者乃在于自然,精神体制中的崇高者所以为崇高者乃在于精神。其实,谢林对崇高作如此划分只是出于论说的方便:既然崇高的发生终究因着作为相对无限者的有限者对真正无限者(绝对者)的象征或真正无限者借作为相对无限者的有限者以获得直观,那末,那作为相对无限者的有限者,如果是自然物(无论是数学意义上“大”的自然物还是力学意义上“强”的自然物),所引出的便是所谓“自然中的崇高者”,如果是有限而相对无限的人的精神,所引出的便是所谓“精神体制中的崇高者”。真正说来,崇高之为崇高最终在于对真正无限者或绝对者的直观,而要获得对真正无限者或绝对者的直观,便既不能没有用以象征真正无限者或绝对者的感性无限者或相对无限者,也不能没有其精神与真正无限者或绝对者相契的人。因此,所谓“自然中的崇高者”其崇高并不在于自然客体本身,诱发崇高的自然物(“感性无限者”)作为真正无限者或绝对者的象征不过是人借以获得对真正无限者或绝对者直观的中介。而“精神体制中的崇高者”的情形却不同,其中作为绝对者或真正无限者之象征的悲剧主人公本身即是因着直观绝对者或真正无限者而赋有崇高感的人。就此而言,某一“大”或“强”的“感性无限者”的自然物,其本身原是无所谓崇高的,而精神体制中的那种作为相对无限者的人反倒可以径直被称为崇高的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谢林有理由说“只有在艺术中(而不是在自然中——引者注),客体(悲剧主人公作为可直观的客体——引者注)本身才是崇高的”,尽管他同样有理由说“既然精神体制,即有限者因之而降至无限者的象征之因素,就此而论,依然无非是同主体相关。”(注:谢林著、魏庆征译:《艺术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
无论是美还是崇高,底蕴都在于对绝对者或真正无限者的直观,而直观无限者,无论是获得美感还是崇高感,又都不能不借重有限者。崇高与美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其更大程度地被认可为美或更大程度地被称之为崇高,仅仅在于被直观的无限者与借以直观无限者的有限者的关系:在崇高中,有限者对抗无限者却又作为无限者的象征;在美中,有限者表现无限者而与无限者相调和。谢林在撰写《先验唯心论体系》时就已注意到,崇高和美都是以同一种矛盾为依据的,但他又认为二者间的对立也异常明显,——自然景致可以是美的却不因此就是崇高的,可以是崇高的却不因此就是美的——尽管他断定,这对立只是发生在直观的客体而不是在直观的主体方面。其后,这段文字被修订为:美和崇高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客观的对立;真实的、赋有绝对性的美的东西总是崇高的,而真正崇高的东西也必定是美的。在《艺术哲学》中,谢林则更多地强调了崇高与美的相互涵纳。他指出,“无限者呈现为有限者,主要是作为崇高者显现于艺术作品”,而“有限者呈现为无限者,主要是作为美好者呈现于艺术作品”(注:谢林著、魏庆征译:《艺术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同时,他也指出:
“处于其绝对性中的崇高者将美好者纳入自身,犹如处于其绝对性中的美好者将崇高者纳入自身。”(注:谢林著、魏庆征译:《艺术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这即是说,如果崇高者不同时也是美的,它将不成其为崇高,而只会使人感到可怖或怪异;同样,真正赋有绝对性的美,也应或多或少地震撼人心而使人或多或少地产生一种崇高感。谢林认为,把美与崇高融为一体的最好例证莫过于神话中诸神的形象,他们身上的崇高与美的比例往往取决于其受限制的状况。美的必要形式总是要求其受到一定的限制,由这限制带来的无限性的消减又总会使美的程度在神的形象中相对于崇高而有所提升,但无论如何,神成其为神,其形象决不至于仅仅美而并不崇高或仅仅崇高而并不美。例如宙斯,他既非老年,又非青年,其形象不受什么限制,崇高在他这里对于美就占了上风,而阿波罗的形象受限制就较多些,其青春之美固然比宙斯更美,而其显现的崇高却又势必逊于宙斯。同样,天后赫拉的形象可谓之崇高的美,而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形象相对于赫拉则又可称叹为美的崇高。
四、黑格尔:崇高——“理念越出有限事物的形象”
在谢林诉诸富于诗意的美感直观对哲学作了某种艺术洗礼后,黑格尔逞其沉郁的思辨以一个包举万有的庞大体系再度把艺术观审扬弃于哲学的逻辑。同是把鲍姆嘉通以“美学”命名的那个相对独立的学域称作“艺术哲学”,谢林的艺术哲学是其“(同一)哲学的工具总论和整个大厦的拱顶石”,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则只是运作中的绝对精神“自己二元化自己,自己乖离自己”从而自己“发现自己”、“回复自己”的一个环节——它在宗教哲学的俯瞰下,并最终笼罩于哲学的纯粹思辨:“思考和反省比美的艺术飞得更高”(注: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页。)。并且,同是以有限者表现无限者界说美,一为“所谓美,无非是被实际直观的绝对者”,一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注: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2页。),但两者的意蕴确已相去甚远:谢林虽曾断言美与崇高的相容互涵,即所谓“真实的、绝对的美的东西总是崇高的,崇高的东西(如果是真实的)也是美的”(注:谢林著、梁志学、石泉译:《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70页。),却终究把崇高作为美感直观或艺术直观中的独立的一维,因而他也对美和崇高作如是分辨:“在彼(在崇高者中),有限者似乎呈现于对无限者的反抗中,——尽管它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其象征。在此(在美好者中),两者始而处于调和状态”(注:谢林著、魏庆征译:《艺术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黑格尔则全然把审美在“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意味上一维化了,崇高在失去它作为审美的一个独立维度的地位后只是被视为美的一种有缺陷或非健全的状态。
黑格尔是在论述象征型艺术时说到崇高的,而象征型艺术在他的美的评判坐标中却不过是真正的艺术(古典型艺术)的准备阶段或所谓“艺术前的艺术”。这种艺术前的艺术诚然被认为是美的理念借感性形象显现其内蕴的肇始,但在黑格尔看来,此时,理念本身还是抽象的,还不曾定性,因而也还没有为自身找到定性的形式。“抽象的理念所取的形象是外在于理念本身的自然形态的感性材料,形象化的过程就从这种材料出发,而且显得束缚在这种材料上面。”(注: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5页。)的确,狮子可被用来象征刚强,圆形可被用来象征永恒,但这被象征的刚强、永恒还只是内涵显得空疏的理念的抽象属性,与之相应的则是显现它的感性形象——狮子、圆形等“自然形态的感性材料”——“在外表上离奇而不完美”。黑格尔说,象征型艺术与其说具有真正的表现力,不如说只是某种图解的尝试。
对于“象征”,黑格尔作了如下的界说:
“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因此,我们在象征里应该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意义就是一种观念或对象,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注: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页。)
依黑格尔的看法,“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不过在单纯的符号(如语言符号或徽章、旗帜等色彩符号)里意义与表现意义的形象间的关联是任意的,而艺术的象征是另一种,它的意义与表现意义的形象之间有着密切的可喻性联系。艺术象征在于以具体的个别事物表现某种普遍性的意义,而那具体个别事物的形象本身的特征即已能够作为对某种意义的暗示。形象对意义的这种暗示作用意味着二者间的某种协调,也意味着二者间的非可全然协调。狮子固然可以象征刚强,但刚强并不就是一头狮子,而狮子除象征刚强外也未尝不可用以象征凶残或其他精神性状。形象和意义间的这种既相应而又不相应的关系决定了艺术象征的模棱两可性或嗳昧性。黑格尔认为,一切象征型艺术都可以视为对意义与形象的互不适应所作的斗争,这斗争的展开构成象征型艺术的三个阶段或三种象征方式:不自觉的象征、崇高的象征方式、自觉的象征(比喻的艺术形式)。其中,崇高的象征方式是象征型艺术最具典型性的象征方式。
在崇高的象征里,意义作为有着独立、普遍而绝对性的精神第一次与感性的现象界整体对立起来,它为把自己从感性的具体事物中彻底净化出来而否定现象界,却又终于不能不借它所否定的现象界作为表现自己的材料。黑格尔认为,崇高是一种表达无限的企图,而在现象领域里又找不到一个恰好能表达无限的对象。他引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论述崇高的话说:“真正的崇高不能容纳在任何感性形式里,它所涉及的是无法找到恰合的形象来表现的那种理性观念;但是正由这种不恰合(这是感性对象所能表现出的),才把心里的崇高激发起来。”(注: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9页。)这是“不自觉的象征”的反题,崇高把普遍性的精神提升到一切直接存在的事物之上,正因为这样,倘囿于“不自觉的象征”的畛域,便可能发生“真正的象征的性质就消失了”的问题。
如果要使无限因而绝对或普遍的精神成为可观照的对象,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即既把它作为绝对而纯粹的精神。(一种精神“实体”)来理解,又把它作为创造一切现象界事物的力量来理解——由于它创造了诸事物,它便可以借这些被创造的事物显现自己。但无论如何,绝对而纯粹的精神仍是要超出个别现象而提升自己于个别现象的总和之上的,因此那种与现象世界的肯定的(积极的)关系复又转化为否定的(消极的)关系,非如此,精神便不能从生灭中的种种个别现象那里净化出来以显示自己不为现象所限的绝对性或普遍性。依据绝对或普遍的精神与现象世界的这两重关系,黑格尔把崇高的象征方式的艺术分为两种。一种取肯定现象事物的方式,借现象事物观照和称叹现象事物所由创生的神,一种取否定现象事物——不管它多么丰富多么雄伟庄严——的方式,托显神对于它的所造物的无与伦比的崇高、伟大。前一种是泛神主义的,古代印度和波斯的颂神诗是这种艺术的范例;后一种以犹太教的颂神诗和寓言诗最为典型,它由鄙夷万物的卑微与虚无来申达人对神的敬畏和惊赞。在黑格尔看来,
“用来表现的形象……被所表现的内容消灭掉了,内容的表现同时也就是对表现的否定,这就是崇高的特征”(注: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0页。)。
依照这一特征,他以为,那种由否定森然万象而仰颂唯一尊神的犹太教诗篇之情调才可堪称为“真正的崇高”。然而,被如此确认的崇高已经不再像康德所标举的崇高那样是对作为“世界的最后目的”或“作为本体看的人”的称叹,而是对战栗于神的威仪以致精神重心不能自守的人的贬抑:由于“涉及人方面的崇高是和人自身有限以及神高不可攀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就觉得在神面前,自己毫无价值,他只有在对神的恐惧以及在神的忿怒下的颤抖中才得到提高。”(注: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6页。)
五、结语
1、从康德到黑格尔,“崇高”在美学乃至整个哲学沿革中的境遇牵系着人的境遇。当康德、席勒把人的自律地提升着的精神境界视为崇高的内在依据时,他们所眷注的是人的尊严的自持或人的灵府的自守;诚然,崇高必得显现在一种非同寻常的对待性关系中,但一切造成人的感性生命之不堪的大自然的威压乃至无可规避的厄运的追逼,都只是借以见证人的崇高心灵的外部条件。谢林试图把崇高作为美感直观或艺术直观之一维归诸有着实体意味的“绝对者”,然而他对所谓“被表现出来的无限事物”、“被实际直观的绝对者”的那个“被”的终于未能略去,显然小心翼翼地为“主观的东西”在“同一哲学”中留够了主动的余地,而正是这一点使他得以在论说崇高时更大程度地援引席勒。不过,“绝对者”毕竟作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先导,“崇高”在后者那里已经不再那么蒙宠,——它被纯然思辨的逻辑安排为艺术哲学中一个不起眼的环节,只是为了用于指谓绝对理念尚未找到其感性显现所必要之恰当形象的情形。黑格尔所辨说的“崇高”没有了使人心有存主而重心自在的品格,它被用来喻示初始的神的孤卓和超绝,也因此被用来喟叹人对那高不可攀的神的恐惧和仰赖。
2、“崇高”与“美”(优美)在康德、席勒乃至谢林那里是作为审美判断或美感直观的两个性态有别的维度提出的,无论是康德、席勒还是谢林,都不曾把这两个审美维度截然对立,也都没有把它们牵混为一。康德未遑论及悲剧,但以“崇高”——而非“美”(优美)——收摄悲剧的精神性状终是顺理成章而别具一种深趣。席勒和谢林借着“崇高”这一独特的审美之维对悲剧的观审是耐人寻味的,显然正是它牵动着悲剧的最敏感的神经:这或如席勒所言,“只有‘人’这个字的全部意义上的人,才能作受苦的对象”,而“主动的或者能够达到主动性的精神永远应该由一切人类的痛苦显露出来”,或如谢林所言,“真正的悲剧性的崇高者基于两种条件:精神个体在自然之力下筋疲力尽,同时又通过其心灵体制居于上风”。黑格尔依然沿用了作为审美范畴的“崇高”,但他不再以它为一个独立的审美维度。他把“崇高”置于“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唯一被认可的审美维度下,赋予它以阐释“艺术前的艺术”的使命。既然“崇高”终究只是被关联于粗陋的象征型艺术的,它也便理所当然地与悲剧无缘。不可否认,黑格尔以“绝对精神”在剧中不同人物那里的片面实现——这些人物各执“神性的东西”之一端——解释悲剧的冲突可谓新颖而深刻,然而,替绝对精神上场扮演一个必要角色的人物却不过是那善于施“理性之狡计”者的资具。黑格尔的确说过“人本性上是自由的”(注: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2页。)这样的话,但人对于黑格尔说来从来就不是本体意义上的主体。依他的本然旨趣,所谓“人本性上是自由的”,不外是说“‘精神’(绝对精神——引者注)——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注: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6页。)。
3、美学在康德、谢林和黑格尔那里都只是价值祈向隐然可辨的哲学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美”和“崇高”的价值在怎样的分际上被认可取决于不同哲学体系的价值重心。康德是以“至善”(“德”、“福”配称)的求达为其哲学的职分的,“美”(包括“崇高”与“优美”)对于这一以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为契机的哲学说来原只是“至善”的某种补足,所以康德乃至断言“美是道德的象征”(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01页。),并由此得出这样的推论:“一个人……对于我所判为崇高的无动于衷,我们就说他没有(道德)情感。”(注: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6页。)谢林的“同一哲学”的宗趣系于其理念因素与现实因素绝对同一的“绝对者”,这能动的绝对者把自己展露在三个幂次上,它的最高幂次的展露同时即是它在最高幂次的被直观,亦即“美感直观”。因此他说:“同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三幂次相应的为三种理念(作为神圣者的理念,既不属于现实世界,也不属于理念世界)即:真、善、美(包括‘崇高’于其中——引者注);同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第一幂次相应者,为真;同其第二幂次相应者,为善;同其第三幂次相应者,为美”(注:谢林著、魏庆征译:《艺术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与谢林的“绝对者”略可比拟,为黑格尔哲学所措意的是融实体与主体于一身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自我显现而自我认识固然必得历经其艺术的定在以凭恃直观和形象,但其閟机的最后道破却不能不诉诸纯粹的思辨。命运般的逻辑所追逐的是被思辨地理解着的“真”,这“真”之幽趣即所谓“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注: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页。)“崇高”在康德的自律的道德之“善”中生发,在相应于谢林的“绝对者”呈现之最高幂次的“美”中栖托,在黑格尔的思辨而逻辑化了的“真”那里黯然失色,这并非偶然的嬗变诉说着那必得寻问于美学之外的美学之秘要。
4、黑格尔之后,叔本华一度就“壮美”作为意志自我否弃的一个或然性环节说过不多的话,从此,“崇高”在美学史上虽不能说全然销声匿迹,但确已鲜于被人提及。我们正处于一个人之生趣过重地累于外骛而精神内向度日见萎缩的时代,这时代里人们孜孜以求的是关涉利害、得失的“权利”,所荒顿的却是人生之尊严赖以养润的心灵“境界”。一如悲剧的衰微,“崇高”违别我们已经够久了。“美”正渐次沦落为当年叔本华所鄙弃的那种“媚美”,与“告别崇高”的轻佻呼叫相唱和的是熹音湛湎中的人们的泛艺术嬉戏。然而,文化危机的消息毕竟早就报告着某种可能的运会,它在警示人们作必要的人文自审时也提撕人的审美心灵再度唤起那富于悲情的“崇高”的一维。
标签:康德论文; 席勒论文; 美学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哲学论文; 判断力批判论文; 宗白华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