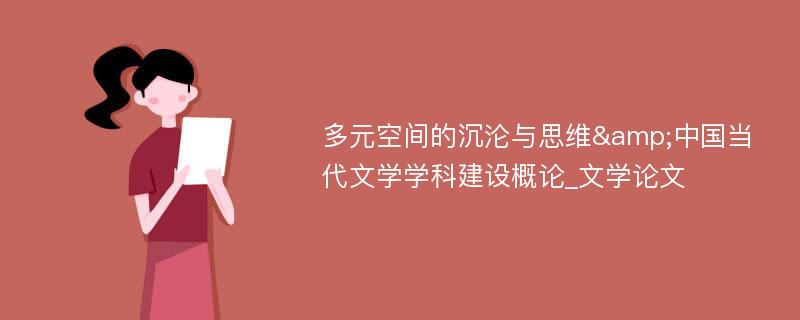
在多重空间里沉潜与运思——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进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当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空间论文,里沉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们需要回首前尘萧瑟行时,当我们在市俗的漩涡中沉溺太久而渴念传达天真、蛮朴、昂奋又不无悲欢的人伦世相与心迹情韵时,自然会想到“几度夕阳红”①的中国当代文学,关注它的生态、得失、性格和命运。
这些年,以中国大陆文坛而言,似乎有数不清道不尽的“尴尬”、“困惑”、“危机”、“下海”等声浪迭起且为媒体“炒”得纷纷扬扬。我则以为,这些“存在即合理”的现象被不适当地夸大了。事实上,地火依然运行,文学照旧发展;从研究与批评的层面,仍有令人钦羡的诸如“新人文精神”②、“新理性主义”③、“走文化诗学之路”④、“当代文学的理想与崇高”⑤、“向全人类的思潮与智慧开放”⑥等等知识命题的呼唤和探讨。尽管很有些人的姿态与文字如同茂盛的泡沫一般虚弱而空洞,也尽管当代文学的某些疆域日趋陷入文化企业⑦和江湖骗子的掌握之中,但严肃的学人、作者、批评家并没有从应有的真诚、良知和文学立场上后退,而是能在较长的时间里和较高的层次上耐得住孤寂,操持着人文关怀与精神家园。这才是当代文学真正的力量。
我们为中国当代文学磨难过,感奋过。不过,如若作冷静的省思,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着眼,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的确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趋时性(应时政、经济或风潮而多变)、争战性(各执一端乃至群趋偏锋)、青春性(热气有余而略显浮躁)和疲沓无力(缺乏哲思、慧学、理论的穿透)等特点。如今,文学的转型必然要求研究的分流、选择和深化。看来,向科学性、稳定性而又鲜活性、独创性转换,以加固学科根基和建立自己的阐释系统与学术规范,应当提到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赞成这样的意见:当代文学是复合的空间而非单一的空间⑧。空间(加上时间)也是一种文化尺度,用以度量人们文化活动的距离与进程。我们的研究视野,实际上也经历着从“封闭的空间”→“距离的空间”→“共享的空间”的转移。“封闭”必然单一,且形成排他和自大的心态;“距离”产生阻隔,而有地域切割与历史割断的人文之虞;“共享”基于和鸣的祈向与互补的策略,因之而激发“一体多元”的文化热望。
“共享的空间”自然是多重的、复合的。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我们看到的是整体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地图。我们将不至于把“大陆当代文学”等同于“中国当代文学”,而是合乎情理地把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包容进来,并寻求普适性与区域性的有机联系(并非简单的添加与拼贴);我们将不至于把“中国当代文学”(实际是汉民族)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分离开来,而是确立统一的多民族文学的空间结构;我们将不至于把某种被夸大为历史的神圣的创作方法作为衡量一切文学的标尺,而是以“有容乃大”的襟怀鼓励多种“主义”多种文学在正确方向下的共存共荣;我们也将不至于因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诸如“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等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是处在同一地平线上进行真诚、有效、取长补短的文学对话。我们在同一天空下沐浴阳光和呼吸空气。任何一位作家和批评家,所创造、所论证的只能是文学空间的一角,谁也无法占有全部。但同时,其生存状态、思维模式、价值尺度和书写实践,又总是一种走向真理或背离科学的文化行为;也因此,文学空间的多重性和复合性,不但不丢弃、而且要强化以历史的和审美的价值为基点的有深度的文化批评。
一旦要独自面对世界,当代文学研究自然不可陷入悬浮状态。潜心于自身的学科建设,倒也不必急于建构大堂屋、大体系,而是集数十年来的理路和经验(包括教训),先从不同角度归纳并深入探讨当代人在文学方面遇到的共同问题,依此照亮文本的真面目、真价值和真精神,也依此熔铸出一些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研究当代文学无法回避“当代性”这一理论话语。人们惯于把已经发生或正在出现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都冠以“当代”。但“49年以后”的说法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流行的“当下性”也只能说明现况而难以吸纳与凝聚散金碎玉。任何时代都会使那个时代的文学染上独特的色彩。“当代性”乃是当代文化思潮、思维活动、精神状态和社会现实人生的一个整体的、汇合的、深刻的文化结晶品。“文学的当代性”也就成为对当代文学的精神现象进行理性归纳的一种知识形态。据个人的观察与体会,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这种“当代性”在中国文坛上,至少突出表现为下列性征:(一)文化错位。一方面西方话语充满了强势性、殖民性和支配性,另一方面人们又将“西方”过分理想化、浪漫化和神圣化,从而在与异质文化的冲突中过分淡化了自己的文化认同。摇摆于排拒与拜倒、抱残守缺与仰赖异邦之间的文化错位,更使价值取向的自主和思想精神的独立显得分外重要。(二)过渡形态。今日之中国依然是过渡时代的中国。社会与文学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都处于过渡状态。进取的胆力和实验的精神常常成为文学的生命之轮,“圣徒”与“浪子”们都为之消耗着心力和才情,成功往往以惨重的失败为代价。新的并非一切都好,但一切好的多半是新的。因此,真正的“当代性”将不是集中在任何可行性的实验上,而是更有效地把文学才华集中到艺术创造上。(三)心理冲突。敏感和智慧的文学家与批评家,越来越深刻感受到带有普世性的时代的心理冲突并诉诸于文学研究。诚如哲学史家施太格缪勒所言,越是当代,那些旧有的“知识和信仰已不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必需了。形而上学的欲望和怀疑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对立,是今天人们精神生活中一种巨大的分裂,第二种分裂就是,一方面生活不安定和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方面又必须作出明确的实际决定之间的矛盾。”⑨中国当代社会现实也以置人的灵魂于险象环生之中而激发着作家们的焦虑与想象。“形而下”的生存物欲和“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之间的冲突,加强了心理的紧张度。“火浴”的大磨折和“求索”的大痛苦,使中国人“长于史而短于哲”的传统⑩开始得以当代性的改造,尽管远远不足,但“形而上”的寻觅和文学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正以一种辩证的“突变”方式生长起来。(四)开放态势。在世界已不再阻隔和整个文化要求“和平建设”的当代,文学要向全人类的思维、思潮和智慧开放,同时也意味着向政治、经济、科技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开放。当代文学自然会更富灵气地既在历时性上与过去对话,又在共时性上与“他人”对话。“纵”“横”两轴的互动,决定着它的沧桑感和超越感。而一些“前沿地带”、“荒野地带”、“交叉地带”和“中介地带”的裸露,为创作与研究提出了众多新课题,也检验着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透视力和创造力。
对于“当代性”的把握,将有助于增强文学研究在对象、性质、方法上的稳定性和批评实践上的蓬勃生机。这一切自然应建立在科学剖析的基础上。重视“当代性”的省思,使我们有可能找到自己的逻辑起点,找准对象“割肉”,而对当代文学批评界较为盛行的郢书燕说、率尔操瓢、“捡到篮里就是菜”乃至“三流作品、一级评论”等等非良性现象,在学术上作有效的规避。
从“当代性”出发,我们的理论思考就可以展开对当代文学一些基本命题的讨论。缤纷的中国当代文学世界,若作简约的梳理,大致有如下兼俱“整体”与“特殊”的问题进入我们的视野。
古与今。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贯穿始终。要么维护太陈旧、太僵硬的“古”,要么追逐太时尚、太潇洒的“今”,两种弊端都无法处理如古与今的关系。某些先锋文学自命为“传统的叛徒”,事实上我们都是传统的子孙。传统与当代无法完全割裂。“古”与“今”是对立统一。“今”中有生命的东西总和“古”中的精华相关联。在创作与研究中,优秀文化传统将赋予我们精神价值和品格,而当代文化精神又成为文学不断更新的内在驱动力量。有相当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需要开发并照亮我们的文学苦旅,同样,也有更多富于创发性、焕发着当代人精神生命内在光辉的成果,汇入到传统的长河里来。
南与北。诚如现代文学史家杨义所言:“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古时以南北之分较为明显:北方接受胡人文化,南方则接受蛮人文化;北方是黄土地的文化,南方是绿水滨的文化;北方文化比较粗犷、开阔,南方文化比较温柔,多情思。这种文学性格上的差别,显然不能绝对以地区分,但是南北文化的差异的确是一个明显的现象。”(11)迨至近世和当今,“南与北”又发生了变异与廓大,如:上海——海派和北京——京派的分野;东南——沿海文化和西北——内陆农耕文化的差异;西南——多民族文化和东北——旷野文化的殊相,等等。这当然并非严格的判别(如蒙古族、维吾尔族即居“北”,京派即有不少“南”迁者)而是稚憨的把握。“南与北”在现当代文学中已经不单单是区域性问题,其深处潜隐着文化血缘和文化性格,并涉及生态环境、文化交流、传播演变、文学步履诸具体问题,研究它,乃是“一体多元”的当代文学的重要侧面。
城与乡。从“青纱帐”到“大都会”,象征着当代文学中的“城与乡”。“乡土文学”维系传统文化,“都会文学”带有先锋倾向。文学中的“城与乡”往往剪不断理还乱,且“城”中有“乡”,“乡”中有“城”。从“当代性”角度看,有些名为“乡土文学”,实则走马观花后对乡土抛洒一些留恋或同情,作家却轻松地挣脱了乡土对精神构成的重负;有些名为“都市文学”,也不过是用蒙昧的水准去玩赏蒙昧,以“阿Q穿迷你裙”的方式去追求“土”、“俗”、“浅”而排拒高品位文化,其潜意识与小农格调并无二致。“城与乡”的交响本可以为文学推演出精彩的活剧,值得注意的是有人逃避有人退隐。这也需要从继续深究中寻找坦途。
此岸与彼岸。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长久的隔膜与阻绝,最受创的是文化、文学和学术。都称之谓中国当代文学,但实际的研究和运作却是破碎和割裂的,这就难以展现“文学中国”之全景。淡化对立情绪,凝聚时空和才能,这种从“和”出发谋求文学整合的努力,将使我们发现造成遗憾的一切,同时也辩证地造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特殊且动人的一幕:文学因时空的间离而在不同地域中生长并呈示着不同的命运、情致和性格。这种同一民族文化传统延伸过程中的互异性,恰好提供了互补的可能性。一方面,通过对于阻隔的省思,此岸(或彼岸)因主客观局限造成的某些文学匮缺,有可能在彼岸(或此岸)有浑重的存留,而歧异所拥有的功用,正在于消弭各自的缺憾;另一方面,以整体性视野“隔岸观火”,拉开审视时空双重距离,倒易于客观、冷静,因而也可能作出更为全面的判断,有利于对历史、文化和文学事实进行梳理与汇通,比较公允地总结出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文学之荣衰、消长、优劣、得失以及不同的步态。从类文化的观念上看,在“文学中国”的视野内对两岸文学加以整合,将呈现我们企盼的完整和丰富,也会使某些沉重的历史话题和敏感的文学话题得以纳入科学研究的视域。这是在多重空间中体现民族自信力和文学感召力的积极运思。
灵与肉。文学长廓中的人物都是血肉之躯。问题在于见人、见面更要见心。从“剧情主线”的强调到“人生的追问”到“灵魂的拷打”,后者的匮乏,说明了文学传统中那种重“形”、重“行为”而对“神”则“敬而远之”的儒家“诗教说”的影响。这一片面性,导致了对真实的血肉人生的隔膜和对解剖一个个活的生命的乏力,也总使人感到缺乏那种心学的意蕴和风采。灵与肉如同一个铜板的两面,重视书写与研究“魂”,方能为当代文学开启一扇通向更高境界的窗口。
东与西。“文化错位”现象反映了“中西”之争的欹斜。文学中“东方(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在当代文坛上亦相当突出。海峡两岸文学曾经有过西方化(欧美化)或俄国化的理想,其经验、其教训,仍需让后来者继续领悟。中西文学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别,主要是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别。如果对这种类型差别不做深入研究或有意忽略,对西方文化——文学亦步亦趋,以西方人为“主体”而反以自己为“他者”,显然缺乏应有的理智。我也不大理解所谓“新时期大陆文学十年走过了西方百年路程”(12)的说法,因为这把发展程度的差别同文化类型的差别混淆了,而且实际上也没有那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文学跃进。看来问题的研究还必须重新回到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本身”的探索上来,而不应把“西方”作为不可动摇的定向。中华民族的当代文学目前面临“欧洲中心论”解体的时机,就有必要在世界文化的语境中,以“我”为主,以进取的新文化精神,对自己的文学进行科学的、系统的诠释(包括重读),也重新研究西方文学与文论,进而在文化比较中总结“东与西”历史地积累的既有差别又可汇通的经验,以便从多种角度检视人类在当代文学方面所遇到的相关性或相似性问题。
以上的论列不免以偏盖全,但私心以为都是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中难以规避的问题。作为一门学科,当代文学有待于走向成熟。它需要有自己独特的对象、严密的范畴;它需要对本学科的特点、规律、共性与个性有充实的论证和深入的分析;它需要有独立的逻辑体系和概念系列;它需要有自己的学术视野、认知方式和研究策略,而不是对“旧模式”的修补或“他模式”的挪用;它需要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和学科自身的特色,并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取稳定性与鲜活性之间的协调。
这门学科的建设,尤其要求其研究者从激情型转向学院型。为此,有必要倡导中国自己的“新学院批评”或可称“学者化批评”。这种批评固然以学者、专家、教授为中坚,但而非将研究局限于深宅大院去搞脱离现实的关门提高。事实上,真正的“新学院批评”,将以心态的自主性、批评的学理性、阐释的公允性、学术的规范性和思维的创造性为追求目标。具体地说,这种批评应具有的品格和特征是:(1)决非掉书袋,也不用凝固的结论或死板的知识去先验地框缚活跃的艺术生命,相反,总是力求在相当的文化背景下,对于对象和问题作庄重的历史与美学的透视;(2)从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比较和碰撞中,从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互补中,发现与论证重要的知识命题;(3)用人类能看得见的地平线来研究与把握文学和学术发展的脉动;(4)以“立”为示意中心,立足于探索,着眼于“建设”;(5)思想家的冷静、艺术家的悟性和解剖学家的精心相结合,用清爽的智慧滤选阅读行为;(6)批评者与对象之间保持平等的对话和适当的距离;(7)潜心进行文化资料和知识成果的梳理,并不断“重读”,逐步形成在相关领域中可资运作的、带有一定规范性的理论模型;(8)做道德文章,同时对不同观点者怀有学术雅量;(9)不尚空谈与装扮,但求实在与厚重,行文走笔,以“辉煌的枯燥”和“壮阔的简洁”为优雅的极致。我们自然不可能要求每一篇论著、每一部专书都合辙于上举数端,但作为总体的批评风貌,若能达至如此境界,毕竟象征着当代文学研究的繁胜之域。
扪叩之见,谨献刍荛。限于篇幅,也只是提出一些问题而未及充分展开。愿同行的开拓者们操持这一片芳草地,坚持这一门学科建设艰难而壮丽的进程。
1995年5月12日晨修讫,北京,
注释:
① 参见《三国演义》卷首词,它既体现了历史的沧桑感,也客观且洒脱地呈示对世态炎凉的多重思考。此点对当代文学研究者不无启迪。
② 参见《旷野上的废墟》(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张汝伦等四人对话《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1994年第3期《读书》),王蒙《人文精神偶感》(1994年第5期《东方》),杜书瀛、钱竞《颓落与拯救——论当代中国文学的道德风貌与文学家的人格建设》(1994年第5期《文学评论》)。
③ 参见许明:《新理性: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1995年1月7日《作家报》总3007期。
④ 参见蒋述卓:《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当代人》1995年第4期。
⑤ 参见夏林:《北大“批评家周末”:呼唤理想主义》,1995年5月7日《北京青年报》。
⑥(11) 参见邹桂苑:《文学要向全人类的思潮与智慧开放——李瑞腾专访杨义》,台北《文讯》1995年第3-4期。
⑦ 就当代文化而言,有必要将“企业文化”与“文化企业”加以区别。前者系企业自身形象创造中的有机部分,为文明建设之必须;后者往往变成伪装体面的骗子的乐园,如“包工头充当制作人”、“批发商升任出版家”等等。
⑧ 参见於可训:《九十年代:对当代文学史的挑战》,《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
⑨ 〔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中译本上卷第25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1月版。
⑩ 吴宓在日记中载陈寅恪早年有“中国哲学不行,史学高超”之说。参见《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版。
(12) 此说并非哪位论者的论断,而是时下文坛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
